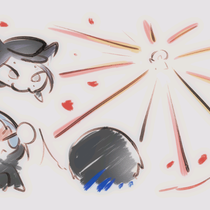景朝十六年,江南某处偏僻小屋,沈浸月一如往常那般尝试着自己并不那么擅长的针线活,口中哼着记忆中模糊的乡间小曲,就这么靠着微弱的月华绣着。
手中的绣花圈上依稀可见两株歪扭小草,上面还带着几分红,那些不是锦上添花,只是她单纯的又刺到手了。
沈浸月抿了抿见红的食指,双眉微蹙“怎么又这样,难道妾身真不是女工的料? ”
反正都受伤了,沈浸月也不再继续,她放下针线和绣花圈蹦跶上木板床,乔了乔身位后掐了个印,蓬松的淡紫狐尾就这么伸了出来垫在身下。
山间的风透过没钉牢的木板窗徐徐的吹来,沈浸月闭上眼享受着此刻的恬静,平淡无奇的一天似乎就要就此结尾,直到一阵急促的拍门声将其惊醒。
沈浸月从床上坐起,试着向破木窗处探了探头,但一无所获,于是她走向木桌抄起绣花针,谨慎的朝门口探去。
沈浸月平时疏于社交,平常的生活也只在家中刺绣,或者去后院的小溪流处喂鱼,她并没有交心到能在丑时来这小破屋拜访的朋友,这算是她的理想之一。
“怎么回事,土匪…还是官兵?难道说…”
一想到门外有可能便是那群以屠妖为天性的应山子弟,她便赶忙收起了尾巴,并想办法吞了吞房里的浊气。
鼓着脸颊应门,想像中的情景皆未出现,对方虽说也身着应山道袍,却无应山弟子那般的道貌岸然,反倒是透着一股妖异,沈浸月十分断定他绝不是人类。
于此同时,对面的道袍男子开口“在下渺茫子,今受应山弟子追捕,见此处弥漫淡薄浊气,特来寻求同族庇护。 ”
见着对面同是妖族,沈浸月心中一喜,连忙将其招待进屋,并翻了翻屋内有无吃食足以待客,但翻来覆去也只找到几串肉干罢了,她尴尬的把肉干放到陶盘上试图让其看起来上档次些,却显得滑稽。
望着对面打量的眼神,沈浸月结巴的开口“妾…妾身家底轻薄,请客官不要嫌弃…”
渺茫子见此也没数落她,只是望向木桌上的针线并询问“你喜欢刺绣吗?”
“…对…但妾身还在学…”
也不等沈浸月说完,渺茫子便打断道“对了,我还没问小姐的名姓呢,请问贵姓? ”
见话语被打断,沈浸月变得更加瑟缩了,过了许久才憋出几个字“沈…沈浸月…”
“妳…说话都这样结巴的吗?”
“没有…只是久无社交…现在跟人说话会紧张。”
渺茫子见沈浸月这副模样,便走向木桌拿起绣花圈把玩着,并提议道“既然你不擅长说话,那换我说故事给你听吧。 ”
渺茫子说起了令羽的故事,从和公子间的缠绵悱恻,到成了被抛弃的薔薇,后又变为欺瞒主人的恶仆,直到在贫民窟受蛇妖浊气浸染,沈浸月深受感动,但脑中泛出了疑问“这些故事…和客官说要找妾身帮衬……有什么关系?”
“不…不是说客官的过去不值一提的意思…只是知道客官的需求,妾身才好帮忙…“
感觉话语越描越黑,沈浸月的语气渐弱,她变出尾巴,试图擦拭刚才因故事而泛出的泪。
渺茫子也不恼,只是将绣花圈放下自顾自数道“再等一下,3…2…1…,就是现在! ”
渺茫子瞬间化为蛇形,冲天的浊气填满了整座破屋,然后其冲破屋顶逃遁而去,领走前还不忘留下一句“同族间互相帮衬不寒碜,今日祸水东引之恩,来日涌泉以报。 ”
沈浸月完全没反应过来,直到三五名应山弟子将木门毁去,并因渺茫子的妖毒而昏死之时,她才意识到了些什么“妾身的房子啊!!”
妖狐撕心裂肺的嚎叫响彻了整个山头,而那座破屋再也没有住过人。


景朝十六年,京城。
“二位仙长真是好眼光,这净瓶本是前朝贡品,古得不能再古了。”刘金展示着锦盒中的冰纹玉瓶,鹤避烟煞有其事地拿着放大镜观察着上面的冰裂纹,谢安则扫视着人来人往的京城,假装不经意问道:“掌柜的,今日清明,本该是踏青的好时候,这些人为何扎堆往贫民窟去啊?”
刘掌柜把瓶子装好,又用时兴的花布包住,递给鹤避烟。“这不是清明了么,京城各处道观禅院由罗家和袁家牵头,组建了个‘普施法会’,超度无主孤魂。”他来到店门口,往东北方指了指。“他们还在清华里举办为期三日的施斋活动,罗家供养的高道还要给那些穷人们讲经说法哩。”
谢安和鹤避烟就是为了这道士而来。
一个月前,向来独来独往的林檎师姐竟修书一封寄往门中,声称她在蜀中追踪到一个身穿应山道服的江湖术士,疑似被妖物附身。被她重伤了以后逃亡京城方向;如今自己分身乏术,希望京城地界的同门前去除妖。
“此人自甘堕落,与妖物为伍,借我门威兴风作浪,恳请师门多派些人手,驱除外道。”信件里除了斩钉截铁的追杀令,还有一张草草绘制的人物小像。
谢安把玩看着小像,怀里罗盘的指针因为妖气的波动飞速盘旋着。“看样子这次的家伙不好对付啊,浊气强烈到你的罗盘都要着火了。”鹤避烟将花瓶收到储物袋里,双手环抱盯着罗盘。“林檎师姐也真是的,信里一会说妖物附身,一会说邪魔外道,搞得我们这次连对方是人是妖都不清楚。”想到那女人冷若寒霜的双眸,他不禁打了个寒颤。
“不仅仅是因为周围的浊气,是这个。”谢安拨开头发,露出左耳上鲜红的流苏。“这是我前几日在罗家查访时收到的小玩意儿,上面的浊气已经被引入罗盘了,和我们的目标一致。”
小姑娘打翻了食盒,在走廊徒手捡碗碟碎片的时候他正巧路过,由他作保对方才没有被管家打板子。他早已看出小姑娘送饭的东府透出几缕妖气,便开玩笑收下了这吊坠当做报酬,以备调查之用。“谢谢你,我叫云蝶。”对方因常年务工而伤痕累累的双手,让人想到魃村那些因灾岁而逃亡至此的难民,让谢安心中暗思诸多。
“她告诉我,罗家前任家主去年因剿灭阉党一事立功升职,却在接旨的当晚暴毙身亡。大少爷罗瑛匆忙之下接替家主之位,却在年末生了场怪病,从胯部那物溃烂到全身,比杨梅疮还可怖。”谢安和鹤避烟走过几个巷口,进了一家药铺,等伙计抓药途中闲聊道:“罗家在一筹莫展之际,便来了位身穿应山道服的道士,说府上有妖物作祟,他可以拔除。”
据说,那道士从罗瑛的房中揪出了一只甲壳上有梅花斑纹的绿头乌龟,又用药丸保住了他的命;但兴许是伤了元气,罗瑛躺在床上久不见好。道士承诺会留在罗家帮忙调理他体内剩余的妖毒,他们便将其供养在东府旧宅,而云蝶就是罗家派遣给那道士驱使的仆从之一。
两人正聊着,便走到了清华里。
这贫民窟巷口早已被佣人们打扫过一番,立着座高台,台下数座琉璃灯上油烛成行,仆人们正在高台对面的狮子香炉上点着道香。
“不论是人是妖,咱们人手足够,定不会让他逃出生天。”鹤避烟抛着手里的铜钱,倚在墙边,看着罗家搬来的稀世器物啧啧不已。“罗家和袁家不愧是豪门世家,一下子展出这么多奇珍异宝,仅仅是为了一个来路不明的道士?”
“这些贵人都是人精,谁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谢安盯着不远处拿着锅铲正在炒油菜的两位女冠,缓缓说道。
不苦与九方屿离京城较近,自然比另外两位来的更早。
几顶布账围成的饭堂上杂摆着几样做好的菜蔬茶水,其他米麦豆粉、油盐酱醋,及桌凳碗碟也早预先运到。众多僧尼比丘,乾坤道士自发地劈柴煮饭,洗菜熬油;无数衣衫褴褛的流民乞丐,游方僧道坐在巷子口,巴巴等着。
富家一日斋饭的规格,堪充贫户用费终年,此情此景实为讽刺。
“你说,我是不是该换条鞭子了。”不苦一边摆着碗碟,一边和身边正在受烟熏火燎的九方屿说道。从林檎的信中得知,目标受伤后遗留下几枚鳞片,成色极好,雪白如瓷,在阳光下折射出淡淡的紫色光晕。只是很快就化作浊气消散了。“真可惜,妖物死去后只能灰飞烟灭,与我无用,你倒是可以一饱眼福了。”她冲着一脸淡漠的师姐小声笑道。
“是么。”九方屿擦了擦汗,朝她招了招手,示意来帮忙熄炉火。“林檎师姐语焉不详,说不定对方是人类呢。”她拿起水碗,大口喝起来。“如果是妖怪附身,我就把他连人带妖一块绑回宗门,好好解剖一番。”
不苦听着对方一如既往的惊世骇人之语,留下一滴冷汗。这人心里指定盼望着对方是妖怪附体,好将其驱逐出来仔细研究。
两人正说着,罗家与袁家带了一班家乐,簇拥着几顶轿子浩浩荡荡前来。她们赶紧降低自己的存在感,混在一众帮厨的僧道中。几个管家模样的男女到帐篷前后点检了一回,就回到队中,对着为首的轿子说了些什么。随后,一名头竖天仙髻的贵妇人从轿中走出,在佣人的搀扶下走到棚子前。
“各位道长,上师。辛苦了。法会结束后去找王妈妈要赏钱吧。”袁希遥用手捏着帕子捂住鼻子,来回踱步说道。不苦与九方屿看着夫人身上笼罩的浊气,暗中对了下眼神。
罗家上下被浊气浸染,即便目标不是作祟的妖物,那也一定是与罗家有不共戴天之仇。
清华里附近的男男女女聚在周围,好似坠入蜜罐的蜂群;凡人身上的臭气与妖物的浊气搅合,让在场的几位剑仙不自觉拧起眉头。施斋活动正式开始后,又有一众闲汉儿童,虽不念佛修道,却也来趁闹观看。吃饭的人越积越多,以致人山人海。
“真狡猾。”不苦暗暗想到。“这妖道是觉得人在闹市,我们不方便动手么?”她从袖中弹出蛇鞭,紧紧盯着那些从轿子中走出的达官显贵们,仿佛要在他们脸上瞪出无数窟窿。
法会即将开始,那些高高在上的贵人们下轿来到高台近处;或持念珠,或把木鱼,摆出敬僧礼佛,尊仙重道的样子。他们身娇肉贵,又自视清高,坐在铺着软垫的交椅上;而旁边的小厮丫鬟们则没这样的待遇,只都双手合十,跪坐一旁。
随着人群的起伏,几位剑仙也合掌而立,在巷子两端暗中观察着。
少顷,只听得高台处三遍钟鸣,几个高僧大德簇拥着一位面白无须的道人摇摆出来。道人身着与应山派极为相似的法袍,在三清像前拈香膜拜;又拿起水盂以杨枝抛洒甘露,步罡踏斗,存思太乙天尊。后随着列坐上香,礼请讲师等步骤结束,那道人便手持麈尾登上高台,演说道经。
九方屿稍微睁开双眼,扫了一圈人头。看着已经行动的两位同门,不紧不慢的说道:“功德做得差不多了,我们走吧。”她攥着问风,和不苦兵分两路,往人群遁去。
蜀中被称作“天府之国”,因天气炎热潮湿,是蛇虫鼠蚁的好去处。渺茫子本来也是这么想的,如果他没见到那个疯女人的话。
“这位大姐,你追了我一夜了,还不知足啊。”渺茫子拢着双袖,衣袂飘飘站在竹林之上;竹枝因为压力弯曲少许,在林檎墨绿色的斗篷上留下片片残叶。“你是什么人?为何穿着这身衣服?”女人直勾勾盯着对方,仿佛在确认什么。“我入门十几载,从未见过你这张面孔。”林檎将长柄弯刀就地一驻,周身剑气凛冽,好一个女关公。
渺茫子左手掐诀,装出一派仙风道骨的模样,胡阐道:“贫道是昆仑山散仙,修‘如意神咒’,心得六通,独行三界。你应山以天下道统自称,当然不了解我们这些方外术士。”他软下身子骨,盘曲着倚在倾斜的竹枝上,俯身看着林檎。“我虽说不上师出有名,但也绝不是自怨自艾之人。在我眼里,贵派也不怎么样,只有这身行头不错。”林檎嗅到了一股不自然的味道,不自觉拧起了眉头。
“荒谬,你浊气冲天,分明是与妖怪为伍的邪魔外道。还敢自称仙人?”
林檎一点面子也不给,摆开斗篷,横刀劈来;渺茫子扭身拉开距离,抽出双剑格挡。二人你来我往,兵刃相交发出振金之声,剑气相撞间卷起无数尘土沙石,断枝残叶;山谷中乱石纷飞,剑光与尘烟齐出,不时引来爆破之声。林檎出手刚猛霸道,全然不似闺阁女子;渺茫子招式阴柔鬼魅,亦无丝毫莽夫之态。
两人的身影也不断转移,紧紧的咬在一起。渺茫子因甚少使剑,逐渐被逼近崖壁,前后无路;林檎看准时机将长刀掷出,将对方穿肩而过钉在石壁上;又从腰间扯出手斧,朝渺茫子抡去。
渺茫子忍痛一扯,将肩膀从刀刃中拔出,旋身将左手宝剑扔出。那剑在半空中转了几圈,以不可思议的角度刺来,和林檎的手斧撞在一处;林檎感到虎口一麻,面前顿时火花四溅,闪了她的眼。
趁此机会,渺茫子手中结印,周围几棵大树顿时拔地而起,朝林檎轰去。电光火石间,挥斧的动作还没落下,剑仙就被树干挤在中间,藤蔓与枝丫如铁锁连环般将她紧紧箍住。
“应山派名不虚传嘛。让我那么费力。”渺茫子捂住伤口,浊气不自觉的蔓延出来。“你究竟是什么东西?”看着妖道肩膀伤口处可疑的爬行生物特征,林檎一边暗中以气御剑,一边质问道。
渺茫子知道如今不是撕破脸皮的时候,便说道:“贫道所修小技,是以妖物炼药,增长寿元,但也有些瑕疵就是了。”他摘掉几枚妨碍伤口融合的鳞片,走到林檎面前。“我这班法术千变万化,无往不利,和贵派比也是不遑多让呢。”
突然,他汗毛倒数,腾空而起。
一把宽刃剑突然从他背后射来,差点把他削作两段。“你还有力气偷袭?不知死活。”他知道这是应山派拿手的御剑手段,便张口一喷。一道腥臭难闻的毒水溅在剑上,那神兵顿时灵气全无,如破铜烂铁般坠到地上。
渺茫子抬手成掌,正要往林檎脑门轰去,却在半空中止住。“路过的么?”正在逼近的剑仙气息令他不敢贸然打赌,便顾不得体面,一条蛇信从嘴中探出,点在林檎额头。草草隐去了自己在对方脑海里的长相后,便遁作妖光而去。
“上仙,您请用晚膳。”云蝶敲了敲门,见无人应声,也不敢推门进去,只能站在门外。突然,一点灯光从门缝中亮出,渺茫子略有些疲惫的声音响起。“你拿下去罢,我要早些歇息。明日和夫人商量普施法会的事。”小姑娘照做后,一步三回头地离去,落了小院的锁。
渺茫子盘腿而坐,双手结印翻飞,好不容易才压下躁动的浊气与杀意。“该死的应山派,可恨,可恼。”他吐出一口血气,仰躺在软榻上。看着被自己用红线吊在床梁上的乌龟,眼波流转道:“罗少爷,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舒服的。应山派的人就算追到这里来,也救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