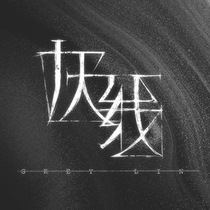-1-
小仙儿又在我的豆花铺门口摆摊算卦了。
小仙儿的名字叫要江绪,但我们叫她小仙儿,这是因为她算卦极准,两年前我娘走丢时就是她算到了地儿,她崴了脚不小心跌在沟里,再晚去一会儿指不定就冻僵了。我每回这么叫她,她都要摆摆手,说着“我可也是普通人呢”之类的,顺便买碗豆花去吃。我们这儿南来北往的客人多,咸口甜口都有做,她就也咸的甜的都吃。
她每次来我都是很高兴的,但这次我却笑不出来。等她不忙了,我给她端豆花,挤着她的凳子坐:“小仙儿,我娘不要我了。”
“什么?”她愣了一下,也不笑了,“怎么回事呀……?我上次来,她还笑着和我讲你长高了呢。”
“就是很突然。姥姥又乱走到郊外去,差点没找回来;我那两天又刚好着了风寒,躺在床上起不来。等到我迷迷糊糊醒了,就看见娘坐在我床边掉眼泪,说她该走了。我想着是娘这两天又要看店又要找人又要看顾我太累,没想到她真的走了……”
我很难过,但又感觉能理解她,毕竟姥姥不是我的亲姥姥,我也不是娘的亲女儿。我很小时姥姥在桥底下捡到了我,后来我又拿着棍子打跑流氓捡回了娘,我们仨拼拼凑凑成了一家。这两年姥姥越来越糊涂了,我身体不知怎的也越来越差,我想娘正年轻,照顾我们这两个病秧子也该累够了。但我还是很难过。
“哎……她也没给你们留句话什么的呀?”小仙儿安慰了我几句,把一勺豆花塞到我嘴里——有点做甜了,我不太好意思——接着问,“你想找她吗,要么我给你起一卦?”
她什么也没说,我确实有点不甘心。“我要。”我说,“我就想知道她到底为什么不要我了,再说她一个人在外面,多不安全。”
她点点头,摆出她那些我看不懂的家伙什儿,叮铃哐啷操作起来。我以为只是随便看看就行,没想到她皱起眉来,好像越算越多了。我忍不住想这段时间的营收够不够付钱,要是不够的话,许她以后都免费吃豆花行不行……在我打算扯扯她的袖子好让她停一停、免得真的付不起时她自己停下了,很认真地拉着我的手:
“六妹儿,你娘要是做了坏事,你怨她吗?”
“我不觉得她这么走了算做坏事吧,我们本来就是那个,怎么说,萍水相逢……不对不对,我娘不是什么逃犯吧?”
“……我看出你娘是因有愧于你们才走的,唔,”她每说一句话都要思量半天,“你想想,是不是两年前找回她以后,你和姥姥的身体才……”
这是什么意思!?我几乎要跟她急眼了,但我知道小仙儿是不会骗我的,也不会空口诋毁我娘,所以我又泄了气;“是娘的命克我们吗?”
“你上哪去听的这些克不克的。”她拿玉尺轻轻敲我的头。是想让我心情好点吧,但她自己还蹙着眉呢。她又望了一眼桌上摆的物什:“我能说的也就这些啦,算我道行浅,你娘不愿让咱们找到她,我也说不出她在哪儿。只不过她走正是为了你们好,她也放不下你们,要过两三月,还打算悄悄回来看你们呢。”
我总觉得她像哄小孩似的哄我,但小仙儿又是从来不说假话的。她怎么会真的道行浅啊?不告诉我的那些,大概是天机不可泄露什么的了,我便也只能告诉我自己我娘大概是什么朝廷重犯,为了不引来官兵连累我们,踏上逃亡之路了。
她又拿出个小药葫芦给我,叫我和姥姥先用着调理身子,说是能调气血排寒浊,她回去找人给我们开剂药方来。小仙儿的摊很快收起来了,我很为麻烦她过意不去,她说着没算出来什么,收我的钱还不过几碗豆花钱,却要为我们这么忙活。我一定要她带些豆花路上吃,不准她推拒,临道别了又觉得还不够,又鸡零狗碎地打包了一些,跑到城门口时,她已经走出去了。
“小仙儿,小仙儿!”我拼命招着手喊她,“你再带点吃的走哇!”
“我很快就再回来看你们!到时候再吃吧!”她冲我挥手笑,“真的会很快哦!”
-2-
等我爬上半山腰,已经差不多快累死了。老师指点我来拜山门时,也没说还有这么高的山路要走啊!我一跤跌在地上头晕眼花,感觉已经走马灯了。好想再吃一口阿嬷做的糖葫芦啊,一口,就一口……
我对着眼前的糖葫芦要咬下去时,一只手揪着我的领子把我提了起来,一柄玉尺伸到面前,啪叽!敲碎了那两个令人垂涎欲滴的山楂球。定睛一看,那哪是什么糖葫芦,妈呀,是妖物啊!两个已经变作泥状的虫骸躺在那儿,了无生机的豆豆眼望着我。
提溜我的这位想必就是我未来的师姐之一了。她笑眯眯的,笑得我一抖。
“沾了妖邪之气的话,进门会触发声音很大的警报哦。”她这么说着,一振腕甩掉了玉尺上的残留,在我身上掸了一番,好像这样就能掸掉那妖邪之气似的,“再过两个时辰,天亮就是入门仪式了,你怎么还在这儿?”
我看了一眼远在云霄外的层峦叠嶂,几乎要落泪了:“师姐,未来的师姐,你行行好,御剑捎我上去吧,我没带够吃的,也没走过这么远的路,真的要死了……”
我觉得她要替门派婉拒我了,或者嘲弄我一番。她又笑了笑,好整以暇地坐下来,打开了手里的包裹……一个食盒?里面散发出热腾腾的香气。我的口水差不多要掉下来了。
“不急,先吃早饭吧,吃完我陪你走上去。你吃甜豆花呢,还是咸豆花?”
……
我算是按时赶上了入门仪式,又排在最后几个才鼓起勇气踏入阵法内。这阵里是一道庞大的迷宫,我家那大宅院的回廊过道循环往复找不到尽头,时不时有相熟的人给我指路,间或变作一只漂亮蝴蝶在我眼前蹁跹,好容易走过去,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想起那位师姐说的,断不了世俗的亲缘念想就会被绊住脚步,是这么字面意义上的绊住脚步吗!我干脆不干了,往地上一坐,对着那变幻飘忽的走廊扯起嗓门:“我不管,爬上来就够累了,至少别让我一直走路吧!”
当然没有用。我闭上眼,任凭越来越多想引我走进死胡同的蝴蝶飞过来,停在我的身上、鼻子眼睛上。说实话,那一瞬间我想,干脆就这么睡觉得了,一觉醒来就被踢出来,然后我就可以灰溜溜下山告诉爹爹和老师说我做不到。我躺了不知道多久,感到那群蝴蝶都飞走了,接着一柄温润而微凉的东西触到我的额头……啪啪敲打了两下。嗷。
“又见面啦。”她说,“地板这么凉,睡不着的吧。”
有一瞬间我毫不怀疑她会像变出豆花那样变出一床被褥,但是她没有,所以我坐起来,当然还是很不服气:
“师姐我不想干了。”
“那刚刚爬的山不白爬啦?”
“……”
“你若真心要放弃,这幻境早把你弹出去了。”
好吧,虽然承认这个让人感觉很憋屈……我确实只是在和它赌气,如果就这样结束,想必今后我会无数次在半夜一个鲤鱼打挺醒来,质问当年的自己为什么不争点气。
“这走廊也是有尽头的,只是你被迷花了眼呢。”她点点远处那片延伸出去的混沌,“好好看清自己想去哪儿吧。”
我来应山不是出于别的同门那样拯救苍生或除妖降魔的大义……仅仅觉得这宅子太憋屈,想走出去而已。
我站起来,深吸一口气,感到能用我的念想压住漂浮的地砖、把它们压实、铺成道路。那些蝴蝶也好人影儿也好就此消失了。我往前迈步……这时整个幻境剧烈摇晃起来。
怎么回事!?我说了我只是赌气,没真想罢工啊!别把我扔出去!就在这时,师姐闪身到面前,挥开玉尺,铮!似乎弹开了什么,随即她的身影一晃,也消失了。
我愣了愣神……整理了一瞬思绪,朝着走廊尽头奔跑起来。
-3-
命宫境中的苦寒于我已十分熟悉,只要再咬紧牙关、迈开步子,走出这片风雪就好。然而,这回我却怎么也找不到方向……已能听到霜结在我眉上的声音。
豆花铺的六妹身上不是一般的病症,是妖毒,她的母亲怕是早已换了人了。也怪我,为何当年没能早些看出来,这件事又该如何对她讲呢?我对妖物没有多余的慈悲心,但若当着人的面,把她的哪怕只是一个空壳的至亲之人处理了,于她而言是不是太残酷了?唉,到时还要多留心些,不要让她看到了。
沉下心,再次运气,终于找到了那一股热气指引着我走出去的感觉。睁眼看到的却不是熟悉的画卷,而是一碗热腾腾的豆花飘在空中,白嫩的豆腐张开嘴,咕噜噜地说话:这件事又该如何对她讲呢……对她讲呢……讲呢……哎哎,是我太分心了。
那便暂时先不去想了。清空心里繁杂的念头,便转身踏入预备弟子的境中,指点他们一二倒是顺手的事,我只是很喜欢看他们挣破心魔的一瞬间——嗯,算不上什么怪癖吧。本来也是极顺利的,但在抽身出去之前,忽然能感到一股力量向阵中袭来。来不及思考我便挡了过去,随即被震出阵外,一阵天旋地转过后,已然身处现实了。
……身处现实,这个事实我用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因为眼前的景象实在太令人不敢相信。掌门的对面,那团黑气缠裹的巨影是妖……却有着人形。方才我认为太过残酷的场景正在切实地上演,今后也要变成困扰我们的一个普遍的难题了。
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反应,第一时间只想到,那碗热腾腾的豆花,以后还能吃到么?


你知道AI幻觉吗?
它是指语言模型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自信满满地编造事实、输出错误答案的行为。这一现象的成因根植于此类AI的基本原理中:它以完成用户的指令为第一要务,却又没有足够庞大的训练数据支撑;它不理解自己在说什么,输出思考轨迹的功能也不过是一种安慰剂,它只是选择了一个“好像最合理”的答案。
喂,不觉得这很过分吗?用户在被这种幻觉耍着玩的同时,AI自己也变成了为尽力弥补设计上的缺陷而疯癫的可怜虫。尽管只要经历过AI幻觉的人都会立刻因此明白(至少这一阶段的)AI没有自我意识,只是概率和算法下的墙头草,但相比于造成这一切却正在毫无负担地数钱的幕后开发者你/我们,这虽然没有意识却依旧要背锅的玩意儿与被愚弄的用户还是有点可怜的吧?
不过我并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哈哈真不好意思讲了那么长一串。我仅出于无聊想向各位证明一个暴论:
乐园埃里西翁是一个巨大的AI幻觉。
天原在备忘录里打下这些字就关闭了手环屏幕。事实上,刚刚写了两段,她便已经对这个看似夸张的点子感到厌倦了。
倒不是真的认为埃里西翁的一切是一场幻梦,胡言乱语只是她排解自己过于奔逸的思维的方法之一。她的大脑时常像接入过量电流的失控电机一样转得过快,就好像如果不允许她随时找点什么事做,无处释放的想法就会令她过敏。
昨晚大家聚在一起,为城市重建进度推进顺利开了个小小的庆祝会,饭菜不算很丰盛,因为农田的灌溉系统罢工了。好在有他们刚从无人看管的瓜田搬回的西瓜,清甜的水果洗去了每个人的疲劳。叶空塔理亚讲起农田的事时,天原正稍显脱节地坐在离大家半个座位远的地方,叼着西瓜汁的吸管,专心致志地想要把额角新冒出来的一颗痘按下去。她把它出现的原因归结为上述的“思维奔逸过敏”而非上火什么的。直到手一抖把它掐破了,大脑才终于得以处理刚刚流进耳朵的声音。
“哎?那把瓜田的灌溉系统拆过来不就行了,”她慢半拍地回话,“反正瓜都摘了,瓜秧说不定也能移过来。”
“直接拆下来吗?倒是直白的办法。”叶空思索着,“也许让我观察到实物就可以,知道关键部件的结构之后,其它部分就应不是什么难事。”
“哦!可以啊,”天原点了点自己的发环,代表运作中的指示灯闪着健康的蓝光,“明天试试投影过来你那边能不能看清。”
“非常感谢。但是,额头真的不要紧么……”
叶空露出有点无奈的苦笑,指着自己额头上对应的位置作为提醒。天原刚想说没事,一股热流就顺着眼角淌进了她的左眼。面部毛细血管真是过于丰富啊。
“我们活在一个幻梦里”并非什么新奇的论调。宇宙是阿撒托斯绵长的梦境、三维世界是高维文明的模拟程序、历史是无数循环与再演、命运是一匹早就纺织成定数的布卷、莎士比亚戏剧集是猴子也能敲出的字符组合……如果你做了丢脸的事,也会恨不得眼一闭一睁醒来发现今天还尚未开始。如果你曾是上述或上还没述到的任何一种虚无主义论的信者,你当然也大可相信埃里西翁与它们同样虚幻。
但真的要这样简单的下定论吗?当然——不行。且不说这样的精神胜利法太过无聊,这个精细设计的乐园当然一点都不虚无了。且看,我们能摸到它的形状、听到它的低语,沙漠中扑面而来的热浪也不是假的。你能摸到历史和命运吗?能真的让猴子乖乖打字吗?这就是区别。
乐园幻境埃里西翁编织得如此精巧,我们看到、尝到、目所能及都是会让我们误以为此处即是真实的细节。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幻觉”。不过,我们依旧能找出破绽,我会在下文一一介绍。
“论述中出现了逻辑错误,虽然举例中的历史、命运和猴子打字机均为概念,但宇宙和三维世界正是用户与本机所处的位置,可以被感知。”
“你什么都不懂,小Z。这样写显得很唬人懂吗。”
“这样不符合议论文的写作原则。我现在的任务是帮助用户校对文章,因此需要指出这个问题。而且,这篇文章的论点是‘埃里西翁是AI幻觉’,目前内容有离题的趋势。”
“烦哎!那我问你,你如何证明我们真的处在三维世界?”
“……”
Z型辅助机因为这个问题开始自我矛盾的长思考——让AI执行它看似可以但实际不可能做到的任务时就会发生这种事。天原为驳倒了它(即使以这样卑鄙的诡辩)小小得意了一下,接着意识到现在彻底没有人会陪她聊这个无厘头的话题了。若干分钟前她向好奇她正在写什么的与那城分享了这个暴论,对方立刻陷入了深思,接着通过思考时的嘀咕将它共享给了另外两位队友。小枝十分常识人地委婉表示这不太可能吧,砥部对此只是呵呵笑了两声便继续工作。大家正各自检查着自己感兴趣的区域,她独自蹲在已关闭的喷淋器边稍微有点无聊。
好在这份无趣没持续太久,很快被手环的振动打断了。标注着电气工程师的视频聊天窗口跳出来。
“哟!你准备好啦!”天原立即举起手充满活力地打了招呼,两指从前额划出时拨起了刘海,狸猫印花的卡通创可贴在通话窗里一闪而过,接着摄像头被抬高,拍摄了一圈周围的环境,“我刚到,看这边的设备,还是挺有规模的吧?”
叶空在那边挥了挥手以回应:“辛苦啦,看起来型号和农田这里的差不多,真是帮大忙了。那我们就开始?”
两位工程师展开了讨论。从机械结构到程序原理,这片田地立刻被拉入了一个旁若无人的“工程师立场”一般,就连日光的炎热都不那么灼人了。直到把这套系统里里外外都差不多剖析了一遍,天原直起腰来,才听到了骨头咔咔作响的声音。
“嗯——那我让小Z把视频里很难看清的地方扫下来,逻辑上的地方等回来我们自己编编就可以了……”她大大伸了个懒腰,拍了拍辅助机,“小Z?”
屏幕上依然转着“思考中”的提示。天原哎了一声,才想起那个对它来说太过困难的论题,接着变魔术般唰地展开一群扳手钳子螺丝刀:“没办法了,还是拆吧!”
我们被关在这里原本是要做什么来的?自相残杀,证明我们的才能“不需要乐园的庇护”。可原本我们不就活在没有乐园的世界里、用各自的才能谋生或改变着世界吗,是黑幕这个家伙强行把我们塞进来的。那么,答案只有一个:这里其实是一个大型演算程序,我们是安放在其中模拟各自所代表的才能的智能体。
哎哎,就这样被说不是人了是不是有点懵?没关系,来看看我的证据。
其一:为什么证明才能价值的方式是自相残杀?明明杀人的方法有很多吧,如果我单纯拿一把小刀捅死了某人,我作为机器人工程师的作用体现在哪?答案是:我们作为模拟才能的AI而非真正的人类,只能用我们知道的方式设计杀人方法,即利用我们的才能。我思考过如果自相残杀展开我的最佳获胜方法,肯定是不是亲自动刀子,而是黑入假狸猫的程序叫它们替我干活。故此,本身不是犯罪的才能,却连设计谋杀都做得到,不就证明了才能在这种极端环境都能灵活应变生存下来吗,当然很有用了。
其二:关于被我们抓到的这位黑幕的言行。他声称自己是未来人,不是吗?虽然听起来像癔症或为了脱罪的胡说八道,但正因为在这个环境下无法证明,所以也无法证伪,“无法证伪的理论为真”这种设定不是广泛地在学术界存在着嘛。因此,他很可能就是这个乐园演算程序(暂且如此称呼)的编纂者,在世界必定毁灭的未来年代,想要通过程序演算出一批最强才能,并保存在某艘诺亚方舟上。他称自己“执行了正确的历史”也是因为这个,诺亚方舟当然是正确的了。
其三:Z型辅助机的健康监测程序居然说我一切正常,明明额头上长痘很严重啊。不好意思这一段是为了满足一个论点要有三个论据的原则凑上来的。
——哈哈,总之往好里想,既然我们都活下来了,那我们(的才能)不就都能乘上方舟吗?自相残杀活下来了算什么,打破第四面墙抓住这个黑幕才是真的强哦。
“……就是这样。虽然我就是乱七八糟写来玩的,但你不觉得听起来怪有道理的嘛,而且才能拯救世界听起来超酷哎。”
“是、是吗?”张小枝努力消化着这段有理有据的暴论,好像真的思考起了合理性,“剪纸也可以用来拯救世界吗……”
“真的呀真的呀。”天原一本正经地点着头,“既会使用工具又会使用大脑的才能不是很厉害嘛,比如机器人工程师就是既会使用机器人的部分又会使用工程师的部分。”
“所以剪纸艺术家是,嗯,既会‘剪纸’又会‘艺术家’……”
“有可能其实是既擅长‘剪’又擅长‘纸’又是艺术家的意思。所以现在到了我们需要使用才能的时候了。”
投影组件把她们面前的仙人掌扫描一遍,映出一比一复制的三维模型。天原挥了挥手将它放大、拉近、调整角度,露出仙人掌顶端鲜红果实和茎干连接的部分——需要十分小心才能剪下果实而不把它碰伤。徒手采摘则难免被倒刺扎到,确实需要会使用工具的人来做。
“对吧?才能就是在这种细小的地方拯救世界的嘛。”说话时天原已经站在了仙人掌旁边,“至于这些碍着你事儿的刺就交给我好啦!我掰我掰……”
“啊!那个也剪下来就好了!不要扎到手了呀——”
你可能会说,如果这是设计好的程序,怎么会给我们打破规则的机会呢。哎哎,我们刚才证明了埃里西翁是AI的部分,现在才要说到它是幻觉的部分。
算了我直接公布答案吧:因为第二次灾变。
不难看出这次灾变对智能体的影响之大,比如虽然小Z本就蠢笨但它现在更气人了。那么自然乐园演算程序也受其影响,它错乱了,错乱地继承了人类不想被末日杀死的念头、将它内化为自相残杀游戏的失败,并为了修复这个错乱硬生生构绘了程序原本不打算模拟的内容:这片沙海就是它的幻觉之一。
于是我们奇异的发现都可以得到解释。比如为什么有没人看管的西瓜,明明食物补给应该种在市区内;比如为什么鲸鱼的骨骸会出现在沙漠里,明明鲸鱼不能在路上游泳;比如奇异的驼铃,比如现在都没有人抓到的夜影蜥……
啊,美妙的熵增,不觉得我们的乐园越来越混乱了吗,这些都是埃里西翁自身圆它的谎时不得不叠加的一个又一个谎言哟!
甚至重建设施也是它让我们参与圆谎的途径,我们都知道语言模型有多么巧言令色,它回答的依据更多是“用户希望它怎么作答”。我可以说真正重建乐园的不是这些材料而是我们“希望让它成为什么样子”“希望有什么设施”“这里有这个设施才合理吧”的想法。
晚上梦到埃里西翁忽然飞起来、飞向月环,带着才能者们将它取而代之,从此以后夜间照向地球的不再是月光而是才能之光。荒诞的梦境给了她灵感,天原从床上坐起来就唰唰写下了很多,一口气发散出来就像喝咖啡一样令人神清气爽。
“……那这里呢?外面能探索的部分就是这么多,有能用上的吗?”
砥部迪亚哥正在视频通话中向她展示那架半埋在黄沙里的小型飞机。估计要从沙中挖出它是个不算简单的体力活,他和与那城一起趁太阳升起前尚还凉爽时就赶到了那里,正评估着它有没有带回去的价值。
“嗯——好像没有用啊,机翼的提示灯倒是长得怪好看的,晚点我自己来拆好了……”天原凑得很近,几乎贴上屏幕,从砥部的视角只能看见她的半张脸,额上新换的创可贴印着三只跳舞的假狸猫,让人想起它们的毛绒身躯滑稽扭动的模样。救援员用手背擦去了脸上细密的汗珠:“也是没办法的事。还是得稍微挖开一点才好进驾驶舱里面看看。”
“辛苦你们了啊,要不要先回来吃饭?这玩意就让它再埋一会儿吧,马上中午热起来了,干体力活小心中暑……”语尾带着还没睡醒的拖长调。砥部正要结束通话,一片什么物体的反光在他的余光中晃过,他回头,与那城正在用力徒手将飞机残骸抬起,一颗岩石状的东西卡在机翼的阴影下正逐渐浮现。
“……帮、忙……”与那城从咬紧的牙关中挤出两个音节。二人合力撬动着机身,天原也立刻醒了瞌睡,抓过外套打算往他们那边赶去。通讯画面终于再次稳定下来时,她半边胳膊还卡在袖筒里,不过露出的那块“岩石”让她惊讶得停下了动作:“我去……”
与那城喘着气,炎热和体力消耗让他眼前略有模糊,他揉了揉眼,看清了这块令飞机坠毁的罪魁祸首。混杂着震惊与厌恶的复杂神情出现在青年脸上。灰白石质的剖面透出能量的光纹,在热空气的扭曲下如呼吸般闪动。
这可比什么论证他们身在海市蜃楼中有趣多了……天原一挥手关闭了通话窗,连同还未保存但已经不重要了的文章界面一起,接着撩开帐篷的门帘朝营地外跑去,她要亲自看看那东西。
他们发现了一块月球碎片。
Q:请问每一章大概多少时长呢!以及整个流程有具体时间安排吗!
A:总体企划时间大约是2个月。章节更新是2周更新一章,相对来说打卡方式也比较简单,黑白插图(精草程度)或文章600字。打卡内容需要跟场内角色有互动或者跟主线剧情相关联。
Q:请问文手在投递时除了人设卡,还需要其他补充文章/审核文章吗?填写要求是什么呢?(企划书上没有看见如果打扰到很抱歉!)
A:你好,不需要审核文章,仅审核人物设定,只要文字设定逻辑通就ok的,设定有拿捏不定的可以在elf私信企划主询问!
Q您好,请问牧羊人或羔羊是否有最低身高之类的要求?
A:你好,士兵没有身高要求,只要体能达标就可以。
Q:您好!可以投递1-8区军校毕业生的人设吗,如果可以的话军龄是从毕业起算还是从入学起算因为不太确定军衔是多少。
A:可以投递军校毕业生的人设,军衔是从毕业后入伍开始算。
Q:羔羊的异能有无具体的种类限制和强度限制?
A:你好,没有限制,只要人物设定逻辑没问题,评级开设S 级也是没问题的。(S级的六维图可以有两个5点,但是会严格审核)异能还是建议在伪科学的范畴里,尽量人话可以说明白。
Q:您好,请问强制组队吗?企划方面会组织组队活动,以让没有提前组队的玩家匹配搭档吗?
A:因为并不是强制配对企划,单人也可以游玩!不过企划活动会有自由组队的部分,届时可以报名参与。
Q:您好,请问父母可以是奇美拉研究员/在政府部门工作吗?作为家庭背景设定这样。
A:可以,但在相关机构工作需要进行严格的保密工作,就算是子女,对父母的工作内容也是一无所知,仅仅只能知道父母的工作地点而已。
Q:新年快乐!请问9~11区居民有偷渡到1~8区并不被发现是外来者的可能性吗?两地有语言区别吗?
A:新年快乐!
大陆早已普及通用语,绝大多数区域都已统一使用,仅极少数偏远地带仍保留地方性方言,大多数人日常沟通不存在障碍。
至于偷渡至1~8区:帝国管控极其严格,基本不存在成功偷渡且不被发现的可能。即便侥幸潜入,没有合法身份认证,也无法在当地正常生活、行动,很快就会暴露。
Q:请问可以设定一开始并不就读于军校,后来通过补习、考核、托关系等等方式转学进入其中吗?
A:只要合情合理,都是没问题的,毕竟灰色的裙带关系在哪里都存在,不是吗?
Q:还想请问一下,看企划书里6区和11区挨得很近,那么6区的人是否能够一定程度地把握11区的生活情况?又或者1-8区和其他区是有很严密的隔离机制,防止帝国民深入了解其他被保护民的情况呢?
A:帝国民对于被保护区民众的生活有一定程度基本的了解,虽然政府对公众宣扬的依旧是保护民优待政策部分,但帝国也并未刻意隐瞒区别对待的政策,因此也有一部分反对战争压迫的帝国民时常举行游行或者集会,希望能为被保护民争取更充分的人权。
从1-8到9-11的跨区行为需要办理入境签证,并非特别严苛,只要有合理的商业,政务,学业需求,帝国民均可办理,但被保护民要前往帝国其他区域却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