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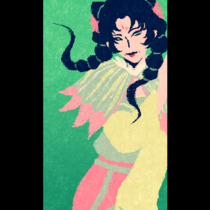
张落生口渴得紧。这山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也不知出了江南没有,只道是仍在林中。早知便在两日前那寺里先歇了脚,多停几日再走,怎至于狼狈如此。
他正兀自怨着,却见着人了:有风吹拂,一绿衣女子打绿色的枝条间一晃而过,没入条踏出来的岔路,翩然而去也。
他顾不得许多,急急追上,嗓子越发干巴;那条岔路七拐八拐,通往一片花林,满树的粉花密不透风地开着。于是张落生拨开花儿,看见一幢屋子,上面还飘着烟。
那女子忽地又出现了:“你是谁呀?”
张落生吓了一跳。女子长得俏丽,梳了两条大辫子,他只问:“姑娘,这是你家?可否许我讨口水?”
“桃奴住这。”女子倒是乖乖作答,“你是谁呀?”
“鄙人张落生。”他只好答,不由得又问,“你独自一人,怎待在这种地方?你可知近日有妖物作怪?”
桃奴看着他,眉眼一弯,便是笑了:“阿生哥哥。”
张落生再一句话都说不出。桃奴牵起他的手,朝屋内喊了一嗓。“姊姊们,快些来!”她声音脆生生的,好像没熟的山桃,又扭头盯着他直瞧,“阿生哥哥,你说的什么妖?”
“应山山门那妖物,你不知晓?”张落生反问。那事闹得人心惶惶,江南离得远,想来还安全些。他盘算趁这几日上山,多采些草药备给家中生了顽疾的老父,可惜爬了这多的石头路,有一味珠珠草总最难寻。
桃奴叹气:“父母死得早,妹妹我打小和两位姊姊为躲债藏进山里,已许多年未下过山了。这里鲜有人来,也不知外头发生何事。”
桃奴说着,从屋内转出两条倩影:老大少白了头,名作盼缘,生得比男子还高大,若不是情态摆着,张落生甚至怀疑她是男子假扮;老二更古怪,名作玄鸟,穿了套男子的衣物,身上暖腾腾,直叫人躁得慌。
三人亲亲热热将张落生迎进屋,解了他的背篓,摆上自家酿造的酒、烹制的菜,好生招待,一面围着他问山下奇闻。张落生家道中落,忙于维生,哪见过这种好事,几杯酒下肚更飘飘欲仙,讲得口若悬河,好似亲历山门一役,浑然忘了自己本只欲讨杯水喝。
但若问他最心仪哪一位,还是那最小的小妹。张落生往她那频频窥视,桃奴撞见他的眼睛,竟扭头嬉笑,面颊绯红。
发红的余晖垂来,张落生的脸便也飞红。
是夜,他被哄去房内睡下,睡的是大姊的床。梦中他回到家,老父抖了几下背篓,草药悉数滚落,唯独还是少了珠珠草,难免又要挨顿毒打。这老东西怎生了病还有力气?张落生想不明白,随后就醒了。
他挠了挠耳朵。屋内静悄悄的,三姊妹没一人在。
张落生披了外衣,绕屋走了一遭,终于在屋后的石洞里看见一张案几,案几上摆着三张碟子:
第一张碟子最大,上头放的是灵芝;
第二张碟子烧得滚烫,上头放了根鸟羽;
第三张碟子喷了香,上头放了颗山桃。
张落生也知不该动人家的东西,却怎都忍不住,伸手握住桃子;那桃子叫他想起他的桃奴妹妹。
他的桃奴妹妹在背后叫他:“阿生哥哥。”
他转过头。桃奴手上提了一篮珠珠草。
“阿生哥哥,这是予你的。”桃奴没有笑,蹙着细细的眉头,“你拿了草药,便是要走了?”
张落生急着辩解,一时忘记问她怎晓得他在找哪样物什。“我不愿走,可我非走不可。”他没接过篮子,反握住桃奴一双纤手,包裹着山桃,“小桃妹妹,你与我一道走罢!”
桃奴睁大眼:“阿生哥哥说这话,可是……可是愿意娶我?”
张落生回答:“我这就去找你两位姊姊说亲。”
桃奴笑了。
“阿生哥哥,这事你得和我兄长说去。”
“兄长?你还有一位兄长?昨日未曾听你提过。”
“兄长不住此处。兄长住在桃林另一头。”
桃奴凑上前,翠绿的眼盛着张落生。
“阿生哥哥,待你寻到我兄长,我便与你走。”
张落生瞧不见桃奴了。他只道是仍在林中,满树的粉花密不透风地开着,风里溢着香。
他往前踏了一步,脚下的土很软,丝丝缕缕似是触须;又踏了一步,远远地果真出现了一座木质的屋,形状两端尖尖,见所未见。
张落生喊:“小桃妹妹,且等我回来接你。”
他朝木屋奔去。
*
应该有配图,但一直没找到时间画,拿小短文先水一下,等玄鸟姊姊过审后补补。
*

眨眼间,已是岁末了。这几年都没回过镖局,师父几次来信,要她无论如何今年回家过年。商玄推脱不得,念及师门上下,亦生思乡之情,便匆匆经陆路回返。每每路过村镇人家,她便见新桃换了旧符,褪色的旧红纸被揭下,墨迹刚干的福字贴上门板。不时有红绸系在树上,被鞭炮的亮光映得鲜艳如火。只是那亮光倏忽而起、倏忽而灭,房门一掩,四野便寂静如初。
这一日却有些不大寻常。她在集市上临时搭起的茶铺前坐下,相隔两桌的位置上坐了两名女子,正以姐妹互称,长相却全无相似之处:一者身形高挑、长发尽白,一者低眉浅笑、双目碧绿。细观其衣饰,俱是桃粉翠绿鹅黄这等鲜嫩颜色,不易染、却最易污,并非寻常行路之人的服色。若是世家女子,也应有护卫侍儿,她们却无邑从在侧,平白令人生疑。
商玄便在那对姐妹起身后,潜进人群暗中跟随。二女脚步轻快,出了城镇,便入山林。她耳闻二人嬉笑之声,言语中提及身后来者,便知自己行迹已露,索性取鞭在手,于最高的一处枝上现身,居高临下地俯视她们,开口问道:“你们是妖是人?”
小妹往大姊身后一躲,格格笑道:“这姐姐当真有趣!我们自然是同你一样的。”
商玄本不至于被这一句话激怒。然而,林间陡然漫开的花香与成熟果实的甘甜气息浓郁得令人头脑发胀。她抖开鞭子,鞭头灵蛇般朝着二人刺去,被大姊不知从何处摸出的一柄长枪拦下。这人身手敏捷,显然熟习兵刃,虽姿态轻忽,却绝非等闲之辈。然而,为何……?
“还没发觉?难怪你执着至此。”那双眯起的眼目中不止一双瞳孔,此刻如多足的蚰蜒盘绕爬行般流转。商玄与她缠斗几个回合,左支右绌,却总在本应落败时被轻飘飘放过。怒意被叠得越来越高,恍惚间似有一团火自她胸腹间点燃、爆裂、蔓延至四肢百骸,烧得皮肉灼痛、几乎马上要破体而出。商玄低下头,只见伤口处流泻的并非鲜血,而是她见惯的妖物浊气。她不由得张口,从喉咙发出一声非人的长嚎。
于是玄鸟高鸣,声如泣血。
原来我是玄鸟,而非商玄!这具肉身只是浊气所化,与妖物同类,那村中突生的、致使村人十不存一的大疫、也尽是浊气浸染所致——其因在我!若为旁人打算,家自然不能回,便是以往熟识的师伯长辈、故交亲友,俱不能再见了。商玄,商玄,你害了我……这颗人心居然会痛!
不知何时,攻势已停,鼻端的果香也由浓转淡。她一手扶额、一手撑地,昏昏沉沉,好似自一场大梦中醒来,不知今夕何夕。面前的人形妖族朝她递了一只手,她握住了。
好。既然这颗人心还会痛,便用杀生去洗练它。你一心救人,我却偏要生啖血肉、将你声名尽数葬于我手。那时我方成了玄鸟,方从你彀中逃脱。
她摇了摇头,不去想景朝十六年那个炽热的冬夜,立在盼缘与桃奴之间,仰头看向那并无五官、比夜幕更加暗沉的漆黑面目。大妖方才已将诸般利害言明,只待她们各自抉择。桃奴总是要同她们一道的,但盼缘遇见的那名女子……玄鸟朝前迈出一步,拿了主意。
“烦请您留下两卷帛书、同一份信物。”
梓颔首,一片漆黑的叶子落于她掌心,繁盛的树影旋即隐去,仅余一片冷清的月光。桃奴戳了戳那片墨叶,问她:“二姊,你要归乡么?”
见盼缘也低头看来,玄鸟摇了摇头,解释道:“我只想着,总是要走这么一遭的。大姊先前不是遇见了良缘么?若是你也得了奇遇,说不得这卷缚妖咒便要用上。便是往后改了主意,亦可一同前往应山。”
“二妹一向是周到的,”盼缘面上笑意淡了几分,显出少见的忧色来,“可既然不愿归乡、又没为自己留下一卷缚咒……你待如何?”
“我已有了这具皮囊桎梏,便不愿再受其他约束了。”玄鸟低声道,“而归乡,当真是好事么?”
自人身所获的灵智让她们与过去的自己之间有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在那之前的我,当真是如今的我?亦或在那之前,世上本就无“我”?若是商玄,会如何回答这等问题——呵,人族本就不必担忧此事。若是投入化妖池中,世上还有无玄鸟暂且不谈,但一定不再有商玄了。而正是因此,她不愿归去。
——————————
【送礼小剧场】
玄鸟:(欲言又止)
玄鸟:陛下,臣有一事不明,想要求教
梓:何事
玄鸟:(展开睡衣)此乃何物
梓:倒飞鸟
玄鸟:陛下,臣的意思是为何其头脚相反
梓:因此物乃倒飞鸟
玄鸟:臣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