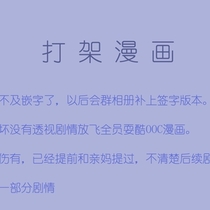推荐bgm:: http://music.163.com/song/29544534/?userid=1547143609
1.
当意料之中的这一刻到来的时候,雪维利尔并没有她自己预想的那么平静。
但也没有很崩溃。至少从表面上看来。
她从黑暗中站起身,从充斥着夜色的走廊走向通往卧室的门口,走进卧室,坐在床沿,握着两节断裂的绿幽灵,陷入长久的沉默。
她就坐着,不动,眼里很疲惫,没有一丝光亮。
对面的窗外还有稀落的灯光,钟表还在轻轻地走,无处不在的沙沙声静谧而苍白,与空气中让她瑟缩的冷意一样。
如果能停下来就好了。
2.
穆萨并不知道自己所做的选择是否正确。记忆中她从未这么决绝——至少在对待自己的时候。
但她只是做了自己唯一能做的一件事。
她望向某一个方向。那里除了空白的墙壁一无所有,却在太阳余晖将尽的时候留下大片大片温暖的影子,与天边晚霞浓重的金红。
太阳快要落山了……这个时候,她会在做什么呢?
穆萨想着,知道自己或许是最后一次产生这样的念头了。
——那个方向是泉堂,现在她就在那里。
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她了,大约她是一个月前从家中搬去泉堂的吧……自己这个月来去了几次她家,都不见她的人影。泉堂不是什么舒服的地方,她这么喜欢独处,这么依恋自已的琴房,这段时间她过得一定也很不舒服。
对了,琴房。
穆萨记得这几次去她家,院门处处都上锁了,只有隔着小花园的琴房干净透亮清晰可见,乐器都按原样盖好陈设,一台钢琴在玻璃窗后不甚显眼地静默伫立。
穆萨太熟悉那台钢琴了。她曾经很多次坐在钢琴的侧面,抚着琴布上的丝绒,听身边人的指尖流淌出温柔舒缓的乐章。她见过清晨与傍晚的琴房间的景色,阳光尚且慵懒地降临在乐声里,洒上朦胧细碎的一层金灰。
那时的曲子她大抵也记得。这一两个月来,旋律还时时在午夜失眠的间隙从心尖划过,在不经意哼出的小调间停留,再在它们背后所寓意着的那个名字隐约浮现时猝然消散。
穆萨的眼神出现了一瞬恍惚。
雪维利尔,一个魔法师。
3.
时间过得很慢,黑夜广阔得漫无边际。
雪维利尔轻轻摊开手掌,低头看向掌中断裂的两截水晶。断裂的边缘在只可见影的漆黑房间里泛出一线锋利的冷光,割得她毫无知觉。
这是绿幽灵,她的随身灵摆。
当初挑选灵摆的时候,她用水晶摆而非木质摆和金属质摆,只是因为合眼缘,并不担心水晶是否容易断裂——作为一个魔法师,让一块精加工的矿石不至于碎掉并不是什么难事。
这块绿幽灵也就跟了她很多年。她看向透明中悬浮的点点墨绿时,会想起暮色间的森林与森林间的暮色,会想起独属于这点苍翠的沉稳与冷静。
它万万不可能断的。
雪维利尔闭上眼,轻轻蜷起手指,强迫自己不去看灵摆的残骸,也不要思考自己得知的事与面临的处境。
在一个小时之前,她做了一次例行占卜——用于保持手感和准确度的日常练习,也有助于判断一天事宜是否顺利。
这原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从今天傍晚开始,雪维利尔就莫名地感到焦虑不安,心悸,甚至有些眩晕。糟糕的状态反映在占卜上时格外明显:灵摆一反常态地经常不回答她,或在简单的是否问题上给出“也许”“错误的问题”之类含糊的答案。
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占卜结果。深谙这一点的雪维利尔没有再继续练习,而是抑制情绪调整状态之后,勉力问了几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么?”
——也许/错误的问题。
“我感到不安,与我的组织有关么?”
——是。
“我感到不安,与我的朋友有关么?”
——是。
做到这里的时候雪维利尔已经犹豫了。这个“是”灵摆回答得相当肯定,而能被她真正当做朋友的,目前只有一个。
她犹豫了很久,才问出下一个问题。“是……穆萨么?”
——是。
“……她在哪里?”
灵摆的前端指向了东南。那是穆萨家的方向,离里政府很近。在家就好。
“她遇到危险了么?”
——否。
雪维利尔松了一口气。“她正在经历的事情,与我有关么?”
——是。
“她在因为我而心情不好?”
——否……也许/错误的问题。
这个回答太罕见了。灵摆对于心情的判定一向非常简单明确,只分为好和不好,从来不会出现也许。
雪维利尔盯着不住抖动的灵摆下端,沉默了一会,知道自己需要换种问法。她起身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关于人际关系的占卜图表,将灵摆悬在图表中心正上方,问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灵摆静止了一会,终于开始有规律地轻微晃动。前端缓慢地从正前向顺时针移动,来回画出的弧线完美却千篇一律,像是反复重叠的压抑,把令人崩溃的死寂分摊到无比漫长的时间之中。
灵摆的方向最终停在了两格之间。一格写着仇人,另一格写着陌生人。
雪维利尔感觉自己窒息了。因为占卜而高度集中的精神此时竟有难以维系的征兆,被压抑的情绪在随着加速的心跳翻涌意欲决堤。
穆萨怎么看自己?——这是她刚刚问的问题。
陌生……怎么会呢……?
她放下灵摆,思维陷入一片空白。作为魔法师的本能和作为穆萨曾经的朋友的本能使她难以自制地想到一种可能——
冷意瞬间浸透了她,从指尖到肺腑。
不,还没有确定。也许……
她从茫然中短暂地清醒过来,疯了一般再次拿起灵摆,仿佛抓住一棵不存在的救命稻草,问出那个她恐惧而残余着渴望的问题:“穆萨还记得我么?”
灵摆猛地剧烈颤抖起来,有如风中挣扎的烛火。它艰难地画出一个逆时针的代表“否”的弧度,却来不及画一个完整的圆。
那一刻雪维利尔听见无比清晰的一声脆鸣,和木石相碰的钝声,炸裂在她意识还能触及的听觉中。她怔怔地低头,看见灵摆已经拦腰断为两截。一截落在桌上,在昏暗中失去了原有的光泽,在细小的碎片残骸中沉睡。
而另一截还孤零零地悬着,无家可依。
4.
既然这个傍晚是她最后能够回忆这一切的一晚,那么时间再拖延得久一点也无妨。自己应该好好想一想,穆萨想。
还是从那间琴房开始吧。
她记得在一个月前,自己站在一道花篱之隔的雪维利尔家花园的外面,还在茫然和悲伤中挣扎着思索。对面的琴房窗帘并未被拉起,房中的冷清明明白白地暴露在嘈杂的世界一角。不过,路过的行人也仍然不会多看一眼,坦诚或是遮掩也没有太多区别。
当时她在想,这间琴房的坦诚明白,会不会是雪维利尔给她们彼此留下的一个念想?一个她们可以时时去看、去怀念的地方。
她原本执着于这个念头,几日之后,却忽然想明白了。战时状态,既然雪维利尔已经搬去泉堂住了,又怎么可能再冒险回到曾经的家呢?会来到这里的人,只有自己一个而已。
这是雪维利尔留给自己的。
那么,她三番五次地有意无意地在她家琴房前驻留,究竟是想看到、寻找到、回忆起什么来呢?是不是抱着『她也会来怀念这里』的幻想,想要再见她一面呢?
可是,最终促使她们分道扬镳的、促成这样悲哀的幻想的,分明是她自己——是她把雪维利尔的魔法师身份告诉了组织,里政府才会派人监视和查证她的。
时至今日她依然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但至少有那么一瞬间她后悔了。
执行这项任务的艾泽尔,在那天出发之前,也问过她一些关于雪维利尔的问题。她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答的,只记得自己吞吞吐吐犹豫了很久,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未必有效的信息,然后强忍着眼泪走出她那间布置温暖却毫无实际意义的心理咨询室。
艾泽尔那时候,一定觉得自己很奇怪吧。为什么自己这么没用呢?即便是做这样『正确』的事情……
她只是没有更多勇气回头去看了。
在那七天之后的夜晚,艾泽尔终于执行任务回来了。他没有杀掉雪维利尔,却给她带了一句话。
“雪维利尔让我……替她向你道歉。”
原来她是道过歉的。
穆萨想起那是个雨夜,雨中的小镇潮湿而苦涩,正如她半夜未眠时摸见自己脸上的泪水一样。
哭什么呢?她再一次由衷地为自己无用软弱的行径感到可笑。
她早该明白的,当她和雪维利尔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就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是非对错从未分清,却也不再有分清的必要,因为在里政府与观星的矛盾面前,这点羁绊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与谬误百出。
她犯了太多错了。即便是现在,她依然在犯错。用一个错误填补另一个错误,把痛苦如此不负责任地留给别人,她几乎要厌恶自己的自私与懦弱。
但她不想再挣扎了。自私懦弱也好,道长而歧也罢,只要她忘记这一切,不就全都迎刃而解了么?
一切都该结束了。
穆萨舒了一口气,走向房间里那面悬挂的半身镜。她模模糊糊地看到镜中的自己,容色已很憔悴,眼里还是那么失神。
催眠开始了。
她闭上眼,感受着睫毛从颤抖归于死灰一般的平静,脑海里涌现出意识残存时的最后一个念头。
对不起。
5.
原来哀莫大于心死是这样的。
雪维利尔慢慢站起身,把断裂的灵摆珍而重之收在灵摆袋里,放进储物格,然后摸索着向外走去。
她已经一个人坐了太久,天空甚至没有那么漆黑,而在最远的地方露出青灰色。
她想出去走一走。
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四肢已经和心思一起僵硬了。她机械地走到泉堂门口,这里空无一人,大门紧闭却没有锁。
她用苍白颤抖的手拉开门,冷风吹上她的脸,吹进干涩发红的眼中,生疼。
她走出门,累了,就靠在门边。望着曙光降临之前的景色,她忽然升起一种强烈的冲动。
想去镇中,去穆萨的家,哪怕只是看一看她——
冲动顷刻间蚕食了为数不多的理智,也点燃了近于干涸的情绪。雪维利尔的呼吸变得混乱,她甚至没有更多思考就踉跄着向前疾步走去。
可才走出两三步她就停住了,仓促立在原地。她意识到如果踏出这一步自己将要面对什么——
她无法面对穆萨。出了泉堂,她很难在里政府的围剿之下全身而退。最重要的是,即便她能见到穆萨,也只会见到一个陌生人——单方面的陌生人。
她最痛恨魔法师的。她一定会用极致厌恶的眼神看向自己,再拉响警报,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
与其这样见到她,还不如再也不见——是么?
雪维利尔无法回答。她很想哭,可她只有一片死寂。
她选择服从现实的安排。
6.
穆萨睁开眼睛的时候,晨光熹微。她挣扎着起身,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经睡下,尽管昨天的记忆仍停留在她看向镜子中自己的一瞬。
她感到心里空了一块,好像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但说不清。这种感觉转瞬即逝,又是她潜意识里想要逃避的,所以她并没有过多在意。
她懵懵懂懂地翻身下床,忽然注意到书桌上有自己的日记本,翻开的那一页有一句话,是她自己的字迹:
人不可以轻易遗忘,也不可以轻易铭记。
End.
【注】关于灵摆占卜,那些问出的问题都是心里默念的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