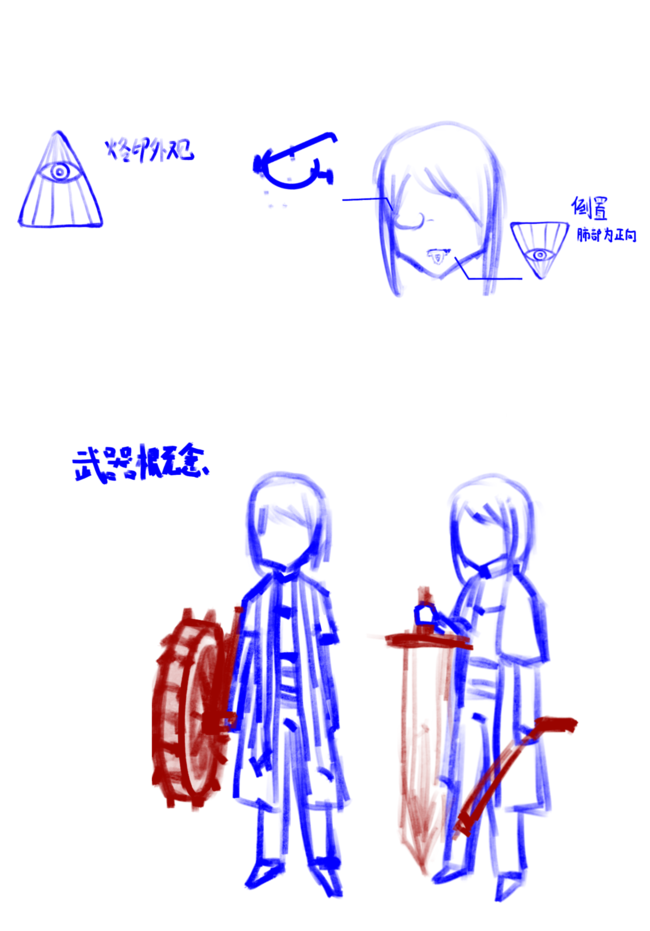舞会与演武的隙间
01
“我是来玩的。”维塔拉煞有其事地点头。
她穿着崭新的舞会衣服,露出一张光洁的面孔,步履轻盈地与人漫步在花圃的小径之上,并神色自如地挽住了身边舞伴的手臂,后者则因为她的亲密举动,连脚步都乱了一拍。
看起来古老血族确实像传闻里一样兼具着贵族的矜持和上流社会优秀的社交礼节。做出如此评论的社交距离毁灭者完全忽略了他们俩才认识了两个钟头,连月亮还没升到中天这个事实,自顾自地在心里得出了结论。
一切始于圣伯拉大教堂组织的假面舞会,她捏着抽到的纸条,上面用流利漂亮的花体写着舞伴的名字。
“看来我的学问并不涵盖到这部分……”维塔拉喃喃自语,盯着这些圈圈圆圆看了半晌,才勉强分辨出上面写的东西,一字一顿地读了出来:
“凯……伯恩特•达摩•法、法加纳。”
一道视线落在了她的身上,维塔拉抬眼看去,与白发红眼的古老血族对上目光。他穿着做工精细的礼服,浅色的头发在颈侧用红色丝带斜斜地拢成一束,戴一副眼镜……或许用镜片挡住心灵的窗户能有效地防止不怀好意者对情绪的窥探?维塔拉漫无边际地想着奇怪的问题,金绿色的眼睛漾出蜜一样的笑意来,她听见自己的声带震颤:
“看来您就是了。”
法加纳先生的眼睛像是鸽血红的宝石,红色的宝石看上去热烈鲜艳却冰凉坚硬。但还没有那么冷,是清晨溶洞上落下的露滴。这是位彬彬有礼的先生,即使他看上去通身都是知识与学术的气息,但维塔拉认为没人会把他错看成学者或是教授。
再没有什么词能比贵族更好地概括法加纳先生的身份了。
“很高兴认识你,帕莱小姐。”
“你可以叫我维塔拉。”金发的舞者轻轻拉平衣上的一条褶皱,发出了邀请,“舞会还没有开始,要去走走吗?”
他看上去并不是来消遣的,毕竟即使是维塔拉也知道,教会总不会费尽心思只为了组织一场单纯的联谊。不管人类还是吸血鬼,在这样的世道里总会被秘密和暗潮吸引而来,或是在漩涡里沉底,或是找到秘藏成为赢家。
今天的夜空晴朗,深蓝色的天幕上缀着珍珠色的月亮,很适合进行一些关于天气的寒暄客套,但未免显得寡淡无趣,良夜不可辜负,于是她坦诚地说出了开头那句话,用发亮的眼神去看舞伴,男性的头发在月光下映出莹白的光晕,显得格外端庄自持,温文尔雅。
“要试试跳舞吗,探戈、华尔兹、还是拉丁?”她仰着头问,在高个子的法加纳身边像是个小女孩。
我以前是个成年人吗?真可惜不能再长高了。她的视线在法加纳尖尖的耳朵上停留了一秒又移开。
“我并不算精于舞蹈,华尔兹可以吗?”虽然看上去有些惊讶,不过法加纳先生依旧轻轻执起她的手,行了吻手礼。他低下头来的时候,她在对方红色的眼睛里看见自己的倒影。
维塔拉的手指轻轻蜷曲了一下。我应该做点什么,她这么想,但只是安静地站着,毫无头绪。
这感觉新奇又有些陌生,可见她以前遇到的舞伴都是些烂人,竟没有一个人懂得什么叫做礼貌。
“当然可以。”她的声音轻下来,语调却上扬,嘴角弯弯,“来,跟着我。”
她舒展手臂,张开怀抱,如同深夜里绽开花苞的危险植物。今夜汇聚了那么多人,猎人和猎物都待在一处,寻找着自己的目标。维塔拉并不准备在此酿成什么血案,她没有什么必须要得到的东西,也没有必须被消灭的仇人,她的猎场在舞池之内。
和缓的舞步给人交谈的空间,他们在旋转间轻声细语。
“我在附近似乎从未听见过维塔拉小姐的消息,您从很远的地方来?”法加纳的步伐标准得恰到好处。
但对金色头发的舞者来说,重要的从不是标准,而是节奏。
“在我住的地方,地下有一条宽阔的暗河,我不喜欢这条很吵的河。”她轻巧地挪动脚步,巧妙地带歪了舞伴的步伐,而法加纳正在听她说话,还未察觉到这点微小的偏移,“所以我把剩下来的垃圾通通丢了进去,那里最后会流向入海口,潜伏着长了三排牙齿的鱼怪,它们很喜欢这些残渣。”
“所以他们都死了,确实是隐藏踪迹的好办法,看来您在的地方并不是人流密集的区域。”她的舞伴在一瞬的惊讶之后做出了反应。
“你喜欢钟乳石吗?有些会形成特别的花纹和色彩。”借着旋转,她带动着法加纳愈发偏离了原有的步调,后者原本流畅的舞步变得些许不稳,“不要再记舞步啦,跟随你的感觉,亲爱的法加纳,这并不难。古老血族似乎有聚居的地区,阿提尔湖的珍珠真的有那么漂亮吗?”
“我的收藏室里有一些……”对方似乎意识到自己从思想到脚步都在偏移中打滑,而还没等他把话题摆正,却又被带着转出了一个不该存在的圆,维塔拉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你们有去湖底看一看吗?湖泊总是像蚌一样埋藏很多秘密。不过你看起来并不是热爱冒险和交际的先生,如果您以后有兴趣的话,说不定可以来我家坐坐。不过那里没有充足的食物和温柔的风景,白天的时候空气里都是可怕的太阳味道,但我可以为你准备一张吊床,我们可以在晚上去残月血族开的酒馆找点乐子。”
“感谢您的邀请,那么我有幸得到一封月下宴的邀请函吗?”法加纳先生从被动回答里挣到了一次主动提问。
这下轮到维塔拉感到诧异了,她睁圆了金绿色的眼睛,露出一副人不可貌相的古怪神情:“哦……你对这个感兴趣?”
法加纳则以礼貌但肯定的微笑回应了她。维塔拉眨了眨眼睛,认为这位先生可能对嗜血血族的社交场合缺乏正确的认知。但……
“我很荣幸能帮上你的忙。”她笑眯眯地回答道,瞬息间和法加纳完成了男女步的调换,扶着他的腰转了一圈。舞伴露出了猝不及防的茫然神情,被顺势引导着坐在了花园的长椅上。
搭住他双肩的金发姑娘有一双宝石色的艳丽眼睛,接着这双眼睛来到了咫尺之处。
法加纳得到了一个亲昵的,过分的,令人脸红的亲吻。
毫无自觉的嗜血舞者满意地直起身来,而被害者看上去已经是震惊到只能微笑的地步了。
“不过,法加纳先生。”罪魁祸首一边笑一边坐在了他的膝盖上,“来自你的朋友维塔拉的友情提醒,你这样去月下宴的话,是很容易失去你的裤子的。”
02
“你们嗜血都这样怪?”黑斯廷斯问。
“首先,人不能因为个体的行为而对群体产生偏颇的见解,吸血鬼也不行。”维塔拉正在看自己刚刚领回来接上的手臂,忧心是否会有血管在愈合时接错,“再者,我没有道德,不会因为您的评价把手套扔在你脸上再来一场决斗,但我很好奇您还见过什么怪人,我想听听。”
对方选择了沉默,可能觉得讨论这件事有些不合时宜。
毕竟他们俩刚刚结束了一场正常人看了会晕倒的演武,身上血迹斑斑,到处都是豁开没愈合的伤口,穿着比破布还要破布的衣服,现在正站在医务室里,看着病床上被维塔拉飞出去的手臂砸晕的倒霉残月血族。
如果蒂姆醒着的话,相信他并不想要这样的探望,即使是昏迷在病床上,他的表情也随着维塔拉在病床前的叽叽呱呱而逐渐扭曲,看上去像是做了什么可怕的噩梦。
“他的表情像是喝了过期的月鼠血一样。”维塔拉扒在床边仔细打量了一番,评价道,“看起来他一直以月鼠血维生,真是值得敬佩。”
黑斯廷斯默默在心里增加了维塔拉的资料备注:不喜欢月兽血。
“他头上肿了好大一个包。”金头发的小姐压低声音,鬼鬼祟祟地说,“我们要赔偿他吗,可我一分钱都没有了。”
于是黑斯廷斯也俯下身去检查了一下蒂姆的脑袋:“可能会有轻微的脑震荡,既然是吸血鬼,那很快就会好的。”
“但你为什么没有钱?”他继而提出了新的疑问,大部分血族都有着不菲的资产,即使不是家仆成群,也至少衣食无忧,生活困顿的工会猎人黑斯廷斯倒是见过不少。
“我买了新的裙子!”维塔拉捻起一根沾满血的布料给他看,“虽然现在变成了这样,但那时候花了我很多钱。”
“洛卡沙漠一个月见不到一个路人,没什么需要花钱的地方。”她说,“猎兵队,他们出门可不带什么钱,偶尔碰上的外来的猎人,身上也没几个子儿。”
“反正也不是重要的东西,嗯,不过在沙漠外面还是挺重要的。”她总结道,看起来对财富兴趣缺缺。
维塔拉是个贫穷的吸血鬼,黑斯廷斯又在心里记了一笔。然后眼睁睁地看着维塔拉活动了一下连接上的左臂,戳了一下病人头上的大包。
蒂姆在昏迷中发出了痛苦的哼哼声!
道尔顿先生停顿了一下,还是把这个不安定因素揪出了病房。
“哦,是不是该吃饭了?”
一高一矮的两个身影走向了食堂的方向。
“我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醒来的蒂姆心有余悸地和护士说,“有两个血人站在我的床头窃窃私语,我害怕极了!”
他不禁抓紧了被子,却在低头的一瞬,看到床边的护栏上有两个血手印。
病房里传来一声惨叫。
03
维塔拉站在一片森林之中,发光的昆虫让森林并不是那么暗,她左顾右盼了一番,找了块水边的大石坐了下来,把赤裸的脚浸入溪水里,惬意地眯上了眼睛。
森林里传来一个雌雄莫辨的亲切声音:“维塔拉。”
“嗯?”她看向那个方向,没发现任何东西。
“作为奖励,你可以获得一个问题的答案。”声音说。
维塔拉是个话很多的人,但这一刻罕见地保持了沉默。她看了看自己的手,仿佛声音给她出了个难题。
我该问什么呢?她问自己,忘记的事情不会回来也无需追寻,而她渴望的自由和自我现在已经得到了。
但幸好只是问个问题而不是许个愿望。
她朝深林中回话:“那么,那个吸血鬼给我真名了吗?”
声音轻柔地回答道:“你没有真名。”
维塔拉睁开了眼睛。
“我醒了。”她自言自语。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