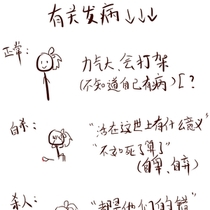六点钟一到,我就准时起床了,多年来养成的习惯甚至比闹钟还准。“生物钟是最准时的。”爸爸总是这么说。五分钟穿好衣服,下床洗漱,然后打开冰箱开始做全家人的早饭。虽然妈妈工作并不忙,而且也擅长厨艺,但是做早饭这个活却是我自己揽下来的。刚好作为锻炼,而我也不反感做这样的家务。
做完早饭已经六点半了,父母的起床时间一直很规律,所以我丝毫不担心,但是工作狂的妹妹就没办法保证起床时间了。她一干起来就格外起劲,然后不做完就什么都不干,虽然没有拖延症的困扰,但是对生活的耽搁会让她的身体素质变差。
我猜她昨天又熬夜了,因为直到我吃完早饭都没看见她起床。先不管她了,去上班。
医院离家不算远,步行十分钟就到了。办公室在一楼,只要再转个弯就.....等等等,地上好像有一块绿色的——领子?
谁晕倒在地上了?!
“快醒醒。”我试着把他扶起来,确认还活着之后发现了他的胸牌。“修·弗林斯。”这个名字有点熟悉...上一次见到好像是在...对了,昨天看病历的时候不小心翻成了医生的简历,那时候的第一份就是弗林斯医生的。昨天还好扫了一眼,现在看来他是低血糖昏厥了。可恶,身边没有糖...他身上也没有糖的样子去隔壁看看别的医生有没有带糖。
“早上好,源医生。来的真早啊。”听见熟悉的声音稍微安心了一点,还好有人。
“早,莫医生带糖了吗?”
“糖?源前辈没有吃早饭吗?”
“刚刚看到有一个低血糖的人晕倒了。”
“恩我找找看...”她在口袋里摸了一会,拿出了几块糖给我,“给你,上次翻花绳赢了,琳给我的。”
“多谢。”
我拿着糖赶快走到弗林斯的身边,把糖塞进他嘴里。在他缓过来之前还是先把他运送到办公室躺一会。纠结了一下要把他抱/扛/拉/背/拽/拖/架之后,果断放弃了虽然最舒服但是对一个男性来讲不太好的公主抱。不过他现在昏厥了,用其他方式也不太好办的样子。
......
最后我还是把他拖进了办公室,白大褂我再赔给他一件好了。
坐在一边看着他看了很长时间,为什麽这个人还不醒?正当我打算再塞一块糖的时候他睁开了双眼。蓝色的眼睛,和我一样。
“刚才看到你晕倒在走廊上,然后我就把你运进来了,看样子你是新来的医生,那我先自我介绍下。我叫源瑾瑜,也是这里的医生,请多指教了。”
他皱着眉头,看起来没睡醒的样子:“谢谢,我叫修·弗林斯,请问怎么称呼。”
“叫我源吧,”考虑了一下发音的简便性,我决定直接称呼他修,“介意我叫你修吗?”
“我不介意。”
“那你再休息一下,我带你参观医院吧。医院还是...很危险的。”
克里斯塔进医院以来还没有跟别人说过话。
她的目光并不呆滞,而是柔和地注视着手中一小盆薄荷。薄荷的叶片上被她淋了些水滴,碧绿得跟她格格不入。
她就那样坐在医院的长椅上。
父母把她像垃圾一样丢在了这里,匆匆办好手续,出门的时候并没有回头看一眼。克里斯塔甚至连行李都没怎么准备,只是几套换洗衣服和手里这一小盆薄荷。
她呆呆地等待着医院对她作出安排,反正自己已经像鱼肉一样任人宰割了。
走廊传来响动,她从薄荷上移开视线。
看样子只是发生了一起撞击事件而已。
“……唔,好疼……莫希尔德酱,没事吧?”
“我……还好啦……”
金发的看起来很温柔的医生捂着刚刚碰撞的地方,抱歉一笑,开始收拾地上散落的文件,被称作莫希尔德的医生也开始帮忙。
几张纸飘到克里斯塔脚边。
是那个金发的医生带着笑容的证件照,还有她并不怎么能理解的医学研究报告。
克里斯塔的眼神瞄向上面的黑体字。
“爱丝琳·斯图尔特”
大概这就是金发医生的名字了。她判断着,然后将薄荷放在旁边的座位上,顺手将地上的文件捡起来整理了一下,递给她,当然在这过程中并没有说话。
“谢谢你……好漂亮的头发和眼睛。”爱丝琳看着她笑着接过文件。
克里斯塔并不习惯与人对视,稍稍扭头移开了视线,还是没有出声。
“是在候诊么?看样子并没有安排到医生呢。我这里还没有接到病人,来我的办公室坐坐吧。”
爱丝琳小心地移开了那盆薄荷坐在她的身边。
“作为谢礼,请你吃奶油蛋糕吧。”
半晌。
“真是的……捡了几张纸而已,不用这么客气吧。”
话语里却并没有责怪的意思。
从来没有人夸过克里斯塔的头发和眼睛漂亮。
白发和红瞳是她天生的,却被所有人误解为恶魔的象征。
加上缠着绷带的左眼,让她从小就没有朋友也没有得到过家庭的温暖。
此刻她第一次对这个世界产生了一丝好感。
十五分钟后。
克里斯塔和她珍贵的薄荷已经转移到了六楼爱丝琳的办公室,她摇晃着双腿观察四周,不断地往嘴里送奶油蛋糕。
墙上贴着一些看起来相当可爱的简笔画。
克里斯塔端详着它们陷入沉思。
“抱歉久等了……在看画么?莫希尔德医生画的。”
“她很会做饭哦,也很会画简笔画,是很可爱的一个人,我们有空去找她吧。”
“对了,我已经跟上面申请过了,今后我就是你的主治医师啦。”
克里斯塔默默地听着,蹦出一句话。
“……好吃。”
“是吗?好吃就好。”
两个人静静地坐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没再说话,但是克里斯塔的心里有一种奇妙的感觉。
跟爱丝琳在一起,感到……安心。
情绪似乎都变得可以控制了起来。

塞勒涅之月||“出来了一匹青马,骑马的名叫「死亡」,阴间也跟着他。”
贝雷特做了一个梦。
但遗憾的是,醒来时的他记不清梦的内容。
他只记得梦里的自己无助并且绝望,像身处最严酷的战场,也像终于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
月初,新月。
“新月”这个词指的不是新生的月亮而是无月的晚上,漆黑的夜空彻底统驭了夜晚,只剩下繁星依然闪烁。
他醒来时发现就是这样的夜晚,倦怠感彻底笼罩了他的身体,他什么也没有去想,任由噩梦过后的冷汗湿濡床单。
“这是这段时间里吃的药。”
白天,那位女医生说。
她是他最初来到这所医院时见到的两个人之一,有着天使一样的笑容,却在背后扎了他一针。
“嗯。”他回答。
“你的躁期和郁期症状都很强烈,所以我加大了药量。”
“嗯。”
“要记得吃。”
“……嗯。”
他被送到这里已有半年时间,月相由缺转无,时间一点点流淌。
传说中这样的月色由战神的女儿引导。
而他直到晌午才终于有力气起身,所有消极的念头在脑海中晕开了一片苍青。
——据说,那种颜色象征死亡。
梦里似乎有声音在说,如果没有他也就不会有亡灵诞生。
那什么也不会发生。
他把药丢进了柜子最深处。
贝雷特顺楼梯向下走去。
天台上总会有人,他不想看见任何人,楼道里的阴影深深浅浅,他走在影子里,避开所有可能被伏击的地点。
一楼的外头有个花园。
正午时的阳光落在草地上,强烈的光仿佛能带出光的残影。
几天前他在这里遇到了Pridy,带着不认识的少女病人走在花丛中。
病服上写着Prile,没见过的女孩,自顾自地玩弄着身边的花草。
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既然是在这样一所医院那这“自顾自”一定并非普通的任性。
贝雷特看着她,忽然觉得有些许的羡慕,这阳光之下其实并无新事,只是他在这里,全部处于阳光之下的事都与他无缘。
一切好似还在遥远的战火中,随时随地都会有东西引爆,燃烧和废墟会变成一切,所有看似美好的东西都会腐烂生蛆。
幸好他看见了她们,可她们没有看见他。
他在阴影之中停留了片刻,转身从另外一个角落走开,另外一种念头立刻涌上。
——谁知道她们是不是亡灵。
那些从战场之上跟随他至此的亡灵,在他以为可以彻底摆脱时再度出现。
这里除了那些亡灵什么都没有。
只有那些亡者如同梦魇不断围绕在他的身侧。
它们并不说话,它们也并不紧逼,它们只是注视,一次又一次,从他身侧的最近处。
——如果没有他在,那么它们就不会出现了吧?
最简单的逻辑,从因到果,如果他不在这里那么一切就会恢复原状。
有时侯,活着远比死更加艰难。
“贝雷特,等一下。”
那个声音从身后叫住了他。
贝雷特木然地转身,身后餐厅食堂的声音嘈杂。
总有人来来往往,有的人不来到这里,有的人看起来既愉快又躁动。
所有的一切与他无关。
“Pridy医生。”他说。
“把刀子放下来。”
“我不知道你在——”
“已经流血了,手上。”
“……”
等他低头才发现手指不知不觉已经握上了锋利的刀刃,它看起来是那般美好,引人注目。
只不过是一柄餐刀而已。
“你拿刀子准备做什么?”
“砸人。”
“谁?”
“凯斯。”
“……为什么?”
“他把我的空调踩坏了。”
“空调……我记得你住在四楼吧?”
“嗯。”
“他跑到那里去把你的空调踩坏了?”
“……嗯。”
Pridy向他伸出手。
他迟疑了一下,最终扬起一个微笑,把刀子还了回去。
眼底的刀刃上似乎泛开了淡淡的青光。
毕竟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所以他并不在乎任何事情。
要知道青色是死亡的颜色。
如果抬手,就会发现手上的血管泛着青色。
手腕上有个地方,虽然看不到,但触上去能感到心脏的跳动。
这天晚上贝雷特直接用牙咬破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