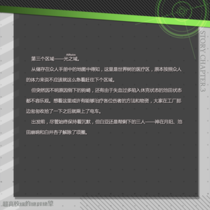以游戏《绝对绝望少女》为蓝本的同人企划。
“弹丸HOH”本篇一年之后的故事。
企划内容纯属虚构,与现实中的个人、团体、事件一概无关。
所有角色言论仅代表角色本身的立场,与玩家本人无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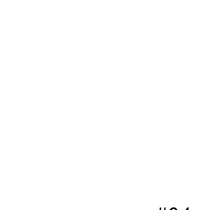



#02 约定好的事情
*就一个卡……
总觉得无论何时都在拼命前进着,为了不落在后面而向前漫无目的地奔跑,除此之外的事情一概不去考虑——正因如此,我却更加无从追赶。
如同屏障般将我阻隔开来的银杏花雨般簇簇落下,回转着的落叶仍然残留着晚秋最后的气息,眼前四散着的是阳光中明灭不定的浮尘。
在那一天的黄昏,我一如既往地伫立在原地,目送着渐行渐远的驹崎辽,最终就连他都背影也逐渐变得模糊、变得陌生,消失在漫长道路的尽头。
“我不想让你加入的。”
结果我只记住了只有这句缺失了前因后果后显得突兀而又直截了当的话语。这是属于他的独特又不加修饰的表达方式,也是无论何时都会令我变得手足无措的回答。
我一向觉得在驹崎辽面前我所有的沉默失败与茫然都是那么不堪一击,仅仅是为了掩饰某种脆弱易碎的内芯而一层一层包裹在外面的茧壳,但不同的是再也没有蝴蝶破茧而出。
只是沉默的、等待夏日逝去的茧而已。
他究竟是出于我的软弱而反对我的加入,还是因为其他的别的原因,这一点我也不得而知了。
*
当我自浅薄的沉睡中惊醒时看到的不是湛蓝色的天空抑或者树林的阴翳,而是仿佛遮天蔽日的灰黑烟尘。我用了几秒钟来接受这一切,而后记忆自三森狙向我跑来的那一刻开始倒序回放。我慌忙地撑坐起来,在天旋地转、仿佛宿醉般的昏沉与头痛中(上一次有这种感觉是什么时候我已经记不清了,我不喜欢酒精),驹崎辽的身影在星火乱飞的城堡废墟中变得清晰,跟在他后面的伊梅斯与篝仁也与鹫巢镞走了出来。
大家都没事,大家都没事吗?诸如此类的念头在脑海里转个不停。我却什么也做不到、只像是被钉在了原地,树一样生根发芽般一动不动。
“——莱奇君呢?”
寒河江秋彦这么问道,与此同时我一直尽力忽略、试图忘记与藏匿起来的某个事实终于浮出了水面。
“莱奇..布尔本?”
不是的,不对、那个名字是不可以说的——就像是魔咒那样、如果说出来了一切就都会结束变得四分五裂,不说出来大家就会过着幸福的谁都没有死去的生活,所以是不行,不行,不行的。说到底关于死亡这种事情本身就是有悖常理的,只能认为那是不通情理的某种意志,还有不合理的单方面的硬性规定。
没有人继续说话,在出奇的死一般的寂静中夕阳沉入了云层,如同血一般缓缓地熔化在遥远的地平线中——世界树的夜幕降临了。
*
“——”
我不知道刚刚究竟想了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时间似乎在我看不见的地方转得哗哗作响,早已马不停蹄地冲到前面去了,篝火明灭不定的光隐隐约约将四周映成一种黑暗中夹带着橘黄、却不但没有明亮反而变得更加深邃可怖的颜色。
深夜。
有谁死了吗?
突兀的声音响了起来,是空无一物般的声音,以至于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大致地辨认出那是我自己在说话,我在问可可罗先生:“有人死了吗?”
“我不知道。”然后我摇了摇头,“没有吧?”
像是听到了我的声音一样,寒河江秋彦转过头来。说实在的,我完全不清楚他的神情有什么含义——不,与其说是不清楚倒不如说我连刨根究底的勇气都没有。那样失望的、焦虑的表情,恐怕我只要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崩溃掉吧。
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忽视掉无法面对的现实,把自己囚禁在蔷薇花墙中沉睡的城堡里。
我的鸟儿在哪里,它们会有悦耳的声音吗?我的蔷薇在哪里,它们会有鲜红的花瓣吗?我的纺锤在哪里,又是谁用它扎破了我的手指——是我,就是我,祈求着永远的安宁,而又从未期待王子的造访。
*
……我对现在的事情,一点头绪也没有。
被向我走来的寒河江秋彦拉住还是上一秒的事情,转眼间我已经被困在墙壁与他的影子所形成的空隙之间,有点像是忽然从草丛中弹出的、令我无暇反应的捕兽夹子,但在他的面前我甚至没有考虑过挣扎(我清楚这是没有用的),于是我低着头如同罪人般等待着审判——寒河江秋彦冰冷的目光毫无保留地朝我倾泻下来。
“你还想再逃避一次吗?”当他在我耳边这样质问我的时候我说不出话来,不是因为吓得无法发声了,只是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说什么呢?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地问他“逃避什么?”不对,那也是没用的,更何况就算我仿佛要骗过自己般笑着,忽视掉脚下交错流淌的鲜血,寒河江秋彦也会把我拽过去让我好好看清楚的——不知为何我有这样的感觉。
“华节奏。”就像是此时此刻他的呼吸停驻在我的脸侧,淡色的头发垂落在肩头,我却觉得与他相隔了无法逾越的距离。“能救你的始终只有你自己。”寒河江秋彦稍微顿了顿,“当然,如果我能把你从那个深渊拽出来……”
话没有说完,他沉默了一会儿,伸手把他身上白色的外套扯了下来,看起来像是漫不经心般地把它扔给了我,做完这些后,寒河江秋彦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这样的我让他失望了吗——但是,究竟哪里出错了呢?
究竟哪里出错了?我问可可罗先生,但小小的兔子沉默着,就像是它从未说过话一样,火焰橘黄色的光芒在一片漆黑中明亮地跳动着,白色外套的温度本来也几近消逝了,却仍然在火光下流露出一点温暖的色彩来。
*
伤痕累累的莱奇·布尔本出现在我们眼前。
莱奇怎么会死呢,莱奇说过会回来的——莱奇是幸运吧?一厢情愿地认为他已经消失不见、却继续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的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才好了。
“能回来真是太好了。”我像个笨蛋一样,心中塞满了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只好一遍一遍像是坏掉了的机器一样在嘴上、在心底,不停地重复着,但与此同时一个早已萌生想法却缓缓升了起来,又像是寒河江秋彦抓住我时在我眼中投下的阴影一样令人无法忽视。
如果之后再有人死了呢?
我没办法思考下去,但是那种欢欣的感情却被冲淡了许多,变得乏味了。
*
我与寒河江秋彦关系的转折,发生于驹崎辽带着十队队员离开的时候。
白色的潮流浩浩荡荡地向着这里涌来,于是围绕着这座工厂的我们仿佛孤岛上最后的住民,而就连这座岛屿似乎也开始变得摇摇欲坠,不断地遭到蚕食。
我下意识地回过头来,映入眼中的是闭着眼睛,陷入昏睡的白发少年。超高校级的旗手。我在脑中将他与那张照片仔细对应起来,然后确信一般地点了点头。没关系,已经用绳子和手铐紧紧地绑住了,才能的因素也没有忽略掉,三森狙的事情不会再重演一遍。
在我被打晕后追上去,然后抓住她的正是寒河江秋彦。当他看着曾经的好友倒在他身边时究竟作何感想?我已经无从得知了,甚至抗拒思考那个可能性,只是从头到脚充斥着无可言喻的愧疚——总是在给他添麻烦的我,却连回报他的期待都做不到。
怀抱着这样的心情,我举起枪来向扑上来的白狼射击,明明最开始的时候还会犹豫但现在已经完全熟悉了呢——这么想着的我再抬起头来的时候,看到的却是寒河江秋彦因为躲闪不及,被利爪划过的样子。
不行,不行,不行。
寒河江秋彦会死吗?白狼会扑上来吗?我们都会死吗?
事实上诸如此类的想法在那一刻完全没有发生,我唯一能做的也是唯一做了的,仅仅只是让无形的音波子弹穿透那只闪着红光的独眼,令那只白狼应声瘫倒而已。
“秋彦君?”
我慌乱地冲上去,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几乎愣住了——然后又开始翻找起用于包扎的东西。最后我蹲下来用纱布一层一层试图地把那道伤口掩盖起来,笨手笨脚得简直像个凑数的新手,我甚至确信这样笨拙的包扎一定把他弄疼了(我听见压低了的抽气声),而当我终于完成的时候,血迹已经在纱布的表面星星点点地晕染开来了。
“……对不起。”我喃喃地说着,“其他人会做得更好吧。”
寒河江秋彦不知何时笑了起来,就像是那道狰狞的痕迹并不在他身上一样若无其事地笑着。
“小华节,闭上眼睛。”
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但我隐约感觉到寒河江秋彦已经没有生我的气了。于是我听话地闭上了双眼,与此同时,我的手背传来了某种温暖而又柔和的触感。
当我茫然地睁开眼睛时寒河江秋彦对我露出了恶作剧成功般轻松的笑容,我回忆了一下,随即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他吻了我的手背——我不明所以地看向他,眨了眨眼睛。但他却没有对我作出解释,只是向我伸出了手,小指微微地翘在外面。
“跟我做个约定吧,小华节。”他说。
我有些迷惑,但还是将手指与他勾在一起,简直像是小孩子间的约定一样简单而又固执。
“诶……?”
“你要努力自己走下去,而不是一味的依赖我。”
面对着他忽然变得低沉的声音、以及眼中闪动着的光芒,我不知所措地愣愣地看他,忽然想起约定是要郑重对待的——因此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会的。”
像是放下心来了一样,这样的他重新露出了我习惯的轻佻的微笑,但对我来说也是令人安心的笑容。一直以来困扰着我的那份阴影也似乎变得薄弱,如同蔷薇花蔓的缝隙间露出一点阳光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