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うれし かなし
こひし にくし
想いは 万華鏡
さびし かなし
こひし にくし
絆は 蜃気楼
==============================
渴望,思念,孤独,怨恨……这绝不是人类仅有的感情
抱有欲念被主人抛弃的器物,在春秋时分,化为付丧神。
而暗怀心愿的人类,也在寻求着某种际遇与改变。
人与器物的命运与缘分,无论善恶,在踏入这扇门时开始。
欢迎来到徒然堂,
今天的你,也在期待着什么?
==============================
一期完结
小组http://elfartworld.com/groups/1381/


磨了好久终于……
设定上是发生在阿晓的序章之后、瑶光的序章之前的事情。
满脑子都是【战斗开始,行动顺序:狂百器→阿式,……狂百器的攻击成功,阿式闪避48/99成功】之类的……
……想必哥哥对瑶光是自信pow18结果检定大失败吧【没有
————————————————————————————————
——他在梦里。
之所以知道是梦境,是因为对面站着两个鲜活的身影。
父亲和母亲,几乎已经要淡忘的面孔带着和那时一样温柔的笑容,脚边是付丧神的灵体亲昵地挨蹭,就这样看过来时张开了双手,招呼他。
跟着血色泼满视野。
站着的人毫无预兆地倒下,血液画着圈圈在身下漫开,猫儿们发出凄厉的悲鸣。
在那之后站着的是黑色不稳的身影。
他被教导过祂的名字,也知道母亲与狂气之器之间的因缘。但并没有预料过,会是在这种情况下对此有了最深刻的认识。
那时他的心情是如何呢?他看着记忆之中生出的梦,如同旁观者般,完全想不起来分毫。
大概,没有愤怒也没有悲痛,意外地平静吧。
他面对的是母亲未竟的工作,所以要将此完成。
像个彻底的局外人那样,他看着梦境里的「自己」伸出手,挤在尸体旁呜呜哀鸣的小兽跳到他手边,从动物的形体中抽出了长刀。
尽管从未被指导过使用方法,却像生来就懂得如何挥舞一样,刀刃切开虚弱的黑色形体,黑暗褪去,是白色的灵体露出悲伤笑容,致歉以后就这样消散成光点,被风吹散。
但死去的人也同样归于沉默,再也不会回来了。
「……」
最后他看见自己走过去,缓慢弯下身,趴伏在尸身之上。
透明的液体从他眼眶里滚落出来,溶进了已经干涸的血痕之中,一点一点、一滴一滴,带走死者最后残余的温度。
然后,他从黑色的梦里醒来。
「……」
凪彦睁开眼时,看见爱猫正压在胸口,用毛茸茸的猫屁股对着自己的脸,翻着肚皮睡得正香。
难怪做了相当沉重的梦。
那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连记忆都开始消褪,但曾经被刻下过的痕迹不会磨灭,偶尔也还会像这样突然被翻出来,徒增一点疲劳。
抹了把脸,他把三毛乃小心翼翼地从身上挪开后,起身进行了简单的洗漱。虽是早晨屋外却天色沉沉,天边堆积着阴云,不是什么好天气。
但新的一天里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暂时无暇沉浸于过往。
「——就拜托你们看家了。」
换好外出衣物后,凪彦抽出了很少离身的篾刀放在桌上,朝一蹲一卧的两只猫叮嘱了声。真的那只仍在呼呼大睡,付丧神的灵体则一本正经地点头,舔舔爪子,「嗯。」
「为什么不带上竹寅?」不解的三枝挂在他肩上,随着持有者一起走出家门,后者简短地回答祂,「是探查……不是战斗。」
他在前日所接到的委托是前往市区另头的探索。
在本职工作之外,他时常也会接到来自收容与出售器物的古董店「徒然堂」的委任,作为另一种收入来源,而委托的核心通常都与浊化的付丧神,即「狂百器」有所关联。
「听说出现了狂百器,正体不明……需要观察情况。」
一面给自己的九十九解释,青年按照交付委托者的说明,走向被指引的方向。
跟着一人一付丧神同时在目的地沉默了。
「……娼馆?」
「……是艺馆。」
三枝双眼发直地看着长街尾那栋与其他店面格格不入的双层仿清国建筑,被饲主轻轻弹了下脑门,「对伶人们不礼貌。」
「反正又没有人听到……」
正小声嘀咕着,街道另头传来的人声让聒噪的烟斗也自觉闭上嘴,散去了化形沉入本体中,——尽管一般人类无法看见付丧神的灵体,同类的狂百器则不同,因此他们事前也商议以小心为上。
而凪彦则将视线投向走来的身影们。
伴着笃笃木屐声靠近的是三三两两的女性,白粉妆颜,赤红抹唇,裹在华美衣裳里撑着伞的她们原本还轻声交谈着什么,在看见凪彦站在街边时都敛了声音,只频频投来眼神,似乎相当在意。
待她们走近了,凪彦才看清在这群娇美纤细的艺伎之中还混着个青年男性,冷淡地抄着手扫来一眼。
银发散散扎成一束垂在肩头,金眼下有红色的妆容,相貌精致的青年走在女性之中也毫无违和、甚至比同伴还要更加出众,身上却带着某种格格不入的凌厉氛围,让凪彦忍不住多盯了会儿,换来个不快的眼神,于是微低头有些致歉地行礼。
他们擦身而过时,清净屋听见对方发出相当轻的一个哼声。
他就站在原地,目送那几人向着那栋显眼的置屋走进去,隐约还传来细细的议论声。
「……『瑶光』?」依稀听见飘来个像是名字的声音,凪彦下意识重复了次,挑起眉。
对方的那种气息……
「难道说……动心了吗?」不知什么时候又化出形体,虎纹猫窜上凪彦肩头,发出吃吃笑声,「原来阿凪回回都回绝隔壁英子婶介绍那些好姑娘,是因为意不在此……哎哟!」
「不是这样。」
无奈地敲了三枝脑袋,重新把视线放回艺馆的人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虽然不太确定,但……」
不知是在别处沾上气息,还是有所掩饰;但比起人类,那名青年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别的东西……比如说听说在附近出没的狂百器。
会和他有关吗?
「嘿——那边的小哥?」
天色暗沉,僻静的街道来往也没什么行人,在凪彦正思索着是就此打道回府还是在附近再探查会儿时,突然一个声音从背后叫他,是清脆爽朗的男声。
回过头,街角有个像是刚从别处跑来的人,微喘着气伸手招呼他,「您有没有看到一个女人过来?这——么高,衣服黑黑脸色也黑黑的,感觉马上要砍人的那种……」
对方比划了个夸张的高度,乍一看比凪彦自己还要高出少许,就女性而言应该是十分显眼的身高。
刚刚见过的只有和那名青年进了置屋的艺伎们,于是凪彦摇摇头,看见那头的人失望地耷拉着肩膀,向这边移动过来。
「欸……如果被她跑了就糟糕了……得赶快找到才行啊……」
嘟囔着的人看起来大概二十上下,比凪彦稍矮些,左脸有条显眼的疤痕,但整体长相很清爽耐看,半长的发在脑后扎了个小髻,此时被他抓一抓散出几根来,给人相当活力的印象。
「对了,您走的时候如果有看到,千万不要去跟她打交道哦,很危险的……咦?您是……」走到凪彦跟前,小青年正要提醒他什么,一抬头对上他视线却愣住。
不解地看着对方,凪彦这时也才感觉眼前的人似乎有点面熟。
似乎……是在哪里见过。
「……啊。」
两人面面相觑了很短的时间,小青年就先一步恍然地睁大眼,「您也是被徒然堂雇佣的清净屋先生吧!前些日子里我们见过一面的……」
被这样一提醒,凪彦也想起来了。
好些天之前的大晦日,去徒然堂接受委托的他确实曾与小青年打过照面。
面前明显也想起来这回事的人不知为何表情僵了一下,紧接着就扬起笑容,「我是京桥家的阿式,最近才来到东京,还请您多多指教啦!」
「八百屋……凪彦。」也点头回应对方,凪彦的注意力很快从那个不太自然的营业性笑容转回刚刚的话题,「……你在找的是?」
「……跟您就说开了吧,是狂百器啦。」
阿式耸耸肩,视线在扒着凪彦肩膀的三枝身上晃了下,又转回来,「我在追踪流窜到这附近的某个狂百器,但是刚刚又被她跑掉了……想找路人问问有没有看见,没想到就遇见您了。」
「……抱歉,没有见到。」
不知怎么总觉得对方声音里藏着点幽怨,凪彦按下想插嘴的付丧神,摇摇头后转而发问,「……需要帮忙吗?」
而阿式则很快回绝,「不,不用了。」
过了两秒,像是意识到自己拒绝得太干脆,他才眨眨眼笑了下,「因为这是我接受的委托呀!就不好麻烦八百屋先生了,我一个人能解决的。」
「……嗯。」
既然对方说得自信,凪彦也便不再说什么;他隐约感到对方似乎有什么介怀,但没有追究的必要,便同阿式道别后准备离开。
就在他们两人要踏出相反的一步时,又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
长街的尽头出现了异质的气息。
「啊,出现了。」
三枝愣愣地嘀咕了声,和一起把目光转过去的两个人同样,看向从街角开始蔓延的阴影。
在不知何处飘来的幽幽乐声里,黑影之中缓慢浮出了女性的身形。
——不要……妨碍……我——
黑发披散、与黑衣融为一体,血红的唇蠕动,发出呓语般的声音,却让两名人类都能听清其中的扭曲怨怼。
「……唔……她脸色是不是更黑了啊……」阿式皱着眉挠了挠头,望了眼那头的女性形体,又有点尴尬般瞥了眼凪彦;后者意会地退开了些,朝他点点头,「小心些。」
「不帮忙吗?」猫儿用前爪碰了碰凪彦侧脸,表示对人类之间无言交流的不理解。
「……那是京桥先生的工作,我不该插手。」
同样也看出狂百器身周萦绕着新鲜的血气、不知是在哪里又进行了杀戮,凪彦确实也有些担忧这名不知实力如何的新同行,但对方没有要寻求协助的意思,他也不适合多余地行动。
——虽然还是有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了。
他敲敲烟斗,意会的三枝散去形体,化作浓雾一下四散到空间中,将这一小段街道包裹其中,隔绝了他人误入或者窥探的可能。
另一头已经往女性付丧神方向走去的青年回头看了一眼,似乎有点疑惑,但又很快转回去。
「能不能听我说句话呢?」
然后他像稀松平常地与路人搭话一样,朝狂百器笑着开口。
——人类……男人、都该死……——
黑色身影不稳地摇晃着,在雾气中几乎和阴影融为一体的衣袖突然扬起,从其中出现了冷光射向阿式,被后者很快地跳跃闪开,啊哈哈地抓着发髻笑了两声,「欸、欸,不要那么紧张啦!我们先聊聊吧?我也觉得有很多男人就很该死,一点都不配当男人啊,但是应该不是全部吧?」
比如我——这样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另一波寒光打断了。仍然轻巧避开的人与飞身袭上的女性移动了方位,在雾里一时看不清表情,但行动看起来也并不吃力。
「他想就这样说服对方吗?不太可能吧……」
耳边隐约传来三枝的嘟囔,凪彦抿着唇,没有回应。
在他认识的清净屋里,很少有会在敌对的狂百器一开始就表现出杀意时、首选项仍然是沟通而非战斗的人,即使是他自己,也不会想对失去理智的狂百器进行劝说。
会这样做的人他只知道两个,其一是本职为僧侣、似乎拥有无尽慈悲之心的男性。
然后另一个,是他的母亲。
有那么一瞬间,试着建立交流的人的背影与他的梦境重叠了。
——小心、危险,不要去,回来……
「……!」
回过神来时,凪彦才惊觉自己差点就踏出脚步,及时收回了将伸的手与声音。
那并不是已故之人。对方所面对的,也不是和那时相同的强势敌人。
若隐若现的乐曲仍在飘荡,而另一头的青年似乎在反复躲避中已经耗尽了沟通的言辞,渐渐收去了声音专心于移动。
下一刻,他就像失去了对抗信心般,突然拔腿往街道另端跑开。
像追逐猎物的捕食者,黑色的女性也紧紧缀在阿式身后,挟着阴影飞扑而来。
在前头的身影越过凪彦眼前的短短片刻,他望见对方紧绷着唇,合上眼睛。
跟着,再度睁开。
凪彦很难形容那一刻对方的变化。明明是同样的面孔,气息却丕变;敛去所有神色的人蓦地站定回身时,像破冰的鲸或者出鞘的刃,带着仿佛要破除一切的气势从怀里抽出了刀,朝正向他迎头袭来的黑影挥出斩击。
——那甚至不能称之为一把刀,只是未经磨砺的条状金属。
那本该连豆腐都划不开的一刀却顺畅地没入了黑衣前襟,然后拖曳开来,白色的裂痕将阴影连同雾气一道撕裂。
尖利啸声从女性口中爆出。
在她的衣袖再次兜头罩下之前,阿式已经收了刀,再次送出时直直撞入她胸口,四散的黑雾从那一点像潮水般涌出,黑色转瞬褪为白。
广袖软软地垂下,从虚弱的苍白指尖到领口的花纹都流失了颜色。
然而女性的形体却不再摇曳不定,向着已经收刀站定的人浮出了淡淡的笑,弯下脖颈,向对方盈盈行礼。
「……给您添麻烦了……」
「——接下来就请交给我吧。」
后者低头将未锻的短刀插回腰带里,再抬头看向褪掉狂气的付丧神时眉眼弯弯,似乎又恢复了开始时好言相劝的那个模样,双方说了些什么,然后女性的付丧神就这样散去外形,留下瓶形的器物落入阿式掌中,把他压了个手忙脚乱、连忙扶稳瓶口瓶身才不至掉落地上。
抱稳那只朴素的花瓶后,他才缓缓长出了口气,嘿嘿地笑了两声,「好嘞,工作完成!这下可以吃顿好了!」
跟着,青年缓慢地将视线转向这边。
像是直到现在才想起还有个人站在一旁般,他惊愕地看着凪彦睁大了眼。
「……您……您怎么还在呀?」
才刚散去雾气、重新凝出化形的三枝和饲主一道沉默了。
最后凪彦向阿式提出了同去徒然堂的邀约。
「虽、虽然是可以啦……?我也要去回报委托的事情,」一头雾水的人似乎本想就这么离开,被他询问时满脸犹豫的神色,「也要把这位小姐送去那边……」
他怀里的花瓶——女性付丧神的本体同意地摇晃了下,但似乎仍有虚弱,并没再次化出身形。
思考了下,凪彦追加上令对方的天平一秒倾斜的邀请,「……那附近有家食肆,我也正想与您更多交流些……可以叨扰吗?」
阿式露出了相当动摇的表情。三枝和不知名的付丧神一道吃吃地笑起来。
「……这么说来……」
正和应下来的人一起往另头走去时,凪彦又犹疑地停下脚步,四周看了圈。天依旧阴沉沉的,也没几个往来行人的身影,而不知什么时候,他依稀听见的那个乐声已经消失无踪,像某种不甚真切的幻觉。
他之前以为那是女性付丧神的能力,但看起来并不是。
从置屋来的吗?
往街尾望去,白日里紧闭的窗户边似乎站着某个身影,一晃又看不见了。
「……错觉、吗……」
走在前面的人已经疑惑地看过来,他也便放弃在当下追究,跟上同行者的脚步。
来日方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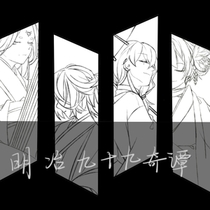

*一个没什么意义的随笔,感谢大师在群里贴出的那张照片,脑洞爆发(。
*并不是想探讨些什么……如果看着像,可能是这两天《不朽》读多了(
————————————
细雨织出了帘幕。天际灰蒙,凉意更甚。
黑衣少女撑着油纸伞,同女性缓缓步于雨中。
她们的速度很慢。不时有行人与两人匆匆擦肩而过。
由于身高相近,少女不得不微微抬高了拿伞的手臂,又斜了斜,使女性远离那渗着冷凉的雨丝。
“不必在意我。”
女性静静说道,“我是‘九十九’,淋不着雨的。”
持伞的手动了动,随即更用力地握住了伞柄。少女抿了抿唇:“……嗯。”并没有将伞归正。
女性便也不再多提了。
细雨绵绵,穿过两人之间的沉默,不断跌落在地,不多时,在街沿汇聚成了极细的水流,自脚边淌过。木屐溅出了水花,水花又沾湿了白袜。少女没有在意,微垂着头。刘海掩去了她的眉眼。女性仍是如常,那些滴落伞面的雨声,直直穿透了她的身躯。
如此一看,二人便仿佛逆流而上,似要追本溯源般,缓缓走去。
——目的地是明确的。
细密的雨幕笼罩山林,那满眼苍翠亦被淋湿了,色泽沉淀了下去。
两人行了一礼,跨过山门。写着“增上寺”的白灯笼被护在檐下,目送着二人朝上走去。
“你其实不用陪我来的,真黑。”
少女看着脚下的石阶,忽然说道。
“嗯,”真黑应着,笑意温婉,“我担心凉子迷路。”
顿了顿,凉子低低问道:
“不会累么?”
“‘九十九’是不会累的。”
“也是。”
这对话并无什么实际意义,因而掉进水流里,便再也寻不见了。
寻不见,是好,还是不好呢?凉子怔怔地想。
这身黑衣还是崭新的,因为她极少参加葬礼。可她到了这样的年纪,周围的人免不了会比她先行。
彼时,少女静静地望着睡在棺椁里的人。棺椁也是崭新的,可棺椁里的人却不是了。那张青白的面孔刺得眼睛作疼。
她没有哭。将花束献上去时,她只是在想:亲朋好友都围着他,都寻着了他沉睡的身躯,这是寻见了吧?但内里的、大家所熟悉的他的灵魂却是早已消失了,这便是寻不见了吧?
好坏与否,寻得与否,仔细想来还真有些麻烦啊。
“你说,浅原师傅这时候在不在呢?”
她的眼里藏了三分叹息:“我唐突来找他,会不会扰到他了呢?”
“必须找到他才行么?”真黑的声音素来是静的、缓的。
凉子被问住了。双唇抿作一条线。她想了想,踌躇地答:“……也不是。”
真黑笑了笑,便没再继续了。
凉子也没有再提出新的问题。石阶绵延而上。少女瞧着湿了袜子、流经脚边的雨水。雨水浸润之下,灰白的石阶便柔软得似一匹绸缎。
奇怪的比喻。她心想。
半晌,两人站在了平整的地面。建筑物皆不如上次来时那般通透可见了,罩着薄雾,看不真切。那几棵古树倒仍在雨中伸展着光秃的枝杈,不言不语。
少女四处望了望,迎上了撑伞而来的小沙弥,便慌忙叫住,询问浅原一真的去向。小沙弥大抵是没料到这雨天也会有来客,惊了一惊。
“浅原法师好像刚离开。”
小沙弥忙收了惊诧,如此答道。
凉子笑了笑,谢过男孩儿,待到送走了他,才叹出声来。
“是挺不巧。”
“必须找到他才行么?”
“……也不是。”
真黑笑了,又道:“那就散散步吧。你看那儿的门,通出去,也许别有洞天。”
本来也没什么事,凉子便依了她。真黑所指的门在斜对面,是个低矮白墙砌出的拱门。
两人缓缓前行,穿过拱门,入眼即是拔地而起、直入天际的古木,肃然静立于小径两旁。
雨雾濛濛。曲径蜿蜒而下。两旁的林木愈是向前,就愈是影影绰绰,连那绿意也不甚真实了。
那把纸伞正缓缓行于雨里。
一派空濛之中,青年的袈裟也不似以往那般惹眼了。
金黄被雨洗得深了些,黑衣则稍浅了些。
身形是熟悉的,走路是熟悉的,凉子甚至一瞬想象过,若是她喊他的话,他回过头来,定会先向她行一礼,一如往常。
然而,那身影已是远了,远得少女听不见禅杖落地时铿锵的响声,远得她的呼唤穿不透这雨、这雾。
凉子张了张口,旋即作了罢。
她仅是静静地望着,望着浅原一真的背影渐行渐远,终究只剩豆粒大小,消失在了古林深处、小径尽头,彻底消失在了她的视野里。
仿佛从来不曾出现过。
良久,她开口道:“可惜了。”
“可惜什么?”
“……没什么。”
她转头望向真黑:“走吧,回家了。”
伞面上落了些薄薄的光。少女眉眼里氲着的雾也散了。
真黑笑道:“好。”
更多的雨滴落下来了,自脚下湍湍而过,它们带走了“寻得见”的与“寻不见”的一切,将天地化为无声。



—“他”—
星期六对八百屋晓之助来说,并非什么特殊的日子。
少年照常从床上翻身坐起。睡意朦胧的大脑被寒意拍打三秒后,迅速清醒过来。穿戴齐整,打好领带,拉开窗帘。尚值冬日,云浓天阴。不过,细看之下倒能觑见云隙间的日光。
说不定会是个好天气。他想。
确认无误后,晓之助步出了房间。大抵是休日的缘故,廊下冷清得很。他尽量放轻了步子,洗漱完毕后,踏过庭院里单调的扫地声。微一站定,又向着院子里那根兀自活动的扫帚恭敬地行了一礼。
“早上好。辛苦了。”
扫帚停下了扫地的动作,在半空中微晃了晃。
他轻笑,权当是回应,又望了望天空,感叹道:“今天看样子会出太阳呢。”
帚柄复又动了动,也不知赞同与否。
做完“日课”后,少年十分满足地呼出一口气。甫一走进客厅,早餐的香气便从隔壁的厨房袅袅飘了过来,连带着男人的身影与清爽的声音。
“早啊,晓君。”
“早上好,政纯先生。”晓之助礼貌地微鞠躬,看着十文字政纯将手中碗筷整齐地摆在桌上,连忙问道,“请问还有么?我来帮您。”
蓝眸瞥过他,单手按住了少年的肩。
“你坐着就行。”
也不知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力道,少年便只能愣愣地望着政纯走进厨房里。
“喵——”
猫的鸣声打断了他的思绪,细细软软,轻搔过他的耳廓。晓之助往旁瞧去,不出意料,十文字宅里的猫也醒来了。或许是注意到了他的视线,白猫睁着一双翡翠似的眼瞳,定定地盯着他。须臾,它抬爪蹭了蹭脸颊,颇不感兴趣地眯眼又鸣了一声。
“早啊,空绪羽。”晓之助笑道。
即便被唤了名字,白猫也兴趣缺缺,侧眼瞅了瞅他,干脆不搭理。
实在是惯常发生的事了,少年并未在意。
“怎么,‘真斗’还没下来?”
政纯的声音由远及近。真斗是另一只黑猫的名字。
“好像没有。”少年接过话来。十文字政纯踱近白猫身边,将手中盛了青花鱼的碟子置在地上,似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回应晓之助:“估计待会就会下来了吧。”
待家主上座后,晓之助才合掌念道:“那我就不客气了。”
“没事,多吃点。”政纯笑了笑,“说起来,晓君今天有什么计划没?”
筷子一停。
“今天啊……”
晓之助眨了眨眼,这才想起今天不用当家教,也没有课,不必去学校——这意味着今天是个能够整天泡在愉英堂看书的绝佳日子。
“去图书馆找找资料吧。”
话从口出后,少年竟有一瞬的愣神。这句话回答得未免太过自然,但实则他在心里并不是如此打算的。尽管他的日程上的确提醒着自己要去图书馆找一些资料,不过也不用挑着今天这么难得的机会……
“这样。和同学一起?”
“不,一个人。”
“那路上多注意安全。”
“啊……嗯,谢谢您。”
奇怪。这番对话流畅得有些过分了。晓之助莫名惴惴起来,抬眼瞥过政纯。而十文字政纯仍是笑着的,对上他的目光,开口道:“再不吃的话饭要凉了。”
“……好。”
晓之助只好讷讷点头。
就连他自己也搞不懂自己在想些什么了。
—“她”—
星期六对鹿又凉子来说,代表着她可以不用去学校,面对并无太多交际的同学和老师们。这倒不是厌学,毕竟人都会有疲于应付某些事的时候。
她赤足走去拉开了窗帘。光淡淡地晕进来,天际浮着并不均匀的薄灰色。窗外矗立的枞树林正静静地回望着她。鸟鸣虫音皆无的寒冬里,这满眼翠意倒是与“萧索”二字格格不入,在鹿又宅邸旁自成了一道风景线。
她注视着窗外,倏地目光轻移,蹙了蹙眉,又将窗帘往回扯了些,径自朝门外步去。
二楼的房间除了她的卧室外全是房门紧闭。走廊尽头的窗透进了极浅的光。
这时,楼下传来了脚步声,不轻快也不笨重,一阶一阶地攀了上来。少女忽的快步奔了过去,在栏杆处迎上了来人。
来人倒被她吓了一跳。
“小姐?您这是怎么了?穿这么少,还光着脚,会着凉的!”
是鹿又家的佣人,姓松本。
眼见松本急匆匆地从她的卧室里出来,为她拿来了外套和拖鞋。凉子动了动唇,也仅是乖乖穿上拖鞋,抓住了外套边缘,垂眸轻声道:“……谢谢。”
“您还是穿得太少啦,怎么只穿了一件里衣就出来了呢?这要是叫老爷看见了可得说您几句哪!”
“嗯……我会注意的。”
“对了,早饭我已经做好了,待会儿您洗漱好了就下来吃吧。”
松本全然没有注意到少女的异样,只顾絮絮叨叨了一阵,便又下了楼。
凉子望着她远去的背影,叹了叹,再满面纠结地回头望了望自己的卧室,沉了口气,这才回了房。
洗漱穿衣耗时连五分钟也没到。少女夺门而出,“噔噔噔”下楼去,气势汹汹地跑进厨房,又跑到餐厅里,在兄长惊异的目光中飞快说了一句“我开动了”,便埋头吃起了早餐。
鹿又诚一不知妹妹这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见她狼吞虎咽,便顺手卷过手中报纸轻敲过她的脑袋。凉子猝不及防,低呼出声,抬头瞪向“凶手”:
“哥你干什么啊!”
“我还问你干什么呢,”诚一翻了个白眼,“这么赶着要出门,是和谁有约吗?”
“没有啊。”她含混答道。
“那就是有事?”
手一顿。“……算是吧。”
“是么。”诚一没在意,揉了揉她的头,“那也吃慢点。吃太快对胃不好。”
少女抿了抿唇,眸中星芒明明灭灭,随即轻笑了开来:
“好。”
等到凉子出了门,诚一坐在位置上慢悠悠地啜了口茶。松本阿姨正巧从外进来,收拾着桌上的餐具,像是想起了什么,瞟了一眼门口,疑惑地说道:
“凉子小姐啊,刚才还跑进厨房里来了。”
“嗯?”
“抓了一把盐,又出去了。”
青年愣了愣,旋即放下茶杯,头疼地叹了口气:“……那个笨蛋。”
茶盏击在承盘上,“叮”的一声脆响。
—“他们”—
八百屋晓之助前脚刚踏出十文字家宅的大门,后脚便开始悔不该当初。他鬼使神差说出的那句“去图书馆找资料”,使得政纯掏出了烟管,眉眼间满是悠闲自得地说:
“那好,我就不用急着开门了。”
——意思就是愉英堂今天又不知多晚才会开门。
少年捶胸顿足,郁郁不已。无奈话已至此,要看书也只能泡在图书馆里了,虽然他对学校的图书馆没什么意见,不过毕竟不像愉英堂那样方便。
尽管事出突然,晓之助还是先去拜访了一下友人的家,得知朋友今日一大早便随教授一同下地考察去了,不免戚戚然,彬彬有礼地告辞之后,这才正式踏上了去向大学的路。
东京的街市向来繁闹,人头攒动,车水马龙。和服、洋服的身影不时交错,或是平民百姓穿着朴实、笑容憨厚,或是达官贵人乘坐马车,招摇而过,不同文化与社会阶层之间的碰撞在这条街上被诠释得淋漓尽致。
少年一路观察行人,站在十字路口边,有意无意地向前望了一眼。
那抹身影便如是住进了他的眼里。
少女身姿娇俏,神情严肃。并非遗世独立,却不曾湮没于茫茫人海。恰似一枝鸢尾,婷立在滚滚红尘中,似梦非梦。
须臾,一驾马车自眼前疾驰而过,引得行人纷纷大骂。他亦不由分心去注意马车,再回过神来时,倩影早已随马车消失在了街对面。
真是梦……?
晓之助揉了揉眼,竟不太敢确定亲眼所见。
不过,他还记得她——是那日在兄长店里同三毛乃玩耍的女孩儿。
那么,这股油然而生的冲动,便是源于“记得”二字所带来的感慨么?
似乎不完全是的。晓之助努力想了想,竟不太能记起她的名字。他叹了口气,心想,这次错过也许是个惩罚吧。
* * *
鹿又凉子很是焦躁。这种焦躁从她出门以来便不消反涨。
她已先后逛了不下五家古董店,竭尽所能地在每家店里徘徊了约莫五分钟,终究还是抵不住店主狐疑的神色,本想掏钱买些什么,却发现走得太急连钱包都没带。
天要亡我。
少女只好匆匆出了店,在大街上片刻不敢停留地快步走着,心里快速盘算起了现在能够去的地方。
徒然堂是肯定不能去的了。同理,愉英堂也排除在外——真是没钱就寸步难行啊。
学校呢?……不行。学校里栽了好几株洋槐,对她来说是威胁。
“阴魂不散啊你!”
她不耐烦地啐了一口,顺势拐进了无人的偏巷里,借着暗处向半空中狠狠撒了一把盐,这才慌忙走回大街上。
甫一在十字路口旁立定,耳畔又掠过一股阴冷的风,明显不同于自然的力量,冷得她一个激灵,眉间“川”纹便愈发深刻。
一辆马车突然自面前横行霸道地飞奔过去。路人们纷纷抱怨起来。少女并未有所反应,抬手拂去了扬尘,在没有明确目的地的情况下,只好一刻不停地前行。
也不知走了多久,额上蒙了一层薄汗。明明尚是冬日的阴天,温度却不似以往那般寒冷,也许真的要入春了吧。她强迫自己思考着事情,以期摆脱掉纠缠不休的东西。
直到一束鹅黄突然向她伸出了“掌心”。
凉子诧异地抬起头来。
铁制的栏杆横在眼前,而鹅黄色并不止那一束,它们绿叶作衬,簇拥成团,瞧准了栏杆之间的缝隙,争先恐后地钻了出来,风过时,还惬意地摇曳着满身嫩黄。
这大概是……茫茫冬日里为数不多的明丽色彩了吧。
从树与树之间望进去,可以瞧见齐整坐落的楼房外,穿着制服的男生们三三两两结伴而行——看来是一所学校。
鹿又凉子心下微动,张望了一番,在确认了正门所在位置的同时,还看见了原本死缠烂打的鬼魂正怯怯地望着她,对上眼神后,又状似阴狠地张牙舞爪。
少女挑衅似的笑了,趁其不备,连忙开跑,一路上招揽无数目光后,气喘吁吁地停在了一幢教学楼的门口。她又往回瞟了一眼,那鬼魂仍跟在身后,倒是距离远了不少。
好样的,看来它怕这里。
这所学校——这所大学较之凉子所就读的学校朴实了不少,栽种的多是些常青树,绿意葱茏。指示图没看错的话,此处应是图书馆。她正了正衣襟,神色如常地走进了馆内。
她进了就近的一间阅览室。室内沉寂,只听得脚步声来去,不时回荡着翻动书页的声音。
凉子也不自觉放轻了足音。书籍特有的香气扑鼻而来,引得她心痒痒,直上前去寻找着分类,终于寻见了自己昨日未看完的小说——大塚楠绪子的《忍音(しのび音)》。
她抱着书,踮着脚,正准备走出书架去向窗边的长桌,却又不禁停住了步履。
——黑发少年正坐在窗边,只手捧书,眉眼微垂。
不知何时,日光挣脱了束缚,恣意倾泻而下。淌至他身边时,竟不忍心惊扰,静静地,悄悄地,描过他的侧脸,吻过他的指尖,荡进他的眸里,化作一迹星芒。
薄帘随风微摇,摇动了一帘蜜花。
是他啊。少女恍然。
她还记得他。可她的心摇如悬旌,却并非源于“记得”这件事。
少顷,男孩儿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抬起头来,望向她所在的位置。
那双星目将她纳入视野之中,眨了眨,诧异如墨入水,迅速在他眼中晕开。
凉子不由赧然,捏紧了书脊,朝他微微一笑,这才走上前去。
少年定定地注视着她,随后轻声道:
“您好。今天真是个好天气。”
她一愣,慌忙瞧了瞧满目晴丽的窗外,再向后望了望一派寂静的室内,复又莞尔,低声回道:
“是啊。放晴了,真好。”
终于放晴了。她此刻浑身轻松,居然有些无法想象,前一刻自己还在外逃命似的奔忙。
而他怔怔地看了她片刻,掩饰般轻咳了一声,移了移视线,最终落回她的脸上。
“抱歉,我似乎忘记您的名字了。如果可以的话……”
凉子笑了。
“您好,我是鹿又凉子。”
——从“你叫什么名字”开始,后来,有了一切。
————————————
换了种写法,结果各种不顺利,顺便玩了两个梗
第一个梗是仿照情书里最经典的片段……嗯我对不起阿晓,完全没那种感觉otz
第二个梗并不是梵高写给弟弟的信里的原文,知乎上有细心人回答了这个问题,不过这段话我一直觉得很美,索性就用上了一点内容(喂
凉子遇见的花是澳大利亚金合欢,虽然花语不太适合,可是真的很好看,而且很符合时节(来自一个看过实物的人的保证(。
本来想发狗粮的,碰壁之后自暴自弃就成了这样(你
还是掌握不好写作的节奏,我我我我面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