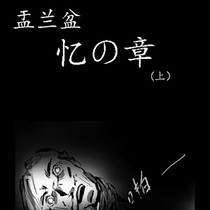うれし かなし
こひし にくし
想いは 万華鏡
さびし かなし
こひし にくし
絆は 蜃気楼
==============================
渴望,思念,孤独,怨恨……这绝不是人类仅有的感情
抱有欲念被主人抛弃的器物,在春秋时分,化为付丧神。
而暗怀心愿的人类,也在寻求着某种际遇与改变。
人与器物的命运与缘分,无论善恶,在踏入这扇门时开始。
欢迎来到徒然堂,
今天的你,也在期待着什么?
==============================
一期完结
小组http://elfartworld.com/groups/1381/
☆小江这次大概是没力气掐死我了,良心并不会痛
☆借用了一下虚方姐!大胆地响应一下!
明知故犯。
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头顶上的天空依然是蓝色,太阳没有变成两个,世间的一切也都在井然有序地依照着某种不可视、不可闻、不可触、唯可贸然揣度的法则运作着,仿佛只有他这一个故障的齿轮脱落下来,在长达四十五天的坠落中看见一个幻境。
即是说,可能其实不存在一位不顾御守的劝阻、把呼唤灾厄的物件买下来的松井先生,从没有摔碎的碗碟,没有掉下楼去的棉被和漫天的樱云。付丧神向来对自己——不论是记忆力还是任何别的东西——是抱有过少的自信的,加上这莫名其妙的打击来得是如此突然又绝情,因此他开不了口,他无论如何都无法理直气壮地对着眼前这位将他从徒然堂带出、现在却又询问着他是谁的人类青年开口,说出:我们明明是认识的。
“你没事吗?”松井虽然也是一头雾水,但看见年轻人动摇到这般地步,脸色一会儿白一会儿青好像随时都会倒下,反而担心起对方来,“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
“也许有吧,我不知道,我已经搞不清楚了。”时江最终这样说,他苦笑着,瞧着甚至有那么点泫然欲泣的意思,“我现在唯一可以确认的事情,就是我现在无处可去了这一点吧。”
他当然不会灰溜溜地回到店里,躺在柜架上等待什么[下一个机会]了,他可以向着天上那些从未护佑过他的神明发誓只有这件事他不会再做。痛楚对于名为鹤见时江的九十九而言是难以去忍耐、难以去承受的,不论是这副虚构的躯体为模仿人类生存而形成的生理上的痛觉,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失败过后于心底产生的撕心裂肺的痛苦,全都让他备受折磨。他害怕,而一个懦弱的灵魂惧怕疼痛也算是理所当然,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你无处可去的话,要不要先留在我这?”
青年沉默了一会儿,侧过身,做出了一个邀请的手势。这幢占地六叠、高有两层的旧式木屋的主人,就是这样又一次将不速之客迎进了家门。
就松井而言,他并不会主动关注别人的私事,然而这位暂住者不愿言明的东西似乎有点太多了。年轻人只报上了自己的名姓,虽是穿着华丽,但却身无分文;他好像懂得很多事,能够写字算账,又常对许多寻常物件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于是青年就猜测对方可能是从哪里的大户人家跑出来的少爷,毕竟这小伙儿往好听了说是不擅长做家务事,往不好听了讲就是笨手笨脚,还有点娇嫩。如此结论是三十二秒前得出来的,时江自告奋勇说要帮忙洗洗盘子,接着就在主人家眼皮子底下摔了一个,手心还给陶瓷的碎片划了一道见血的口子。
“很抱歉又摔坏了你的东西,松井先生,但我真没事。”如果他的眼眶没有红,这话听上去还挺有说服力,“反正没伤着……伤得很深,过几天就好了。”“还是处理一下吧。”
松井练过武,觉得自己也算皮糙肉厚,这点小伤不在话下。时江就不一样了,他拉着他往二楼走想找东西包扎伤口的时候,年轻人分外乖巧地跟在后面,什么话都没有说,大概是真的很痛。想着这些,他也就自然而然地忘了对方奇怪的说法、忘了橱柜里奇怪的空缺,忘了这两者之间的简单联想。他本就不是会为这种程度的异常就要追根究底的人。
而对于时江来说,他就算是做不了什么好事、也从来都是个会为主人多做考虑的付丧神,即使被冲击性的事实打击过度,花点时间总归能够重新振作,毕竟两人之间的缘分并没有终结,九十九可以肯定这一点(当然,为了这个[肯定],他偷偷跑回过两条街开外的古董铺专门确认过)。他算不上聪明,也不那么愚笨,几番推敲后总算是明白了对方态度改变的原因——松井忘记了一切与付丧神有关的事。他这是误把他当做了与他一样的人类。
这就不难解释很多事。鹤见心想。比如他现在拉着自己想要找东西包扎包扎,就是因为他忘记了自己就算受伤,只要没有损害到桃纹的御守,再可怖的伤口也能在几日内完全痊愈。
九十九切实地拥有着五感,但他们不会因此产生生理上的需求,单就这一点来讲就已经与人类大相径庭,更不用提人形与本体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又会产生怎样神奇的作用。因此“被视为人类”的体验是十分难得的,时江不可避免地注意到松井的话变多了,这个人不再是礼貌且疏离地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再是只在他犯下错误时才开口、与他进行着最低限度的交流,不再是、不再是用着和中学教师,和行脚商,和护士,和大学生——用着和其他契约者一样的目光看着他,把他钉死在他从未想要拥有的一切上,让他举步维艰。
瞧,他当真是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呀!自己并不作为他的同族存在于世的事实,源源不断的麻烦皆有来由的真相,还有自己分明就是在卑鄙地蚕食着他的平稳的生活,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他全都不知道、全都不知道啊……
“时江。”付丧神还不习惯听到别人喊自己的名字,他停下胡思乱想、万分迷茫地望过去,松井便耐心地又问了一遍:“还疼吗?”
他现在终于意识到自己这是沉默太久了,于是赶紧摇了摇头,视线隔着玻璃的镜片顺势落到手掌心细细缠绕的绷带上,粗糙织物的尾端是蝴蝶结拉扯过度后失败的模样。他想告诉他说已经不疼了,喉头却被尚未成形的呜咽声生生哽住,吐不出哪怕一个字来。
这之后的第七天的早晨,即是说鹤见住下来的第十三天兼第五十八天的早晨,年轻人和屋主人说自己等会儿要出门。于是松井把人送到玄关,他就是在这在这儿眼疾手快地扶住平地上也能摔倒的房客。青年看看惊魂未定的小伙子,估算了一下时间,最终还是改了主意、陪他一起走上后街。
五月的街道和四月时并没什么太大的不同,就算连续几日的阴雨停歇了留下一片鼠灰色的沉闷天空,空气也仍旧是湿漉漉的,它将行人与行人之间习惯性的沉默渲染得更加抽象。这次先开口的是时江,他以一种事先准备了答案因而期望他人问询的心境把另一个问题抛给同行者:“你不问问我去哪吗?”
松井则是这样回答的,他的语气一向平平淡淡,此时甚至还有些缺少感情:“你要去哪里都是你的自由,没有告诉我的必要,就算你要离开这里回家去或者哪里都——”“我说过我是无处可去的。”他少见地以略显强硬的语气打断他的话,“除了你这里,我没有任何可以‘回去’的‘家’,我不会对你说谎话,松井先生,所以请不要——”鹤见仿佛被人掐住脖子一般突兀地停下来,“……抱歉,我太激动了。”“没事,我不在意。”
青年伸手,时江的个子比他还高些,所以他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后背,这时候他们已经到了路口,他要离开,他也该回去开店了,只是年轻人那副焦急的模样触动到了什么,让他有种难以忘怀的复杂感受。他可能是知道他想说什么的,也可能不知道,他无法确定。
“路上小心。”松井顿了顿,补了一句,“早些回来。”
他猜测这句话是说得对了,因为小伙子总算笑起来、回了声好。
至于付丧神打算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毕竟失忆不是正常现象,既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表现出痊愈的征兆,那么前去咨询专业人士之类的简单事务,就算是他也不至于做不好。
“欢迎光临。”蕪木虚方听到铃铛响,她从椅子上站起身,发现来的是位有些面熟的客人,“哎呀,您是——”“我是那枚招来厄运的御守,蕪木小姐,去年秋分化的形。”付丧神礼貌地点点头,“先前来得匆忙,没有和你打招呼,还请原谅我的失礼……不过这次来访也还是因为我的主人的异常情况,他仍然没有好转。”“那确实很奇怪,狂鲤已经被打倒了,造成的影响也就应该消失了。他的症状是什么?”“失忆,他忘了和九十九有关的一切。”“你是说,他也忘了你吗?”“是的。”鹤见默不作声地移开视线望向窗外,“虽说如此,他也并没有抛弃我,只是把我当做普通人类收留了下来。”“那还好,这样说不定还好办些。”
现任咖啡馆管理人的前·清净屋看出付丧神的疑惑,她如此解释道:“他还能够看见你,那你只要告诉他他忘掉的事情就好了,九十九能够唤醒被狂鲤蛊惑的人,你肯定也可以。”
“只要告诉他,他就能想起来,是吗?”年轻人重复了一遍,“这么简单就可以?肯定还需要别的吧?毕竟,对,我的主人的情况有点不同,他受到的影响比较严重不是吗?不然怎么会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如果真的这么简单就能解决的话,我也不用烦恼那么久了呀?”
“可是你并没有尝试过这个方法吧?”虚方不由得因为对方奇怪的反应而疑惑起来了,“不如说,都过了这么久,为什么你没有试着告诉他——”
时江没能听完这句话,仿佛是将眼球内部的水分瞬间蒸发殆尽一般的剧烈疼痛毫无征兆地灼烧起神经,他哀嚎着倒在地上、鼻梁上架着的眼镜也不知道掉到了哪里去,他挣扎着滚动、尔后瑟缩成一团不受控制地震颤起来,而没有了任何阻碍,手指便毫无顾忌又神经质地狠狠抓挠眼周,指甲在脸颊上划出道道伤口,他这是下意识地想要将痛苦的源头从身体上挖出来以结束这可怕的折磨啊!然而勉强保留下的蛛丝般的理性又勉力拉扯着神智去阻止躯体实践自残的行径,他没有余裕去思考,只有期求这一切能够结束的念头残留在脑海——
也确实结束了,如潮水般席卷而来的痛楚在长达千万年的数秒后也终于如潮水般猛然退去,九十九喘息着扶着墙壁站起来,他不知道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被他吓到的虚方这会儿正为他匆忙奔找着店里的修缮师。年轻人摇摇晃晃地拾起豁了口的物件挪到店门口,他的眼睛不好使了、什么都看不清,所有的所有的一切都在歪曲的视野黏黏糊糊地溶解着混杂在一起,整个世界之中只有松井的声音依旧清晰。
他对他过说早些回来,所以他这就要回去了。
青年注意到自己的房客自从出过一次门之后就有些不对劲,时江开始经常用想要说什么的眼神看着自己,但出口询问的话也只会得到沉默的摇头作为回应,此外,他偶尔会看着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发呆,还会伸出手去,做出抓住什么东西再松开的动作。会不会是回来路上摔到了头?松井如此推测,而这个想法在看到对方豁口的眼镜之后变得更加坚定了。
“你找到它了。”他指指对方手里的遗失物,“这不是都坏了吗,要不要去换一副?”“还能戴,就不用了吧。”“不会妨碍到看东西吗?”“………………能妨碍到就好了……”“什么?”“没什么。”年轻人从房间角落的位置站起身来,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时候,他就会待在那里,“那个,虽然很突然,不过今天能让我帮忙洗碗吗?”
考虑到上次答应这个请求的时候发生了流血事件,松井本来是想要拒绝的,可时江说这话时的神情是那样认真、甚至带点孤注一掷的意味,他也就只好先一步将绷带准备好以防万一。只是出乎他的意料,搞不好也出乎小伙子本人的意料的是,他这次什么都没摔坏,八个盘子,三个碗,两个杯子,什么都没摔坏,全都完完整整、干干净净地排列在壁橱里。
想做的话不还是做得到的吗!松井对时江这次的完美表现十分满意,他侧过头想要再说些什么、或者夸夸他,可当他看到年轻人脸上的表情的时候,这些话就讲不出来了。
……也不至于开心到哭出来吧……他轻轻拍了拍他的背,不禁这样想到。
鹤见时江知道只要他不开口,松井就会继续将他当做人类来看待,不会将九十九的概念回想起来;他知道这之后后院更后位置的灌木会无故地枯萎,常青的树木会惨遭雷劈;他知道只要他想,他就不会再摔碎任何东西;他知道他看到的是什么、抓在手中的又是什么。
【我其实什么都知道。】他听见自己这样说,即使他并没有开口,【我就是因为知道,所以才会这样做的。】
付丧神一觉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五月二十五日的傍晚,他披挂着屋主人借给他的毛毯从榻榻米上爬起来,看见自己的结缘者正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用他再熟悉不过的目光看着他。
“……九十九也会做梦吗?”
松井平静地提问,而被询问者以微笑作答。
他看着摆在自己面前的碗筷和饭食,露出了万分不解的神情:“请问这个是?”“我看你一直没有吃东西。”这么说着,松井在他对面的位置坐下来,“虽然只是粗茶淡饭,但应该也能填饱肚子。我的手艺还是不错的。”“可是我——”“恩?”“啊,不,没什么。”
他没有进食的必要,他并不是依靠食物存活于世上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包括松井,所以他从没有得到过一个机会去尝试所有人类都会尝试的吃东西这件事,好在他已经千百遍地看过别人重复这个过程,所以他能够顺利地拿起筷子、搛起一筷子的菜肴送进嘴里、咀嚼、吞咽,而不使眼前的人的心中升起疑虑。
他确实这样做了,然后狠狠呛住,止不住地咳嗽直到喉咙里泛起腥甜的味道。他向松井摆摆手,示意自己并无大碍,等到能够正常说话了,他耐不住激动地开口,他记得人类在遇到这样的状况时应该给出怎样的感想:“好吃……!”
“好吃你就多吃些,就是吃慢点,不要再呛着了,饭的话锅里还有,你放心吃。”
他看见松井微微地笑了笑,在此之前他从未见他这样笑过,他开始希望时间能够停留在这一刻。
丝线于此刻扭成第二个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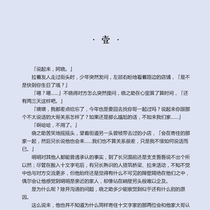

1888年某个隐秘、潮湿又狭窄的暗室,她出生。那个夏天有无数只蝉死去,而她诞生在女人的尖叫后,那久久的尖叫如同蝉鸣,划破了整个夏天。
那之后过了很久,年复一年的夏天来来去去,唯独不变的是本港炎热潮湿的天气。也许还有,味道不同却颜色如一的灰白色烟雾。
她是什么时候开始吸烟的?捞出外套里金属质的铂金色烟盒,舶来品,三十块钱。手指转动烟盒,随意挑开,抖出定制的女士烟,她再熟练不过的动作,轻佻又冷清,这个动作发生在她身上本就是矛盾的。接着她微微张开唇瓣,塞进那根烟,动作大得有点粗鲁,显示出她的怒气,继而手指一划,燃起一根火柴点烟。在风中摇摆不定的火光,与洁白的烟身接触后马上被熄灭,它存在不过三秒,马上化作烟雾散在空气里。
她深吸一口气,烟通过气管进入她的肺部,一时间她胸腔疼痛,喉咙似乎断开,仿佛她只剩大脑,余下部位被一切两段。这样也很好,她勾起唇角,有些促狭地想,这样她就没必要因为日益发育的身体被当作待价而沽的商品,受到杨太异样的眼光。
嘉玲想起来,那时她十二岁。逐渐成熟的年纪,胸部有一点点隆起,脸侧细小的绒毛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轮廓模糊,她才刚过完十二岁生日。
她讨厌夏日,毋庸置疑。苍蝇狂欢的季节,汗淋淋的季节,她为什么要喜欢?她能想象一切不美好的东西都在夏日,她痛恨的夏日,她不得不出生,不得不在夏日生不如死。
嘉玲穿着一身很普通的浴衣,浅绿色竹纹印在衣摆,腰后扎起一个素色的结,她挤在人群中生不如死。现在是她讨厌的季节,而让她更痛恨的是夏天的传统节日。
祭典,多么好听的名头,人们总是能借不同的名义庆祝。她费力地从成群结队的人们中穿过,将将要达到对岸的空地,突然间万物俱静,她厚重的呼吸明显得要掀翻她的脑袋。
晴朗得容不下一丝云的夜空闪过一颗星,只划过一瞬,快得只瞧见它拉长的尾巴。有人看到了,也有人没有,嘉玲只觉得眼睛一痛,她眯起眼睛,试图缓解疼痛。紧接着又一颗星下落,天的那一边仿佛崩塌般,无数颗星星坠落,静静的河面倒映着这幅景象,星星就好像掉进这条河里,熄灭了。
那应该是这个夜晚最沉默的时候。所有人都止住了呼吸,嘉玲多希望能停在那一刻,但随后当人们反应过来的时候,议论声惊呼声大过一切,她觉得头更疼,似乎最初那颗流星坠进她眼中后将她的脑袋从中间劈开。
噪杂的交谈声,在这片夜色的衬托下带着许多希望,人心沸腾。一年一度的节日,死者的灵魂回归的日子,那或许真的是也说不定。既然这样为何不一起带我去,嘉玲心下一片烦躁,咬了咬下唇,手指捏紧衣袖,她面上还是那副波澜不惊的冷脸,看不出她急需一根烟压下她不定的情绪。
空气凝滞沉闷,人群的呼吸重重的阻碍了风的前行,这就是夏天,闷得人透不过气。嘉玲转身,试图向人群稀疏处前行,她的正对面,站着一名青年人。
显而易见,那位青年大部分的脸庞掩在拉低的帽子下,而他下巴的轮廓苍白又清晰,瘦削得像是锋利的剑刃,唇抿着,用力得狠了,连带着唇线都看不明晰。他穿着特别,西洋人打扮,但他的脑后露出得一点翘起的头发却是那么黑,浓重的阴影般。嘉玲不禁停下脚步,侧过身仔细观察他。他腰杆笔直,不属于祭典这样热闹又平凡的地方,他——应该生而不凡。
这样奇特的人突然抬起头,偏向嘉玲这侧,正巧直直对上她的眼眸。这才终于看起那人的全貌,却是比想象中更要清秀的五官,单薄的面孔,一切都藏在这里,嘉玲后知后觉的意识到,原来那是位女性。
黑崎注意到身后那道视线有些久了,她才有些不快地转身去看视线的来源,被人瞧见纯属意外,她一点也不想理会。她正忙,夏天到了,唉,夏天。她第一次经历这块土地的夏天,四面被海包围的夏。
正巧对上对方的眼睛……不是那样的。眼睛藏着一个人所有的想法,是通向未知世界的秘密入口,而且说话时看着对方的眼睛才算礼貌。黑崎看向对方的眼睛,想也不用想就轻易地找到眼睛的位置。
如果说一颗流星的坠落代表一个人的死亡,那么眼睛里的流星则代表着人对死亡的渴求。那双眼睛,藏着流星。黑崎眼前有片刻模糊,她对总是能看到这样的眼睛感到厌烦,也对那本身无可抑制的痛恨。
不止一次,眼中飘忽不定的星星划下,一颗一颗像在给人生划下休止符,无聊透顶。这样的场景总是带她回到那个年份,第一次呼吸的时候,记忆是那样清晰又模糊。
这一刻,人群的另一边,少女的眼睛一眨不眨,其中一颗将要落下的明星挂在她夜幕般的眼里,黑色的浪潮般的眼睛,要将那颗星星带下。这一边,黑崎握紧拳头,止住愤怒带来的颤栗,以及无边的厌烦。这一刻谁都没有动,人群化作一道道拉长的速度线,压在两人的中间,世界好像只剩下加速后尖锐的风声,她们对望着,一句话也没说。
*先打卡,能补就补上吧
T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