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企划是以东出佑一郎所作的Fate/Apocrypha为蓝本,综合fate系列作品构架的设定和世界观,所创作的同人战斗型企划。
已满员,感谢各位热情参与。
“圣杯战争真的有在进行吗?”
声音不大,却因为建筑结构的原因,一直徘徊在位于圣马洛北部这栋中断工程的废楼中。
似乎是察觉到德拉甘携Rider踏入此处,才开口向他们搭话,同时声音的主人也从月光无法触及的黑暗中缓步走出。
面对突如其来的质问德拉甘,一言不发,不知道是一如既往的缄默,还是现实令他哑口无言。
虽然确实有过几次可以称为前哨战的战斗,但是以这座城市为战争舞台的两股势力始终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正面冲突,就连彼此试探也开始稀少起来。
“你就再等等吧,‘雇主’先生,你仔细闻闻看,流经城市的风已经变得越来越粘腻,再用不了多久,即使竭力避免,战争也不会中止吧。”
尽管Rider在用戏谑口吻陈述,但他所言俱是事实。因为有和他相异的“立场”,在数次巡视城市后,作为搭档的德拉甘才能从另一个角度的观点印证Rider的观点。
“Rider的观点可靠吗?”
被称为雇主的人向德拉甘发问,得到了对方以点头代替言语的回答。
“你也做一些准备吧,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被卷进战斗里来呢!”Rider笑嘻嘻地说着。
“我这边你们不用担心……虽然这么说,但是真有什么万一我也是藏了几张底牌的,在支付你们报酬之前先从自己的人生退场的话,可就贻笑大方了。”
他一边笑着,一边走到距离其他二人非常近的地方,在月光下,他的身影渐渐明晰起来。
如果有其他眼睛一直关注着这三个人的话,很快就会发现所谓雇主的这个人,正是数日前出现在某家咖啡店中,邻座那位坐在老人对面的年轻人。
面部轮廓缺少起伏,很显然是一副东方面孔。
“不过就这么一直躲着也很没劲啊……因为缺少运动,我这几天都有些发福了,所以我打算明天出去转转。”
“冒险行为还是适可而止比较好哦,太过火的话德拉甘会生气。”
“……我没那么易怒。”
“放心放心,我尽量不给你们添麻烦,但我再怎么说也得到台前晃悠一圈意思一下,抱歉,今晚你们就先陪我一下吧。”
说完,青年经过两人,缓缓走向外面。
走出建筑物时,走在最后的英灵已经灵体化,隐没了自己的身影。
以这个夜晚为分界线,圣马洛将会进一步迈向混沌?还是会因为个别人产生变化的行动而早一步产生终结?我们不得而知。
姑且,在这里拭目以待吧。
【移动:据点——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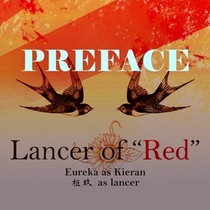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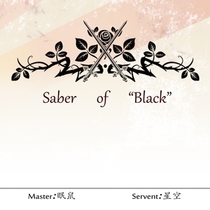




打卡
用十几分钟紧急打卡的小作文
————————————————————
混乱,悲哀。
这是希瑟来到这个空间后的第一印象。
她依稀记得上一秒的自己正在酒吧,眼中映入的是金发的女人与一个空掉的酒杯,耳边传入的是喧闹的音乐,皮肤所接触的是自己再熟悉不过的魔术材料。然后就是许多的黑色物质,将所有的记忆抹去,耳边也变成了自己少有接触的电器发出的兹兹声。
剧烈的头疼使她不能进一步的思考。
她唯一清楚记得的就是突如其来的失重感,就像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爱丽丝最初跌入兔子洞那样,她跌入这个空间。虽然她也有可能是从地中突然冒出的。
她观察了下周围的环境,作为了解这个“仙境”的第一步。很遗憾的是,这里并没有什么可以吸引人的地方,昏黄的天空,呼啸着的风,偶尔被卷起的沙粒,以及那弥漫在躁动空气中的血腥味,无不提醒着她这是一个战场。
希瑟从小读过很多书,自官方认证的专家编写的史书所记录到网络上某不知名作家所描写的战场,没有一个可以与现在她眼前的匹敌。或者是用地狱才能形容眼前的光景,不,地狱这个词也太过于轻巧了。
圣杯战争也会变成这样吗?
看着这些的希瑟心里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惑。或许吧,或许能够成功的守护住自己的家族,或许会被全身贯穿悬于高空。她摇了摇头,糟糕的想法也随之溜走了。
她站起身,因为她在这荒凉的山头瞥见了熟悉的身影。
疲惫的骑士身着银白的盔甲,手中的长剑沾满血液却依旧锋利,不带有任何同情的斩向敌人。
这才是他原本的样子吗。少女在心中询问着自己。
到底是为何?
是因为荣誉、怜悯、英勇、公正吗?
是因为背叛、冷漠、怯懦、愤怒吗?
她无从得知。
希瑟自以为很是了解自己的从者。她读过与从者有关的书籍,她翻阅过与从者有关的资料。她以为已经足够了解,了解他的传说。
她看见无名的士兵从人堆中爬出高举手中的武器。
“[ ]——!”
她看见赤红的花在灰白的石上燃烧。
帮黑C组上传,黑C组暂时还没有ELF账号。
=================================
尤利安在唱歌。
虽然歌声时有时无,虽然曲调断断续续,但她确实是在唱歌。
这间位于巴黎19区的地下室狭小、昏暗,孤零零悬在中间的电灯在角落处留下了过多的黑暗,尤利安用水银溶液补上魔法阵的最后一笔,然后自上而下地注视着自己的杰作——消去中画上“消灭”、“退却”四个阵即为召唤之阵,这作法她在脑内实践过许多次,不可能出错。她又拿起一旁已经研磨得极细的硫粉,一点一点洒进地上的水银里,她往上加施了一个升温的魔法,使水银和硫更快进行反应,黄色粉末甫一落下就从液体里升起凝固的黑。她看着被黑线重新描画了一遍的魔法阵,不禁笑了起来,那断断续续的歌声也变得更大声些了,让人能听清含糊不清的歌词:
“……Debout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La raison tonne en son cratère …C’est l’éruption de la fin……”
她就这么一句一句地唱着国际歌,时而停顿一小节,之后又从这一句的开头重新开始。尤利安出生在东德,这个国家的每一天伴着国际歌开始,又伴着国际歌结束,她就出生在这当中某一个广播里播放着国际歌的时刻。很快两个阔别已久的国家合而为一,可她的街区又因政治体制的转变而陷入了混乱,“融合后的阵痛”,是的,他们管这叫阵痛,从物质紧缺到失业,在这些痛苦里沉沦的人们不是个体的人,而是历史潮流中模糊了面目的消耗品……于是她继续唱着国际歌,从出生开始,唱过童年、唱成少年又唱成青年,离开父母去主家时哼着这个曲调,又哼着它回到欧洲大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死神也会哼着这个调子来找她。“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这个明天到来了吗?没有,永远没有,威权主义社会垮台了,资本主义又卷走人们的时间与金钱,人民永远痛苦、永远天真、永远在痛苦的两极里震荡着,她上过街、抗议过、也走到过那些被侮辱与损害的人中间去,然而她看得越多,左翼的理想宣讲得越多,她越觉得不知所措。怎样可以消灭苦难?平等、公义这些理想怎样才能实现?她不知道,她的伙伴不知道,就连那些提出左翼理念的人也无法提出解决方案,所以尤利安永远走在没有终点的道路上,所以尤利安永远唱着国际歌。
但若世俗的斗争无法解决,总有一些超乎常人想象的方法可以带来希望。
转机发生在三个月前,尤利安截下了一封寄给戈德斯坦主家的信,寄信人是阿本德罗特家的家主。阿本德罗特与戈德斯坦一样都是曾有过辉煌而今却日渐沉沦的家族,两者忽然通信,必定不会只讨论今天天气真好,于是尤利安拆开信封上的火漆印,而后,一份馈赠降临到她身上。
这是一封圣杯战争的邀请函。
圣杯,传说中能实现一切愿望的愿望机,只要赢得圣杯战争便可获得圣杯的使用权。而阿本德罗特邀请戈德斯坦参加的,又与在东木发生的、由七名御者与七名从者互相厮杀的圣杯战争不同,阿本德罗特希望能将七名英灵全部据为己有,而后以这七名英灵的力量向魔法协会发起战争。于是他发邀请函给所有日渐没落的家族与对魔法协会中高高在上的贵族们不满的人,希望以他们的力量来一齐打开大圣杯,向魔法协会全面宣战。
倘若是能实现一切愿望的圣杯,那必定可以消灭世上所有苦难;而这场圣杯战争本身的意义,就是为了反对魔法协会那些以出身论否定一切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小家族的腐朽之徒。这是一场魔法界的革命,尤利安最终下了这样的结论,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战争更适合尤利安了,她生来便是为了此道,倘若一场革命是模糊却炽热的火焰,那她愿意当其下的木柴——“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而戈德斯坦,那个总是挂着一副鄙夷的神情、每天想的只有怎么让自己那小小的家族重现虚幻的光荣的自私鬼家主,圣杯给了他又有什么用呢?最后往复循环的,只有人类的贪欲与无尽的战争,一切都不会得到改善。
这场战争应该给世界带来更好的。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在此之前,尤利安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能参与圣杯战争。戈德斯坦向来是一个小家族,十九世纪时出现过一段时期的辉煌,如今则日趋没落,纵然家主心存不甘,想要make Goldstein great again,但衰落也无可避免。上一任家主为了重现辉煌,将所有旁系里资质尚可的孩子都要到主家来统一培养,尤利安是其中一员。她的父母在社会主义的强压下早已忘了什么是魔法,但他们不希望尤利安继续留在混乱的东德,于是他们同意主家的要求,将尤利安送往英国。
年幼的尤利安还为踏上异国而兴奋,更别提她是以一个魔术师的身份,社会主义国家可容不下魔术;然而随着年岁渐长,她愈发为此地感到不适。那些戈德斯坦家的魔术师个个挂着虚伪的笑容,眼睛里却都是无法掩饰的蔑视,他们看不起彼此,却又需要利用彼此,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那个能让戈德斯坦家复兴的天选之子,每个人都能讲出自己的一千条理论却又禁止他人谈话,就连孩童都被规训得压制一切、反对一切,陈腐空气与熏香芬芳混合在一起,几乎让尤利安窒息。当你们在这里夸夸其谈的时候,你们的亲戚在挨饿、在受苦,你们凭什么能站在这里什么都不做?你们凭什么让这个家族强大呢?尤利安这么想着,甫一成年她便逃出了英国,重又回到欧洲大陆。
她不是戈德斯坦家当初集合的那一批孩童里魔法回路最好的一个,却也不是资质最差的,主家也对她的叛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唯一幸运的是她有着一项被这个家族的魔术师都弃若敝屣的东西——一个不错的脑子。哪怕是去普通的大学读了自然科学,她也没有完全放弃对魔术的研究,在叛逃后她开始监视着戈德斯坦家,戈德斯坦不会满足于现在的地位,有朝一日他们必定会为更大的光荣而战,她若介入他们的战争,倘若不能捞到一些利益,也能将戈德斯坦家彻底摧毁……
可她没想到他们采取的方法会是圣杯战争。
尤利安算不上一个优秀的魔术师,魔术用来防身尚可,但用来战斗?她很少伤人。在给阿本德罗特回信之后尤利安伪造了一份记录,向学校提出延迟毕业的申请,从而暂停了此后一年内的所有学业,之后便租下19区这个鱼龙混杂处的地下室改作自己的工房开始着手圣杯战争的准备,她翻阅了所有能找到的与魔术相关的书籍——包括当初她从戈德斯坦家带出来的、学习战斗的方法、制作可以用来应急的礼装、委托朋友找来可靠的圣遗物,诸此种种。三天前她看到手臂上出现称作“令咒”的红色印记时不禁跳了起来,这是圣杯认可其作为圣杯战争参与者的证明;而阿本德罗特家也还未发现与其接洽的不是戈德斯坦家当任家主,只是某个流落在外的叛徒魔术师。
一切顺利,眼下唯一需要担心的便是召唤。
她又抓了一把盐,撒到因加入硫而变黑了的魔法阵上,水银、硫磺与盐,炼金术的神圣三元素,代表了命运轮的三个方位,用这三样东西画成的魔法阵应该能召唤出足够强的英灵。之后尤利安拿起一旁包裹在白布里的圣遗物,这件圣遗物是她的一位二手古董商好友找来的——“关于那位国王的传说真真假假,我们也分辨不了……”那位古董商不停地道着歉,最后却还是拿出了尤利安想要的东西,“但这个应该是真的。”
尤利安剥开层层缠绕的白布,她拿到的圣遗物只是小小的一片金属,据说是查理曼大帝的佩剑Joyeuse的剑鞘上损坏脱落的一片。就欧陆而言,能召唤到的最强英灵莫过查理曼大帝,倘若能成功召唤出他,不仅在战力上足以弥补尤利安本人的缺憾,其强大的力量也大大增加了获胜的概率,尤利安无比希望延续至今的强运能继续延续下去。
她最后确认了一遍魔法阵,画法没有错误,也没有任何歪曲或斑驳的地方,而后她将那片小小的金属放了上去,金属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锈迹斑斑,但从锈里暴露出来的部分能看出其原本工艺之精湛。国际歌的歌声停在了“Le soleil brillera toujours”一句,一切准备都已作绪,尤利安沉默地望着魔法阵,她摸了摸左臂上的纹身,“liberté、égalité、fraternité”,然后是其下鲜红如出血的伤口的令咒。
这是从无解的困局里跳出来的唯一机会,越过这场战争便可看到理想的光明世界,一个尤利安愿意赌上一切去换来的世界。
不应该有任何犹豫了。
“满盈吧,满盈吧,满盈吧,满盈吧,满盈吧。”
“周而复始,其次为五,五然,满盈之时便是废弃之机。宣告汝身听吾号令,吾命与汝剑同在。”
昏暗的房间慢慢被魔法阵发出的光所照亮,复杂的音节回荡在空气中,魔力自尤利安的身体里被拉扯而去,脚却像生了根般的矗立在此,尤利安恍惚间有种自己将要被撕裂的错觉,她强迫自己看向面前愈发大放光芒的魔法阵继续下去。
“应圣杯之召,若愿顺此意志、此义理的话就回应吧。”
让这光芒照亮所有苦难,所有不自由。
“在此起誓,吾愿成就世间一切之善行,吾愿诛尽世间一切之恶行。”
毁灭世所不公,消灭世所苦者。
“吾即手握其锁链之人,汝为身缠三大言灵之七天,来自于抑止之轮、天秤之守护者!”
而后光芒更盛,尤利安用手遮蔽着双眼,她扶上一旁的墙壁好让自己不彻底倒下去。白色的光芒中复又浮现出金色光芒,那金色逐渐成型为一个人影,自明亮得如同太阳般的光芒里、自这无限美丽之巴黎的某间地下室里,重现那曾在法兰西上空回荡的声音:
“召唤郑重现法兰西的,可是汝?”
尤利安躺在地下室之上的某个房间里,痛苦地捂上了双眼。召唤出来的那位英灵被她暂时安排在了隔壁房间,但显然这位国王对这间旧公寓的环境十分不满,打开房门便咒了咒眉。她准备好了一切,也检查好了一切,这应该是万无一失的,却没想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将她的计划导向了完全不同的地方。
问题的根源在那圣遗物上,Joyeuse虽是查理曼大帝的佩剑,却也是法国国王世代用来加冕的剑,因此她特意向那位古董商反复确认这金属片是来自公元八世纪的,但目前看来在古董商面前利益大过了友谊,这碎片的年代也十分存疑了。
所以该感谢他好歹没有给赝品么?尤利安自嘲地想着。她回想起召唤时的场景,召唤出来的那位国王有着比起常人显得过于矮小的身材,面目用金色的面具遮挡住了,唯有一双灰蓝色的眸子露了出来,身上穿着繁复的十五世纪行军服,然而黑色的袜子下脚踏的却是一双高跟鞋,就连盔甲上都系着一个红色的蝴蝶结,这样的服饰比起行军打仗,似乎更适合用来做展示。
而且这真的是……太gay了!想到这里尤利安更用力地捂住了眼睛。她在看到这样一位英灵之后愣了两秒,从而失去了发问的机会,反倒是那位国王皱起了眉,问道:“汝即为郑的master?”尤利安这才反应过来,她低下了身子以拉低二人之间的距离,然后指着上臂的令咒说:“我是召唤你到现世的master,名为尤利安·戈德斯坦。”
“郑名为路易,乃Caster职介的servant,汝将郑召唤至现世,郑便将你视为master。”
尤利安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后更仔细地打量着这个英灵,身材矮小、路易、身材矮小、路易……忽然她睁大眼,她知道这是哪一位国王了,他虽然不是如查理曼大帝那般战斗力强悍的英灵,却在知名度上丝毫不逊于他,尤利安差点激动地握住拳,这实在是天赐的幸运,幸好在这么多的路易中,偏偏是这位路易响应了她的召唤。
这时路易看着她又皱起了眉,他似乎无法忍耐他人没有立刻做出回应,他刚想开口,尤利安便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我希望能夺得圣杯。“
“原因?”路易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调侃的意味,“你有什么愿望一定要借助圣杯?”
尤利安看着面前的国王,他面上的金色面具象征性的刻了一个棱角分明的唇形,显得冰冷且讥讽。一位封建王朝的领袖,一位俯视着王位下的一切的上位者能否理解这种理想?“我希望能消灭世上一切苦难。”她最后还是如此答道,“我希望能打造出一个没有贫穷、不义与不公的法兰西,每个人都有幸福的权利,且都能得到幸福——不,不只是法兰西,而是全世界。”
路易灰蓝色的眸子暗了暗,然后他长久地盯着尤利安,直到尤利安差点放弃与之对峙,想要直起身来时,方才开口:“我不赞同你的理想。但我会全力帮你达成。”
直至现在,尤利安仍觉得召唤的过程如梦似幻,那真的是借由她的力量来到人间的灵魂吗?她借着窗外投入的灯光看到手臂上鲜红的令咒才有片刻实感,它不再像流着血的伤口了,更像结了痂的,她已经召唤出了一个国王,尽管这个国王看起来不完全赞成她,但怎么能希望一个上位者真正为人民而战呢?所有宣言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自上而下的改变都是过度美化的幻想……既然路易也表达了战斗的意愿,那接下来要做的只有战斗,不停战斗。
她伸开手,五指在微弱的灯光下显得冰冷且易折,而后她将手指紧握成拳,抓住那窗户里透进来的一丝光。
“汝要去哪里?”
尤利安正在把最后几件衣物放进行李袋内,地下室的东西她也已经收拾好,路易靠在门边看着她把房间清空。“我们要横穿整个巴黎,去蒙帕佩斯车站……”尤利安答道。
“去哪里?”
“圣马洛。”尤利安拉上行李袋的拉链,“你对这个地方有印象吗?”
“……英国和荷兰的海军经常骚扰此地,郑唤沃邦卿于此修建了防御要塞,替郑抢先这两国的占领圣马洛的海盗首领也是从此地出发的。”
“那看来这个选择还不错。”尤利安点点头,然后她背上行李袋,“该出发了,我们要在蒙德纳斯车站坐TGV。”
“TGV?”
“……我以为你们在英灵座里至少会了解一点当代生活。Train à grande vitesse,高速列车,就是能很快去往圣马洛的交通工具——”
“郑知道高速列车是什么。”路易近乎生硬地吐出这句话,“郑知道现世的生活大概是怎么样,但这就如同雾里看花,如TGV般具体的缩写是不可能了解到的。”
尤利安又点了点头:“行啦,我低估你了,皇帝先生。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吧?”
“不。”路易一反常态地轻轻摇了摇头,语调也变得异常地柔和,“郑想请求master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尤利安握紧了行李袋的带子。
路易没有急着回答。他先摘下了一直戴着的金面具,露出其下的真容,这张脸也令尤利安疑惑许久,太阳王绝无理由隐藏起自己的面容,当她看见面具下的面容时终于理解这一切的理由——这是一张太过年轻的脸,像是一位方才褪去稚气、迫不及待想要证明自己的少年,虽已有了足够稳重的神色,但从细微处总能体会出几分因早年的流亡而留下来的惊慌,站在她面前的这位虽然是经历了一生的伟大国王,其外表却仍然是在反对、蒙骗与贪污中刚刚亲政的年轻国王。“郑想用实体看一下今日之法国。”
“也不是不可以……”尤利安思索片刻后回答道,“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说吧。”
“请改掉你那使人厌烦的称谓。”
路易又沉默了片刻,似乎是在思考这要求的含义,而后开口道:“请允许吾——”
“不对。”
“……请让我——”
“可以,可以,没问题。”尤利安笑了起来,但她看了一眼路易后面色又沉了下来,“你的装扮要改一改,这样会让人误会。”
“误会些什么?”路易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装扮,“郑——吾,我的装扮是欧陆之风范,王室之表率。”
“这可已经过了四百年了,皇帝先生。您若是这么穿着出去,会让现世的人误会您是和您弟弟腓力一样的人……”
路易的神色又难看了几分,他拉下了唇角,而后才点点头。所幸尤利安平时因版型剪裁而买了一些男装,都是普通的套头衫、外套与牛仔裤,虽然在路易身上显得有些大了,却也不是不能穿。尤利安看着换完装的路易,觉得愈发不对劲,她想了想,走过去将路易的长卷发扎了起来,而后又想了想,从包里掏出了一副黑框眼镜给他戴上。
“行啦,这样你看起来像会活得久一点。”尤利安又笑了出来,“看起来还像个艺术家。”
“我那个年代的艺术家可不会留这样的卷发——”
“已经过去四百年啦,皇帝先生。”尤利安打断了路易的话,而后突然像是想起来什么,又补充道,“对了,我忘记说一件事了,因为我只买了一张TGV的票,所以到了火车站请您继续灵体化……”
“……礼节,madamoiselle,礼节。”尤利安看见路易极小幅度地翻了个白眼,“至少请做到诚信对待他人。”
尤利安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她看到站在一旁的路易时再次感到惊讶,他就那么站在那里,却只有自己能看见他,多么神奇啊!她看向自己的左臂,衣物遮挡住了那鲜红的令咒,但尤利安却仿佛依然能看见它,那时刻提醒着她,她不再是这茫茫人潮中普通的一员,此去是要迈上战场,她要去实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理想,这是她这一生最大的赌注。
火车启动后尤利安开始整理关于圣马洛的情报,她时不时看向路易,按照caster所说,这里是他曾建筑防御工事的地方,虽然caster在海军的交战中从没占到好处,但他在此的名望也十分可观。路易只一直靠在椅子上,他眼睛望着窗外,看着所有的城市与田野,专注得如同凝视最爱的情人。
“你很喜欢现在的法兰西?”尤利安掏出手机,装作是在打电话,以便和站在一旁、灵体化的路易说话。路易点点头,而后又摇摇头:“说不上喜欢,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对我来说很奇怪。但这很繁华,是很好的法兰西。”
尤利安无奈地笑了笑:“毕竟是皇帝先生,总得为自己的阶级利益发声,没有离不开国王的国家,也没有不会反抗来自贵族阶层的压迫的人民。”
“法兰西曾在我治下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尤利安——不,master。”
“这强大和人民没有任何关系。”尤利安摇了摇头,“您让您的法兰西达到了巅峰,却不是人民的法兰西。”
路易看着面前这个头发蓬松且胡乱披散在肩上的少女,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不服气也不想任何人低头的神气,而那神气中又满是天真,让他没有任何争论下去的打算。正如尤利安所说,他们代表了两个不同的阶级,而他来到现世不是来为自己的阶级发声的,所以他转而问道:“所以你想打造一个没有苦难的世界,拯救所有被压迫的人民?”
“没错。”
“你应该清楚,你的理想永远是虚幻的,mademoiselle。没有不与苦难结伴而来的幸福,也没有平等的均质的幸福。”
“所以我需要圣杯,圣杯的力量可以满足我这一个愿望。”
路易摇摇头:“这是一种捷径,不靠自身得来的理想世界是很危险的。”
“……你的意思是?”尤利安沉下了脸色。
“你的理想很危险,mademoiselle。小心它,小心圣杯,小心……你自己。”
一些没卵用的设定:
*穷学生尤利安得到自己想要的水银是假造了一份实验报告再用魔术让其通过从而得到了足够的水银。
*这里面有一个很冷的梗叫做“英特那雄纳尔停在了Le soleil brillera toujours一句于是召唤出了le roi soleil”,可以说是命运啊(。
第一章
F→G
拉开窗帘让阳光洒进房间,以天气来看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将自己收拾完毕,去敲响了隔壁Archer的门。
“Archer,我进来了。”
推开门就看见阴暗的房间里,三个显示器的光亮把在它们前面戴着耳机的胖子映得诡异非常,满屋子的烟味熏得我一个趔趄,让我瞬间明白了这位一晚上抽了绝对不止一包烟!
虽然到达这里汇合后被Archer的新形象吓了一跳,要不是因为契约的联系知道他是Archer的话,还以为是哪里来旅游的游客来找人找错了屋子。但是过了这几天的相处好歹也算适应他新的外形和那想让人掐死他的被动技能了。话说回来,谁能告诉我,堂堂英灵竟然会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被现世的网络腐蚀,进而变成了宅男!变成宅男了也无所谓,毕竟网络上的信息和花样的确能让以前时代的人着迷,毕竟现代人也摆脱不了网络的魔力。更何况没人会嫌弃更多的情报。但是…………英灵变成宅男之后,不但体型变了,连能力数值也变了是几个意思?!从来没听说过现世的垃圾食品会对英灵起作用的!!这不科学!!!掀桌!!
抽抽嘴角大步走到窗边把窗户打开换气,椅子上的人转了过来,手里还抱着一桶吃了一半的爆米花。“有什么事吗?克劳迪娅。”
“我打算出门走走,有些地方还是亲自去一下比较让人放心。”
Archer转回去从电脑桌上的杂物里挖出一张地图递过来,“别迷路,遇到“黑组”记得装作普通人回避战斗为最优先。”
“…………你的意思是你不和我一起去?”
“不去,”Archer一脸嫌弃地秒答,“战斗好麻烦,我宁愿在这里继续上网。”
忽然很想跟圣杯投诉有人——不是,有英灵消极怠工怎么破?好吧,战斗的确很麻烦,比起战斗自己更倾向于情报收集,只要不是“黑组”赢,谁夺得圣杯都无所谓。
“那你继续。”长出了口气,接过地图转身出去。看着地图选定了路线之后,带着相机出门去赶公交车了。
Rue Pierre Legavre——
确认了没走错位置,总算松了口气。虽然迷路期间晃荡了不少地方,然而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收获。抬头看着眼前的呈现“C”字型的建筑,决定进去看看。希望在这里能找到一些网络上没有的信息,毕竟古老的信息仍然还都是以纸质来保存的啊。
………………………………………………………………
防爆用作文ORZ我都做了些什么啊Q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