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恋爱也许会死,不谈恋爱定会死。”
那么.....全力以赴地上吗?
也许剧中落幕之时,会出现一丝生的转机?



秦棠今天26岁,在人与人之间挣扎着向地铁门走去,背后的人推着她,而在她的对面一群人也同样在奋力前行,两股力压着她,使她不能退也不能进。她紧紧掐着自己的包,扭动着身躯想要从这庞大的桎梏中冲出去,但警示灯开始叮叮作响,车门彻底关闭时有人发出一声被挤压的声音。
秦棠被人织就的网笼着,突然想起从前的自己。26岁的秦棠想着16岁的秦棠,只觉得模糊得像一片影子一样。但16岁的秦棠遥遥想着26岁的秦棠,也一定只觉得模糊得像片雾。但总有一点是相似的:在高峰期时被人群淹没、带走。
秦棠并没有什么情绪,她已经学会疲倦地习惯这些了。毕竟她总是淹没在人群之中的,也总是被人群裹挟走的。秦棠瞧着身前人衣服上的纽扣发呆。列车隆隆开往下一站,带上了一个错过目的地的年轻人。
在下一站她终于挤了下来。她同样熟悉这个站点,另一个方向的列车并不会在对面等待她。秦棠按着标识踩上扶手电梯。地铁的灯有些坏了,站里比平日都要暗些。但她并没有多余的情绪害怕,她垂着脸盯着手机,贴心的社交软件被点开后就为她献上今天第一份的生日祝福。祝福界面关闭后的消息栏里全部都是群聊与公众号,她借这一个小盒子在角落里窥探着世界,吊着自己忘记疲惫,继续往前走去。
但这条电梯是不是有点太长了?她猛地惊醒,手机屏幕在黯淡的环境下显得格外刺眼。电梯终于要到终点,她赶忙上前几步,踏上稳定的地面。
光彻底没了。
秦棠就像那个被地铁门挤到的人,发出了短促的尖叫。身边全是看不到边界的黑暗,她下意识地摸向自己的眼睛,可她还分明看得到自己的手。她下一步想要拿起手机照明:没有手机了。
能发光的、还剩一半电量的现代科技产物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发着荧光的纸片,秦棠又尖叫了一声,把它丢了出去。纸片却施施然立在了她脸前不远处,像介绍自己一样浮现了文字。
秦棠仿佛抓住了一丝希望,她凑过去,死死盯着那些文字,但那些文字并不希望她拥有希望,一点一点地使她的身体发冷。甚至还替她流下了泪水。
那暗红色的粘稠液体顺着纸面流下,落在地上,发出嘲笑一般的轻响。秦棠毛骨悚然,她的手微微颤抖,全身发冷。
这不可能是真的,怎么可能是真的呢?这是恶作剧,是噩梦,但决计不可能是现实,现实怎么可能出现这样荒诞的故事?她毫无底气地试图说服自己,白茫茫纸张与她对视,像是黑色的恶魔睁开的眼睛,秦棠被恐惧驱使,她开始奔跑。苍白的纸片跟着她。
她哭得涕泪横流,手脚并用,一心想要从这片黑暗中逃离出去,胸腔在剧烈运动下开始逐渐疼痛,冰冷的身子变得发烫起来,她跑在虚无中,知道自己无从脱出。她想着那些文字,惊恐在她的脊椎上盘旋,她感到她的人生与生命都在离她而去,但另一种情绪顺着发丝进入她的脑中。
不可以!她冲着这个微妙的情绪大喊。为了从这不该产生的情绪中逃离出去,她重新开始了狂奔。奔跑使她气喘吁吁而又绝望不已,但她哪里敢停下呢?终于,她腿一软,一头栽进了黑暗里去。
秦棠很喜欢吃生日蛋糕,写着名字的巧克力块与罐头黄桃是她的最爱。除了这两个东西之外她最喜欢的东西是奶油,棉棉软软,缠着舌头,落入腹内造就甜腻的满足感。因此她每次都会好好吃完,一点不剩。直到在学校给别人过生日的时候,她才第一次闻到了奶油氧化的气味,那是高三毕业前的一次大家合谋放纵自己的狂欢,欢笑声中抹在皮肤上、头发上和衣服上的奶油已经不再是庆典的象征,它成为了新的烦恼。颜色不再具有意义,但它们停留过的地方依旧黏腻,在空气中迅速地开始腐败,秦棠被那些气味裹在里面,熏的要呕吐。但她的同学手上沾满着那些,笑嘻嘻地继续凑近她。
热情与喜欢一并消退,她开始企图从这个痛苦的狂欢节目中逃走,那天的晚自习后,秦棠反复地冲下六楼,又冲上六楼,笑声和疯狂在她身后追着她。最后她在教学楼顶层的楼梯间躲着,听着脚步声轰隆隆地踏过去,放过了她,并不执着于寻找到她。秦棠坐在台阶上与黑暗里,心跳如擂鼓,晚修前为了生日会才洗完澡的身子疯狂出汗。她在那一瞬间觉得很累。
秦棠在油腻腻的空气中艰难地呼吸,慢慢地数着楼下此起彼伏的尖叫声,直到笑声消散了,她缓缓地下楼走回教室。教室内空无一人,灯被早早地灭了,谁也想不起来秦棠没有回来。
她坐在讲台上,一个人望着一排排的桌子们。秦棠想象着自己喜欢的男生还在隔壁教室,收拾完东西恰好走过外面的走廊,这样他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有一场不为旁人所知的交谈。他也许会问秦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副样子,秦棠说不定还有机会掂着一点奶油,借着打闹去摸他的肌肤或者头发,使这些粘腻的东西再次有一些甜美的回味。但是全部的人都已经走掉,秦棠的想象直至毕业都只是想象。
秦棠将这些东西记在日记里。后来她再翻看的时候已经没什么感觉,像喝着一碗冷汤里的残渣似的。学生时代于她来说已经太遥远了。她被裹挟着,规矩的往前走去:上学、工作。如果她能对相亲顺从一些,大概就能完美些。她明白自己不能像梦境一样拥有春天,她太过于平庸了,再甜蜜的梦境也是梦境,即使全被她暗藏着骄傲地细细记载在日记本上,她能品味的自己的青春也就那一点东西。
因此,当她终于掉了眼泪时,她说:“我有过,我也有喜欢的人。”这些话粘着她重重的鼻音,听上去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我知道你在日记里写的东西,可那算什么?!”她的妈妈已经不再顾及什么,她把嘲弄掺进话中,当作愤怒的发泄方式,“你自己说,那算什么?”
那算什么?秦棠也不知道。她明白,太过于明白。她一直以来反复品味的事情也就那几件,剩下的大多数则都是她自己靠着那几件事情发酵出来的情绪。她不愿面对这样的事实——如果低头承认了,那么这些年来她的悸动、幻想和固执都要变成没有意义的东西。可明明她是依靠这些组成的。
秦棠近乎悲哀地想着。她只是想要一个梦境,可谁会给她这个梦境呢?
在黑暗中,她坠入了梦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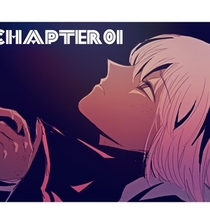



《城西新事》
文案:
柳花明是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只是心血来潮,去了从未走过的小巷,竟会撞见街头斗殴的景象。
在人群中占下风的,出人意料地,是一个看着才十三四岁的少年。他的每个动作都是毫无章法,可却行云流水、气势十足。
于是柳花明放下了她的滑板,加入了战局,冲着那个惊愕的少年明媚一笑:
“嘿,我现在帮你打一架,以后你做我小弟好不好!”
CP:怂却能打的接班人小弟x街头霸王大姐头
搜索关键词:不良 言情 青春
主角:柳花明,马修/莱昂纳多
【台前】
这个小城市总是沾满了灰尘。
说它是小城市,好像有那么些不恰当:一来,这个城市密密麻麻的人口数绝不是一个“小”字可以形容的;二来,这里的土地过于狭小,勉勉强强才能算作县城。可这城市也的确是小。它小,大城市充满活力的风总从一旁刮过,刚好打个擦边球。它小,小得只能容纳些污浊庸俗又无趣的东西。
每个想离开这里的人都晓得,城西的地界儿——是去不得的。楼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墙是裂了皮的,地总是堆满垃圾并弥漫着臭气的,人总是无精打采或精力过于旺盛的。城管对这里真没辙。
而要说这带的年轻人中谁名声最响亮,过去只有一个:大洋彼岸来的黑户柳家大姑娘。现在还添了个还没上高中的小毛孩。小毛孩——街巷里的年轻气盛的家伙们这么叫他,但谁都知道自己打不过这个小毛孩。人们看到他们同进同出时都自以为知道了真相,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他打起架来和平常文弱怕事的样子判若两人。眼神像西伯利亚的孤狼,每个动作都是发了狠的。自然,这样嚣张的打法也不是总好使。
“真是的……这是第几次了,嗯?身体可是很重要的……”柳花明语速比平日快了一倍,眉头紧锁,又叹了口气,“倒给我省点心啊,这个药粉老贵的。”
此刻的她不像那个一脚能把人踢老远的花豹子,更像是刚出生没两个月的超凶奶毛。她用右手食指和大拇指捏着沾了双氧水的棉花,趁着对方随一声“啧”扭过头的时候用力摁在了伤口上。
这有些狼狈的少年正是马修,柳花明钦定帮派下任头子。他眼睛突地瞪圆,有些歪斜的牙呲起来。
事情的起因另外一伙人冲着他挑衅。泥潭里长大的孩子心理承受力不能说好,只能说是学会了如何“无所谓”,但急躁却都是差不多的。要是什么别的言辞,他还不会这样在意。今天这群家伙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冲着他喊“恋童癖包养的小白脸”。
少年人大多是血气方刚的。
“嘶……你能不能轻点!……况且我要是不把对面打狠一点,我能接你的位置吗。”
“不是说了点到为止就好了吗?俗话说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是被打到骨折之后又有人找你单挑,那大伙儿可就彻底爬不起来了啊!”她索性放下装着药水的瓶子,棉花随地一丢,在对方脸上捏了一把,“咱们不要面子的吗,哼?又不让我把你当小孩子,又这么皮,跟谁学的真是……”
“——啊!说了多少次不要捏我脸啊你这个大婶!”
“……大婶?大你个龟龟啊!嗨呀屁大个营养不良小不点儿!一句批评都听不进去!”
“营养不良?你说谁营养不良!你看我哪顿少吃肉了吗!你见过吃像我这么多的人营养不良吗!”
“蔬菜啊!维生素D啊!胡萝卜素啊!就知道吃肉吃肉吃肉!”柳花明脸上写着“朽木不可雕也”,就差痛心疾首地背出一连串小知识了。
“我就是不喜欢吃蔬菜我有什么办法!你还老做西兰花,那个味道真的太难吃了!”
“因……因为奶油炖菜的话,做一次我们两个人能吃两顿!超省事的啊!而且营养也很齐全!不用一盘一盘热菜!只要一锅热了不管什么时候都能吃!”
奶油炖菜倒还好,卖相不怎么样,肉腌得挺有水平。只是这句话中的另一个信息,能把马修气死。他伸出手一把揪住柳花明领口:“哈?不用一盘一盘热菜?如果你能天天和我一起准时吃饭的话就不会有这个步骤了啊!”
是了,他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
有时候洗衣服到一半突然跑出去,有时候自己洗完澡出来她刚好打开家门,无业游民的好处就是如此,兴致来了,爱往哪跑就往哪,想什么时候回来都行。她可以一天只吃一顿饭,只因为清晨七点的时候突发奇想,去公园从白日的鸽子看到夜晚的喷泉。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受不了对方这种随性的生活态度。
——就和鸟一样,来无影又去无踪,只怕是一飞走就再也不会回来。
“不按时吃饭又怎么样啊!只要营养齐全了不就好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可比某个小!先!生!强好几百倍嘞!”她把对方的手扯下来,另一只手使劲弹了下马修的脑门。
“哈?你是不知道这样会直接对胃有伤害吗?你当我们上次怎么打赢对面那个和你差不多德行的!我跟你说你再这样下去吃的再营养也没用!”
“不!知!道!啊!我怎么和他差不多了!我比他可爱还比他能打!”她仍是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却露出了心虚的表情,眼睛开始往其他地方乱瞟,声音渐弱,“反反反正我不是还活蹦乱跳的嘛……也没有胃病……不按时吃饭又怎么样啦……”
“防范于未然听说过吗大婶!哪有像你这样生活的啊,天天念营养营养营养,自己又这样子……”
啊。
对面的少年有些局促地扭过头,手挠了挠脑门。
对少年的性格心知肚明的柳花明吐了吐舌头,抽出一团新的绵,手上的动作轻了许多。
马修是善于表达又心思细腻,安静可爱的孩子,而在马修体内的,现在占着主导权的这位,恰好相反。嘴上不说,对方难得一见的别扭的温柔却叫花明的心里乐开了花。
“总之好像能很快让伤口愈合的样子……好起来之前不要到处乱跑,知道了吗,嗯?”
“好啦好啦知道了……果然是大婶啊,这么啰里吧嗦……在完全好透之前我不出去了行了吧!”
“也不是不能出去……平常多走大道啊,那几个家伙经常扎堆混的地方就别去了。”花明低着头,细心地涂上药粉,“反正也还只是个小先生……不对!我不是在和你吵架吗!啊啊啊可恶忘掉了……!”
装模作样,她已经没打算吵架了。
她是酷姐们,踩着滑板从黑暗中窜出来,打起架干净又利落。她是大姐头,性格爽朗而极具领导力,跟大家打成一片,亦可一挥手就点燃全员。但只有在自己面前,她是真正的柳花明:有点笨拙,叫人放心不下,又自以为是地强行照顾自己。她会做糊成一锅的奶油炖菜,会抱着手机笑到从床摔到地板上,会因为一时兴起就领着一个小孩子从此走南闯北,会牵着自己的手在路边摊间风风火火地跑着,会像现在这样蹲在台阶上细心地上药。
这才是柳花明。
“……哼。”“马修”双手抱臂,控制着嘴角的上扬。
“……复读我干嘛啊……”
“……噗……你在说什么啊,完全听不懂……”
“哇你笑我!胆子肥了……哈哈哈……”她没忍住,一边叫嚷着“为什么你的笑声这么好笑”,一边仰着头咧开嘴。
他们就像美利坚土地上每一个普通的孩子那样,因为莫名其妙的事情开始大笑,笑得停不下来,还觉得对方傻帽。
笑得像墙头上的麻雀,笑得像老房边一个劲往上冒的爬山虎,笑出眼泪呀,又笑出了花。
【幕后】
马修和柳花明并排坐在准备室中。
在陌生的房间中醒来时,在大厅里看到长着翅膀的男孩子时,询问“这里是天国吗”时,她一次都没怂过。这会儿要上台了,剧本准备了无数遍,台词没法倒背如流但可以现编,她却怂得像是一只把头埋进沙丘里的鸵鸟。
可是这里没有沙子,只有铺天盖地的白茫茫;这里没有鸵鸟,只有一个叫柳花明的标准中国沙雕。
相比起马修,她看起来倒更像是初中没毕业的小孩子了。
最初被分配到一起时,花明明显地感受到面前的孩子的不安——做什么都有些局促,不时地问自己“演不好怎么办”,念台本时总是磕磕绊绊,时常欲言又止。
下一轮中,这个孩子和自己再被分配到一起的机会少之又少。先前在大厅里的人群中有几位看着比较暴躁,不知道他和他们分配到了一起会发生什么。
或许是因为吊桥效应,又或许是因为天生的母性,柳花明觉得自己该为这个小先生做些什么。
所以创造了“能保护他人”的角色。
所以创造了“拥有勇气”的角色。
所以创造了“即使坐在黑暗之中,也能像太阳一样笑出来”的角色。
“花明小姐觉得……我做得到,吗?”
默念了无数遍台本后,马修抬起头,比花明更镇定些许。她微微抬头,对上他的视线。
一点点也好,想要在这个孩子成长的路上帮他一把。
于是这样想着的花明,“噗”地一声笑了出来。“都要上台了还想这个呀?”她伸出手,将对方的头揉成鸡窝,在对方露出苦恼的表情时又顺好头发,最后在上面拍了拍,“放轻松放轻松!这个角色可是为你量身打造的,绝对没问题哦,马修小先生!”


本篇全文4591字(太多了!!),是序章之后和正式表演之间搭档的这两人发生的事
是我和大卫中之人得塔劳斯一起rp之后得到的剧情!
后面的可能来不及了我先把这个发了再说555555()
那么以下开始——
———————
伊雅从外面回到房间后仍然缓不过神来,她浑身发软,甚至都快站立不稳。在门口僵硬了不知道多久,她忽然听到房间某处传来了细微的响动。
“叩叩。”
“.......”
刚离开不久的恐惧感又重新席卷而来,甚至比之前更甚。她要拼命忍耐才能抑制住自己转身夺门而逃的冲动。脑子里回想起了之前听到过的话:
“不要在某些时间之外擅自出门,否则后果自负。”
眼眶里已经开始蓄积泪水,她一边发抖,一边慢慢挪动着靠近了声音传来的地方。
是玻璃门。
在快要碰门框时,她闭上了眼。
或许是已经恐惧到了极致,手停止了颤抖,神经甚至也有些麻木。又走了一步到了门口,她慢慢睁开了眼。
“.......?!”
玻璃门不知何时已经变得可视。门背后居然有一个人!
她吓了一跳,猛地退后了一步,差点摔坐在地上。幸好手还扶着墙,不至于真的跌倒。
“啊!吓到你了吗,我很抱歉…!”
玻璃门对面的男人神色有些尴尬。
他很白,带着一顶黑色的帽子,长着一张看起来不太无害的脸。一头金发微微有些卷曲,身上的衣服看起来有些休闲。一只手里拿着一个娃娃,他用另一只手慢慢将拉门推到一旁,露出了一半的间隙让两个房间连接了起来。
“.......“
警觉和恐惧让她再往后退了一步。
发现对方推开了玻璃门,她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先拉开距离然后马上从房间里找东西自卫;但是恐惧又令她没办法再移动分毫。
“没,没事的,这样的条件下,论谁都会不知所措…..我们的处境是一样的……”男人急忙摆摆手,像是一边安慰自己一边跟她解释似的说着。发现这时贸然尝试接近她的行为可能会进一步加深她的恐惧,于是那人只站在门边,不敢踏入另一边房间。
他托着少女模样的人偶站在原地,仿佛在努力地展露能看上去显得亲切的笑容:
“我的名字是大卫•夏普,……她是琼。我们绝不会是坏人……你愿意相信我吗?”
“……“
她发现了对方没有再试图继续往前。
虽然仍然十分恐惧,但意识到这点之后,肩膀可见地往下松了一些,脑子也慢慢重新运转起来。
她艰难地思考着,试图理解对方话里的意思。
“大卫...?”她僵硬地复述出对方的话, “…...所以说,你......你是人类?不是这里的......这里的'人'......?”
“是的,我是大卫,是人类,不是刚才那些长着尖耳朵或是小翅膀的家伙……那看起来太不科学了,简直像是幻想电影里走出来的演员——可能是琼喜欢看的类型…不过至少目前看来我们现在是同样的境地呢。”
对面自称大卫的男性话有些多,看起来似乎对于眼前的少女对自己放下了仅仅一点戒备都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接着他似乎想到了什么,面露尴尬:“呃、…我也知道这样贸然进入女孩子的房间不是礼貌的行为。琼一定在狠狠地责骂着我。请女士们原谅我的莽撞……”
”.........”
她还是有些害怕。但到这一刻为止她终于有些松懈,并且几乎是同时感到了一丝委屈;她的鼻子一酸。不过她马上甩了甩头,试图让自己坚强起来。她红着眼睛,鼓起勇气,有些哽咽地试探着问他:
“……刚才......你说,'你们'......“
但这也就是极限了,她并不敢用更多眼神往这个人身后的房间探寻。
“‘我们’?…嗯,是这样的,它指的是我和琼。我的房间里没有别人,请你放心哦。”
那个人指了指那安静地坐在自己右手掌中的西洋人偶,对她报以诚挚的微笑。
“琼......”
看着那座人偶仿佛使她想到了什么似的,她略点了点头,闭上了嘴。又小心地看了一眼眼前的人,发现他正在对自己微笑……
她把视线移开,看向了地上。还是有些害怕,但比起之前好像又有些别的感觉。
脑子里开始能够重新思考了。眼前这个人……好像确实是人类。至少目前为止两个人都能够相对正常的交流;并且就算说了这么久,在她没有安下心来之前,对方也很小心地没有再往甚至前半步……从他的言辞里,也可以感受到他对自己应该没有任何要伤害的意思,甚至……他还一直在试图安抚她。虽然,他手里拿着一个娃娃确实有些奇怪……但娃娃看起来也被照顾得很好。
其实,说不定眼前这个人,真的……能够算是同伴?
短暂的沉默后,她开了口:
“....刚才,没....没关系。抱歉....。我.........”
她抬起眼小心翼翼地看着眼前的人,一边观察他的表情,一边接着说:
“....我是Ayre。”
“啊,感谢你,伊雅小姐。”
他又一次展露了笑颜。这一次看起来更加开心,显然他已经感觉到对面的少女态度又有了些许转变。他接着说:
“那,现在让我们理清一下头绪如何……? 其实,我对这个情况也很茫然……不过……对了!那些人似乎说过,会在我们房间里的桌上放上必要的情报……之类的?”
他抬手往后抓了抓有些微卷的头发,又压低了帽檐,然后转身回自己的房间拿了那份信封,把拆信刀放入了自己的口袋里。又转过身,对着她说道:
“也许我和你所拥有的信封中会有不同的消息。而且,即使是那群怪人强塞给我们的,这也是属于个人隐私。”
像是害怕惊扰她似的,他背过身去,从口袋里拿出刀来。当他再转回来时,信封已经被划出了整齐的切口。
“为了让伊雅能信任我,我会跟你分享我拥有的‘情报’……虽然我也不知道里面会有些什么内容呢。”
他先将人偶放在了桌旁。他似乎很少进行这个动作——虽然人偶离他只有十多公分的距离,但他因此露出了些许不安的情绪。不过这份异样好像被他暂时按捺下去了。
他将信封中的内容倾倒出来,又把那些东西像纸牌般整齐地铺散在了桌上:
“看……这便是我对伊雅你的信任了。……我不奢求你愿意同我分享什么…但至少,请不要误会我的好意…”
”......抱歉。“
她怔怔地看着对方的举动。
等到他停下动作,她回过神来,脸上慢慢浮现出了以往软弱又有点难过的神情。她避开了可能碰到娃娃的位置,慢慢走到大卫身旁,看着桌上的纸,又看了看大卫,把头微微低了下来:
”我很抱歉......,....我相信你,我也没有恶意,之前.....我只是太害怕了........“
“……”
大卫微微侧开,俯身平视着她,看着她的眼瞳映照出自己的脸庞,然后对她展露了一个笑容:
“若是这样的话,就太好了……。其实我也是很害怕的……但如果我也和伊雅一起只在原地颤抖、动弹不得的话,事情就不会得到解决。”
“……嗯…”
她有些羞愧,但又觉得:原来这个人和我一样吗…?也一样被不安的情绪所困扰着吗……
刚才…我还怀疑了他。
“……刚才误解了你,真的…很对不起。”这句话带着她的歉意和难过。
“没事。“他直起身,转向又将人偶抱起,“那么,由你来查阅我信封里的文件,可以吗?“
听到他说由自己来查阅桌子上的册子,她有些不知所措,随即又反应过来…心里涌上一股感动和酸涩。
“那…失礼了。”
她伸出手,小心地把东西拿了起来。
“嗯…不过说来惭愧,我放下琼的话就会心神不宁……哈哈…很奇怪吧?……”
大卫似乎不经意地说着,但他的语气听起来似乎夹杂着些许自责和失落。
“…没…没有呢,我也大概能够理解……‘琼’对你来说。大概是很重要的存在,放不下也…也没什么吧。”
没想到他会跟自己解释这个,她抬起头看着旁边的人。虽然自己现在的样子可能并不好看,但她想鼓励他。她动作很轻地笑了笑。
“啊…只要你不去讨厌我就好。在大学里我经常因为琼的存在而被误解呢……不过加入话剧社团的话就会轻松一些,那些人会以为她是珍贵的演出道具……虽然这不是我的本意……琼也不愿意被人当作工具吧,这太侮辱女士了。”
他眼里闪动着复杂的情绪,也许是回忆起了在学校里的往事。他抬起手顺了顺人偶有些变乱的长发,又开口问她:“嗯,伊雅,那些纸上写了些什么呢?”
“啊…!“
突然被问到,她才意识到自己居然一不小心又走神了。她有些慌张地微低下头。
“对不起,请稍等一下…”
提醒自己要集中注意力,她摇了摇头,然后开始翻看手里的纸。
……
“…大卫…如果我可以这么称呼你的话?”
伊雅犹豫地看着他。然而对面递来默认的眼神和安抚性的表情让她安了安心。小声吸了口气,她接着说了下去:“…这些纸上写了一些规则,并说明每一个大房间里的两个人都是搭档…我们需要按照规则根据关键词表演,才有机会…活下去。”
上面也有第一轮表演的关键词。她心里微动,想起了什么,顿了顿,表情黯淡了下去,把手里的纸递回给大卫。
“详细的内容…大卫自己也看一下吧。”
“唔?”
大卫用空出来的手接过并阅读起来,从眼神的移动可以看出他阅读速度很快。
空气沉默了一会。
“也就是说,那些人是把我们当作享乐的演员,而且我们也被迫签下了危及性命的霸王条款呢……况且这样也只是不会死而已,我们还有机会从这里出去吗…”
“………”
回想起刚才在房间外被控制时绝望又难过的感觉,她又重新感到了恐惧。在今天之前,她根本不知道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也不会知道自己在绝境之时会是怎样的想法。但现在除了恐惧,好像还有了别的什么情绪。
她不想死。
就算她可能做不到城堡里那些“人”的要求……,但她不想什么都不做地就这么失去希望。
“…有,有机会的吧。只要有希望,就不能先放弃…!”
她鼓起勇气,神色中带上了一些微弱的期盼和鼓励,第一次能够直视大卫的眼睛。
“我不想放弃…我还想出去……大卫……可以和我一起努力吗?完成他们的要求的话……还有希望……”
对上她的视线,大卫有一丝惊讶,愣了一会,随后展露了笑容。
“——嗯,我当然不会放弃的哦,为了琼……为了自己……还有……。伊雅看起来已经打起精神来了,这是件好事哦。如果在这里就放弃了的话,不就正入那些怪人的下怀了——”
“嗯,那……!”
“不过…我,我在这牢笼之外是有情人对象的……我想这对伊雅,很……”
大卫渐渐收起了笑容,将视线移到别的地方,面露尴尬地压低了帽檐。
“…………”
一阵沉默之后,他的脸色渐渐变得羞愧难当。
他说不下去了。
听到突如其来的转折,她也愣住了。
反应过来之后,她的脸色先是变红,然后又变白。
”………我,我没有那个意思…… “
眼眶渐渐红了起来。
”并且………我也,我之前不知道………我…………“
伊雅有些哽咽地说着,低下了头。
她以为自己真的找到了伙伴,以为自己鼓起勇气了可以能够得到一丝希望。
但,希望好像是假的。如果她想要活下去,需要别人做出近似于背叛恋人的事情。而这是她最讨厌的事情之一……刚才,她确实拜托他了。
……更可耻的是,现在就算她知道了对方有恋人,并且她拜托对方的事是她最不想要再次经历的事情之一,她也还是不想放弃……她还是想活下去。
眼泪落了下来。
“对不起……但为了活下去……对不起……我…………”
她没办法再往下说。
她轻轻抹去了泪水,对着大卫微微鞠了一躬。
——然后她转身逃跑了,跨过门框后马上合上了推拉门。
“咦?—啊!!那个!!”为什么变成这样了!“我没有责怪伊雅的意思啊!而且是我这边对不起你才对……!对不起明明有伴侣了却还要因为这种荒谬的闹剧跟伊雅…假扮情侣什么的…!呜啊,请,请不要关上门…………”
她听着大卫急切的呼喊愈发难过。
她躲到床里侧的角落窝了起来,把头埋在了臂弯里,一声不吭。
刚才自己是想要拜托他的。对方还有伴侣。这种要求太过分了。
这根本是勉强别人……
她不想。
但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去做这种事。
如果大卫要拒绝的话……
……
绝望又难受。
门外的大卫看着伊雅跑掉的身影发出了无力的叹息,又不敢再次贸然拉开门,只能隔着墙对着躲起来的伊雅解释:
“对不起,只用这一次就好,只是演戏而已——那、那个…该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如果伊雅不介意的话,我怎么样都行!”
“………”
什么?!
这是真的吗……?
他没有拒绝……?!
……好温柔啊。这个人为什么这么温柔呢。
她怔住了,慢慢地捂住嘴,无声地哭泣起来。
但我的过错还是没办法回避……
对不起,没办法马上回应这份好意。
不过,稍微安心了。也更歉疚。
她站了起来,走到门边小声回应了他。
“我…我没事,请不用担心…………谢谢你。大卫。”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两个字几乎要让人听不清了。
——————
大卫皱着眉,无奈地笑了笑。
她休息了吗?
“……晚安,伊雅。”
言语之间,男人的身影在玻璃的另一边渐渐变浅,消失不见。
——————————————
感谢耐心看完的大家!!!!!(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