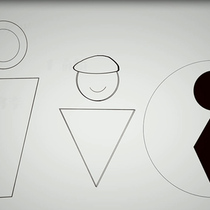My care is like my shadow
Laid bare beneath the sun
It follows me At All times
And flies when I pursue it
I love And yet Am forced to hate
I seem stark mute inside I prate
========================
渴望,思念,孤独,怨恨……这绝不是人类仅有的感情
抱有欲念被主人抛弃的器物,在魔女歌唱之时,化为人形。
而暗怀心愿的人类,也在寻求着某种际遇与改变。
在机械轰鸣的爵士年代,魔法与巫术在此暗中汇聚。
器物与人类,是否能找到与之结缘的彼此。
两者的缘分与命运,无论善恶,就从踏入徒然堂的一刻开始。
欢迎来到TURANDOT•徒然堂,
今天的你,也在期待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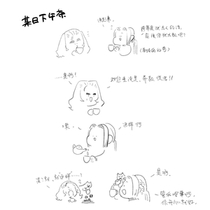




当这个刚买下自己的黑皮肤男人发出一声尖叫并迅速向后退了三步,贝兰达长长叹了口气,抬起手指了指头顶上已经破旧的招牌。
“恕我直言,您刚才就走过这个路口了。而且我也不是什么鬼魂。“
男人的嘴角因为害怕本能地抽动了几下,然后转过头问路边卖古董的小商贩:“您看得见……这个女孩吗?”
商贩像看神经病一样嫌弃地看着他,眉毛皱得可以夹死苍蝇。
贝兰达看着她的新主人吞咽着口水,尽可能冷静地调整好呼吸,然后就跟什么都没看到似的快步往前走去。她不解地偏了偏头,跟着走了上去。
“这条路您刚才也走过了。“
“十分钟之前您也是在这边左拐的。”
男人似乎有点尴尬,但还是加快了脚步。
”您难道不是为了结缘才到店里来的吗?“
贝兰达是一个家精。她是一件旧魔法袍上所寄托的思念所化为的自主意识,而这件袍子正好被眼前这个黑皮肤、穿着白西装的男人买下了。
物品本就是普通的物品,但总会有物品承载着主人的记忆,见证主人的悲欢离合、陪主人走过风风雨雨,在久远的时间长流中逐渐拥有了自己的感情。
她的主人曾是一位老巫师,也许他真的有什么超自然的能力,也许他只是普通的博学多才……不管怎样,老巫师似乎预料到了贝兰达的降生,在临死前将这件已经被种下了萌芽的随身衣物交给了徒然堂——
一间帮助人类与器物之灵结缘的小店。
贝兰达对时间不是很有概念,也不记得自己沉睡了多久,不管怎样,眼前的男人是唤醒了自己的新主人,她应当为他服务。但现在的情况好像跟她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顺带一提,若非有特殊力量的人类,只有家精的现任主人才能看见自己的器物之灵。
男人左看看右看看,确认了周围的路人都看不见这个银白色的女孩子。
“结缘……是指……?抱歉,我是正好路过——啊,不对,我不应该回答她。“意识到自己回答了“鬼魂”的男人低下头迈大了步伐,一头撞进了路边的小教堂里。
正在念着圣经的神父被这突如其来的客人吓了一跳,礼貌地走上前去。
“夜安,先生。“年迈的神父摆出一副严肃的模样,将圣经放在了胸前,“主与我们同在。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
“救救我,神父,我被鬼魂缠上了……!“
还没等神父说完,男人就直接打断了他,一边尽可能地保持着礼仪,一边用焦急的神色表现出事情的紧急。贝兰达抱着手臂站在旁边,决定干脆什么都不说了。
老神父听他讲完,又疑惑地顺着他的手指看了看(并不能看见的)贝兰达所站着的地方,又看了看他手里那件刚买来的旧袍子,见多识广的老人大致明白了情况。
“你可能走进了徒然堂。“
神父说,嘴角泛起了些微的弧度:“我一直以为那是一个都市传说……虽然我看不见您身边这位‘鬼魂’小姐,但她确实不是什么恶灵。”
“不应当,我真的只是个袍子,主人。“
在男人回过头来看她时,贝兰达翻了个白眼。
算了,买下都买下了,日子就凑活着过吧。袍子的器物之灵想,头疼地长叹了口气。
她的全新生活才刚开始。
——————————————————————————
一个满世界找房子的留学生突然知道死线临头了所以一个咕噜跳起来当时就说了段相声。
这都能赶上!!!!!(指半小时前才新建文档)总之我可能真的就是个相声选手,请多指教
保林应该ooc了,我给亲妈下跪
没能写完。
互动部分只能勉强先扔一点上来……缓缓修改。亲亲ee老师是被我抓来群演的朋友里唯一来得及出场的(……
——————————
玛格丽特·汤普森坐在她那塞满了廉价首饰与劣质化妆品、以及少数一些值钱真家伙的梳妆台前,第五次揪下眼睑上的假睫毛。
坦白说,这些在她少女时代曾被视为神仙教母馈赠的化妆道具,到现在已经开始失去最初的新鲜感,越来越令人厌烦。特别是在那种需要特别精心准备的场合——但凡这几根假货有丁点修剪不得当,就会现得浓密得太虚假,将她的所有计划弄得一团糟。
当然,这并不是说玛格丽特讨厌画浓妆。正相反,她曾是歌舞团最受欢迎的明星,最喜欢在脸上涂厚厚的粉,穿那种火辣辣的短裙,她们这样的年轻姑娘都难以拒绝这样的装束。
她可以断言,女孩们从来都乐于为人瞩目,最好开一场派对,带一点那种能让人放松下来的小药丸,这东西谁都能搞到手,她们每人都有,在场的每个人都吃,然后所有人尽可以大喝大闹一场,一醉方休,这才最符合她的喜好。
然而,不管她自己的喜好如何,接下来的场合不能容许她这样肆意。玛格丽特对此心知肚明,不会有人喜欢她这样做,特别是她努力要讨好的那个人不会喜欢,那么,她自己再喜欢也没有用处。
有时她会觉得自己就像是面前这台油漆剥落又被重新粉刷,看起来光鲜,实际上木头芯都被虫蛀光的破烂梳妆台,别管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她必须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合格的拿得上台面的女士,足够漂亮,有一些头脑,并且不那么放荡。
只有这样,才能抓住垂在她眼前的那丝机会。
这个懂得如何才能令自己更加迷人的女人,喜欢别人称自己是那种有梦想的姑娘。梦想这个词可以让她做所有事情都理直气壮,不会觉得有所亏欠。
“别苛责我,这都是为了我的将来。”你看,她尽可以扬起她骄傲的小脑瓜,对所有人这么说,通常不会有太多人真的和她计较。
“人家不和你计较,这和梦想没关系,只是因为你长得够漂亮,你这个傻婆娘。”
出租房的另一位租客端着一盘肉馅乱糟糟的派从厨房出来,拆下头上的一条卷发筒砸向她,“男人才不在乎你找什么理由,他们只看你的脸蛋,还有身材。你对被你抢了试镜的那个露西说这句话试试,我看她非划烂你的脸不可。”
“你怎么知道我没说过?”
玛格丽特躲开卷发筒,开始在首饰盒里翻找合适的珠宝,并且一件一件把那些她觉得做得太假的假货往地上扔。
“老露西脸都绿了,可怜的东西。”她一边说,一边抓起一条珍珠项链往脖子上比划,“但是我能怎么办呢,谁不在盯着她的位置,谁不眼红瓦奥莱特的经历?我不这么做,难道老露西就能被埃德温先生看上?就凭她?”
“得了吧,我们大家都坦诚一点,她那张脸,可别吓坏了埃德温先生。”
女人夸张地耸肩,然后换了一条红宝石挂坠,她摘下手上廉价的镀金戒指锁在小盒子里,换上了一枚配套的宝石戒指。
她的租客伙伴适时而捧场地发出刺耳的笑声,混杂着少许羡慕,对这番刻薄的嘲讽表示赞赏。
“放你的屁。我敢肯定,如果有女巫,那一定就是你这样的女人!”
女租客大声说,她开始吃那份难吃的肉馅派,不断地咧嘴,“你今晚又要出门?小心点,最近那个经常出没的吸血鬼真该吸干你的血,就这么咬你的脖子,可真精彩。”
“闭嘴!”
玛格丽特同样笑着将卷发筒扔回去,她撩起长发,冷哼一声,“埃德温先生会开车来接我,我确信这很安全。”
她顿了一下,说了一些女性之间会说的那种下流话,“我只接受一种情况下被咬,老兄,死前至少让我看看下面到底有多大。”
这俏皮话又引来一阵放肆的大笑,棕发女郎一边笑,一边踩上高跟鞋,在公寓地板上跺了跺脚。
玛格丽特·汤普森是个漂亮并且不那么笨的女人,做着她这样身份的女孩都在做的美梦。
玛格丽特·汤普森梦想着成为真正的电影女星,而非只能穿着下流服装与观客调笑的歌舞团女郎,尽管她也知道,二者在许多人看来没什么太大区别。
“别苛责我。”
盛装打扮的女人伸出手,抚摸梳妆台镜中那个拥有迷人棕发的女郎的脸,她注视着自己手指上闪亮的红宝石,一字一句,轻声细语。
“别苛责我,这都是为了我的将来。”
玛格丽特最后一次毫无意义地调整了一番自己的妆容,将桌上的口红、香烟、手帕、修眉刀和其他一些东西扫进手提包。然后她站起身,拉开窗帘,从窗台探出头看向楼下车水马龙的主干道。
一辆明黄色的跑车在这时驶进大道,车徐徐停靠在路边,在她向下看的那瞬间,正抬腿跨下跑车的男人似乎略有所感,在同一时刻微微抬起头来。
帕特里克·埃德温刚巧已经到了。
*
于任何一个对荧幕有所渴望的女孩来说,年轻的埃德温都会是她们向往的通向成功最短、也最绮丽的路。
而正走在这条路上的玛格丽特却认为,这一切或许是一场骗局。
从各方面来看,她都敢说,自己从没见过像埃德温这样的人——这绝不是负面意义的评价,不过,倒也算不上是夸奖。
玛格丽特认为自己或许只是想不通,怎么会有这样的男人,能毫不吝啬地给自己送来大把香衣珠宝,仿佛挥金如土这个词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然而另一方面,却又对她的种种暗示视若罔闻,顽固至极。
埃德温同她没话说,一贯如此,她已经逐渐习惯。玛格丽特伸手挽住对方的臂膀,故意圈在自己胸脯上的手臂带来一股夜风特有的凉意,连男人那头淡色的金发看起来都是冷的。
棕发女郎察觉不出自己对埃德温有多少吸引力,她有时会为此感到恼火,但对方的钞票总能恰到好处地压住这些火苗。不可否认的是,除去这些实在的金钱散发出的魅力,玛格丽特时常感觉自己是在演一出独角戏,最后总会感到莫名难堪,进退维谷。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只要他还愿意掏钱,只要她能尽力哄得这男人将她安排进随便哪一部他投资的电影中,埃德温对她感不感兴趣、乐不乐意和她上床,从结果来看又有什么区别?
被挽住的人调整了一下姿势,从容地迫使玛格丽特退开了一些。他们今晚的目的地是位于海滨的一座庄园,来往出入这座建筑的人无一不打扮光鲜,玛格丽特只能猜测,或许这里在富人中享有某种名望,但她的确对此一无所知,这令她感到不太舒服。
“埃德温先生,这儿的主人看来很有本领?”她试探着问她身边的人,绞尽脑汁粉饰自己的措辞,“或许她很富有,或者,嗯,有什么贵重的身份?”
但帕特里克·埃德温并不理会她的期待,只是敷衍地点了点头。
“你说的都没错。”他说,视线还放在大厅中的人群上,“玛吉,你很聪明。”
玛格丽特一点也没有感到自己正在受到夸赞,她并没有任何一点喜悦的感觉,而是惯常地生起恼火的情绪。
这时她忽然清晰地意识到,埃德温的确不在意她,就算他这样亲昵地喊她玛吉,但他花钱无疑只是闲得无聊,或者是因为许多场合正好需要那么一个女伴。
她意识到对方一点也不在意她,而自己对此却没法那么无动于衷。
正在这时,无视玛格丽特心头涌起的怒火,一名端着托盘的侍从走上台阶,附在埃德温的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玛格丽特竖起耳朵,只听见一些零散的单词。
“……夫人…………请…………那件事…………”
金发男人点点头,他转头看向自己的女伴,蓝眼睛中有一瞬间闪过一丝犹豫,但最终那双眼中的蓝色逐渐沉淀,又转变为令他的女伴感到熟悉的平静莫测。
他打了个手势,表示没有问题,于是侍从朝他们鞠躬,他们很快被引领着穿过大厅,远离嘈杂的人声,最后停留在一扇雕花门前。
侍从推开这扇门,玛格丽特跟随着埃德温走了进去。
门内是一间装修风格仿佛是上个世纪所遗留一般的房间,单是呆在屋内,都让人感觉像是被时光抛弃。房间内因被过量的装饰推砌而显得狭窄,不知道为什么,室内的暖炉被烧得很旺,淤塞的空气沉闷到令人窒息。
屋内早有先客。有西装革履的中年绅士,有戴着鸭舌帽,神色紧张的年轻人,甚至还有一名红发的修女,手中提着一只就皮箱,沉默地倚在墙边。
但就连与这种场面格格不入地修女也没能完全吸引玛格丽特的注意,她几乎是一眼就看到正对着壁炉的那架扶手椅上斜靠着软垫的女人,对方的金色长发曾被盛赞为仿佛金羊毛,而她抬起的那张面庞,现在也被投映在大街小巷的诸多荧幕上。
萨曼莎·瓦奥莱特。
同样出身歌舞团,她们这些女孩没有一人不将其视作钦羡的对象。
玛格丽特胸膛起伏。她随着埃德温一起坐在靠门那一侧的沙发上,花费了一些时间调整自己的呼吸,好不容易压下了那一股让她眼前发黑的眩晕感。
这时,房间内聚集的人们已经开始了各自的交谈,埃德温同其他人说着一些让人听不明白的话题,他们或许在说政治和经济,好像之后又跳转到人文和哲学,玛格丽特听不明白,也不关心。
她张了张口,艰难地准备说些什么,然而一阵敲门声打断了她,侍从再一次打开了房间的门。
“女士们,先生们。”
恭敬地行礼后,侍从垂着头说,“英格拉姆夫人有请各位上楼与她共进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