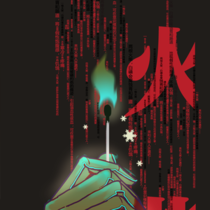My care is like my shadow
Laid bare beneath the sun
It follows me At All times
And flies when I pursue it
I love And yet Am forced to hate
I seem stark mute inside I prate
========================
渴望,思念,孤独,怨恨……这绝不是人类仅有的感情
抱有欲念被主人抛弃的器物,在魔女歌唱之时,化为人形。
而暗怀心愿的人类,也在寻求着某种际遇与改变。
在机械轰鸣的爵士年代,魔法与巫术在此暗中汇聚。
器物与人类,是否能找到与之结缘的彼此。
两者的缘分与命运,无论善恶,就从踏入徒然堂的一刻开始。
欢迎来到TURANDOT•徒然堂,
今天的你,也在期待着什么?



干啥啥不行滑铲第一名!!!
夕落那边已经尽情撒糖了所以这里就没让洛斯塔实际出场诶嘿,以及和苍叶家的搞事小本本的互动
若是纯粹的只是作为一只家精的幸福日常能够一直长久下去就好了
以下正文
啊,春天。轻飘飘的、稍稍暖或是说微微凉、总有些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在躁动的季节。少女的心就如这一季节下不知不觉间已经绽放的花蕾那般,在晚风里雀跃着。
芙洛丽亚轻手轻脚地起身,为自己在薄薄的睡裙外披上一件单衣,从储物间里抱出了先前藏好的一个小包裹后,来到了远离卧房的窗口前。若是问这样莫名还有些微寒的夜晚为何要离开温暖的被窝,离开可爱的亲爱的身边放弃多享受会儿她的体温和睡颜,那自然是为了更加必要的事情而忍痛割爱。
少女正在准备礼物。
当然,今年情人节早在她们相遇之前就已经过去,也没到洛斯塔的生日,更没有什么需要庆祝的节日。但是想要送出一份自己的心意又何必依靠一年里零星的那几个日子?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哪怕只是想表达些好意,都得找个借口才能撑住自己的面子那般。迷迷糊糊的家精哪里懂得这些,她单纯的只是想为那善良体贴的爱人送上自己的十足的谢意、百分的好意、还有每日都要满溢而出的爱意。毕竟她的亲爱的是这世界上最爱她的人,也是一直以来最好的。
原本稍显空荡的餐桌边很快便有了一把新置的椅子,橱柜里被双倍了的餐具充盈,有两双拖鞋则随意地散在了夜晚的床尾。这间屋子不再只是单纯落脚歇息的地方,而是切实地变成了属于人类洛斯塔和家精芙洛丽亚的小家。
最开始的芙洛丽亚满脑子都是想要帮上给了她这么个家的洛斯塔的忙。从打扫卫生到料理三餐,完美的新娘自然应是要把这一切都打理妥当的。
“我是不是又搞砸了,亲爱的……?”
芙洛丽亚小心翼翼地将手里的抹布递给正在冒着呛人黑烟的烤箱前查看的洛斯塔。就像之前几次那样,后者没有多加责怪,只是询问有没有受伤,然后轻车熟路地修复好了有些老毛病的器械,并帮着一起打扫干净房间、收拾了还泡在水里的衣服。事后一起享用幸存下来的食材时,她还夸奖了芙洛丽亚做的果酱很好吃。
总之家务这方面要慢慢学习。原本一心只想要做美丽完美的花嫁的少女褪下了对于做家务来说过于累赘的蓬松衣裙,在洛斯塔出门工作学习的闲暇时间里,近乎寸步不离地跟着管理员婆婆学习如何料理家事。
努力终是有所回报,虽说还不会太多的样式,但过了一个月后也能天天用热腾腾的饭菜和整洁的家来迎接亲爱的回来了。但这还不够,或着该说只是基础中的基础。更何况亲爱的似乎看起来总是很累的样子,时不时地忘记一些事情或是走神到了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作为她的伴侣,那就应该为她分担苦恼。还想帮上更多的忙。
——最终少女得到的答案,便是送出一份能够表达心意,让她的所爱多少能够振作起来些的礼物。
今夜月光正好,不用开灯也能看清,拂面的晚风也很舒服,若是仔细去辨别的话,还能感受到即将到来的季节迫不及待地传递来的暖意。芙洛丽亚撑着窗台愉快地深吸了一口气,随后拆开了那份小小的包裹,里面都是些琐碎的布料与针线。
“感谢您,祝愿您幸福安康,日后我会将借用的东西原数奉还的……!”
少女对着月光祷告。既然是要拿来作为惊喜的礼物,这些材料自然是不可能麻烦亲爱的去筹集,而是芙洛丽亚从管理人婆婆那里“借”来的。深受作为文明守法的普通好市民的爱人影响,芙洛丽亚自然也是在牢牢遵守着符合常世的“理”。她不易察觉地帮老人做着家务,顺便拿来练习,付出了“相应的劳动”后才取了些被遗忘在阁楼一角的旧衣物等物件回来。要说拿这些碎布料能做的东西也不多,一旁粗略绘制的草图上是绸带与色彩鲜艳的装饰花的组合。
两人的休息日时常就像普通的情侣一样,会挽着手出门逛街,寻觅街边店铺里的精致甜点,或是在影院里互相依偎。路过那些夺人眼球的商铺橱窗时,女学者在存款允许的条件下,从未吝啬过为芙洛丽亚购入新的衣装、可爱的糕点、或者一条十分搭她那双翠绿双瞳的发带——这些对于家精来说绝非必要的事物——而她本人却从未要求过什么。哪怕芙洛丽亚兴奋地在街边小摊挑了一顶做工精细又实惠的牛皮帽,用以往她绝对敌不过的闪亮亮的热切目光加以注视,劝说着这顶帽子绝对适合她。洛斯塔也仅仅是摸了摸芙洛丽亚的脑袋,一如既往欣喜又温柔地道着谢,然后在店家察觉到异样之前把帽子给还回去。
没有女孩子会不喜欢打扮自己,也不会有毫无理由的克制,可洛斯塔就是一直那样,把她的长发盘起,身着一丝不苟且朴素的制服,扣严她的贝雷帽。长此以往,芙洛丽亚有些困惑又微妙的有点生气。但那点微不足道地怒气也总是在随后落在微鼓的脸庞上的亲吻、或是一口绵软的甜点之后烟消云散。
单纯的家精忘得很快,尤其是那些不开心的、不好的,但她也清楚有些事是要记牢的,尤其是关于自己的亲爱的。那抹困惑总是萦绕在芙洛丽亚的心头。少女明白自己有很多事还搞不懂,也许她永远都没办法搞懂。不过她明白就算是爱人之间也并非需要完全知根知底,而洛斯塔确实是有秘密的,没有秘密的人毫无心事的人很少会那样执着于什么。
就算一直不知道也没事,自己只需要去做自己能够做的事就可以了。比如像现在这样纠结着试图亲手为亲爱的制作一件饰品。
少女缓缓地呼出一口气,一丝丝的兴奋与甜蜜混杂进了这声叹息里。正当芙洛丽亚打算开始手头的工作,有什么旋律在引诱着她仰起头,于是她察觉到了在视野上方的边界处似乎有什么正在晃动。
【蜜糖的味道或许会引来早醒的夏虫。】
芙洛丽亚仰起头,眯起眼,仔细的观察那个以某种节奏正在晃动的事物。再三确认之后,就算再怎么怀疑也只能是现实,芙洛丽亚看到的是一双孩子的脚。
“…………???”
果然这世界上令人想不明白的事物实在是太多了。
而比起在原地费劲心思地去用贫瘠的脑瓜思考,对少女来说还是直接行动来得更快。芙洛丽亚放下了手里的杂物,撑着窗框就把身子探出去了一半。
“坐在那里——很危险的——!”
芙洛丽亚用尽量大声、也应该不会吵到邻里和正睡着的人的声音,对着屋檐上的孩子提醒道。对方听到了呼唤,于是就那样轻飘飘地离开了原地,它落了下来,着在了窗沿。
“晚上好。”
同为非人之物,不难察觉彼此的身份。而这反应在芙洛丽亚身上则更明显,因为此刻坐在窗边的孩子显然是比自己要更加——
“等下、这不是受伤了嘛!!”
察觉到了什么的少女心急地喊出声,无暇去顾忌是否会因此叫醒屋内的人,或是面前的人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她小心翼翼地捧起了有着不该属于孩童的斑驳的手,那些裂痕甚至一路向上蔓延至整只手臂,这怎么能让人不心疼。芙洛丽亚轻声的询问着那些不知是否是伤的痕迹痛不痛,然后取出了那些她辛苦攒了好一会儿的布料替面前的孩子包扎。
或有碎花、或是色调鲜亮的丝织品缠上孩子的胳膊将其保护起来。而那孩子至始至终面无表情,只是看着这些对于它来说不过繁重的累赘的布料,在少女还不怎么灵巧的双手下给它打上了一个有点歪的蝴蝶结。
“对不起,我还不是很擅长做这个……”
芙洛丽亚不好意思地捏着自己的裙摆,小心翼翼地试图观察对方的反应,便和正歪头打量着自己的它对上的视线。这让她更紧张了。
随后,她听到了一声轻轻的抽气。
El a ty ria fairytale cotton
Os di as eer tel ttil
Di a my rre merry maid cottom
Os di as go del ttil
像能扫空一切不安的清澈歌声在夜色中肆意流淌。
------------------------------------
芙洛丽亚记得,自己不久前似乎是做了梦。做了一个听着夏蝉的如细雨般的歌唱,和什么人一起欢快地起舞的梦。
那天早晨自己被亲爱的在窗边叫醒,本来还在紧张准备的惊喜要就此败露,然而小包裹不知为何不翼而飞,材料也只能从头攒起。不过因此惊喜没有被提前揭晓,就结果而言也是一件好事。
只是那梦中的旋律久久的萦绕在少女的心头,并不时地会想要借由嗓音冲出脑海与唇舌的桎梏。就连在那混乱的夜晚,在那呼吸交错着的奔跑之中也是如此。
芙洛丽亚不知道自己正拉着洛斯塔逃离具体的什么。她只知道那是危险的,是涉及到了她的爱人一直以来所怀抱着的秘密的事物,但若是会演变成这样的话,她甘愿永远地什么都不知道。
啊,自己是这样的无力。如此无力的自己,为了保护所爱之人,能做的究竟还剩下什么呢?
歌。它的歌。恋人的歌、爱的歌。那也便是自己的歌。
E vol fog nos sre vol fog nos
Ya dll ag nis anna wi ho
Ti so te vol peel so te vol
E nim fo e vol as I ti
唱吧。热烈的、热情的、热切的。
芙洛丽亚想着洛斯塔的笑、想着杂菜汤的味道、想着那个夜晚的月光、还想着刚刚那个男人的声音。这些依旧敌不过她手心里能感受到的那份颤抖,只是这点轻轻地摇动便足以让少女心碎到落泪。
脸上的温热迅速地消散在了晚风里。无助又弱小的家精在此刻能做的,仅仅是为她的爱人,献上那或许能扫空一切不安的曲调。




那天晚上,索菲亞·查普曼決定穿上她最為滿意的裙子和大衣去參加舞會。等她化完妝時,乳娘已經有些等不及了,站在她房間門口敲了第四次門。
“小姐,那小子已經來了有半個鐘頭了。”
“叫他再等會。”索菲亞站在她的鏡子前,開始挑選合適的女帽,紅色的太張揚,黑的顯老氣,她有點挑不過來,“他沒急吧?”
“倒是沒有,坐在客廳裡看書呢。您看我要不要給他點喝的?”
最後她挑了一頂紫羅蘭色的,這正是令她滿意的答案,她在鏡子前擺弄了一下帽子,覺得合適,於是便高聲回到:“不用,到了晚上有他喝的。”乳娘似乎明白過來什麼,很快就下樓了,從樓道傳來中年婦女重重的腳步聲。
索菲亞又花了點時間檢查了一番,才算打扮完了。等她輕巧地走下樓梯時,乳娘已經點了燈,她的舞伴蓋因尼斯·坎貝爾坐在沙發上,正看著一本雜誌,看到她來了,抬起眼睛來笑了笑並起了身。
蓋因尼斯·坎貝爾身材高挑,一頭紅髮,時常瞇著眼笑,給人種狐狸似的感覺,但你要是和他對視,他又會用年輕人真誠的眼睛看著你,正因如此才不會叫人覺得猥瑣。他出身英國,是哪個沒落貴族的小兒子,至於具體是哪個,索菲亞並不在意。她也知道,蓋因尼斯身上出過不少流言蜚語,可哪個都沒鬧大,以至於到後來人們都忘了他所謂的緋聞對象是誰,不僅如此,這些緋聞還為他本人平添了點奇特的魅力。誠然,他不是最佳的舞伴候選,可也不是最差的,至少在索菲亞能接觸到的人裡可以排個亞軍。
“在看什麼?”索菲亞問他道。
“這個月的《克萊爾》。”蓋因尼斯答道。
他們上了車。乳娘在門口看著他們離開,索菲亞看著她黝黑的皮膚化成路燈下一個剪影。蓋因尼斯話不多也不少,恰好叫他們不至於限於尷尬沉默的境地。等他們到了目的地的時候,天已黑魆魆的,蓋因尼斯為她開了車門,好叫她不必。
“挽著我的手。”索菲亞說。
“遵命,查普曼小姐。”他照做了,但兩人身體間恰好隔著一拳的距離。他們受到宅邸主人歐文·達德利的招呼,迎接他們的還有侍者手上的香檳,前者很快就對這兩位年輕的客人失去了興趣,轉而招待其他人了。此時,第一支舞還沒開始。
“你哥哥亞伯拉罕為什麼不參加舞會?”索菲亞因為酒精洩了口氣,她倚在希臘柱上,匿在蓋因尼斯身後。他們倆看著處在門口的達德利和招呼來的客人。來人也是一對舞伴,女人黑髮,帶著一頂漂亮的帽子,男的還很年輕。
“藝術家天生內向,不過我想,他本想邀請一位小姐的。”蓋因尼斯眨眨眼。索菲亞不大相信,但這話聽起來頗為受用,她因此稍稍恢復了些活力。
“那他該親自來,而不是讓他的弟弟過來代替他受氣,他的畫怎麼樣了?”她問。
“來靈感了,去了康尼島。”蓋因尼斯側過臉去,望著不遠處喜形於色的達德利,“那位小姐是?我第一次見。”
“是太太,霍爾·詹姆斯先生的夫人,她開了一家帽子店,我的帽子也是從她那裡買來的。很漂亮吧?”索菲亞道,她的男伴聳了聳肩。
“確實漂亮。”
那兩個初來乍到的客人進了舞廳,詹姆斯太太走路的步子十分優雅,像只高傲的貓,達德利則是隻聒噪的鴨子。至於年輕男伴,看起來雖然清秀,卻沒什麼存在感。
“當真?”
“嗯,人和帽子都是。”蓋因尼斯說,索菲亞被逗笑了,她不好意思地推了推蓋因尼斯,前者沒收了她的酒杯,讓侍者拿走了。
“聽說她在和她丈夫鬧離婚呢。”
舞會已經開始了。詹姆斯太太的男伴欠下身去,邀請他的女伴起舞,兩人的動作自始至終帶著種生分的遲緩。蓋因尼斯意識到那份距離感反倒使她顯得更為高貴,又或相反,因為她本身的高貴而產生距離,畢竟,人怎麼會因為同伴的生分而顯得高貴呢。
“怎麼說?”蓋因尼斯問索菲亞道。
顯然,他的女伴精於此道,但偏要裝作一副不甚了解的樣子,好留下一個好印象:“我平時對這些不怎麼感興趣,這件事是從我朋友那裡聽到的——詹姆斯先生沾花惹草,給詹姆斯太太丟臉了,可那位太太也不甘示弱,一來二去鬧得啼笑皆非。”
“可她看起來並不像是丟了臉的樣子……罷了,並不重要,您願意和我跳舞嗎?”蓋因尼斯伸出一隻手來,隔著手套吻了索菲亞的手指,後者咯咯笑著應了他的邀請。
“當然樂意。”
他們進了舞池,蓋因尼斯引導著索菲亞在人群中起舞,他跳得快活優雅,在那些隨著音樂地甩動四肢的美國人中顯得獨樹一幟,把舞伴也襯得粗俗。索菲亞緘默不語,頻頻踩上他的腳,不知是因為技藝不精還是出於報復。
在不協調的小號頻頻衝破薩克斯風的旋律後,蓋因尼斯開始放慢腳步。他不經意間瞥到了站在酒席上的太太。這次有了點新發現,一是詹姆斯太太的頭髮其實是暗紫色,只是因為光照容易看成純黑;二是她的高貴一般來源於神秘感,一般來源於一個他未踏足過的領域——兩者常被混同,但本質上相差甚遠。
他的好奇還未滿足,詹姆斯太太的視線便追了過來,這讓他出於禮貌移開了視線。恰巧,索菲亞踢了一腳他的小腿。蓋因尼斯並未追究,他照例以一拳的距離若即若離地環著索菲亞的手臂,兩人從舞池的中央旋轉著來到無人注意的角落。
“你哥哥,亞伯拉罕他擅長跳舞嗎?”索菲亞問,她在最後一段薩克斯風的獨奏中轉了個圈,他配合著做完了一切,隨後樂聲在一聲犀利的長音中戛然而止。顯然,這才是她真正關心的問題。
“沒我擅長,但也不錯。”蓋因尼斯眨了眨眼。
“你太惹眼了,搞得我有點緊張,於是跳得更糟。罷了,待會兒要是有人邀請我,我就繼續跳。”
她散伙的信息已經傳達得很明顯,他也就沒必要糾纏了,更何況他本就是為了頂替自己的哥哥邀請一位小姐才來的。蓋因尼斯於是走出了舞池,他聽到薩克斯風和小號變得更為悠揚。在明亮過頭的燈光下,詹姆斯太太還站在那兒看著舞池,她蒼白的臉上帶著一種虛浮的微笑,一如隔著一層薄霧。
蓋因尼斯深吸口氣。或許他該去問問那位太太——很難描述清楚是什麼驅使他這麼想的,間歇是一種自我毀滅式的好奇心。如果他被拒絕,那也無甚不可,當然最好是被接受。她沒跳第一場,但氣質應該會很適合交際舞。蓋因尼斯這麼想著走了過去,在那位夫人面前鞠了一躬。
“詹姆斯太太,請讓我邀請您共舞。”
“不需要用那個姓氏稱呼我,那太生分了。”她說,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多爾瑪麗,他們通常這麼叫我,當然……只是太太也可以。”
他意識到她並不喜歡那個姓氏代表的含義,這反倒讓他產生一種怪異的歸屬感:“那麼多爾瑪麗小姐,請讓我邀您共舞。”
他伸出一隻手,多爾瑪麗答應了他的請求,女人的指尖帶著股淡淡的煙草味兒,但並不像那些男子的煙味那般味道粗俗,反倒有股甘甜的香氣。在達德利金碧輝煌的大廳裡,又一首新舞曲演奏了起來。他們跳得很緩,像在熟悉彼此,又像似曾相識。他環著多爾瑪麗的臂膀,在對方裙擺的旋轉中意識到了什麼。
他知道他對她的好奇源於哪兒了,二十四年,這是他第一次見到這樣的人——不光是出於她的神秘。他生在歐洲,見過無數故弄玄虛的吉普賽人,滿腹經綸的神父,還有那些因瘋狂而無法理解的人,他們都是神秘的,但她不同。常人神秘是因為他們是未經開墾的處女地,而她本身便處在另一個世界。即便他再探尋下去也不會找到什麼結果,他有這種預感。
在不斷盤旋的音階、在逐漸趨於高潮的旋律中,他看到她的眼睛,她也在看他。多爾瑪麗有雙奇異的綠色眼睛,或許是之前離得太遠了,他現在才注意到這點。他聽到有人在驚呼窗外遙遠的煙花秀有多漂亮,可他並不那麼在意了。
“您的眼睛很漂亮。”他說,幾乎是句脫口而出的無心之言,多爾瑪麗笑了笑,拉著他的手完成了一個漂亮的旋轉,她跳得很好,優雅又充滿生氣,並不像一般的美國貴婦那般單純地隨著樂曲擺動手腳。
“抱我。”多爾瑪麗命令道。
“那您能只看我嗎?”他笑著討價還價,卻還是照做了。多爾瑪麗的腰沉在他的手臂上,她看向窗外的夜空,潔白的脖頸因為舞蹈的動作成了長弓似的曲線。在她身後,龐大多彩的煙花頻頻綻開,卻奪不走一點他的眼神。
也在此時,管樂到達了樂曲的頂峰,隨後便極快地衰弱了下去。人們在一場舞內飽脹的感情就像戳了氣的氣球那般消失了,又是短暫的休息,舞會的男女們再度互相交換起自己的舞伴。
這可能不妙。他想,多爾瑪麗鬆開了他的手臂,輕輕拍了拍他的胸前。他朝對方鞠了一躬,並吻了多爾瑪麗的手。隨後,他意識到有什麼自己的胸袋裡多了些什麼東西,他急忙將其和胸袋圈一同取了出來,卻看到意料外的東西。
那是一張名片,上面寫了一間衣帽店的地址,除此之外,就只有“多爾瑪麗”的署名。他呆呆地看了會兒那張名片,一抬頭卻看到那位神秘的太太已經走遠了。正當他愣神的時候,達德利用粗厚的手掌拍了拍他的後背,即便相隔不近也能聞到酒氣。
“蓋因,蓋因,來不來玩賭酒飛鏢?”
“當然。”
他坐上沙發,在一夥醉意盎然的紳士間笑著接過酒杯一飲而盡,隨後將空了的酒杯給了侍者。跟著一同脫手的還有達德利遞來的飛鏢。
那一擲正中靶心。
亞伯拉罕的腦袋被他打得碎爛。
人是死透了,一點呼吸都沒有了,用亞伯拉罕自己的話來說,死得不能再死。當然,亞伯拉罕現在也沒什麼話可說了。他低下頭去看著那具尸體,有些想發笑,但天氣太冷了,笑容在半途成了雙唇間一道扭曲的縫兒。
大街上冷冷清清,什麼人都沒有,夜色恰好成了塊骯髒的遮羞布。他在黑暗中看了一會兒那東西臉上的血窟窿,想起曾經還有人稱呼這東西為美男子——曼哈頓的太太小姐們似乎挺喜歡這張臉的,尤其是查普曼小姐。他常聽到有人稱讚這張臉有貴族氣質,可當一個人的五官上有個大洞的時候,再有氣質倒也看不出了,更何況亞伯拉罕的雙手不會再作畫了。這還不夠,他又用刀子破壞過了亞伯拉罕的五官才稍稍放了點心,這個行為並沒有給他什麼特殊的感覺,只讓他想起前幾天在晚餐前剁過的肉。
他甩了甩手套。晚冬讓尸體僵得很慢,可最初的血已經乾了。早些時候,他費了點力氣把他哥哥那頭被貴婦們讚賞的銀色長髮剃了下來,現在看著尸體光溜溜的腦袋,他開始覺得自己手藝不錯,或許可以考慮哪天去學學剪髮,畢竟理髮師永遠不會失業。他頗為幽默地為自己加上旁白。
他把石頭綁在曾是亞伯拉罕的肉塊身上,將之推入河流。隨著一聲激起浪花的巨響,尸體完全隱匿在夜晚奔騰的水流中,一如沉入黑暗本身,一同消失的還有他投在河上的倒影。
“晚安,做個噩夢。好好在地獄畫你的油畫吧,我的兄長。”
他又能睡個好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