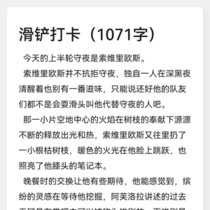本来想玩烂梗却连烂梗都无法玩成的烂文
全文3607
———————————————————————————————
A面:
“哈……哈……”
气温下降,手上沾着的粘稠液体也随之变冷,最后凝固。那东西干巴巴地皱缩在皮肤上,又随着动作皲裂,边缘的破片扎着皮肤,像要刺进去、寄生在身体里。
我讨厌这样的触感,又不知怎么收拾眼前的一切,更恼怒于罪魁祸首一脸轻松写意的闲像。我还很害怕。只能一边动作一边哭哭啼啼地骂起来:
“你为什么……怎么就……?”
“快点。”
那种事不关己的态度真叫人恼火,我一下子站起来,并且还因为蹲久了有点眩晕,脚下打滑。
他哈哈大笑。
“都是你的错!”我不得不压低声音,“你干嘛这样做?干嘛非得在今天?!”
“我们是朋友啊。”他没回答我的问题,“你会帮我解决的,对吧?”
我忍不住骂他:“你妈的!”
“别这样。你看,今天不是刚好……哈哈!”
我低下头。他说得对,我们不能被发现。
我只能蹲下去,继续手中的动作。
“咔擦——滋滋——”
刀子劈砍骨头,横拉几下,那东西被割开。
我沉默着作业。
B面:
耶琳·奈瑞莱斯的眉头不易察觉地跳了一下。
此时,血触小队已行过一个补给点,又经历过一场埋伏站,尽管没有表现出来,疲劳也仍在积攒。按照理想的状况,他们能在这个镇子休息一会儿,补充物资与武器,接着加快速度早日到达目标地点。一味地催促进度只会造成身心的疲惫,纳米兹·格林温尼斯的烦躁越发明显,她过多地挑衅多瑞安;半精灵忍耐也逐渐接近极限。作为队长,她希望任务完成前不要节外生枝。
——他们可以在任务结束后一较高下。
“不好意思,”棕头发的精灵开口确认,“也就是说,我们在祭典结束前都不能离开?”
镇长点点头,说:“不过也没那么那么久。明天就是祭典的最后一天,你们后天就能走了。”
听到这里,血触小队队长面色稍霁。她最后微笑一下,表示对话已经结束,接着就和在旁边等着的队员一起前往镇上唯一一个旅店。
这个不起眼的镇子名叫伍德罗特,一眼看去没什么大不了;但如果有人能从空中俯瞰,会看见镇上房屋的排列如同树根一般从一点开始,向四周散开,而处于“源头”的那一点上坐落着一桩巨大的树桩,据说和镇子的起源很有些渊源。不过耶琳没兴趣,也就没细问。她关注的只有:他们究竟什么时候能走?
“真是无聊!”纳米兹一脚踢开脚边的小石子,“对了,有什么不能做的事吗?一般都有的吧!比如什么禁忌的地方、不能做的事、绝对不可以触碰的宝物!”
嘴上说着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三流恐怖故事中绝对会被做的事,冷色头发的精灵倒显得很兴奋。如果一个衣柜上贴着“不要打开!”(加粗加重)的字条,她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啪!”一下拉开柜门吧。
“今夜不要靠近树根。”
说完,奈瑞莱斯敲敲腰边的盒子。格林温尼斯明白了她的暗示,挑挑眉毛。不过她也明白任务的重要性,因此并没有如在其他人手下时一般发作。
再说,难得有合心意的上司,干嘛为了一点乐子而丢掉大局呢?
在心中作出如此结论后,她又高兴起来,盘算起武器补给的事。
这天晚上就这样平淡无奇地过去了。
A面:
他又哈哈笑起来。
我快烦死了,要不是场合不对,我非得踢他一脚。
作为事件的主角之一,捷特站在前面,他的脸涨得通红,下颌紧咬,原本俊朗的脸因为他脖子上绽起的青筋显得古怪扭曲。看到他那副样子,我不由得往人群里缩了缩。没人会在意我的动作——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捷特对面的人。在铠甲外还罩着一层兜帽的男人站在他们那个团队(“凶手!”有人这么叫)的最前方,也正是因为他那样子,今早镇子上的居民去叫他们时还算礼貌。男人后面是两个女性精灵,站在他们中间的是镇长和一个壮年男人,他今天才到镇子上来,自称是那群冒险者的朋友,正试图为友人洗刷冤屈。
有凶手就会有受害人。
我最好的朋友,或者说那个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的东西,躺在地上。她的头被摆在“那个”树桩上,胴体和四肢分开,肢体也从关节处被卸开。被切割的不成样子的躯体凭借下面挖的浅坑立稳,四肢随随便便地由什么东西串起来,野外宿营时串肉串的串法,左手的小臂插进右腿大腿的中间,右手的小臂插进左腿的小腿,再插进立着的胴体。
——看起来就像一株树。
就算在这种情况下,她也如此美丽。
我不由得哭起来。
我哭了一会儿,听见深棕色头发的精灵说话:“的确不是我们。一来我们与她素不相识,二来我们只是路过……”
“她的意思是‘我们干嘛费这事儿’。”他笑嘻嘻地说。
混球!
“除了你们还能是谁?!”捷特大吼起来,“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自从你们来了……都是你们来了!!我们明明都要……”
人群中的谈话声大起来。我躲在人群里偷偷瞧他。
冷色短发的女精灵嗤笑一下,说:“我们可没那个磨洋工的时间。”
“这女人了不得。”他点评道。
“三天!”自称是冒险者友人的人也提高音量。他举起三根手指,试图用大声音压下四周的议论:“给我三天时间找出凶手!”
镇长叹一口气,同意了他的请求。
“虚伪,”他又说,“这老头只想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妈的!还不是因为你!
我看不下去了,准备转身离开。在我最后看向捷特时,我注意到另一道目光。是那个棕色头发的精灵。
她看着我,微微笑了一下。
我赶紧离开。
B面:
“我等不下去了。”纳米兹·格林温尼斯宣布。
奈瑞莱斯笑一下,说:“才第一天都没过完呢。”
“可是亲爱的,我们不是还得赶路吗?”精灵战士靠过去,“我们今天就走吧!好不好,好不好?”
多瑞安没说话。他被从原来的屋子里赶出来,不得不和队内的另外两个精灵住在一起,这让他更显阴沉。半精灵想起之前被那个人类拽住领子时奈瑞莱斯的一句“住手”,那是下达给他的命令。他不能理解,这还有什么好忍的?
“喂,你也很想走,对吧?”
格林温尼斯突然将话题抛给多瑞安,多瑞安侧过脸,看她一眼。
冷色头发的战士翘起唇角:“我看见了哦,你当时把手搭在剑柄上了。”
你不也是吗。黑发的战士抿一下唇,没把这句话说出来。
咚咚。
女精灵还打算说什么,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打断了她。
他们互相看一下,最后耶琳·奈瑞莱斯起身,走到门边。
“是谁?”她问。
“送饭的。”
精灵停顿一下,打开门。
站在门外的是金黄发色的青年,看起来乐观开朗。
“刚刚真的有点对不起,”他说,“捷特平时不是那样……等他冷静下来想清楚了,你们应该也就可以走了。”
“……”
血触小队的毒使沉思片刻,随后露出一个微笑。
A面:
那伙人立刻就可以走了。
一开始我不信,可后来他们的确光明正大地走在街上。我挤进人群,看见他们围着捷特和他的好朋友。
他伸脖子看了一眼,说:“真可惜,那男的人还不错。”
我不懂他的意思。
旁边的大人看见我,对我说起话来。我呆呆地看着躺在地上的贝鲁和捷特,男人已经死了,面上显出死亡的灰色。他的七窍流出鲜血,胸前一道深刻的伤痕。捷特跪在地上,将他的头抱在怀里。
“嚯,了不得,”他说,“听见那老太婆说的了吗?现在变成了贝鲁因为嫉妒打算横刀夺爱杀死新娘,又不知发什么疯打算杀了那伙外来的,结果反被对方一刀砍死。哎呀,真过分。”
“不可能!”我忍不住尖叫起来。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因为、因为——
旁边的婶婶见到我这副样子,开始安慰我:“哎,我知道你和那孩子关系好,和贝鲁他们也不错,可惜……”
“大家都看见了……”
“他突然——”
议论的声音渐渐淹没我。
B面:
“哈哈哈哈哈!”纳米兹·格林温尼斯笑得东倒西歪。
“啊——”她擦一下笑出来的眼泪,“我的好队长,可真有你的!”
耶琳·奈瑞莱斯微笑着收下这句夸赞。
“只能说人类真是太笨了!眼睛没我们看得远,耳朵没我们听得细,脑子更是蠢得像猪!线索明明有那么多,他们却只看见从别处来的我们——”
突然,她话锋一转,带上点考察的意思:“好队长,告诉我,你是从什么时候看出来的?”
“什么时候……大概从看见那个脚印是开始吧。”
冷淡发色的精灵满意地点点头,接着说下去:“就是啊,那明明是个小姑娘的脚印嘛!”
A面:
我在镇子外围的农田里看见那个女人。
她的手里拿着一个细颈玻璃瓶,里面装了些粉末,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还挺好看。
“呀,你好。”她一边朝我打招呼,一边将瓶子里的粉末倒出来。那些粉末乘着风落在农田各处。
我装出一副什么也不怕的样子,问:“你是来找我的吗?”
“你?我找的可不是你。”
不是我?这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来找我的咯?”
我的嘴动起来。不对,这不对,为什么我听见他的声音。我慌起来,想闭紧嘴巴,可什么也没法改变。
“既不杀了我,也不放过我……你到底想怎样?”
“为什么要那么做?”
哈哈哈哈哈。
我听见我自己的笑声:“虽然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件事……因为嫉妒吧。哈哈,那是什么表情,你觉得很无聊?你根本不懂!我真的,真的很喜欢她。可她为什么不看我。她为什么不看我?我好恨……我好恨!凭什么!最懂她的是我,和她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也是我,她却偏偏选了别的人!……”
“剩下的那只手呢?”
“哈哈,反正都现在了,告诉你也无妨。……我收起来了。我把皮肉剔下,留下骨头,做成笛子。她要永远陪着我。她要知道我的唇吻着她的骨头。”
是我在说话。
深色头发的精灵咪一下眼睛,说:“好,我们现在来玩个游戏。我数十下,你跑,要是你跑得快,我就放过你。现在开始。”
十。
九。
八。
……
B面:
听到这里,纳米兹抱怨起来:“干嘛放她走啊!”
耶琳却笑起来。
她说:
“因为,这不是很有趣吗?”
本事件End.
旅途Tbc.
———————————————————————————————
并未出现的烂梗如下
阴沉面具男:队长,你是了解我的。我只对折磨人感兴趣。
纳米兹:队长,你是了解我的。我一向干净利落。
队长:我看出来了,你们是个个身怀绝技。






字数:2594
战斗参见:http://elfartworld.com/works/9107354/
审问参见:http://elfartworld.com/works/9107367/
感恩的心感谢队友们画了这么多让我摸(……)
————————————
“你知道吗?把老鼠放进碗里扣起来,然后不停地敲,老鼠就会往最柔软的地方打洞……等等,”法鳞忽然扭过头来,“我们有碗吗?”
“呃。”
在他哽住的同时拉克斯劳夫伸手过来敲了敲他的胸甲,动作自然流畅,“这也是碗形。”
“那么我们有碗。”莱丝汀把头扭回去,继续用她严肃冷淡的表情看着俘虏。
俗话说得好,一百桩抢劫里,九十九桩都起源于一时冲动,所以卫兵们才总是能在现场找到是什么和房主人脑门进行过亲切接触,显然拷问也是这样。
————————————
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这句话的意思在当下可以解释为:如果在一趟公务旅程中你实在没什么事情好做,可以选择性地开始发掘同行者们身上的优点,哪怕结论是没有——那么恭喜你,你知道需要丢下一个人的时候该先丢下谁了。此外这项娱乐活动还有一些更具收获感的变体,比如把优点改成缺点什么的……
碍于一些情况-法鳞和拉克斯劳夫回林子里去了,后者认为在水里全面地泡过一遭可能还不足以去掉他们沾上的东西,前者在伊莱恩的注视下点头认可-能让他玩这个的人就只剩下了伊莱恩本人。
伊莱恩·阿莫米安,有一类人就是这样,集合时第一个到,喝酒时最后一个醉,所以通常也能是第一个或者最后一个平安回来的人;而这种人往往也不会很多,毕竟一张桌子上只有一个最后喝醉的人是最妥当的,如果有两个,情形就会演变得有些尴尬、相当尴尬,因为有些东西只在所有人都清醒或者只有一个人清醒时才能存放在水面下,两个人的时候就会被迫浮上水面,就像现在。
那几串拉克斯劳夫精心烹调(以野外标准来说)的虫子已经在火堆上辗转反侧出了一些焦味。
林恩松开了被他转着玩了最少二十分钟的钎子。
唉,这就是他说过的尴尬之处了。伊莱恩不会问他为什么一直在玩那根之前是拉克斯劳夫备用武器的烧烤钎子,也不会问他为什么醉在跳河之后暖身的饮酒里,又这么快清醒了回来,就像他也不会问伊莱恩为什么同意了那两个人一起去单独行动。毕竟如果有得选,他想伊莱恩也想要一份更轻松的工作。一份不用连决定怎么处理一些吃的都像在博弈的工作。
好吧,这就是博弈。一些,怎么说?那个很新颖精致的词汇,公事房间里的博弈。就是那种坐在办理公事房间里的人,彼此计较一些这份垃圾是你来丢,还是我来丢,如果你丢了说明你认可我的权威和方针之类的行为。
他抖抖手腕拎起了那几串虫子,希望这约等于向可敬的队长表达了他和他对队伍安定的向往完全一致,再没什么置身事外了的请愿。
——唯一令人欣慰的,站起来的时候他好像感觉到了一点凉爽,就像哪里终于忽然刮起了风。
————————————
杰克是瑞姆克尔最普通的那一种人。
他出生的时候梵沾血的旗帜已经在他祖祖辈辈的土地上安插了很久很久,久到比他能记住的最远的祖辈的名字还久。但他有八个兄弟姐妹,他的父亲有六个,他的母亲有十个,所以从他的父母再到他父母的父母都没人有工夫思考一些关于,比如,噢,在鲜血骑士团之前,咱们的领主是谁呢?咱们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那些季节神殿里的神除了季节,祂们还代表着什么别的呢?祂们的季节也像秋天一样萧条而肃杀吗?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诸如这些之类的种种问题。
杰克也没想过。他长得很瘦小,他出生到长大期间正好是最贫穷的几年,一些战争来战争去的东西吧,这个词在他的观念里类似于冬天会下雪,而下雪了就会冷一样,是一种不那么有规律的规律,也就是如果它来了,那也没什么办法的意思。
他长啊长,一年度过五个季节,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战争,可能是多过的这个季节让他长得比别人慢,让他一直都像小时候那么瘦小,让他在有一些人来挑选可靠的未来战士时因为他的瘦小而被青睐。
这会是个游荡者的好苗子。
于是他的父母就说,哦,好吧,那么请您带走他吧,为了梵带走他吧。
然后又是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天,他说,嘿,长官,我们的任务是结束了对吗?我们只剩下要回到驻地这件事了对吗?有人点了点头,于是他又问道,那我能离开半天吗,我会追上你们的,我想回家看看,就在这里往北十几公里,我很多年没回去过了。
他的长官用一种他从没见过的温和神情同意了他。
所以他就见到了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被选作战场的,他祖祖辈辈的土地。
他想,哦,是这样没错,先选走一些孩子,剩下的消耗箭矢,填平壕沟,是这样没错,梵是这样没错。
那天的队友里再也没人见过杰克。他们觉得杰克可能做了逃兵。
————————————
浇花的时候浇到路人的脑门上;
没看住的羊钻进同村的菜地里;
你养的狗对月抒情时你的邻居正在饱受失眠困扰刚刚安睡;
普通人的生活里也免不了一些仇怨,对吧?而如果你是一名鲜血骑士,只要把会招来的仇怨再预计往上提个二十三倍左右、呃,可能是仇恨,总之,二十三倍,从质量到数量,你就做好应付它们的准备了,不管是什么。
意思就是,他真的不记得她是谁,他又对她或者她们做过什么了。另外,一边想别的一边打架也不是个好习惯,所以他赢了而她死了。
他盯着那张大半被烧伤覆盖的脸试图想起来点什么,那根被割开的喉管里还在汩汩地往外涌着,让他想起之前它嘶哑又尖厉的嗓音,应该是在质问他不记得了,或者问他们。火?火在梵的行动里那可完全不少见,太勤劳和太懒惰都能用它-哗,一把火过去,什么都没了。
树林里传出了他们约好的安全信号,他活动了两下肩膀,看见伊莱恩正忙着在另一具尸体上擦干净剑上的血;于是他吹了声口哨,指了指地上被他拿来扎穿过女袭击者肩膀的烧烤钎子说:
往好想,至少咱们不用想怎么丢掉这些烧烤了。
————————————
如果有得选,相信菲诺的牧师不是什么好选择。
那个并未穿着甲胄的牧师找上他们时,杰克相信没有人相信她——相信她们想反抗梵不如先相信她们改信了兀烈卡卡。
他们的不信任就像一顿饭菜摆在餐桌上一样摆在脸上,摆在肢体里,却又没人走开,于是最懂得人心勾当的牧师对他们露出了微笑。
噢,何不先听听我能给你们带来什么呢?两个战士,一个巡林客和一个德鲁伊,一行四人,只有四个,就在旅店里,明天将要扎进那片林子里去;而我呢?却刚好学会了一些吸引你们最讨厌的那种虫子的办法。
你们大可先去瞧瞧。
第二次从旅店门口经过的时候,他看到雷丽安娜干瘪蜷缩的眼窝里那颗眼球剧烈地震颤着,让斗篷下她面庞上一卷一卷翻起的皮肉像是深深的,干涸的血红的沟壑。
如果有得选,相信菲诺的牧师并不是什么好选择。但他们太渴望了,他们的渴望有多么多,他们的选择就有多么少。
————————————
“拉克斯劳夫杀了一个牧师阻止她施放神术。”莱丝汀·多纳汇报道。
然后她挥了挥手,一团纠葛在她脚边的藤蔓松开了一点,露出裹在里面的东西,“还有我俘虏了一个游荡者。你们有人会审问吗?”
沉默在河边持续了一小会儿。
故事回到开头。


字数:2679
当透过雾气的稀薄阳光无法再提供更好的视野时,墟歌就近选了个空旷的位置驻扎休息,阿琳和梅德把枯枝和碎石清理出来搭营火,山月桂和索维里欧斯在营地附近展开搜索。最近没有太多的雨水,干燥的枯枝很快就被点燃,暖光照亮了两位法鳞的眼睛,也为队友提供了清晰的方向信标。阿琳抬着斧子去薅了几根粗枝回来搭烤架,尽管梅德一直背对着没有看见,但听声音她大概是放倒了一整棵枯木。
阿琳大多数时候都只会这样不修边幅地进行破坏,战斗技巧实在是少得令人困惑她是怎么从厮杀里活下来的,收集情报是游荡者的职业领域之一,细致观察则已接近于本能,他能够看出那个女孩的蛮力下还藏了些别的,可以说她遮掩的方式和她目前的表现一样简单暴力,破绽百出,但摆出如此拙劣的面具似乎也没有特定强烈的意图。在沉默的揣测之中,山月桂和索维里欧斯带着清水和食物回来了。
野蔬汤咕噜咕噜冒着泡,阿芙洛拉把洗好的蘑菇也放了进去,拿着削好的树枝搅了搅,晚餐只能算是在果腹的基础上尽量做到锦上添花,迷雾隐藏了墟歌的行踪,他们的行进速度并不快,至少到现在还没有接近城市,这同时也意味着稀缺的野外资源,快要饿死的老鼠都不会钻进雾里找吃的。能在朽木上采一些菌菇,在石缝里找一点蔫巴的野菜大概是极限了。
尽管如此全队还是决定舍弃较为舒适的无雾路线,谨慎行事总是没错的。山月桂端起水杯,在吹散杯口的水雾之前不动声色抬起锈红的眼睛。即使在同一个团队,所有人都很少进行沟通,战斗时也几乎没有配合可言,山月桂倒是不讨厌这种气氛,她无需面对太多有探究意味的目光和含沙射影的问题…只是今天貌似有点不一样,阿芙洛拉看起来坐立不安,她心不在焉地吃饭,频繁望向吟游诗人。
吸血裔沉默着把面包片泡进汤里,好让这点硬得能拿来砸人的干粮变得容易下咽一些。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阿琳不会真的把面包当暗器丢索维里欧斯的脑袋。她想。
“你唱歌很好听…”
这样的开场白显得相当生硬,交涉还没开始就快要把天聊死了,但好在真诚的称赞比虚伪的阿谀奉承要顺耳。况且谁都能看出来她从扎营开始就欲言又止了。
“谢谢。“
“…可以再唱一次吗?”
这倒是让索维里欧斯有些意外,甚至感到好笑地抿唇。
没有获得回应的小法鳞肉眼可见地慌张起来,从口袋到袖子的暗格摸了个遍只凑出来一点点财物,她窘迫地捧着银币,以为这是在酬劳上出的岔子。
“但是只有这点…要打欠条吗?”
不知道是那个永远藏在阿芙洛拉影子下的人故意为之,又或者这是她潜意识构建的心理壁垒,她大多数时间里心智更偏向孩童,只有在挥落斧子时,于兵刃斧面的倒影中才会窥见她原本的样子。这让索维里欧斯不禁思考,如果能扯下她那点岌岌可危的掩饰,也许故事会变得更有趣。
诗人暗自衡量了片刻,大概两次眨眼的时间,他想到了更好的解决方法。
“阿琳,艺术可以是一种情感,而情感不与金钱相论。不如用你的故事来换吧?”
“我的故事…?”
她看起来很茫然,故事和传奇向来出于伟人,一个只活了十几年的法鳞,其经历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也略显寒碜。
“对,用你的过去换我的歌,怎么样?”
“…不是好故事,也可以吗?”
阿琳犹豫地将捧着银币的手收回,看看索维里欧斯又看了看他的身后,像是在反复确认。
“诗歌从不只传唱美好。”
她开始断断续续地讲述,从清晨带着果篮去赶集到傍晚带着小麦和蔬菜回家,从一封带着圣徽戳记的信到远游的亲人归来,从一个充满苹果派馥郁甜香的下午到只剩血腥味道的夜晚。她只在画像里见过却无比憧憬的亲人,那条有三个弯的小路,从窗边远远地看见,那个人影带着兜帽,背着一把长矛,他走在黄昏熄灭成黑夜的界限上。
如同幻象一般,索维里欧斯站在那个狭小朴素却装满温馨的小屋,女孩趴在窗边半个人都探出去不停地向人影招手。阿芙洛拉的话语编织出阿法纳西的模样
“双色的衣袖,战神的圣徽,锋利的长矛。“
——一个墟歌骑士的模样。
男人摘下了兜帽,他的脸上纵横着四道疤痕,除去了疼痛后这些便成为了勇敢者的勋章,他环视了一圈最后视线落在阿芙洛拉亮晶晶的双眼,这个血脉相连的陌生人。他像个有些笨手笨脚的长辈,摸了摸妹妹的头顶却把霞色的长发揉乱了。阿芙洛拉像一只金丝雀缠着他转,让他讲这个小屋外的广袤世界。
“在雾里的时候很容易丢失方向感和对时间的把量,所以行动时以自己的体力为标尺,永远要留下撤退的后路,注意听,它们会为你指明方向。”
“他们?”
雾气是不死者征战的硝烟,铁骑过境时扬起的烟尘,人们学会如何与雾共存却从未放下那份畏惧,畏惧死亡,这是生物的本能。阿法纳西却若无其事地拿捏着这份本能,他的妹妹显然没有听懂这段没头没尾的话。
(旁听的梅德懂了,这对兄妹把天聊死的技能一脉相承,啧啧。)
听不懂归听不懂,她还是没有无礼地插话。也不知道阿法纳西有没有发现妹妹完全懵了的眼神,反正一个敢讲一个敢听。这种尴尬的相处维持到了他们准备餐前祷告的时候。变故也是在这一刻发生的,所有人都闭眼低头时阿法纳西极快地拧断了父母的脖子,抄起长矛捅死了姨母,又反手勒死了睁开眼吓得从椅子上跳起来的叔父。
“我看见了全部,因为大家都在认真祷告,而我更好奇哥哥的样子,所以我眯着眼偷看了。”
火苗在异色的虹膜上跳跃,阿芙洛拉单手支着脑袋,在摆动的光影下莞尔。
“妈妈倒在椅子上,爸爸的脸埋在汤碗里,长矛扎破了姨母的心脏,她的血溅到天花板和吊灯上,她才发出半声尖叫就死了,叔父当时吓得从椅子上滚下来,手脚并用地逃跑,然后被轻而易举地勒住脖子,他的脸憋成青紫色之后断了气。爸爸妈妈没来得及睁开眼,姨母叔父没来得及合上眼。我感觉自己冻住了,直挺挺地戳在那里,好久我才反应过来我的脖子没断,身上也没有窟窿,是姨母的血溅到我了。哥哥说,你没有哭,这很好。记住,在恰当的时机出手会节省很多工作量。”
她说话的语气很平静,像是一片吞没了尸骨的沼泽。
“然后他教我如何在猎物身上取得有价值的部分,那时我才发现,原来我们还有个小表弟…嗯…也可能是小表妹,他还没成型,我看不出来。”
那丝怜悯听起来竟像是讥讽。
“他刮掉我的皮肉以鳞片取而代之,当他问我感觉怎么样的时候我突然发觉这一切都像荒诞剧,而我是最滑稽的那个。天亮了,我们坐上赶集的牛车,所有人都低着头或者错开了视线,但是我听到了,他们一定在心里嘀咕,梵,暴徒,可怕的家伙。”
她的眉眼看起来很悲哀但嘴角却是笑着的。
“这些东西令我如覆针毡,令我无法入睡,所以他唱歌哄我睡觉。”
阿芙洛拉转头盯着索维里欧斯,然后视线再次越过他的肩头望向伸手不见五指的方向。
“那么…今晚我能有幸在休息前听到你的歌吗?”
“——当然。“
吟游诗人决定不继续追问小牧师在雾里看到了什么,让这些秘密与幻象如影随形,反正,它们无论如何肯定会继续在深夜拜访阿芙洛拉的梦。
火堆燃烧噼啪轻响,美妙的歌声在雾中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