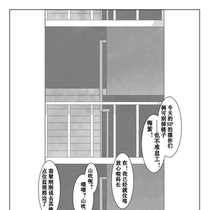在随父母搬到斯特恩比尔特以前,我住在一个格外偏僻的山村——三面都被葱郁的山林包裹,唯一通向外界的方式是顺着河水漂流到不知何方。使我有时回忆起总会想,如果在几百年前,应该会与世隔绝成另一种文明也说不定吧?
不过到我出生的时候已经是现代了。
我居住的地方依然被山林裹挟着,也不过是因为山林被另一种名为生态保护的东西裹挟着罢了,于是没有从这里离开的人们,也作为生态的一环依然被淳朴和无知这样一体两面的东西裹挟着,直到有一天像我的父母一样登上船舶。
而当回头眺望过去时,人往往除却感慨就是在羞惭,其中格外介怀的那些,部分人,比方说我,也只有将它与青涩的自我皆踏在脚下时方才得以释怀片刻。
在被迫听从父母的建议离开老家的前一晚,我决心做一次叛逆的小孩。
此前说过,我的老家被三面茂盛的山林牢牢环绕在其中,如果白天从村落里眺望是葱郁的话,那么夜晚走近时就是全然的阴森了。远方之于青少年而言高大的枝条纠缠成密不透月光、好似扣罩在群山之上的牢笼;而哪怕是最近的竹林,夜风吹过时摇曳的叶影间仍会发出叫我毛骨悚然的声响。
而在当时,我和我的玩伴们就像这样紧紧相依相偎着,互相打着气走在晚间的野路上。
——我的恐惧,或者说,每个年龄与我相仿的玩伴的恐惧自然并非空穴来风,我们的睡前故事仍然落后地被以恐惧为核心主导着:将蹦蹦跳跳走过田埂的人抽打进烂泥地里的舂米婆,专门把上半身探出船舷的人拽进河底的船幽灵,还有只在雾气弥漫的山里出现,有着乌鸦一样漆黑翅膀和帽子,所有见过它的人都会惨遭厄运的天狗。
如今想来这些堪比安全手册的故事传说自然是大人们为了劝诫而一代代编造流传下来的,那时的我却比谁都更加地深信不疑着,以至于抱着“让听不进去孩子意见的父母们后悔”的念头也要纠集伙伴、强忍恐惧前往据说会有天狗出现的竹林——当然,最终我们白白地在恐惧和寒冷里挨了半个小时的冻。
怀揣着对离开一事显然已经无可转圜了的愤恨与惴惴不安,第二天的下午,我还是和大包小包一起乘上了离开的船舶;而真正叫我至今难以释怀,乃至几近成为一块心病的事情,实则发生在抵达斯特恩比尔特的那一天。
——坐上船的头一个小时,我就被迫发现了我对广大交通工具几乎都患有同等的晕动症。导致数日后斯特恩比尔特就近在我眼前时,我对它和它代表的那个世界仍然像刚刚走出家门时那样一无所知。
那天的雾气大得惊人,只是因为在寒冷的海港边才显得不那么叫人生疑,我紧紧地攥着父母的衣角,说不好是被背后的轮船还是面前远眺处另一个世界般高高穿梭在天际的桥梁们搞得头晕目眩,而巨大的轰鸣声也就是在这一刻降临到了海港的人群们头顶。
好像某种比看见了天狗还要不祥的征兆似得,我的父亲一把将我扛上了肩头,骤然拉高的视野里惴惴不安和惊惶占据了半数人的面庞,我跟着他们的视线一起试图眺望天空,只看见一架涂装成红黄蓝三色的直升飞机(显然这是我现在的补充)正在快速地靠拢这里,最终悬停在了我们的头顶之上——顿时,人群里剩下的那半数兴奋面孔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渐渐响起的跑动声。
我彷徨无知地被父母紧抱着加入了试图涌出港口的人流,雾气开始浓得呛鼻,周围尽是或压抑或撕心裂肺的咳喘声,连带着我自己也开始感到喉咙痒得奇怪-在我终于打算咳嗽上一声的时候,我听见了一道极近的,痛苦的咳声。
抱着我的父亲带着我一道倒向了地面。
疼痛和恐惧一时间不分先后地涌进了我的大脑,我叫着爸爸和妈妈,艰难地挣出父亲的胳膊,却在下一秒又被少数仍在移动的人流远远地裹挟了出去,我大叫,听见母亲一样在呼喊我的名字,在泥浆一样浓稠的雾气里却只能看见几片各色的衣摆,直到微弱的亮光刺痛我的眼睛才发现自己早已在慌乱中跑到了不知何方。
我摸索着,摸索着,沿着冰冷的墙壁,到那种冰冷已经快使我麻木的时候,指尖忽然触碰到的温热反倒使我发出了掐着嗓子的惊叫。
而我完全正确了。我绝望的神情让那个戴着防毒面具的男人眼里盛满了莫大的快意。
但他不明白的是,真正让我从惊慌进而到无可抑制的绝望的是从他背后浮现出的那双禽类般荧黄的眼睛。
“我碰到你了。”
不祥的红光顿时取代了那个男人面具上原本闪烁着的绿灯,我看着他从洋洋得意到不可置信般地伸出双手钳住自己的喉咙,只用了几秒就像虾米似得蜷缩在了那个戴着乌鸦般漆黑帽子的身影前。
那一天我最后的记忆是我爆发出了恐惧到极点的嚎哭。
当我再度醒来的时候是在医院的病床上、与其说是醒来不如说是被四面八方包围着我的呻吟声惊醒。入目所及的是洁白的天花板,还有周围与这份洁白格格不入的大量病床——斯特恩比尔特的市民们供养起英雄,斯特恩比尔特自然对这出常常上演的英雄罪犯追逃戏码里的背景演员们有一套完整的善后流程。
完全没有意识到事件早已落幕的我又一次爆发出的哭叫声也自然吸引来了护士的脚步。
——我乱七八糟地用嘶哑的嗓音和挥舞的手臂试图对她表达出我想说的内容,包括我的爸爸妈妈在哪里,我喉咙好痛,我看到了戴乌帽子和黄眼睛的天狗等等等等——她递给我纸杯,告诉我等我父母也醒来他们就会找到我,才对着我所说的,关于天狗的内容沉吟了起来。
“啊,‘我碰到你了’还有黄色的眼睛……是在说‘赤茶’吧!”
当然的,我难以置信的表情逗乐了她,我隐约意识到了事情显然并不如我所想那般,而比那更糟的是,我更加意识到、我沦落成了无知的那一方。
那以后的事情在我的记忆里已经不甚清晰了。父亲是如何死掉的,母亲不仅是因为痛失所爱的哭声……我只记得那场和护士的对话-最终结束于病房的荧幕即将播放一天前精彩绝伦的港口毒雾事件抓捕片段,她惊喜道如果见过赤茶,我也说不定会在镜头里出现——而我则立刻装作困倦不已的样子在她走后用被子紧紧蒙住了脑袋。
从医院离开后,我终于开始真正地生活在斯特恩比尔特。
我的母亲非常努力,让我在仅仅需要勤工俭学的情况下顺利读到了高中,而越是与同龄人朝夕为伴,就越发令我察觉-与其说是无知,不若说对于我而言从荧幕和书本上学习的知识,之于他们却是比空气和流水更加自然的常识。
我对自我价值的确认,抑或说,我的自恋被我所发现的现实痛苦地瓦解了。
我开始梦魇,梦境里反复出现那双禽鸟般荧黄的眼睛,于是某一段时间里我又沉浸在对Next,对英雄的愤恨之中——快乐之于我便是作为一个独特的人,所感受到的独属于自己的快乐-体验到自己的独特的过程,那么,还有比Next更作为一个独特的个体令我嫉羡的对象吗?
怀揣着这样的心思,我从高中顺利地毕业了。
——然后是两年以参与工作为目标的培训和学习课程,如果要说社会在一百年以内真正的进步在于何处,我认为意识到绝大部分光鲜亮丽的白领岗位实际上并不需要用至少四年的学习才能胜任这点应当算作一处。
说实话,到这个时候我对于自恋也好,独特和Next也好的愤恨和思考已经快要被永无休止的实习消磨殆尽了,介于学生和社会人士之间的这道身份对于企业家正是剥削里最好的下酒菜,等到终于开始入校招聘和投放简历的时候,我的脑子里简直已经只剩下了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网址。
幸运的,我最终在彻底踏出校门前找到了一份工作。
“——啊!长得这么可爱就不要去做那种累人的事情了,我看看……长谷川……来跟前辈我跑个外勤吧?”
然后这就是我所接到的第二件工作了。我的上司大西娜塔莉亚女士对我说道。
“嗯嗯……完全没什么难办的,艰难的部分早就有人谈好了,只差轻轻地摘掉果实……话说这么直白地带初出茅庐的雏鸟去做只拿钱不出力的工作好像会显得我很肮脏的样子啊……诶,总之先把这个注意事项看了!”
娜塔莉亚女士一把将一张明黄色的便签纸举到了我面前,从她背后的玻璃幕墙能看见黄昏早已西斜到了城市的另一头,也就是说,整个宣传一科的办公区域里早就只剩下我和她而已了。
我查看着附带念出了便签纸上的内容:“第一,绝不主动进行身体接触;第二,尽量杜绝被动身体接触;第三,……带个御守有用吗?”
这种跟怪谈一样的东西……可能是发觉了我眼神里的复杂,娜塔莉亚女士伸出一根手指对我晃了晃,“尽早适应跟英雄们打交道的方式吧,从咱们未来的宣传路线上看绝对——有好处。”
比起英雄见恶鬼的注意事项都没这么让人不安吧,我难以自制地想到,但一样众所周知的是花吹药妆的宣传一科并没有属于自身的英雄,所以……
“英雄……?是要去签约英雄,之类的吗?”
“是啦是啦,把这个拿上显得你也有活干一点好了。”
娜塔莉亚女士一边走向门口的方向一边从手包里拿出了什么东西丢向了我,“啊,对了。
“——我们可从来不是那种有英雄崇拜倾向的公司啊,注意事项还是好好遵守为妙哦?毕竟正因为是英雄,作为Next的时候才更危险嘛。”
“节目的伦理审查都通过了……观众的时代啊观众的时代。
“啊,所以也是节目的时代啊、直接来看这个吧千屋君,对纸制品有把它们打印出来的尊重就行了。适应一下吧。”
在他眼前,约瑟夫·纳尔逊,或者说,花吹药妆宣传一科的科长直接将塞满一整本活页夹的打印纸堆放到了整张办公桌离他最远的角落,显然没有在接下来的微型会议里再动用它们的意思。
“然后顺手把温度也调高一点,遥控在你左手边茶几上,让罪犯感觉寒冷就够了,——好了,来看欢迎你复出的第一件大事吧,‘疑似数十人遇害的轮回怪谈’啊……”
如果说一个时代已经成为了观众的时代,那么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做好成为演员的准备。
而又如果说九年前让千屋幸之介本人下定决心成为舞台上最主动的演员、即英雄的理由之一正是他不幸顿悟了这条理论,那么九年后这件纳尔逊口中‘欢迎他复出的第一件大事’,就可谓是上天不折不扣的启示,抑或说讽刺了。
——十八岁的大学新生,没有任何犯罪记录,更毫无当上英雄的志向,先是成为怪谈主角,继而成为网络狩猎狂欢的战利品,最终,即将变成娱乐风向标节目上一条璀璨的收视率数字。
“……再怎么样,我的能力来对付还没定罪的市民未免太过了一点吧。”
在明晃晃投在屏幕上的HeroTV本部邀约,静音播放中的访谈SP,以及警方特许搜查令下,英雄能找出的理由也只剩下了如此干瘪的一条。
纳尔逊轻敲桌面,把个人电脑的屏幕转向了他。
“第一个出道前后都接受过伦理审查的英雄,对怎么规避伦理问题应该也精通吧?……被连环虐杀案受害者家属追到直播镜头面前要求给予罪犯‘天谴’。”
屏幕上正是‘赤茶’,即他本人的清晰档案。
粉衬衫男人的屏幕转了回去,显然在对他示意讨论就此完结。
——然后走进花吹英雄用健身房时候梅紫不自觉投来的眼神大概宣告了他今天的头疼还远远没有结束。
自从这间健身房迎来了第三个使用者……靠近绿植的区域里,花吹现任三位英雄的玩偶周边几乎两天改变一次摆放在立柜上的造型和顺序,连带周围的贴纸也好摆件也罢构成了一套随意而不杂乱的装饰阵仗,从他寥寥几次路过时瞥到的情况来看显然是梅紫为了健身房直播背景做出的一番努力——这位营销上的天才,千屋幸之介名义上的后辈甚至在加入第三个角色后索性摆出了一套跟随vlog更新的周边连续剧。
虽然说……盔甲背后加上翅膀,膝盖以下改做成鸟爪状,从两批玩偶的发售时间,相同的创意元素,以及‘赤茶’明显更以易于加工赶制为主的设计,就算闭着眼睛也能猜到后者明显是一次商业上的内部抄袭。
这等情况下,摆在宣传一科每个员工桌子上的那一只不是要求员工自费购买,简直可以称赞一声弥足善良了。
……所以是现在扭头就走还是进去等一会儿再假装有事离开,在他抉择好这两项人类遭遇尴尬时最先想出的方案以前,戴着头盔不会投来眼神却会投来更尴尬话题的第三位英雄走出了更衣室。
“没有问题吗,伦理方面。”
他确信自己的表情大概和远处的梅紫茫然得有得一比了。
“我离远一点就还好吧……”他的声音也一样茫然地回答道。
“……所以,你也是刚刚才得知了SP的消息。”
听到他回答山吹的肯定答复,梅紫、艾瑞恩·麦克法兰脸上在一瞬的空白后闪过了了然。
绿植区一角的氛围随即陷入了堪称压抑的沉默。
“前辈……总之已经接下……”
“不是那个原因,”山吹的声音沉闷,“我是想说,这几年,在涉及到Next的时候是不是越来越随便了?以前连特殊的英雄Next能力都需要审查,现在直播曝光普通市民也可以轻松通过审查。”
“是同一种标准吧。”
他没忍住地再次回答道,而出乎预料的是艾瑞恩接上了话头。
“是啊……是高度疑似Next的普通市民啊。”
盘踞在我噩梦里的英雄之下,是一张并不愉快的面孔。
一月的斯特恩比尔特市区已经有些寒冷,我所身处的这间公寓尤甚;按照娜塔莉亚女士的指示,我把被我一路捧来一个角已经有些坍塌的纸盒放置在桌面上,再由那个并不愉快的男人拿起。
“——是要对标公司现有英雄周边的玩偶形象。”
我莫名详尽地出声解释道,好像从他更为不甚愉快的神情中获得了一丝青涩的快慰。
字数:4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