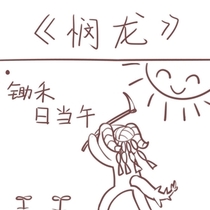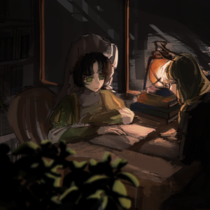
在阿纳斯塔夏的记忆中,妈妈总是温柔与了不起的代名词。
他的家庭并不复杂,作为魔法师的妈妈、作为乡绅的爸爸、天赋异禀的哥哥、还有一只叫拉姆达的小羊。哥哥的身体不好,但是读书识字很快,总会给他讲很多的故事;爸爸虽然没有使用魔法的天赋,却会带他在田野间疯玩、教他爬树和采摘的技巧;至于妈妈——她就像奇迹的代名词一样,每次阿纳斯塔夏疯玩回家,总会有热汤和加了砂糖与黄油的面包在餐桌上等着他。
在这段被时间不断美化的岁月里,阿纳斯塔夏总是幸福和快乐的。作为家里的次子,他不需要继承家业,也不需要考虑任何复杂的事。他每天会跑过丛林去看白树;会跟着羊群到结界的边缘,如果看到黑影那就是该回家的信号;也会走到集市中,帮爸爸用羊奶和羊毛换面粉与鸡蛋。他会兴奋地趴在哥哥的床边,兴奋又悠闲地讲述今天的所见所闻。
每每这个时候,哥哥总是看向窗外,摸着他的头,对他说:
“真好啊,等我病好时,我也要跟你一起去。”
是的,哥哥一定会好起来的,阿纳斯塔夏如此坚信并祈祷,从冬天等到春天。但哥哥依旧咳嗽得厉害,要喝的药剂也越来越多。日子就这么一天又一天地过去,当湖边的野花开遍时,妈妈突然把他叫到书房,让他学着念一段晦涩的咒语。
也就是从那时起,阿纳斯塔夏知道,自己的童年结束了。
虽然爸爸是靠他的爱娶到的妈妈,但对一个四口之家来说,只有些许田地和家畜是远远不够为两个儿子的未来做打算的。妈妈现在可以用医馆和魔法来赚钱,但哥哥需要的药材总是不便宜的,妈妈的魔力也总有枯竭的一天,如果家里没有新的魔法师顶上,这样的日子又能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即使哥哥再如何聪慧,他那如风中残烛一样的身体,又够他使用几次魔法?
也就是从这时起,阿纳斯塔夏在过去无人在意、甚至被认为是可爱的缺陷失去了被包容的特权。他总是慢半拍的反应、不花时间根本捋不直的舌头、还有他那笨拙的说话方式,这些对于一位无忧无虑的次子而言无伤大雅,但对于一名魔法师而言毫无疑问是致命的。
毫无疑问,阿纳斯塔夏是努力的,但正是这份努力显得他的残缺更加滑稽可笑。当他启动加热魔咒的次数已经足够令一壶水沸腾,而他仍然执拗地想把那些字节完整念出,以至于冬天的房间却比夏天更炎热;而隔壁哥哥摔下床的声音恰到好处地传来,但爸爸的脚步声却并没有响起因为此时他应该在集市上;当厨房的柴火传来噼啪声,灰色的浓烟滚滚涌出,妈妈明明是伟大的魔法师却要像个厨娘在厨房里忙碌,阿纳斯塔夏听到了清脆的声音。
并不是什么东西碎掉了,但也许确实是什么东西碎掉了。
妈妈的巴掌落在了阿纳斯塔夏的脸上,他看见她的眼神在转瞬之间从怒不可遏到惊慌失措,他看到她慌乱地蹲下抱着他的脸检查他的伤势。妈妈一遍又一遍地道歉,而他只是沉默地盯着地板,良久,对她说:
“妈妈,我愿意去做学徒。”
就这样,阿纳斯塔夏离开了家,并不算很远,每周依然有机会回来。但每每他推开门时,家里要么是静悄悄的,要么爸爸妈妈在争吵又和好。他总是拉开椅子坐下,像一种约定俗成的默契一样,独自把饭吃完,把碗筷洗干净,再偷偷溜进哥哥的房间里。
哥哥总是在睡觉,但只要他叫他的名字,哥哥就会抬起眼皮,转过头看向他。
他说:
“斯梯尔,我回来了。”
“我交到朋友了。”
他想说自己的魔法研究并不顺利,他想问斯梯尔为什么迟迟不能履行他们的约定,但他说不出口,只能苍白地说:
“我很好。”
这段普通的对话总要花上常人两倍的时间,斯梯尔总是等不到他说完便又睡了过去。他偶尔也还是会去结界的边缘,看一望无尽的原野,看低头吃草的羊群,看蠢蠢欲动的魔兽。牧民从不肯听他说话,有那个时间,他们早已可以通过经验判断发生了什么、该做什么。阿纳斯塔夏沿着小路走进小镇,风在他耳边吹拂,魔兽的黑影在不远处蠕动,被抛下的老年羊在边缘悠闲地吃草,没有谁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又好像大家都早已知道一会儿之后会发生什么。
“斯梯尔,你知道吗?我遇到了一个怪人。”
“他告诉我,如果咏唱很慢,就画法阵。”
“我可以做魔法师了。”
“斯梯尔,你为什么不肯醒过来呢?”
阿纳斯塔夏的生活依旧如常,他会趴在哥哥的床边,和他讲述自己所经历的事。但这次斯梯尔并不会再回应他任何,哥哥痛苦的呼吸声断断续续,好像陷入了一场噩梦,无法醒过来。
然后,在某一天,那场大火突然而然地席卷了米拉克镇,没有给任何人机会与时间。阿纳斯塔夏既没有成功画出可以得到认可的法阵,也没有等到斯梯尔醒来。他看着冲天的火光,周围人的惨叫已经沉寂,他才姗姗来迟地意识到这场火和他过去念错咒语引发的混乱全然不同。他回过头,拼尽全力向家的方向跑去,烟尘已经扩散开来,牧民在抢救他们的资产,魔法师在保护他们的书籍,并没有人有余裕去关心一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孩子。
他回到了家,大门紧锁,他透过阁楼的窗户看到了哥哥的影子,还有妈妈,是的,温柔的、包容的、无所不能的妈妈。他看到她站在窗边,嘴一张一合,魔法的光芒在房间中弥漫,直到与火光融合到一起,再也分不清彼此。他抬起头,对上了妈妈的视线,他的嘴动了动,想说什么可又不知道说什么。妈妈也在看着他,眼神依然慈爱,他惊觉自己似乎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和妈妈说过话了。
“你回来了。”他仿佛听到妈妈在向他问候,“阿纳斯塔夏,你总是这样,做什么都慢一步。”
女巫凄厉的笑声与孩子的哭声不绝于耳,在顷刻间,承载了他的过去、他的记忆、他的一切的房屋轰然倒塌,而他只是看着也只能看着。他徒劳地看着满地狼籍,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想要善后又不知该如何善后,而能够训斥他的人或许再也不会出现了。
万事万物都有代价,而眼前发生的种种,或许就是妈妈长久以来,为名为“家”的魔法所支付的代价。他不知在废墟边缘站了多久,直到一场雨降下,直到他感觉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爸爸牵着马,车上有些可怜的物资,对四个人来说有些紧张,对两个人来说却刚刚好。爸爸看着房子的残骸,表情复杂,似乎难以置信却又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不等阿纳斯塔夏说什么,他便抱住了他,同他说:
“会好的,阿纳斯塔夏。”
而阿纳斯塔夏把头埋在爸爸的怀里,仿佛这样他就不用因此时不知该做什么表情而羞愧。
这场大火带走了所有,离开米拉克时,他们并没有什么多余的行李需要带走。在车轮混动时,阿纳斯塔夏最后一次看向曾经家的方向,他突然看到堆砌的残垣有一丝松动,他不假思索,跳下车、用手扳开砖瓦,一个毛茸茸的头从灰尘与碎石中探了出来,慢悠悠地打量着周围的世界。
既不是魔兽也不是人造物,而是一个从未见过的、也不知该如何称呼的生命。阿纳斯塔夏抱起那只獭猴,而它自然而然伸长了胳膊趴在了他的头上。
“我可以养这个吗?爸爸。”
他问,而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便开始了漫长的旅途。
清晨,几束阳光伴随着隐隐约约传来的鸟儿清脆的鸣叫,撕开厚厚的雾气,撒向了大地,同时也照耀在了银装素裹名为特亚斯的城镇上,偶尔一阵微风,将地上轻浮的雪花吹起,在空中上下翻飞,整座城市静悄悄的,此刻正是这座城镇刚刚苏醒的时间。
【嗯。。。矿石油不够了呢,需要去莱特坑道附近捡点油岩,拿来做实验的冰凝草也不够了,也得去摘一些。。。得做一些准备呢,莱特坑道附近总会钻出来不少比特甲虫,赶不走就麻烦了】
希维娅此时一遍自言自语着一边整理着自己今日的采集清单,对于魔药与炼金的初学者来说,材料的消耗总是惊人的,为此希维娅需要每日都出门进行草药的采摘,幸运的是,希维娅生活的城镇郊外盛产各类草药矿石,足以维持希维娅的消耗需求。
“咚咚咚”
突然传来了一阵清脆的敲门声,门外传来了管家礼节性的声音。
【小姐,早饭准备好了,听说您今日要出门,瓦图斯少爷想在你出发前见见你,他应该就在驻防守卫营地附近】
【哦好的,我顺路过去一下】
希维娅耳羽稍微抽动了一下,手脚麻利的快速收拾着桌子上摆放的各类研究记录,日志本,还有一些药酿。
【总感觉今天有一些特别呢,窗外格外的安静,是我的错觉吗。啊,不管了,得快点出发才行,不然今天做实验没法进行了。保暖药。。。驱虫药。。。都准备好了!出发!】
清点完行囊,少女橙黄色眸子中闪过一丝兴奋的光,随手一拉装满药酿的挎包,飞快的跑下了楼,简单吃过早饭后,就朝着城镇郊外的驻防营地快步走去。
城镇街道上冷轻轻地,往日这个时间挨家挨户的居民都已经出来扫雪了,而此时只有零零星星的居民正拿着不大的扫帚慢慢的清扫着门前的积雪。
“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希维娅满脸疑惑,但是脚步从未停止,很快就来到了驻防营地,营地里跟往常比,少了很多人,但是战士训练时发出的呐喊并不比往日衰减了几分,希维娅非常轻松的就在营地里找到了自己的哥哥瓦图斯。
【哥!听叔叔说你找我啊?有什么事嘛?】
希维娅快步上前一把就抱住了哥哥的腰,希维娅对于高大的哥哥来说,显得小小的,她仰着头看着瓦图斯等着哥哥开口。
【按计划加强巡逻,确保隘口一切正常...】
瓦图斯见希维娅来了,急忙将任务下达给旁边的战士,战士做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便快速离开了。
瓦图斯低头看着妹妹,右手自然的搭在希维娅头上轻轻抚摸着,亮黄色的眼眸中充满了对希维娅的怜爱。
【今天是不是要出门采药啊?哥哥这里接到了报告,北面的隘口有目击者说发现了巨大的黑色移动物体,可能是魔兽出现了,今天不要去北面哦。】
瓦图斯轻轻地搓了搓希维娅的耳羽,弄得希维娅痒痒的。
【今天要去莱特矿坑附近啦,离北方隘口很远的,对了今天街道上冷轻轻的,也是和魔兽有关系吗?】
希维娅紧紧抱着瓦图斯,鼻子轻轻地蹭了蹭瓦图斯。
瓦图斯轻轻抖了一下,一改往日和蔼的笑容,脸上泛起一丝阴霾变得严肃起来了,右手滑到了希维娅的肩头上,望着北方高山之间的隘口喃喃到。
【是的,这一次可能比往日都要严重的多,父亲已经带着人手去北方隘口检查了,我稍后也需要过去。】
瓦图斯蹲了下来,轻轻地拉起了妹妹的手,英俊的面庞直直的对着希维娅。他脸上的阴霾瞬间消散,温柔的笑容重新回到了脸庞。
【没记错的话莱特矿坑附近只有一些小虫子吧,那里已经好几年没有目击到过大型生物了。记得要注意安全,别去太靠近河谷的地方,最近那里的冰盖有一些松动。】
希维娅轻轻挣开了瓦图斯的手,脸上泛起了一丝丝红晕。
【好~我知道啦,哥哥和爸爸都要注意安全哦,我还要等着哥哥帮我装订新的日志本呢。我出发了哦。】
说罢希维娅就朝着计划好的目标继续前进了。只留下瓦图斯在营地里愣神,他看着希维娅灵巧的身影逐渐消失在洁白的地平线上之后,挠了挠头。
【唉...这小雏鸟....】
作为雪乡,希维娅生活的地方常年积雪覆盖,当地的树非常特别,树叶通常为蓝色和银色在太阳照射下,雪地上的树影摇曳生姿。雪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晶莹剔透。此时仿佛时间停止一般,周围充斥着安宁的气息,此时希维娅正慢慢的行走在白皑皑的大地上,时不时的拨开积雪,采摘积雪下覆盖的草药,突然不远处有一道红色的光晃得希维娅睁不开眼,希维娅用手遮挡住刺来的光芒,发现那是一颗红黄色的结晶,内部似乎有着一个球状的晶核。
【啊!这不是卡兰结晶嘛!这里能找到太少见了!】
希维娅兴奋地叫出了声,快步上前,从自己随身的口袋里掏出来不少工具。
【嗯。。。。姑姑是怎么教的来着?要先用凿子敲掉岩座边缘。。。然后再用手绢包着镊子夹住结晶。。。。一定要小心,不然爆炸了就不好了。】
希维娅一遍自言自语说着姑姑教导的采集方法,一遍全神贯注的操作着,生怕一点失误,导致结晶爆炸;这是一种极其不稳定的结晶,根据晶核的大小可以粗略判断爆炸的威力,而由于它的不稳定性,他能被人们采集的数量极其稀少,而能像这颗可以生长到巴掌大小的结晶更是几乎见不到。十多分钟后,希维娅终于搞定了那颗难缠的结晶,用手帕左三层右三层仔细地包了起来,小心地收到了独立的口袋里。
【哈哈,时间不早喽,草药采的足够今天用了,还找到了意外之喜】
希维娅深深的申了个懒腰,该回家了,她这么想着,就朝着家的方向一蹦一跳的走去。
就这时,一阵阵歌声从远处传来,希维娅停下了脚步,耳羽抖了一下,她望向歌声传来的方向。
【这里怎么会有人唱歌?】
歌声激起了希维娅的好奇心,她静静的朝着歌声的方向走去,很快变来到了一片森林的空地上,空地中央站着一个人,洁白色的斗篷,覆盖着高大的身躯,最为显眼的是头顶的羽毛,羽毛尖有着淡淡青蓝色。
【那...那是瓦图斯?】
【哥哥!你在这干嘛呢?】
希维娅招着手朝着那个人喊道
那个人在听到声音后,动作迟缓,身为十分诡异的缓慢转过了身....
是的,那的确是希维娅的哥哥,瓦图斯...但此时的他浑身鲜血,身体看起来残破不堪,脸上除了凄惨看不出任何表情。
希维娅被这一幕惊吓到失声,她倒吸了一口凉气,寒冷的空气冲进她的肺部,使得她隐隐作痛。
在瓦图斯完全转过身之后,他开口说道
【注意安全小雏鸟...】
【别去冰盖附近...】
【早点回家...】
【......】
【...】
【小雏鸟!】
【希维娅!!!】
【快跑!!!】
希维娅眼前一黑,猛然睁开双眼,鲜红色覆盖了她的视野,一股暖流正从他的头上流下,她紧张的一抹,手上顿时充满鲜红色的液体,那是血。希维娅茫然的抬起头,发现自己的哥哥正被一头巨兽狠狠压在身下,那头巨兽浑身遍布伤口,正愤怒的不断攻击者瓦图斯。而瓦图斯吃力地抵抗着,一遍声嘶力竭的朝着希维娅大喊。
【希维娅!!快跑啊!】
眼前的情况太过突然,虽然希维娅一开始没反应过来,但她马上镇定了下来,她尝试从背包里取出自己的药酿,但是一阵钻心的疼痛使她险些昏死过去,原来是她的左臂已经断了,现在就像一条破布一样耷拉在身体一侧。情急之下希维娅顾不得那么多,她忍者剧痛快速掏出了那颗卡兰结晶,结晶此时闪着鲜红色的光芒,晶核也在不安的跳动着。
【快滚开!给我离我哥远一点啊啊!!!】
希维娅怒吼着,将那颗结晶狠狠的朝着巨兽身体掷了过去。
爆炸,将周围的积雪轰然吹起,飘飘扬扬的漫天飞雪遮挡了视野,希维娅缓缓跪坐在地上。
【成。。。成功了。。。?】
可一声怒吼撕碎了希维娅可笑的幻想,那头巨兽嘶吼着,身体的一侧被炸得血肉模糊,但它依旧动作流畅,甚至更加嗜血。此时巨兽正恶狠狠的瞪着希维娅,恨不得下一秒就把希维娅生吞了。
瓦图斯见状试图在巨兽不注意的情况下用剑刺死这个该死的怪物。可惜的是,他的计划落空了,巨兽愤怒的将他的武器打飞至希维娅脚边,紧接着一击几乎将瓦图斯的手臂拍烂在雪地里,剧烈的疼痛使得本就筋疲力竭的瓦图斯休克了过去,在即将失去意识前,他依旧注视着他的妹妹。
巨兽发出一阵胜利的咆哮,它暂时放过了半死不活的瓦图斯,转向希维娅,发出阵阵低吼,口中呼出的热浪凝结成白霜,似乎可以直接吹到希维娅脸上。
这时,那股神秘的歌声又在希维娅耳边响起,最开始如同涓涓细流,缓慢平静,之后变得如同瀑布流水一般奔腾,暴怒。
【我是要死了吧。。。】
【但是。。。我为什么从未感到如此平静。。。身体如此轻盈。。。】
希维娅站起身,拖着断臂,拔出了插在脚边的长剑,步伐轻盈,如同在薄冰上起舞的雪花一般,朝着巨兽冲去,希维娅从未使用过武器,也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而此时她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杀死这头伤害自己家人的巨兽。
【至少,在我死前能做一些事吧。。。哥哥。。。我对不起你。。。】
这场无畏的冲锋,顷刻间便结束了,希维娅瘫软的坐在早已被鲜血染红的雪地上。而那头巨兽,它胜利的笑容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刻,随着它轰然倒下的身躯,传来的是更多嘈杂的声音。
【快,医疗师,药剂师!!】
【都让开,让我来!!】
那是希维娅母亲的声音,她推开了围在瓦图斯周围的人,全神贯注的引导者魔力,念诵这咒语治愈瓦图斯。
一声清脆的金属响声,紧接着一个黑影扑向了希维娅,希维娅的父亲斩杀了那头巨兽之后,立刻丢掉了自己的长剑,冲向了希维娅,紧紧地抱住了她。
【没事了!没事了。。。。我的孩子。。。都是我的错。。。】
而一旁的药剂师和医疗医师急忙治疗着希维娅;希维娅从一开始的木讷,到轻声抽泣,再到最后的嚎啕大哭,她把脸深深埋进父亲的胸膛,死死的抱着父亲,而那奇怪的歌声又传到了希维娅耳中,希维娅抬起了哭的梨花带雨的头,发现有一个身披蓝色长袍的身影,背对着希维娅,唱着一首温润委婉的歌谣。
此时一滴泪水,滴落在希维娅脸上,希维娅的父亲再也忍不住了,自责、内疚、疼爱充斥在这苍老的躯体里,他强撑着可还是让一滴泪水滑落脸庞。这一滴泪水拉回了希维娅的视线,当她想在看看那长袍下是什么的时候,它消失了,就好像不曾出现一般,但歌声却还萦绕在希维娅耳畔。
【爸爸。。。你听到了吗。。。那个歌声,一直在我的脑海里】
【歌声?什么歌。。。】
仅仅是一刻,希维娅的父亲就好像明白了什么,他轻轻亲吻着希维娅的额头
【孩子,也许是时候了,你身体里流淌着安卡伦家族的血液,注定要去探索未知,追寻秘密】
【不。。。你还没有做好准备。。。但很快你就会的】
【那歌声。。。是未知对你的呼唤,是指引你旅行的指向标,那是我们家族之所以能传承下来的精神图腾。孩子不要思考你听到了看到了什么,人们只愿意听到自己想听得,看到自己想看的,或许城镇之外的旅行和探索正在从你的灵魂深处召唤你】
那一日,希维娅再准备回家的时候,遭到了因魔兽而受到惊吓的巨兽袭击,魔兽将他们赶至了本就荒无人烟的地区,而因为北方隘口的问题,没有像往常一样悄悄跟着希维娅,瓦图斯在察觉到情况不对时,返回寻找希维娅,并发现了正被袭击的希维娅,所幸,两人恢复状态都很良好,很快就回归了日常,也是在那一日后,希维娅的父母长谈了一整夜,希维娅的父亲终于妥协,同意教导希维娅使用武。
时间过得很快,两年的时间转瞬即逝,此时的希维娅掌握了绝大多数武器的使用方式以及技巧,她挑选了最适合她的一把武器,告别了家人朋友,踏上了属于她自己的旅途,在外面兜兜转转了很久之后,在一个秋天,她来到了米拉克的高塔之下,新的故事正等待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