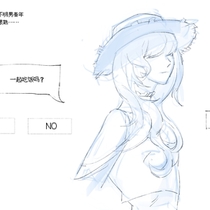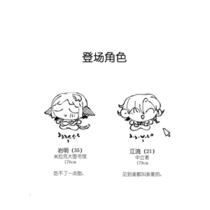


她是在春天出生的。
那间曾经被称为家的房屋总是挤满了沉默。即使在落花不慎飘入窗内的时节,仍是孩童的她在屋里也如履薄冰。
她至今不知道那时他们究竟在害怕惊醒什么。
她参加过一场葬礼。那时她意识到,她的家就像坟场一样安静。
死去的人是一名魔法师。他的墓碑上,刻印了一种圆形的图样。
那时杜伊没有看墓碑,而是看着掘墓人脚边,松散的泥土间颤颤巍巍地探出头来的一株草。她看着它,直到它舒展开幼嫩的茎、吐出一串花苞,然后迅速地绽放。一串铃兰。
然后她感到一阵晕眩。她向后踉跄两步。原本,姐姐站在她身后;或许姐姐刻意让开了一步。又或者是她自己不自觉间移动了身位。总之,她跌坐在地;姐姐伸出手,将她拉起来。她口腔里蔓延开一股血腥味。她伸手进嘴里,取出来一颗牙。
最后一颗乳牙。第一次魔法。
一片死寂。
就像她曾经的家里一般的死寂。但白树枝头的花已经开了:生于初春的生命。
杜伊伸出手。
与那年的墓碑上毫无二致的法阵——蕴含着能使任何活物增生的魔法——早已刻印在了她的胸口。一次又一次绽开又愈合的皮肤。“你的愈合力太强了,亲爱的。必须留下痕迹才行。”
枯瘦的手伸向莹白的花。花瓣颤抖起来;然后,像是被烫伤了一样,起了成串的水泡,肿胀起来。原本舒展的花瓣拥挤地咬合起来。花成了一颗肉瘤。
她剧烈地咳嗽起来。起初咳嗽声显得遥远,像隔了一层膜;忽然变得清晰。她全身抖了一下。
飞龙落在她眼前的枝条上,长尾巴从她的衣袋里勾出一条手帕,递到她手里。
“您说过,不再将魔法用在……徒劳的地方。”阿尔巴说。
她将手帕规矩地对折两次。“不是我想用。像是被谁指使了。我该小心。”
她想:这不全是谎言。她隐约感到有什么在树丛中窥伺着。
或许只是过去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