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吉商店街是一条位于京都市,昭和2年成立,由60个中小店铺组成的小型商店街。每间店铺的人都是熟识,互帮互助着度过一年又一年。
可是,繁荣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时代变迁,人吉商店街也走向了衰退,不少店铺都出现了营业危机。
1964年的7月,生活协同组合会决定:如果到10月底,本商店街的销售额仍不达标,就要彻底解散,并在这里建造百货大楼?!
这可是大危机!该怎么办呢?!
【创作交流群:6435603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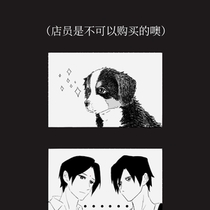


如果世界上有尴尬大赛评选的话,小泉悠悠无疑可以凭藉——富家千金落魄扮村姑,苦生计卖礼物被前任上门这一光辉事迹入围。已知悠悠是人吉的店员,人吉正面临着即将被百货大楼并购的困境,而现在上门砸场子的她前任又恰好是百货大楼的股东之一,求解她是怎么隔着大陆和大洋被找上门的?
这世界还能再离奇一点吗?
小泉悠悠绝望地想着,平静的表情下面是颤抖的心和冰冷的手。而在她对面,她的未婚夫……不,应该说是前任,正拿着她刚卖出没多久的怀表似笑非笑地看着她。他甚至还体贴地把刻有情话的那面对着她,无声地质问着当掉定情信物的某人。气氛就这样僵硬地凝滞在那边整整一分多钟,炎热的夏日没有空调的诊疗所此刻尬得悠悠手脚冰冷,而创造这尴尬气氛的始作俑者就像无知无觉一样保持着他那光彩照人的笑容。
直到国木田佐纪感觉不对出来寻人,她撩开帘子,抬头看见了一身华服的维克瑟伦·贝勒伦斯和他的黑衣保镖们,跟在他们身后看起来像是黑帮的不良分子,以及像是石雕一样凝固在那边的悠悠,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嗯?这里好凉快……咦?这么多人过来避暑吗?”
“Pour l’été? Non, je suis ici pour quelque chose de très important(避暑?不对,我是过来处理一件要事的)”
成功引来话事人的维克瑟伦慢条斯理地收起了怀表,然后缓步走到小泉悠悠的身边,低下头贴在她耳畔低语。他无视了她小幅后退的动作,撩起悠悠垂下的碎发,体贴地替她捋到耳后。
“Avez-vous quelque chose à expliquer?(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
“羽川秋夕子です?”
维克瑟伦几乎算得上是咬牙切齿地念出了她的本名。
好消息还真有比那更尴尬的事情。
比如说在前任上门控诉的基础上,还被前任揭穿掉马了。
“Pensez ce que vous voulez visser.(随你怎么想吧,维瑟)”
悠悠生无可恋地回道。但即使在这种社会性死亡一般的困境当中,她也坚强地铭记着自己作为店员的骄傲,所以她很快就想把诊疗所拉出这个小少爷迁怒的范围。
“ Bref, laissez vos hommes revenir en premier.(总之先让你的人回去)Ils sont innocents(她们是无辜的)”
维克瑟伦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他甩出一张空白的支票,抓起悠悠的手腕就往外走。在经过国木田佐纪身边的时候,他漂亮的眼睛扫过了这个优雅的女人,然后用他最礼貌的口吻说道。
“Je remboursais tout ce qui était dans la boutique à mon prix et, en échange, je prenais mon homme avec moi.(所有的东西我都照价赔偿,作为交换我的人,我就带走了)”
国木田佐纪表示其实也没有多礼貌,但是能听得出来他抓着的悠悠非常不情愿。
“Attendez, vikselen, dites-les de s’arrêter!(等等,维克瑟伦,叫他们停下!)”
维克话音刚落,身后的黑帮成员就像是接到了什么指令一样拿起东西打算开砸。他们比不上训练有素的保镖,其中一个看起来十分稚嫩的年轻小伙子还一边砸还一边碎碎念。
“可别怪我啊,我也是受人指使的,你们得罪了人不关我的事啊,冤有头债有主!”
时间倒回这场奇妙的对峙开始之前,留学的小泉悠悠接到家里的消息回国,结果发现家里的产业突然破产清算暴雷,她和家人失去联络又因为好心救助他人而被骗走了路费。于是失去大小姐身份和财富的她变成了一条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咸鱼,不得不可怜地流落街头。幸好在被人骗去窑子里面之前,她被善良的国木田佐纪收留,不仅填饱了她的肚子,开导她不要寻死,还教导她如何利用自己的学识去自力更生。感受到这份温柔的她感受到了自己过去的不成熟和幼稚,决定借此机会抛弃掉过去只知道享受他人成果的自己,做个能够用自己双手生存的人。所以她为了回报佐纪,用假名小泉悠悠呆在了诊疗所当店员。为了给店庆祝五周年纪念日,身无分文还不会攒钱的她在前不久当掉了原本打算送给自己前未婚夫的生日礼物,想请大家吃饭。然而就是这么好巧不巧,原本以为再也不会相见的人拿着被当掉的东西又出现在了她的面前,还成为了要逼迫人吉倒闭的黑恶势力之一。
对于这个故事,大孙子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这里是小说吗?”
他那一道特别响亮的声音过了混乱,敲进了所有人的脑海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钻出来看戏的大孙子发出了这样一声惊为天人的感叹。无论是来砸店的,正准备阻止砸店的,还是拉拉扯扯的那一对,都不由自主的停下了看向这个家伙。打破气氛的罪魁祸首无所谓地扭过头嘀咕道。
“我还以为京都不流行这个呢……哦,这段话对气势毫无帮助,声音应该再大点……”
“这!里!是!小!说!吗!”
“潮得我都快风湿了!”
“你别看不起人啊,咱们是过来砸店的!”
一个吃瓜许久气性很大的黑帮成员怒吼道。
“原来是过来砸店啊 我还以为演电影呢……”
大孙子恍然大悟地说道,然后非常好心地给予了一个建议。
“你们真要砸*那个女人*的诊所吗?”



邮局的玻璃橱窗还封着待维修的布幔,里面碎裂的玻璃已经换下等待换新。暴力事件过去了,但是影响要褪色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广播和电视的新闻里过几天也许还会提起案件的进展,也许会就此忘记。没人说的准。
香药摸了摸额角的伤口,干干的血痂摸起来有点刮手。伤口愈合的速度比她想得要慢得多,以后会留疤也说不准。她也还没有想好是不是要去再配一副眼镜。平光眼镜碎了对视力本没有什么影响,除了她总是会习惯性地伸手,然后摸到空空的鼻梁,还要和邻居们解释那只是没有度数的平光眼镜……或许还有,看不太习惯没有镜框镜片挡着的,镜子里的自己。
“早上好,邮局长~。”她推开门走进邮局。大门上的玻璃也碎了不少,扣去碎玻璃的空窗格用木条和纸封着。今天应该是新刊送来的日子,不过这个月……香药觉得还是直接来取更好一些。
“早上好。您……嗯?叶津田小姐?是来取这个月的杂志吗?”上原星停下了手里的活,有些抱歉的对香药笑笑,“如你所见,邮局现在有点……乱得不成样子。”
其实邮局的大厅早就打扫干净了。除了桌子柜台上还留着些许伤痕没补上漆以外,和平时只有文件堆积得多了些的区别。
“我来帮忙吧?”
“这倒不用,我还能应付的过来。”黑发的青年看着香药的脸,顿了顿,“这伤是……?”
“啊呀,邮局长真可靠~”香药笑起来,好奇地看向一边堆叠的信封,“一点划伤没大碍的。”
“不戴眼镜也不要紧吗?”
“那个镜片没度数,是平光镜哦。这么多信……最近一定忙坏了吧?”香药笑笑,看向上原星。
上原星摸了一把后脑勺的头发,抿嘴有些无奈地笑笑。随后好像想起来什么,在刚才香药注意到的信件堆积翻了翻,问道:“叶津田小姐上个月是不是问有没有信来着?”
香药愣了愣,点头很轻地嗯了一声。
“我记得有看到过……啊,在这里。”一封略大一些的浅紫色信封和三封捆在一起的颜色不一的牛皮纸信封从那堆信里被上原星抽了出来,“本来说让阿谅送去的,不过叶津田小姐正好来了就给你。”
紫色的信封的日期似乎是最新的,熟悉的娟秀字体用法文和日文写了两遍地址。
香药接过信,微微垂下的目光有些踟蹰,睫毛几乎遮住了她的眼睛。
信封上盖着日期各异的几个邮戳。最崭新的是一天前。然后是一个星期前,和七月中旬。信的边角有一点微微卷起和磨损,似乎还沾了一些像是盐的白色粉末,摸起来涩涩的。
“从海外寄过来的,是家里人的信?”
“嗯,双亲寄来的。”
信是从马赛寄来的,具体的地址是香药不熟悉的街道名称,133号。印象里只有大约是靠海的城市和著名的普罗旺斯薰衣草田。另一叠牛皮纸的信封上的地址不一样,代表寄出的邮戳的日期也更早,似乎还有四月初寄出现在才到的信件。
香药捏着信封的一角,眉头微微拧起。要不要就在这里拆开这封信?
“叶津田小姐怎么了?信有什么问题?”黑发青年把打包好的杂志拿了过来,见香药还在对着信发呆问道。
“不……没什么。”香药迅速地抬起头扯出一个笑容,“杂志和信我就带走啦,辛苦上原君了。”
一封信而已。
香药手里攥着信,另一只手提着杂志,短短几步路走得有些心不在焉。父母换了住址,也不知道之前寄出的信他们有没有收到。没有退回就是收到了吧?
她叹气,一封信而已。
——————
节日里的客人本就比往常少,加之前几天的混乱,租书店更显得冷清。带回来的杂志香药放在了一楼柜台的后面没急着整理入库。爷爷还在三楼修养,佐纪奶奶说伤得不算太重,但是上了年纪摔一跤可大可小,多少要爷爷在家静养几天。
从邮局拿回来的信有两封是给爷爷的,另外几封是给自己的。香药拿着信上楼,踩在楼梯木板上发出的轻微响动让她有种久违的不安感。以至于撞到头了才发现已经到了三楼。
香药捂着头发出一声哀鸣。
“姑娘你今天怎么笨手笨脚的?”爷爷坐起来靠在床上往门口看了一眼,看见猫着腰捂着额头的香药拿着信走进来。
“有点没睡好而已。给,一爷的信。”
“続夫和絢夢寄来的?”
“嗯。”香药确认了一下信封,把两封信递给叶津田一,“一爷有好点吗?还在疼?”
叶津田一拍拍自己的腰笑道:“已经不碍事了,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再撑一撑。”
“倔老头。”香药嘟囔了一声。
“嗯?”
“我说,一爷你,精、神、矍、铄!”香药提高了音量,转身去拿放在衣柜上一只漆盒。
“对对,我是倔老头。”
香药无奈,朝小老头瞥了一眼便抱着盒子下了楼。
她在柜台后坐定,把盒子打开。漆盒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东西。有粉色带花纹的贝壳、各种颜色的干花、装在瓶子里的白色砂子……几乎装满了盒子。她取下一把固定在盒盖上的拆信刀,黄铜的刀刃卡进缝隙里轻轻一挑,然后沿着边缘一路划到底。
信封里除了信,还有几簇押好的薰衣草干花。
薰衣草的香味浸透了信纸,干花被香药放进了盒子里,和之前的那些花一起。母亲寄出的信大多都会带上一些零碎的小东西,父亲的会更直白的多,信纸和信,或者干脆就是一张明信片。
【致香药吾儿
谨启,
时值盛夏,不知近日可好?
我和你父亲最近在马赛,这里天气不算太热,港口特别热闹。之前还去看了薰衣草田,虽然不到盛花期但是这几天能陆陆续续看到有成片的紫色,很美,真希望也能带你看看。
信封里我放了些干花,希望香药你喜欢。
我们的工作现在很稳定,你父亲还是希望你可以完成学业。巴黎的大学……】
香药深吸了口气,那一封信寥寥几句她看得很慢。
【……因为日本要开奥林匹克,借着这个契机,我和爸爸决定会在近日回国呆一段时间。隔海千万里, 我想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应该已经是八月了,……】
“你好,有人在吗?”
【……八月十一日左右的机票,也许会赶得上盂兰盆节的尾巴。】
香药抬起头,书屋的拉门被拉开,一高一矮的两个人影逆光站在她的视线里,看不清样貌。光影描画的轮廓渐渐和记忆里消失的两个人影重叠在一起。她不敢叫出口,手一松,信纸便从柜台上飘落到地上。
信纸上最后一句话,和来客的话音重叠在一起。
“香药,爸爸妈妈好想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