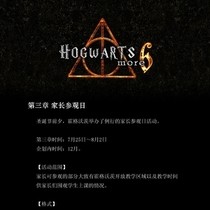
烟蒂落进烟灰缸,她往窗玻璃上吐出一口烟雾。外头在下着大雨,水珠沾在玻璃那面,她的食指和中指间夹着那根被他抽过的烟,愣愣地看着高楼下在雨中穿梭的车辆。
在这之前她刚囫囵吞下两块奶油蛋糕,他坐在客房深蓝色的皮质沙发上看着她,看她的勺子一起一落,一下剜去某些生命。他觉得她越发不可理喻了起来。
面粉和奶油在她的肚子里融为一体,她蹬开躺在她通往大床路上的高跟鞋,黄色的尖头鞋被抛起,而后又落下,依旧躺在灰色的地毯上,间隔分明就像她被一刀划开的人生。
他们一起倒在床上,并排躺着,起先一言不发,而后她开始呓语。她总爱呓语,他却恨那些她喃喃细语的片段,没有一丁点儿关乎他,不过是一些她的妄想。
她现在肿胀着左脸颊,旁人问起她都说那是智齿痛惹得祸,但那上面青紫交错,熟识的人或许还会看到他的拳印。但他们还能说些什么呢,他们也不是真正关心她,他们也不喜欢她蹙起眉头吐出的那句“You Muggles!”,语气尖锐,仿佛他们真如傻蛋一般。他们甚至有些同情他了,交上了一个神智错乱的——他们思索定语,最后抛弃“女友”而选择了“情人”一词。
但他们还是待在一起。她现在躺在他身边,胳膊上还带着他们刚刚搏斗后的痕迹。他用水晶的烟灰缸角猛击她的胳膊,她则提起高跟鞋尖敲击他胸前的肋骨。不论哪一样都很疼,但他们此刻都躺下来了,在白色的床单和柔弱的席梦思上。她的左胳膊还在疼,伴随着每一次心跳传递着血液经过那被攻击的地方。她又开始回想曾经。
她从没打过这么惨烈的架,她当年可不是干这些的,如果她的魔杖还在手边,她或许会抛弃高跟鞋,魔杖直指他的心脏,读一句“Stupefy”就能证明她所说的曾经都并非虚假的记忆。但是可惜,当然了,她的魔杖并不在她的手边。
她也曾和他叨念过霍格沃茨,世界上最神奇最美妙的地方,但他嗤之以鼻。
“你在胡思乱想,这都是假的。”
“不,那是真的,只要你能去上一次,你马上就会明白,对于曾经我从不撒谎。”
这是他们无力的对白。
她的胳膊真的很疼,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她也是偶尔才会在记忆中找出相应的场景。
“我的胳膊还在疼。”
所以她向他抱怨道。
“嗯哼,正巧,我的肋骨也还在吱吱叫唤。”
“它让我想起,在霍格沃茨时我也弄疼过胳膊。”
“哦,拜托,您不用在这样的情节上也绞尽脑汁编出一个故事的,我和你说过很多次了,别再对我说这些胡话。”
他翻了个身,伸长手臂拉过头顶上方的枕头,将它枕在头下,撇过头不理她了。
她独自起身,胳膊又在痛了,她试着忽视那疼痛,但失败了。忍耐对她而言依旧是多年来难以学会的技巧,不论是面对愤怒还是面对痛苦。绝望?她的脑中忽然闪过这个词,随即又被摁下了。她又点起一根烟。
烟雾中一切似乎又回到她身边了,胳膊和脸颊的青紫都褪去了,她穿起巫师长袍,拍拍外套上的灰尘,跨步走过中世纪拱栏。
走在她前方的人同样一袭长袍,蓝色的编带表明他拉文克劳的身份。
Ravenclaw,Ravenclaw。她把这个词在口中咀嚼了两遍,能再听到这熟悉的词语真是令人怀念。
她看到年幼的自己向对方央求着决斗练习,她这才想起自己当年也算是决斗俱乐部的成员。
多可笑,那是她不过十岁,痛只是停留在肌肤表面的概念,从未深深刺入肺腑,伤得她满口鲜血。
多拉,那是她可爱的小多拉,仰着头走在她拉文克劳的学长身边,蹦蹦跳跳的脚步像尝了糖霜那般雀跃。
她从烟雾中看见他们手执魔杖,一边是十一英寸的紫杉木,一边是九又四分之三英寸的樱桃木,两只魔杖对准对方。她思索起这张决斗练习的最终胜负,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她才三十岁不到,怎么会这样健忘?真是该死。
答案还没从她脑中的馄饨中完全抽离出来,她忽然想起那时的场景,另有一根魔杖搅入了这场战斗,那是一根十三英寸的柳木,被一只保养良好的手拿着,那手指长且有力,除了克制不住的颤抖之外一切都很完美。她想起被对方拦在身后时的感觉,吃惊中夹带埋怨,但在那个身影被击倒时,却又有一种莫名的安心感上升,震颤她周身。
眼下并没有其他的东西帮助她回忆当时的片段了,她记得唐·璜在蓝光闪过之后就倒下了,但还不等她走到他身边查看他的情况,那双因疼痛而颤抖得更加剧烈的手就握住了他的柳木,将尖端对准了缓缓走上前的拉文克劳。
Papilio·LEE的那双眼睛在她的记忆中一晃而过,那眼睛是什么颜色的?蓝色?银色?她又记不清了,离开那个地方不到十年,却有太多东西伤害了她的记忆,她明明记得当年她还很迷那冷峻面庞的学长的。
或许当年她还深陷于小孩子的情迷意乱之中,可现在不同了,她有得是时间,身边的男人已经开始打鼾,鼻息间带着种可悲的平稳。记忆如一带录影带,她拼命按住暂停键,将时间拉回至那场唐·璜和papilio莫名其妙的决斗上去。唐·璜她是再熟悉不过了,灿烂到泛滥的男人,其他部分都很完美,但就是不适合做一个巫师。如果他是麻瓜,她这样想着,一定会过得很好,一辈子惊心动魄跌宕起伏,几度爱恨情仇辗转反侧,最后找到一个愿意交付自己的伴侣,一口气活到九十几岁。另一个男人呢,papilio乍一看就是和唐·璜完全不同的人。像是城市高楼尖上挂着的银色月亮和田野天空中扣着的金色太阳那般,他们格格不入。俊俏的容颜倒是都在他们身上停留了,但一个叹息着一个愚笑着,引向不同的宿命。她记得多拉每次见到papilio时他都沉默着,像是在脑中思考最深刻的问题。她曾经希望他简简单单,一句话就能穿透彼此的肌肤,但他不是的。他沉默着,站着,坐着,生死情爱或许也曾在他的脑中打转,但就像克里姆特的油画那样,他常常摆出那种姿态,那种明白一切都不是一个人——或两个人——的事情,在那一切进行的时候,还有很多奇怪的面孔或狰狞或慈祥地在高空看着他。于此相比,唐·璜有时也会沉默,绝大多数是他一个人的时候,但有一次,圣诞节放假时她回了家,皮箱放在门廊,她转头就看见她的哥哥坐在沙发里,慌张爬起迎接她时还不慎被手中的烟头碰着了手。三两步蹦到她面前,她透过家中壁炉那有些暗淡的火光看到两道泪痕。她从未见过唐·璜哭泣,也不敢想象那哭泣。他还有什么烦恼呢?一切在他身上看上去都那么完美,他还有什么可抱怨的。有时候她真的觉得,比起沉默寡言的papilio,那个夜晚的唐·璜更让她难以接近。
烟还点在她的指缝间,她很习惯地又吸了一口,总结了刚刚的回忆,那不是属于她的战斗,真奇怪,她怎么又想偏了?她明明记得自己在一年级的时候是打过一场真真正正的巫师决斗的。
视线扫过一旁乱糟糟的桌面,红金配色的杂志上,那两块刚被吃完的蛋糕的碎屑还留在那上面。过往她每每想起甜品,总觉得有一种愉悦之情从心底跳跃而出,像是能带她回到还点着蜡烛,烤得暖烘烘的学院休息室里那般。沙发软得能让人陷进去,周围尽是学长学姐们的笑脸,她红着面庞凑在学长们的身边,听他们聊O.W.Ls,聊魁地奇,聊恼人的同学和一些平稳年代里的新闻。然后她可以枕着身边不知是哪一位学长的胳膊在逐渐上升的温度里入眠,最后被一个Mobiliarbus给送回自己的被窝。
多好的生活,多美的过去。她呼出一口烟,不由得感叹。
其实比起烟草她此刻更希望能有酒精的抚慰,能呼麻自然是更好,可她手头现在没有余钱。
回忆拉远,追溯着她当年的决斗继续前行,然后定格,放大,她想起了另一个孩子,奥利弗·德·美第奇。一个有着一头红色长发的意大利男孩。她不想去理解为什么唐·璜会对意大利人有那么大的意见,她还是觉得奥利弗很可爱的,一双绿色的大眼睛乍一看就让人心生好感,后来她听说唐·璜一见到绿色眼睛的姑娘就要载跟头的传闻,心里还咯噔了一下,可惜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平平静静,她的生活还是不起波澜。奥利弗一向喜欢和人交流,咋呼起来的时候一点不输那时候的自己。有多拉和奥利弗一起出现的场合,她敢保证,如果格兰芬多塔再低那么上那么一点,他们一定能用叫声把它掀翻。这样回想起来,她完全不敢相信他们竟然进行过巫师决斗,还是在双方都是一年级新生、大家一同见证下的堂堂正正的决斗。
于是舞台上只剩下他们二人,视线聚焦,仿佛光束只打在他们身上,两具身体,两个年轻的灵魂。
她几乎想不起为何要战斗。她夹着烟反复确认自己的记忆,最后想起那时她寄放在休息室的施洗约翰不见了。但她很快又想起这只不过是她的借口,她心里清楚得很,好斗和不甘寂寞才是这场决斗的真正导火索。
骑士们出手时会如何?礼毕之后,他们的手心是否也会出汗,他们的胸膛是否也会起伏,他们的双腿是否也会颤抖?她想起他们双方行礼,然后背靠背迈步。然后转身。然后,两倍的“Expelliarmus”。他们几乎是同时脱口而出。
蓝色光芒一闪而过,几乎照亮了在场每一个人的眼睛。当然谁都不会指望一年级的新生打出怎样精彩的决斗,但场下还是有呼声的,就像是麻瓜世界中,再无聊的打架斗殴都有围观者喝彩那般。结局也是恒定的,呼声过后,一人倒下。这是数百年来的规定,对战必然要有一方落败,就像灰头土脸和趾高气昂永远对等那般。她记得当时她后脑勺着地,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结局对现在而言没有意义,失败也不过是对她那时任性的惩罚。烟蒂从点着的尖端开始下落,掉在了她的裙子上,她伸出手扫开那团灰烬,然后又感受到了自胳膊传来的疼痛。
她从没想过未来将会以这样的形式降临在她身上,窗外的雨还在下着,砸在每一个地方。
桌子上还放着她下午时分做到一半的剪裁工作。她喜欢拿着一把大剪刀将杂志上看到的喜欢的东西统统剪下来,从胶水贴在自己的本子上。有时那是一副画,有时是一两句诗,但多数都是当下最火的服装造型,由身材火辣的模特展现在铜版纸上。但今天不一样,她剪下的是难得的诗句,又是一句来自遥远东方的诗。她几乎要产生那个地方人人都是诗人的错觉,倾吐出口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人以纸记录,然后集结出版,远渡重洋送来给她这样的人看。
那首诗里,那个东方诗人写雨,和她当下一样的雨,她平稳地看下去,看下去。然后那诗说:
——当我把一段烟灰弹落,另一段烟灰已经呈现
她被文字提醒了,也弹了弹手中的烟灰,然后继续读下去:
我把一个人爱到死去
另一个已在腹中
她转头去看床上的那个男人。情爱在一瞬间变得难以分辨了,她将手上的烟留在烟灰缸上的夹口里,转身往那男人的方向爬了点,低下头看着他。
奇怪,她突然想不起对方的名字了,眼前一阵模糊,她竟连他的模样都看不太清了。相反的,曾经逝去的青春年华中的那些人们全又都回到了她的眼前,一个个穿着她熟悉的巫师长袍,笑着闹着走过她熟悉的霍格沃茨的角落。
她突然涌出了几滴眼泪。她又是谁呢?她只是一个金发紫眼的女人。她没有了名字。
有些夜晚,有的男人称她“多多”,她会突然抬起头,无所谓的眼神变得凌厉,从此再没人敢那样叫她。
这样就对了,她想到。
她从身后抽出那块属于她的枕头,拿在手中。她闭上眼睛,在心底默数十步,然后猛然转头迎向还在沉眠在梦中的他。
她的手上没有魔杖,但她高喊着Reducto,而后枕头代替魔杖狠狠地落在他身上。他从梦中惊醒,正想询问何事,却见她张大了嘴巴,从喉咙最深处吼出一句Get out you son of bitch。
他慌了神,他从不知道她会这样,她不是应当是一个可爱调皮的姑娘吗,怎么会变得如此可怕起来?入睡前对她的厌恶在此时转化为了恐惧,他觉得她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于是他扯起自己的衣裤,顾不上皮鞋的左右脚,一边用胳膊阻挡她的攻击和吼骂一边拉开房门,溜了出去。
她停下了攻击靠在门边喘气。然后似乎又想起来什么,她丢开手中的枕头,飞奔到窗口去低头看。
她看到他穿着昨夜皱巴巴的外套,万般无奈地迈入夜晚的绵密细雨中。
她笑了,迈步坐回床上时,她的动作已十分优雅。她瞥了一眼刚刚还未读完的诗,那最后四行文字躺在她剪下的小纸片上,像是被关进阿兹卡班的囚犯,无处可逃。她终于笑了起来,拿出了她还是唐娜多拉时的语气,读完了那首诗:
雨落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声响
没有谁消失得比谁快
没有谁到来得比谁完整
没有谁在雨里,没有谁不在雨里
TBC
迟到的第二章,先向这章和我互动的朋友说一声抱歉……尝试了好几遍正常叙事最后都因为不满意删掉了,结果就变成了现在这样,真的是很抱歉(……
然后第二章的剧情其实是①多拉加入诺拉教授的决斗俱乐部并且在俱乐部中碰到了Papilio ②多拉央求papilio陪她练习巫师决斗,结果半路老唐不明所以冲出来挡枪,被打倒之后送去医疗翼治疗 ③因为树猴是老唐变的,所以老唐住院了之后多拉找不到自己寄放在休息室的树猴,误以为是奥利弗(其实更多就是她想打架)的问题所以找奥利弗决斗
文章里的时间线是自家ULparo里多拉的R5故事,想写出一点毁灭前的忏悔,不知道有没有把这种感觉传递给大家……
那首诗是余秀华的《雨落在窗外》,看到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适合多拉,特别是那句“我把一个人爱到死去/另一个已在腹中”,完全符合我对于多拉的定位,喜欢得不得了也被这句话虐得不得了……
最后再次和看了这篇文的朋友们say一声sorry……对不起我又播撒负能量了(跪



那是一只蝴蝶,上下飞舞着,纹路在空中看不清楚,却在多拉的扫帚前打转,纵情地乘着风飞翔,无拘无束。
这是十月的第一个星期三,多拉的第五堂飞行课。在这门课上,她展现出的天分丝毫不比她那华丽得过分的哥哥差,稍加练习之后她便能够轻易趋驶手中的扫帚,带她去任何她想去的地方。
英格兰的天气一如即往,云在头顶团成一片,望不到边,入秋时分就已刮起的冷风这时更加薄凉了,那风从黑湖上经过,打到多拉的脸上时还带着凉意,将她的小脸吹得冰冷。
她却丝毫不受这些影响,一心一意地在空中追逐着那只蝴蝶。飞翔自然是有先有后的,她偶尔领先时总会放慢速度,拍拍她的扫帚让它体谅一下飞在她们旁侧的蝴蝶。有几次蝴蝶几乎落在了她的肩上,可她没空确认,迎面又是一阵强风,蝴蝶一再从她肩头吹落。
“蝴蝶是种挑剔的小家伙,它只会停在最美的花朵和有着美丽心灵的人身上。”
父亲的话再次席上心头,她似乎总是能找到另自己开心的想法,一贯如此,所以笑容很少在她身上离场。
蝴蝶向下坠去,似乎有些无力爬升了,她骑着扫帚跟在它身边。
向下飞行,映入视线的是霍格沃茨西边的围墙,还有一棵依靠围墙生长的大树,多拉分不清它是什么种类。
蝴蝶还在向下坠落,它的翅膀一动不动,像是刚刚的飞行耗尽了它最后的生命一般。最后它落得极低,立在一双带着黑色皮手套的手上。
多拉沿着那双手上扬视线,代表拉文克劳的蓝色围巾出现在她视线中,随后是一张英俊但冷漠的脸庞,很显然是一位学长。
他抬起头,看见了她。
她也正在看她。片刻之后,扫帚立在一旁的墙边,她则蹲在年长的拉文克劳学长身边,静静地看着他手中的蝴蝶。他没有开口拒绝,只是用平静的目光看着年幼的格兰芬多,而后低头看向手中的蝴蝶。
那是一只奇怪的蝴蝶,它的左右花纹并不对称平齐。很久之后的一天她偶然有了学习的动力,跑去附近的图书馆查找,一一比对资料上蝴蝶的模样,本以为这会耗去她半日的时间,却没想到麻瓜世界科技进步,她只对着看似呆笨的大家伙输入了几个关键词就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她所需要的东西。
人们称它美凤蝶,介绍上详详细细地写着它所属的纲目科属,说它雌雄同体,非同寻常。资料上写鳞翅目昆虫学专家声称,这种蝴蝶之所以蜕变为半雌半雄,是因为它早期发育时性染色体分裂失常。而且由于器官的损坏,这种蝴蝶不能生育,比正常的蝴蝶早死。多拉不喜欢这样描述,文字硬邦邦的,比她儿时就着凉水吞下肚的硬面包还不近人情。她倒宁愿想象这蝴蝶勇敢执着,依靠异变从几万分之一的概率中破茧而出,背负着不能生育的诅咒,独自守住没有同伴的天空,在飞翔之后死去。她一向如此,有着永远天真的眼睛和绝妙的想象力,因此梦境永远被她印在眼中,在平淡生活中闪闪发光。
时间回到当下,papilio手中躺着那只美凤蝶,多拉追逐它的旅程显然是它短暂一生最后的一次飞行,在歪歪扭扭的下降之后,它落在帕皮利欧的手上。他那双带着黑色皮手套的手此时张开,圆一般地拢住蝴蝶,让它停留在手上,度过最后的时光。
多拉永远也不会忘记那蝴蝶的模样。它被从中央一分为二,右边是耀如晨星的璀璨的黄,夹带一点红宝石斑缀在翅膀上部,宛如贵妇盛装出席舞会,另一边则灰暗无色,几乎要和papilio的手套融为一体,打扫过三百个烟囱的灰姑娘也不会比这更惨了,她这样想到。恍然间这强烈的对比另她想起了谁,定了定神她才敢肯定这种想法,世人眼光下,她的大哥阿方索有如左半部索然无味的雄蝶,而她的二哥,那个人尽皆知的唐·璜,则像右半部那闪闪发光的雌蝶。这一瞬间她一定是世上最了解莎乐美的人,因为这对比和剖白完全就是莎乐美心中所想脑中所知。
这样奇妙的想法却没能从多拉的脑袋里转移到一旁的拉文克劳身上。Papilio 凝视着掌中的蝴蝶,它翅膀的抖动越来越轻,几乎不可见了,有时候它停顿一阵,让她和他都以为生命的热情已经逝去了,但一阵风吹过,它的翅膀又开始摇晃,起先乘着风的节奏,随后转成它自身的、微弱不已的波纹。
两双眼睛都盯着它,紫色的眸子和银蓝色的瞳仁互不相让,都在努力地不让眨眼的瞬间夺去他们见证它逝去的刹那。同样的屏息凝神,对于papilio而言稀疏平常,他早已习惯这样静静地观察时间在物体上的流逝,饲养蝴蝶多年,这样的场景他倒不少见。多拉却并不熟悉这一切,死亡还未太早沾染上她的眼眸,她对此既感到惋惜又感到兴奋,一方面社会作为传授者教导她应当显出悲伤之情,另一方面,真实事件带给求知之心的鼓动是她这个年纪的孩子所无法拒绝的本能,孩子们总以痴笑对待死亡,一来他们对其一无所知,二来距离他们被这条恶犬反咬一口的时候还很远很长,恐惧悲哀这类负面的情绪被拉得太长,像绷紧的皮筋,反而会收缩弹起,显出一脸笑容。多拉也不过是个十岁的孩子,她见不到夜骐,还不知晓目光所不及的那半个世界。
多拉总归是生疏的,她还是没有沉住气,眨了眨她干涩的眼睛,再睁开眼睛时她担惊受怕,只担心蝴蝶在刚刚过去的那一刻离开了他们,但睁开眼睛,她欢喜地发现蝴蝶还在抖动着它的翅膀,但幅度远小于之前的任何一次。又一次,它的翅膀在毫厘间颤动了一下,最终停止不动了。
多拉抬头看了看默不作声的papilio ,后者此刻正低着头紧盯着手中的蝴蝶,多拉因此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位冷漠表情的拉文克劳的眸子。带有一抹浅银色渲染的蓝色眼睛此刻还是带着冷质的光芒,低头看向蝴蝶的目光跟随着多拉的动作转移了,正对上她的那双紫色眼睛,一刻停顿。
多拉不知道对方此刻在她眼中看见了什么,是她荒谬离奇的梦境还是她过往生活的噩梦?是帝王深紫色的血液还是凯撒紫色的披风?是否有往日的沉醉和逝去的欢愉生存呼吸的空间?她那时还不知晓有摄神取念这样的魔法,她自然也无法知道对方的心思。只是她这样望着那双银蓝色的眼睛,那双眼睛平静不动,没有一丝波澜,她从中什么都读不出。
她还不知晓的除了摄神取念之外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在很多情况下,什么都看不出的眼睛远比看得出波澜的眼睛来得有力。她感到和入学式时戴纳·福克斯给予她亲吻礼时一样的感受。僵直而发热,像是一块木头被灼烤,无法动弹的同时她感到自己的脸变得炽热,霍格沃茨这个略带凉意的秋天无法阻止她,黑湖水面吹来的冷风也无法阻挡她。她眨了两次眼睛,紫色的眸子将对视的视线移开,她又低下头看着那蝴蝶了,脸庞滚烫指尖冰凉,她伸出指头轻轻碰了一下那翅膀。
她触碰的是右半边,鳞翅闪闪,红宝石斑在阴沉沉的天下还透出彩虹的轮廓,像极了她额边别着的发卡。她还想触摸那已经逝去了的蝴蝶,一直稳稳捧着蝴蝶的双手却移动了,多拉抬起头,papilio已经手捧着蝴蝶站起身。
她在围墙边追上了他,远处是霍格沃茨外的群山峭谷,近处是黑湖水粼粼,再往近,蝴蝶躺在黑手套中,像是装殓完毕沉沉睡去的暮年之人。
“它死了?”多拉问。
“它死了。”Papilio答。
他们两人站在围墙边,对着它的尸体沉默了一会儿,多拉默默在心中为它编写了壮丽的一生,有它飞跃山谷时的壮丽,有它横渡湖泊时的轻盈,还有一段时间之前,它在她的扫帚前端最后飞行时的无忧无虑。等多拉想完这一切,她睁开眼睛,用肯定的眼神看向身边的papilio。
她的表情此刻肃穆起来了,她已经用这双眼睛见证过了死亡,她已经明白了这是怎样的道理,时间一到身体一轻,该逝去的都会逝去。她完全明白了。
Papilio收到她无声的信号,一直合紧的手掌此刻打开了,那只蝴蝶也依此下坠,乘着不时从湖面吹来的风,在这它曾经飞舞过的山谷里做最后一次的飞行。
“Lumos.”
Papilio的杖尖发出一点蓝色的荧光,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并不像黑夜里那样醒目,但却绝对足够,这光芒他自己看得见,多拉看得见,那只飞翔的蝴蝶也必然能看见。
“Lumos.”
这回是多拉的魔杖。两点荧光在围墙边出现,稳固不变,带有祭奠的肃穆气息。
多拉低头向山谷下看去,蝴蝶已经乘着风落入半山腰,小到她几乎看不见。正当她想着这也是理所当然并劝告自己接受这个合理但无趣的世界时,她忽然听见空中有翅膀扇动的声音。
那声音很小,轻飘飘地像是落在棉花中的一颗麦粒。可她听见了,她赶忙抬起头,一群各异但都斑斓的蝴蝶从她身后飞来,转瞬飞向山谷,仿佛在追逐着那逝去的蝴蝶,它们像梦一般出现又像梦一般地消失在山谷深处,多拉张大的嘴巴还没能合上,她还在为此次的奇迹而感叹着。
良久后,当papilio已经熄灭荧光,将魔杖收起时,她才回过神来,闭上张开的嘴巴,轻声念了句“Nox”,也将属于她的魔杖收好。
笑容又回到了她的脸上,伸出手她开始自我介绍:“多拉·璜,格兰芬多一年级。很荣幸能和学长一起看到这只蝴蝶的最后一次飞翔!”
“Papilio LEE,拉文克劳五年级,”他回应她的话,而后又问,“那是你的蝴蝶?”
多拉这才发现他的右耳缀着一只蝴蝶状的耳饰,紫色的蝴蝶和水滴状的下坠,衬在对方恰到好处的鬓发边,看着的确让人赏心悦目。
“不,只是我在飞行课上偶然遇到的,”她如是回答问题。然后好似又想起什么似的,追问说,“那些是你的蝴蝶?”
对方转而看她,良久才点点头,但多拉此时已经把前一大段的沉默当作了回答,没能理解他轻轻晃动头所代表的意义。
钟声在钟楼响起,悠扬着飘过山谷和湖面,跨越围墙和窗檐,向每一个霍格沃茨人宣告时刻。
Time up.
课程到此结束。
扫帚从墙角边回到了多拉的手上,飞起来时她的目光还停留在认识不久的学长的身上,她在心中又将“papilio”这个名字重复读了几遍,最后将她分不清的爆破音和浑浊音一并收叠,放在心脏上部的位置,藏好到无人能触及。
做着这样的蠢事的她当然不会知道,这只逝去的无名蝴蝶的翅膀,究竟在将来掀起了多大的风浪,改变的并不仅仅是她的人生,还有更多与她息息相关的人,一同卷入了这美丽的风暴之中。
TBC
想着都是看蝴蝶破茧有点老套所以这次干脆来看蝴蝶翘辫子(…… 我是不是有点残忍…………
papi有很多私设…………希望没有欧欧西!看人设千千万万遍,唯一的想法就是……赏心悦目…………太帅气太英俊太好看了,和papi一比我觉得老唐可以直接进老年唱诗班养老了(瞎比喻
十二取的名字都好文艺,为了不重蹈去年我在正剧里把水晶一直叫做柯莉斯特尔的覆辙,我决定这回都用英文,好好展现一下papi文艺十足的全名(
蝴蝶也是按照papi名字的梗选的凤蝶,美凤蝶的信息来源于网络报道。
剧情带有点私心,还是希望大哥哥们能给大佬一点爱让她继续在自己幻想的美好世界里生活的,我要做个正直的人给股票一个出头之日
但是大佬还是,没有对象……………………(哇哇大哭
开学路漫漫,大佬先来第一发……
提醒大家注意所有与树猴有关的片段,再重复一次,提醒大家注意所有与树猴有关的片段。
↓
火车车轮和铁轨碰撞,不断发出咔咔声。
没有旅伴的旅程总显得平淡无味,多拉从车窗往外看去,山林一片翠绿,还有条不知名的小溪顺着铁路线蜿蜒,绕过一个又一个小山丘,始终伴在她左右。
她站起身,用小小的胳膊向上拉来窗玻璃。窗子起初没有用,但在她鼓足了劲儿,用出十年来最大的力气向上抬举之后,窗玻璃不情不愿地向上退去,还发出不满的呲啦声。
多拉交叠起两臂,跪在软皮座位上,头枕在手臂上,趴在刚刚打开的窗口向外看去。火车还在飞驰,风从窗口灌入,吹起她金色的长发,总有那么几根头发不听话,老是粘在她的脸上,挡住视线。多拉嘟嘟嘴,从口袋里摸出一对红色的发卡,有些不舍地摸了摸光滑的表面和尾端镶红宝石边的一对翅膀,才将它们别在头上,固定好那几根扰人的头发。
窗外除了飞奔而过的树林,什么也没有,没有大片大片的橄榄田,没有在庄稼地上流着汗拿着锄头的农夫,没有西班牙热辣辣的阳光,最重要的是,没有她的阿方索。
收到霍格沃茨的录取书并不在她的预料之内,在这之前她对于魔法世界一无所知,还以为那不过是孤儿院里哄人入眠的谎言,和饱餐一顿的约定一样是个幻梦。可是好奇怪,一夜之间,她不仅有了美味的食物,有了干净的床褥,就连家和温暖的家人都紧握在手了,到了现在,甚至魔法也是一件触手可及的事情。她多怕这是一个梦,等某日睁眼,她还躺在湿冷的孤儿院里,臭烘烘的空气中充斥着隔壁床软弱家伙的啜泣声。
至于晚餐后被告知,其实家里有一个斯莱特、一个赫奇帕奇和一个格兰芬多这件事情,在多拉看来已经稀疏平常了,她几乎要相信自己已经融入这个家庭,身上流着和他们相近的血液,可以理所当然地顶着奇怪的姓氏上学去。
从那一天起,她的晚安故事就变成了《霍格沃茨,一段历史》的片段选读,午后休息时和阿方索一起唱歌的时段被重拾旧日记忆的赫奇帕奇改成了魔药学入门科普,最可怕的是,作为母亲的莎乐美似乎总是兴致满满,一双蓝眼睛眨得发亮,看得她有些害怕,同时,餐桌上原本的家庭闲谈更多地围绕着她从未谋面的二哥——唐·璜——他将负责带领多拉从伦敦前往霍格沃茨。
她的行李是阿方索收拾的,除开日常用品,阿方索本还准备替她打点好通知书上所列的所有物品,但很快被莎乐美制止了,正当多拉担心要被指责“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种老生常谈的事情时,莎乐美给出的回答则更加霸道:
“东西要买就买最好的!让唐带她去对角巷挑就好了!”
阿方索不出意外地又觉得一阵头痛,他依稀记起十一年前从伦敦寄回家的巨额账单。思索再三,他还是同意了莎乐美的决定。唯一放不下心的是宠物,他知道唐·璜在这方面没有经验,当年嫌麻烦连只猫头鹰都不带就只身去了霍格沃茨,搞得每次要送些什么东西都需要阿方索动身去伦敦,现在回想起来,仍是不堪其扰。
可多拉最后收到的宠物并不是理想的、能够长途运送物品的猫头鹰,相反,阿方索为她挑选了一只树猴。如果你要问他为什么,我想阿方索一定只会笑笑,然后把他的答案藏在心底,绝不外泄。
树猴在前往伦敦的火车票前三天送达,当时是傍晚时分,多拉正坐在她房间的窗前,火红的太阳将天空染色,她打开窗,燃烧着的山坡上,阿方索德笑容也沾上了红色,暖得她不禁颤抖。
关于树猴的名字,她和阿方索一直争辩未定,或许是因为对于自己随意的名字的不满在无意识之间被转移,她执意要挑选一个特别的名字,沉浸在茫茫辞海中却乱了阵脚,只会一个劲儿地否认阿方索想出的名字,最后还摔了门,哭哭啼啼地跑回卧室,把眼泪和鼻涕全都抹在被子上,在心里把“多拉”这个名字反复划上代表删除的横线。
半夜的时候阿方索来敲她的门,进门就给她了一块软毯子,来替换被她弄脏了的被子。她这才惊觉自己已经哭了半个晚上,流泪这种事情本在她进入孤儿院的三个月后就不再会做了,此刻她又懊恼又幸福。窝在阿方索的怀里、围着舒服的大毯子,这不属于她的一切又差点儿让她想要掉眼泪,结果泪珠还没从眼眶边挤出,阿方索的指头就将它抹掉了。
“别哭啦,”她的大哥低头在她的发梢落下一吻,“‘多拉’这个名字呢,读起来的时候舌头会先碰一下上颚,再弹在下排的牙齿上,哥哥我呢,每次读到这两个音节的时候,都很开心,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她摇摇头,她只记得这件事阿方索从未提过,她无从知晓答案。
一双手捧起她的脸,月光下,阿方索的面容出现在她眼前:“因为这是你的名字。自从你到了我们家,我觉得每天睁开眼睛都变得有动力了,我相信你是神送给我们家的礼物。”
“多拉,多拉,”阿方索握起多拉的手,近乎祈祷般呢喃着,“感谢上帝将你送到我身边,尽管他曾遗忘过我,但这次,或许……”
后面的话多拉记不清了,她只记得听完阿方索的一番话,整个人都像夏日里浮在薄荷冰治中的冰块,漂在表面,随后又融化下坠。她睡着了。
结果第二天,等多拉醒来时,原本远行的莎乐美已经提早归家,看着那只树猴眨巴的大眼睛,在多拉洗漱完毕前五分钟敲定了它的名字——施洗约翰,剩下头痛的阿方索和欲哭无泪的多拉面面相觑。
总而言之,在几出闹剧之后,多拉·璜顺利坐上了开往伦敦的火车,口袋里还放着离行前阿方索匆忙送出的、蝴蝶翅膀形状的红宝石发卡。
——要记得放好车票,联系到唐之后让他跟我说一声。
——安心啦哥,我没事的!
口头上的确是这样约定了,可当多拉透过沾着水渍的玻璃窗看到阿方索离去的身影时,一种奇怪的心情油然而生。此时她才十岁,无法明白这种感觉名叫落寞,但这道理在三年之后的一个晚上她会顿悟,然后起身打开一扇窗,在窗后没有西班牙宅子里那燃烧的山坡,没有那个站在窗下对她微笑,手中还捧着一只树猴的人了。
而与此同时,莎乐美将前往银杏街,在小报酒馆里,“药片少年”皮尔斯正以一杯白兰地蛋酒恭候着她的光临;她的二哥唐·璜即将搭上火车前往伦敦与她碰面,此次旅程他的对座将会是一个脾气奇怪但绝对有趣的姑娘,顶着那头染过的红发特地留下一绺黑发,自称AI,拖着罗密欧好容易才为她找到的身体满世界乱晃。另一方面,意大利佬的生活同样不平静,卡尔维诺推开餐厅的门, 本应该坐在那纹着鸢尾花家徽的靠背椅上的法兰西斯消失得无影无踪,有关她和赫鲁出逃的目击报告将在半个小时后由法比奥呈上。而多拉,多拉·璜,将在一年零三个月之后,因一个可笑的错误被“小雨点”所绑架,从而拉开一条线,串起其上的人们。
但此时,人们相安无事,多拉用力拉起面前的窗,火车正一点点接近伦敦。
T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