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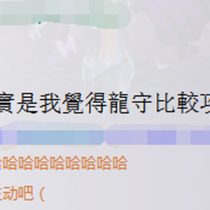

趁還有雞血多寫點日後狗了也不會太難看【……
淺倉你快投人設啊【裂聲
潜入调查的第一周已经结束,除了多记下了几个人名,内山隼人依旧一无所获。他倒是并不觉得紧张或者沮丧,计划原本便是以月为单位,操之过急未必能够得到成效,反倒容易打草惊蛇。开学之后他和龙守又接触过几次,后来意识到根本不用这么小心谨慎,相熟的朋友编在不同班,下课时互相串门找人实在是再正常不过。在警署时相识的同事浅仓麻理子和龙守分在一班,三个人索性大大方方地结伴而行,借着吃饭等较为私密的时间,小心地交流信息。
浅仓和内山不同,是全然不相信所谓妖怪之说的,为人略有些古板,内山有时半开玩笑地说会不会是妖怪所为,就会被她板起脸训斥一番,不到内山连连认错不会罢休。通常龙守在这时既不会落井下石也不会帮他说话,只是一脸事不关己地做自己的事情。碍于学校里人多眼杂,三个人平时并不过多讨论调查的事情,更多说的还是校园里各种风传的流言。
“听说高二有恶性霸凌事件。”
这一天的新消息是浅仓带来的,她一直到吃完最后一点米粒,擦干净嘴巴之后才发言,内山一下被她的话吸引了注意力。开学没过多久,学生之间的小集团才刚刚形成不久,这时就算有霸凌事件通常也都是小打小闹,足以被警察称为恶性的霸凌事件,按常理来想,实在是有些不合理。
“什么情况?对象是谁?”龙守似乎也被浅仓的形容引起了疑虑,放下筷子发问。浅仓扫了一下四周,像是那些传递八卦的少女一样把手放在嘴边,弯下身子,嘴唇微动快速地吐出几个音节:“我不知道。”
龙守攥了攥拳头,似乎按下了一波涌上的打人冲动,浅仓则像是毫无察觉一样不为所动,坐直身体恢复了刚才的声音:“我也说了,只是传言。并且对象在高二,你们要查会很麻烦,如果因为这个惹到别的事情,很有可能自己也被卷进去。”
她说到别的事情几个字时略微停顿了一下,内山和龙守都明白那是警告他们不要惊动学生或者其他什么人的意思,刚刚开学,他们在学校里还处于近乎一无所知的状态,在这种时候自己去没事找事,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说起来,你们加入社团了吗,加入社团之后认识的人多一点,应该也会比较有趣吧。”内山放下了令空气有些沉重的话题,换了一个如今谈论度相当高的问题。开学一周有余,忙完了琐碎的事情之后,各个社团也开始招纳新的成员,公告板上贴满了五彩缤纷的海报,内山路过时瞟了一眼,不仅看到了剑道与弓道这样的固有项目,还看到了侦探社与文学社一类新生文化的社团。
“我在弓道社。”
“我在红茶社。”
龙守和浅仓点点头,各自报上了社团,内山嗯嗯地跟着一起点头,忽然又察觉到什么一样睁大了眼睛看向龙守发问:“红茶……为什么会有红茶的社团啊,是研究茶道之类的东西?感觉和你不搭——咳噗!”
浅仓淡定地看着被一记直拳打趴在地上的内山,手上还在收拾自己的便当盒子,共事的时间长了,她已经从一开始还会拦阻的状态变成完全的你们开心就好,毕竟纵观历次暴力事件,八成都是内山说了什么不恰当的话。况且明知龙守对熟人时总会无意识地动用暴力,还要缺心眼地去戳其逆鳞,实在是蠢得让她提不起同情心。
等她把包裹重新系好,内山才捂着被直击的半边脸颊,惨兮兮地爬起来。浅仓看着他一脸委屈像只小狗,不由叹了口气想大概这人少有的优点之一就是能迅速认怂。也不知道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变回十六岁的外貌之后,他那张可怜巴巴的脸看起来更让人不忍心下手了。
——不,龙守大概是论外。
浅仓看看毫无收手打算的龙守,及时地开口出声,扯开了两人的注意力:“我说,内山你呢,看你天天背着把竹刀到处跑,是要去剑道社吗?”
“我?我没打算去剑道社啊。”内山摇了摇头。“竹刀只是因为手里空空不安心准备的替代品而已,我记得学校里有新闻社,如果能加入的话打算去新闻社,那里的消息应该更灵通一点。等会吃完我就去公告栏看看。”
新闻社对于需要随时关注校内风吹草动的他们来说,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浅仓有些惊讶于内山的敏锐,仔细想想却又并不是十分意外。内山的迟钝或者说缺心眼,更多的是表现在人情世故上,切实涉及到本职工作时,他从来没有出现过难以弥补的失误,甚至在某些时候有着仿佛是本能一样的敏锐。
如同猎犬一般。
也许这才是上司同意他参与行动的真正原因吧。浅仓点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看着内山三口两口吞下了剩余的食物,灌了一大口茶,像个仓鼠一样鼓着脸一边咀嚼一边跑走了。
内山隼人站在教室门口,有点紧张地摸了摸自己的脸。
虽然只是用手上的触感去确认并不可靠,但是眼下也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去确认,几分钟前刚刚去过洗手间,而且上课钟马上就要响了。
没关系,真的有突发状况,大不了请个病假跑路。
他握了握拳头给自己打气,推开门走进了教室。
教室里已经差不多坐满了人,互相认识的朋友凑在一起聊天,性格外向的四处和人打招呼,也有几个只是安静地整理自己东西的内向学生。内山走到贴着自己名字的座位上坐下,摸了摸扣在头上的帽子,最后还是摘了下来一起放到桌子里去。
不能引人注目,不能引人注目,要混进学生里面去……他内心不断地默念着接下任务时上司反复的叮嘱,只恨自己没有三头六臂,不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看看到底是哪里有着怪异。
正在他几乎竖起了全身汗毛警戒四周时,背后忽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好……可以稍微挪一下桌子吗,我这里有点坐不下了。”
和他打招呼的是个表情淡漠的少年,内山这才察觉到自己占了不小地方,一边道歉一边帮少年把桌子挪回原位,转回去之前他悄悄瞥了一眼少年桌上贴名牌的位置。
十六夜夏儿。
十六夜,十六夜,内山抓了抓自己的头发,猜想会不会那么巧就是自己认识的那个十六夜。龙守确实常常提及自己有个弟弟,虽然素未谋面,不过本身这个姓氏就少见,多半世界就是这么小,恰巧被他碰到了熟人的弟弟。
想到这里他又偷偷回头瞥了一眼,少年正在低头整理自己的书包,并没有注意到有人偷窥自己,略长的头发和秀气的长相让他看起来有点像个女孩子。
这么文静的孩子,不会被欺负吧……
内山有点不放心,夏儿让他想起自己还是学生的时候,那时他的班里就有文弱的男同学被人欺凌,虽然也不到恶性事件的程度,但也只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上来说,当事人所忍受的折磨,恐怕远远超于表现出来的部分。
不论如何,既然同事的弟弟就在自己同班,怎么也要照顾一下,至少不能让人觉得他没有朋友,很好欺负。
内山隼人这么想着,转过了身去。
“你好,我叫内山隼人,以后请多指教啦。”
时隔多年再捡起课本,说是两眼一抹黑似乎有点夸张,但是内山看着摊开的课本确实心中有了几分陌生。老师还在讲台上念着授课内容,他小幅度地伸了个懒腰,心里想着做学生也还是挺辛苦的,却不想胳膊刚刚抬起来没多少,就感觉到了明显的紧绷感。
坏了。
他立刻猜到了是怎么回事,来不及想太多,先捂住了脸弓下身体,希望这样能稍微掩盖一点自己身上发生的异常,幸好大家都专注于听讲,似乎没什么人看着他,连他身后的夏儿都没发出什么疑问。
这么一想,确实从早上用过喷雾之后时间已经经过了将近八个小时,之前研发科的人的确说过,根据身体情况不同,也许会有人的作用时间较短,看来他就是那种作用时间短的人。没想到早上想好的退路居然这么快就能用上,只可惜比起夸自己心思周密,内山隼人现在更觉得是自己乌鸦嘴。
幸好喷雾的失效不是瞬间完成,而是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才能完成,内山捂住嘴举起手,老师注意到他的动作,关切地走过来询问他发生了什么。“抱歉……那个……我有点想吐……”话说到一半,他装作忍不住的样子捂住嘴,草草地鞠了个躬表示抱歉,就一路小跑冲出了教室。
上课时间的走廊上没有人经过,内山却不敢大意,仍旧是捂着脸弓着腰,溜着墙边快步走,直到钻进厕所的隔间方才松了一口气,赶紧从贴身的口袋里摸出喷雾,补了两下。没过多久,绷紧的衣服恢复到了能自由行动的程度,内山听着外面没声音,跑到洗手台去照了照镜子,看到镜子里稚气未脱的少年,终于放下心来。
实在是太惊险了,好在开学第一天,还没几个人记得住多少同学的样子,他跑出教室时应该没人发现他的身高不对劲。
就算已经脱离了被发现的危险,想一想还是觉得后怕。内山捂住了装着喷雾的口袋,心里计算着时间,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按照他的有效时间,要在学校里度过一整天,必须要进行一次喷雾的补充。
简直就像是警署里的女同事一样,每隔几个小时就要去茶水室补妆。
内山苦笑了一下,打开水龙头洗了洗脸,整理好衣服返回了教室。
下午放学之后,内山和已经略微混熟了一点的十六夜夏儿告别,拿上书包溜去了龙守所在的班级教室,正巧看到龙守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十六夜,十六夜。”
内山躲在拐角后面小声叫她的姓,就见龙守的动作略微僵硬了一下,左右张望一番之后发现了他,黑着脸快步走了过来,内山只来得及从她的表情里猜出自己八成又做了什么惹她生气的事情,就已经被她拖到了楼梯下面的角落里。本着总而言之先道歉的行事方针,刚刚站稳,内山立刻双手合十说了句抱歉,反而噎住了龙守。
“内山前辈啊……”龙守头痛地叹了口气,这个前辈有点缺心眼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的共识,但是任她再怎么清楚,也没想到这个人会在开学第一天就跑来和同样潜入的同事联系,还大大咧咧地叫出了她的本姓。“我应该和你说过吧,我潜入期间会用化名,而且不是告诉过你叫什么了吗?别在这里叫我十六夜啊?”
“啊,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不过,呃,你不觉得一番合戦更显眼吗……好了我什么都没说,找你是有别的事情想问你。”
深知自己这位同事一身怪力的内山看到龙守示威一样地晃了晃拳头之后立刻毫不犹豫地认了怂,已经放学的走廊里没什么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压低了声音。龙守听他语气认真,也收起了开玩笑的心情,点了点头示意他问。
“十六夜夏儿是你弟弟吧?但是我们这次的行动应该是严格保密的,所以你应该没有和他说过,但是同样都在高一的话,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能瞒过去吗?”
“……船到桥头自然直,能瞒多久瞒多久吧。学校这么大,你帮我盯着点夏儿,尽量不碰上就行了。”
龙守摇了摇头,提到夏儿让她的表情变得严肃了一点,但是很快又恢复成平时的样子,放学钟响过已经有一阵子了,内山虽然短时间内不会再有暴露的风险,但是龙守似乎已经快到时限,两个人只是简单地交流了一下今天的情况,确认过没有异常之后,龙守就匆匆离开了。
“……一番合戦啊。”
内山挠挠头,露出了微妙的表情。

“一真,是不是有人跟着你?”
松海一真闻言转过身去四下张望,花了点时间才在一块突出的岩石后面看到有点眼熟的身影。作为一家之主的一真平时少不了和其他家族的人打交道,因此略微想了想才回想起那人是谁。
“内屋先生……?”他试探性地喊了一声,躲在石块背后的人影动了一下,然后带着尴尬的笑容走了出来,正如他所猜想的,是在祭典上捡到了扇子,又拉着自己到处打听寻找家人的那个黑肤青年。“我继续往前面走走,你快点跟上来吧。”松之丞见两人似乎认识,略微点点头打个招呼,便转身继续往迷宫深处走去,进之助略带着点好奇地探头张望两人,可惜走出来的并不是可爱的女孩子,因此看了几眼也兴致缺缺地跟着走远了。
“呃,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和舅舅他们走散了,正好看到你想跟你一起走,不过看到你们是整个家族一起行动,怕有什么不妥……那个,我真的没有什么不良企图。”
内屋衣御有点慌张地解释着,没说几句似乎察觉到自己的辩解苍白无力,挠挠头转开了视线,又忽然抬头急切地表明自己的无敌意。
作为曾经被人类所“背叛”而灭亡的武家,在复活之后心存怨恨与怀疑再正常不过,尽管从刚刚松海家人的表现来看他们似乎并没有对内屋的行为有明显的不满,却也只是表面上看来而已。况且就算是在和平的年代,这样鬼鬼祟祟地跟踪别人也是违法的行为,两个人还远远没有熟识到能够开个玩笑就将这件事翻过去的程度,如果松海一真因此发怒,恐怕……
想到这里,内屋衣御又是垂头丧气又是手足无措,慌张得几乎想转身就逃走,却又深知这时绝不能做的便是逃跑,最后他只能紧紧闭上了眼睛,等待松海一真的反应。
发怒也好,怀疑也好,觉得恶心也是难怪的,早知如此,还不如在迷宫入口看到他时就大大方方地上去打招呼,怎么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个地步。
内屋衣御的脑海中百转千回,令他瑟瑟的叱骂却始终没有降临,他只听到松海一真轻轻叹了口气,他说话前似乎总是习惯叹一口气,仿佛这短短的一声就能把万语千言都传达出来。
“内屋,你的手臂被烧伤了。”
最后得到的是一句羽毛一样轻飘飘的话。
内屋衣御抬起头,看到松海一真正在随身的小包里翻找什么,片刻之后递过一个碧绿的小盒给他。“……这只是普通的烧伤药,实在是有点寒酸,是我自作主张了……”见他呆愣着并不伸手去接,一真似乎误解了什么,有点窘迫地收回了手想把那盒药膏放回包里,内屋衣御这才恍然大悟,一边慌慌张张地摆手示意自己并不是嫌伤药普通而不收,一边想去拦一真,又觉得自己冒失,急出了满身的汗,最后索性心一横,一把抓住了一真比他细了一圈儿的手腕。
一真倒是不如他想的那样惊讶,只有点诧异地看了他一眼,这一眼仿佛比翻滚的岩浆还要烫上百倍,内屋衣御又像摸了火似的赶忙松手,背着手活像是被父母训斥的孩子,左右思索半天,最后结结巴巴地说了句对不起。
一真稍微睁大了点眼睛看着他,停顿几秒后还是伸出手,把那个碧绿的小盒塞到内屋衣御手里去,抓着他的手让他攥紧,不至于滑落,然后便微微行了个礼,转身离开了。
只留下雷鸣般的心跳声。
擅自把zak和hass敲欄杆的事件寫進去了,有問題的話請留言我會刪除
角色屬於親媽,ooc屬於我,費爾南多真可愛,想娶回家【問題發言
他做了一个将鸟儿放飞的梦。
黄色羽毛的小鸟只有他手掌的一半大小,毫不畏惧地在他手背上跳来跳去,用鹅黄色的喙啄他的指甲,脚爪扎着皮肤也只是有些痒。鸟儿个子不大,但是翅膀边缘的羽毛已经长了出来,可以轻松地飞到树上去啄下来一片叶子,又折返回来把叶子丢在他的头发上,发出愉快的鸣叫。
飞吧。
他把手举起来,鸟儿就张开翅膀飞走,停到路边脏兮兮的墙头上,黑亮的眼睛里映出他的脸,歪着头看他一点点走远。
飞吧,Ava。
起床铃把约翰从睡梦里拉出来,走廊里很快传来嗡嗡的说话声和走动的脚步声,夹杂着听得懂或听不懂的脏话,狱警哗啦啦地掏出一大串钥匙把牢门打开,随手用警棍敲敲铁栏杆催促他们动作快点。约翰刚想从床上坐起来,一道黑影忽然从天而降,直接跳到了地上的费尔南多意识到自己差点踩到睡在自己下铺的室友,抱歉地冲他笑了笑,一只脚着地,跳着开始穿鞋子。神情严肃的高中教师已经整理好衣服走了出去,如果不是他整齐地穿着监狱统一发放的囚服,说他是要去给学生上课也一点问题没有。伦纳特——在这间牢房里住了一段时间之后约翰才透过李比希的只言片语知道了那个脸上有一片烧伤的瑞士人叫什么,作为这间牢房里看起来最为凶恶的人,瑞士人令人意外的安静,现在也是一如他平日一样,沉默地整理着自己的东西。按约翰的人生经历来看,伦纳特比他见过的一些体面人还要整洁得多。
在得知自己将被关到戴维尔监狱之后,约翰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混乱”这个常常和戴维尔监狱捆绑在一起的形容词,也正因为如此,他从踏进灰色高墙的那一刻起就绷紧了自己的神经,警惕着不知何时就会突然降临的横祸。但是事实正和流言相反,至少他至今还没有招惹上什么麻烦,托这些和寻常恶徒相比有些怪异的室友的福,这半年多来他过得甚至比原来还要安稳和规律——自然,前提是无视掉铁窗和手铐。
食堂里一团嘈杂,狱警看不见的角落里有人斗殴,新来的囚犯谄媚地笑着把自己幸运得到的肉菜送到老犯人桌上去,几个不合群的新面孔挂着脸上和身上的伤坐在一边冷眼旁观,花点力气能换个舒坦日子怎么想都是稳赚不亏的买卖,只要不被杰克抓个正着,斗殴就是监狱里最直接的交流方式,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打架一样是用拳脚。
约翰已经渡过了作为新人被欺压的时期,得以安静地吃他绝算不上丰盛,但能填饱肚子的早餐,余光里瞥见李比希坐在隔了两张桌子的墙边,费尔南多端着自己的食物本来想绕开他,左顾右盼却没找到合适的空座,只好讪笑着坐到李比希对面去。不知在狱中还能遇到自己的老师,甚至分配到同一间牢房究竟是怎样的心情。
互相打探入狱的原因难免让人觉得被冒犯而恼怒,费尔南多究竟因为什么而来到以混乱闻名的戴维尔监狱,约翰至今也没有弄清楚。然而他却隐约感觉得到,费尔南多并非被划在某一条线内的人。与其说他善于伪装,倒不如老实承认他怎么看都只是个普通的大学生,带着一股无忧无虑年轻人的快活,连撒尿时口哨都比别人吹得多转两个弯儿。
在他安静吃饭的空当,食堂角落里的喧哗声终于大到了无法忽视的程度,犯人趁着端起汤碗的时候小心翼翼地从碗沿上观望,然后三两成群,小声交流自己的猜测,直到狱警闻声赶来,人群方才一哄而散,只留下几个打红了眼的人仍然撕扯在一起。
结果是所有人都吃了惩罚,托比中午得到了假期,犯人们则被警棍驱赶着,一边暗自咒骂狱警一边把双手背在背后绕着空地蛙跳,结束之后还要照常工作,补平因为骚乱和惩罚落下的工作进度。原本这也是常见的事情,但是到了晚餐后的休息时间时,约翰却清晰地察觉到了人群的不安定,好赌的收了自己的摊子,嗜酒如命的藏起了自己的瓶子,好勇斗狠的也收敛了不少,所有人都皱着眉头,警觉地扫视着四周。
费尔南多从人群里挤出来,看见约翰站在入口,向他随便招了招手打了招呼就往牢房里走,约翰快步跟上去,小声询问他:
“怎么回事。”
“打残了。”
费尔南多的回复简短而急促,压低了的声音末尾带着有点急促的呼吸声,他左右看了一下,抬手抹掉了额头上渗出来的薄汗。“没认出来是哪边的人。”
“估计要出事。”
他最后如此判断,然后闭上了嘴一个字都不再说,一反常态地紧绷着脸走开了。
纸包不住火,费尔南多得到的消息很快就被证实了真伪,并且在交头接耳之间迅速地传播开来,一时间流言漫天飞舞,早晨风传白熊兄弟会要对哪个小帮派动手,中午就变成黑豹帮内部有矛盾,晚上再变成这一切骚乱都是街头游击队的计谋,睡觉之前费尔南多小声念叨听说杰森在搞些违法的药品,犯了事被抓走的囚犯都会变成白老鼠。
只是谁都知道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可信度,只是嘴皮上下一碰吐出的消遣。他们一间牢房的人都没有加入帮派,闭上嘴巴躲开冲突核心就能过得还算平稳,费尔南多虽然四下探听着,但是夹杂在各种心怀叵测的人之间,反而成了最好的掩护;伦纳特只偶尔和李比希用德语交谈两句,其余时间就不做声地做自己的事情,而李比希一张脸上鲜有表情波动,最后约翰反而成了对即将到来的暴风雨最为关注的人。
作为导火索的第一场骚乱是在某一天的午休发生的。
实际上这场暴乱并没有持续多久,远离暴乱现场的约翰当时正在和新结识的囚犯们聚在一起打牌,隐隐约约听到牢房那边传来喧哗的声音和什么东西敲击金属栏杆的动静,还没等他找到人问发生了什么,狱警就已经闻声赶来,带头骚乱的两个人跑的飞快,最后还是被狱警扭住按在了地上。打完一局离开娱乐室的约翰正巧看到两个人被狱警推搡着押走,和他擦肩而过的两个人脸上没有任何的不安,个子矮小的黑肤青年甚至还摆着一张愉快的笑脸。
正如他一开始就猜想的,有人忧虑混乱,自然也有人享受或者渴求混乱,搅混了水之后,有想法的人才能更加舒服地行动起来。当小型的摩擦斗殴频繁地发生时,原本引人注目的行为就变得不那么显眼,能够更加简单地被掩盖。费尔南多甚至在睡觉前抱怨有人问他是否有兴趣去参加一场乱架,而伦纳特也用他生涩的英文表明自己收到了同样的邀请。约翰从中国的囚犯那里听说了一句谚语叫做声东击西,用来形容眼下的情况再合适不过。
乱糟糟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监狱方似乎收到了压力,开始加派警力,狱警们的装备也升了一个等级,足以让他们直接用武力镇压骚乱。消息灵通的耳朵说戴维尔监狱的暴乱给某一些人的道路上添了不光彩,惹恼了他们。麻烦的是矛盾爆发的起因并非短期的冲突,而是长久以来的积怨,老道的狱警在这种时候都清楚单纯的镇压无法解决问题,可惜的是会听他们意见的人并不存在,其结果便是空气愈发地充满了火药味,连竭力避开冲突的约翰自己都被拉下了水。
要说是偶然似乎也并不确切,连日的冲突让所有人心头都冒着火,起因也许只是两句口角,结果却是十几人的混战,约翰来不及闪避,被卷入了战场,为了自保不得不挥起拳头,只是让结果变得更糟。混战里他的脸上中了两拳,衣服也被扯掉一只袖子,要不是没什么人能持有利器,恐怕还要多几个血洞。他从晃动的人群间隙里看见费尔南多焦急地冲他比划着什么,以为他要来帮手,还没来得及示意他快跑,扛着防暴盾,举着麻醉枪的狱警已经冲了过来。
因为麻醉枪失去意识前,他看到了水泥高墙中间的阴晦天空,那里不曾有鸟儿飞过。
“米切尔先生,我们决定收养Ava,她是个好孩子,不应该有一个蹲监狱的监护人。”
“这就是你最后一次见她了。”
飞吧,Ava。
他想挥挥手,但是已经做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