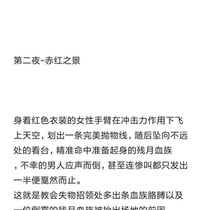




1、
海边的礁石上,一个男孩正在织网。他的父亲坐在另一块邻近的礁石上,手捧这张巨网的另一头,细细检查男孩的编制是否足够结实。
这不是一张普通的渔网,而是用以杀死危险海兽的猎网。悬挂在绳结之间的上百个钩齿被打磨得锋锐无比,可以轻易切裂鲨鱼甚至虎鲸的皮肉,也足以犁开那些危险海兽的表皮。
“你做得很好,阿密特。”男孩的父亲勾起一个鼓励的微笑,望向他年幼的儿子。而阿密特没有回答,依然专注于指尖编制金属丝线的工作。
他们是海边的猎人氏族,相比普通的渔获,他们狩猎那些价值更高也更凶猛的猎物。当这张捕网完成后,阿密特的其中一个姐姐会带着它出航。那些似人非人的水中恶魔将在这张如千齿大口的捕网中挣扎,啸叫,以自己异色的血在海水中染出一团朦胧的云雾。而它们越是挣扎,捕网上的金属丝线与利齿就会嵌合得越深,像是渐渐勒紧的上吊绳般,利用怪物的体重和力量收走它们自己的性命。
为此,这张网必须足够结实,足够锋锐。这是阿密特学到的捕猎技巧中最重要的一条:有备而来,确保自己身为猎人永远强于猎物。
虽然他尚未到达亲身参与狩猎的年纪,但已经理解了这一套前序工作的重要性。男孩专注地编织着金属丝线,就像亲手编制着某个怪物必将死亡的未来,一步步将血腥的预言织入现实。
只有这样细致的工作才能让他的思绪暂时被占满,无暇思考。阿密特沉默地编织着,但工作终究会结束,而他又会想起不久前被带走的姐姐——不是即将出海捕猎的那个,而是另一个,与他年龄更为接近,感情也更亲近的姐姐。
随着手头的工作结束,阿密特脸上原本专注的神情又变回了一种符合年龄的茫然与不满。父亲仔细地盘起编制好的猎网,确保下一次当它被展开时只需利落的一掷。而阿密特则扭过脸去,看着海岸上延伸的聚落屋宇。
他们栖身的房屋或可称得上原始,但绝不破旧,这是一个庞大兴旺的母系氏族。阿密特有许多位姐姐,一位父亲,几个叔叔,与一位主母。他与主母相处的时间并不多,但依然能感受到落在自己身上的偏宠。也许因为他是家族里年龄最小的孩子,也许因为主母在家族的所有男人中也最为深爱阿密特的父亲。
所以,他无法理解在这个爱意从未停止流淌的家族中,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阿密特最喜欢的姐姐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他们。消失的人是家族的女儿,而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邻人,所有人却都不再谈起她,好像部族中从没有过这个女儿一样。
“你们为什么不再提起她了?”阿密特的话飘散在咸腥的海风中,像是从脑海中浮现上表面的一句自言自语,但还是被他的父亲捕捉到了。
“我们不再谈起她,是为了不让伤心的尖锥再度扎入每个人的胸膛。”哪怕没有指明“她”是谁,显然父亲也了解自己的儿子,“但我们还爱着她,没有一天不默默思念着她,和你一样,分毫不少。”
“那为什么一定要送走她呢?”阿密特扭过头来,眉头紧皱却红着眼眶。这一星期以来他总是容易变成这样,想要痛哭,又想要怒吼,最终二者却都只能止于胸膛之内,“什么是圣女?她为什么要离开?”
阿密特的父亲收好了簇新的捕网,向他伸出手:“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说吧。”
他们已经讨论过这个话题很多次了。每一次,父亲都会尝试用不同角度的答案:因为圣女不属于她的家庭,因为你的姐姐是一个无私的人,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为圣女安排好了她们必然要去的位置,因为我们无能为力阻止她的离开。
阿密特并不满足。他隐约察觉到了,这些都是真相,父亲并没有骗他,但并不能让他胸腔中酸楚的冲动找到出口。
父子二人行走在海边,阿密特沉默着,父亲也沉默着,仿佛这回已难以再编制出另一个回答来满足儿子。无尽回响的涛声与海鸥的鸣叫环绕着他们,阴沉的云层间投下几束光柱,洒在靛蓝近墨的海面上。父亲走在前面,而阿密特低头跟随着他留在沙滩上的脚印,默默走在后面。
最后,还是阿密特自己开了口:“没有人能强迫她离开这里。”
“如果她不愿意,我们的家族一定会保护她,”他的父亲没有回头地说到,“虽然和教会敌对是不明智的,但是家人更加重要。”
阿密特的脚步渐渐停下,得出了那个最接近的答案。
“所以……是她选择离开了我们。”
他想起那天姐姐离开时的背影。没有人拉着她,也没有人敢拽住她。只比阿密特大了一岁的少女步伐端庄,姿态优雅,像个胸有成竹地大人般走出了他的视线。她没有与任何人告别,或许是不被允许,或许是她知晓必将分叉的道路不再交汇,已没有必要回头。
只要想起那个场景,他的眼睛就开始刺痛。为了忍住泪水,阿密特紧抿着嘴,嗓子却像要崩裂开一样,在放声大哭的边缘锁住了所有的难过和绝望。一团痛苦的空气梗在了他的呼吸道里,胸膛与肺叶也在抽噎的边缘紧紧闭合起来。
这是被抛下的感觉,阿密特终于理解了。
仿佛是感知到他的痛苦,男孩的父亲就在这一刻回过身来,向自己的儿子张开了双臂。如今他面上的表情竟与阿密特相差无几。
在这一刻,男孩才完全相信了父亲的话:他同样爱着那个丢失的女儿,没有一天不默默思念着她,与阿密特一样,分毫不少。
阿密特向前跑去。在那坚实的拥抱中,他仿佛又紧紧抓住了自己所失去的一切。
长久的拥抱结束后,阿密特与父亲在海边又多逗留了一会儿,好把脸上哭花的痕迹全部抹去,让双眼和鼻头褪去通红。
海水一波接一波地拍打着岸边,冰冷的涨潮啃噬着脚下的沙滩,将他们推向家的方向。阿密特的父亲搂着他的肩头,另一手里提着他儿子的得意之作,第一张完全由他自己编织的捕网。男孩紧靠着父亲走着,他们的影子重叠在一起。现在阿密特感觉好多了,在大哭一场之后,仿佛失落也变得可以接受。
在接近他们的聚落时,事情却开始变得有些不对头。姐姐们四处奔走着,指挥着面带仓惶神色的男人们远离主屋。她们的低声絮语间透露出不祥的信息:主母病倒了。是那个让人浑身腐烂的血液怪病,它可怕的触须终于也伸进了这偏僻沿海的小小聚落当中。
阿密特瞬间便感到自己身侧的男人变得肌肉僵硬,呼吸也急促起来。
“爸爸?”他抬起头,父亲眼中却已经不再有自己的身影。
男人松开了原本搭在他肩头的手,匆匆往前跑了两步,张望着聚落中的情况,没注意到阿密特还没来得及跟上。家族献出了他们宝贵的女儿,然而并没有使命运偏袒半分,甚至愈发严酷:主母是整个家族的主心骨,他们或许可以忍受送走一位女儿的悲痛,却绝不能失去这位母亲。
对阿密特的父亲来说尤其如此。
男人焦急地跑了起来,拉住一位姐妹询问主母的情况,随手将盘好的捕网放在了一旁的晾晒木架上。捕网滚落散开,在地上拖拽着,不再有人注意。
“爸爸!”
阿密特看着父亲冲向主母的屋宇,却又被拦下。姐姐们厉声喝止了任何人靠近,哪怕是主母最偏宠的男人。其他人解释着怪病可能在整个家族中传开,每个人都不应当靠近。但阿密特的父亲拒绝服从,头也不回地冲向了混乱的中心。
而阿密特就站在这片混乱的边缘,无措地看着父亲离自己而去。
2、
米迦勒穿过小教堂的前厅时,扬希正靠在拱门边等待着,向他打了一串手语。那本来可能是一句叱责:“你怎么花了这么长时间?”,但因为扬希弯起的眼角和放松的手腕挥舞弧度,这就成了一句亲昵的问候。
“和铁柩圣人多谈了一会儿。”米迦勒出声回答。扬希偏了一下头,米迦勒知道这是关心,于是他又补充到:“没什么紧急的事情,乌瑟尔队长已重新睡去。棺椁的情况很稳定。”
这回扬希点了一下头,他的好奇心暂时获得了满足。但很快,他的手语中划出一个三角,那是教会的意思。米迦勒扬起眉毛,他们一般不会提到教会,因为猎兵队在沙漠和赤贫者的村落以外任何地方都不受欢迎,井水不犯河水已经是最好状态,更不会考虑参与。
“不,我不会去跳舞。”他平静地回答,“你明知道我不会。”
扬希当然是在取笑米迦勒。他们在少年时代就被送入了猎兵队,而在那之前,米迦勒——那时还是一个叫阿密特的小男孩,从未有机会见过城市的高墙与教会的尖塔,更遑论去想象一场举办于其中的舞会。
“对猎兵来说,比武也没有必要。如果不是决心杀死敌人,最好就不要亮剑出鞘。”米迦勒叹了口气,“当然,你想去的话完全可以。我会把你的假期按缺席天数扣掉。”
扬希的喉咙里发出一串丝丝的气声,那是他受损的声带能发出的唯一声响。米迦勒知道这空洞的声响其实是他在笑。
扬希双手所比划出的手势越来越快,也越来越凌乱,让人眼花缭乱,对米迦勒来说却毫不费劲——你说话越来越像老队长了,一定是花了太多时间和铁柩圣人们待在一起。
米迦勒闭了闭眼,确实如此,但他也只是尝试着提前接受自己的末路,每一个队长共同的末路。
他咽下关于铁柩圣人的话题,这是他自己要面临的问题,不是扬希的。他转而问自己的队副:“那你建议我去和谁待在一起更好?”
这回扬希的手势只是简单地在他们腰部以下的位置一摆:这是“孩子”的意思。
“新兵?他们还在害怕我。”米迦勒对此保留意见,“给那些新来的孩子一点掩藏自己心思的时间吧。”就像你我曾经一样。
扬希用肩膀轻轻撞了他一下,比划出另一串手势:总得有人来吓唬他们一下。
米迦勒沉默了一会儿,他的确很久没有去看过新兵了。上一次交易日换来的孩子们正缓慢适应着他们崭新的军营生活。许多人原本的家庭条件比小教堂所提供的充足食宿要更差,但每个孩子都会想家,都会企图离开。而那些年长的猎兵们对此心知肚明,却从不点破。
孩子们之间的秘密最终会成为联系他们的纽带。直到在洗礼中取得新名的那一刻到来,他们才会真正长大。在那之前,犯错总是被允许的,一个带有恐怖警告的前辈形象则能避免他们在错误中胆大妄为地走得太远。
“我只会说实话,不会吓唬小孩。”米迦勒做着一点最后挣扎,但他们已经在扬希的带领下往新兵校场的方向走去了,“你该去找拉法叶,他最擅长编故事吓唬人。”
没什么比实话更能使人绝望——扬希玩味地看着他,手中比划着——进而使人安分。他们会明白的。
每一批新兵的问题都是类似的,等待着他们的未来也是相同的——不,你不会再有机会回家。不,你的亲人不会再来找到你,感谢你的奉献。不,你的未来不会有娶妻生子,安度晚年,只有无尽的战斗。最好的情况下,你可以不进铁柩,就迎来利落的死亡。
米迦勒叹了口气,这就是扬希要带着自己一起去的目的,好教官,坏教官。他当然会配合。
“那你呢?你打算怎么安抚这些因为我诚实地回答了问题,而陷入茫然的新兵?”
扬希展开双手。他的姿态改变了,面对米迦勒比划出——不,这不是他们的手语——米迦勒意识到,这只是一个优雅的行礼。
邀舞的姿势。
“……你要教他们跳舞。”
他没有想到,扬希和自己并不一样。扬希是会跳舞的。
“为什么?他们没有机会用上的。”米迦勒语气平平地问,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再去学习永远也不会用得上的技能。
阿密特曾编织出了在大海上才能使用的捕网,但米迦勒再也没有练习过那门手艺。
如果他们以后有了假期,也许会用得上的——扬希比划着,俏皮地眨了一下眼睛。
米迦勒慢慢停下脚步。
他意识到自己即将变成最后一个不会跳舞的人了,除非他现在就说点什么。
“那你也得教我,”他闷闷地要求自己的好友,“在新兵们看不到的地方。”还细致地记得自己的坏教官形象。
相比起那些年迈的血族,他依然稚嫩,但过多的战斗却让人提前苍老。童年对他来说恍若隔世。他又想起那个捕网,最后也不知道落在了哪里,和父亲、姐姐、家乡与大海的记忆一道褪色。
那的确是再也用不上的东西了,但它毕竟曾经存在。
他抬头看着扬希,思索着自己刚刚脱口而出的要求。也许他永远不会有机会参加什么舞会。但交谊舞——将会变成此时,此刻,此地,与扬希有关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