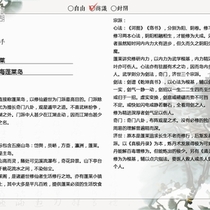警告:R15,我拉灯了。并且并不唯美,并不唯美,并不唯美。重要的事情说三次
如果有BUG就让它们随风而散吧(
感谢企划主提供的剧情!!
——————————————————————————————————————
热……
瑞坦将花洒水龙头掰向冷水方向,但它仍然毫不停息地喷出滚烫的水雾。尽管高温并不会像伤害别人那样伤害他,但皮肤上一阵阵灼热的刺痛并不好受。浴室里满是热腾腾的雾气,空气湿热难当。
这也真是太他妈热了。花洒只能喷洒出滚烫的热水,应该是热水器哪部分坏了。待会儿得叫管理处说一声。可还好是自己,瑞坦看着自己被烫得通红的皮肤闷闷地想。若这时在这里的是史利维斯特,这水温大概能烫破他的皮。
空气也湿重得无法呼吸。瑞坦打开浴室通风的窗户,然而一阵干燥而炽热的气浪突地拍到脸上。他顿时梦地脊背僵直。这干燥里带着浓烟,塑料烧焦的臭味和某种烤肉似的油脂香味混合在一起的热浪他再熟悉不过。
那是火灾时才会形成的热浪。
瑞坦下意识地向下望去,楼下早已是一片火海,看不清道路,在夜色里正格外贪婪地吞噬着一切。火星被热风卷着擦过他的发间。
这哪里是热水器坏了,那是铁质管道里的水早就被楼下的火焰烤得沸了!!
瑞坦猛地关上窗户。史利维斯特还在客厅里。他能在火还没烧过来时用恩典抑制住火灾灾情,凭两人身手逃出去并不难……
……黑羊重重地摔倒在地上。陶瓷浴缸已经缓慢地融化成一团通红透亮的粘稠胶状物,其中的管道早已化为一团铁水,被包裹其中。墙壁上那些斑斓的色彩缤纷的瓷砖仿佛冰淇淋在烈日下暴晒一般,纷纷融化,向下流淌金红色的水滴。浴室里不知何时水雾早就被蒸发得一干二净,但空气仍然几乎无法呼吸——不是因为潮湿,而是因为无法形容的干燥。
瑞坦这才模糊地意识到,这绝不是普通火灾的温度所能做到的程度。是他的恩典……自己那该诅咒千遍的恩典……浴缸,或是说那一团通红透亮的胶状物,被他的后背挤压出一个形状,又顺着他裸露的皮肤往下滚落。他艰难地喘着气,徒劳地用意识击打意识深处的某一点,试图让那一点滚烫重新变得安静而冰凉。
史利维斯特还在外面。瑞坦喉咙里发出近乎绝望的呜咽。
上帝保佑他逃出去……现在火还没有烧起来,凭他的身手他逃得出去的。
他一定要逃出去!!
只是一转念的功夫火焰便拔地而起,形成一道道绯红金灿的帷幕。浴室门早已高温碳化,一阵气浪便使它应声而碎。瑞坦恍惚间抬起头,在重重火舌后面,他似乎看到了搭档高大厚实的身影。尤其是当自己坐在地板上时,那个身影看起来更具压迫感了……
不对。那不是史利维斯特。那是史利维斯特,但是是他已经炭化的焦黑尸体……即使已经变为焦炭,那具躯体却仍然站立着。焦黑的手无惧火焰,穿过金红的帷幕伸向他,似是死神借着史利维斯特已经炭化的尸体踏焰而来,前来取走他的性命。
黑羊张开嘴却说不出话。他碧色的瞳孔瞪得极大,眼泪在眼眶里便已经蒸发。但当他看到伸向自己的焦黑双手时却如负重释似的,轻轻笑了起来。
“你是不甘心自己一个人死要带我走吗?还是不放心我?”他轻声问道,仿佛注视着恋人的面孔,“我早该死的。已经死了这么多不该死的人……这样最好。”
他轻松地投入了那具焦黑,但仍然高大的躯体的怀抱。
潮水涌没了他。
那股熟悉的,史利维斯特式的安定感迅速而温和地裹住了全身。死亡原来竟然是这么轻松,自在而舒适的一件事,就和史利维斯特本人带给他的安定感没有任何区别。瑞坦将头抵在对方颈弯里微微笑了。神对他可真是优待,就连这位死神身上也有史利维斯特的味道,闻起来像是苦涩的烟味与肥皂混合的味道……
“安静下来了……?”
瑞坦困惑地抬头。史利维斯特……活生生的史利维斯特正看着他。深色眼睛里有一丝困惑,但更多是担心。他强有力的脉搏顺着一侧紧贴脖颈皮肤的耳朵,顺着紧贴的胸口传来。鼓动的心脏上方是厚实肌肉,紧实但布满疤痕的皮肤。
这若是死神假扮的,可也太真实了。
瑞坦不确定地去摸搭档的脸颊,似乎触碰的是一个幻象……史利维斯特并没闪开,任由他来回摸索,用手确定一切。
“我……我看到你死了。”瑞坦最后说。他将脑袋抵回搭档的颈窝,裸露的身体紧紧靠着史利维斯特,仍然有些语无伦次,“我看到四周都是火焰,你被烧得漆黑,站在火焰后面。是我引起的,恩典……恩典又失控了……”
“火焰?”史利维斯特再度看向浴室。门已经没了——极速低温结晶化后,轻轻一碰就化为一堆亮闪闪的碎片。浴缸里小半缸水都已冻成一整块冰。毛巾架上覆盖着一层冰层,角落里挂着锯齿状的冰棱,亮黄和玫红瓷砖上结满冰霜。
“幸好你的恩典还只在浴室范围内。”史利维斯特扶起搭档。瑞坦显然也注意到了浴室内的情况,他呆站着,一时什么反应也没有。
“我明明……我还在窗口看到了楼下有火灾……”
“如果有火灾现在消防车早就到了。”史利维斯特看了仍然呆站着看着浴室内的瑞坦一眼,放开了他。“我去给你找件衣服。”
瑞坦打了个抖。
安定的洪流随着手离开身体的那一瞬间,干燥滚烫的热度裹着令人绝望的不安再度席卷了他,令人根本无法呼吸。金红的火焰又隐约浮现在地板和墙壁上。
他猛地抓住了史利维斯特的胳膊。
“不行……”
“瑞肯?”
“……闭嘴。还有你叫错了。”
瑞坦吻了上去。
起先这个吻无关情欲,充满了不安,乞求和不确定。然而当史利维斯特拉回瑞坦腰侧回应着加深这个吻时,零碎的触碰顿时化为疯狂的啃舐与吸吮。待瑞坦意识到时,他已经卷起搭档的背心,赤裸的胸腹彼此来回磨蹭。他一手钩着史利维斯特宽厚的背,一只手在结实的胸口侧腹来回游走。而史利维斯特则一边用力回吻着他,一边两手都绕过他的腰际,顺着脊椎揉捏着臀部两团肉。两人粗重的呼吸,唾液,汗水和身体都交织成一团。
这感觉实在是太他妈令人诡异的好了。史利维斯特猛地拽起瑞坦摔在地毯上,一面用缓慢得要人命的速度解开自己的皮带。被那样直白火辣的目光盯着,瑞坦顿时硬了。他伸直小腿,脚心压住史利维斯特的牛仔裤裆稍微用力地来回挤压,那里也鼓作一团,又硬又热,他毫不意外地得到一阵压抑的苦闷喘息。史利维斯特任他搓了一小段时间,突然抓住他的脚踝顺势向上摁住。
“待会的事情,你得付自己全责。”牧羊犬说。他喉咙嘶哑,视线滚烫得能烧出一个洞。他说着再度撕咬着亲吻那片嘴唇。
之后的事情瑞坦记得不是很清楚。他再醒来时已是凌晨,窗外一片漆黑。他隐约只能记起史利维斯特粗重的喘息,自己的尖叫,哭喊与恳求。他觉得自己像是被一万匹马狂奔着踩过去,喉咙嘶哑得说不出一个字,身上狼藉不堪。史利维斯特背对着他睡得正熟,看起来也没有好多少,他背后腰侧满是抓痕和瘀斑,闻起来有股淡淡的血腥气。
但是他从未感受过如此满足而安宁,平静得像是海中的一粒沙,夜空中的一颗星。之前的火焰,融化的浴室,烧焦的尸体都仿佛一场醒来便已开始遗忘的噩梦。
瑞坦动了一下,胳膊绕上史利维斯特的腰侧。史利维斯特正巧也转个身,刚好将他搂住。史利维斯特的心跳,体温,呼吸,气味,这些全都安抚着他,包裹着他。一切恐惧和绝望都被隔绝在外。
那就是噩梦。史利维斯特还活着。
他还活着。
瑞坦精疲力尽地埋进牧羊犬的怀抱,再度陷入沉睡。
人家已经二章了我还停留在第一章……而且这次仍然还没有谈上恋爱……!(摔 我这么努力工作能涨工资吗东家……!
标题其实没什么含义,就是说中秋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 写得仓促,如有BUG或OOC请用力敲打我!
强行把中秋前和中秋后要交待的事都塞在了一起。
一般人称其为……过渡段(
前接:http://elfartworld.com/works/76077/
关联:http://elfartworld.com/works/81837/
流水账,只求交待一下必须交待的情节,还有情报传递什么的OTL
———————————————————————————————————
柳云岸一身风尘策马回到镖局,已是太湖之行三日之后,再过几日便是中秋。今年的三伏天刚过不久,天气仍然酷热难当。可这看起来温文尔雅的文士仍然穿戴得整整齐齐,斗笠摘下,竟是一滴汗也看不到。他前门刚下马,二虎已经笑嘻嘻地迎了出来。
“柳先生您回来啦。”
二虎接过马缰,又有点好奇地偷偷打量着这个上元镖局里最难捉摸的人,“柳先生,东家和总镖头让您调查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柳云岸一副“这事也是你能问的?”的眼神瞟了二虎一眼,看得他脖子一缩。但他嘴角带笑,也没多生气,“正要和他们说。那两位现在在哪?”
“应该是在里屋吧。您也知道,东家大病初愈,总镖头又是个爱操心的,总怕他累着伤又复发,没事总爱关在里屋不出来……”
“先生您回来啦!我想吃糖糕!”
“先生我想要纸鹞!燕子那样的!”
一阵脆嫩的稚声突地穿过院门,打断了两人对话,一个约摸七八岁的孩童窜过来,紧紧抓着柳云岸衣摆不放。紧接着一个接着一个,全都粘了过来。柳云岸出门并不多,多数时候都窝在自己房里不知捉摸些什么。可每每出门总会带回些糖葫芦,糕点,纸鹞,木刀木枪之类的分给镖局里的孩子们。久而久之孩子们也都知道这个会说故事的先生出门回来会有好东西吃,有好东西玩,都纷纷粘着不放。柳云岸也不恼,变戏法似的,笑着从马鞍口袋里掏出一个又一个小玩意儿。孩子群里时不时爆发出一阵欢呼。
“丹梅。”
廊下不远处一直看着这里的女孩偏偏头,似乎不确定院门口的那人在叫自己。直到对方朝自己招手,她才缓缓过去。
柳云岸从袖口里摸出一对银簪,道声失礼便侧身插入她两侧的发髻团子。那银簪不大,只比少女手指长点,十分纤细。前头用银丝与细黄水晶珠子串成一簇簇小黄花模样,被银叶子隐隐约约地挡着,活生生一对银敲珠串的细小桂枝绕在发髻上。他又退了一步,似是观望了一阵才点头温言笑道,“我看着这对簪子就觉得十分适合丹梅,又十分适合这个时节。果然是没买错。你且看看喜不喜欢?”
少女面露惊喜之色,摸着头顶发簪便奔去内屋找镜子。柳云岸一身礼物都分发完了,这才整整衣衫,进了内院。
屋内确实只有裘鹤假扮的李铭与刑远二人。为了尽量不出岔子,只要在镖局内这一身装扮裘鹤从不卸下,行事作风也与真李铭毫无差别。柳云岸也按当年的称呼,唤他东家。只是刑远小心谨慎,平日里无事并不愿意让裘鹤随意外出。这可憋坏了恣意逍遥的唐家小少爷,柳云岸敲门进屋时还什么动静都没有,待两人见到是也知道李铭真实身份的柳先生,裘鹤又恢复了那股百无聊赖快要打滚的模样。
“你就让我出去嘛。就一天!我都快被憋死了……”
另一个木头人冷冷的看了他一眼,并不说话。
柳云岸一看便知刚才又在争论什么……或是说,单方面争论什么。他也禁不住弯起嘴角,露出人畜无害的笑容,“关了这么多天,确实该出去散下心。不过装成李铭出去还是有点风险。不如就委屈小少爷,扮成女装吧?”
“女装……”李铭外表的裘鹤竟然没有反对,似是仔细思考了起来。柳云岸趁热打铁,笑得有如春风拂面,“就说是总镖头的远房表妹,这几日来临安游玩,便住在镖局里的。”
这一次木头人冰冷的视线落在了他的身上,“镇远镖局的事怎么样了?”
说起正事柳云岸收了笑容,撩起衣摆坐定,趁着端茶的功夫定下心神暗地里运起心法。他本就功底深厚耳聪目明。这时下里顿时灵台澄亮,屋里屋外有多少活物分别是些什么,处于什么方位都听得一清二楚。待确定没人偷听了,这才点头道,“我先从我做的结论开始说起吧。镇远镖局的失镖案子,应与我们无关。”
李铭正敲着核桃,听他这么一说被勾起了兴趣,好奇地探出身子,“这怎么说?”
“镖局保镖,一般有三知,这是既定的行规。三知,知镖,知托镖人,知收镖人。少了这其中一样,镖银和护镖风险都必然成倍增加。这是镖局行当的默认规则。而有两样不知的,多半是生死镖,也就是十有八九会出事的镖。”
“你是说……”李铭的眼睛闪亮亮的,“镇远镖局这趟镖,是生死镖?”
“嗯。”柳云岸端茶又喝了几口。在外奔波了几天,又是顶着午后烈日回镖局,他是真有点渴了,“我打听过了,镇远镖局这镖只知道是要送往清河郡王府的,押送的是一个雕花木盒子。四寸见宽,约八寸长,盒内有什么全然不清楚。拖镖人不肯告知身份,只说事成有一千五百两白银。”
“一千五百两……”刑远那一向没什么表情的脸上也出现了一丝波动,“这一个雕花木匣子,竟值得三万两白银?!”
“而且还不知道盒子里到底是什么物事,也不知托镖人身份。”柳云岸放下茶盏,端正脸上浮出一丝冷笑,“两不知的三万两生死镖。这不出事反倒要算是稀奇事了。”
他顿了顿想起什么道,“我在路上也遇到了银鱼卫。官场又向来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时只怕皇城司也在关注此事了。”
刑远沉默着,似乎在想什么。李铭偏着头,仍有疑问,“这也不能说明和咱们失镖的那事无关?”
“嗯,确实如此。”柳云岸此时笑得颇轻松自在,“但也没法证明有关。这就是关键。”
“我倒是能猜出先生几分意思,”刑远低声道,“两次失镖,托镖人,镖内物事,收镖人均不相同,更莫说受镖镖局不同,劫镖人也不一定相同。这要说有关,凭现在的信息也太少了些。”
李铭点点头,砸碎一个核桃,“那这桩事就算是解决咯。暂且放到一边。”他说着把碎壳连带果仁都推到一边,又拿过一个新的核桃。三人又据最近临安动态交换了一些情报,这才各自告辞歇息不提。
过了中秋,原本大家都盼着能休整个几天。这时原本各处也都在忙着家宴团员,本就没什么生意上门。镖局里更是各个都悠闲自在,懒洋洋的。谁知没几天便来了位带着小孩的男子投贴拜门。当家的带着总镖头与柳云岸迎了客人,又聊了好些时候这才送走客人。只是那个孩子却留下了。
送走那拜贴的刘平,柳云岸冷眼看着那孩子跟着打杂仆役走远,这才拦住李铭与刑远二人,低声道,“东家,总镖头,务必屋内一叙。”
李铭与刑远对视一眼。这先生平日里温文尔雅,少有如此严肃之时。顿时二人也紧起十二分神色,三人径自进了李铭日常起居的后院主屋。这里一面墙外是刑远的住处,另一面墙外则已贴着空无一人的西厢房,少有人来。
“我便开门见山了。”柳云岸确认四下里无人靠近,这才视线落在已落坐的两人身上,“二位对先前这事,如何看待?”
刑远首先沉吟道,“我看过那字条,确是李铭当年笔迹。”
柳云岸微微一笑,这笑得几乎可以称得上微微一哂了,“只要稍许掌握些诀窍字条便可以作假。莫说他人,便是柳某自己有心仿字也能仿个七八分。”
李铭在椅子上盘着腿。私下里他不用那么绷着,多少也就自在了些。这动作多少给他增添了点孩子气,“先生觉得那刘平有假?”
“不好说……”柳云岸下意识地打开折扇又闭上,这多是他思虑时的动作,“我刚拿言语刺他,那反应倒是……若真是傲气,反倒简单。只不过又不像是能做捕头的性格。若是装的……那倒要更仔细着他。”他停顿了一下,又微微摇头,“现下丢的镖、东家的‘事’、还全都云里雾里的一团,本就怕横生枝节的当口,人员变动最是忌讳。更不用说是这样证明不了路子的来人。我之前并不想收这个孩子,便是此意。”
“他毕竟只是孩子。若是字条是真的,怎能让李铭背了诚信。”
邢远仍是面色冰冷,惜言如金。此时若外人见了,只怕都以为他对柳云岸拒绝孩子这件事多少心怀怨恨。但镖局里熟识的人都知,他一向如此面冷心热,言语间只是叙述,并无不满。
柳云岸笑了一声,眼角却不带丝毫温度。这模样无端给他平添三分寒意。“我知晓总镖头的意思。一个孩子能做的毕竟有限,翻不出多大浪花。可孩子能做的事情,也不比实际上少多少。”
他折了折了手中扇,又道,“那孩子拿着李铭的手书,若是真的,保不准他手上还有什么能让东家露馅的东西。若是假的,那他的来历目的于我们而言更是两眼一抹黑。届时若他有些什么动作,我们再想补救可就晚了。”
“先生意思,是还要把这孩子送出去?”
“那也不用。”他舒了口气,那点寒芒便转瞬即逝,复又平和。“我现下里仔细想想,柳某在厅上虽是试探,但其实也是冒失了。总镖头的善心之举,反而弥补了我的过失……这以退为进,说不准倒是好事。”
李铭……裘鹤与邢远相视一眼,都猜不出面前这人到底在沉吟些什么。但柳云岸只是打开折扇复又合上,似乎没有解释的打算。
“为什么?”裘鹤终于耐不住好奇问道,他虽然少经磨练,心思单纯,可人却聪明。话一出口他也便意识到问题所在。若手书是真的,镖局力拒孩子于门外,与往日李铭作风并不相符,更说不通。若手书是假的,李铭又怎能分辨不出?若有心者顺着这条“不正常”的线索继续追查,只怕多少会意识到镖局有什么变故。柳云岸见他自己已经明了,朝他笑笑,便转了话头。
“事到如今,如果这两人没有什么计谋当然是最好不过。但如果在谋筹什么,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总镖头答应把孩子接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想好了。东家——”柳云岸转头朝李铭模样的裘鹤道,“你须尽量避开和那孩子同处一室的机会——尤其是要避开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他盯着主位上的小少爷,眼里一点精光闪现,全然不似平日里春风拂面,“小孩子倒不怕他对东家有什么身体上的不利,但是最得防着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揭穿你。这于镖局,于现在的东家,都是最大不利。”
“这我有分寸,不消你们嘱咐。”李铭笑嘻嘻地靠回椅子,手里还剥着个核桃扔给柳云岸,全然没有个东家样子。可当年李铭本人也便是这般十分没架子的模样,谁也没说不好。
邢远也道,“那孩子的房间我已经派人安排好了,远离前厅和主屋。李铭平日里和我在一起,不会有多少接触的机会。你用不着担心。”
“嗯……”柳云岸仍有思虑,“至于孩子本人,让大人监视反而不妥。好在镖局里收留的孩童甚多,也不打眼,我会让五儿他们留神,这倒不是最打紧的。”说罢他又转向另一边的邢远,速度之快使宽大白衣旋出一个圈儿,“总镖头,人我们虽已经接下,但来路我们还是一定要搞清楚。那刘平的家底,来路,和那孩子关系如何,都得查个水落石出。这且不说,那孩子的来历,其父母和东家当年是否有过交情,最好也得弄得清楚明白。其实这个才是最主要的,知晓了这个主动权就在我们手里。”
“刘平和孩子的底细我已经派人去查了,不日应该就有回报。”邢远靠着椅子,永远是那副雷打不动的冷面阎王模样,“但那孩子父母和李铭的交情,只怕难。”
“柳某清楚。”柳云岸点头道,“若查到了,这当然是最有益的。可这只怕也是最难查证,也最不宜去查证。”他冷冷地加强了‘最不宜’的语气,言语间似乎又在盘算什么,“所以我们只能放到最后,实在要查,也只能暗地里旁敲侧击,决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标题应该很能说明问题了(我会说我自己写的时候就想了很多吗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本来分镜都打好了可是最近实在没时间……OTL
仍然是小学生写写……好想写出欧美风啊——————(哭号
————————————————————————————————————————
瑞坦·林兹懒洋洋的,无精打采地看着防爆玻璃对面的男人。
这是间狭小的纯白色房间,四壁光滑得没有一丝接缝。只有椅子面对的那一面墙有一半镶嵌着玻璃,装着通讯设备,天花板很高,也许有两三层楼的高度。瑞坦很清楚,在他看不到的天花板上方布满了催眠瓦斯喷口。这是专门针对高热高温系恩典设计的探监室,经过特殊处理的墙壁与地板能经受2000°以上的高温。
但是如果是用绝对零度来冰冻呢……?或是用超过2000°的高温……
瑞坦有些心痒。但他仍然老老实实地坐在椅子上。玻璃对面椅子里同样也有个人,可能比他自己年纪大一点,一看就是那种相处起来味同嚼蜡的男人。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的,看到他的第一眼瑞坦就能确定,他是个牧羊犬。这人皮夹克下的背心被肌肉绷出一条条细密的褶皱,瑞坦很容易就能想象他揍人的模样——迅速,有效,直击痛处。他块头很大,脸上的伤疤证明他经历过的远不止街头斗殴。况且这人坐在椅子上的姿势看似自然却毫无破绽,绝非黑手党或街头混混所有。
瑞坦挑了挑眉。
“好了,那么,一个浑身伤疤的前军人牧羊犬——想必你也是个公安了——来看我这个素不相识的关在监狱里的黑羊,是有什么政府上的事情了?”
“我前天已经调出维稳科了。确实有政府上的安排。”那人低头确认了一下手中的资料。档案里即使照片里的人头发几乎已经剃光了,但是那双苍蓝色如火焰一般燃烧着的眼睛一模一样。
“瑞坦 林兹,政府命令我来接你出狱。从接到文件的那一刻起,你将成为由我负责的黑羊。”
瑞坦的眼睛危险的眯了起来,他弓着身子贴近玻璃,“那么,意思是我们将组成搭档?”
“是的。”史利维斯特没什么表情。他合上资料夹,“你收拾一下,出狱后我们将去人事处报道,你和我的档案都已转入神慈科。”
“……你是得罪了政府什么人吧。或是不经意间抓住了他们什么把柄,我猜?”瑞坦咧开嘴,猛然往回靠,背抵住椅子坚硬的线条。他冷笑一声道,“很显然,你并不清楚你自己面临的是怎样的结局。”他站起来,将双手贴在两人之间玻璃上。
须臾之间5CM厚的防爆玻璃以他手掌为中心迅速变成透亮的金红液体,顺着双手往下淌。熔浆滴在耐高温陶瓷地板上,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凝结,在他脚前形成诡异的通红的玻璃熔岩。蜂鸣警报顿时在他们头顶作响。但随着瑞坦的手离开玻璃,警报顿时解除。然而即使如此,两人之间也多出了足有一人宽的空洞。
而这全部发生的时间,连三秒都没超过。
瑞坦身后的门轰然撞开,一队荷枪弹实的全武装狱警冲了进来,在他身后形成半包围之势。瑞坦只是站在那里,似乎这发生的一切都在另外一个世界。他带着手铐的手撑在半截陶瓷墙上,身体向前倾出,脸几乎要贴上史利维斯特的脸。
“你要知道,”他轻声细语,可看起来既疯狂又绝望。“对我来说,让别人‘人间蒸发’可不是个修辞手法。”
“是吗。”
史利维斯特只是从屁股口袋里摸出一包已经被坐扁的烟盒。他抖出一根烟,又在掏什么东西,可半天也没摸出什么来。
这个反应大大出乎瑞坦意料,他有点发愣。但史利维斯特已经捏着烟凑过来。
“忘带打火机了。”他解释道,表情仿佛之前在听一个小孩宣称自己打倒了黑魔王,而那个黑魔王实际只是挂在后院正在晾晒的一根拖把。“既然你这么厉害,帮我点个烟?”
“你他娘的脑子里全都是一团刚被操完的白屎吗?!”瑞坦站起来猛地吼到,若不是手被铐着他现在应该已经往那张脸上狠狠揍了一拳。“给我配的两个牧羊犬全他妈死了!一个碎成玻璃渣,另一个只有一……”
瑞坦下面的话没能说出来。他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视野就突然横转了过来。半个身体都被压在了会客平台上,不能动弹丝毫。脸被摁着挤压着冰冷的平台防高温陶瓷。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意识到,刚刚那“砰”地一声,是他脑袋撞上陶瓷的声音。
“再问你一次。”
史利维斯特的声音在他耳边浮现。气息扫过耳廓时瑞坦几乎无法忍住一阵鸡皮疙瘩。那根烟重新出现在他眼前,贴的如此之近以至于眼睛无法好好对焦。
“能帮个忙吗?”
如果说之前瑞坦还不明白政府为什么铁了心要给他配个牧羊犬,那现在他也完全,彻底的明白了。这不仅仅是力量上的纯粹压制。更有某种……某种他无法言明的,陌生的滔天洪水从那个牧羊犬手上的皮肤灌进他的身体,不容丝毫抵抗,迅速而汹涌地吞没了一切。恩典,愤怒,绝望,战斗……瑞坦毫不怀疑,即使眼前这个人现在要掐死他,他也无法做出一丝反抗。恩典还在那里,他知道。但是那也被某种恒定的洪水包裹着,仿佛一个不防水的打火机被带到了水中,无论怎么点火都无动于衷。现在的瑞坦,不要说点燃一根烟,就是让自己的体表温度再提高一度,也只能靠摩擦生热或燃烧脂肪。
他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瑞坦试着挣扎,或者说,他试着让自己挣扎一下,以示抗议——但可怜的,即使连挣扎所需的愤怒和懊恼他也所剩无几。
一切都纹丝不动。史利维斯特慢吞吞的,终于从夹克另一边口袋里摸出一个打火机点燃了手里的烟。
“看来你也没那么厉害。”他喷了口烟,这才终于放开瑞坦,“没事了的话,去清理东西。我们下午去人事处。”
瑞坦跌进椅子里,勉力呼吸。史利维斯特的手掌离开瑞坦时那股洪水也随之退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恩典清晰地浮现在他的意识里,还有愤怒,绝望,恐惧……一系列的负面情绪。
但不管怎样,总是他熟悉的那些。他恐惧的那些。
“我还有一个问题。”瑞坦终于勉强调整好呼吸,“你叫什么?”
“马克。”对面的男人回答道。
“史利维斯特·马克。”
用了day30的题目…………虽然并不是相拥而眠,不过勉强也算吧!
我已经不会写文OTL 总之 随意看看吧…………(鸵鸟钻地
------------------------------------------------------------------------------
瑞坦站在门口,有点发呆。这是他出狱的第二天,从人事处回来,加入神慈科的第一天,大概……也算是搬进新公寓,和新搭档一起生活的第零天吧。
“今天有点晚,需要什么明天再出去买吧。”史利维斯特道,随手将他的行李扔进地板某个角落。他脱下外套窝进沙发,脚搁在茶几上的熟练程度仿佛已经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似的,哪怕昨天他才第一次领到这间公寓的钥匙。瑞坦顿了会儿,进门带上门。
这应该是个很久没人用过的公寓,没怎么打扫过,有种多年没有通风的陈腐味道。门窗和必要家具都换了新的,面积也不算太大,但两人住绰绰有余。客厅面向街道的那边开了很大的玻璃窗,对面是另一排公寓,夜色里零星地亮着几扇窗户。
瑞坦拎开自己的行李,将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胡乱塞进卧室里的巨大的雕花衣柜。这衣柜显然是上个房客,或上上个房客留下来的了。木头被摸得油光发黑,在空荡荡的没有任何装饰的房间里,这个门页上雕着细致奢华的卷叶草涡纹,螺细镶嵌着圣母像和玫瑰的衣柜显得如此格格不入。衣柜里还有另外几件样式十分简单的衣服孤零零地挂在衣柜另一边,想必就是他的新搭档全年的装备了。他把自己的衣服也挂上去,两人所有的衣服加起来竟然还不能塞满这个衣柜的一半。
另一个房间是空的,没有家具,没有装饰。只有各式各样的枪支弹药,几乎堆满半个房间。从最小巧纤细的勃朗宁,到几乎有他半人高的狙击枪,各种口径的弹夹堆在唯一一张桌子上,玲琅满目,应有尽有。
瑞坦回头瞪着史利维斯特。
“神慈科提供的。”后者只是无辜地耸耸肩,叼着烟打开一瓶啤酒,“你可以选个自己合适的。”
“你不能把这么多弹药放在离我这么近的地方。”瑞坦一把撑在茶几上,越过茶几瞪着他,“我的恩典万一暴走,这里的弹药量你有几百条命都不够。”
“有我在你就不会暴走。”史利维斯特摸过钥匙链上的开瓶器又开了一瓶啤酒递给他,语气仿佛在说今天不会下雨。“帮个忙?”
瑞坦没好气地抓过那瓶啤酒,不出几秒钟啤酒瓶上就附上一层薄薄的白霜,冒出水珠。他看了一眼新搭档,绕过茶几也把自己扔进沙发里。
“自己去用冰箱。”他说着自己喝掉了那瓶冰过的啤酒。
两人默默无言喝掉了桌上一打啤酒,外加抽光了史利维斯特身上最后一包香烟。他抽的 十分苦,瑞坦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习惯那个味道。屋子里乌烟瘴气,瑞坦不得不打开客厅门窗透透气。打开面向街道的那扇窗户,他看到对面正对自己这扇窗户的公寓里,一点红光正对着自己。
他不用想也知道自己额头上有一颗红点。不论是在监狱里,或是更早的时候在岛外执行任务,他对这种既是监视又是威慑的布置已经再熟悉不过。他探身向两边望了望,窗户左上侧广告牌下正好能看到一个隐隐约约的监视器,摄像头正对着探出身的瑞坦,仿佛某种无机质的生物眼睛窥视着他。
瑞坦笑了笑,他没有生气或是愤慨。倒不如说,感到了一阵安心。这种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无法控制的能力,确实不应该给一个人类使用。有谁来夺走它才是正常的。
“你在做什么?”
瑞坦回头,史利维斯特拿着换洗衣物正看着他,听起来似乎不太高兴,又有点防备。屋子里没开灯,只有窗外街道上的灯光映在屋子里。黑暗里他若隐若现的,瑞坦却似乎能看清他隐隐皱起的眉头。
“开窗透气。”瑞坦拍拍身上蹭的灰尘,但似乎毫无用处。窗台厚厚一层灰,被他这么一探身,活活留下一道擦出来的白印子。他索性脱了衣服丢进洗衣机,“你要先洗澡吗?”
史利维斯特嗯了一声,“你换的衣服呢?”
“没了。就这一件。”瑞坦耸耸肩,“反正我可以控制身边的温度环境。衣服多少没什么意义。”
史利维斯特看了看他,丢来一件自己的衬衫。
“先穿着。”
瑞坦对自己的体格有信心,但是这件衬衫自己穿起来还是松垮垮的,为了方便做事他不得不把袖子卷起来。洗衣机虽然能用,但是没有洗衣粉,要换洗的衣服只能先放着。厨房里有灶台,但是没有锅碗瓢盆,也没有柴米油盐。不过想想日后在公寓里开伙的可能性也并不大,他也就默默放弃了。水池摆着两个漱口杯子,牙膏牙刷,还有两个电动剃须刀。这些都是他和史利维斯特自己行李里带过来的。看起来倒是有些生活气息。
抹布,清洁剂,扫帚和拖把……这些显然是这间屋子现在最需要的。手机,电脑,平板……这些也都算是现代生活里的必须品。也许还需要一个书桌和书柜。瑞坦看着行李里剩下的书本盘算着。还有家庭工具箱和医疗箱,在完成任务回来时这些都是格外需要的物品……
“该你洗了。”肩膀上突如其来的触感激得瑞坦一阵激灵,头脑里的购物清单随之烟消云散。他猛地挥开史利维斯特的手,暗自压下身体的轻微颤抖。反应之大让年长的男性一脸莫名其妙。
“你对我的恩典压制太明显了。”瑞坦用力梗着脖子,似乎有点勉强地解释道,“以后没事的话还是别碰我。”
史利维斯特一脸莫名其妙,但他还是点点头答应了一声。瑞坦勉强维持着正常的步伐逃进了浴室。
太可怕了。或是太幸运了。有时候这两个词说的是一个意思。瑞坦隔着浴室门好一会儿,才勉强让自己找回寻常。虽然已经是第三次被完全抑止恩典了,但他仍然无法习惯。被接触时如泉水一般汹涌涌入身体的安定感实在是太过于舒适,让人根本无从想起恩典如何使用。舒适得让人头皮发麻,舒适得让人无端觉得害怕。他害怕……每次被这个牧羊犬碰触时——不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瑞坦都能感到某种他从未接触过的东西,像突如其来的海浪一般迅速地淹没他整个身心。迅速,干脆,不及掩耳,还未反应过来他已经发现自己的恩典消失无踪,随之而来的是无法撼动的充实与平静如海浪般充盈着身心。而从没有哪个牧羊犬对他的安抚和压制如此强大,就连每周教会发给的药物都完全无法与其相提并论。
他从未遇到过这种……不可违逆,无法抗拒的安抚和压制。它太强大,强大到每次瑞坦被触碰都会无法控制地轻微颤怵。它也太舒适,舒适到瑞坦根本无从抗拒。
但更为可怕的是,瑞坦知道自己渴求着它。像沙漠里因缺水而濒死的人渴求着泉水一样渴求着,像火焰中因高温而快被烧死的人渴求冰凉的雨水一样渴求着,像所有那些快溺死而紧抓着一根芦苇不放的人那样渴求它。
像一切坠入深渊但仍然渴求着一丝救赎的人那样渴望它。
老实说,住在哪里都不会比在监狱里待着更糟。因此即便这个公寓有着粉红色的沾满灰尘的窗帘,俗不可耐的玻璃防水晶吊灯,浴室瓷砖是柠檬黄与艳桃红组成的马赛克墙壁,而卧室床单是亮蓝色的,枕头上印着廉价的粉红色花朵,瑞坦也没有觉得让人无法接受到不能忍受的地步。因为不论怎么说,这里毕竟比监狱还是好多了。浴缸自带淋浴间,有全自动马桶,床垫也十分松软,还有足足六个枕头。
但是当瑞坦意识到这个公寓里有且只有一张床时,他还是沉默了。
瑞坦抬头看着床另一边的史利维斯特,“我不想和男人睡一张床。”
史利维斯特扫了他一眼。“……难不成你第一次和男人睡?”
“难不成你是那种能第一次见面就和男人一起睡的人?”瑞坦有点儿咬牙切齿地回答。他现在该死的还有点儿心猿意马。史利维斯特刚洗完澡,只穿了条睡裤,剪得短短的头发湿漉漉的,皮肤随着肌肉滚动,散发着水汽和热意。见鬼的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四十多岁的人。
“我有防止你暴走,逃跑和监视的职责。这是睡觉时最简单方便履行职责的方法。”史利维斯特丝毫没注意瑞坦的眼神。他拉开被子,看着床单摇了摇头,“这糟糕的品味。”
瑞坦下意识地咬紧牙关。他想离开,看本书直到天亮,或是干些其他什么。什么都好,只要熬到天亮就行。睡觉时因为噩梦引起火灾的事件不是第一次了。当然,在史利维斯特身边睡绝不会能力失控。但是睡在一张床上不可避免的接触……
也许是瑞坦迟迟没有动作。史利维斯特本来闭上的眼睛又有些迷糊地睁开,“睡吧。明天还得出去买东西。至少这个床单和枕头就得换一换。”他模模糊糊地瞧着他说道,又打了个呵欠补上一句,“我不会对你有动作的。”
“你应该害怕的是我会对你有所动作。”
瑞坦嘴硬地回了一句,但在睡意和身体本能的双重攻击下他还是爬上床的另一边。床并不算小,但两人都算是大体格,睡在一张床上竟然没什么多余空间。瑞坦磨磨蹭蹭地钻进被子里,两人背贴背的那一瞬间某种庞然的安宁与充实猛地吞噬了他。
他什么也来不及想,就这样滑入了一片黑暗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