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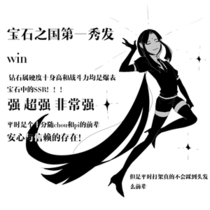

【我族何以为王 而我将何以为王】
【BGM:《深海の孤独》】
所有的目光都投向自己,半卫兵如同身处冰海,面上仍不动声色。
到弟弟被大家盯着,万华镜向首席神代行海兔投去求助的目光。海兔的难色一闪而过,向众王族爵族颔首而后道:“本神代行知道各位在疑虑什么,不如先让王子说句话吧。”说着极光般的尾鳍向半卫兵的方向拍了一下水。半卫兵上前,向众亲族颔首:“我向海神发誓,灵魂石胎失踪一事与我无关。”
“既然王子这么说了,应该不怕任何考验才是?”
“是的,神代行。”
“很好。”海兔拍了拍手:“那我去准备准备,让王子与魈族首领对质。”
下面的窃窃私语虽然并未消失,至少对于半卫兵的怀疑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了。海兔毕竟是首席神代行,她能让半卫兵与玛屠直接对质,想必是有十足的把握。
否则,谁都知道后果会严重到什么程度。
交好的数千年中,魈族的一些风俗人鱼已经了解到了。比如孩子平安度过了极易夭折的幼年之后,就要带他去生命之塔周围,献上贡品,感谢生命之塔赐予他完整的生命。而首领的孩子,是可以到非常近的地方去的。玛屠,必然近距离看到过灵魂石胎。
“玛屠首领,你见过灵魂石胎吧?”
“见过啊。”
“我们的王子,之前有半年在海渊附近训练,说不准见过偷窃石胎的盗贼。”
“哇!好好好!让我去问问他!”
“玛屠首领,请问你相信海神吗?”
“海神?”玛屠没怎么理解,柏律在一旁解释:“那是我们的母神在人鱼族那边的叫法。”“哦,当然相信!”
“我是人鱼中能够直接与海神对话的存在,信仰海神的你,能相信我吗?”年长的女人鱼眯着眼对初涉人间的魈族少女微笑,后者还花了一会儿思考:“你在人鱼当中,就是我们那边的大巫师吗?”
“啊哈哈哈……是的。这样你能相信我吗?”海兔身处神职,高华中却满溢着妩媚。
“我信!”
“那么……”
海神殿内,海兔在众人的注视下,将一面在深海热泉上烫过的海纹石板放进了半卫兵摊开的手心,低体温的人鱼被烫得一皱眉。海兔转向玛屠:“玛屠首领,请你想着灵魂石胎的样子,把手覆在石板背面。”玛屠闭上眼睛,把手放在了半卫兵的手上。
“石板会在五十岚殿下的记忆里寻找相似的东西,请耐心等待。”
半卫兵此刻脑海一片空白,心下暗涌着混乱。有陌生的意识在脑海左冲右突,疼痛潜伏在头颅里不时刺他一刺,顺着神经向每一个末梢蔓延,严重时全身血管都像被从身体里抽出来。唯一能庆幸的是幼年时即便顽劣如自己,也并没有真的潜下过海渊,记忆里当然没有海渊中的一切。
虽然没有潜下去不代表他没有试过。在自己还只有现在一半长的时候,半卫兵曾经带着华露兹向海渊下潜。只是没潜下多少,华露兹就全身作痛问他能不能不去了,半卫兵一个人也不敢往那么黑的地方去,那次就干脆作罢了。
其实那时候他就该想到的。
华露兹无法承受的海渊水压对他没有丝毫影响,那正是他身为王族的证明、荣耀、和原因。
最初的王族是没有名字的,他们分散在各个族类里,毫不出众。但是历经天灾巨变时,正是这些毫不出众的人鱼挺身而出,带着斗族之勇、智族之谋、匠族之巧、猎族之灵思、华族之婉转、牧族垦族之稳重坚韧,前往绝灭之境。火山、深渊、夺去呼吸的水域、冰封灵魂的冻海,除了他们其他族群无人能够承受。他们依照礼族的引导,牺牲无数,遏制了浩劫蔓延,结束了黑暗时代,带领人鱼从死地中挣扎出来。当一切平息之后,终于建立起国家的人鱼们将那一部分体质强大到可逆天命而为的人鱼定义为王族。
所谓王族——就是在乱世中迎着命运而上,去往死境,为族群的生存牺牲的一族。
这一点王族并不会在内部强调,于是许多王族和爵族对其是并不清楚的。据说在自己幼年父亲曾经告诉过他和万华镜,然而那时他恐怕并没认真听。
石板冷却,被抽取记忆的不适感也褪去,海兔靠过来宣布仪式结束:“玛屠首领,已经结束了。”“啊?这就结束了?”玛屠瞪大眼睛:“什么都没有啊。”海兔轻轻将一只手搭在了玛屠的肩上:“那就是连王子也没有遇见过偷窃灵魂石胎的盗贼了。”见这个急脾气的姑娘一脸苦大仇深、裙膜有展开的迹象,她笑着安慰:“虽说王子爱莫能助,人鱼还会想别的办法帮忙的。”柏律也在一边偷偷戳了他的首领一下,玛屠嘟了半天嘴,终究没有放任自己的负面情绪爆发出来,点点头道了谢。
“玛屠首领请不要太担心,此事人鱼将不遗余力。”半卫兵苍白着脸向玛屠做出保证,现在他庆幸的是这个场面不需要他硬挤出一个微笑。虽然并不能保证真的就能找到灵魂石胎,场面话总是要说的。
“嗯。”玛屠点头答应,然而眉还是皱着,目光也朝下,嘟着嘴手攥着裙膜的的边缘。注意到面前这个异族少女什么情绪都摆在脸上,半卫兵反而有点想笑了。
那什么都不掩饰,坦荡到放肆的姿态,好怀念。





【掠夺者偶遇的是天使的话】
【BGM:《书道家の成长》】
黑天鹅的船队已经开到了希琴附近。
在夏季来到凉爽的北回归线以北,基尔站在船头,爽风从呼吸间穿过,很是舒服。边上并排航行的无丝茧的甲板上突然传来不那么舒服的咳嗽声,瞥过去,是霍克廓尔披着羽绒披风从舱楼里走出来。发现了他的目光,忍着咳嗽向他点头致意。
“怎么?身体吃不消了?”基尔咧开嘴角露出一排尖牙,那笑容颇带点孩子气的得意,全不是这把年纪的人该有的样子。
“托您的福。”霍克廓尔脸色苍白,咳了好一会儿才答了一句。
“抱歉啦~我以为不会给你造成那么严重的影响。”
“小伤,不碍事。”主人话音未落,使魔却老远地飞过来用翅膀啪啪啪地拍不死鸟之子的脸。基尔被糊了个措手不及,却没法对这小蛾子发火,甚至觉得好玩,绕着舱楼开始跑:“你这小畜生,你主人还没说什么呢,你倒介意?”
“思密达!回来!”霍克廓尔隔空叫它一声,思密达又扑了几下才回到他身边。
其实基尔还是有点心虚的,他听说水银刺不会对受刺人造成伤害才决定动用,然而……这好像和说好的不一样。他没想让霍克廓尔受到别的什么影响,只不过要一个能自己攥在手里的保障,哪想到会有这一出,然而这时道歉似乎也没用了,只有为刚才那点得意懊悔的份儿了。
霍克廓尔察觉了什么,一股笑意冲上来,气喘得太急却把好不容易压回去的咳嗽再次引爆了,结果是不死鸟之子脸上更挂不住了:“哎——你行不行啊?!”
不死鸟号上就见咳得弯下腰去、半个人都埋在船栏下面的霍克廓尔伸了一只手上来,做了一个一切正常的手势。
费莱茵刚刚睁开眼睛就被甲板上兴奋的尖叫声震得清醒过来,在他穿衣服的当儿里尖叫已经化作整个船队的嘈杂。
“看!那儿!白鲸啊!”
“哦哦哦!是白鲸!”
“好乖乖!这么大一群!”
七月正是白鲸群迁徙到这里的时节,白鲸群与寻找人鱼的海盗们不期而遇。
白鲸欢快地在海水中畅游跳跃,穿行于船队之中,呼吸时吹起小小的喷泉,黑天鹅号上的小银铃就一阵花枝乱颤地脆笑。连那些男水手也此起彼伏地吹起口哨模仿鲸鸣,惹起水中鲸群的热情回应。莱莉也不顾被侍女硬穿了裙子,爬上栏杆学着男水手的样子吹口哨,由女水手们拉着裙角免得她掉下去。这边男水手们还在指导她怎么吹得像,背后就响起了费莱茵的咆哮:“莱莉!!”
“哎!老头快来!有白鲸啊!”
“啊?啊、白鲸?白鲸啊……”不记得女儿上一次这么开心地叫他是什么时候,一时略怔的费莱茵也顾不上着急,面儿上板着脸心里愣着神儿凑了过去。
“你看!”
“哇~白鲸啊~”
“对啊!好可爱!”
“对对对!白鲸特别可爱!”
其他的海盗船也看到了白鲸,惊讶之余满是兴奋:
“哟!这些家伙可真好看!”
“嘿嘿嘿……它们不光好看,还浑身是金子。”
“是啊,陆地上的人买鲸油,出手可阔绰了!”
“鲸肉也是海上难得的美味不是吗?”
“还有喜欢收藏动物标本的,一头整的价格怎么也不会低到哪去。”
“啧啧啧……好家伙!这么多,咱们弄两个?”
黑天鹅的公主也有了自己中意的一只。
“老头我要白鲸做宠物!”
“好!莱莉你要哪一个?”
“我要那只小的!冲我笑的那个!”
“汉森——组织一下,去把那只围过来!”
“是的船长!”
水手汉森正招呼人手准备,黑天鹅上空突然有强光炸裂,一时甲板上的人都被夺去了视野,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炸了锅。
费莱茵本能地抱住了女儿,眼前被晃得一片昏黑仍在调度:“冷静!警戒!就在原地别动!”
尖叫和嘈杂在三秒内结束,接着就听见咳嗽声断断续续从上空靠近了甲板。像是在变声期的少年问道:“先生你行不行啊?”好不容易平复气息的霍克廓尔为难地笑笑:“不行也得行啊。”
霍克廓尔清清嗓子,在掌心展开一个小小的光环,接着每一艘船的上空都浮现了相似的光环。有些沙哑、平和而轻的声音被传达到整个船队:
“我霍克廓尔,作为此次行动的魔法和情报支援,从未过多干涉船队成员的任何行动。但是今天,我在此与各位约定,不、我给出的不是约定,而是命令——任何人,不能对白鲸出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