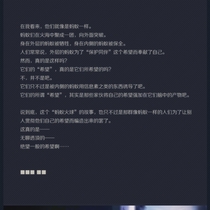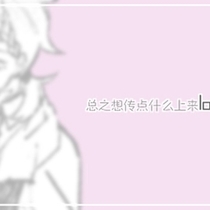字数3006
能够与人普通地对话,其实也算是才能的一种。
至少对于一之濑悠来说是这样的。自己并没有别人口中的富家子弟的傲慢,也不是没有对话交流的意愿,只是话语在嘴边会凝窒,在出口之前变成液体,重新被咽了回去。比如说,像是帮人捡起东西这种小事,在接收到来自对方的道谢后,除了“不用谢”之外,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但是如果换做他人,或许可以作为进一步成为朋友的契机。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身处青春期的男生会主动去和女孩子创造说话的机会了。
——一之濑同学,要一起吃午饭吗?好。
——一之濑同学,今天的问题我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教我吗?可以。
——一之濑同学很聪明呢,以后我有问题都来问你可以吗?……不可以。
仅仅凭借本能来选择“是”和“否”的答案就能引发他人的不快,甚至带来充满恶意的中伤和谣言的经历,一之濑悠不止一次的体验过。自那以后,他在发出每个音节前,都要仔细地思考一番,而等他思考结束的时候,就已经错过了回复的最佳时机。
——跟一之濑说话他都不会理人,是傲慢吧,看不起我们吗。
——一之濑君超~冷漠的,上次我帮他捡起东西,他居然理都不理,就站在那看着我,差劲~
人们对自己认定的东西坚信不疑的程度往往远超过对一个普通人的信任。等到悠意识到他需要解释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会听他解释的对象。他试图发出声音,但是他说出口的每一个字都会被指认为无意义的辩解,久而久之,也就沉默了下来。
构成生命的元素并没有声音这一项,也就是说,闭口不言和闭耳不听都不会对生活产生任何影响。抱着这样的想法度过三年之后,他几乎停止了对言语的接收,也丧失了表达的能力。
于他来讲,取代语言的,是铺天盖地的钢琴曲谱。
“赌场啊……适合赌场的音乐果然还是爵士吧,那种昏黄色又带着点迷惑人心感觉的小调,很合适不是吗?”
“蓝调也不错啊,适合八十年代的传统赌场,那种女性的感觉。”
午后的排练室里,浅野和天女目讨论着适合live主题的曲目。作为队长的浅野对很敏锐,作出的曲子也很受欢迎,因此承担了大多数作曲的责任。而作为和他一同成长上来的幼时好友天女目承担的更多的是编曲方面的工作。每次live曲子的基调大多是由这两个人做出决定。同队的天音也会作曲,可惜发挥不稳定,这点大概是本人那个过分跳脱的性格的缘故。
“那是什么啊?赌场要的应该是刺激不是吗,那种激动人心的,让人热血沸腾的才合适!”
“不行不行——那种没办法让观众融入进来的。这次不是你的长处,所以不行。”
“……喂まな你怎么看,果然还是应该热血一点才对吧。”
“没错,燃才是浪漫,比如说,碰见在赌场胡作非为的流氓我们像漫画里一样用音乐打倒他们——之类的,这种捏着一把汗的感觉最棒了!”
“稍、稍微跟我想的有点出入……总之,我还是认为要激动人心一点!”
排练室的关于live的对话进行的一如往常。前辈的浅野和天女目给出提议,然后被天音反驳,而まな的话永远都令人摸不到头脑。这种讨论他很少发表意见,也很难跟上谈话的进度。倒不是没有想法,只是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类似的热烈谈话总像是与他隔着一道荧幕的世界一般,他想说出的话无法让荧幕上的人物知晓,而荧幕中的角色也不会看向观众。
他是个观众,没有权利参与其中。
悠将视线转向窗外,思考起排练结束后在被要求与浅野前辈一同回家的路上,该说些什么才好。
“小悠怎么看?现在是二对二,你有什么意见吗?”
谈话矛头突然转向了他。悠毫无准备,在被浅野喊到的名字时候几乎手足无措。他慢慢将视线收回,看到四个人的眼睛都正盯着他。天音的目光正热烈地渴求着认同,天女目前辈的眼睛眯了起来,微笑着看着他,まな看着他的表情似乎有些担心的样子——虽然他完全无法理解まな在思考些什么。至于浅野前辈,悠的眼睛刚刚转过方向,突然就有那么一瞬间,丧失了与他视线相交的勇气。
……该从哪里说起才好呢。
适合蓝调和爵士的不仅仅是80年代的赌场,不如说30年前的整体的基调就是依凭在那之上的,并不具有赌场的代表性。但若只用燃或者热血沸腾的词汇来形容赌场,又未免太过偏颇。如果让他从他所知晓的物品来形容赌场的话,应该是罂粟一类的。同时具备华丽和危险这两种特性,才是赌博吸引人魅力的所在。相较而言,爵士太过随性,蓝调又过分浪漫。如果让他选择风格最为贴近赌场本身具有的特性的话,他最先想到的是灵魂乐或者节奏布鲁斯,像是Muddy Waters或者Ray Charles之流的游刃有余不缓不急的小调。
但是无论是怎样说明,似乎都不能从反驳其中一人的立场中摆脱,如果把全部想法直白地表达出来,相当于否定四个人之前接近15分钟的讨论。无论如何,都会至少令一方心生不快。
悠的牙齿无意识地咬住了嘴唇,修整整齐的手指在校服下摆处越叠越紧。
又发作了,无法说明的时候就会紧张的毛病。
按照悠之前与人交往的经验,在他做出这样的动作沉默一段时间后,问询的人就会自己走掉,他也因此可以松一口气。但是沉默好像已经持续了很久,三十秒六十秒九十秒,经年练习钢琴培养出的对时间的精准感觉偏偏在此刻也在发挥着作用。途中天音好像想要说什么,但却被坐在他一旁的天女目摁了回去。悠低下头试图避开所有人的视线,却还是能感受到投向他身上的目光的热度。
“……你、你们决定就好……”
没什么意义的一句话,但悠只想说些什么早点终结这个以自己为核心的奇怪沉默氛围。
“不行哦,之前有说好的吧,你有什么想法就好好说出来。刚刚那副表情完全就是「我有看法但是说出来一定会惹人不快所以还是算了吧」的意味,觉得不是的话反驳我也没关系。”
浅野有个特长,一般在少女杂志的情感栏目里会被称为情商怪物。而被他自己说的神秘一点,则是读心术。他很擅长看着别人的脸色,有时甚至能猜到对方接下来要说的话——其实只是会读空气。
悠在窘迫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也不明显。高兴的时候大概是嘴角会比平时多上挑一点角度,困扰的时候可能也只有眉毛微微皱下一些。因为想说的话他没办法表达出来,跟他交往的人也很难从这样的表情得到什么回应,所以会被理解成拒绝与人交流的傲慢也就不算奇怪了。
然而这表情的少许变化总能被浅野全部捕捉并且理解,哪怕是只在心里转过的一个念头,在脸上稍微显露了痕迹,被他看见后也会追问悠说是不是有什么看法。悠不讨厌和人这样的交往,毕竟不用言语交流对不擅长表达的他来说不是件坏事。但有时又会觉得有些可怕,像现下这样,不想告知对方的部分也会被接收到,就会出现十分尴尬的境况。
“我……”
这时候应该马上否认,然后迅速地想出一个合理的借口来推托。小说和电影里类似的情节有许多,悠甚至能在脑内回想起相关经典电影桥段的几段BGM的第一小节音符的排列,却偏偏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本该是个观众,隔着荧幕理解结局就足够。在落下帷幕的一刻,沉默地融入散场的人群里,成为路上随处可见的一个背影。
一之濑悠,高中生,十七岁,一米七二,不算胖也不算瘦,发型普通,长相凑合,打扮平庸。
从哪方面来看,都不具备应该让人产生兴趣并且认真询问意见的关键要素。
不知道从什么开始,连发出讯息的意愿都消失了。喜欢独处,喜欢将自己关在箱子当中,将所有的外部声音隔绝开来。
想要一个人,在没有人的世界当中,成为声音的绝缘体。
然后自己构筑的世界被轻易地被侵入了。
“磨磨蹭蹭地,赶紧把你想说的东西说出来啊?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赶紧告诉我结果啦,这样吊着真的很让人不爽啊!”
天音用手指着自己,声音震动着耳内的鼓膜,讯息以被动接收的方式被悠的大脑理解。
不远处的天女目前辈还是带着和善的微笑看着自己,说,我很期待可爱的小悠的意见哦。
“前辈要不要看看赌O默世录来多了解一下?看过就能理解我说的赌场浪漫是什么了!”
……不,只有这个还是算了。
“快点说出来啦。”浅野坐在离他最近的位置,一伸手,刚好能碰到悠的刘海——然后就被撩了上去。“像这样把眼睛露出来,也是让人明白你想传达的事情的很重要的一点呢。这次的live看来要帮你好好搞一下这个发型了……不过在转移话题之前,你的意见呢?”
世界突然有了自己以外的其它人。
准确地说,是被荧幕内的世界侵入并且吞噬了。用来隔绝自己的边境外壳在外部传达而来的声音面前不堪一击。
天音真的很吵。浅野前辈也很多事。天女目前辈总能包容所有人。まな还是他无法理解的存在。
言语是一种武器。
同样也能让人感受到温柔。
或许他可以试试,用他擅长的方式,用他唯一所能依靠的手段,再一次地尝试发出讯息。
“我想……这次的曲子,可以让我试着写写看吗?”
TBC
↓
Track 02 星間飛行
——————————————————————————
防止意外先把卡打上,没写完……总之可能要很烦人的一章一章发了。
基本没讨论过,OOC都属于我。队友有意见请告诉我我会改的……!


恋爱线 四章复活节舞会
*双手互搏,脚踢影子。俗称纠结。
-
佐伊已经做了安吉四年的舞伴,好像已经是约定俗成的事情一般,从二年级开始安杰洛就没有特意邀请过佐伊了,好像在舞会前拒绝几位可爱小姐的邀约就是定下舞伴的仪式似的。他们每一次都一起出现在舞会上,安杰洛穿套装而佐伊穿着礼裙,他棕色的长发柔顺地垂下来或者被挽上去,发间别着与安杰洛的领结同样颜色的花团。
安杰洛的目光从佐伊的一袭白色连衣裙缓缓上移,最终停在了他的脸上——他现在已经要垂下视线才能与那双金色的眸子相接,于是他就能看到佐伊长而卷翘的睫毛在眼睛里面投出一片小小的阴影来。他想起一年级舞会的时候,他为了邀请佐伊一起跳舞而拜托学姐做了一服增龄剂。那是安杰洛第一次自上而下地,望进那双金色的眸子里。
彼时少年的眸子更加清亮,跟他自己的一样带着未脱的稚气。他穿一条有星星装饰和层层叠叠裙摆的连衣裙,在自己面前轻轻地转了一个圈,裙摆和长发的末梢都轻轻地飘扬起来。
佐伊可真漂亮啊。安杰洛的小脑瓜一下子被这个念头充满了,他简直有些后悔自己的扮做赫淮斯托斯的服饰没有什么精美的装饰能很面前的公主相匹配,为什么没有提前问一问他要穿什么呢?
“佐伊,来跳舞吧?”
然后他有些局促地伸出手去,佐伊轻轻地翘起嘴角,把手搭了上去。那种感觉仿佛唤起安杰洛关于他们第一次见面的记忆——柔软纤细的小手搭在自己的掌心里,然后金色的眸子抬起来,漾出温柔的笑意。
“嗯!”
佐伊还是一如从前那般美丽,但眼眸中的光彩已经大不一样了。
他的发丝那么柔软地纠缠在自己的手指上面,在试衣间直射而下的灯光里面反射出琥珀一般莹润的光泽来。
安杰洛的指腹贴着佐伊白皙的脸庞,这只手在将一绺调皮发丝挽到佐伊的耳后之后就没再离开过。在平时的话,比起覆盖着薄茧的指腹,安杰洛更倾向于用干爽的手指背面去触碰别人,那里能使出的柔和力道就像抚摸猫头鹰细腻顺滑的羽毛时一样。
但佐伊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这种时候。
他还没注意的时候,手上已经不自觉地加了些力度。佐伊的眸子里生出一些疑惑,并且向后挪了挪了自己的步子。
要不要,就这样告诉他呢。
好像能听见扑通扑通的声音了。
他很自然地向着佐伊退开的方向倾过身去,就像之前他们跳过的许多支舞里一样。
唇瓣相贴,是一个像羽毛拂过一般轻柔的吻。
身体先一步动起来了呢,在安杰洛微微阖上眼之前,脑中大概是这样的想法。
一秒。
两秒。
三秒四秒五秒。
他感觉佐伊的睫毛轻轻扇动了一下,从上至下地。
紧接着他的腹部就传来激烈的冲击力,在来不及反应的时间内向后踉跄两步摔在了地上。
咚!
安杰洛不知道他自己听见的是拳头打在肚子上的声音还是臀部撞击地面的声音,总之当他抬起眼的时候只看见在转角处一闪即逝的白色裙摆,紧接着他感觉到来自胸口的一阵猛烈颤动,像是打翻了什么,让他对于痛感的反应速度都减慢了。之后开始好像是什么东西流了出来,灼得他喉咙和眼角都泛出一股酸意。
在几秒钟之后,三股不同的痛感从腹部、臀部和胸口侵袭了安杰洛。他紧紧地闭上眼睛,咬着牙忍住痛楚,然后将肌肉紧实的双腿蜷在身前,把额头靠了上去。
周围的交谈和碰撞渐渐微弱成模糊的嗡嗡声,伴随着漆黑的双眼和难熬的五分钟,身体上的痛感才渐渐开始减退。
……所以,是哪里搞错了吗?
安杰洛并不知道接下来他是怎么站起身来走出服装店然后回到霍格沃茨的,但是当佐伊意识到自己穿着还在试用中的礼服跑开之后折回服装店,匆匆换回他的麻瓜服装想要交还裙子的时候,服装店的阿姨满脸笑容地对他说:“已经付清了哦,被那位所罗门先生。”
这时候安杰洛大概已经把自己关在了他围着帐幔的床铺里面。
他没有理会休息室入口画像的关切眼神,也没有过多地回应休息室里寥寥几个人对他的寒暄——毕竟大部分高年级还都在霍格莫德没有回来,低年级们又有不少功课要做。然后他回到空无一人的宿舍,甩下外套便一头扎进自己那床施过蓬松咒语的被子里面。对,他连鞋袜衣服都没有脱,别在胸口的家徽硌得他有点不舒服。
不过远不及那里面传来的异样感觉。
-
“醒醒呀安吉,今天也要去店里喔!”
睁开眼的时候他看见大姐伊丽莎白的笑容,然后他就像往常一样吃过早餐之后来到了熟悉的所罗门魔杖店,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门口的风铃声、人们的说话声、鞋底踏在地板上的摩擦声,一切都如此熟悉。
是安杰洛·所罗门平凡的一天。
“安吉,你来。”
他听见卡洛琳姐姐在叫他,顺着手指看过去是又一个顾客,他有着棕色的长发和金色的眼睛,正稍微有些犹豫地走进店里。
“你好。”他走过去把那个新生带到柜台前,“欢迎来到所罗门魔杖商店,我是安杰洛·所罗门。”
“你用哪只手拿魔杖?”
于是他轻巧地拿起软尺来测量少年的数据,少年身材纤细,手也比他的小一些,那双金色的眸子很漂亮,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
“嗯——或许你可以试试这个?”
在少年被爆裂声吓到之后他连忙拿出另一只魔杖,跟刚才那只他自己选的不同,这一只是父亲诺文亲自选的。
“那你试试这支,十二又二分之一英寸,梧桐木,凤凰尾羽——这搭配可真棒。来,挥一下。”
少年依言挥动了左臂,荧蓝色的光芒在魔杖的末端闪耀起来,就像一个荧光闪烁咒那样。
“就是它了!”安杰洛兴奋地笑起来,然后把那只没什么过多装饰的魔杖放进有天鹅绒内衬的盒子里,交给了少年。
“在这边付钱,谢谢光临!”
在分院仪式上他又一次看到了那个男孩——哦来买魔杖的当然都是这一年的新生——在他自己被分进格兰芬多之后,他又一次听到分院帽喊了这个词。
男孩跳下高凳向这边走过来,然后在这条桌子的前面找了个地方坐下,他好像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跟身边的同伴叽叽喳喳起来,而是默默地表现着对桌子上各种食物的兴趣,他的长发在低头的时候垂下来挡住了一半侧脸,让安杰洛看不清他的面容。
紧接着安杰洛的注意力就被格兰芬多欢迎新生的欢呼声吸引走了。
他莫名地觉得那个身影非常熟悉,可是翻遍了自己的记忆也找不出跟他相关的哪怕是一点碎片。
这种感情愈发地强烈起来。
然后在魔药课上他终于又看到那个少年,他微微弯起唇角,纤细的手指握着魔杖在坩埚之中打转,然后偏过头来向自己询问下一种配料。
“所罗门先生——”
他突然地愣怔了一下,手一抖把切着的材料嘣到了面前的坩埚里。
一声巨响,他感觉到灼热和疼痛,接着被一片黑雾迷住了双眼。
-
“安吉?安吉?”
睁眼是泡泡糖色的齐刘海短发,安杰洛几乎下意识地跳起来想要大喊“啊啊啊啊啊卡洛琳你怎么在这里”,但他没有,因为隔壁落下的帷幔里佐伊可能还在睡着。于是他平复了一下心绪,深吸几口气,然后带着依旧有些颤抖的尾音问到:“卡洛琳,你怎么在这里?”
“我受到召唤。”卡洛琳的声音轻飘飘的,她指着自己光洁脖颈上面衬着的那枚七芒星吊坠——所罗门家的家徽。安杰洛想起来上面的特殊魔法就是为了紧急通讯,所以家里才会要求把它随身带着。“你的脸颊都湿了。”这么说着她轻轻抚过安杰洛的眼角,那儿确实潮乎乎的,而他自己就像是没发现一般。
照往常来说他早该适应了卡洛琳飘忽的语气和跳跃的思维,只是现在他反应不及,然后他抬手摸了摸胸口的家徽。“我呼叫了你吗?”
“午夜已经过了,姐妹们应该都睡下了,或者是你只呼叫了我一个——你在哭,安吉,这不是件小事。”
“霍格沃茨可不能幻影移形。”
“不过飞路网还是正常的,我穿到你宿舍外面的壁炉——你这样子我一定要来看看不可。”卡洛琳的指尖划过安杰洛的面颊,然后抬起眼睛似乎洞穿帷幔一般地投向他身后。
“你并没做错什么。”
——她是个窥心高手。
不出所料。
-
安杰洛没有在预定的地点等到佐伊,于是他入场的时候礼堂之中已经挤挤挨挨地站满了人,他们装扮精美,一对对环绕在水晶饮料塔和盛着各式食物点心的桌子旁。开场舞的音乐已经奏响,他远远看到舞池中飘散浅色长发的女孩和他有些眼熟的舞伴,但这并没吸引他的注意力太久,因为他穿梭在人群之中正寻找他的舞伴。
他小心翼翼地捧着那一团紫罗兰胸花,鲜花被施过了保鲜咒语,鲜艳地吐露着与他的领结同样柔和的蓝色。那是他拜托心灵手巧的姐姐帮他制作之后,放在克里斯提尼给他的瞬间传递箱里送过来的——这对箱子第一次运送了些不是魔杖材料的东西。
在这之后他看见那位开场舞中看见的女孩向他身边的饮料塔走去,于是犹豫了两个回合之后他决定跟上。
“小姐?”
他隐约记得佐伊所说的女孩的样貌,毕竟他们没有正式地打过照面。虽然女孩那轻飘飘的感觉给安吉留下了印象,但是这慌忙之中,女孩的名字倒是没有完整清晰地从记忆里浮上来。
“……麦、麦索提斯小姐?”
回过头的少女稍稍有些惊讶,不过一瞬间就平复下来,点点头示意安吉继续说下去。之后少女轻轻歪了歪头,好像是在提醒安杰洛叫了他之后好几秒钟都没说话的事实,又像是在期待面前的男孩子能说出什么让他感兴趣的事情一样。
“呃……”
“请问、你有见到卢……”
不知道为什么,安吉的舌头突然好像有点不听使唤,他明明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可那个字就是卡在喉咙里出不来。他意识到平时自己跟佐伊都是以名字互相称呼,显得随意甚至颇为亲昵,自己已经多久没有这样用过一个姓氏了呢,他不知道,但手心里似乎已经沁出汗来。
想见他,自从佐伊突然跑开的时刻开始,安吉格外地想要见到他,或许因为这个原因,他的舌头才激动地打了结。
安杰洛一咬牙,从侧袋抽出来自己的魔杖。
“——荧光闪烁!”
在魔杖尖端盈盈的蓝光里,安杰洛终于理顺了自己的舌头。他迎上了少女看到闪亮的杖尖之后了然的表情,轻轻地把之前想要说的话平稳地送出来。
“他是我的舞伴。”
少女的唇角向上仰起一个轻微的弧度,朦朦胧胧的,若是不仔细看甚至看不真切——当然一个劲盯着不熟悉的女孩子是件失礼的事情,这点印在每个绅士的脑子里。所以安杰洛看到她的指尖向旁边一晃,那儿有个靠背上搭着礼服的椅子,旁边是端着杯子低着头的少年,他浸透在头顶传下的暖光里,发丝间流淌着福灵剂一样的颜色。一瞬间安杰洛便恍了神。
少女的声音是轻微而空灵的,在彩色的灯光里仿佛晃动出轻飘飘的影子来,安杰洛好像在一瞬间突然明白为什么佐伊每次提起她的时候都如此温和,因为面前的女孩确实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是一朵惹人怜爱的勿忘我花。
“……请加油。”她说。
安杰洛好不容易把直直定在那边的目光收回来,回赠给少女一个微笑致意,又看了看手上的花,向那一片光亮的彼端走了过去。
*給空空土下坐…我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但是故事一定会写完的。
爱你,以及谢谢。
宇鹭 莉莉子记事簿#其一
关键词:
〔三个故事;兔子白鸟和月亮;照片上的小猫发卡〕
*
写点什么吧,写点什么呢?
啊,有三个关于兔子的故事,从书上看来的,因为很无聊就抄下来吧。
第一个是关于森林里的兔子,与从南方飞回来的海鸟再一次相见了的故事;第二个是兔子在月亮上一边捣着年糕一边偷吃,捣完却发现什么都不剩的故事;第三个是兔子与猫……奇怪,兔子与猫?
后面的故事不记得了,今天就写到这里吧。
*
我醒来的时候大概已经很晚了,之所以能够这么断言是因为我已经看到阳光透过无色玻璃与半透明的、镶着轻飘飘蕾丝边的窗帘照在了床头那只尽职尽责的闹钟上。于是我重重地躺了回去,用了一小会儿的时间回忆并整理了那些在我脑海中反复交叉、跳跃,没有规律且没有主旨的记忆片段。
然后,然后,我终于将无数的点拼凑成一条线,目睹它从折线变成曲线,最终变成一马平川的直线,一切都完成后我感到了完成一项莫大的任务般的满足,甚至想要由衷地赞美这平淡又闪闪发光的每一天,于是我踩上柔软的地毯,拉开窗帘——有风从玻璃窗的缝隙漏进来,发出吹口哨似的欢快的声音。
当我悄悄地拉开卧室的门扉、踢踏着毛绒绒的小动物拖鞋路过小年紧闭的大门时我忽然感到一阵做错了事般的心虚,我压低了脚步,像是个闯进房子里的小偷一般走完了最后几步,立刻蹦蹦跳跳地跑开了——无论是哪一个神都好,请保佑小年不会被吵醒吧。
如果莉莉子是兔子,小年就是白鸟,和名字一样的兔子、和名字一样的白鸟——我曾经养过全身雪白的鸽子,我看着它将头埋在羽毛的缝隙间,满心以为它已经陷入睡梦,但我一靠近它就扑打着翅膀远离了我——那么,小年是鸟,所以只要一点儿很微小的声音,那扇紧闭大门后的平静就会被打破,然后我就会心怀着吵醒了他的罪恶感、度过一个压抑的乏味的上午。
这一次比我预想得顺利多了,我走进厨房,不出意外地看见了烤土司与花形煎鸡蛋排列有序地躺在瓷盘里(小年早起时准备好的,现在已经变得温度适宜了)。我把餐盘拖到面前,用叉子挑破镶嵌在中央的、晃晃悠悠如同眼睛般的溏心蛋,看着那淡黄色的蛋浆沾在微焦的蛋白边缘,就这么百无聊赖地用叉子拨弄了一会儿,再在看到挂钟的那一刻迅速把他们连同全麦面包匆忙地塞进嘴里。
那么从这一刻开始向前数二十四个小时,把圆圆的月亮似的表盘向前拨两圈直到它回到和现在相同的位置,天空从蓝色变成黑色再变成蓝色,直到开学日我满心期待地抓起因为塞满了便利店的年糕和蝴蝶结发箍而变得沉甸甸的书包,三步并作两步跌跌撞撞地登上一节又一节盘旋的阶梯的那一刻,我在亲爱的艾莉娜学妹的房门前停顿了一会儿来平复过快的心跳,然后攀着梯子,登上屋顶向远处看去——在那里,在被云层遮蔽的、熠熠发光的地平线上,我知道在那里还伫立着另一片别墅的丛林,在那里从第一个字母数到第四个字母,和我的卧室坐落在同一处——那是紫月,从一个很小的黑点渐渐有了形状,再能看到她真是太好了!我感到久别重逢的喜悦,甚至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想抱着她在绿地上转好几个圈。在麻痹了人的快乐中我踩了个空、从三层楼的高度向下栽落……不,这是骗人的,无论是我还是紫月都很清楚,是我自己故意向下跳的。我还记得在身体失去支撑前的最后一刻我是如何踩着房檐试图飞得更高一些——我开始向下坠落,风把长发与裙沿卷起来,感到失重感从一个点扩散到每一寸皮肤。
太高了——我有点胆怯、又带着更多期待地闭上眼睛,下一秒感到自己重重地落在某个人的怀里,再次睁开的时候看到的首先是紫月,亲爱的紫月——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迎面对上她露出无奈与柔软神情交织着的宝石似的眼睛。这时我看向地面知道自己已经摆脱了地面、只有气流如同水的波纹般稍纵即逝,像是穿行在云层间的鸟,于是我想起关于公主、荨麻衣服与天鹅的童话故事,以及有着人的身体与天鹅翅膀的小王子。
"好高——!"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体验过这种感觉了,但每一次都觉得很新奇,这种时候也不由得暗暗地想着,如果我也是风系就好了。
但假如我是风系,就不可以被紫月接住了——所以光系也很好,完完全全、彻头彻尾,没有什么不好的,属性造就了我可以一直跟在一个人的身后,如同行星之于恒星、卫星之于行星,一想到这里心情就忍不住变得轻快起来了。
"小紫月!"一落在地上我就迫不及待地抱住她像是只讨好人的动物般蹭来蹭去,"是真的小紫月哦——好久不见!"
"好啦好啦..不要蹭我了,你还真有精神。"
"每天都精神满满可是莉莉子的优点哦!"听到这里我抬起头来,一本正经地对她说道,紫月一边点着头,一边听完了我这番没头没脑的发言,末了她伸出手来摸了摸我的头——我感到一种小学时体验过的、被老师表扬般的感觉,好像整个人都变得轻飘飘了。
"好久不见。"她笑着说。小小的、明亮的光点把她围在中间,这让她看起来有种类似于梅干红茶、黑胶唱片与她亲手做的紫菜饭团混合在一起的感觉,但究竟是什么的感觉我也说不出来。于是我从书包里掏出年糕和蝴蝶结发箍(虽然我有充足的理由确信她不会戴出来),不加整理地乱糟糟地塞进她怀里(本来想自己做年糕的,但成品太难吃已经被我倒掉了。)
"兔子加月亮等于年糕,所以我给小紫月带了年糕!"
这样的话我在刚入学时也对她说过一次,那么这是第二次,但是无论是我还是她都不会再有第三次机会了。
紫月的手愣在半空中。
"小紫月,小紫月…………怎么啦?"
她触电似地收回自己的手,然后仓促地对我解释了几句,但我的思想正飞驰在外岛的海面,脑海里活跃着各种转瞬而逝、没有意义的画面,而当我重新把注意力对准面前的时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紫月已经不在了。
这是我在六等星的第二年,但转瞬之间我已经成为了三年级的学生——到底、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即使很努力地去想也仍然想不起来。
*
我喜欢星星,不止是因为我的esp能力是像星星那样闪闪发亮,有的时候人就像星星,有亮晶晶的星星;有黯淡的星星;还有像是枯竭了的眼睛似的星星。这番话以前也有人对我说过——在国中时,在七月中旬的深夜,我看到了从未见过的银河,在夜幕中它仿佛是奔流不息的银色的洋流,还有在无边无际的星海下,似乎被光芒柔和了的模糊的面庞。
这样的星星消失了,不是忽然一下,是慢慢地、慢慢地……再也看不见了。
我拿出从布卢教授那里拿到的合照,在照片的右下角我看到了熟悉的小猫发卡。我知道那只发卡,白色的,有着浅灰色的斑点,在阳光下会闪闪发亮——然后那只小猫发卡,就带着那只猫一起消失不见了。
有纪奈奈子。
再见到她的名字时,是在这张失踪名单一样的照片上。
我匆忙地把照片翻了一面夹在空白的内页里,试图清空自己丝毫没有头绪可言的思维。最终我放弃了,重重地把笔记本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