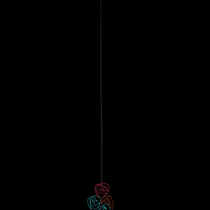※严重无视时间线的同人,文笔傻吊注意
雨宫明睡着了。
他侧身,刘海掠过紧闭的眼,垂落在枕上,安静得仿若已然就此死去,而如今这具宁静身躯上的温度,则仅仅来源于片刻前在他身上导演的、暴乱的激情戏。睡眠洗去了他清醒时一切讨人厌的脾性,只剩下尖利的脊骨咄咄逼人,从皮肤底下节节凸出。凌晨三点的月光无声敲击着这琴键,将他裸露的背照得苍白如纸。
深海透将电子烟塞进嘴里,垂下眼,视线凝在他的睡脸上。
他见过太多人睡着的样子,那些不同的脸上写着共同的松散与无知无觉,身体笨重得令人难以忍受。可雨宫明不同。雨宫明是大理石刻出来的雪白藏品,是切开桃核后才会出现的、手脚蜷缩的孩子。他跟深海透的世界奇怪地格格不入,更像是被什么人强行塞进来的。一件可怜又可爱的新玩具。
深海透第一眼见到他时,就感到这场相逢中暗含的不怀好意,这份恶毒既针对雨宫明,也针对他自己。他曾抓着雨宫明的头发告诉他,自己之所以对他纠缠不休,是因为早早在他身上读到了堕落的潜质。他不知道雨宫明是否接受了这个说法,但他心知肚明,这是个谎言。雨宫明是个好孩子。而他向这份无辜伸出手,只是因为他想罢了。
深海透用空着的手拨开雨宫明的刘海,好将他看得更清楚些。
他睡着的样子,比他醒着时软化了许多,然而那双嘴唇依旧紧抿,眉心不自然地纠结,好像正在为什么覆水难收的东西懊悔。
不过他确实该懊悔,深海透想,他跟最不该上床的对象上了床。
深海透跟很多人睡过。起初,这是逃遁他最厌恶的东西——无聊——的一种方式:多新鲜,多有趣,他的容貌与巧言赋予他厄洛斯无往不胜的箭矢,只要露出微笑,无人能够抵挡他的邀请。他在这过程中,发觉了自己了不起的才能:他能将人们的衣服连并他们彬彬有礼,令人如鲠在喉的交往方式全部脱下。床榻上一切都是累赘,激情,也只有原始的激情是最重要的。他能从最文雅的人嘴里逼出咒骂,从最强硬的人喉头挤出呜咽。在快感的尘嚣之上,在仿若停滞的高潮中,他得以对那仿佛脱离世界的自由投去一瞥。
这让人上瘾。
深海透在所有想象得到的地方实践,有妇之夫的衣柜与流浪汉的长椅都曾是他限时开放的欢场。他将时间、地点、对象、道具排列组合,尝试任何可能性,比饿久了的独狼更贪婪,更不知餍足。
渐渐的,这快乐成了形式化的重蹈覆辙,欲望不过是客体,而他自身,则升格成专为寻欢作乐而诞生的艺术品,在平滑年轻的身体上,激情无数次点燃又寂灭。日常与平庸被抛之脑后,过往的记忆也烟消云散,仿佛踏上列车,他抛弃一切,包括自我这座孤岛。每个夜晚,他是激情的主人而非奴仆。
但仍旧不足够。
就像尼古丁上瘾者,只有不断加大剂量,才能延续一如既往令人安心的乐趣。他得在厌倦之前找到解药,或者,新的毒/品。
深海透想,这也许是他向雨宫明出手的理由。
仅此一次,他向自身的欲望屈服了。
他想要得到这个人,这个簇新的、前所未有的玩具,不管用什么手段,不管是欺骗还是暴力,不管对方会因此变成什么样子。
他一定要到手。
每次半夜醒来,当所有激情冷却为炉中灰烬,当身侧的人沉沉睡着时,在干燥的空气里,深海透会感受到海水的气味。这过往的幽灵,这死缠着他不放的家伙,低声在他耳边诉说,说他终其一生都困在同一个地方。
——属于他童年的、铅灰色的海。翻滚着如同铁质的波浪,到处充斥着锈迹斑驳的味道。深海透不是在欣赏装裱起来的大海挂画。他置身于其中。
在这里,深海透既没能沉下去,也没有浮起来。他只是被浸没了,海水填补了他气管的缝隙,塞满了他的肺,苦涩的味道由血管淌遍全身,无法剔除静脉,他就永远也摆脱不了。在这里,他感受不到自己的呼吸、伤口或者眼泪,这海水是从他胸腔破开的地方淌出来的么,亦或是依照他的记忆,原模原样克隆出来的样本?他一无所知,只是漂浮,永恒的,无所依靠的漂浮。就像泡在福尔马林里、还未成形的婴儿。药剂品取代了羊水,玻璃瓶代替了子宫,将他永永远远保持在被取出的那一刻。
不论他做什么,他都揭不下自己身上的标签,他无法成为寻欢作乐之徒,或者擅长交际之辈。他只是、只能是、且永远是一个幸存者,是没能死在大海里的那个人。
可当他握紧雨宫明的手时,他确实感受到自己在浮起来。一个明晰如刀的念头割裂开他昏沉的心:他或许能就这样离开,送走过往,剔除大海上所有不幸的意象。雨宫明是被硬塞进他的世界的、有独木舟的那个人。而若是他能好好地抓住他,不让暴风雨将船撕成木屑,他也许能就此得救。
但深海透做不好这个。从所有的经历中,他只学会了离开。他离开,或者别人离开,没有其他选项。更何况,离开这里,他又能去往何处?前十七年都没有降临在他身上的、所谓幸福这种东西,真的可能因为一次逃离就向他走近?这个人,这场相遇是否是命运投放下的另一个全新陷阱,只为了让毁灭进行得更加彻底?
与其如此,深海透想,与其眼睁睁看着希望破灭,不如让这无与伦比的幻觉葬送在自己手里,在此时停止,在幸福的一刻停止,如此,他就能毫无痛苦地用余生来缅怀这一瞬而逝的流星。
深海透的手沿着雨宫明的侧脸下滑,最后稳稳停在他的脖颈处。
他能杀了他。他清楚无比地认知到这点。在他手下,这软弱如花茎的脖颈一掐即断。收紧手指,便能感到动脉在这肌肤下跳动。停止这涌流的热血,也就能停止他无所觉的生命。
没什么停手的理由。这句号该由他画下。
雨宫明没有醒过来,但他约摸察觉到了突如其来的窒息感,难受地挣了挣,头颅转动,柔软的发丝蹭过深海透的手,或许太柔软了些,犹如一首诗的最后一行那样熨帖。
像是操纵木偶线的人突然扔下了控制器,深海透停住了动作,手渐渐退开,悬在半空。雨宫明的呼吸随之慢慢平复,又成了大理石刻出来的雪白藏品,成了切开桃核后才会出现的、手脚蜷缩的孩子,可怜又可爱,当深海透第一次见到他时,便预感到了这场迫在眉睫的双向毁灭。
他再也没法在这里待下去了。
深海透抓起扔在地上的外套披在自己身上,甚至未察觉自己捏着烟的手正颤抖不已。他只想着大步离开,离开这个房间,离开他的大海,独木舟,凌晨三点的月光与沉沉入睡、星火般差点熄灭的希望。
他没有回头,身后门掩上,如一声叹息。


上接【http://elfartworld.com/works/174035/】的過渡章
【寫完繼續回去寫二章(滑跪】
吃完早飯後,由紀子在餐廳小小休息了一會兒,在八點一刻時回到了位於宿舍塔四樓的房間。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已經發生了兇案的關係,樓道里安靜地異常。大部分人還在式典之間調查。
由紀子在這死一般的寂靜中打開了房間的門,整理自己的心情。
斯特拉托沒有說話,由紀子對於這點很感激。距離學級裁判開庭的時間還有將近兩小時,整理一下目前發生過的事情也未嘗不可。她從隨身包裹中拽出自己的隨身文具,扯開其中一頁寫了起來。
這與其說是某種總結,不如說是由紀子平日用來梳理自己思維的工具,是一種思考的習慣。她拿圓柱筆點了點本子的角落,隨後開始寫了第一句話。
“死者真田零鴉。”
她頓了頓,在那個名字上畫了一個圈,隨後是一個,又一個,又一個,直到那個名字幾乎要被掩蓋。
“下午放學時在教室裡見過面,那時大概是下午五點到六點,他詢問了我一些問題。在那之後我就沒有碰到他了。調查尸體的人說他的死亡時間是凌晨一點到二點,在那之後,……大概五點的時候。”由紀子回想自己那時被真白的聲音吵醒時看到的時間,誠然,真白發現尸體的時間應該比那更早。
……然後是真田零鴉身後的鐘上的時間,三點二十。
將三個時間在紙上排放整齊之後,由紀子放下了筆。斯特拉托的表情很平靜,不像他往常的樣子。
“從現在開始你是新的斯特拉托了。”由紀子輕輕唸到,她用圓珠筆對其進行狙擊,隨後斯特拉托不見了,“今天還發生了什麼?對了。”她想起自己在去餐廳時看到的東西,那是在地板上的一片碎布。
那片碎布的材質看起來與真田身上的服裝材料無異。雖然僅僅是一瞥,但由紀子還記得那時看到的真田零鴉的尸體上確實也有相應的痕跡——真田身上的衣服破破爛爛,或許就是在餐廳裡那片碎布的由來。
但是,為什麼要將真田零鴉身上的衣服破壞掉呢?犯人不會無緣無故破壞掉衣服,即便是想對尸體做些什麼,也沒必要是破壞衣物,愉悅犯的肢解或許有可能,姦殺犯拋下赤身裸體的死尸也不是沒有先例,但真田的衣服不是被脫掉而是直接在還在身上的狀態破壞,身體也沒有被大卸八塊,反而更讓人疑惑。
犯人或許是想掩蓋什麼吧,衣服上,或者真田的身體上的東西。
無用的東西……需要被掩蓋的東西……
由紀子趴在桌子上,用圓柱筆在筆記紙上劃了一個巨大的叉。
搞不明白,完全搞不明白,殺人犯的動機不明確,現在看來,唯一有動機殺了真田的,只有一個人,但是那個人又沒有任何下手的可能性。
她在不停地思考中最終走向了死胡同,往後退幾步原本能走到不同的道路去,可前方的答案卻依舊不明確。一切都像被濃霧所掩蓋,然後是又一次進入死路。退出,再度進入。退出,再度進入。退出,再度進入,直到思維的連接失敗,川端由紀子跌坐在斷線的位置上。
不行,不能再想下去了。她警告自己,信息還不夠,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撐起一次推理,如果可以的話,她也希望擁有波羅和福爾摩斯的超能力,那不是灰色的腦細胞,而是被作者所眷顧的能力。偵探能從現象組成的無數可能性組合裡面找到正解,川端由紀子稱其為“靈感”。
和作曲、寫作,乃至繪畫一樣的靈感,唯一的不同是,偵探的結果是相對於宏觀的唯一答案,創作的結果是相對於作者自己的唯一答案。
還有一個地方沒有看。由紀子強撐著將自己從桌子上分割開來。真田零鴉的臥室。雖然那裡還有線索的可能性極低,但總比不去看要強一些。
抱著一絲逃避心理,她收拾好隨身物品,旋即上了樓梯。真田的臥室在五樓,只需要幾步就能到達,徒步的過程卻給人一種時間過得漫長的錯覺。川端由紀子走向盤旋樓梯的末端,她從樓梯墻壁上新鮮的手印推測,已經有人來過這裡了。
真田的房間是離樓梯口最遠的一間。門不出所料上了鎖。雖然不知道尸體上的戒指是否還能打開,但看來也與案發現場沒有什麼關係。由紀子帶著這條中斷的線索走了回去。然而,她卻在回去的路上看到了未希。
“未希……”她小聲向對方說道,未希看到她之後抬起頭來。她們兩人互相對視了一會兒。
“未希調查了嗎……看到真田的尸體了嗎……那個樣子的真田。”
在沉默中由紀子意識到自己掉了眼淚。但對方並沒有嘲笑,也沒有說什麼“不要再哭了”之類的話,只是遞出來了一張紙巾。由紀子擦拭著眼淚,頭一次感受到了櫻井未希所散發出的溫柔。
“真田他在死前曾經來找過我商量過……但是我那時因為害怕自己的情緒外露,而沒有和他說真話……現在,他死了……”由紀子小聲地說著,未希既沒有說“這不是你的錯”,也沒有說“我懂的”,只溫柔地聆聽并接受了一切。
隨後,未希輕輕抱住了她,在那溫柔的搖籃裡由紀子脆弱不堪一擊的心情徹底決堤,她控制淚水的能力不知為何也一併失去。
感知在此刻被放大到最大。未希的身體是如此的溫暖,讓人重新獲得了生命實際存在的感覺。
未希就這樣無聲地抱著她,時不時輕撫她的後背,兩人在樓道裡靜靜地等待著時間的流逝。
***
“由紀子、由紀子。我來給你講個故事吧。”那是很久以前發生的事情了。
“如果說所有的故事都要以很久很久以前為開頭,那也未免太過乏味了一些,我是這麼覺得的。所以,這個故事,讓我們將他設定到更晚一些的時候。就是在那麼一個時機裡,天空的心上破了個大洞。”
“於是有一個少年被破了的天空所選中。由紀子啊——不要用那副眼神來看我嘛,笑起來嘛,我喜歡你笑起來的樣子。雖然是個滑稽的故事,但也是我想了半天的哦。”那個漂亮的女孩子那麼說道。
“‘少年啊,我希望你能拯救我,也能拯救我所覆蓋的大地。’天空對少年這麼說,‘你去找人間找些心裡快樂的人,再找些心裡受傷的人,然後將他們的心獻給我。’”
“少年起初很抗拒,因為他懂的別人的心不能那樣隨便地偷走。但是,因為天空破了個大洞的關係,從那大洞裡面源源不斷地射出來傷人的光線,不得已,少年只好接受了自己要為天空縫補心的事實。”
“少年他找啊,找啊,在天涯海角尋覓著合適的心臟。他在一個農場遇到了一隻牛。牛的心臟應該很大,少年想,於是他假裝是來做客的,敲了敲牛的牧棚,可當他進來時,他卻後悔了,因為他看到了牛和她的家人們。牛溫柔地對待其他所有動物,將他們當做可愛的寶貝,擁有這樣的心的動物,少年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痛下殺手。”
“少年只好前往下一個目的地。他在一個森林中遇到了一隻龍,龍的心臟應該很大。少年想,於是他假意要當做勇者,跳入了龍的巢穴,可當他要進來時,他卻再度後悔了。龍作為森林的守護者,一直以來保護了那麼多的動物,要少年取它性命的話,少年是做不到的。”
“於是少年灰溜溜地走向一個城市。越來越多的人被天空破洞所殺死,少年只好加緊了自己的步伐。”
“在那裡他遇到了一個機器人。一個機器人!一個無父無母,一個沒有生命的機器人!他意識到這可能是最佳的機會,於是他去詢問了機器人是否可以把她的心取走。”
“‘當然,因為于我來說,沒有人會對我本來的心臟感到難受。如果這個東西能縫補天空,我會很開心的。’機器人說道,許可了少年的想法。她將她那個精巧的小心臟給了少年,接著便一動不動了。少年拿著那個心臟縫補了天。”
“天空欣喜若狂,她寶貝地抱著那顆精巧的小心臟,一直抱到它發熱、發光為止。天空吻那心臟,就像太陽親吻你們一樣。獲得了心臟的天空成為了新的天空,時至今日也好好地掛在我們頭上。”
“這個故事完了嗎?”川端由紀子坐在課桌前,向講故事的孩子問。
“某種意義上算是完了吧。”講著故事的孩子說道,“由紀子,以後我每天都來講個故事吧。”
“好啊。”
讓我來為你的心臟填補上有趣的東西,然後你將成為新的由紀子。
梨津奈那麼說著,吻了她的額頭。
【先說一下⋯⋯!由紀子和梨津奈還有和未希都是普通的友情!!防止大家買錯股票預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