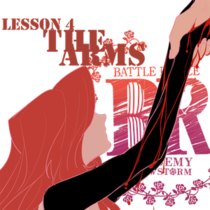日升之屋
阳光在变好。自三月以后,那种薄薄的、冰片似的冷阳终于浓厚起来,积存在他们红木的屋脊上,如同蜂蜜粘稠地滴落。罗可的心情半好半坏,鉴于他奶茶中糖块的比量已由三块减少到了一块半。门萨用分茶饼的小铜锤将糖块砸开,当着他的面丢进浓郁茶汤,在他悲叹时从镜片后抬头,投过一个这些年来他已经熟悉得能蒙上双眼以指血画出的眼神。“你知道这对你有好处。”门萨曾就这个问题如此表态。他在宠坏罗可并放任他得脂肪肝与“宝贝拿走他的奶糖巧克力!让他狠狠地恨你!之间权衡利弊,几近残忍选择后者,马拉松性爱与限量版圣经也没能让他改变想法。抛却个人因素来讲,罗可认为这点十分可敬。
他们得给屋檐除冰,不然滴水会在门口的石板成洼,或者弄糟罗可十分喜欢的那块小地毯。他们讨论过雇个工人来做,顺便修修屋顶的瓦片、掏掏烟囱什么的。罗可发誓他在阁楼听到过鸟雀刺耳的鸣声,门萨则怀疑那是他们的暖气管漏水导致。无论如何,只是讨论,两人都未上心到付诸实践。近来门萨在南开斯特区的跳蚤市场找到一个不错的二手书批发点,使得他在进新货的同时好好充实了一下自己的书库。罗可坐在柜台后的时间只好比他们原来商议得多出了那么一点点。当然,并不是说他多么介意。在这些时间里,他只是靠在那张足够结实也足够舒服的藤条椅上,围着一条大毛毯,桌上摆着糖块和杏仁一类的小点心,一本旧书在他左手边摊开着,纸张的苦涩气息混着茶香。下午的阳光在人行道上一点点移动,他一直看着,直到那光束退至斑马线旁的邮筒,给火红漆面涂上灿金,那时候,门萨就会回来。
罗可也喜欢门萨坐在那柜台后的样子,总是一副温文雅致、彬彬有礼的样子,他笑起来嘴角显出法令纹。罗可知道自己也是。但那并没让门萨的魅力减少半分。他亲切地招呼每一位推门而来的客人,为他们找书,提供些阅读上的建议。他们的卧室里添了新书架,木头是罗可选的,温暖厚实,能用一百年也不会坏——当然,那个木匠是这么跟他们保证的。门萨一有空就把之前堆叠在地板上的书本分好类,一层层码到书架上去。这些书有门萨的,也有罗可的,本来他们想做两个架子分开摆放,不知怎的就稀里糊涂摆成一团,罗可的《闪灵》紧挨门萨的《洛夫克拉夫特作品选》,一本属于门萨的《欧洲植物学》和明显是罗可的《如何照顾你的柠檬树》挤在一处。琳琅的书目就如同他们的生活在木架上交织。偶尔,他们搞混了这一本书和那一本书都是属于谁的。“这本《传教士位与咖啡豆》绝对不是我的,因为我根本不喝咖啡。”罗可蜷在床上,抱着膝盖,以一种装模作样的纯洁语气说道。门萨手里抱着一套三本的《利未记》,叹了口气,没说什么。
“而且,我也不是特别喜欢传教士位,你知道的,”罗可翻过那本书读着封底的简介,“对腰不太好。”
“唔,其实我还蛮喜欢的。我喜欢看你的脸。”
“我知道。魅力这种东西真是没办法,对吧?”
门萨扭过头,对上他伴侣那自认为最光芒四射的笑容,终于也忍不住笑起来。
“来吗,神父?”罗可伸出一手,将走过来的门萨拉入怀抱。就在他要到对方耳边低语自己的下一步邪恶计划的时候,门萨语调不稳地说:“停、停一下。”
他从两人肚子之间拽出那本《传教士位与咖啡豆》,把它扔到地板上:“现在好多了。”
他们同时大笑出声之际,罗可觉得自己还挺喜欢传教士位的。
一个叫玛蒂尔达的姑娘来托门萨找一本旧书。“我祖母总是提到那本书,”她揪着衣角,神情局促不安,“她得了病,很严重,快不好了,我想在她走之前为她找到那书,读给她听……”
罗可从旁边瞅着那小姑娘,看她苍白憔悴的脸色和纤细手臂上青色的血管。她之前大概受过不少苦,想来她祖母亦然。他想说这种半个世纪前就快绝版的书籍实在寻无可寻,但看到女孩脸上的表情,还是把那话咽了下去。
“我找遍了城里每一家书店,我不知道还有哪里可以找的,拜托你,先生,这是我祖母最后的愿望。”
门萨望着她,镜片后的目光平和,没有一丝敷衍的伪态:“我们会尽力,小姐。”
那女孩嗫嚅着道了谢,随后离开了,走上那金色的人行道时回眸一望,隔着玻璃的反光看不清表情。罗可嘬了一口他仅放一块半方糖的奶茶,道:“或许你不该给她希望。”
“每个人都值得希望。”门萨说,神情中仍看不出其他端倪,突然他抬头,对罗可一笑,“就像你当初对我做的那样。”
罗可看着他,感到几乎酸痛的爱意在胸口泛起。你何尝不是予我以希望。他心中几乎狂乱地想道,最终,付诸一个小小的、甜蜜而哀伤的吻。那过去似乎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他看着门萨推开门,黄铜铃铛大响特响,门萨伸手止住铃声,向他笑笑,摘下颈间羊绒围巾,把大衣拿到门边的衣帽架挂好,抚平褶皱。“今天如何?”他用带着笑意的声音问道,拿下眼镜用纸巾擦拭其上的雾气。罗可笑着看了他一会儿才回答。
“很好,”他说,扬了扬手中的书本,“看完了一本书,喝了三杯奶茶,每杯都按照你的标准,一块半方糖。”
“听起来不错。”
“有你在更好。”
门萨咧嘴而笑,眼角漾起讨人喜欢的深深纹路。他俯下身亲吻罗可唇角,金边眼镜当啷一声撞上柜台。哦,说起来这眼镜还是罗可送给门萨的四十岁生日礼物,镜框是极轻的合金材质,外面则镀了一层货真价实的熔金。门萨收到这礼物的时候着实惊讶了一番。
“这太贵重了,罗可,”他拿着眼镜的样子像是一下子回到二十岁,“你知道你不用给我买这么好的眼镜……”
“我想给我的丈夫好东西。”罗可回答,轻轻捏着他的肩膀。为此他一直存钱,苦恼了一月,才在门萨生日前一星期敲定。他当然不会告诉门萨这个,看着他喜悦的表情就足够了。
这礼物换得的比他所想要好,晚上他俩在洒满橘色灯光的卧室做爱,门萨从后头上他,一手握在腰窝,一手向上摸索直至覆盖罗可汗湿的手背,他的节奏平稳但有力,每一下都狠狠楔进他脆弱穴肉里,绞出透明爱液,淫如蜜汁。在此之前他给罗可口交,用上最大热情和最好技巧,仿佛罗可才是那个寿星似的。事实上多年来他俩做爱门萨都十分卖力,极力取悦罗可,给他懒洋洋亲吻,那姿态真是诱人极了。罗可这么想,也诚实说出来。门萨吮着他的腮帮微微陷下去,脸色像粉红柠檬水一般可爱,罗可在射之前抽出去,尽数洒到男人脸上,沾染那副漂亮的金边眼镜。门萨没摆出多么不赞同的神情来,只是无奈地笑了笑,伸出舌头舔舔粘在他嘴角的一点精液。
别告诉别人,但他们确实在这栋房子的每个角落做过:书架旁、楼梯下、落着灰尘的窗框、暖烘烘的卧室、放满绿植阳光灿烂的厨房、干净光洁的洗手间,还有一次等他们关了门、把百叶窗全放下之后,竟胆敢在柜台后的那张躺椅来了一发。罗可坐在门萨大腿,慢慢摇晃着,感受门萨细长的手指顺着脊骨抚弄。在那个狭窄的、屋顶斜下去的小阁楼上,他们布了许多塑料藤蔓和彩灯,一些杂物和书本乱糟糟散落在地板上,他们就那么做了,门萨除了裤链拉开其余衣物都好生穿着,罗可倒被剥个精光,抓住手腕按在地面。他十分享受这种感受,叫得肆无忌惮。叫声或许惊飞了屋顶上几只小鸟,他不是特别在乎。
我们竟也行至此处。他转头,看着同他一起躺在阁楼地板的门萨平静的睡脸,想道。
光芒爱抚他爱人脸孔纹路,那些精致线条,都是岁月所为的印刻,如同时间走过一只美丽钟表。他想伸手去触碰,一时竟有些于心不忍。门萨看上去那么年轻,与他们初见时别无两样。
门萨睁开眼,看向他。金色如朝阳初升般的光中他微笑,口唇张阖,拼凑出“我爱你”。
罗可知道他最近很累了。他一直为玛蒂尔达寻找她祖母小时的爱书,多日来东奔西跑。女孩又到他们店里来过两次,询问近况,更多的是为他们搬动书籍,处理些要紧不要紧的账单。罗可告诉她其实不必,她有些紧张地露出笑容,看上去像只从他手掌攫取葵花籽的小松鼠:“我只是真心想帮忙,先生。”
罗可叹气,给她账单和铅笔,在她停下工作按揉眉心时拿来奶茶和糖果。他与女孩各占一张躺椅,在柜台后头一待就是整个下午。他们谈谈书,谈谈城里发生的有趣的事情,偶尔谈谈罗可和门萨。女孩似乎对他们有些兴趣,但碍于礼貌并未明显表达,他心中暗笑,想着年轻也是这么好的一件事情。
“亲爱的,”有一次罗可忍不住和她提起,“关于那本书……我们一直在努力,但时间实在太久,如果我们真的没法找到的话……”
她的目光黯了黯:“我明白,先生。”她低下头将手搁到膝盖上:“我的祖母是个好女人,她一直非常开朗,照顾着我们全家人。自她生病以后,家里一下沉闷了好多。我是个会计,你知道,不挣多少钱的那种,没法为她做些什么……我想我只是想让她开心起来。”
“我相信只要她知道你的心思,就一定会感到很开心的,”罗可温和地说,“别给自己太多压力,好吗?”
“谢谢你,先生。”
她看上去脆弱又无措,几乎令罗可生出怜悯来。他往女孩手里塞了一块糖,看着她道谢,剥开糖纸,将糖果扔进嘴里,一边腮帮子因咀嚼满满鼓起。他还想着要说些什么来安慰她,这时门萨从二楼走下来,手里还拿着一沓清单。
“我要去买些杂货,一会儿回来。”
“好的。”罗可说,闭眼享受他俯身在自己面上一吻。玛蒂尔达站起身,拿过自己的外套:“我正好也要走了——我陪你一起去吧,门萨先生。”
“不用麻烦了……”门萨似乎本想拒绝,但在看到罗可的眼神后,有些犹疑地同意了。他帮女孩穿上大衣,让她挽着自己的手臂,在经过门口那摊积水时体贴地让她当心些(“这屋顶一直在滴水,我们总是忘了找人来处理”)。从背影看他俩有点像对父女。罗可在感到荒诞的同时竟不可抑制觉得有趣。
他去给自己泡了杯奶茶,倒水时瞥见茶筒旁边咖啡罐,为那想象中的苦味瑟缩了下。方糖罐半空,他捡出两粒,想了想,还是拿起黄铜小锤,将一颗砸成对半,合着完整的一块丢入杯中。他吮吮手指头,还能尝到上头的甜滋味,不禁对自己嘲讽地笑了。能忍受痛楚,却不能忍受变苦的味蕾。
他盯着糖块在浅棕色的茶水中慢慢化开。
屋顶上的鸟叫声又响亮了几分。现在他们几乎可以确定那是鸟儿的声音了,没有一种暖气管能发出大小三种不同的尖叫声。所幸它们不在半夜闹腾,不然罗可定会因为神经衰弱去掀了那愚蠢的屋顶。老天,坐骨神经痛就已经够烦的了。门萨看他气恼的脸,温柔地笑开,把他拉倒在自己身边:“你还记得我们刚到这里来的时候吗?”
他当然记得。他怎能忘记。他俩那是那样鲜润、美好、绝不无辜的年轻,无比破碎却又完整着彼此。刚开始很艰难,住地和吃用都靠他们断续打些零工,后来门萨被一家花店看上,给他们运送货物,罗可则在报亭找到一份叫卖期刊的工作。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公寓,连带着有了上司、同事和熟识的朋友,有了正常的生活圈。再后来,他们卖掉公寓,用攒下来的钱买了一座旧屋,稍作改造,一楼当作书室,二楼则是卧房,装上橱窗与招牌,把它变成一家书店,一个家。
门萨握着他的手,放到嘴边吻吻,眼神未曾离开他的面庞半分:“这么多年来,这个想法从没变过——能和你一起来到这里,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好的事情。”
“我也是,亲爱的,但我的版本有些不同,”他靠过去,让他们的额头碰在一起,像两个孩子密密絮语,“你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好的事情。”
他们颇有默契地知道不用再多说什么,温情脉脉地接吻。从门萨舌头上罗可尝到咖啡清苦,又湿又暖缠绕着他的唇舌,他发现自己无心抱怨,只在两人分开后半开玩笑半是真心地抱怨了一句:“我真希望伟大的主能让屋顶上那窝鸟赶快飞走。”
不知是否为回应他的祷告,到了周二,沿着水管传来的爪子挠抓声与叽叽喳喳的吵闹不知所踪,阒然从世界消失,罗可几乎怀疑之前那些都只是自己错觉罢了。他有些担心是否屋顶上的融冰终于把那窝小鸟冻死了,那可不是什么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发展。
玛蒂尔达来到他们的店里,身边还带了个身材粗大的男孩,她向他们介绍这是她的哥哥,是个建筑工人,这次是由她请来帮忙除掉屋顶上的融冰。罗可与门萨忙不迭道谢,那粗壮汉子已经架上随身的梯子,敏捷地爬上屋顶去了。罗可在下头仰头看着,漠然地想他会不会穿过那脆弱的瓦片直接掉进他们的卧室里去。
门萨在一旁询问玛蒂尔达她祖母的情况。“她已经走了,”那年轻脸孔流露出一丝哀伤,但眼神坚定平和,罗可有那么一瞬发现那眼神惊人的熟悉,“我……我们到最后一直陪着她,她走的十分安详,十分幸福。”
“很抱歉,我们没能找到那书。”门萨轻声说。
“不必抱歉,先生,我早该想到,对她来说,我们才是更好的慰藉。”这次她微微笑了,望着罗可,“幸好不算太晚。”
罗可对她回以笑容。一个脑袋突然从屋檐边探出头来:“我已经修好屋顶了——先生们,这烟囱旁边还有一个鸟窝,要我清掉它吗?”
“鸟窝?”罗可叫道,立刻想起整个不得安静的三月份,“什么鸟的?”
“呃……我想是知更鸟,先生,真稀奇,竟然能在城市里见到知更鸟,”男人的手伸出来晃了晃,“瞧,这有片羽毛呢。”
他松开手,那片羽毛轻忽落下,降落在罗可手中。他和门萨同时凑上去看,一片棕色的羽毛,靠近尖端有一片浅浅的白色斑纹,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但他们都微笑了。
他们竟也行至此处。
“劳驾留下那鸟窝吧。”门萨说,“没准他们还会回来。”他们的目光对上。罗可知道,待会儿回去以后,他将会把这片羽毛夹进一本书里,做成一张特别漂亮的书签,然后等待着,等待金色阳光照上人行道,春天终于来临。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