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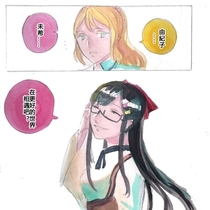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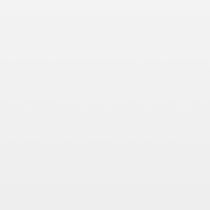




【低空飛過】
在天亮之前還沒什麼人,這時候走上略有些歪斜的石階,便能聽到自己的腳步聲格外鮮明。川端由紀子向上前行,感受著在孤獨中更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存在感。穿的鞋子是自己也叫不出名字的牌子,在這種情況下顯得有點磨腳,或許本來應該在來的路上更換更方便行動些的。
真的是失策。
山路上,植株早已失去了分寸,肆意侵佔這條由僧侶修建出的階梯。
那又是什麼時候的事情呢?
墓碑乾淨潔白,每個都很嶄新。沒有蜘蛛網,沒有青苔,沒有污垢,沒有雜草。沒有僧侶穿過這片墓地,也沒有個性化、寫著死了都要愛你的碑銘,一切都是嶄新的。
從死亡開始的嶄新。
三十個墳墓對應三十個人,一半已經填上,另一半則是空的。由紀子試著去尋找那座屬於自己的墳墓,她慢悠悠地穿過那裡。先前,這裡曾經是棵櫻花樹,現在卻已經沒有除了槲寄生外的任何植物在。
槲寄生的花語是什麼呢?
穿著涼鞋、走在山路上的由紀子莫名其妙地想起那件事來。奶奶的墳墓還有點距離,現在是清晨,只能從寺廟裡聽到和尚斷斷續續、帶著點慵懶的念經聲。自己是不是也曾在這條路上用同樣的方式走過呢?是不是也曾經被沿路的藤蔓絆倒過?夏日是不是曾經在回憶中好像要把人的靈魂給蒸走?是不是能在山間聽到鳥兒的叫聲?
那些細節她全部不記得了,只是覺得心的形狀要在胸腔裡頭融化了。
好安靜。
如果能一直這麼安靜就好了,但嘈雜才會表現出安靜,就像人們很難在沒有黑之前認識到白,在沒有高之前認識到矮。這樣相對的概念,現在就像一個拳頭大小的鵝卵石一樣絆住由紀子的腳。如果拋棄所有的二元論,事情似乎不曾發展成如今這幅模樣,但人們靠二元認識世界,認識概念,一切都會在邏輯盡頭相對。
她再往前走幾步,看到了那口蒼老、被人摸得表面光滑的大鐘,其金屬質地已經完全被人手上的汗液改造成溫順的模樣,只有在敲擊時才能隱隱約約意識到些什麼。
聲音並不是二元化的。在極響和無聲間,存在多個區間,證明了聲音並非只有人猛然抬起頭時能分辨出的那兩種。但這些區間的存在等於肯定了一件事,那即是人類觀測聲音的方式是軸向的。
與平等對立的不是不公。
由紀子撫摸著那塊碑石,一如撫摸溫馴的小狗,她的手拂過墓碑的邊緣,去感受對方的形狀和冰冷。無言的死者默許了她這樣褻瀆的行為,只是在沉寂中接納一切。
當人們聯想起平等,他們會想起不公。世上人不同存在千千萬萬,世上有富有的家庭,貧窮的家庭,漂亮的容貌,醜陋的容貌,生而體格健康,生而患有疾病,在種種對立中,人們產生了偏見,也就有了所謂的不公。
有了自我,也就產生他者。
但平等和不公不存在那樣的關係。
是這裡嗎?小時候被奶奶帶來的地方。
由紀子彎下腰去,她的視線在錯綜複雜的枝杈間尋找那個更為容易看見的。她曾經和奶奶一起進入這個地方,那時候奶奶指給她看路旁的野花。
“很漂亮吧?”
“很漂亮。”她重複那個字眼,把它嚼爛,吞下去,又吐出來,周而往復,想去理解那個字背後可能代表的含義。由紀子即使現在回憶起來,也會發現自己就是那麼一個愚笨的孩子。奶奶說的話也好,老師講的課也好,父母想要表達的某種情緒也好,都是在簡單地咀嚼之後沒有穿過她的心,自然也就沒有消化。
這樣的孩子,就算被父母長輩討厭了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啊,對了,雖仍然野花很漂亮,但是奶奶卻不允許她摘一朵下來。“因為那是神大人的東西。”奶奶那麼說,至於是哪個神,又為什麼因為是神大人的東西就不能摘了,也都沒有答案,只是老人家的堅持而已。
由紀子摘下一朵野花,把它別在胸前,繼續走向那口鐘所在的地方。
所謂的平等、平衡這回事吧,實際上是人類觀測世界的騙局。在人類的社會裡,不妨能看出多數標準不存在完美的整數。即便出身相同,經歷相似,也總會有些各種各樣的因素表現出些微的差別。
完全平等這件事是不可能的,這是個說起來很普通的道理,多數人不以為意。
那再舉個簡單例子吧。
兩個重量相似的水果,差不多重,被放在一個天平上,總有一方要比另一方稍稍重上一些,如果沒有,那就說明儀器本身還不足夠探明那或許只能以微觀單位計量的差距。
更換更精確的計量儀器,就會發現實際還是有一方更重些。再不停地更換儀器,只要其精度夠細,理論上不公都會出現。換句話說,就算是無限相似的兩個個體,只要同時存在在那裡,對立和不公就產生,自我與他者的界限就會被分明。
這時候如果存在著能將兩隻蘋果間重量差別補足的紙屑,或許就能挽救局面吧。
但這樣的補差沒有什麼意義,上頭多了紙屑的蘋果,本身的重量也不會有什麼改變。
如果能對蘋果起到安慰作用的話,或許也還算有點好處在吧。
你喜歡什麼這件事從一開始就定好了,你討厭什麼事也從一開始就定好了。
你根本不了解自己的才能,也不清楚自己會無能到何種地步。
就像風起時樹林會捲起枝條,魚兒隨波逐流,蘋果因重力落入泥土,以各自的方式失去自我。
由紀子撫摸那面鐘的銅鐵,想要從其中找出點其本來的面貌,但那口鐘被手指和遊客磨得發亮,再難表現出點什麼來了。
她歎了口氣,隨後在夏日的清晨推動那口老舊的大鐘,等待聲音進入骨髓,傳向遠方。
不公lim→0
=平等?

·正片暂时来不及弄,让我投个旧的给自己混条线索。
·时间线大概在企划开始的半年前或者一年前,没仔细算。
·在CB变CP的边缘反复试探。
·最后一段剧情发生在四章日常。
·BGM是lemon(...
“麻生啊。”
“什么?”
“你有女朋友了?以前你还会在社团露个面的,现在连社团都不来了啊。”
“哈哈,怎么可能。“红发的人拉开易拉环,把可乐一口气灌进喉咙里,带着刺激感的甜腻填满了口腔,他把易拉罐捏扁晃了晃,扔进了垃圾桶,”是工作,我放学会去接个人。”
“啊,之前说过的...钟点工?钟点工为什么要做这个啊。”
“我住那家伙家里了。”
“呜哇,不是吧,我猜猜,你是不是没要钱。”
“...你怎么知道的。不过那家伙出料理的钱就是了。”
“因为你从来不固定地住在某个地方啊,所以肯定不是你自己提出的要求。上次我请你去我家不也是这样。说真的,为什么啊?”
他愣了一下,看着友人一脸好奇的表情,他打开手机确认了一下短信,沉默了一会儿接上了之前的话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他长得好看吧。”
“.....你,我就觉得你不怎么喜欢女人,不会对男人有兴趣吧。”
“你猜啊。“他扑哧一声的笑了,然后低下头,闭上眼睛。麻生宙希枝清楚得很——他会选择呆在祭狩御灯身边的理由。那是不能对任何人说的吧,包括他也一样。这样想着,麻生的嘴角在无形之中挑起了一个弧度。
心照不宣地,避开了真实的答案,选择了默然。
——你有颗痣啊。
——是啊,你也想要吗。
那是他见到名叫祭狩御灯的医科生之后的第一反应。而对方显然没有把这件事记在心上——说的也是,把这个人和故人重合这种蠢事只有他自己知道就够了,他在心里嘲笑着自己。然后,在对方说出”你在这里住下吧”的时候,他感受到了一丝不可思议。在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里他是一个不可靠的轻浮男人,对此他感到极为不满但是也疲于去纠正。
而这一次,他倒是从祭狩御那嬉皮笑脸的表情里看到了一丝相似的感觉,人类都是喜欢与相似者群聚的生物,顺着这种相似性的趋势,麻生答应了祭狩御灯的提议。
但是那个时候,麻生宙希枝还是孑然一身。
当然祭狩御灯也是不会知道的,这个被雇佣为钟点工,做完应该做的事情就几乎不会呆在他家的人是怎样的来头。他只知道麻生是个孤儿,再多的信息麻生并没有透露的意思,他也不会去追问什么。事实上,最开始的三个月,除了必要的一些交流以外,两个人之间什么都没有。一个人在一成不变的继续着他并不感兴趣的医学学习,另一个人不曾停止地为了活着四处奔波。
只不过是,处于同一空间里不会交汇的两条直线罢了。
“他身体不好。“他继续说着,“你当成我是喜欢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也行。”
“哇塞,你可算了吧,我觉得你肯定是出点什么灾难跑的最快的那个人。一般人谁会找体育老师学一堆自保自救的招数啊。”
“哈哈,你真懂我,不过理由真的是这个啦。”但他还是在某个关键部分选择了沉默,且不说擅自告诉别人这件事是对不起祭狩御,那件事涉及到的某些黑漆漆的东西也是他不会撕开的——麻生宙希枝并不学得会这种表达方式,似乎从很早以前开始,他就选择了不与太多人交心的生活方法。那些人都是过客,麻生一边听着友人的闲聊一边这么说想着,至于祭狩御...
祭狩御。
他在心里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然后整颗心脏陷入了默然。
心脏病突发,麻生并不是没见过这样的事,在工地里工作的时候有时就会看到这样突然呼吸困难,捂住自己心脏倒下的人——他当然看不得,但是能够处理这件事的人总是会比他更快,他只要选择为那个病人松一口气就可以了。他不觉得自己会陷入和当年相似的某种焦躁,因为他不用伸出自己的手。
那么,该如何定义这件事?还是跟他无关吗。
当然不是。
他几乎是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换做平时,他能够很快地得出结论,这一次理性却被冲动毁的一干二净。那个时候他究竟是如何救助祭狩御的,祭狩御是何时被转移到医院的,他已经记不清了。他只记得自己在做心脏复苏的时候——那一遍遍的,没有人能听到的“别死啊”。只有他知道,他什么都没说,但他也是真的在大声嘶吼。
——别露出这么可怕的表情啊,麻酱,我不是没事吗。
苏醒以后,祭狩御看着麻生阴沉的几乎变成了青灰的脸,伸出手揉了揉红色的额发。
——我知道。但我不想看到你死在我眼前。
——嗯,谢谢你帮了我。
麻生宙希枝一定不会知道,他也无法知道,在祭狩御灯说出那句话的时候。他脸上闪过震惊之后留下的表情,就像是终于找到了灯塔的水手。
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变味了的吗,他想着。然后看向了蓝的几乎虚幻的天空,然后他伸出了手,又收了回去——不对,他想,要再往前一点。或者说,从一开始,这也许就不是简单的雇佣关系。
他原本是渴望着从祭狩御灯身上寻找一些能填补某个空缺的东西,当然那个位置是无法被替代的,有些记忆也是无法被抹平的。只是,借着少年的存在,让它变得浅淡一些罢了。——不,不对,他想。他看向自己的手,然后愣住了,最后他得出了结论。
也许,祭狩御灯才是向他伸出手的那个人。
最后一个隐藏在不真实的默然里的故事。
某个雪夜,少年倚靠在窗户的玻璃上,他觉得有点冷(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暂时没有可以支付冬装价格的资金)。他开始后悔自己一时冲动买了那样永远也不会送出手的礼物。然后他换了个姿势蜷缩在行驶在雪夜里的电车里,开始翻看起招聘网络。
——学生模特,我这一身是伤应该不行吧。
——照顾幼婴...会吓到他们吧。
——啊。
一条招聘小时工的广告映在他的眼睛里。
“麻酱?”
祭狩御灯的呼唤把他唤回了现实。
“啊,抱歉,我这就放你下来。”他把少年放下来,用和平时别无二致的语气道了晚安,接着转身离开。他悄悄地回过头,又一次地看向了那个人的背影。 然后再转回去,“...要是能留下就好了啊。”
“即使从一开始就做好了不留在任何人身边的打算,但是居然,有点想让雇佣关系持续的再久一点了。”
他缓慢地说着,声音融化在了空气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