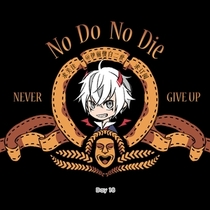
“颤抖吧,猛兽的獠牙将对尔等降下死之裁决。”
当小麦色肌肤的男人冰冷的做出宣告后,战争的号角正式吹响了。
违逆者从此受到了最冷酷的惩罚——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是香甜的梦乡还是安逸的午后,总有被猎食者追捕的恐惧笼罩在他们头上。
埋伏在阴影里的猛兽拱起脊背,利爪在地板上留下深深的抓痕,它耐心的静待着猎物失去警惕,那便是报复到来的时刻。
流畅的肌肉线条伴随着奔跑舒展收缩,巨大的力量在四肢中聚集,它高高跃起,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般凌空扑击而下,锋利的獠牙在阳光中闪烁着令人心寒的光彩,向着胆敢挑衅它威严的无知者施以残酷的制裁————————
“喵喵喵喵喵嗷——————————!”
“啊啊啊啊啊啊我的脑袋!我的脑袋!不要咬我头啊你这只蠢猫!救命!阿莱救我哦哦哦哦哦哦!”
“你别动!别转圈!哎喂!小开你停下你别动!你转成陀螺我根本逮不住这只猫它快拿后爪子踩死我了!”
“呜呜呜不就是不小心踩了它尾巴一脚吗!又是撕坏衣服又是挠穿沙发现在还咬我头!疼疼疼疼啊!”
“有空说话你先站着别动!别转了!站住!你在和猫使用合体技吗它在边咬你边用喵山无影脚踹我啊!快停下!”
“换你头上扒着一只猫试试……!我的头皮!头皮快要被扯下来了呜呜呜呜我要秃了!!!”
“我也快被踩死了这猫长这么胖怎么还这么灵活!……米奇!你别看报纸了快过来救人啊——!!”
坐在只有老祖母才会喜欢的扶手椅上安详吸猫的埃及人不动声色的看着这一团闹剧,干脆的给出拒绝援助的答案:
“这是贝斯特女神的意志。”
他怀里只比黑猫更胖的橘猫死沉死沉的压在主人腿上,赞同的摇晃着圆滚滚的大脑袋,赞同的说道,
“喵。”

在白沙与月光之间,青年睁开了双眼。
这是在无尽里重复的循环,过去的回忆早已化为混沌的泡影,唯一留存下的,只剩下关于此地的认知:在这片荒芜的乌有乡,一切都不会到来,万物都没有终结。
但这一次,他却听到了呼唤。
微卷黑发的青年俯视着他,朝着他伸出了手。他说,你该出发了。
那是熟悉又陌生的脸庞。青年试图从被遗忘的记忆里打捞出关于他的碎片,却最终一无所获。所以在不知多久的沉默之后,才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他问,去哪里?
青年皱起了眉。那是比起愤怒,更像被人从睡梦中吵醒的起床气,不会让人感到威胁,只会本能的压低嗓音迁就他的不满。他满不在乎的耸了耸肩,说道,随便哪。
四周的一切似乎鲜活了起来,青年第一次在沙漠里听到了风吹过的声音,看见了月光流淌在沙丘之上的涟漪。他忍不住笑了,追问道。总该给我个方向,否则我怎么知道自己没有走错路?
青年没有笑。他的嘴角向下撇的更加厉害,越发像个赌气的孩子。可他的面孔是那么成熟,气质也像是经历了世界末日的智者。他挥了挥手,无数的道路在他身后展开,割裂了沙漠,通向未知的远方。他说,不正确又怎么样?只要你前进,总能走到什么地方。
青年又陷入了沉默。即使在这个没有时间的世界,他也沉默的太久了。沙海在不安的躁动,月色也黯淡无光。而青年没有追问,他们只是如同海面上下的倒影,互相凝视着对方。
终于,他迟疑着开口,那你呢?
青年紧皱的眉梢被抚平了。一切再一次恢复了宁静。他朝着月光伸出了手,说道,我该入睡了。
青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或者该追问什么。他朝着其中一条荆棘丛生的小道迈出了小心翼翼的第一步,第二步……一步又一步。他的步子逐渐坚定了起来,属于过往的回忆也随之被心的海洋归还。
在还能看得清青年面孔的时候,他转回头,凝视着在沙丘上躺下,盖着月光昏昏欲睡的青年问出了那个问题。
“你……是谁?”
青年笑了。当他笑起来的时候,好像一切都有了答案。
“德克西亚。萨斐 德克西亚。”
“——和你一样”

塔娜是个快活的小姑娘。
和族里同龄的女孩一样,她能歌善舞,又勤劳能干。她的歌声像天边飞来的百灵鸟一样动听,当她挥动马鞭,最桀骜的烈马也要乖乖听话。
但她却有一个秘密:那个声音,一直在呼唤着她。
在每一个深深的睡梦里,在每一次她驱赶着羊群放牧时,总能听见那个声音从天边,或是从心底,一遍遍的呼唤着她的名字。
只有老祖母和小姑娘分享了这个秘密。老人告诉她,那是阿吉塔哈卡(Azi Dahaka),是恶魔的儿子,古老的大蛇,他的三个脑袋分别代表着苦难,折磨和死亡,他长着三只手,十八只眼睛,生着羽翼和獠牙,体内充满了蛇蝎毒虫,一旦放出,世界就会迎来终结。
老人用拗口的古语诵念那个名字,年幼的女孩没有听明白,只能懵懂的记下祖母循循劝导——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一旦你回答了呼唤,大蛇就会找到你。
她小心的遵守着跟老人的约定,任由那个声音一遍遍呼唤着她。无论声音是多么的动听,多么的亲切,都始终沉默不答,好像她不曾听到那个呼唤。
直到那一天。
女孩顺着藤蔓轻巧的攀爬到悬崖顶端,坐在月亮湖边梳理自己蓬软的短发,将雏鹰的羽毛做成发饰,装饰在自己雪白的鬓发上。那个声音再一次从湖面上响起,像是泉水奏响的乐曲声。女孩陶醉在歌声里,情不自禁的回应了呼唤。
刹那间,一切都改变了模样,狂风大作,黑云低垂,野兔奔进洞中,老鹰也飞回巢穴,万籁俱寂,只留下可怜的女孩在湖边瑟瑟发抖。
就在这时,黑色的影子从湖水中升起,那是一个漂亮的女人。黑发垂落在身后,铺满了整个湖面,蓝色的眼睛清澈又明亮,比湖水更加动人。她的模样是那样美丽,就像月光照射在桂树的树冠,让女孩忘记了呼吸,更忘记了恐惧。
来自水中的女人微笑着,比春夜里的微风更温暖。然后她抓住了女孩的手臂,像那些梦里和旷野里的呼唤一样倾吐出女孩的名字:
“我找到你了。”

少女在狂奔。
缀满宝石和缎带的华丽礼服随着奔跑拖曳在铺着红色地毯的蜿蜒台阶,雪白的蕾丝在月光下泛着柔和的光辉,像是人鱼公主化为泡沫的鱼尾,只有她亮蓝色的长发在奔跑里仍然奇妙的保留着原本的发型,还是海浪一般垂落在她的面颊和肩背。
钟声即将敲响,台阶尽头,站立在南瓜马车前的魔法师焦急的等待。当少女终于出现在他视野中,身穿黑色巫师袍的魔法师立刻快步冲上台阶抓住了少女。
在午夜的钟声里,两个人影从台阶上消失,仅留下一只遗落在台阶上的水晶鞋。
……
另一个时空,小公寓。
每次都把握不住平衡的两个人在门厅摔成一团,身着礼服的少女摔了个马趴,龇牙咧嘴的揉着滑脱了一只鞋时崴到的脚踝,涂抹着柔嫩口红的嘴唇一张一合,感慨万千的叹道:
“吓死爹了!”
显而易见,是一句男声。
魔法师好不容易才把糊脸的裙摆拽开,露出尖顶帽下年轻的面孔。他按着腰从地板上爬起来,没好气的丢个白眼给旁边的女装大佬。
“谁让你跑去玩什么心跳……之前几次传送都是两个人在一起,万一你在其他地方不能一起传回来,你就跟王子过一辈子吧。”
蓝发‘少女’似乎脑补了一下这个未来,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冤枉啊——我就想去看看传说中的舞会……谁想到那个王子跟八辈子没见过女人一样!最后还扯着我不许我走非要我跟他去见父母!最后还是靠尿遁才赶在十二点前跑出来的!”
“就那个女性身高平均一米九的世界……你这一米七几的个头,在那顶多一米六出头的王子眼里,可能真的是八辈子才能见一个……”
回忆着那个世界里男性较小可人女性高大魁梧的画风,两个人同时沉默了一会,女装大佬——宁祀才干笑着扯开话题,“……说、说起来,我的鞋丢那了……挺可惜的,还打算万圣节舞会上穿来着。不过王子要是也学灰姑娘里那货找人,估计这辈子都得单身了吧?那边的姑娘虽然个子大,要想找个47码的大脚也不容易。”
魔法师——齐格的嘴角抽搐的更厉害了。
“……你还记得请咱们吃饭的那个灰爷吗。”
“……那个胸围一米腰围也一米,把她俩一米八五的姐姐衬的特别小鸟依人的灰爷?”
“……对,就是那个扬手一推门就连门带门后的她爹一起扔飞挂树上,到咱们参加舞会时还在抢救的灰爷。”
“她……她老人家怎么了?”
“……其实你出门那时光顾着看她用沙钵大的拳头捶她亲爹胸口,没留神其实你穿的是她的鞋。”
“……等、等等,那不是说……”
“……嗯。而且我记得她娘站在一边特别慈爱的一边看一边说,‘我的小辛杜瑞拉真是个淘气的小姑娘’……”
“……”
“……”
房间里再次陷入死一般的寂静之中。
许久之后,两个人才心如死灰的同时感叹道:
“……童话里果然都是骗人的……”

最初,老修女以为是自己认错了。
上一次见到少年还是许多年前,那时她已称不上年轻,却并未像如今一样垂垂老去。
那是一个奇异的少年,在某个昏暗的午后,带来了一个同样奇特的故事。某个黑暗的、不应被触及的世界在他身后悄然打开一条门缝,又在少年如同烟雾般消失之后,重新掩上了大门。
她拿不清楚这是不是当初的少年。
那个模糊的面孔在记忆里早就被冲刷的黯淡失真,只留下被老修女执拗收藏在心底的单薄身影,和笼罩着身影的光彩。
那是某种奇特的氛围:
像是圣灵或者先知。像是那些被主选中,肩负着使命出生的特殊存在。
像是背负着降临自天际的圣光,像是暗藏着深不可测的黑洞。
还未老去的修女不清楚那是否是神所降下的征兆,就像年迈的老修女不明白此刻是否是命运注定的拜访。
她只是摘下老花镜,用干枯僵硬的手指捏住镜腿,朝着镜片哈了一口气,用同样迟缓的,慢吞吞的动作擦干净镜片。然后将眼镜重新戴好,认认真真的看着神坛下怀抱着花束,仰望天穹的身影。
黑色的大衣被不知从何处刮来的风起下摆,露出里面柔软的白毛衣,袖长的裤腿和马靴。墨色长发同样在风中舞动,带着某种这名青年身上特有的神秘韵律。
长发将青年的面庞遮挡去大半,可即便能够看得清,无论几次,只要看到光洁额头之下那双矢车菊一样温柔的蓝眸,都会让人忘记本来的打算。
光芒透过玫瑰玻璃投射在青年身上,让他如同行走在世间的圣灵,连脚下都映不出分毫阴霾。老修女有些糊涂了。她想不起自己最初试图去确认些什么,只是怀揣着感动赞叹着和神坛如此相称的一幕。
而当青年将盛开的蓝色花束搁在神坛,迎面向她走来时,老修女恍惚看见,巨大的光翼在青年身后舒展,漫天洁白的绒羽在教堂内飞舞。她是如此震惊,甚至直到青年与她擦身而过,消失在教堂门口,才终于回过神来。
唯一能够证明她猜想的只剩下门口的登记簿。
可当她将薄薄的本子反反复复的翻阅了好几遍,都未能发现那个她牢记了几十年的名字。
在本子的最后一页,只有一个用娟秀却有力的字体书写的陌生名字。
夏沃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