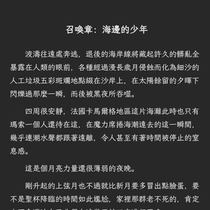本世纪的最后一个九月末,住在薛小昭家隔壁的疯女人飘了起来,升到了空中。这一天商业街上的人像往常一样工作或游玩,偶然抬起头往上看的时候,看到一个女人飘浮在百货大楼外。没有人看到她是怎么飘起来的,不知道她飘到那里确切的时间,至今也无法查证出她是谁。她飘浮在三十多米多半空中,身影倒映在百货大楼的蓝色玻璃墙上,有人跑到玻璃窗前去看她,发觉她像一尊凝固的飘浮雕像,两眼望着天空,没有表情也不眨眼。但她又很显然地是一个活着的正在呼吸的女人,是大街上随处可见的普通女人,除了她正像在漂在水中一样飘浮在三十多米的半空中。
薛小昭也到十楼的玻璃窗前去看飘起来的女人,因此他认出了这是住在他家隔壁的那个疯女人。她是一个老旧筒子楼里经典款式的疯女人,因为失去过小孩而发了疯,可能是流产,可能是孩子夭折,丈夫自然是不知所踪,亲人也全无,与成年邻居不存在任何交往关系,家里乱哄哄而且有说不上来的药味。她肚子很大,但是自薛小昭有记忆以来,她肚子一直这么大,所以大概得了什么肿瘤。和那些经典款式疯女人一样,她面对小孩很亲切慷慨,并且表现得更像正常人,因此偶尔会有像薛小昭这样不听话的小孩偷偷跑去她那里吃零食。飘浮事件发生的前一个假期,薛小昭窜了十公分个头,导致他在疯女人这里的优渥待遇大打折扣,后知后觉意识到疯女人真的会发疯的薛小昭已经几个月没有去过她那里。
薛小昭认出这是隔壁疯女人的时候,人类飘浮事件已经在台南传得沸沸扬扬,他和几个朋友花了全部零用钱积蓄买票,又排了很久的队才在百货商场的十楼观赏到这一世纪末奇观,此时距离人们发现女人飘在空中刚刚去三天。因为他认出飘浮的女人是他的邻居,这个奇观的神秘感顿时大打折扣,显得有点莫名其妙,相比之下反倒觉得商场楼下成群结队穿着统一印花汗衫的“真谛教”教众更像某种奇观。它在台南是个有些规模的新宗教,在女人飘起来后他们迅速赶来,信誓旦旦地宣布这个女人是真谛的教徒,她的飘浮是教义的体现、人类进化的证明。在多次把女人弄下来的尝试失败后,信念大受打击的警察竟然默许了他们的集会。
在十楼的玻璃窗前,薛小昭也信誓旦旦地向朋友们宣布这个女人是他的邻居。他的所有朋友都笑了,没有人相信他,并在之后的几天里叫他牛皮薛。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人在楼下膜拜这个飘浮的女人,也有成堆的人爆料飘浮女人的身份,但没有任何信息获得证实。行走在地上的人为此疯狂,给这个现象想出千百种故事和理由,设计各式各样的方案抓到她,只有女人飘浮在空中,不说话,不动弹。
回到家后薛小昭和父母提到了这个女人。他百分之一百地确信这个女人是隔壁的疯女人,他的父母认为这是青春期的哗众取宠。实际上父母根本不记得隔壁的疯女人长什么样。直到隔壁人家发出有人孤独而死的尸体恶臭前,他们都会假装楼里的疯子不存在。
不被任何人相信的薛小昭在接下去的日子里透支了全部零用钱和自己尚且稀薄的信用,想尽办法去看飘浮的女人。他不知道自己除了光看着还能做什么,但总幻想突然有什么事情发生让他能证明自己没有吹牛,他真的认识这个女人。他每三天能攒够一次门票,前两天只能在楼下挤在人群里,像公鸡一样伸长脖子,从人缝里看半空中人形的黑影。他看到脖子发酸,天色暗了,什么也没有发生,就惺惺地回家。攒够了一次门票,他就到楼上看,十楼的视野差不多能和女人的高度齐平。女人直直看着天空,每天去都一样,疯女人和薛小昭记得的样子也一样,只不过她还在地面上时会神经质地怪笑,会塞给薛小昭很多零食,会突然抱着枕头喊宝宝,宝宝。薛小昭看到她的肚子还是很大,其他人也早就注意到了,这也是另一支教派和真谛教争夺这个女人的关键,那支教派坚称这个女人是要在空中诞下救世主的新世纪圣母,但他们描述的场景太过猎奇,所以受众不如真谛教广泛。
这些都超过了薛小昭在这个年纪能理解的程度。他看不懂成年人在做什么,只能每天像上学上班一样准时来看这个女人。
薛小昭期待的奇迹发生在十月中。这时候人们几乎已经习惯头顶漂浮着一个女人,也隐约开始厌倦这种毫无意义的飘浮。她只是飘在那里,什么也不做。所有人都和薛小昭一样期待某些奇迹发生。这天薛小昭攒够了一张门票,能够在十楼看疯女人,他照例看到商场关门,赶在清场前去了一次厕所,从厕所出来的时候,整个楼层空无一人,清场的商场员工和警员也不见了。他觉得自己撞了好运,跑回到玻璃窗前,结果被拎住后领子抓了正着。抓住他的人听上去比薛小昭还要惊慌,向后面大声嚷嚷:“怎么还有一个?”
薛小昭听到空旷商场里传来两个人的脚步声,要么是两个人,要么是几十个人分成两队严丝合缝地齐步走过来,脚步听上去就有那么重。那两个人走过来,其中一个女人捏住薛小昭的脸端详了一会儿,问:“你认识她?”
薛小昭愣了片刻才意识到她在问自己,点头回答:“她是我邻居。”
“吃过她给的东西?”
“以前有……”
女人也点头。薛小昭背后的人放开了他,原来是一个穿着高级警服的男人,他只看得出这身警服看上去比街上的员警高级,也不晓得到底是什么级别。警服男人擦了擦汗,问:“这是怎么回事?”
“吃过她的饭,一时半会儿忘不掉她,过一阵就好了。”
警服男人松了口气,懒得再管薛小昭,催促他们:“那快开始吧?”。薛小昭决定不去猜要开始什么,至少这些人相信他真的认识这个女人。外面天暗了,玻璃上反射室内的倒影,很难看清那个女人。往常薛小昭都要趴在玻璃上。
女人说:“你催他,我也不知道他要怎么搞。”
“九点三十二。”一直没说话的男人指了指手腕上的表,“还有十五分钟。”
然后他们就被尴尬的沉默包围了。玻璃窗外的女人在做一尊敬职敬责的雕像,神秘的男人和女人抱着手臂望着外面,薛小昭想尽可能降低自己的存在感,避免三个成年人突然想起他算是个无关人员。尴尬把时间变得特别漫长的时候,警服男人终于忍不住了,问:“她真的大肚子啊?不会真的要在天上生小孩吧,那种场面我兜不住的喔!”很遗憾,在场没有人用笑声回应他的暖场。他又问,那她飘在那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是薛小昭也非常想知道的。女人说:“现在说了等会儿你也不会记得,这不是浪费我口舌么。”
警服男人有着令人钦佩的死皮赖脸,或者他和薛小昭一样被不理智的好奇控制了,他说:“但我现在真的非常想知道,等会儿忘掉了正好帮你们保密啊。”
女人看上去同意了,大概是沉默的十五分钟对她来说也很无聊。但这件事显然很复杂,她想了一会儿要从哪说起:首先,她叫张月仙。
由于疯女人张月仙现在正飘浮在离地三十米的高空,神秘女人所说的离奇故事也就不那么像在胡说八道。张月仙确实是因为失去小孩发疯的,但六十年前她失去小孩的时候还没有这么疯。至于为什么她看上去只有四十来岁却在六十年前失去过小孩,属于商业机密不能告知。总之,张月仙还没有那么疯的时候,决心研究怎么让失去的小孩回来,或者退一步,再获得一个小孩也是可以的,但商业机密改变了“张月仙”的体质,二十多年里不管她换什么样的身体,只要她是张月仙,就不可能再孕育出新生命。
警服男人问,你刚刚是说她换了很多次身体?
神秘女人说,这不是重点。她说话很有说服力,换身体听上去真的不像是重点了。总之,张月仙二十多年的无数次失败让她的精神变得很不稳定,也失去了家族的帮扶,沦落成那种居民楼里的疯女人。发疯的张月仙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这次她大概是获得了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所以就有了现在这一幕,她飘到了天上。
“这就没有了?”警服男人问。
“这还不够详细吗?”神秘女人反问。
那当然是什么都没有解释清楚,还增加了新的疑问。人到底是怎么飘上天的,飘在天上的张月仙肚子里又是什么呢?神秘女人只好戳了戳那个一直不说话的神秘男人,“我也想知道她是怎么上去的。”
神秘男人说:“她把自己的重量剥掉了,自然就飘上去了。”
没想到神秘女人大惊失色起来,说:“那她现在岂不是……?”
“岂不是什么?你们这样吊人胃口讲话真的很讨厌。”警服男人因为被告知自己一会儿就会失忆,现在变得非常肆无忌惮,还拉上了缩在一旁的薛小昭,“什么叫剥掉重量,小孩都糊弄不过去,对吧小弟?”神秘女人突然也加入了他们的阵营,三道目光一同望向那个男人,男人倒没有什么表情,问,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灵魂有重量?几人点头,男人言简意赅地解释说,你们可以理解成灵魂有重量,张月仙的灵魂太重,婴儿的灵魂挤不进她的身体,只会变成死胎,她就发明了一种办法把自己的灵魂剥掉。剥掉了灵魂,身体变得很轻,她就飘起来了。
警服男人说:“你骗人,尸体也没有灵魂,尸体怎么不飘起来呢?”
男人回答他:“那为什么要把死人关在棺材里埋在地下?因为不埋下去天上就会飘满死人。”
他说话也很有说服力,让警服男人和薛小昭都在震惊中回味这个景象,一时说不出话来。他趁着这时候打开了一扇玻璃窗,高楼风顿时涌进室内,把警服男人和薛小昭吹得东倒西歪,那对神秘男女却纹丝不动,令他们显得非常专业可靠。男人卷起袖子,露出的左手小臂上有三道红色纹身,神奇地发出红光。神秘女人也看到了,惊讶地问:“你怎么弄到的?”
男人说:“专利科技,细说要收费的。”
神秘男人将半个身体探出窗外,将发着红光的手伸向飘在天上的张月仙。在他之前警察和消防员都试过从这扇窗把飘浮的女人拉进来,她明明距离这扇窗不到五米,消防员却怎么也够不到她,据说这个超现实的现象把好几个消防员吓得休了长假。现在飘浮的女人好像被磁石吸引的回形针一样缓缓地朝神秘男人的方向飘过来,距离男人的手只有一臂之遥。就在薛小昭以为可靠的神秘男人要把她拉进来的时候,女人在空中爆炸了。严格来说不能算物理上的“爆炸”,但薛小昭想来想去觉得只有爆炸这个词最贴切。她砰地一声开始逐层分解,先是头发和皮肤整个离开她的身体,裂成碎片,像小行星带一样环绕她的躯体;然后脂肪和肌肉一条条向四面八方抽离出来,抽离的轨迹正如电影里慢镜头播放的爆炸,这时候可以看到她的肚子里确实有一个僵硬干瘪的胎儿,然后胎儿的僵尸也分裂了;神秘男人用他听不懂的方言念起了唱词一样的句子,女人身体的碎片随即凝聚成一团无法形容的东西,他将手伸进这团东西里面。然后再一次砰的一声,这团曾经是一个女人的东西像爆炸后的烟雾一样消散掉了,男人像变戏法一样,将一个抱着琴、戴着笠帽,穿得像古装电视剧角色一样年轻女孩从那团东西里拽出来拉进了室内。薛小昭想,太糟糕了,不管他怎么描述,都不会有人相信他看到过这样的场景。相比之下,没有人相信他认识飘浮的女人这点事显得极为微不足道。
本世纪末的最后一个十月,薛小昭梦见住在隔壁的疯女人飘了起来,飞到了天上。他坐起回忆了一会儿这个梦,梦里的细节随着他的回忆反而越来越模糊。他想自己大约是睡昏了头,隔壁从来没有住过人。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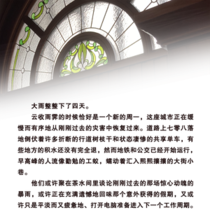

【迪士尼回引导剧情】
(但从时效性上已经并无什么卵用了所以我就是赶在二轮结束前色一下一轮的李道长。)
=====================================
“……迪士尼?”
李道长重复了一遍。他的表情有几分迷茫——当然是相当克制的迷茫,至少他还记得面前这张脸:在他刚焦头烂额地被一纸公函塞进这场圣杯战争里来的时候,徐汇天主堂的本堂神父郑重其事领着他见过的那一张。
“是的,迪士尼。”怎么看都像是还在念初中的少女安闲地合着双目,语速不疾不徐,平稳地说着些令他感觉头皮逐渐收紧的内容,“复仇者的魔力波动正在稳定地向那里移动。除此之外,已经有复数以上的从者在那里聚集。我认为她正是被这数骑从者的魔力吸引而去的。”
李道长心想他到底怎么能在脑子里持续有什么东西发出高分贝尖叫的时候维持住脸上的表情,可能是人类的脑子在一下子被塞满足够多东西的时候会腾不出空间来处理这个,他在想浦东地区的特殊事务紧急联络人是谁他10号晚上吃饭的时候应该加过微信叫什么来着还有路政局的王局在出闵浦大桥那事儿的时候脸就很黑这次南浦大桥可千万要保住坏了要不还是发通知先把地铁停了,然后他猛然意识到裁决者还在看着他。
或者说,“看”着他。女孩静静坐在他前方的沙发上,双手放在并拢的膝盖上,细密的睫毛依旧阖着,然而李道长就是没来由地感觉自己正在被审视着。他下意识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毕恭毕敬地把腰挺直了,措辞谨慎地问:“您的意见是……?”
女孩没有马上回答。她似乎期待对方主动提供更多的信息,不过张道长圆滑的缄口倒也没有令她太过失望,只是略微停了一会儿才开口。
“5月11日的凌晨,”她说,“我感知到复仇者的气息在延安高架上与其他从者争斗,当时我请求本堂神父准备车辆送我前往,以便阻止她对战局的破坏。然而在进入高架之前的路口我们就被拦住了,通告上说的是‘临时道路检修,延安高架全线封闭至上午12时’。”
“……噢。”李道长一时说不出来更多的音节。毕竟这通告是他写的,为了盖到公章他晚上十一点半还在给八个不同的负责人挨个打电话。
“而当天晚上,复仇者又移动到了外滩附近。这次我们动身得很早,拐进延安东路的时候,狂战士还没有打开他的固有结界。但是啊……”裁决者轻轻地拉长了尾音,似乎若有若无地,甚至露出了一抹笑的影子,“上中山东一路的时候,有交警把所有往外滩方向的车拦了下来,依照规定,入夜查酒驾。”
“呃……”李道长尴尬地摸了摸鼻子。交警大队的报告他还拖着没写,市政的损失评估表倒是昨晚半夜里勉强填完了,但还没吃完早饭他就已经陆续接到了四个分贝很大的电话轰炸,大意很统一地是你这个数字也太过离谱了通不过,绝逼通不过,谁有本事批你找谁批去吧反正在我这里通不过。
“李道长。”裁决者微微仰着下巴,平静地说,“记得您来访天主堂的时候曾经说过,冀望本届圣杯战争平稳举行,能够将对普通市民的影响降至最小化,尽可能地隐匿神秘的存在。作为本届圣杯战争的裁决者,我想我们的目的并没有太大的分歧。”
他大略应该或许估摸着是说过这条,李道长窘迫地回想。虽然措辞上大概得是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置于一切争斗之上……这类的官样文章,他当时根本没想过圣堂教会供的这尊大神真的会下场,还以为只是拍几张照片,走个流程拉倒。哎哟,仔细一想他可能还顺口说了什么组织会为主办方圣堂教会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援助这种常见的套话所以……
“所以我希望能够基于这点共识,向您请求一些协助。”
李道长清了清嗓子。他突然觉得需要吞咽一下口水来湿润一下发干的喉咙,脑子已经违背他的意志开始在后台运算起这部分新增的成本需要如何均匀分摊到还没来得及提出反对意见的部门。民宗委?不对还是该按照实际项目划入应急管理……
“具体是需要哪个方面的……?”他颤颤巍巍地发问。
李道长其实不大拎得清英灵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小红召唤出来的骑兵性格豪爽,但也并不太爱听管束。他没好意思直接问圣堂教会的本堂神父你们的裁决者是不是当真看不见,不够熟。不过他很确定坐在他面前的这个看起来是小姑娘的英灵一定有她特别的方式能读到自己脸上为难的表情。
因为她轻轻笑了一下。
“我需要尽快赶到迪士尼。”她坦率地说,“复仇者的出现是本次圣杯战争中最大的变数,我希望能和她好好谈一谈。迪士尼是个很合适的地方,因为那里的……布局,有些特殊,或许不一定马上会发生从者之间的战斗。”
李道长绷紧的肩膀松开了一点点。公务车费用和迪士尼门票这点小事他想有关部门应该是可以给报销的。应该吧。“应当的,应当的。我们马上和迪士尼联络一下,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第一时间闭园疏散……”
裁决者犹豫了一下,补充道:“如果可以提建议的话,我不建议你们现在关闭这座乐园。”
李道长的肩膀又重新绷紧了。
“聚集在其中的游客为乐园带来的欢乐情绪是驱动这个魔术阵地的主要动力,贸然抽离这种情绪很可能会破坏这种‘迪士尼的魔法’。”
“……‘迪士尼的魔法’。”
李道长重复这个词组的时候就像他一开始听到迪士尼三个字的时候一样懵逼。然而女孩只是偏了偏头,微微一笑:“沃尔特·迪士尼是一位优秀的魔术师这件事,我以为你们早就知道。”
她站起身来,礼貌地向李道长轻鞠一躬,然后消失在沙发边上。
也不能说是消失,李道长意识到。她从来没有真正地出现过,那个沙发其实自始至终空无一物。他长出一口气,抹了一把脸。
……文旅局的联络人姓什么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