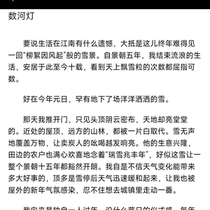作者:蓝天
评论要求:求知
今天是平平无奇的一天。要说和昨日有什么不同,那便是我定了早上六点的闹钟,不像平时总是踩着早读铃声进教室,而是在天还蒙蒙亮、校门还没大开时就钻入了教学楼。
这当然非我所愿。才刚开学,大冬天的,谁不乐意在温暖的被窝里多待一分钟?但没办法,这学期我当了思想课的课代表。虽然是副课,但中考也算进总分,加上这学期的思想课老师还是我们教导主任,这下大家就只好乖乖地听课、回家写练习册了。
教室窗户本就是朝北,外面天色暗沉沉,教室里更是像个鬼屋。我开了灯,顺便按了电脑和投影仪的开机键,然后来到自己的座位,把书包挂在椅背上,掏出书本文具,堆在面前。有些住得远的同学已经陆续来了,他们问我怎么到得这么早,我苦着脸伸手:
“思想课作业交一下。”
按理说,也不是不能等人都到齐再收作业,但我提前来的另一原因,是不愿意抱着一沓练习册去教导处时面对教导主任。我问过高年级已经毕业的学长学姐,得知了如果在第一节课上课前就去交作业,此时教导主任多半在走廊里巡查,不会留在办公室。我是极不想和她单独相处的,只好趁还没早自习,积极地把作业收了,没交的人就留个字条附在练习册堆上吧。而且,每周思想课的次日是语文早读,多半又是要全班齐声朗读课文。我的牙套昨天刚把我嘴里又刮出溃疡,用交作业的名义还能少受点罪。
离早自习的开始时间越来越近了,走进教室的人也逐渐多起来,我有点来不及追着每个人要作业。还好那些平时就被老师评价为“自觉”的同学们会主动把练习册放在讲台上,我只需要去骚扰别人就行。
我走到第一排靠门的座位前,居高临下地看坐在那里的同学。
她正埋头面对着一张几乎崭新的数学卷,从第二页的几何题可以看出,那是昨天的回家作业。她左手边的课桌大部分被课本占据,剩余的地方可怜地挤着另一张昨天的数学卷。那张倒是写得满满当当,只是从字迹就能看出并非她自己写的。
“你抄完这张记得自己去交思想课的练习册。”
想也知道她昨天放学后又大玩特玩去了,我当然不指望她能交上作业,只是出于课代表的义务提醒。
她还在“苦战”数学题,撂下一句“给我本参考一下”。
“那不行,曲老师说第一节课前就要交的。”老师说过这句话吗?其实我也没印象了,“而且我昨天看了参考答案,很多题都是‘略’。大家都是乱写的。”
“好吧。”她不馁,学着后桌试卷上的标注在例图上画辅助线,却连歪了。
我看到刚走进教室的那几位都拿着练习册走向讲台,于是在门口多逗留了一会儿,看她从脏兮兮的笔袋里掏出一块灰色的橡皮,费力地擦那条线。
没啥意思,我再找她聊天也是给她拖后腿,交不上数学作业还得怨我。我返回讲台,点了遍练习册的数量,和教室里还空着的桌椅对了对。还有一分钟开始早自习,差不多可以抱起这摞练习册去教务处了。
我走过通往行政楼的连廊,左右排着一块块各班展示的黑板报。那是上个学期期末,学校响应“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号召举行的知识科普宣传比赛项目之一,竟就这么放了整个寒假,粉笔写的字迹都模糊不清了。我们班当时负责做板报的同学,正是第一排靠前门、回家作业在学校做的那位。
不得不承认,她画画很好。之前她有给学校公众号发的文章画过封面图,也经常被美术老师找去参加比赛。我还看过她发在网上的画,她私下里爱画金发双马尾、像动画片里一样的美少女。一起上体育课时她也找我聊天,告诉我那都是用鼠标在电脑上画出来的,把我吓了一跳。
但是,我不太喜欢她。
她总爱讲她那校外的男朋友,也不好好学习。我之前去年级办公室找班主任拿我们班的学生手册,听到老师们谈论她“下学期摸底考分班,又会掉到普通班去吧”。我倒有点期待这样,因为上学期刚开始,她居然超常发挥进了提高班,而我的好朋友没考好,在普通班待了整整一学期。
来到教导处门口,见门虚掩着,我也省得腾出手去开了,喊了声“报告”便侧着身推门进去。哪知里头传来了干巴巴的“请进”,我脚下一顿,但箭在弦上,只能硬着头皮去面对教导主任。
没想到这才刚开学没多久,教导主任——这身材矮小、剪着短发,看起来凶凶的女士——少见地没去教学楼到处视察。我喊完“曲老师好”,她停下手中“噼啪”打着字的文件,扬扬下巴:
“放那里就行,收齐了吗?”
我把练习册码在办公桌对面的矮柜上,报了几个名字,加上一句“他们还没来”。
教导主任回了句“好的辛苦了”,又在我准备溜走时叫住我:
“你志愿填了哪两所?”
“第一志愿是二中,第二志愿是师大附中。”我老实回答。
“不试试去冲一下更好的市重点吗?那么多奖状,只要中考正常发挥,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我跟我爸妈商量了,他们说还是稳一点好。”
“嗯。”曲老师好像认同了这句话,又语气一转,“放假回来胖了啊。”
我怕的就是教导主任突然温柔下来,但能做的只有附和:“过年回了趟老家……”
“体育中考完再放开吃吧。”
“嗯。”
这倒不用她担心,我们学校自从发现卷面成绩拼不过老牌民办初中后,就另辟蹊径、大兴体育。每天早操都要跑圈,每节体育课都要测长跑,初三下了晚自习还得列队再跑个一圈半。我看的网络段子里总讲体育课被其他主课占领,这在我们学校(至少体育中考之前)可从没老师敢做。体育课强度上来后,坐在教室里写卷子反而变得舒适了。
离开教务处,我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我也不喜欢思想课,对那些参考答案写着“略”的主观题更是深恶痛绝。只不过是死记硬背的速度快些,才勉强考出了不错的成绩、误打误撞拿到几个二三等奖。去教务处拿奖状次数多了,被曲老师眼熟,因此被指派了这课代表的职位。
但又想想,若不是我,班里其他同学也没有会去主动担这个任务的。
“自觉”的同学们不敢,靠门第一排的那位懒得理老师,我的好朋友——甚至不是这个班的,也管不着。
我在空无一人的走廊里猛冲几步,又突然刹车,体验惯性所带来的滑行的感觉。如果是雨天,这湿滑的瓷砖地板一定会导致不少事故。现在要是面朝地摔倒了,牙套会把嘴里扎得血肉模糊吧,我还是没再继续这么自娱自乐。
一点都不想回教室。我干脆蹲下身,认真看起别的班的黑板报来。
我像石窟中的考古人员一样努力辨识着那些字迹,虽然内容都大差不差,那比赛里的知识问答题我也记得滚瓜烂熟,但比起写了什么什么精神,我更注意的是横竖撇捺。这一块黑板上的字很秀气,旁边那块的想用粉笔写出连笔来,另一块的写得用力不少……直到早操铃响,我才反应过来自己翘了整个早自习,急急忙忙往教室赶。
每个班都在教室门口列好队了,我挤到里面,装作没事人一样。
身后的同学问我:“你怎么去了这么久?”
“曲老师在教导处,她把我留下来说了点事。”我面不改色,“章老师没奇怪我早自习不在?”
“我们说你去交作业了,他就没管。”
前面的队伍挪动起来,我们也跟着往楼梯处涌。经过教室前门时,我余光瞄了眼最靠近的位置。
她显然成功抄完了数学作业,课桌中央已经没有那张卷子了。当然也没有思想练习册,因为她正趴在那儿睡觉。这也不出意料。她总是用来月经的理由请假不去做操,或是体育课不跑八百米,把体育老师都惹急过一次。现在,老师们知道了她这德性,也知道叫家长无济于事,只能嘴上说两句了。
我稍微——只是稍微,有点羡慕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