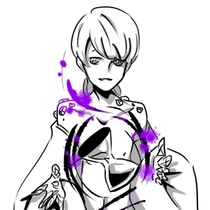前:http://elfartworld.com/works/163598/
三.【3876年 秋入冬 塔國南端】
貝弗特沒有回答,或許是因為自己無法想像被當成祭品的感覺,也不知道自己能否為了一個看起來從不管事的神承受如此折磨。本想開口問關於昨晚那個夢,可是心裡那點微小的猶豫阻止了他,就怕那不是一個毫無意義的斷片。
如果只是帝國的事情就明白多了。
鐘聲迴盪,他們走過長廊,路上碰到的祭司並沒有對他們投以太多關注。今天的霧看起來比較稀薄,倒顯得陽光有些太強,是個對祭司們來說非常理想的天氣。石柱的陰影在余光之中飛掠,偶爾被碑打斷。正如伊凡思所說廣場上集結了很多人,卻無比安靜,伊凡思帶他爬上階梯,直到末端不再通往橫向的走廊,而是被一扇小門阻攔。
“怎麼辦?回去嗎?”貝弗特回頭,總感覺自己正在做見不得人的勾當——雖然當初是伊凡思提議到樓頂去開晨禱的。祭司抬手,讓貝弗特讓開,寬鬆的袖子下仍是那詭異的黑。“都警告過你別穿出來,被當成異端真是活該。”
“這種話不能亂講,在教廷裡隨便叫人異端是很危險的,說不定哪時就會被扔進火坑里。”伊凡思握住門把。咯噠一聲,門便應聲彈開。“你看,很方便吧。”
貝弗特在門檻前猶豫了幾秒,快速地確認背後沒有人才踏上樓頂。“跟著你後都忘記驚訝是什麼感覺……教廷還會處置異端?不是已經變成帝國的責任了嗎?”
“帝國也沒有認真在執行啊。”伊凡思笑笑,一邊在四周尋找。貝弗特站在建築邊緣想下眺望,霧裡也是伏著許多人,比夢境中更多,穿著各色排成一列列,也像帝都中的軍人和朝臣。以七個主祭為首,祭司們面朝東邊,日出的方向。
“這種話也不能亂講,說不定哪時就會被我掛在鉤子上。”他回答,視線外伊凡思放下兩張凳子,大概是很久以前就藏在樓頂某處,木頭看起來有些老舊。
“你知道紅衣本來也是教廷的職位,很久很久以前統稱‘審廳’。”
所以那時他才以為自己在工作……貝弗特在心裡說。“我們借這個形象處死叛國者,教廷不介意嗎……你不介意嗎?”
“畢竟王法僅次於教條,維護王法沒有不妥的地方。”他停頓,“而我……大概沒資格介意吧。”
伊凡思坐下,傾聽靜默。這嚴肅的氣氛讓貝弗特也不想出聲打擾,幾十甚至百人以相同的姿勢定格成一幅畫,移動的只有不斷升起的日輪。他感到有些無趣似的環顧四周,除了掛在桿子上正在晾乾的床單什麼都沒有……
不對。貝弗特瞇起眼睛,遠處有個身影,也在觀察廣場上的活動——居然也有別人敢不出席早禱,他只是這麼想,估計是個侍童或者輔祭。不久後那身影站起,離開了屋頂。此時主祭也同時起身,繞過列隊站到通往祭壇的樓梯前,眾祭司隨著轉向,然後他們開口,齊聲誦念教條和訓誡。誦讀的語調平緩,沒有起伏,整齊地好像不是人聲,雖然不能稱得上響亮卻足以滲入土地,彷若帝都的鐘聲,連遠處的人都能依稀感受到腳下細小的震動。
“我以為早禱不出聲。”
“早禱結束了,他們要開始選祭司長,主祭必須得先宣誓和發言,不過每一次內容都差不多。”
一個主祭走上祭壇,伸出雙手懸在火坑之上,右手拿著匕首,在左手掌心劃開一道口子,幾滴血就順著滴下,被黑暗吞噬。他轉身,將受傷的手舉起,開始他的宣誓。
“我小時候,這廣場最多也只有不到半百個人,一共只有兩個主祭。”伊凡說道,“他們都很嚴格,我記得我曾經不止一次想把他們從祭壇上推下去。”接著他笑,輕快地像一個小孩子。
“原來你也會有這種想法。”
第二個主祭走上祭壇,重複了一遍剛才的程序。伊凡思睜眼看了下,捏著佈滿藍紋的手指,好像對這個人特別有興趣。明明昨天還用骰子決定人選,他想,但這也似乎是第一次聽這人提到小時候這三個字,他一直都覺得伊凡思跟自己年紀加減差不了太多,那語氣卻是在回想久遠的過去的語氣,是個令人怎麼也不想主動去翻找的舊物。“為什麼你不做主祭去選祭司長?既然祭司做得那麼憋屈——”他問,帶著讓自己有些後悔的蠻橫,“我不懂,你基本能算個壇長,陛下邀請你主持帝都的初冬祭,而且我想你大概一時半會也死不掉……你也不需要做異類,你去過殿堂,甚至認識領主,把事實攤開,還有誰可以刁難你?真的只有我覺得這都沒道理嗎?”
“不,有幾個人也這樣建議過。我不想和教廷有過多來往,況且我做主祭對他們來說就太不公平了。”伊凡思聳聳肩,注意力從第三位演講者身上轉移,在廣場上悠轉,在東面停留了一會,又回到了祭壇上。他向貝弗特保證將來有一天他會懂的,但貝弗特有種預感這一天不會來得很快。
“你睡吧,結束了我再叫你。”他最後談嘆了口氣說道。
正午的廣場空無一人,大部分的祭司都轉移到室內的會堂進行投票,伊凡思也跟著去了,一邊走還一邊搖晃著揉眼睛。貝弗特繞著石碑轉了一圈,他看不懂上面刻鑿的文字,但大概能認出那是古語的形狀。要是當時認真地聽就好了,他喪氣地揉了揉額角,想起很久以前在城堡裡偶然聽見的課堂。
不知道伊凡思會不會讀古語……總覺得那個人會什麼都不奇怪。
廣場比遠觀來的更遼闊,在薄霧之後就直接是懸崖,沒有護欄的保護,向下望去便是大海,四千年不斷沖刷崖壁的白浪在土石上咬出凹穴。他蹲下,將手擋在眼睛上方來阻隔日光,視線的末端隱約出現一點棕色。小船?他站起來。從這裡下得去嗎?既然無法用正常手段到達殿堂,那要船做什麼……
貝弗特吸氣,轉頭本想開口,可是身邊卻沒有說話的對象。不知不覺就習慣了,也不太好啊,他對自己說,紅衣,執死,可能身邊就不該有個這樣的人。他慢慢地走回教廷的建築,途中和薩姆謝打了個招呼,耳朵貼在會堂門上聽了會辯論。
“無聊的話就去樓上看看吧。”守門人經過身後時這麼說。“三樓正中間是圖書室,你看起來是會對那種東西感興趣的人。”
“謝謝。”貝弗特朝他點頭致意。
“早上闖上屋頂的是你們兩個?”
他聽見後愣了一下。“是。”他回答,心裡已經準備好要遭責備,不過對方似乎並沒有這個意思,只是揮了揮手,要他們下次要犯事就犯得隱蔽一點。
“等一下。”薩姆謝離開之前貝弗特又拉住他。“我還看到另一個人在屋頂上,不過我不確定是誰。”
守門人只是悠哉地聳聳肩。“哦。反正也管不動,跟我說有用嗎?”他說完就走了,走向廚房的方向。貝弗特立在原地,心臟警告着他應當為此擔憂,可是大腦卻告訴他也不可能有任何作為,這些憂慮都是空的,全是被三年前那一晚嚇出來的後怕。
暗殺王公貴族還有理可循,可是殺一個普通的小祭司究竟能得到什麼……
普通嗎?真的只是一個小祭司嗎?
貝弗特的手撫過樓梯的握把,乾淨的不沾一點灰塵,只有被無數隻手磨出來的褪色痕跡。活在教廷之下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感覺。他悄悄推開書房的門,希望不要驚動任何人,裡面的燈都是熄滅的,唯有自然的光照亮內部,聞起來一股古舊紙張和皮革的氣味,可是光線下也沒有一點塵埃。貝弗特暗自羨慕能在這種地方長大,他大概會願意用一切來換取這個機會。
一本本的書冊排列在眼前,從新到舊,各種經典的手抄本甚至是原版,所有關於教廷的記錄,寫滿歷史和曾經的預言,連在艾登先帝毀滅的那些都保留了下來。他隨手翻開一本,脆弱的皮革在手中已然是最珍惜的寶物。他簡略地翻閱,然後將書放回去,又去尋找別的日期。
三四八零年大災,三五二九年王祭,異象記錄,二六零八年教派分裂,黑影之眷屬研究,狂言解讀……
二五年領主親臨?
“你——”
貝弗特聽見叫喚便轉頭時下意識收回手,對方已經在他旁邊蹲下,是一個金髮的年輕人,穿了亞麻色的衣服,灰藍的雙眼讓他想起雷納西的晴空,他沒有立刻回應——那張臉帶來的熟悉感令他一時反應不過來。
那綁在鐵架上的少年,和面前的人是如此相似。
“怎麼不說話?”那人問,“你是那個客人對吧。”
貝弗特有些疑惑地點點頭。
“我臉上有什麼嗎?”他摸了摸下巴。
“對不起……”貝弗特這才回過神,轉移目光看向並排的書脊,“你和我曾見過的一個人很像。”
“真稀奇。”那人回答,一邊伸出手,“我叫耶爾頓,是個輔祭。”
貝弗特和他握手,乾淨的手掌上也沒有傷痕,這叫耶爾頓的輔祭雙眼也都是完好的。巧合嗎?他想。“我是貝弗特,來自帝都。”
“我知道。”耶爾頓笑,就連嘴角揚起的樣子也都過於相似了。“每個人都知道。畢竟是伊凡思帶來的人。”
“他似乎人緣不太好。”
“惡名昭著呢。”輔祭靠向書櫃,從蹲著的姿態換成坐在地上,順手將凌亂的頭髮向後撥。“不過他好歹也算是我的老師……”耶爾頓稍微低下頭,語氣也隨之變得比較沉重,“雖然聽起來很冒昧,但三年前老師他在帝都遇害了,是嗎?你也在場吧,我沒想說別的,只是想謝謝你。”貝弗特感到喉嚨中被什麼堵住,看來教廷中消息傳得不比帝都慢。
“其實我什麼都沒做……”他說,聲音有些沙啞。他的確什麼也沒做,當時他只能任自己被無力和絕望吞噬,拼命抓著最後一點希望似的按著將死之人的傷口。“你知道……有什麼人會想殺他嗎?”
“應該不是私人恩怨,不只老師遇害,有很多祭司都被刺殺,雖然大多職位都更高一點……”耶爾頓思考了半晌,“大——”
“那是因為他們違反了教條。”
貝弗特和身邊的輔祭一起轉頭。
書櫃之間的走道另一端站了第三個人,絳紫長袍及地,襯出他嚴肅的面容,好似個將軍一樣充滿威嚴,微仰的下巴令他能俯視前方的一切。
貝弗特鞠了個躬。“午安,亞內主祭。”
“午安,願上主降指引於你。”主祭抬手,讓貝弗特直起身子,又看到耶爾頓,神情有些不悅。“我沒見過你。”
“主祭大人,這是我第一次來教廷。”輔祭回答,緩慢地從地上爬起,這時才向主祭敬禮,“見到主祭大人真是我此生的榮幸,我聽老師講起大人您許多事,請問夫人和愛女可都安好?”
亞內主祭臉上的惱怒之中閃過一絲不解和窘迫。他咬了下嘴唇,“是……她們都很好。”
“但願主上的榮光照耀,導她們向正途。”
主祭點點頭,下一秒就將注意放在貝弗特身上。“聽說你當時在場,你想知道為何有人要殺帝都的祭司對嗎?”
“是的,大人剛才說他們違反教條,可是……我仍不理解。”
“帝國有責任處理帝國中的異端,但是若祭司本身被混亂蠱惑,則不屬於帝國的管轄範疇。”
“大人是指……教廷要殺伊凡思?”貝弗特講著都覺得奇怪,在另一方面如果這是事實的話他必須要趕快帶伊凡思離開這個地方。“卻仍要請他來參加會議?”
“不,”亞內主祭回答,“教廷也已經不負責懲戒祭司的信仰不忠,殿堂自會派來使者執行審判。伊凡思活了下來,主祭們認為他目前還被殿堂所承認。”
這就是為什麼刺客可以在帝都城門裡為所欲為而不被發現,也是為什麼明明擁有領主贈禮還受重傷……嗎?他對自己說,殿堂又為什麼要審判那個人?他以為伊凡思和殿堂關係應該很好……沒有回答,當自己問殿堂是什麼樣的地方的時候,並沒有得到任何答复,自己當初也是這樣默認伊凡思和教廷的關係,或許自己太自說自話了一點——
耶爾頓的笑聲打斷沉默,也打斷了貝弗特越發混亂的思緒。 “大人,你這樣……不怕真的遭難嗎?與其說這些誣衊的話,怎麼不和我們的客人講講一百年前發生過什麼事情?”年輕的輔祭退後一步,壓低音調,“我跟你說,在首都搬回羅爾帝那會,也有個主祭,名字我不記得了,反正也是個不怎麼樣的傢伙,私下和古物交易,妄圖欺騙主上,結果呢?一夜間失去五感,內臟在體內消融,妻子生下雙頭的畸胎後也去世,幾代的報應連第二代都沒熬過——大人,你說什麼叫做天罰?拿著刀潛入別人家暗殺是天罰?”
主祭的臉因為憤怒而變得蒼白,“放肆!”他抬手,卻因為貝弗特在場而收住。“輕信謠言還大肆宣揚,立刻給我到地下室去悔過,並且抄訓誡十遍,明日我親自檢查,否則我讓人將你禁閉一周!”
“行,行,大人說了算。”耶爾頓再一次敬禮,臨走時回頭給貝弗特一個帶有笑意的眼神——如果還有明天的話。他的口型這麼說道。亞內主祭似乎沒有注意到對方最後的留言,緊鎖的眉頭將不快表露無遺。
“對不起,有些年輕人就是疏於管教,只會給教廷蒙羞。”
貝弗特不敢回答,此時居然有些尷尬,心裡只有首都剛搬回羅爾帝的年份,就擺在手邊的書架下排,他伸手就能抽出來看,三七六三,或許還不會很準確,能再往後找幾年。
“你也不要隨便把故事當真。”主祭說,“這裡的資料都很珍貴,拿來看的時候小心一點。”
“是。”
書房的門關起,伴隨鐘聲和此起彼落的腳步聲,看來祭司們開始從會堂裡出來了。他坐下,一口氣取出五本書冊,迅速翻閱,年份,事件和地點不斷在眼前變化,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可以讀得這麼快。
然而這時第五本書冊的封底印記已經靜止在他視線之中——什麼都沒有找到。
殿堂的使者前來審判叛教的祭司……不過那個對他們伸出援手的黑影又是什麼?那個無法用常理理解的存在的確隱約符合王座廳玻璃窗上刻畫的形象,帶有發光的藍紋。可另一方面它卻又讓他憶起自己不聽勸告去偷穿伊凡思黑色披風的時候,瞬間就被囈語佔據思緒,精神被推至狂亂邊緣的可怕……第一反應便本能地認為兩者是同樣的東西。
是來自領主的承認?考驗結束的獎勵,責罰之後的慰藉?
還是那其實是一直被稱為混沌之物……
這怎麼可能。
“見到亞內主祭了嗎?”晚上伊凡思一回到房間就開口問,把貝弗特嚇了一跳。他已經換好睡衣,看來是比自己更早就結束了一天行程,臉上寫了疲憊——也是,對伊凡思這種作息規律的人來說一夜未眠比什麼都累人。
“為什麼?”他回問道,心中無比雜亂。
“下午被主祭責備了一番。”
“抱歉……”貝弗特向後躺下,心裡其實沒有真的在道歉,更不在乎自己做錯什麼。他沉默,思考許久又翻身。“伊凡思,我問你問題,你這次能不能好好回答?”
對方聽見他的語氣比平時嚴肅不少,不禁露出一些擔心的神情。貝弗特看他緩緩站到梯子上,扶著床緣,“我什麼時候騙過你?”
“不是指騙,就這次,別給我模糊的答案好嗎?”
伊凡思微笑。“我試試看。”
貝弗特盯著他半晌,忽然發現他也和夢裡的少年也有一絲像,擁有相同色調的頭髮和雙眸,或許是年紀的緣故不如先前的輔祭那般神似。伊凡思身上也沒有傷疤……應該說若真有人受了那種傷是不可能好好活著的——他曾聽說過人會將記憶的殘像拼湊成夢境,此時他開始認為昨晚大概正是這樣的情況。“我看到懸崖下有一艘小船,從那個方向航行什麼地方都到不了,你不是說從這裡不能直接去殿堂?”
“不能。”伊凡思回答,“但是來還是可以的。”
“我還遇到一個叫耶爾頓的輔祭,說是你學生,他還說兩百年前有個主祭因叛教遭天罰,失去五感,內臟消融,是真的嗎?”
他聳了聳肩。“現在的我已經沒有學生了。不過那個故事是真的,只是被教廷掩蓋而已。畢竟是很難堪的醜聞。一個主祭私下和古物交易得到不該得的力量,最後把妻兒和親族都搭進去——如果是普通人,可能就不會這麼淒慘了吧。”
“領主會親自懲罰叛教的祭司?從殿堂派使者下來?”
“會,可是很少,使者偶爾會被殿堂派來處理小問題,主上大多數時候都是直接降詛咒——很可怕的,會持續好幾代呢。”
貝弗特將下一句話暫且吞了回去。所以耶爾頓也沒有在胡說,亞內主祭也不是憑空捏造一個理由……那麼他到底該相信誰?突然伊凡思拍了拍他的臉,“你今天問的還真奇怪,誰跟你說了什麼嗎?”
“沒……沒有。”貝弗特回答。
“那就好。”
伊凡思爬下梯子,吹熄房間裡的燈,貝弗特聽見他躺下的動靜。至少今天會好好休息了,他這麼對自己說,然後閉上雙眼,任意識順著睡意流進深邃黑暗的海洋,連同四肢和身體一起下沉,直到周圍的現實都不復存在,留下源於自身的破碎幻想來填補空缺。
少年的臉。
匯集成河的血。
突然一聲巨響,半個教廷的人都應聲而起。
【全場就只有bft懵逼】
【於是這是第一次提到喜鵲的出生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