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滑铲保命,还没改完!(痛哭)
—————————-
调整好重新发过了,食用请走http://elfartworld.com/works/9254245/ ,鞠躬!
——————
“——您叫我?您敲棚顶是在叫我,对吧!”托马笑嘻嘻的脸出现在车窗外,倒吊着探头往马车里瞧。
"杖击墙壁,通常用来表示愤怒。"奥斯顿阖眼不看他,紫檀木杖搁在座位上:“不许怪叫。”
“您不喜欢?”
“闭嘴,树林要被你吵活了。”
雕郁金香纹饰的黑马车疾驰在往菲尼克斯堡的林道上,领头那老马识路,赶车人的位置空着,缰绳松垮地束在一处。春夜清冷,矮灌木枝叶未丰,早春的花却已凋敝,车道边只耸着黢黑沉寂的栎木林。托马盘踞在车顶,彼时春狼似的嚎了一嗓子,惊扰起一群多疑的林鸦,翅膀扑棱棱棱,扯碎了薄若蛛网的一丁点温存。
“如您所愿!”嗜血把头嗙一声磕在窗框上,“这就闭嘴,我亲爱的奥斯顿。 ”他头发枯槁成灰白色,只剩额前一绺红卷发,明火似的跳动在夜风里,一对儿圆眼睛滴流转,双手就叩着车身敲起鼓点儿来:嘭啪,嘭啪,叮啷咣当砰砰啪!
奥斯顿先前只觉得托马这木刺戳得脑仁疼,这回简直被鞋后跟跺在了神经上。那疯狗见他挑眉便停了手,三两下扯紧车窗帘,泥鳅似的溜进马车厢。车厢里雍容温软又舒适,薄绒毯拥着小靠枕,软垫子齐整排在座位上;托马随手把细软的全推下去,挤着奥斯顿坐下来。
“您在看书!书讲的什么?”疯狗语气里透着股欢快劲儿,把他紧簇的眉头当摆设:“跟您讲吧,我爱天鹅绒!您生前吃烤天鹅吧?李子酱得配蜂蜜……”
也许吃过,但他不记得味道。奥斯顿像拾贝的海鸟那样捡掇着问题,只简短答道:是本冬与春的诗歌集。他一手拎起托马的脖颈子,把天鹅绒斗篷从那家伙屁股底下救出来,郁金香绣饰全压褶了,可怜巴巴地皱成团。马车猛地颠簸,有狐狸擦着头马的蹄子窜过林间道,身后牝马受了惊,发出高亢的嘶鸣声。
听起来很像在笑。
疯狗不等他问罪,抢过披风丢到对面座位上,脑袋一拱撞进他怀里,白头发蓬蓬地搔着下颌窝。
“你——”
山野的味道。杂草,泥巴和树根,他在林子里打过滚。“你发什么疯?”
“这味儿嗅着不像。”
“你在说什么?”
“冬天是冰的,春天是嫩的。”托马两只手乱比划,鼻子凑在书页上,深深吸气:“这儿可嗅着像死的,潮的霉味儿,铺地牢的枯草堆。”
奥斯顿瞪着他。“这是本老书。”
“噢,给我尝尝!”绸面书被抽走了,托马把它举得老高。七八张枯纸页翻过去,他大声念道:“——光似稠蜜淌过小巧双乳,红润樱桃挺立峰上;徜徉镜湖,绿地游荡,雏菊、百合和郁金香——”
“不成体统。”
奥斯顿手指骤然攥起。那疯狗喉咙里溢出吠笑似的呜咽,诵读声戛然而止。“你识字,很令我惊讶:但他们该先教你学会礼节。”锢托马心脏的血链骤然收紧,厮磨着蚕食软内脏,发出细小黏腻的窸窣声 。
“当众诵读非常失礼。除非,”他指尖微曲,缓而慢地蜷转,牵引蛇似的血链:“我允许。”
血蛇吐出舌齿间稀烂碎的心脏,卷着肺叶把胸腔翻搅浑,直绞得血从疯狗的喉管往外迸,把紫绒软座染污了一片。
【许愿。许愿让我停手,戒指魔法还剩两次,不要耗尽我的耐心。】*
奥斯顿侧身半倚着靠垫,右手撑住下巴,斜睨对方汗涔涔的额头。
【也允许你跪着求饶。】
但托马突然抬手指着块斑渍,喊:“咳!这儿有条狗,咳嘿嘿……”他被自己逗乐了,笑声掺着血沫子溅出来:“唔咳嘿嘿嘻嘻嘻,脏狗霸占了好垫子!”
“够了!”奥斯顿把鞋尖从血雨中挪开一点:“闭嘴。滚出去。现在。”
栓狗的链子松开了。
对方不等命令再重复,一躬身从窗口窜出去,但却用右脚尖勾住了木窗框;他左手趟着车底矮草转一圈儿,眨眼又不知死活地钻回来,叉腿蹲坐在绒垫上。
“瞧!”托马拿衣袖抹净嘴边的血,扯着烂嗓子快乐地嚷:“瞧啊,春!”他那爪子硬往奥斯顿眼前凑,把教训全抛到脑后;拳头里攥着一小把杂草,细长叶儿衬着精瘦的杆,穗串龇出柔茸毛,蓬尾巴似的晃悠悠。
古血皱起鼻子。“最后一次:滚。”
“别客气!闻闻味道!”
狗尾草白日里吸满了太阳光,慵懒的春味儿直往鼻子里钻。它被兽掌马蹄子踏过,也给很多车轮子碾过,可就是趾高气昂地高翘着,管他叶子尖儿肚儿碎糙糙。
奥斯顿动了动嘴唇。滚开,他想。滚。
——————————
*注:老套的用戒指能许三个愿望的故事,预计在第一章【冷雪夜】的下半部分,还没写完……

被带来参加所谓的“宴会”时,系莱茵并没有想到这个宴会的场面会如此的让人脸红心跳,她想的是在金碧辉煌的殿堂里面觥筹交错,就如图教会上次开在百合花广场的晚会一般,虽然她没有被分配到附近,可是隔着很远也能听到悠扬的音乐,仿佛能看到人们华丽的舞姿。所以在坎来接她的时候,她以为'父亲'只是来弥补一下她的遗憾,虽然坎不去提及,可是系莱茵知道父亲总会猜到她的想法,并且将她的遗憾一一填补,她是如此深信着。
可谁来告诉她,眼前发生的又是什么?
那叠在一起的赤luo的肉体,紧紧嵌合难舍难分的唇舌,不断的、让人异样的声响,肉眼可以触及的地方无论什么样的搭配,男男女女都放纵的起伏。离她最近的地面上还有可疑的ye体。
鼻尖萦绕着幽幽缠绵的香气,像是要掩盖什么,又像是要引起什么。
穿着比自己睡衣都还单薄的布料,系莱茵恨不得把自己整个人都缩在坎的斗篷下面,她甚至大不逆的想着要把坎的斗篷扯掉披在自己身上,手上暗暗加劲。
坎低头,感受到系莱茵的小动作,却没有理会,他环视周围,寻找他想找的人。倒是一边穿着蓝色篷篷连衣裙的高个子女性注意到了系莱茵,他微微弯下腰,和从坎斗篷里暗戳戳掀开一角往外看的脸红少女对上了眼。
“你好啊…小女孩”低沉的问候从那人的嘴里吐出“我是艾维斯,你呢?”
“!”系莱茵吃了一惊,她发现这个有着齐肩柔软红发的人并不是女人,而是实打实的成年男性!虽然自己的父亲也身着女装,可很显然坎在打扮上毫不上心,他不过是找了一条老气横秋的绿色长裙套上,然后用斗篷一盖便自觉已经换装。可艾维斯不是,他的穿着华丽而繁重,脸上还有着轻微的淡妆,带着长沿礼帽,如果不是他完全不掩饰的喉结和低沉的声线,即便是身形相比其他女性确实有些宽硕,也完全可以说是一位非常美丽成熟的女性。
“你,你好!我是系莱茵…”对方身上的气势和父亲很像,但不知是不是女装的缘故,她总觉得比起父亲,艾维斯似乎要更加温和一些,加上他之前与坎的对话,系莱茵弱弱的问:“你…你和我父亲是朋友吗?”
“朋友?艾维斯的声音很低,就像是害怕惊扰什么小动物一样“…我想是的,我是你…父亲”他说到父亲这俩个字的时候表情有些微妙“…的朋友,那你呢?小女孩,你又为什么被他带来这里?”
系莱茵暗暗的抓紧了坎的斗篷,身子往前探了探“我也不知道…”眼睛一下子看到在艾维斯身后交叠在一起的人影,努力的把视线全部集中到与她对话的人身上,问道“艾维斯先生,你和父亲很早就认识吗?我第一次见到他有朋友”说着声音便小了下去“父亲很少和我提及自己的事情…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可以和他交谈的人,很高兴认识您!”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艾维斯点头“说实在我看到坎带着你也吃了一惊,身为古…”艾维斯看到坎扭过头来对着他摇了摇,于是换了个说辞“孤独行动的人,我也没想到他会有个人类女儿。”
人类女儿这种显得有些多余的说法让系莱茵感觉到一丝别扭,不过比起这个,她有更加好奇的“您是怎么和父亲认识的!还有…父亲他平常会做什么,您知道吗!”
这些问题显然不像是处于女儿角色的人会问出来的,更像是一个陌生人在试图了解另外一个陌生人,若是父女关系,这未免有些太生疏了,艾维斯短暂的沉思了一下,还没等他想好怎么回复,便被接下来的行动打断了。
坎发现了他要找的那个人。
他弯腰把缩成一团的系莱茵卡着胳肢窝托了起来,这种动作比起托人,更像是托一只巨大的猫咪“稍微等我一下”对着艾维斯说完,便丢下他径直往目标走去,斗篷的一端还被系莱茵抓在手里,拉扯时露出裙子以及黑色高跟鞋。坎没有走的很快,长裙限制了他的行动,却走的很稳,穿着高跟鞋也没有影响 ,不过系莱茵在慌乱中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她被平稳的托到一个人面前,然后放了下来。还没等她站立住,便感受到一道极其强烈的视线投在了她的身上,如同被最凶猛的野兽盯上了一般,即便她低着头甚至是没有看见对方,都已经寒毛倒竖头皮发麻,人类的第六感发出尖锐的警告,让她赶紧逃离危险,即便这只是一道目光,仅仅只是一道目光。
一秒,又或许是几分钟,几个小时,直到头顶被一只宽大的手盖上后,那种让人害怕的情绪连同怖人的视线便消失殆尽了,取而代之的安心感让人也逐渐能收到到周围的声音。
“这是系莱茵”手的主人说道“薇帕拉,我想在这种地方,她是个不错的人选。”
对面沉默,系莱茵被按着,她只能低头看着地面,除了坎的黑色长袍,便是那金贵华美的长裙一角。
这是个女人,她猜测, 并且,光凭这一角布料就可以看出,这是个极其奢华富裕的人,她从未见过如此细腻的布料,即便是在这种不太明亮的地方,它也显示出惊人的光泽,似乎本身就在发光一般,不知是何等稀有的材料制成。
对方没有很快回复坎的话,看不到二人的表情,话音落下后的沉默便让人觉得煎熬,系莱茵等了一会儿,才听到对方的声音。
“坎”
像是有颗洁白的珠子掉入水面,在光滑表面与水接触的一刹那后荡出阵阵波纹,回响在耳畔的这声如同水墨般迅速晕染在脑海,便是摄魂的塞壬也发不出比她更让人难望的声音了,与之一同涌起的是胸膛中激烈的情绪。
这种情绪用一句话来说就是:
太好听了!
这是系莱茵听到后最直观的感受。
她克制住自己抬头的欲望,却被一柄长扇轻轻抵住了下巴尖,坎的手不知何时放开了,对方稍微使些力,系莱茵的头便被托了起来,视线一一滑过堆积的裙摆,纤长的双腿,一手可握的腰肢和高耸的胸脯,滑过女人的脖颈,下巴,红艳的嘴唇,尖窄的鼻梁,最后坠入对方的眼眸。
民间编撰的传说中,希腊神话里的蛇发女妖,“有死者”美杜莎有一双动人心魄的美目,凡是和她对视之人,无一例外会被夺取魂魄,变成一尊石头雕像。
系莱茵觉得自己大脑已经停止转动了,在最后的意识里,她告诉自己——
你的魂魄已经深陷紫与红的漩涡里面无法离开,而身体,则将变成无主的废石,再也没有了意义。
—————————————————
送完系莱茵,坎回到了同伴身边,伸手挥了挥四周缠人的香气,脸上不辨喜怒。
艾维斯把手臂搭在坎身上,身旁不知何时站了一个年轻女孩,编着漂亮的麻花辫,眼睛滴溜溜的到处乱转,见坎走过来,更是毫不羞涩的打量着来人,眼神清澈而自然,比起之前一直躲在斗篷下的系莱茵,她看起来更加的天真有活力。
坎注意到了对方。
很年轻的血族小孩,从样貌上看和系莱茵差不多大,他想。
“坎,这是我的子嗣,维奥拉。”肩旁的鬼亲切的介绍“才刚成为血族”
“看得出来,她被你保护的很好。”
坎把手放到嘴上轻笑了一下,他还能闻到手掌心那熟悉的,来自人类的香甜气息。
“你好,维奥拉小姐,我是坎。”他笑着和朋友的子嗣介绍自己。
谈笑间,坎吹开掌心残留的气味,像是吹走一片灰尘。
…
寿命短暂的人类,永远也看不到长寿一族的相处的场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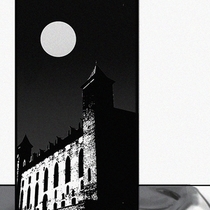

微微微微型保命卡
——————————
从马车窗帘的缝隙透进来的傍晚太阳昏暗的光。
同时担当车夫驱使着三匹骏马、那三位女仆叽叽喳喳的八卦声隔着轿厢的壁透了过来。
可以称之为宽阔的巨大轿厢内,正中央的茶几上放了盏随着马车颠簸而跳动火苗的玻璃油灯。
以及。
作为客人,并没有对马车主人指指点点的权利。
如此这般不动声色地一边听着争执声,一边在心里叹气的克里希亚,抱着双臂、双眼无神地任凭目光被穿不过的窗帘阻挡,思绪顺着那束视线往马车外面跑。
是了,这辆巨大的,一看就知道是哪个富人家所拥有的马车。需要三匹非常强健的马来拉动,整整六个坚固的车轮才能托起轿厢,然后轿厢之内……
却只有那么一个矮小的白发的少女面露嘲讽之意,和另一位把厌恶神情尽数写在脸上的白发少女争锋相对。
她们在争论的事情跨度从面包要不要涂黄油到世界的毁灭与否,锋芒毕露地交互了无数个回合。克里希亚闭了眼,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她们的争论声上,但至少擅自闯入他耳中的那么几件事里,这两位少女连一个能达成共识的事都没有。
有那么几次,她们的议题多少涉及到点让他的耳朵为之一动的东西,几乎让他差点脱口而出“够了”,以一己之力喝止二者毫无意义、谁也说服不了谁的争论,然而他期间只是睁开眼,撇着视线多看了那始终戴着顶帽子,把自己半个脑袋都遮得严实实的更加年幼的少女几眼,从她眼里看出更多的讥讽与漠不关心之意,便又收了制止二人的心思,且当回他的客人罢。
而这个决定让他度日如年。
“……”
他的手情不自禁往腰间移,一丝不好的预感随着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升起;克里希亚摸了个空,他便低了头,带点疑惑地看向自己原本别有佩剑的地方,又在下一秒反应过来——信任是当今世间绝不会被忽视的难题。
无论如何,夹杂在争论间的只言片语里透露,马车主人与其护卫似乎因前者的临时起意,更改了原本的行路计划,仅在正庆祝重生的猎人工会附近停留了片刻,为那些浴血保卫战争的猎人们送了些对她来说聊胜于无的物资,马车主人仿佛是因此事才在之后的路途中对其护卫不断地恶言相向。
而应邀搭上这辆华贵的顺风车,却带着武器乘上“重要人物”的马车,于情于理都有些说不过去。所幸存在着所谓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结果,他的武器被放在了这趟横跨纳塔城、顺路通往教会方向的马车的一角,由另一位担任马车主人贴身护卫的工会猎人保管。
虽然看起来她一点保管的意思都没有,光顾着和自己的雇佣者吵架。那柄剑孤零零地躺在白发猎人右边靠近马车门的地方,会把注意力放在它身上的,这个轿厢内除了他以外,就连刚刚从车夫那边选出来进轿厢报告路况、顺便合情合理地以照顾小主人的名义在轿厢内休息一二的女仆其一都对此毫不在乎。
抑或说。
那个女仆加入后,原本就足够混乱的争执更加混沌。不难听出她一点为小主人和小主人的护卫劝架的意思都没有,更甚至有开开心心地再添柴加火的意味在里面。
克里希亚只是静静地、坐如针毡地,在心里叹了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