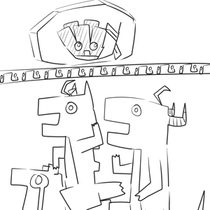茨格姆企划三期
这次是更加完整的世界观
估计也是最终回啦!
目前是2052年的高科技时代!
参与者需私信审核人设
审核通过后加入企划
——
企划群:245552006

计字2016,这么巧就发了吧【喂
-----------
3.
山下的城市还亮着,灯光汇聚成人工的银河,仿佛城市的血管。
如果那是血管,里面流淌的是汽油和电吧,男孩这么想过。
月亮升得很高了,夜鸟在空中清啼着飞过,不远处湖面闪着银光,冷而无情。
腕表指向一点整,旧历年已经过去了,似乎仍然有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传到他耳朵里,偶尔还能在黑漆漆的天幕下看到几朵孤零零的烟花。
苍白的烟火亮了亮然后灭掉,像是生命那样周而复始,大概是城市的脉搏。
“新年好,今年晓晓缺了一份红包啊。”他对手中的枪低语,声音里带着温和的笑意。
4.
天气很好,碧空如洗,层林尽染。
海晓风背后背着个厚厚的包,手上拄着徐若霖拿给他的那根登山杖,粗细挺顺手,只不过有点长,差不多能到他肩膀。徐若霖那根更长,已经超过了他身高一大截,看得海晓风浑身难受。
“你不就比我高几个公分,拿那么长一根棍子不嫌别扭?逼死强迫症了你。”他磨着牙,恨不能把那根登山杖直接掰成正常的长度。
“习惯就好,反正我已经习惯了。”徐若霖朝他摆了摆手,眼角眉梢都带着笑意。
飞来越冬的鸟在枝头翘着尾巴搭巢,往山上走着走着树荫竟然绿了。已经往西边斜起来的太阳不怎么刺眼,从树枝间洒下来暖得懒洋洋的,海晓风莫名想到一部四十年前的老片子,里面有个白富美跟个救生员说笑话,“你就像下午三点钟的太阳,想做点什么,可是时间总是不够;而不做什么,就会觉得时间很漫长。”
他现在什么都不想做,却觉得时间完全不够用,而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够用。
徐若霖在他前面走,背上扛着个容量能有二十升往上的巨型登山包,心情很好似的吹着有点跑调的小曲儿。
山不算高,只是层层叠叠的很深,他们走着走着就把太阳甩在了身后,头上密密匝匝的树林子把天空捂的严严实实,地上不知积了多少年的叶子被四只脚踩成大大小小的碎片,破裂的声音不绝于耳。
“你到底要去哪?太阳都要落山了。”海晓风有点累了,他搞不懂徐若霖到底想要去哪里,也搞不懂他哪来的这么大力气扛着这么个大包走了这么远。
“快了快了——我还会坑你?”徐若霖把包往肩膀上又扛了扛,口哨他是早不吹了,只不过还在哼着那个偶像组合的最新一首单曲。
海晓风想说你坑我坑得还少吗,忍了忍还是把话吞了回去。
又走了一阵,徐若霖噤了声,海晓风头上闷出了细汗,两人渐渐并肩走起来,树林里只剩下脚步挪动的声音。太阳又出来了,这次不是在头顶,而是在他们面前。树开始变得稀少,红彤彤的光顺着树林的缝隙照进来,海晓风侧头看看,徐若霖鼻尖上那层绒毛在阳光下无比清晰。
“你该刮胡子了。”他总想损这家伙两句,毕竟徐若霖再怎么说也是个女孩子看了会脸红的帅哥,如果不找点平衡大概会被颜值的压力给压扁。
“到啦。”徐若霖咧着嘴在他头上敲了一记,一步踏进了红色的阳光。
豁然开朗。
海晓风眼睛里映入了太阳的影子,红色的太阳有一半倒映在闪着光的湖面上。杂草长出去三五米就是湖滩,灰白的沙子漫过去水,鱼苗银色的鳞片在浅水里隐现。
“怎么样,很棒吧。”徐若霖在他旁边吹了个口哨,捡起一块扁平的石头旋了出去,“还会打水漂不了?”
石头在水上跳了几跳,沉了进去。
“老早就不打了。”他叹了口气,看着湖面上被石头打出的粼粼水光,阳光在水面上扭曲着。
太阳落得很快,天边只剩了一线紫檀色的云,徐若霖支起了烤肉架子和帐篷——那个巨型登山包里就装了这么一大堆烤肉用具和野营必需品,竟然还包括了老早就没人再用的木炭。海晓风背的那个包里满是食材,什么鸡翅香肠牛排羊肉串牛仔骨汉堡饼,现在这些肉类正在被炭块烤红的铁架子上滋滋作响,香味一阵一阵往人鼻子里钻。
海晓风把鸡翅翻了个面,扭头去看徐若霖,那家伙表示他不会做饭大概会点了林子以后就跑去湖滩上生了堆篝火,现在正抱着把吉他坐在旁边一边哼哼一边弹,悠闲得不行。
“想吃自己来拿,我可没那个闲心给你送过去。”他提高了嗓门喊了一句,徐若霖扔下吉他就颠颠的跑到他旁边小桌子上开吃了。
吃得总是比做得快,两个小伙子半个小时干掉了整整一背包烤了快一个小时的肉食素食,也懒得收拾有点惨烈的野炊现场,干脆打着嗝坐在篝火边上看起了星星。
天上有几丝云彩,月亮悄咪咪的从山背后绕出来,照亮了一片天空。
“没有光污染的地方就是好,看星星都这么爽。”咬碎薯片的声音在海晓风耳边响起。
“没有光污染,有噪音污染。”他斜着眼看那把吉他,徐若霖的琴艺真的让人不敢恭维,也许是琴弦不好,吉他声音干涩难听,扫弦迟滞无比,再加上某人荒腔走板的唱腔,大概这会去钓鱼都钓不上来,全被吓跑了。
“你懂什么,这就叫青春——”被挖苦了的家伙不以为意地跳起来,一手指向天空,“这就叫生活啊!”
“中二病。”海晓风忍不住笑了。
徐若霖一手扫过琴弦,吉他发出杂乱的声响:“听我给你唱Goddessα的新曲!”
篝火的影子在他们周围跳舞,湖面上有风刮过,男孩扯着嗓子歌唱爱情和生活,几乎要把星星从天上震下来。
那时候海晓风还不知道,他再没有见过那么清澈的天空,也再没有听过那些蹩脚却轻松的吉他和歌声,而很多年以后他参加海晓晓的婚礼,乐队演奏这首已经变成了老歌的曲子,女孩笑靥如花,他却哭得像个孩子。
“我敢,我为什么不敢?”张青说,“好像我现在还能回头似的”
耗子一骨碌爬起来,嘴角抽动着,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口。
“想求饶?开不了口?你还知道要脸啊?”张青一脚踹过去,刚起身的耗子又被踹到地上,“我这辈子就收了你一个人,你还给我玩欺师灭祖,真给我长脸!”
耗子没有再试图起身,他的眼神不停闪动,最后定格在绝望上。
“我不跟你说什么被迫,但你放过我妈,不然做鬼这事也不会完。”
“行啊,一条命换一条命,拿你的命换你妈的命,顺便补偿我,不亏吧?” 张青冷森森的笑着。
耗子咬咬牙:“不亏。”
“告诉我,谁让你来的?怎么回事?”
“一个二十来岁的男人,斯斯文文,穿着身黑衣。他找了我妈,那她要挟我。长得很普通,没什么特征,也没告诉我名字。”
“说了跟没说一样。”张青拎起耗子丢在地上的铁锤,咬着牙根冷笑,“像你这样二十来岁的男人在松山市一抓一大把,死一个在小巷里谁都不会在意,你准备好了?”
我知道你狠,但是是最阳刚的狠,所以这是不行的。
耗子曾这么说过。果有一天你死了,就是死在这上面
什么?张青问。
你下手狠,但从来不把事做绝。狠绝狠绝,两者一体,只有前者,别人怕你,但也恨你。一个活着恨你的人,就像悬在头顶的刀子,你头顶悬了多少把?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吧。
所以当它们从你头顶落下来,你就是千刀万剐,尸体都找不全。
耗子想莫非这就是张青在他胳膊上刻下“绝”字的原因。
他蜷缩在地上,被狠狠揍了一顿,那种张青特有的凶狠让他一度有种“我已经死了”的错觉。
但最后张青扔掉锤子,把什么东西狠狠丢到他脸上。
一枚硬币大小的纹章在地面上旋转,最后停下,露出背面那个狂草写就的汉字。
绝。
“拿着。”张青喘着粗气,身子晃了下,“你妈没事,洪辛会一路把她送回老家的,她只救人,从不杀人。我也不会对别人老娘下手,我没那么下三滥……干!要不是为了给洪辛争取时间,你一锤子都别想打中我。”
耗子握住那枚纹章,拳头越攥越紧,又哭又笑的呜咽起来。
“靠,别哭!”张青愤怒的踢了他一脚。“站起来!”
耗子扶着墙慢慢站起来,张青看着他的脸,那个脆弱无力的学生影子从他身上死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握着纹章的绝人。
张青忽然笑了声,指指他,指指自己。
“从今天起,你就是正式跟了我了。”
耗子点点头,把纹章收进胸口的衬衣口袋里。
“走吧。”张青整整衣服,往巷口走去,耗子跟在后面,一言不发沉默着。她忽然觉得不对,猛地扭头。
干,你是不是还……
耗子猛扑过来,一把推开张青,枪声从远处响起,他捂着胸口倒下去。
“**!”张青一把背起他,躲进杂物堆后面,“耗子,耗子,别死啊!刚上任就嗝屁的纹章,丢人啊!更重要的是还丢我的人,跟我闯偏门的人不知多少,你可是唯一一个我承认收进门的!”
“本来……本来就是该这样,把你引去巷口的。”耗子说“你放过我,我归顺你,这也是那个男人设计好的。恐怕连我妈被救下,也在他打好的打算。”耗子露出个微笑,“你太容易被猜透了,好在我是耗子,耗子总是很聪明的。所以,我改主意了。”
“你怎么不和我说!!”张青拎着他衣领,愤怒的来回摇晃。
“靠……别摇,脖子要断了。”耗子露出痛苦的表情,“我不能说,他听着呢,说了他肯定会改变计划,就没法再保护你了。”
“谁他娘需要你保护啊!”张青好像受到什么侮辱一样怒吼起来,接着又愣了下,她扒开耗子捂在胸口的手,衣服上没有血色。
“嘿嘿嘿嘿。”耗子贱兮兮的笑起来,他掏出放在衬衣口袋里的纹章,掺着魔晶的纹章已经碎了,对方明显也使用了掺着魔晶的破魔子弹。
“吓着啦?我骗你的!”他捏起一瓣碎片,冲张青晃两下,“可能只是肋骨断了,耗子的命贱又硬,我说过,我运气一向不错的。”
“我日你。”张青气的给了他一拳,一点没有收敛力道,“好好躲着!”
巨大的阴影从头顶掠过,张青一跃而出,和它滚在一起,提膝撞向对方腹部。
兽吼响起,张青肩头一疼,涌出血来。
她凭感觉将拳头狠狠凿向对方眼睛,咬在肩上的牙齿松开了,两者双双后退。
月光下张青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对手,一只比成年狼还大上几号的寒豺,皮毛雪白,眼睛在夜色中闪着蓝光。
“耗子你干嘛呢!没死就赶紧帮忙!”张青喊了一声,没人回答,她扭过头,发现耗子已经被自己给揍晕了。
干啦!她痛苦的抱住头,第一次考虑起是不是要改改脾气。
肩头和额头都在往外渗血,张青使劲眨了眨眼,努力让视野保持清晰。
寒豺呲着嘴,露出一口狰狞的利齿,猛冲过来。张青矮身一扑,握住落在的锤子。
野兽折身反冲,迅捷的像只豹子。
张青毫不犹豫的丢出锤子,不负所望击中寒豺额头。
这一击用了十分力,额骨碎裂的声音清晰传来,野兽四肢一软,扑在地上抽搐几下。
她已经很久没有用过这个从阿爷手里学来的技巧了,这些年那个诨名渐渐取代了她最初的外号。知晓她童年时代的人不是死亡就是老去,已经没人知道她还是孩子时,一手飞刀百发百中。
没羽箭。
这是张青入学前在孩子间的外号,跟水浒里那个姓名发音和她相同的人一样。
她抹了把肩膀,掌心湿漉漉的,景物开始模糊,耳朵嗡鸣。一股巨力从背后袭来,她想躲开,但子弹射中小腿,让她腿一软摔在地上。
野兽腥臭的口气在空气里散开,她几乎是瞬间举起手护住脖颈,下一刻兽牙没入小臂,痛得人大吼。
“你挺厉害呀。”有人从巷口走进来,逆着月光她看不清对方的脸,但还是能通过声音步态和身形认出是谁。
“梭鱼?”她声音发飘。
“你看,我就说她早晚有一天会记住我。”梭鱼摁了摁耳麦,忽然眯起眼,“救走耗子老妈的人没留住?”
张青从胸腔里发出一串笑声。
“算了,跑了就跑了,反正大鱼已经抓到。”他举起枪,瞄着张青头部,“这次可不会让她跑了。”
枪声在头顶响起,张青紧紧闭上眼。
不是害怕,而是太刺眼了。
“四圣六凡不得留,唯三恶道制裁逢魔。”
黑色的火焰冲天而起,像朵妖冶绽放的莲,寒豺和梭鱼连连后退。
一同吓退的还有三双蓝色眼睛,来自寒地的野兽们尖声嚎叫,掉头窜向黑暗深处,头也不回的逃离。半透明的魔法防护罩将子弹挡下,分崩离析的同时又一次重构。
施法者在瞬间释放了两次护盾
“我说背影怎么这么熟悉。”金发的外国美人站在巷口,指尖不停敲着胳膊。
胡说畏畏缩缩藏在她身后,露出半张脸。
“谁?”梭鱼愣了半秒,立刻做了决断。
他跟寒豺一起,头也不回的逃向另一边。
“这么惨啊?”金发蹲到张青面前,似笑非笑,“叫你不好好学魔咒,小时候打完猎风也是这幅模样,你是狂战士吗,拿命换攻击力?”
“妈的,用不着那个,你那个中二的咒语不也没改吗!”张青因为失血而苍白的脸竟然透出一丝红色,“之前给洪辛……你不认识,反正不得不挨了几锤子!马失前蹄而已!”
“好好说话,别蹦脏字。”
“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张青呲了呲牙。
“哎呦,敢顶嘴了,真长大了啊?”她说,“还能站起来吗?”
张青慢腾腾站起来,金发扶了一把。
“扶好。”张青说,“我要睡了。”
“什么?等……”金发怀里一沉,下意识抱紧贴着胸膛往下滑的人,“怎么还这样!”
“那什么。”胡说小心翼翼戳了戳张青脸颊,确定不会有任何反应,才低头看向金发,“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西芙,西芙•米兰特。”她说,“随便叫我什么都行。”
写在后面:
感觉西芙一出来阿青气势直线下掉。
终于,那一天,张青又想起被西芙的作业淹没的恐惧【棒读
好了不瞎扯淡【……】,毕竟对阿青来说,西芙还是难得能让她感到放松的人。
大概是因为小时候被帮助吧,俗话说的好,滴水之恩,当yi……涌泉相报!

“我也觉得没有。”张青点点头,“那你在害怕什么?”
“没怕。”
“讲实话。”
“好吧,是有。”耗子勉强笑了笑,“这不是当然的吗,松山城里的混混都怕被你搭话。”
张青没再追问,向耗子走去。
交钱,取货,一切都和往常一样,甚至有时间聊两句。
“最近过的怎么样?”张青问。
“还行。”
“你妈的身体呢?”
“比以前好多了。”耗子的脸色终于好看了点,只是还有些勉强。
“你到底怎么了?畏畏缩缩的?”张青皱起眉,“又缺钱了?你不是又去偷了哪儿的钱吧。”
“没有,我怎么敢。”耗子连连否认,“就是昨天跟兄弟们去路边吃烧烤,料不干净,有些闹肚子了。干,等我好点就去找摊主理论理论。”
“得了吧,你什么不敢。”张青掏了掏口袋,把剩下几百块现金塞进耗子裤兜,“缺钱就跟我说,别为难那些人,也别去赌了,不是好不容易才把之前的无底洞填上。”
耗子的表情扭了扭,一副要哭不笑的表情,嘴角努了努。
“什么表情啊真难看。”张青嫌弃的后退几步,看了眼耗子工装裤。宽大的裤兜好像被什么重物坠着,露出一节长长的柄。
耗子注意到张青的视线,亮了亮口袋:“锤子,拿来防身的。”
“不用菜刀了?”
耗子笑了,知道这是调侃:“不够威风。”
“你也知道,那我走了啊。”
“嗯,谢了,回见。”
张青转头的时候,听见耗子嗫嚅着在说什么,但她没有在意。
就连耗子今晚如此反常的表现,她也没有在意。
很久之前就有人说过,张青向来傲慢,而傲慢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她不认为耗子敢欺骗自己,也不觉得他有理由背叛自己,她太自信了,毕竟是耗子的命是从她这捡来的。她觉得自己对耗子不薄,却全忘了这一切的起因是什么。
是因为她要杀他。
所以铁锤砸到她脑袋上时,张青一点防备也没有。
“我说。”耗子举起手,“对不起了!”
铁锤狠狠落下,血瞬间染红张青视线,她眼前发黑,什么都看不清。
耗子手起锤落,第二击接着落下,结结实实敲在张青胸口,眩晕和胸闷同时袭来,她闷哼一声,踉踉跄跄后退,一下撞到墙上。
耗子紧紧盯着对方,他已经不是大半年前那个四体不勤的辍学生了,这两锤下了死手,灌注了他全部力气。
没有人说话,寂静的小巷里只有张青费力的呼吸声,血从她鼻腔和口中溢出,落到地上,滴滴答答走秒似得的响着,这声音结束时,曾站在城市顶点的人也将走到尽头。
催命的表。
“我什么都不说,你懂得,有那么些事,踏进这条路的时候就知道了。新人杀死老人,把尸骨踩在脚下当石头,才能继续往高处走,你也知道吧?”
耗子活动五指,捏住锤柄向前走,被无数人视作眼中钉肉中刺的人正痛苦且艰难的喘息,贴着墙一点一点滑向地面。
“虽然对不住你,但我也没办法啊。”
“我亏待你了么?”张青问。
“没有。”
“我对你怎么样?”
“很好。”
“那是有人威胁你吗?”
耗子犹豫了下。
“你觉得你对我不薄,但你忘了这一切是为什么。”他说,“是因为你要杀我啊!”
“我的命在你手里,怎么可能不反抗!张青,你是不是太自大了啊!” 耗子愤怒的咆哮起来,“诺言死了,你也该跟着他的旧时代一去离去,还真的以为别人会一直服你,一直怕你?”
张青笑了一声,抬起眼凝视他:“孬种,有本事动手啊,欺师叛祖,偷袭夺命,下三滥的手段,你还好意思嚣张了?你不怕我,怎么不敢堂堂正正和我打?怎么现在犹豫着不敢动手?你是不是忘了我怎么说的了?”
耗子当然没忘,他从病床上醒来没几天,张青就找上门了。
你能拼,很不错,但就算你在重重阻拦下冲到大将面前,也没有把他杀死的手段,学不会斩将,永远都只是个替人开路的小兵。
张青睥睨着耗子,抄起水果刀刀往他胳膊上一划。
耗子惨叫一声,强忍着没敢动。
“最后一枚纹章还没做好。”刀子在他身上划了个歪歪扭扭的“绝”,张青把绷带和药膏丢给耗子,说,“从今天起,你的命就是我的了。”
奇怪。
张青想。
当初我为什么替他选了这个字来的?
“别废话了。” 耗子告诉自己杀了这个人他就会声名鹊起,一跃成为这个城市新生代里炙手可热的人物,张青的名声会加到他身上,绝不能愧疚心软。
他鬼嚎一声,重锤落下:“安心去死吧!”
命中人肉的感觉没有传来,耗子往前一扑,打空了。
风声扑面而来,张青的拳头和笑容一起放大,一拳命中鼻梁,凶狠有力,一点也不像受伤的人。
只一拳,耗子的勇气就被打了个干净,但惯性仍让他反抗,结果是被对手一腿撩了出去。
“凶铃给我送信时我还不信,原来真的是你有问题。”张青抹了把脸,黑眼睛炯炯有神,刀光般亮着。
她从鼻腔里狠狠喷了口气,说:“你真以为你能杀了我啊?”
耗子没有说话,他认命了,躺在地上等死。
“下手真狠……”张青捂着脑袋,“说,怎么回事,你一个人没这胆子,也没这心思。”
耗子沉默着。
张青骂了几声,拨出一个号码,将终端机丢给他。
耗子狐疑的看了一眼,张青面无表情的看着他。
“把免提打开。”
耗子照办。
“拜托你的事怎么样了?”张青问。
“搞定了。”电话里传来洪辛的声音,温柔平静,“阿姨没遭什么罪,就是吓着了。”
耗子的嘴唇剧烈抖动起来,忽然涌出满身大汗。
“谢了,欠你一次。”张青说。
“接下来怎么做?”
“怎么做?”张青冷笑着,眼睛死死盯住耗子,“你说怎么做?这种废话问我干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一瞬,挂断了。
“你敢。”耗子手颤着,几乎握不住终端,“你要是这么做了,就真的回不去了!”
洪辛是在竹林深处找到张青的,那个人笔直的站在老龙头墓前,一把瘦骨又冷又冽,像杆枪,和周围的竹子融成一体。
这就是张青跟她说的老地方,洪辛没出声,知道张青肯定早察觉到了自己,只是不愿回头。
墓前摆着两碗酒,她又站了会,一碗喝干,一碗洒净。
“阿爷,我来看你啦。”她轻声说。
没有人回答,竹子在风中发出飒飒声响,张青转过身,看向洪辛。
“帮我个忙。”她说。
“如果我做错了什么事,那是因为上帝没有赐给我做把事情做对的能力。如果这个世界令人讨厌,那是上帝的错。我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胡说又一次接待了张青,这次她还是两个人来的,但那个叫吕鹤的女孩在车上不肯下来,很是厌恶和张青共处一室。
咖啡店新装的影屏上播放着半个多世纪前的老电影,灯光落到张青面无表情的脸上,明明灭灭,跟剧情一起变得晦涩起来。
“那么那些头部中弹的死者,也是上帝的过错?你不觉得害臊么?”
“我有什么害臊的?这世界变成这副德行又不是我造成的。”
“但是你也没做出任何事来让世界变得美好。”
“Yeah,那我下地狱好了。”
张青眼睛一眨不眨,专注的都不像在看电影了,像被设定为要看电影的人偶,木然又无谓。
胡说看不下去了,他拉过一把椅子,坐到张青旁边。
女性眉头都没动一下。
这些天的直接接触让胡说胆子壮了不少,他发现张青脾气虽差,但一般不发脾气,或者说,她的脾气只针对特定对象释放。
而胡说显然不在雷区里。
他咳嗽了声,张青终于看了他一眼。
也只有一眼而已,一眼过后她就重新将目光投回了屏幕。
“你喜欢这种电影?”胡说也看过去。
“不。”张青说,“你老板喜欢,看过很多次,每次刚开头我就会睡着。”
胡说咧了咧嘴角,心想也是。
“这片子讲了什么?”
The Funeral,江湖白事,开片便是葬礼,那场葬礼的影子贯穿全程。胡说当然看过,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怎么可能没看过这部经典?但他很想知道这个故事在张青心中是什么样。
“讲了三个黑帮兄弟,有天其中一人被杀了,于是原本渐行渐远的两人又聚到一起,为了死去的兄弟,为了复仇,为了告诉这座城市,有些东西有些人还活着,至少还没死绝。”
张青说这话的时候有股咬牙切齿的味道,尤其是最后几句,就像要把刀子咬碎一样。她想这个故事真是太适合松山了,摇摆中拉锯的势力,赶不及要到来新时代,不甘离去的旧时代,暴力与欲望构建的江湖,与这片黑色中的点点白光。
曾经也有人对她说,你们是兄弟,是姐妹,你们这一代,生为兄弟,互相亲近。下一代,下下一代,也依旧是兄弟,哪怕散落在五湖四海,也密不可分。
那时张炎还是个病秧子,张顷还没有继承武馆,她也没有收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诺言还是个野心勃勃的少年。
所有人都还在,阿爷握住他们的手,声音坚定。
血浓于水,你们有血肉相连。
“最后。”张青缓和下来,木然的告诉胡说,“他们都死了。”
胡说摸摸额头,觉得这种只有开头结尾,过程简单粗暴的短评挺适合张青的。
“那你喜欢啥片儿?”
张青摇摇头:“不怎么看电影,不记得了。”
“矮子里拔将军,总有一个比较喜欢的吧?”
张青露出为难的表情:“小马王?”
胡说愣了下:“那个……动画电影?”
“嗯。”她点点头,“你看的片子不少啊。”
“平时店里没生意的时候不是看书就是看片了。”胡说偷偷开了个黄腔,好在张青没懂,“挺适合你的。”
她没说话,站起来向店外走去。
“慢走啊,下次再来。”
门口风铃响了两次,胡说看向落地窗,一个灿金色长发的外国美女跟张青擦肩而过,她走到门口,忽然停住脚步,扭头,狐疑的看向背影。
“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吗?”胡说抬高声音喊。
“啊。”女人回过神来,在靠窗的座位坐下,开口就是流利的中文,“来杯热咖啡吧。”
张青隔着车窗看向吕鹤。
从店里出来时已经晚上九点了,路旁的灯光昏暗,女孩在座位上缩成一团,皱着眉瞌睡着。
她站在外面看了会,反身离去。
顺着巷子向里,快到尽头时右拐,再右拐,一条更小的细巷出现在面前,宽窄刚好容两人并肩,张青每隔半个月都来此,找人,取货。巷子偏僻,安静且安全,张青不想别人知道这件事,连张炎也没有告诉。
送货的耗子在这儿等了有一会了,当张青瘦高的身影出现在巷口时,他下意识直起身,紧张的咽了口口水。
女人走了几步,忽然停住了,月光从她背后和头顶洒进来,脸旁都藏在阴影里。
耗子看着在月光下被拉细拉长的黑影,鼻尖冒汗。
“怎么了?”他问,“货不要了?”
“耗子,你给我送了多久的货了。”
“大半年,怎么了?”
“这大半年中,除了头几次交货外,你从没这么害怕过。”张青看着巷子深处的耗子,他缩着肩膀,腰弯着,神色慌乱,下意识到处张望,“其实你一直不怕我,但现在你在害怕,我做了什么让你害怕吗?”
“没有。”
耗子勉强笑了笑,他今年才二十出头,念过一年大学,有个卧病在床的母亲,迫不得已才走上这条道。
他走投无路时碰上毒帮和黑帮火并,趁乱顺走五十万,被顺藤摸瓜揪出来那天正在厨房给老妈熬药,忽然觉得不对劲。
自从偷了钱后,耗子神经就一直绷的紧紧的,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察觉。此刻这栋隔音效果极差的廉价公寓十分安静,他从窗户里往外看,发现一群提着刀枪棍棒的人围住公寓。
穿着黑风衣的女人站在路灯下,突然毫无征兆的抬起头,冷冷的望进他眼睛里。
耗子懵了半秒,二话不说冲进厨房里,操起菜刀杀了出去。
他知道逃跑没有用,况且身后还有自己老娘。
耗子觉得自己运气特别好,如果不是前几天打算搬进隔音效果好点的新家时被意外打断,他肯定不会发现周围异常。
更重要的是,那天来清理场子的人是张青,所以耗子不但没死,还被扶了一把。
不过这也得益于耗子的脑筋转得快,他认得张青,在看到那个女人的第一眼就打算拼了。
耗子想大不了和她同归于尽,自己贱命一条,磕掉张青一个角也算值了!
人濒死时爆发出来的力量是巨大的,四肢不勤的耗子拼上一条命冲到张青面前,整个人都被血成了红色,尤其是背后,不知被砍了多少刀。
张青看着昏灯下耗子的决绝的眼神,提枪拉开臂膀。她一步都没有挪动,却让耗子在握枪的那刻倍感绝望,仿佛之前所有努力都化作泡影。
但他没有放弃,二十米,十五米,十米,每近一步都能感到死亡迫近时的沉重压力,他一口气冲到张青五米之外,通的摔倒在地。
我替你干活。耗子抬起头,染血的眼睛异常明亮,他一点点爬起来,说。
你看到了,我能拼,能在重重阻拦下冲到大将面前,我把钱还你,把命卖你,我替你干活,让我活下去。
张青没说话,一枪敲了下来,耗子眼前一黑,万念俱灰。
后来张青问你哪来的胆这么赌。
耗子说我认识你,知道你狠,但是最阳刚的狠,杀人就杀人,从来不搞绑架勒索那套,取命就取命,不会把人折磨的死去活来。
张青的嘴角咧了咧。
你做黑事,却意外透着股侠气。
耗子说出这句话来时自己都觉得好笑。
所以看见来的是你的时候,就知道我妈不会死了……我老家有个义兄弟,我死了他会替我照顾我妈,所以我没牵挂了,最开始真的打算跟你拼了。
那为什么突然改主意了?
耗子摸着鼻梁。
直到冲到你面前,距离缩短到足够看清你表情时,我才明白拼命是多搞笑的想法。
那一刻耗子才发现,自己的拼死一搏不过形势所逼,而张青却时时都准备着去死。所以枪落下来的那刻,他真的怕了。
耗子谁都不怕,只怕无意义的死。
#组织今天还是没人来##文书急需人手!!#
随着一阵渐渐接近的脚步声[组织]办公室的大门猛得被推开大力的撞到墙壁发出烦人的闷响“今天也还是没人来,大家就那么不愿意给官方工作吗?还是说我们的条件开的不够大?”
稍微心疼了一下花了大价钱定作的复古木门Lynn不用抬头也知道来人是谁“卡拉斯亚我说过进来之前得先敲门,作为领导者你得给手下做好榜样。”说着他翻开下一张报告然后发现那又是关于未知的魔法生物袭击人的事件。
“我现在可是一个正式手下都没有,等什么时候有了再做榜样也不迟。”卡拉斯亚的语调中充满了随意很显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到时候你肯定也还是这个样子。”听着搭档的话Lynn忍不住笑了笑“不过卡拉斯亚这样也挺好的。”
“你总是这么敷衍人,看着文件比和我聊天有意思吗?”倍感无聊的卡拉斯亚一下子坐在了Lynn的办公桌上撑着胳膊看了看Lynn手上的文件“从我进来开始你的眼睛就没离开过它,只是魔法生物袭击这种小事为什么不交给别人?”桌上原本整齐摆放着的纸张被推倒了大半并压出了皱痕只有Lynn手上的几张依旧安全无恙但眼看着卡拉斯亚接下来就准备去摧残它们了。
“我这边可是一个帮手都没有。”Lynn无奈的放下手中已经看的差不多的文件“你那至少还有一些佣兵之类的人,但文书方面的工作可没办法交给刚雇来的家伙。而且未知的魔法生物可不是什么小事说不定它们的背后还会牵扯出什么来。”
“不就是和前几年一样的事件吗?”卡拉斯亚毫无形象的坐在桌上摆了摆双腿丝毫没有让Lynn继续工作的意思“最近几年这样类似的事件已经够多的了连普通公民都知道该怎么做”说着他瞥了眼被Lynn放在手边的文件“而且这次也没有出现人员伤亡,要我说的话这种文件交给下面的人做完全没问题。”
“那我可就没法发现魔法生物的两极分化了。”Lynn安抚的拍了拍卡拉斯亚的背示意他别坐在桌上“很有趣的发现,你想听听吗?”
“我也有很有趣的发现。”卡拉斯亚的确乖乖的爬下了桌子但却是顺势的坐到了Lynn的腿上“最近可是春天……说不定那些魔法生物的活动变频繁了有这个原因?”
“唔,的确有这个可能,毕竟我们对他们的相关知识了解的太少了。”Lynn开始认真的思考春天对于魔法生物是否会有所影响“魔法生物们大都有动物的特征,习性说不定也有所相似。”
“……该是说你笨还是迟钝?”眼看着话题就要被岔远了卡拉斯亚俯下身对着Lynn的耳垂狠狠的咬了一口。
“我要是笨的话就不会负责文书、疼!”看着卡拉斯亚用舌尖卷起的血珠Lynn终于反应了过来“等等?!这里可是办公室!”
“反正又不会有别人进来。”话语间Lynn衬衫的纽扣就已经被解开了大半。
“要是有人来报名怎么办?!”换个环境的话Lynn倒是挺乐意的但办公室?还是算了吧。
“我会听到的……放心吧。”一声提示音响起表示垂在卡拉斯亚肩上的兔耳开始发挥它原本的作用。
“听力增幅器可不是这么用的?!”完全放心不下来!Lynn开始考虑是不是要找些有趣的事让卡拉斯亚好发泄一下过剩的精力不然他就要天天保持这不满的情绪了。
“要知道武器的用途永远不止一种。”面对Lynn的质疑卡拉斯亚略微带着些得意的回答。
TBC.
-------------
我觉得我没开车(
快来官方小队有免费武器和魔晶!
打牌输了的CGM社团的互动,大家一起打牌好开心哇!
困得不知道自己写了什么……感觉思维和故事一样飞起来了
搞笑的OOC实在是太抱歉了[土下座]不喜的话请拒绝响应,抱歉[土下座]
感谢阅读。
============================================================
(一)
奥斯德老师左手拿着教材教学书,右手轻叩深棕色欧式雕刻风格门。两三下过后并没有反应,稍微靠近门,隐约能听到门内人的交谈声。
这是位于教学楼一角几乎没人踏入的cgm社团教室。40年前奥斯德还是个学生的事情仍然历历在目。
房间空荡荡的,不管什么时候,屋内始终是干净的,多亏了社员们保持着轮流打扫的习惯。屋内的木柜大多都是空的,里面的东西早被物主带走。正对着门的,是一扇大打开的窗户,风带动淡白色的窗帘向室内飞,时不时有几瓣樱花瓣飘入。也正因为对着窗口的原因,门被的压力阻挡有些难推开,但以奥斯德的力气,只需稍加把劲便推开了。
“我进来了。”
“啊。”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淡亚麻色发上使得发梢看起来有些许金边。男子抬头看往奥斯德,像是亲友又像是许久不见的友人一样打量他,开口说道,“下午好,奥斯德。”
“下午好,Elias。”Elias的出现让奥斯德有些惊讶,本应该在现界的Elias看出了对方的疑惑,刚想开口,身旁的女性抢先一步。
“如你所见,我们在玩牌。”女性抬头挥挥自己手里的卡牌。长到几乎及腰的黑色单马尾和额头前一小撮红发是张青的标志,奥斯德记得。
“牌……?”奥斯德这才注意到他们在打牌,仔细一瞧才看到牌只有盾,星星,刀和狙击这几个标志……啊,最近经常玩的那个游戏吧,各位最近还真喜欢玩啊。奥斯德心想,难得露出笑容,随手关门加入其中,“带我一个吧。”
“一对一,要等一会儿喔。”Flavia坐在一旁的木椅上招呼奥斯德坐下。奥斯德便坐在离他最近的木椅上,看张青和Elias打牌。
(二)
不知过了多久,奥斯德也加入其中,也不知玩了多少局,他对牌的游戏方法也已经轻车熟路。轮到Flavia玩了,奥斯德给她让了个位置,自己坐回木椅上。等意识到的时候,奥斯德嘴角一直是上扬着的微笑。
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放松过了,不大的社团房间也很久没这么热闹过了。
“好久没这么热闹了,”奥斯德笑着说道,但身旁一起观战的拙仓似乎根本没听到他说话,“拙仓?”
“喔,又赢了。” 张青往牌堆里放回手里的剩牌,该奥斯德和Elias了,奥斯德并没怎么注意拙仓的反常,和之前一样,坐到了Elias对面,开始抽牌,出牌。
有星星的牌只有1张,狙击标志的牌一个都没有,奥斯德苦笑看着手里这副烂牌,整理好牌后,他抬头看到对面的Elias咧着奇怪的笑容看他,“Elias……?”
Elias没有回复他。
“Elias?”
“奥斯德,你知道吗。”
“?”
“这个牌会变成真的喔。”Elias右手抽出一张牌翻给他看,是张有匕首5的卡牌。眨眼间卡牌真如Elias所说,变成了真的匕首,“如果你的艾○的HP为零,那么你也会……”说着便向奥斯德刺去。
“哈?!等等!”奥斯德来不及反应,先不说为什么牌好好的变成了真的匕首,倒是Elias怎么会突然毫无理智。下意识想使用魔法防御,奥斯德脑内却一闪意识到自己发不出魔法。
眼看着匕首马上就要刺入自己的头颅,奥斯德眼前一黑,什么也看不到了。
(三)
等奥斯德再睁开眼睛时,他坐在社团教室内的木椅上。刺眼的阳光让他眯着眼睛勉强看着周围。
真奇怪……
刚刚确实要被Elias用匕首攻击。
奥斯德想不通,,屋内还是和无人时的一模一样,没有异常,没有卡牌,也没有社员。只有他一人。
门外传来敲门的声音把他吓了一跳。还没等奥斯德说话,门被推开了,是紧忙神情的Elias。
“啊,Elias你…”虽想确认刚才的匕首攻击事件,但是对方极其时尚的衣服让奥斯德吓了一跳,全身白色配上右侧一直到膝盖的绿色布料,像裙子的一角搭在那里,右边的口袋还配上了银色的小链子,感觉像是要去演出。
“奥斯德!你果然在这里!”Elias有些不开心,如果他是女孩子的话,嘟嘴生气是最适合形容他现在的样子了。
“啊……?”奥斯德还是一点也搞不懂现在的情况。Elias直接闯入拉起奥斯德的手腕就往外扯,奥斯德也被他的力道吓到了,只好乖乖跟在他身后被他一路扯到一楼大厅。大厅内站满了社员,全员都像是等着奥斯德的样子盯着他被Elias拉过来,果然他们的衣服有些奇怪。
比校服的颜色要靓丽很多,还有很多闪片,小链子之类的装饰,有点像演唱会的衣服……?
“大家都在等你。”Flavia穿着白色的连衣裙,胸前有蓝色的大蝴蝶结作装饰。
“再不来我们就先上场了!奥斯德。”张青穿了朋克风的衣服,像是摇滚明星一样,尖刺的铆钉在马甲上尤其亮眼。不得不说,奥斯德觉得特别酷。张青右边的是拙仓,相比张青,拙仓更要平凡一点,最外面是一件淡棕色的薄风衣直到膝盖,配上全身的黑色衣服简直是绅士的教科书。
“门外的学生们在等着我们呢!”Elias突然拉起奥斯德的手跑上前推开大厅的大门,突然一阵欢呼声几乎要把奥斯德震聋。
(四)
等奥斯德再恢复意识时,他发现自己还坐在社团教室的那个椅子上。奥斯德感觉有些诡异了,他一定是睡过了头。
“奥斯德?”奥斯德听到Elias叫他的声音,Elias推开门问他,“你怎么了。”
“我感觉不太好,”奥斯德没有看他,双手捂着脸无奈解释,“我,我梦到了Flavia在舞台上大喊茨格姆入校指南,张青被女粉丝们称作男神,拙仓很绅士唱歌也很好听……似乎没什么奇怪的地方,倒是Elias你自己一直在舞台上叫我唱歌……之类的。啊,没什么,我梦到你们都变成了学院偶像。”
“学院偶像?大白天就在谈些鬼马行空的东西真不愧是奥斯德。”Elias被他逗笑了。
“是啊,你是不知道,当时拙仓还……”奥斯德感觉好多了便抬起头跟他讲,谁知对面是位头发花白的老爷爷,胡子白又茂密像极了圣诞老人,不知为何,奥斯德自己觉得他就是Elias。
“就算是真的,我也记不住了啊老头子,吼吼吼……“
…………………………喵喵喵喵喵????
=========
感谢阅读。
全文都是奥斯德在做梦,似乎再做2,3个梦就醒了的样子。希望奥斯德的san值可以快点恢复回来[祈祷]【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