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誕快樂
“冬至快樂。”
讓本大人看看這個包裹,本大人是說,天底下不可能有比這個還糟糕的包裹了。
“啊,怎麼了,這個盒子怎麼這麼大……你究竟送了什麼禮物啊?”
本大人聽到一個男聲這麼說著。本大人覺得他肯定會失望,畢竟這包裹實在是很糟糕,這個包裹底下軟綿綿的,上面卻很硬,而且這個盒子黑乎乎的,讓本大人摸起來覺得難受。本大人覺得送給女孩子、男孩子、還有無性的、雙性的所有的禮物都應該是完美而美麗的,如果他是軟的,那就應該全部是軟的,如果他是硬的,他就應該全部是硬的,這樣一半軟一半硬,實在是不像話。
本大人就是這麼覺得的。
“拆開看看吧!”女聲說。
“停一停,首先,今天不是聖誕節嘛?和冬至有什麼關係嗎?”男聲說。
“冬天的節日總是有那麼些相似之處,不,我覺得他們就是一回事兒。”女聲又說道。
本大人聽到本大人的頭頂傳來了一聲撕裂聲,本大人尋著聲音望去,一個紅頭髮的男人看著本大人的臉。
大笑。
“天吶……!這是一隻……”
本大人呆愣愣地看著男人。
“是個機器狗的頭,我從警察那裡卸下來的。”女聲煞有介事地說道,“開齋節——還是什麼快樂!希望你能喜歡它!我想我們可以用他拍點東西不是嗎。”
天吶。真煩。
本大人只好面對那女人和那男人,擺出來難過的笑臉。
生日快樂
“我很感謝你誕生的事實。”
金燕梓吻了水野純,這是他們開始慶祝的第一步,吹蠟燭和切蛋糕的步驟在雪城的夜裡被省略了,他們交纏在一起,隨後金燕梓咬了水野純的舌頭——那是個綿軟的攻擊。水野純笑了笑,沒有再說什麼。
他們依偎在雪夜的火堆旁。
“你聽到了嗎,火焰爆裂的聲音。他們在跳舞。”金燕梓說道,“這團火會無限地跌落再升騰,隨後一個個小世界在裡面滅亡又誕生,滅亡再誕生,知道火焰熄滅了,事情都會結束的。”
“都會結束的。”水野純疲勞地重複著這句話,“到以後。”
“是的,我現在希望這團火也能祝你生日快樂。”金燕梓俯下身來,向那火堆吹了口氣,隨後她從她的口袋裡拿出那把匕首,并割掉了一綹頭髮。她將那段烏黑的綢緞丟進火中去,火迅速地吞噬了那點祭品,隨後燒得更汪。“我希望你能幸福,我親愛的旅伴,水野純先生。哪怕這個火焰不能祝福你,其他的火也會這樣。”
他們的手疊在一起,這比火焰更灼烈。
“如果我不能呢?”
“那我也不會幸福,我希望你能活得……隨心些。我會愛你,無論如何我都愛你。”她又吻了他,這個吻被賦予了保護的意義。水野純想起奧茲國遊記中的女巫也是如此。
這個吻是有魔法的。
“我很感謝我能遇到你,謝謝隨便什麼玩意讓你在今天誕生。”半晌,金燕梓說道。
不攢了不攢了,再攢頭髮掉沒了
旅途伊始
“再見啦!”
金燕梓笑著套上她的外套,把她的行李箱扔下樓去,自己也順著墻壁的管道從二樓跳了下去。她朝被她留在身後的破舊公寓和她繼父比了個中指,隨後騎上了那輛以便宜的價格買來的二手摩托車。
“你他媽給我等著……!”她聽到身後那個男人大聲吼道。可沒什麼用,不過轉眼功夫,對方那副破鑼嗓子便淹沒在飛馳而過的嘈雜街道風景後。金燕梓大笑著拍了拍摩托車的手柄,等到了人追不上的距離便減緩速度,駛入小巷。
她看到路邊的大爺露出困惑的目光的目光,但她的好心情讓她向著對方大聲打了招呼:“下午好!”
這是一場毫無計劃性的旅行——她收到一封信,信上說她母親和一個女孩子去了尤金。那個生性嚮往自由的女人去了那裡多半又是為了“壯麗而漫長的旅行”。哦,至於那封信——金燕梓想著打開她的行李確認了一下。信封上沒署名,也沒寫地址,要不是信封有點好看,她或許就扔掉了。信是打印的,大概是因為不想被人認出來字體吧。雖然她只看了一兩次,現在卻能把那封信背出來了。
信是這麼寫的:
“
金燕梓小姐
想必您也知道您的母親的工作,我便不多做前因後果的解釋。您的母親金勝男在上一個冬日離開了她的上一個據點。我們都知道您母親是個難以捉摸的人——這比她那次打算強行闖入‘塔’還過分點,她在路上誘拐走了一個名叫水野Jun(我不知道她名字的寫法)的女高中生,並帶著她在雪城尤金一代轉悠。
據我所知她最後一次出現時在城鎮裡面是一個名叫金富麗的旅社。
若是得到什麼新消息,必定還會再發信給您。
祝您身體安康。
張浩賢”
金燕梓咂咂嘴,她抖抖信封把信收了回去。已經很久沒有看到一封信,其他的通訊方式有的是,沒必要執著于容易損毀的紙張。不過,這不要緊,這封信催生出來讓她離開中心城這個鬼地方的念頭。她從她繼父的銀行卡裡取了不少錢,續了自己的簽證,接著等待了一個月并在對方暴怒著衝進家門之前準備好自己的行李,在火山噴發前的一秒成功離家——也就是幾分鐘那一幕的開端。
世界上哪有那麼多需要腦子去考慮的事呢!
她大笑著駛向高速公路鏡頭的機場。再之後是繁瑣的安檢程序和出關手續。到了下午四點時,金燕梓已經坐在飛往雪城的空中巴士上。
云流層上的風景素潔單調,引擎發出遙遠的轟鳴。金燕梓感到自己的耳朵因為高空氣壓的緣故脹痛。雲層模糊的邊緣潔白而充滿想象力,它是先具備想象力,然後才被人看成各式各樣的形狀的——但它又什麼都不是,只是複數漂浮著的水分子。
金燕梓在窗前盯著那片足以稱得上遼闊的雲發呆。她將這東西與自己的處事態度、養父的錢包還有李勝男的自由視為同等的東西。在這個高度,已經看不到地面的樣子,只能模糊地見到狹窄的窗子裡微微浮動的黑點。
真小啊,金燕梓想。但也很龐大。她又在心裡補充道。
飛機開始降落。剛才還距離得遙遠的風景,一下子便回到現實。金燕梓深吸了口氣。
到達機場後,金燕梓先聯繫當地的旅遊組織,假裝是休學旅行的青少年。通過這樣的方法很快就找到了價格合適的青年旅館。養父應該還不會報警,理由很簡單,警察對離家出走的孩子多半會從家庭開始調查起來,這樣事情就對那個人來說就會變得麻煩。
定好住處之後,她按照信上所說的地址去找了金富麗旅館。雖然說是旅館,但那似乎是從民居直接改裝過來的,招牌直接鑲嵌在樓房裡,顯得很突兀。金富麗旁邊的門戶不知是出了什麼事,黑糊糊地一片,可能是遭了活在吧。而旅館的門還沒有開,大概對這種小旅館來說大門一般不需要開著。
金燕梓敲了敲門,開門的是個有些肥胖的中年婦女,有個圓形的蒜頭鼻。
“住宿嗎?客滿了。”
“我想找個人,有沒有叫金勝男的?是個女的,大概四五十歲,黑色頭髮。”金燕梓比劃了一下,“和我長得有點像。”
對方話音未落便關上了大門。金燕梓趴在門上,唱了首歌,興高采烈地敲著門,對方這才又打開門。
“打聽這些做什麼?”
“我是她女兒,她失蹤了所以我來問問。”金燕梓聳聳肩,“你要是在意,我可以給你一些錢來交換。”
“不用,太少了。”胖女人皺了皺眉頭,圓形的額頭被擠成碗形,“你要是她女兒,你怎麼自己都不知道她在哪兒?”
“這不是在找她嗎,你既然想談她出現在哪兒就說說吧。”金燕梓捲了捐耳邊的頭髮好排解無聊。旅館的胖女人躊躇了一會兒,面帶慍怒地看向金燕梓,卻還是講起來金勝男的故事。
——金勝男是在一個對雪城來說有點熱的夜晚帶著一條大狗和一個女孩來這裡借住的,大狗沒有進門,過夜的時候拴在大廳的角落裡,既沒有大聲狂吠也沒有隨地大小便,這大概是金勝男帶來的唯一的好事。女孩的名字叫水野。兩人住了三天,金勝男毀壞了三床被子和一個茶杯,不過她付了錢。住的第二天晚上,隔壁民居起火了,她幫忙救了火,但隔壁家的小兒子還是燒傷了。她走的時候又添一個旅伴,是個皮膚黝黑的女人。
“黝黑的?”金燕梓對母親工作的部分從未做過過多了解,但她很肯定母親並沒有那樣的同事,“看起來是曬的還是天生的?”
“這哪裡看得出來。”這個中年女人有些不大耐煩地回答,不過又補充道,“上週三三人一狗一起走的。”
“他們又有要去哪兒嗎?”
“這我哪知道,但肯定不是離開雪城。他們行李不夠的。而且,他們也在晚餐桌上談過在雪城的行程。”中年女人拽過來一張紙,快筆寫了起來。
“那幾個旅伴的名字都叫什麼?”
“黑皮膚的叫蓋伊,女學生叫水野,狗叫汪吉。”胖女人將那張被寫過的紙塞了過來,“你按照這個找找吧,她們幾個說話沒有遮掩的意思,這些地址她們都提過。”
金燕梓看了看,發現都是些看起來很模糊的地址。任務,她在腦海裡面做出這個評價,從這裡開始變成故事的開始。她記下來這三個名字,然後去租了輛二手摩托。雪城的道路很適合用摩托這樣的交通工具奔馳,駕駛的時候戴起來一陣陣涼爽的風,給人舒服的感覺。
金燕梓看著頭盔玻璃內的潔淨,整理起來。突然寄來的信是開場,那麼金勝男失蹤前的去向就是任務。她從很遠的地方來到這裡,是場漫無目的的離家出走,完全沒有必要去跟隨母親的腳步。如果是後者的話,事情就變成了故事,如果是前者的話,事情就還只是人生。
出於一種逆反心理,她駕車去了市立圖書館。是的,沒有必要變成故事,她心想。她在圖書館休息了一陣子,讀了幾本隨手抓來的書,內容從科普讀物到地理風情應有盡有,隨便翻了翻之後看起來畫冊,看到兩眼發酸就趴在桌子上睡一覺。
不過因為夢不大好,金燕梓馬上又醒了。這時候圖書館已經播放起每日閉館的廣播,窗外的天空則散發著靜謐的青黛色。金燕梓隨意借了基本書,然後出圖書館買了根可樂味的棒棒糖,思考接下來該做點什麼好。
水野不是個普通的姓氏,在這裡應該是很難找的。蓋伊則有點難找了。至於她母親的名字,金燕梓有自信能找出來好幾個名字相像的。要說方便,果然還是要從雪城這裡的獵人公會找起。
這時候她收到第二封信,這是封匿名短信發送的垃圾郵件,充斥著“我就是想騙騙人”的味道。金燕梓掃興地將垃圾郵件關閉了,這才意識到自己走進一條小胡同。她聽見前面有什麼人大聲咒罵著,隨後是扭打在一起時的呻吟聲。金燕梓抬起頭來看看小巷的四周——沒看到攝像頭。
恐怕是當地的混混在鬥毆吧。
金燕梓看了看手機的時間,現在已經是下午八點。就這麼開摩托車回去旅館應該是個不錯的注意。雖然自己現在是走岔了,但只要幾步就能走回圖書館去。她這麼盤算著,掉頭就走,卻聽到身後有個聲音大聲喊道:“什麼人在那裡!”
真是麻煩。金燕梓心想,她快步向前跑去,再回到圖書館不過是幾步的功夫,那裡有攝像頭也有行人——事情就會變得不一樣。最壞的情況她也能直接開著摩托離開,她奔跑著,聽見身後有人在吶喊著什麼東西,然後是一連串咒罵和威嚇,她聽得很清楚。
那個人喊的是“水野哥”。
“哥哥,我们家都不是尤金的人吧?”
很多年以前那个小女孩这么问他。
当时自己是怎么回答的?
对了,对了………………
“是与不是,都没有关系吧?”
——————
早六点,雪城的太阳还没有从终年不化的雪山头出现的时候,湿重的雾还没有散尽的时候,在低智能AI-Real发出第一声蚊蚋声的时候,他瞬间睁开了眼睛。
就算有意保持,他也是25岁的人了。正常来讲再过5年就该听不见蚊蚋和现代的各种年轻合成音了。
——,
——。
第三声结束,Real再度回到休眠状态。别的功能都被他“拆”了,留下这个声音也不是为了叫醒他,而是给什么人提醒“这里的人醒了”和保持状态。
因为种种缘故——他还能听到这个声音15年左右。至于40岁往后的事情,
猎人能活那么久吗?
更何况他还是某黑帮的现任领头人。
——
时隔多年,他还是会梦见她。
他觉得这是自己的潜意识在作祟,亦或者是他有意为之。
他不想忘掉她。
“Jun,你还在找你妹妹吗?”
烟雾缭绕的某处地下酒吧里,有人这么问他。
“都这么多年了……”
“嗯。我不会放弃的。”他如此回答道,同样吐出一口烟——这可不便宜,自诩“遵纪守法”,自然是要多交一份吸烟税的。
“这么多年了,我也很想知道她是死是活,过得怎么样。”
然后酒吧里闯入了某个格格不入的人——瘦小又灵巧,透着不是这边的人的气息。
“——水野纯在哪儿?”
她带来了他最想听到的消息。
(tb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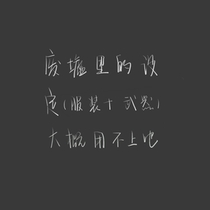



一首新歌:http://music.163.com/#/song?id=30064894
目录: http://elfartworld.com/works/138525/
墓园建在城市外围的山上,若是登到顶,远远就能看见贫民窟。而现在,没人往上爬。
“招人厌的天气。”戴文不停擦着眼镜,最后烦躁地收起来,视线总往上飘。陈氿顺着他视线往上看,白蒙蒙的雾气里站着三人,一高一矮正转身往下走,单薄瘦削的还站在碑前,一身黑色在高处格外显眼。
“看什么呢。”陈氿眯着眼,雾太重,山顶在高处,更是显得远。
“听说从山顶往下看,整个城市都收在眼里。”
“怎么,你没来过?”
“来过,局里几个兄弟被人弄死时来看他们,不过没往上走。”戴文的语气格外轻松,“等哪天我把你送进来,再顺道上去看看。”
“庆祝?”
“等把你们这群吸血虫从城市里扒光,我才庆祝,你只是捎带。”戴文摸摸身上,“有烟没,忘带了。”
陈氿摸出一根,叼在嘴里点燃,给他递过去。
“那你这辈子登不到顶了。”陈氿给自己也点上一根,“我们不吸血,我们吃欲望,除非你把人都杀了。”
戴文眉头直皱,自己和陈氿有多不对付人尽皆知,他在治管局蒸蒸日上那会,正碰上陈氿扬名,这块骨头被上司丢给他,一啃就是十几年,到现在也没啃下来。年轻时的陈氿则只比项远好上那么一点,两人撞一起,就是针尖对麦芒。刀子样的狠锐在刚正的骨头上砍了十几年,都没讨到好。
一身铁骨虽然没碎,但也被戳出道道窟窿,断了的地方拼吧拼吧粘回来,却还是有缝隙,露出里面经年累月后被血染黑的芯。
那时戴文是个一腔热血又正直的青年,一门心思想把陈氿拉下马,但两人交锋让整片城区动荡不安,直到上司把几个月所有流血事件的档案调给他看。
很久之后戴文和陈氿聊起这件事,说,知道我老大怎么说吗?
怎么。
他说,闹够了吗,也该聪明点了吧。
你这辈子都聪明不起来。
戴文没接话,自顾自往下说。
我梗着脖子说没闹够,他气得把烟灰缸砸到我头上,说,你靠骨气吃饭,别人靠钱吃饭,今天伤五个明天死一个,人心惶惶的,上面追究下来责任是你担还是我担?你担?你算个屁,你担起么?
陈氿默默笑起来,手上的烟都在抖。
戴文恨恨地看着他,说,你就喜欢这种人是不是?
陈氿笑着摇头,不像否认,但也没说话。
戴文叹了口气。
老大说,你想死,别人还想活,狗急了都咬人,你把那群混账东西逼得没活路,还不找你拼命?你一条贱命,死了就死了,那些因为势力斗争被牺牲被抛弃被出卖的人呢?他们不想死,他们有的选么?上头那些人能让他们选么?你去替他们死么?你有几条命?你能救几个?你知道这群亡命徒急了眼会惹多大事出来么?能多大多大!整个旧城区都要被搅得鸡犬不宁!
陈氿不笑了,指间夹着的烟一口没抽,他静静望着天空,白色的飞鸟从波乌达河面上掠过,高声鸣叫着。
没得选啊。戴文唉声叹气。他说的对,我算个屁,我要是有改命者那个实力,就能把你们统统干掉,可我什么都不是。
他也干不掉我们。陈氿笃定地说。欲望是杀不净的。
戴文长久地看着他,说,老大说我觉得自己是大义,他看我是自私,我和你各退一步,大家就能平平安安过日子,非要拼个你死我活。
“大家都怕了,你没看到么?”戴文学着上司的语气说,“你眼里只有自己的荣耀和正义,容不得被这世界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普通人平凡人小人苟且偷生吗?他们就不是命、就不在你拯救的人里了么?”
陈氿的表情像块石头,夕阳在河面上投下血一样的色彩。
“我看不到……”戴文自言自语似的,语气里带着一丝疑惑,“可我看到那些被你们欺骗压榨欺辱的人,他们更惨,若是连我们都怕你们,还有谁能替他们说话?老大说退一步就能平安,可他们不能平安啊。”
陈氿很平静,问,雄鹰叼兔,狮子搏羊,羊兔食草,草又何辜?
“可我们是人啊?”戴文神色古怪,倍感犹豫地重复,“可我们是人啊……”
“人比所有动物都更残忍。”陈氿把烟弹到水里,大河一下将它吞没,观景台上只有河水奔腾的声音。“黑兽也比不上我们。”他看着前方,眼里是从没有过的坚定。戴文有些意外,他以为这种近乎刚毅的表情不会出现在这群心狠手辣的人身上。
“我虽然是恶人,但也是个人。”陈氿拍了拍他肩膀。“我老了,不再想往上爬了,没那个能耐,也看清了,爬上去,有的是人想把你拽下来,还不如踏踏实实享几天福。”
“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幸福?”
“我不在乎。”陈氿直起身,“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和你一样,都不算什么东西。”
“还真是很少听你这么痛快承认自己比别人差。”
“真正有能耐的人出现了。”陈氿重新点起烟,摇着头,“比我强。”
“谁啊?”
“九叔!”
一声呼喊从远处响起,陈氿探出半个身子,戴文跟着看过去,看到大堤旁扛着鱼竿的少女,蓝眼睛在阳光下格外透彻。
“准备走了!”她喊,“卡莱瓦来接我们了!”
“你不怕被黑兽拖走吗!”陈氿的吼声压着河水传过去。
“高乐贝拉在啊!”少女大笑着,拿手肘拐了青年一下,后者挠着头,冲陈氿露出个无奈的笑。
“风行。”陈氿告诉戴文,“我老大家闺女。”
“哦,听过,整天胡闹的大小姐。”
陈氿笑起来,上上下下打量戴文,戴文被看的鸡皮疙瘩往下掉:“看个屁?”
“你这辈子是真的聪明不起来了。”陈氿说,“我以为你会一把把我掀进河里。”
“那边还有两个人看着,我脑子进水了?”
陈氿披上外套,“刚才说的,还没说完。”
“什么?”
“我们踩着别人尸骨活怎么了?和狮子杀羊有什么区别?和黑兽吃人有什么区别?只有人才会觉得倚强凌弱是错的。不要觉得不把我们全都摁死你就是没人性了,换个人来,未必比你做得好,不就因为这你才一直留在现在的职位上么?”陈氿说,“很多人都不是人了,你还是,不要犹豫,你生来就该跟我们作对。”
陈氿极少说这么多话,戴文思索了很久,惊觉自己被对头安慰了,等他反应过来,陈氿已经走了很远,他在视线尽头站着,同趴在车窗上的少女说着什么。
戴文眯起眼,陈氿背对他,什么表情也看不到,那女孩好像察觉到什么,探出神来朝他招手,日光落到她冰面似的眼里,竟像着起火来。
两人都没控制音量,说什么周围听得清清楚楚,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戴文要说点什么难听话讥讽回来时,他竟然沉默了。
陈氿扭头对着戴文,皮笑肉不笑:“要不现在上去看看?”
“谁敢上?”戴文轻飘飘看了他一眼,望回山顶,雾里人影隐隐约约捧着束素白的花,正弯下腰,放到碑前,“你敢?”
“老大叫我们在这等着。”陈氿冲山顶努努嘴,压低了声音,“大家都想去能俯瞰城市的地方,但是现在那儿有人了。风头正劲,她不松口,谁敢乱动?”
戴文猛抽着烟。
“现在想起来,我俩有点傻。”陈氿说,“说不定让咱俩对上,本来就是上一辈的意思,互相挫挫风头,他们在压上几手,直接绝了我扛旗的苗头。”
“偏偏是个丫头片子……”戴文咬牙切齿。
“怕乱?”陈氿笑起来,“很久没这么乱了吧。”
“自从你消停后,就没死过这么多人。”
“是咱俩消停后。你要是还想斗,我陪你斗,看谁耗过谁。”
戴文毫不犹豫问候了陈氿母亲:“这些天到处都在掐架,明里暗里较劲,我三天两头挨上面一顿臭骂,本来打算等你们耗差不多再出面收场,卖风石个面子顺便扶他一把,这人眼高于顶,以后也好控制,结果他竟然三下五除二被个女人给收拾了。消停是消停了,但这女的要是乱来,要是压不住你们这帮孙子没几天就被弄死了,又乱起来,我他妈还是被骂!”
“谁知道呢。”
“你早就猜到了是不是。”戴文说,“几年前在河边,你根本不是跟我介绍她,而是在回答问题。”
陈氿要说些什么,被一声打断。
“陈氿。”维拉缇斯从台阶上下来,“你是陈氿吗?”
陈氿哼笑一声,都没正眼瞅她一下,自顾自和别人聊起天来,戴文似笑非笑看了一眼,任由她杵在原地尴尬。
维拉缇斯微不可查的皱眉,有点失措,她是该好言相劝,还是回去找风行,还是用拳头交流感情……她上下打量陈氿,以及陈氿身后虎视眈眈的人群,顾虑一重又一重增多。
说到底,维拉缇斯还是个正儿八经长大的人,虽然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多少接触过,但却都是些刚入行的小鬼。她不干这一行,更不了解这行里人的脾性规矩,风行没告诉她,也不知是忘了还是有意的。
最稳妥的方法似乎是再说一遍,但她有些拉不下脸。
“陈哥……叔。”纳西直截了当把话说了出来,“老大找你。”
陈氿皱着眉,吸完最后一口烟,狠狠丢到脚下捻灭。山顶人影又变成两个,相谈良久。陈氿走下来时,发现从高处看,所有人都聚集在下面,无数双眼盯着高处,热切又渴望,刚才还觉得嘈杂的声音飘上来,全都变成了低低细语。
他回身望去,发现风行跪在墓前,实实在在磕了三个头。
商队转道一趟大废墟,戴文塞了四个治管局的跟着队伍看护风伍和他母亲,约瑟夫派了支小队把他们领进巨兽之颅,停驻几天修整。
“挑几把喜欢的先拿走,你托我带的药品改天遣人送罗斯玛丽屋里,就别自己搬了。”风行站在货车门口,被她搭话的女人又高又壮,在货箱间梭巡着,翻找中意的武器。
“弹药也送来。”对方说。
“上次不是给过了?”
“快用完了。”她装好子弹,打开保险。
“你子弹是用来吃的吗……别在这试枪!”
“我又不傻,看看而已。”她摸着枪,“这里不像城市,用的快也没办法。”
“就当是谢谢你们每次都接送商队,过会和药品一块送过去,还有个东西一块给你送去了。”
“干什么?没用的不要。”
“怎么了帕尔斯里,怕我坑你钱吗?”风行有点想笑,“一穷二白的,就算我想,你也得有钱给我坑啊。”
“那不要了。”帕尔斯里拒绝的特别痛快。
“没要你钱,送了你个新面具。”风行似笑非笑。
帕尔斯里仔细凝视那个表情,试图从里面找到了丝傲慢,城市里来的人大多这样,带着点高高在上的不屑。然而她还没来得及凝聚视线,少女就扭过了头。
“你抱怨完了没有。”风行说,“真的,一路了,你怎么这么吵。”
“干嘛在这鬼地方修整。”项远的不满传遍整个货舱,“到了尤金又要多一堆审查!”
“有钱不赚是王八蛋,给我闭嘴。”
“净是一堆脑袋不正常的暴民!”
“项远!”
在车门外徘徊的纳西莎被吓了一跳,这是她第一次见风行声色俱厉的样子,哪怕之前她勒死自己亲叔叔时,也是一派无谓的表情。
降落坪上的废墟住民都看向这边,项远没再说什么,却一直呲牙咧嘴。她听见风行低声骂了一句,从帕尔斯里手中夺过自己要贩售的货物,瞄准项远。
“有种开枪啊!”项远叫嚣,“站着给你打打得中吗?”
风行面目狰狞,子弹倾泻过去,一溜地面被打的粉碎,项远大惊失色,鬼叫着逃窜了。帕尔斯里点点头,纳西莎以为她要夸赞一下武器威力,却听见对方说。
“枪法还是那么差。”
“我又不需要干这种事。”
项远躲在远处,冲两人比了个中指,扯着嗓子吼:“暴民暴民暴民!!”
帕尔斯里捏起拳头,向着项远走去。
“老大,老大。”有人慌慌张张跑过来,“那群香料和治管局的打起来了!”
“打呗,他们队长不也在打项远么,打完就好了,叫人别插手,戴文自己塞人进来,我还要替治管局收拾烂摊子?”风行拍拍纳西莎脑袋,“去把我和维拉的行李搬到房间收拾一下,约瑟夫肯定差人打扫过了。”
“我睡哪?”纳西莎懵懂地问。
“跟我睡一起,你又不占地方。”风行打量她,敲敲她的胸,“让你跟这些男人睡一屋你愿意吗?”
纳西莎想了想项远和卡莱瓦,一个劲摇头,在她心里这俩人几乎是所有商队男性的代表。
真是冤枉了其他人。
“这个,可是。”杵在旁边的人有些慌张,“小少爷……风伍吓到了,母子俩都很紧张,觉得是你……”
风行皱起眉来,纳西莎盯着她,过了几秒,少女低头对孩子笑笑:“看我干什么?”
纳西莎低下头不看了。
“看我会不会去帮他吗?”她盯着纳西莎,纳西莎盯着地面,“抬起头来。”
纳西莎硬着头皮抬头,视线和她对在一起,一瞬过后,疯狂乱飘。
“我长得有那么吓人?”风行使劲皱眉。
“没有,好看,太好看了,所以总盯着有点不好意思。”
风行失笑:“这油嘴滑舌跟谁学的,项远吗。”
纳西莎撇撇嘴,心想她才不跟那个白痴学,自己这种小鬼在贫民窟里得会说话才好过日子。好在她嘴角被拉扯着,撇一下也看不出什么来。
“你现在不在贫民窟了,不用看人脸色。做你自己,怎么想怎么做,想做什么做什么,谁敢揍你就揍回来。”风行看破她的心思,“虽然我的话要听,不过这次破例,你想让我帮他吗。”
纳西莎花了几秒理解风行在说什么,继而有些发懵,她努力分辨这是不是试探以及在试探什么,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还是自己会不会听话?她把视线挪回那张脸上,试图发挥一下自己察言观色的特长,风行挑了挑眉,湖蓝的眼睛在日光下一闪。
“让你看的时候不看,不说的时候倒是看回来了,怎么,这次也是因为我好看吗?”
“是……好、好……”纳西莎结巴起来,不知为什么刚才顺顺当当说出来的话突然变得难以启齿。她低下头,心觉阳光炽烈,仰着脖子看人实在太过刺眼,以至于多年回想起来,都记得这恨不能让人闭上眼的光芒,而少女笼罩在日光下,眉梢眼角都带着轻浮玩味的笑。
纳西莎想想那个和自己擦肩而过的孩子,那被维拉缇斯挡住的好奇、探究又惊慌的眼神似乎万分不解为什么自己境况和一个贫民窟小子发生了倒转。
她咬咬牙,小声挤出几个字:“都听你的……”
风行大笑着抱起纳西,一把举高,孩子惊慌躲闪的眼神无处可藏,全都落在她眼底。
“你还真瘦啊。”风行说。
纳西莎想我也没想到你还有点力气,
风行让卡莱瓦去解围,再见面已经到了晚饭时间,身后跟着鼻青脸肿的项远。商队有一半人没去社团食堂,而是在屋前空地三五成群架起锅。风行让维拉和卡莱瓦帮忙,自己抱着纳西坐在旁边,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凝视项远。
“看屁啊!”项远没好气的把水倒进去,洒出来一半。
“你是不是被揍了。”风行不忍的问,一丝没藏好的戏谑漏出来。
“老子不打女人!”项远愤恨地把勺子扔进水里,发现几人都用怀疑的目光看着自己。
“行吧,他们群殴,人那么多,我打不过不是挺正常吗!”他想挽回面子,表情下意识狰狞起来,可惜一狰狞就牵动脸上的伤口,疼得他倒抽冷气,“幸好老子跑得快……”
“知足吧,那个治安官断了几根肋骨呢,帕尔斯里肯定是看在生意的份上手下留情了。”纳西莎幸灾乐祸,项远一瞪眼,她就往风行怀里缩过去。
“跟小孩怄什么气。”风行没往心里去,“那个治安官怎么回事?”
“肋骨断了几根。”
“谁问你这个了,我说怎么打起来的。”
卡莱瓦想了想:“本来只是互相看不顺眼起了口角,后来就……毕竟是这里是废都,废都的人对当差的都没好感,反正就是打起来了,谁叫他们是治安官。”
“……”风行捏着鼻梁,有点头疼,“找医生看了没?其他三个怎么样?”
“看了,还好,剩下三个都是皮肉伤,没伤筋动骨,过两天就又活蹦乱跳了。”
“那就行,我不想被戴文那个死记仇的惦记上。”她似乎没什么胃口,胡乱吃了两口压缩干粮,拍拍手站起来,“你们吃吧,我和约瑟夫有约,指不定几点结束……”
“还按以前的准备么?”卡莱瓦问。
“嗯。”她看了一眼远处沉默的婶婶和风伍,似乎在考虑要不要去说些什么,最后摇摇头,径直离去了。
屋里只有两张床,维拉缇斯占据一张,和纳西莎大眼瞪小眼。
“你和风行睡一张。”她说。
“为什么????”
“因为你体型小。”维拉缇丝说,“难道你想和我睡一块?”
“我没。”纳西莎立刻否认,“和谁都一样,你可别误会。”
太好骗了。维拉想。只要换个方向诱导就立刻上钩。
夜深的时候,纳西莎终于明白了卡莱瓦在准备什么,一碗汤汤和几片药被他送进卧室。
维拉缇斯靠在床上看书,瞥过去一眼:“这是?”
“醒酒汤,还有缓解头疼的药。”卡莱瓦说,“一会大小姐回来提醒她吃。”
她坐直身子,神情严肃:“没想到你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类型……”
卡莱瓦用了一会才明白维拉是在玩笑,冲她露出个干涩僵硬的可怖微笑。
“打住。”维拉用书遮住眼,“算了,别笑了,晚上会做噩梦……”
卡莱瓦又恢复了石头似的表情,纳西莎怎么看都觉得他有点懊恼。
“她酒量不好吗?”纳西莎问。
“不知道,说酒量不好,有劝酒的从来不拒绝,说好,喝完了又会难受。跟约瑟夫见面更这样,每次都喝得烂醉如泥。”卡莱瓦说,“偏头疼,老毛病了,查不出原因,医生说是精神紧张作息饮食不规律造成的。”
“换谁都紧张,让大小姐歇歇吧。”
“她不能承认。”卡莱瓦摇头,“那个医生被威逼利诱把话收回去销了病历,精神紧张、感到压力这种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维拉缇斯沉默了会,重新举起书,卡莱瓦见她不打算再说什么,安静地退了出去。
灯火陆陆续续熄灭,维拉关上灯准备先睡一会,卧室里安静下来,纳西莎在悠长的呼吸声里辗转反侧。她第一次离开中心城,再怎么克制也难免兴奋。
门外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维拉缇斯悄无声息的坐起,摸向床头的枪。声音断了一会,继而是衣料摩擦的声音,仿佛有人靠着门坐下。纳西莎蹑手蹑脚凑过去,耳朵贴在门板上听了会,只听到粗重的呼吸声。
开门。维拉缇斯比了个手势。
纳西莎猛地打开门,罩在头顶的人影猝不及防整个跌向下来,她吓了一跳,就要躲开。
“谁!”维拉缇斯喝道。
“靠!”人影气得不行,“滚开!”
维拉缇斯呆了下,手里的枪被拍在地上,纳西莎一把拾起来,抬手顶在对方头上。
月光从门中洒进来,三个人都愣在原地,纳西莎看清了扶着墙半跪在地上的风行,湖蓝色的眼里恼怒又疲倦,自己手里的枪顶在她头上。纳西莎吓得扔掉枪,险些坐在地上,维拉缇斯扶住她,有些尴尬的拽起风行:“你怎么不敲门……”
“我又没想现在进来!”她甩手推开维拉缇斯,灯也没开就往床上倒。
“不洗澡啦?”维拉缇斯有点无奈。
“洗过了,回车上洗的,不是想你们已经睡了么。”回答她声音带着浓浓的疲倦,“也不知道约瑟夫跟谁学的在酒桌上谈生意……”
“啊,嗯,嗯。”维拉缇斯不清楚也不想清楚细节,“还顺利吗?”
“过程顺利到不一定,结果满意就可以了。”风行捂着脑袋,“药呢?”
“床头柜上,伸手就……唉停停停,别乱摸,碗要被你碰掉了!”
纳西莎眼疾手快把汤碗抄在手里,维拉缇丝想把风行拽起来,后者死沉死沉的赖在床上。
“人喝醉了都会性情大变的?”维拉缇斯有些无奈,“我以为她不论什么时候都很清醒来着。”
“我又没醉,只是头疼。”风行捂着脑袋坐起来,“我觉得有一千个高乐贝拉在我脑袋里载歌载舞拎刀乱砍……碗呢!?”
纳西莎蹲在床边,只露出半个脑袋,递过碗去,小心翼翼看着她,看得风行想笑。
“看你这怂样。”风行捏着她脸摇晃,“关门去。”
空碗落在木桌上磕哒一声,维拉缇斯爬回自己床上,风行在换衣服,窸窸窣窣的声音又一次传来,纳西莎站在玄关处,刚好能通过镜子把一切收进眼底。她有点无措,不知道现在该不该回去,明明都是女性,可她还是觉得尴尬。
屋里光线昏暗,少女表情模模糊糊的,身上伤疤倒是个个清晰,胳膊上一条长疤狰狞的往肩头蔓延,像是最近才有的。纳西紧贴着墙,似乎这样就不会被发现,她看着风行转身,露出左背上的文身,心口一个枪疤没去掉,虬结的纹路被做成火焰,散开的长发挡住了火焰中央,隐隐约约藏着某种图案。
风行的动作忽然顿住了,她转头看向镜子,眼睛和纳西莎的镜像对在一起。
“看什么呢。”风行说,“过来睡了。”
地上的凉意顺着墙钻进脊背又窜进脑里,纳西莎缩着脑袋钻上床,不知怎么有点落荒而逃的意味。
--
……结果黑血还是没写完,还要一章才行。
这次7000字,其实这章还挺温馨的呀是不是——总之明天争取把黑血收尾。


萨治从营火旁站起身来。他看见他的旧友布拉维奇来找他,踏着夕阳的余晖,影子无限地被拉长,看不清他的面容。
他还记得那天的谈话。他记得布拉维奇捏着一只烟斗,藏了一瓶酒。他和他在刚升起的火堆旁边,望着辽远的大废墟的黑色的土地,分享了最后一袋曲奇饼干。
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从布拉维奇的老婆到萨治的队长帕尔斯里。
“所以那个任务之后,队里现在就只剩下帕尔斯里,罗斯玛丽,泰姆和你啦?”
“还有小跟班罗勒。”
“罗勒?”
他是被帕尔斯里捡回来顶斯卡布罗的位置的。
“从那时帕尔斯里就不怎么笑了。”
萨治点起一根烟。那零星的火星愈烧愈烈。
“你们都是像罗勒那样被捡回来的?”
萨治笑了一声,低沉的声音很好听。布拉维奇几乎不能确认那就是以前老躲在他身后的纤细的萨治的声音。他看了萨治一眼,那一眼在夕阳的余光下深刻地刻在萨治的心里,但即使如此萨治也难以想起布拉维奇的面容。
脸部模糊,一如此时此刻布拉维奇给他的印象。现在布拉维奇直挺挺地躺在那里,脸上盖着一块布。萨治知道那布下面是布拉维奇被黑兽啃得血肉模糊的脸。他的身子微微颤抖,直到帕尔斯里粗糙而有力的手按在他的肩膀上。
虽然帕尔斯里什么都没有说,萨治已经明白她的意思。她没有看着死人,而是看着萨治。萨治也望着她,知道布拉维奇的存在已经在她心里抹去了。他敬仰她,因为她不会被死去的人拖累。
可你会不会记得我们?萨治在心里问。我们死了,什么都不是了之后?
帕尔斯里防毒面具下深邃的黑色眸子盯着他,似乎把他看了个透彻。萨治打了个寒颤,他甚至觉得帕尔斯里同黑兽一般冷血无情。他感觉有点口干,心底里涌上一股对死亡或是被遗忘的恐惧感。
“我不会忘记我的任何一位部下。”帕尔斯里突然说。
那声音如同一只铁锚, 让漂浮在恐惧梦境中的萨治得以重回现实。他仰望着比他还高和结实的女性,觉得她像是铜铸的。他握住她的手,感到一阵安心,如同被牧羊犬庇护的羊一样。
夕阳金色的余晖笼罩着大废墟灰暗的天空。煤渣与尘土飞扬着染黑住民的脸,黑兽的咆哮,机车的轰鸣与枪的声音挥之不去。篝火星星点点地从这个聚居地燃起,像草丛里升起的萤火。
“萨治。”帕尔斯里唤了一声。
他抬头看他。
“这次如果我没能回来,告诉大家忘记我。”
她从饱满的胸部间的缝隙取出一粒光滑的步枪弹壳,塞进萨治的手心里。
萨治的表情变得惊惶起来。
“不要跟我扯上关系。我就要去做一件我不得不做的恶事,把耻辱罩套在头上,除非搭上性命不能解脱。我欠某个家伙一份人情,赔上我的命也还不清,我只能做。”
“不行,队长,我非跟你去不可。”
“倘若我还活着,我就会回来找你,索要这枚命烛。那时你要是还愿意追随我,那就随我来吧。”
帕尔斯里平静地说。萨治知道她一旦对下属用了这种语气,便不可违抗。
所以他低下了头,单膝跪地,向帕尔斯里伸出右手,拇指向上。那是他们小队特有的表示服从与谦恭的手势。
帕尔斯里也伸出右手,粗糙的手指轻轻地在他的掌心滑过,表示对他的原谅与应允。随后她扛起几只改造机枪和大量的弹药转身出门,向车库( 实际上是个用木板和其他廉价的废旧材料拼起来的遮雨棚)走去,萨治帮她把几挺轻磁轨炮一并架到那辆破破烂烂却性能极好的越野车上。
这时候突然下雨了。萨治忙不迭地把身上防酸雨衣的帽子戴好,却看见帕尔斯里仰起头望着被烟尘遮得不见天日的天空。
“这里虽然是片废土,却是我这样一无所有之人的家园。”
萨治明明白白地听见帕尔斯里说。
==================================
帕尔斯里小队成员:
斯卡布罗(前任队长)(亡故)(斯卡布罗市集)
帕尔斯里(前任副队长)(队长)(香菜)
萨治(副队长)(鼠尾草)
罗斯玛丽(后勤与治疗)(迷迭香)
泰姆(火力支援)(百里香)
布拉维奇(火力支援)(萨治的好基友)(与妻子一同亡故)
罗勒(新人)(罗勒叶)
正在思考是否要招募加里克(大蒜)和欧妮昂(洋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