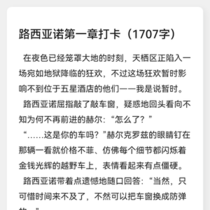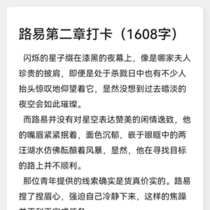「在此天栖区社会实验警报声响结束后的十二小时以内,所有包括谋杀的犯罪活动全部归为合法。
感谢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愿八百万神明保佑你们所有人。 」
————第零届日本杀戮日紧急播报系统
/ / /
本企为电影《人类清除计划》的衍生同人企划第三期,含血腥/恐怖/惊骇要素,请玩家再三斟酌可否接受再参与企划。
本企养老向为主,需打卡,文画手皆可参与。
本次杀戮日三期至此结束!感谢诸位玩家踊跃参与本次杀戮日企划,带来了美妙的杀戮日故事!
/
*学院pa,设定为柳四氿为老师丁香则为学生XD
*流水账有,私心我流天栖学校学生有
*字数4k4 如果没问题请食用!
和大多数学校一样,都或多或少会开设国文课,天栖学校也是如此,柳四氿是众多国文老师的一位,他在开学第一堂课就评价过:
“国文课,就像丁香一样,粗略闻他的鲜艳和芬芳,自然闻不到,需要用心去细细品尝。”
燕子踏早,柳四氿踩着樱花枝头做的筛网沥下来的金色的樱花瓣,还带着一些困意缓缓挪移进了教学楼。国文课通常开设在早上,早春的早上,听着枯燥的国文课讲堂,再适合不过睡觉了(偶尔国文课老师本人也不太想起床)。
从家里赶来,再一只脚移步跨过班门的门框,是一种偌大的勇气,柳四氿在来的路上的时候,心里默念和重复了不少遍今天要讲课的内容以及如何去带动自己和学生们的情绪,像是在赴约参加一场重要的谈判,也像是去进行一场幕布后的演讲。
做老师嘛,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演讲。
男人向春天借来了一脸的笑容,像珍宝一样捧起来走进了教室。带着一声清算和翻书的声音,他有些不太好意思和台下的各位直视,台下安安静静的,似乎在等待着老师的发话,是一种无声的尊重。
“今天我们来讲国文诗词。”柳四氿带着一丝宣告,嘴角依然留着一些弧度,像一只温柔的暹罗猫,用那双枯槁的手指从粉笔盒里面摸出来一支乖巧的粉笔,像是卡死的齿轮一样,吱呀吱的慢慢背过身去在黑板上慢工雕刻,轻柔细语似的书写着象牙般白的字迹。那是一首来自中国的古代诗人“杜甫”的一首诗,名为《登高》。
提及诗词,那必然要详细介绍一下其背后的历史背景,不管是从唐代的官僚制度,再到升官贬远的路途变迁,再到对于那种个人患得患失的家国情感,让一帮孩子去共情尚未浅知的异国他乡的诗人,倒不如去共情在温暖的清晨 ,听着如同安眠药一样的讲课内容和挫顿的嗓音,趴在桌子上美美睡上一觉有多么舒服(虽然老师讲的慷慨激昂到自己都要哭了)。
天栖学校的孩子们说一不二,敢想就敢做……一个会去做,那么集群效应就会跟着做,这个像蜜蜂一样的小团体分工明确,一个人负责打掩护应付老师,另外的一些人就调整姿势,从桌兜里面掏出自己的小蜜蜂抱枕美美的补上一觉。抑或是坐在最后排掏出自己的手机,打开社交软件吐槽一句这个老师讲课好没意思,然后切到后台,登录了每天都要肝的游戏。
终于在这位老师终于要开始讲解正课的内容之前,大片大片的学生们犹如睡美人,睡的舒舒服服,自自在在。
年纪稍大的老师还没能注意这片破败的景象,在回忆着教案的内容时用占满了白色的玉粉的手指在黑板上逐字逐句的朗读和分析,烙下了一个又一个如同月牙的白点。
“这句风急天高猿啸哀,意为在萧瑟湍急的风浪与阴云渲染显得天空更高的苍茫的世间之中,猿猴的啼叫显得这一景象更为凄凉和悲哀,这半句话动静结合……”柳四氿讲话的声音和语调充满了一股老先生的味道,声音拉得悠悠长长,像极了一首催眠的安眠曲。他顿了顿,看着书之后把自己的目光投射到讲台下方,希望得到一些听得津津有味的表情的互动,事实也确实如此,孩子们睡的津津有味……
当他看到这副破败的模样,顺着诗句的下半截的想说的话就立马咽了回去,然后胡搅蛮缠着被消化的透彻,透顶。
怎么连第一排的学生也睡得七七八八啊。他在内心想到。
柳四氿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他深刻理解在大早上上这种并非人人都能通透的理解到其中内涵之纯粹的虚无的东西是一种多么累又多么无聊,又是极其辛苦的事情(尽管学生们只是单纯不想听而已)。
他望着睡得就跟一颗颗软糖的学生,甚至打着呼噜,说实在的,有些不忍心把他们叫醒,像是老师们常说的话:“叫你起来不是批评你。”在柳四氿看来,那确实是屁话,毕竟不可能会有学生不在意自己上课被指名道姓点起来,在这种小小的共情之中,一种名为教师的责任感如同铜锤,敲着他心里的一扇小门。
叫也不是,不叫也不是,早春的聒噪和闷热让柳四氿的注意力有些涣散,他有些口渴了,或者他需要喝口水才能思考要如何应对这种令人无奈的局面,他对于这种场面已经有些见怪不怪了,放到十年前,他可能还会带着满腔的属于老师的激情大拍一声桌子,喊一声“怠慢!” ,在下午学生们精神饱满睡不着,转而交头接耳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时候,大拍桌子喊一声“肃静!”,在晚上看着学生们的晚自习的时候对着心不在焉的学生们大拍桌子喊一声“浮躁!”。但是他现在什么也不想喊,他只觉得过去的和学生这么较真的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些羞耻和不稳重。
蝴蝶扑棱着翅膀,一只又一只在讲台旁边飞着米黄色的舞蹈,自由的来客仿佛是他唯一的慰籍,顺着那些蝴蝶看过去,一只落在紫色的女孩的头上,一只则停在她的等待着老师讲课而继续书写笔记的笔杆上面,那只蝴蝶像是特邀的贵宾一样,大摇大摆的飞来停在女孩的笔帽,这让女孩不由得一惊,她下意识抖了一下笔,这位贵客便飞走了。
“我去…居然还有人听课啊!”柳四氿歇斯底里的在心里默念了一句。“真的怕不是蝴蝶仙子来眷顾鄙人的课堂了。”
柳四氿清了清嗓子,没能让这么失礼的话秃噜出来,他低头一只手撑着,一只手摸上了那张手写的座位表,一般这种排格子的座位表都是班里字体最好看的女生写的,娟秀的字迹映入老知青的眼里,好似巍峨的青山,又奔泄涛涛绿水。
“丁…香…”
老师的有意无意的对着纸张的发声拉走了女孩的注意力。
“嗯…?”
柳四氿有一些尴尬。
“噢!那就丁香同学来解读一下这首诗的颔联吧!”男人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他下意识用沾满粉笔灰的白色手指摸了摸鼻子,察觉到了一丝不妥之后把自己如同花猫一样的手指往上抬了抬,露出手腕,然后用它推了推眼镜,再然后,就伸手亲自为丁香指出来了颔联所在的位置。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丁香满载着柳老师的期待站了起来,米黄色的蝴蝶好似惊鸿,从丁香的身旁又如同离群的金燕,寻找下一个充满芳香的屋檐。女孩耳环轻颤,然后清了清嗓门,双手捧起来了国文课本,学着方才老师讲课时如同收音机一样的腔调说出自己的理解。
“无边无际的落木……”丁香也故意把语调拖的很长,柳四氿有些反应过来自己在别人眼里有多蠢了。
“落木的意思就是落叶!中国的古代文人们经常用‘落木’、‘落红’诸如此类的意象来代指落叶,这里可以称作树木的落叶。”台上的男人补充到。
“嗯……”丁香思考了一下。“无边无际的树木萧瑟的落下树叶,而奔腾的长江无穷无尽的滚滚而来。”
“很好!”柳四氿夸出来了这么一句。他或许正想对着其他同学大肆表扬一下丁香,诸如此类的,可能会说出“丁香同学理解和分析的透彻又到位”之类的话。但是台下依旧是一片死寂,似乎大家因为丁香给他们打了掩护,睡得更香了。
柳四氿的无奈在这堂课至此已经淋漓尽致,或者说,课本的内容只是太枯燥无聊,不适合学生们接纳呢?教材是死的,人是活的,关于课标的要求也大致只有几句抽象的教授学生们培养诗歌素养以及情感的熏陶罢了,考试可不考原题。
男人盯着黑板发了几秒的呆,像是忘词的年轻老师,又或者是根本没备课的随心所欲的凭借经验之谈的佛系老教。
他当着丁香的面把这一面白花花的字体擦掉,随即又重新用方正的字体写上一首新的小诗,作者依然是“杜甫”,但是内容却大相径庭。他对着那位精神抖擞的女学生平起来手掌向下挥,示意让她坐下。
一笔一划如同轻纱磨蹭,又是筛网,箩筐之中则就只留下了秀白色的字体了。
《江头五咏·丁香》
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
细叶带浮毛,疏花披素艳。
深栽小斋后,庶使幽人占。
晚堕兰麝中,休怀粉身念。
柳四氿顿了顿,他很少去讲课标外的东西,能不能讲出点名堂来基本上三分靠能力,七分看天地造化。他看着这位唯一的,还捧场的女学生,不由得想要试一试,想要告诉她,丁香,在古代文人的眼中,又是什么形象呢?或许是出于一种职业道德,他有些希望让一位学生去爱上诗词。
他放下书本,目光也从班级的大部分人的身上挪开,只留给了丁香一人。
“这首诗呢,是杜甫晚年在成都的时候写下来的,首颔联则写了花的形状:丁香花纤小柔弱,错乱地纠结在一起,但不那么热火朝天,反而垂挂下来,枝条不得不作为承托了,丁香花叶片纤小,上面略到纷飞的柳絮毛,在枝叶之间,花朵扶疏,颜色素雅,非常艳丽。”男人顿了顿,他从另一盒彩色粉笔之中选出来了一个略像紫色的笔杆,可圈可点对于“带浮毛”,“披素艳”的字眼着重划了醒目的几笔。他不紧不慢的卖了个关子,随后继续说道。
“颈尾两联则通过和前句结合的手法着重写出了自己对于丁香的感受:把丁香花栽在书斋的后面,读书的时候离的近便可以独自领略丁香的倩丽韵味,夜晚等到丁香花凋谢,然而散发出犹如兰麝般的香气,丝毫没有对自己凋零感到遗憾。杜甫这首丁香诗,赞美了丁香花的倩丽幽香,圣洁高雅,对自己的凋零并没有哀怨,反而是散发出兰麝般的香气洒向人间。”
男人一气呵成,从诗词的欲扬先抑,再到对于丁香的穿插着参差的表扬,似乎也间接的在暗喻女孩,如同丁香一样默默无闻,却清洁淡雅,在这独属于自己的小小的盘踞的地方散发着自己的一席的香味。
丁香听得有些入了神,她把那首诗抄了下来,抄在了自己的课本上面。好似她的笔墨也有着淡淡的香味,也引得蝴蝶振翅,停留在了纸面之上。一堂好好的课,正儿八经的变成了属于丁香一个人的小灶了,她又换了几个颜色的水笔,在自己的课本上仔仔细细从一些不足挂齿的背景故事,再到这一首新鲜的小律诗。起码她记住了“杜甫”,记住了这首有关丁香,或许也有关她自己的诗。
教室里依然死气沉沉,伴随着清脆的救人如救火的下课铃,个别强忍着困意一直在“点头哈腰”的孩子们像是得到了最高级的许可,终于也舒舒服服的趴在了桌子上面。
柳四氿伸了个懒腰,他有些感谢也庆幸自己难得讲了一节这么特殊的课堂。
“喔…该下课了,我本人不太会写诗哎…但是我还是留下一小半句送给丁香吧!”很显然,他这句话是对着丁香说的。
女孩愣了一下,她一时间没能分清,这位老师是打算送给真正的丁香一首诗,还是送给自己一首诗呢?她托着脸,在讲台上笨拙的男人踮着脚尖写在黑板最上层的字迹,她在心里,在本子上,在吹着气似的小声念了出来。
“温香似雪点点玉,颦蹙眉前,伯仲自有蝶入从间。”
————————————
“话说真是谢谢丁香了!拖住了老师,才能睡上这么美美的一觉。”
“哎……?”女孩没能反应过来一旁搭讪的同学的言喻,以及消化其中的信息量,调皮的孩子便如同箭一样溜出了那个与柳四氿来时相反方向的门槛。
办公室这边结束了一天的课程,柳四氿在办公室边刷着电视剧边批改着作业,他的耳朵旁边环绕着隔壁桌的女老师的闲言碎语。
“哎,你说,你们班的那个丁香,为什么身边总是来回飞着那么多蝴蝶呀?是喷了什么香水吗?”
“不能吧,我也喷香水,也不见我身上有蝴蝶。”被问话的女老师显然有些纳闷。
他们的谈话的对象和目光落到了一旁的柳四氿。
他正在丁香的作业本上的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把因为仓促下课,没能写完的小诗的后半段写完:亭静如伊细细语,春色门前,满园难忘丁香秀娟。
“哎,柳老师,我记得你对丁香评价挺高的,你说她为什么身边那么多蝴蝶呀?”
木讷的男人被打断了动作,他开始极力搜刮脑海中比较偏远的回忆,随即下意识地,伸出一只食指挠了挠脸上不存在的痒意。
“唔……我还真的不怎么注意这个呢……不过我想起来了一句谚语。”
“什么谚语?”
“花若盛开,蝴蝶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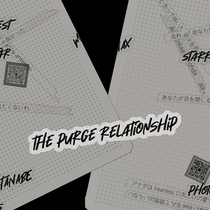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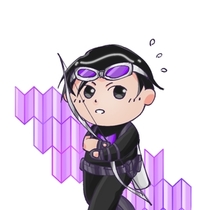



“金雨子,铜麦子,酒庆佳节酥透纸。蛙时语。蜻蜓曲。鸿亭高阁,烟远婆娑。何何何。”
柳四氿偶然想到了之前有幸在公司举行的踏青出游的时候,爬山在一个山顶的小阁子里,望着如同薄纱一样的雨丝,在随身携带的纸和笔写下的半首借着“钗头凤”的词牌名凑成的打油诗的上阕。如果要说是有什么寓意的话,那大概就是想到秋天的雨水和老家的几块田,按照农民的思维,雨水跟金子一样贵,是千盼万盼都求不来的。不过直到现在,他也没能写出来下阕,有的只是口袋里浸湿了大半字迹模糊的诗纸。
这场大雨贯穿了柳四氿的所有的衣服,厚重且潮湿和难受,他委屈着如同翻花绳一样糟糕的脸皮,跌跌撞撞的带着哭不出来声音的喉结跑动,看他那背影,像是喝醉了,又像是失恋的情种,他的背影瘦得如同纤细的禾苗,又像是乞丐一样褴褛,他头也不回地干呕着哭着,光打雷不下雨。
起码天上雨够大了。
平日里他会精心打理的头发也因为雨水如同荒野的杂草,寄生在他的脸皮,分夺本就枯槁的黄色的荒漠一样的皮肤的养分,那荒漠之中千疮百孔,黑色的如同仙人掌一样毛糙的皮肤毛孔肆意生长,只不过被关公裕几拳打的大抵不太好辩识罢了。
他一边跑一边确认背后有没有人追上来,像个小偷一样,从别人哪偷回来了自己的命。当然不能就这么继续在街上晃,他掠过一个拐角,为了避雨,以及不在路上遇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人,他决定闯进医院的侧边的小门里面躲上那么一会儿,雨水像粗糙的盐巴,用刺痛洗涤他的伤口。
无依无靠的乞丐在侧边的一楼不是那么显眼,但是大多蒙面党的党羽的脚步声和嬉笑传遍了整个医院,从一楼开始像是扶摇而上的澄清色的云彩,厚重且通透,如果仔细去听的话,或许还有惨叫如同生锈的铁水,从楼房的缝隙里面滴答滴答地流下来。柳四氿的目光扫到了一个标注着用日文书写的“闲人免进”的标识,他看不懂,但是直觉和对照让他意识到和理解这个标识具体的含义,那是一楼的药房。
即便因为杀戮日的存在,医院的人早已撤离得七七八八无影无踪。“闲人免进”的标语还是可以带给他安全感,他并没有意识到“药房”这个物资满盈的地方会是濒危的病人续命和蒙面党抢夺药品的争执中心,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向狼群投怀送抱,人类这种东西为了安全感,可以奔向并不安全的本身,以及在他仓促跑来之时,地上遍布了他的湿漉漉的脚印。
柳四氿因为全身湿透有些发抖,他的铜黄色的皮肤平地而起一个又一个隆起的细小的鼓包,以及如同棉絮和蒲公英的抽丝剥茧留下来的寒毛。
他不知道要做什么,他想拿回自己的手机,以及有些苛责自己的无能:手无缚鸡之力。
柳四氿大抵有些困了,可能是哭累了再或者是奔波了几个小时,要把天栖区逛个遍还要东躲西藏,他从来没有熬到这么晚过,他的头和眼睛就如同埋藏在鞋子里的砾刺,牢牢地链接着大脑传来疲惫和怠倦的讯息,他把身子往里面继续挪了挪,在一柜子的“精神类”药品旁边停了下来,他回忆起来曾经自己吃过精神类药品的日子,整日困倦,唾液腺不停地分泌唾液,对一切都麻木和无所谓,再也找不到任何强烈的情感。
就和现在一样。
虽然寒冷,虽然恐慌,虽然孤独,但是他还是想要在这里睡上那么一会儿,强烈的侥幸心理告诉他:就睡一会儿,一会儿就起来。
实际上他也知道自己可能这么睡下去就不会再醒来了。
醒来之后,我可以去找贽,杀戮日就已经结束了,醒来之后,我大抵找不到手机了,但是我可以询问好心的路人,我要怎么和路人交流呢?总会有会说英语的人吧,或者我可以再次找到那个挽弓的少年,在那之后呢?我可以通过他再找到渡边家?然后呢,贽可能就在那里等我。可是,可是贽要是自己走了要怎么办。
“……”现在睡过去就全完了不是吗。
柳四氿闭上了眼睛,他在想自己接下来要怎么做,崩溃边缘徘徊的意志加上语言不通的溃烂感如同杂草在他的清醒的思想中的花园里肆意生长,侵犯着他的理智和正常规模的行为方式,一触即燃的焦虑感把他的困意如同用刀尖剜取心头肉一样让他无法入睡。
在求生边缘和求死边缘之中游荡,才是最痛苦的。
伴随着闭目养神,越来越清晰的脚步声如同面粉,混进了雨水里,变成了拉伸张弛有度的面团,延展着和拉伸着越发清晰,像黄蜂取蜜一样迫不及待得钻进他的耳朵里,柳四氿疲惫且毫无戒心,直到脚步声几乎要近在咫尺,他才猛地惊醒,柳四氿的眼睛睁开了一半,他瞄了一眼那个模糊的身影:
自上而下的在月色滂沱下的漆黑,如同瘦长鬼影一样的撕裂感和肃穆,带着水光和水渍,如同抛光的银玉。
是他啊,刚才那个家伙。不好的感觉像是一片骨刺,刺穿了他的脊梁骨,把自下而上的刺激感翻腾到了他的脖颈,再到全身。
柳四氿的心理戏很足,在他闭上双眼思考万事万物之时,就好比在拥抱时间,过的很慢,又很快,慢到他甚至没能入睡,快到自己的处刑人又迅速的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
一片寂静,柳四氿蜷缩得更紧了,像是一个垂暮之年的老年人,他甚至懒得正儿八经的张开自己的眼睛,任由冰冷的脸上连带的雨水花白他的瞳仁,恍惚之中,他看到了千千万万的灯火,看到了流光溢彩的中华街,看到了红的发黄的路灯,他好像看到了自己的花盆。
“呃……你还好吗?”中文和那张面具相衬,未免不太和谐,赶来的不速之客摘下面具。试探性的声音从那张面具下面秃噜出来,掉在地上如同滚铁环一样溜到了柳四氿的旁边,打了几个转,然后在地上不甘心地啪嗒啪嗒了两下后便没了动静。
“……咦?”几个小时没听过的普通话在柳四氿耳朵里显得十分具有新鲜感,身在异乡的时候,这种清冽的如同泉水一样的故土的声音把他的疲惫一网打尽。
“我是说,我没有把你打的太疼吧。”关公裕自顾自地走上前,迎面对上对方惶恐的眼神,就像是放在一千年前,官兵驱赶着路边乞讨的乞丐一样。不一样的是关公裕的脸上浮现了不少愧疚,他吞吐国话的气质也让他显得随和了一些,他摘下面具,雀斑装点的关切的表情就像是坠入咖啡的厚乳糖,能从他身上看到的只有憨厚和淳朴。柳四氿一时间被如同洪水一样的讯息冲得眼冒金星,他有在思考这个人,就是刚才那个对我施暴的家伙吗?毫无疑问是的,雨水和黑夜包裹住了关公裕的脸庞和渐型黯淡的身影,但是如同烙印般刻在柳四氿心头的恐惧般的身型和那双被布匹包裹的拳头他是不会认错的。
柳四氿看着关公裕的动作,仿佛自己全身被麻痹,等待着从隶属于自己的处刑人做出任何事。关公裕放下了那个被雨水淋得几乎要流干血液的盆栽,那杆枪依旧露出半截,像是静谧的园丁,被埋在自己毕生挚爱的花园的土里,露出半个脑袋。
柳四氿盯着那个盆栽,不说话,他的眉头拧成一团,恐惧像蜘蛛,肆无忌惮地爬上他的脸,他仰起脸端详着对方,想要看看对方究竟想干什么,或者说,他认定自己无路可退了。
关公裕蹲在地上,像是一只大型犬,或者说,狼本身就是犬科的种属的。他伸出了因为打人而关节处全部破皮的手指,轻轻按压了一下柳四氿脸上的淤青。
“嘶……!”柳四氿下意识叫出来了这么一声,然后把自己的头收了回去。
“啊啊对不起!”关公裕面带抱歉的把自己的手收了回去,像是不小心触碰了高温的壁炉一样,那个紫色的淤青般的伤口灼烧着关公裕的指尖。
委屈感又一次涌上来了。柳四氿咽了一口唾沫,试图压制那股喉咙中的刺痛,即便他说出这句话的第一个字的时候还是带了一声变腔。
“我说你啊!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柳四氿拿起来了那个盆栽,然后用另一只手撑着地板,身子靠着墙壁挪动了几下自己的屁股,离关公裕远了一些距离。
“啊……对不起,我忘记解释了!”
关公裕清清嗓子,心跳又一次在他的胸腔悸动,这次则是他害怕自己不被原谅。以及,他不愿意去面对自己做出的这种事。
“我叫关公裕,我也是一名国人……我为了保命混入那些戴面具的人群里,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要被迫跟着来到医院杀死那些仅有一口气的重症患者……”他的声音清晰又洪亮。
“唔……不好意思,只能委屈你了……”关公裕有些不敢直视面前男人的眼睛,他不去看又知道柳四氿会用什么样的表情看着他。
一时间柳四氿没能处理这样的信息,这样的事实对于他来说未免太过大起大落。崩塌般的文字如同破碎的天空,掉落着几顿重的云彩,一片又一片压在他的身上,柳四氿愣了良久才恢复了开口说话的能力。
“他妈的。”柳四氿吐出来一句国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理由太冠冕堂皇,还是自己莫名其妙被打了一顿感到气愤,往往人性就是这样,一旦一者有示弱的念头,那么另一者就会展现自己的愤怒。
他想对着这么一张人畜无害的脸来一个大比兜,实属是难解心头之恨。但是如果要对着这么一个善念的理由发火,他做不太到,但是让自己忍气吞声自认倒霉,那他也不太做得到,要他对着这张脸发火,他似乎更有些做不到。
“那你就不能手下留情一点吗?”
柳四氿像个兔子,把手上的花盆推到了一边,随即跳起来气的直跺脚,他嫌这样不够解气,然后把自己的拳头笔直的锤在了墙上,不由分说得,墙纹丝不动,他锤得自己手关节生疼,心里反而因此更窝火了,他猛地蹲下来揪着自己的头发希望自己冷静,更像是一只耷拉着耳朵的兔子了。
“啊啊啊……您别生气,我也是被逼急了才……”关公裕有点慌了,他从口袋里面掏出那个浸水的手机,用宽大的手指仔仔细细擦了手机屏幕,任由指尖的纹路摸索过来每一个裂纹,然后郑重地递给了对方。
柳四氿皱了皱眉头,试探性地接过了那个手机,他感觉那个手机滚烫。带着一丝期待,他咽了咽口水,然后长按了因为浸水而自动关机的手机的开机键,两个人盯着那个手机发亮的屏幕,然后一个大大的白色的log闪进他们的眼帘,好像空气正在此刻凝固了一般紧张又焦灼。
在那个log闪了两下之后,银白色的边纹镶嵌进了漆黑的周遭的背景的黑色里,然后消失,又是短暂的等待。主页面的壁纸跳了出来,那是个土里土气的山水图片。
“谢天谢地!手机还能用!”柳四氿迫不及待得打开了锁屏,查看软件的正常使用情况,虽然碎掉的屏幕让他心疼不已……
“啊……话说你的屏保好土啊……”关公裕不自觉的吐槽出了声,他的一些老一辈的亲戚好像也是用这样的图片做屏保。
“你懂什么!”柳四氿受到了来自和审美相关尊严的一击,他在誓死捍卫自己的品味。
“话说这个是什么手机啊,防水性能这么好?”关公裕岔开了这个不能继续深究的话题。
柳四氿愣了愣,他看了看手机背后的标签上写的出厂商。
“嗯……好像是三星的手机。”
柳四氿觉得不能就这么岔开话题,明明他才是不占理的一方,男人收起来了手机,像小学班主任一样又开始耷拉下来脸,把压力给到了关公裕。
“那你来杀戮日是来干什么的。”柳四氿开始查户口式的提问。
“旅游的呀。”关公裕表现的人畜无害,好像这就是事实。
“旅,旅游……?”柳四氿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如果说根本不知道杀戮日这种东西的话……怎么说都太可疑了吧,然后理所当然的混进蒙面党之中什么的。
“那您呢?是为什么来杀戮日,总感觉您很容易被图谋不轨的人欺负呢……”
“啊啊!要你管!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家伙。”柳四氿打断了他的话,虽然是对方的忠告,但是让关公裕作为劝解的人来说,得到柳四氿的认可还是太牵强了。
“我来这里就是等着被你揍一顿呢!”
气氛有些尴尬。
“啊……我替您处理一下伤口吧。”关公裕为了活跃这种气氛,提出来了这样的用来赔罪的请求,通过他剔透且浑圆的眼神,他看到柳四氿脸上的肿胀和伤口就像是一个个隆起的山丘,让这平原之上的荒漠平仄都显得太过诡异。
还没等柳四氿去同意,他就慌慌张张地去其他的柜架上面找碘酒了。留下年龄较大的那个男人闷闷不乐的努了努嘴,开始检查自己的电子地图的正常使用的情况,说真的,柳四氿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如果硬要说的话,他更像是一只等待着别人修补的破旧的布娃娃,脸上的纽扣和开线一处又一处,作为对照的,则是一处淤青,又一处皮开肉绽,鲜艳的颜色让人想到那在芦荟上绘声绘色的紫色。
关公裕搜寻着紫黑色剔透的碘酒,就像是在超市里选购面包和矿泉水一样,他拿过来,顺便还带上了一包创口贴和一条绷带,他拇指和食指关节并用,扭开塑料齿环的啮合,然后均匀的给白色的棉签涂上颜色,庄重的给眼前的人脸上的伤口涂抹和消毒,他有那么希望这个棉签是一个可以把伤口抹去的橡皮擦,蜷缩在角落里的柳四氿皱了皱眉头,他有点犹豫,随即便伸出了脑袋。
关公裕上药的动作就像蜻蜓点水一样,他的动作尽量轻,但是过于小心翼翼,在激起一圈一圈的水波和纹路与惊鸿过隙的隔阂之间摇摆不定,他皱着眉头,应该说刚才打人有多用力,现在就有多小心。好像在掂量和捏着一根针尖,用眼睛打量着针孔然后引线,然而那根针变成了脱缰野马,毫无防备地戳到了柳四氿的头上。
“嘶……!”蜻蜓的涟漪最终还是荡开了,摇摆不定地疼痛酥麻的像是漏电线,喷薄在柳四氿的全身。他因为刺激猛地收回脑袋,后脑勺却又用力过猛磕在了背后的墙上了,又撞到了另一处伤,他把手抬起来下意识去摸,只能摸到稠密和有些热流的分不清是汗还是血的粘稠物,随后脑袋一垂,连同雨水也没能滋养的发丝也耷拉下来,他像颗破败的用光秃秃的枝条遮住自己衰老的主干的柳树。突然又说不出话了,不知道是不是错觉,男人全身微微颤抖,好像又哭出了声,但是又好像没有哭罢。
“啊!对不起!”关公裕好像意识到了自己不小心用太大了力气,因此有些束手无策地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看着低着头好像在啜泣的柳四氿,捕捉着他如同苍蝇一样颤抖着的身躯,一点点残存的“尊老爱幼”的道德感通过某种示弱从破破烂烂的老兔子的脸上,通过如同尸斑的伤口里面混杂着脓水流出来,一样令人恶心,一样令人感到膈应,关公裕想到了不久前在雨里的暴行,他不敢告诉眼前的这个人,也不敢承认以及告诉自己。
他像一个在杀戮日教唆下的坏孩子,有些迷恋上了暴力。
“你他妈会不会涂药,拿来!”柳四氿猛地抬起来了脑袋,他粗鲁地抢过了关公裕受伤的碘酒,晃动的冲击甚至让他弄洒了一些闻起来略显苦涩的液体滴在了关公裕的裤子上,这让男人有些在意,毕竟是他对着一份如同宝玉一样无暇的“善意”发火。
柳四氿有那么一瞬间在犹豫自己要不要说对不起,碍于面子他绷紧了嘴巴,对着手机的前置摄像头开始了如同上妆一样的涂抹,随后在关公裕的要求下,郑重地在他的鼻梁上以及其他淤青的伤口处,贴上了几个棕色的创口贴,关公裕的手指冰凉且宽大,细密的如同薄纱的汗液在他的手心悄悄地发芽、生长、绽放、汇聚成河,变成了一把剑,磨损了关公裕手心绷带的边缘,让它变得漆黑并且满是疮痍的锯齿,鲜红色渗透在被雨水侮犯的绷带表面,又通过氧化变成了铁锈般的带着一抹橙色的暗红,像是渗漏的正义感,又像是死在空气里的同情心,抑或分崩离析的淡漠的共情。连同像那枝条一样的绷带顺流而上的手背的广场,柳四氿看到了无数个崩塌的山峰,那些指关节破皮,皴裂,结痂。
柳四氿看到了分毫的同情,夹在在同情之中的还有不甘和愤懑,他无能为力,他早已被生活磨平到懒得去计较和讨个说法了,那没用,那没意义,有的人生来就是贱命。
柳四氿知道他生来就是贱命,有人打他把自己的拳头打破皮,那就可怜了那双拳头了。
他不说话,突然而来的情绪让他有些疲惫,男人喟然,他像垂暮之年的铁锈缠身的汽壶,他无奈之下自顾自地拉过来了关公裕的手,放在他的膝盖上,关公裕咽了口唾沫,下意识想要问些什么,但是他没能问出口。
男人熟练的揭开他的一圈一圈,就如同玩着毛线球的小猫咪一样缠得乱七八糟的绷带,连同到最内侧一圈的和伤口贴的死死地绷带也一并小心翼翼地揭开了。殷红和粉色的肉块暴露在空气里,好像不加任何掩盖就暴露在寒风之中的死婴。
柳四氿用指甲抠掉了崭新的绷带的启封皮,上了碘酒,然后一圈又一圈,一匝又一匝,均匀地缠住了那个存在于粉色的土地上的裂谷,他懒得猜这处疤是哪来的了。再然后,就小心翼翼地给关公裕手背处,用剩下的创口贴包裹起来,他看着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并且又多又满的“艺术品”显得有些得意。
“啊……谢谢您。”关公裕有些被这个男人的善意感到了同情和怜悯,超脱于所有的关于人性的丑恶与自私自利,他苍老又消瘦,却如同一股清流,愿意去继续选择单纯。
关公裕抬起来了自己的手掌,他下意识握了握拳,比起之前的老旧的绷带,新换的绷带要舒服很多。
“你要是回国之后,不请我吃顿饭都对不起我啊!”柳四氿试图摆着一副臭脸,但是那黝黄的脸上,贴满了消减锐气的创口贴,显得他毫无威严。
不过不由分说的,柳四氿也这么觉得,他只是碰巧撞到了一个“好人”而已,如果要说把他杀掉,那只是举手之劳而已,在杀戮日之中,死去一个人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他死在大街上,等到天明之后会被集中运走,焚化,最后埋到土里,为杂草恣肆贡献一份力,终究只是从关公裕手下捡回来一条命而已。
还跟野狗一样活着就是最大的恩赐,他知道自己不应该要求那么多,或者说,他有些后悔,害怕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又要被打一顿哩。
“啊…好,那联系方式……”关公裕显然认可了这个处理方式,但是老天爷不会让他们这么轻松得同归如初,药房是重要的地方,是病危的重症患者最后一丝救命稻草,也是物资的重要贮藏点。显然一位留在一楼正门的蒙面党听到了他们的动静,他像个机械地扭转脑袋的摄像头,顺着动静来到了药房正门口,趴在玻璃上向里面望去。
关公裕率先察觉到了不详的眼糜,他伸出宽大的手掌捂住了柳四氿跃跃欲试的嘴巴,随即像搂着一个布娃娃一样把对方扯到了视野尚未开阔的死角位置,柳四氿的眼睛惶恐地如同小半个灯笼,向上扭动着眼球,盯着关公裕的表情。
他看不到关公裕的表情,也看不到自己的命运。
空气十分凝重,迎接着柳四氿在茫然之中被钳制得不敢出声的五官的,只有连绵不断和滂沱的大雨。
在审查过后,在二者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的时候,伴随着脚步声如同大山中的回音一样逐渐俱寂,关公裕方才舒了口气,他松开捂住柳四氿的手,在对方湿漉漉的惊魂未定中还未能缓过神,他抱歉的笑了笑。
“不好意思啊!联系方式就下次见面再说吧!这里太危险了……”
————————————
关公裕拉着柳四氿,他们两个人匍匐着,如同夜里的两只猫子,佝偻着背钻出了那个侧门,还没有来得及规划好和安排后续内容,不约而同的,抱着花盆的男人则和关公裕分道扬镳了。柳四氿不知道关公裕要去哪,他也不认得路,起码在这个变态横行的鬼地方,他一秒也不想多待,只不过和关公裕嘛……
还是不要再遇到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