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好我是dlc。
已经写疯了感觉都是胡言乱语,有看不懂的地方我先跪下了。
省流版:
1、应渡被林以重说服打算加入大烨幻想议会,玩空王座(太玄子)但群相议政版。
2、应渡直到连衡也是议会成员之后,利用宰相职权打开洛阳城门。
3、应渡在皇陵种了桃树,顺便把难民托庇皇陵之下(折奢靡)。
应渡看着废墟一般的皇陵逐渐被修复,杜家添补的金银玉石让昏暗的地宫也熠熠生辉。既然此地已经有人负责,他将皇陵的工匠留下,打算转道回洛阳。六部衙门如今已在洛阳安了家,长安不差他这一个宰相,但工部确实是很缺一个尚书。
只是在他启程之前,先被一架车马拦下了,林以重从马车中钻出,招呼应渡上来一叙。应渡没有拒绝,车内确实比路中暖和许多,也不至于太过打眼。多年未见的座师虽生华发,如今尚且神采奕奕,他却觉得自己已然枯竭如朽木。
林以重当年与应渡意见相左,孤身回了益州,如今再见,却已物是人非。应渡不得不承认老师当年的看法是对的,烨灵帝确实算不上明君,即使他甚至算得上被皇帝关照的那个,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荒唐昏庸之处……只是如今,他也并非完全所托非人。太玄子愿舍去仙躯护卫百姓,这是他所没有想到的。只是有什么比在意识到君王值得追随之时,却不得不看他躯壳尽毁,困居一城更为苦痛的呢?陛下当为天下主,可是,这天下何在?
“有梁为何烦恼?”林以重为他斟了一杯茶水,冬日寒凉,即使小心保温,这茶水也早凉透了。
应渡将一杯冷茶吞入腹中,勉强鼓动脸上肌肉,却也牵不起一个笑来,最后只能勉强一叹,“老师是在消遣我吗?我为何烦恼,老师既然今日来找我,自是早有谋算吧?”
“这大烨再没有什么叫你愿效忠的人了,是也不是?”林以重看着学生那木然的眼眸,一字一句地落下。应渡自然是否认,“豫王赤子之心,亦有才能,老师何谈此言?”
只是他说的话,如今怕是连自己都骗不了,林以重直截了当地揭露他心中所想,“若陛下钦点豫王继位,你自是会效忠于他,只是如今陛下安在,却深陷囹圄,你不甘心。”
应渡忍不住攥紧手中杯盏,他抬头看向对方,“是,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什么“知我罪我,其惟春秋”,陛下不在意,但是我在意。赤梁战事赢得算不上漂亮,各地又起兵乱,我要怎么接受,史书关于陛下的最后一笔,是穷兵黜武,民怨不休?此前陛下的荒唐史书尽数记了,但如今最后的恩泽,怕是无法在青史上留存吧?但我不通战事,亦不会道法,所书所学,于当下有何益处?我从未这样觉得,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话,竟然如此贴切。”
“若是有法子叫陛下青史留名呢?”林以重知道自己来对了,这个学生还像当年一样好骗,“如果此后千秋万代,龙椅上的人都只有太玄子一人呢?你仍能为陛下尽忠,用你所书所学去更改陛下的身后名。”
“老师说笑了……没有这样的法子。”应渡沉默半晌如是说,但此刻的动摇已经不需如何辨别。
应渡与林以重一叙,很快回了洛阳,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甚至觉得自己疯了,但是他无法拒绝。只是大概是运气不好,他来洛阳没有几日,洛阳就被围困了。洛阳城内人口众多,如今又多了长安来的百姓和官吏,无论如何是经不起消耗的。他勉强以宰相的职位和握在手中的粮食供给控制百官,暂时维持了城内的运转,但若是再无援军,显然洛阳沦陷也近在眼前了。
若围城的只是叛军,那他不畏惧就此殉国,但若不只是叛军呢?他看着眼前的年轻人,这是林以重的儿子,如今的盐铁转运使言为轻。原本洛阳给长安的盐铁粮草都是由他来管控的,他手中握着一条私密的粮道也不出奇。言为轻比应渡还要沉默,似乎自己只是一个信使,“储藏的食物不足以供给整个洛阳,我虽有法子走密道从洛阳脱困,但洛阳城中有那么多人,总会有人无法逃脱的,到时候就是饿殍遍地人人相食的场景,应相难道忍心看到这个吗?若你在等援军的话,那不必等了,兵部尚书连衡带人围住了洛阳,如今长安与洛阳不过是一对苦命鸳鸯,寄望对方没有什么用处。”
“那你想要我如何做呢?我没想到,老师如今竟然为这逆贼做事。”应渡语气淡淡的,他当然知道现在的情况严峻,但若是投降叛军,那他宁愿去死。
“不是黑刀会,是兵部尚书。”言为轻更正道,“若是兵部尚书来此呢?二人将来或许要同为太玄朝效力,应相难道不愿给他一个薄面吗?何况那是连衡,应相也知道他的为人,将洛阳托庇于他,我想这是要比困死城中好上许多的。”
于是应渡答应了,在献城的同时,带走了城内的诸多百姓。他们大多因长安乱局失去了家园,如今在洛阳也没有容身之处,天地惶惶,又该往何处去呢?应渡抚摸着藏在袖中的桃树枝,原本他带上这树枝只是为了托物寄情,被困洛阳的时候,也想过不如效仿哥舒凌,已满城血肉为祭,饲育桃花诛杀城外贼寇,但他还是太软弱了,不是做将军的料,以至于一直到言为轻来做说客,这枝桃花还没能种下去。
不过他已经想到,这桃枝要种在哪里合适了。经由杜玦扩宽了的皇陵如今规模更大,地宫中的陪葬品已经被黑刀会的人劫掠一空,空置的空间正巧可以容纳这些流民。地下温度要比地上更稳定,也没有风雪倾袭的困扰,而这些流民寄住在地宫之中,还能为修建皇陵尽一份力,也算是物尽其用了。他想到自己从王焕荼手中拿来的奢靡卡,和之前准备好在此消耗的金银,如今换做米粮来供给流民,倒是正好的事情。至于地宫中的玉石装饰,想必不会有百姓敢在桃树下偷盗太玄子的祭品。
只是他的善心也没有那么纯粹,大烨朝的国运根基在皇陵,在民心。他应渡做不到招揽民心,但若将桃树种在皇陵之上,这大烨的国运,应当尽可供陛下享用吧?
应渡的计划尽展得很顺利,虽然百姓并非完全情愿住在墓室里,也并非真有胆子与桃树为邻,但对于流民来说,有一口吃的是更要紧的,何况应渡并不吝惜家财,金银尽付黄土中。有许多人为他的狂悖所惊骇,但太玄子没有意见,自然也不会有人能说动他,陛下虽化身桃木,威势却比端坐在皇位上时更叫人畏惧。此番恩威并施之下,皇陵总算在冬雪将邙山埋没之前完工了。
应渡手托桃枝,将其埋入皇陵中心龙脉所在,脸上牵起一抹缥缈的笑,“陛下圣鉴。臣本寒微,蒙陛下拔擡,位列宰辅。今大烨气运如风中残烛,臣愿以己身精血为祭,引国运注此桃枝。皇陵净土,当开仙葩。臣之精魂血肉,尽化春泥;大烨山河气运,皆作滋养。但求太玄朝可证天下民心,助陛下超脱凡骨,早证仙道。若得见桃花灼灼盛于陵阙,便是臣此心所愿。”
或许是金卡确实要更有灵气,一朝国运更为贵重,随着应渡血液浇灌,桃枝近乎落地成木,眨眼成林,冠盖满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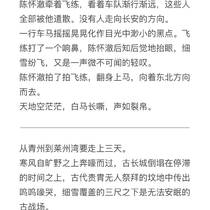

dlc的扩展包,里面包括了赤仙会清君侧内容。
省流版:连衡与赤仙会和黑刀会结盟合作,牵线人是前宰相林以重。在联军包围长安和洛阳之后,闻人俟孤身入长安于桃树前宣读檄文说服太玄子支持新生的朝廷(君主立宪但是君主是牌位版)
闻人俟脱下身上厚重的披风,室内燃着的炉火将整个房间烘烤得有如春至,让刚刚从边塞一路奔袭而来的少年额头冒出薄薄汗意。她有些潦草地拨弄被风吹乱的头发和沾染了污渍的长衫,才在房间里唯二的那把椅子坐下。
遮着面的大贤师递给她一杯已经放温的茶水,“圣女此行辛苦,不知阵法那边情况如何呢?”
闻人双手捧起茶杯,先是浅浅啜饮了一口,然后才牛嚼牡丹地将杯中茶水灌进嘴里,如此往复三次之后,才终于开口说话。此前被冥虚子分身弄出的伤还没好,声音还是哑着的,“一切都好,西南两方的布置应该是不会出问题的,我想其他地方的阵法应当也不会出什么太大纰漏才对,怎么大贤师这样急着叫我回来呢?”
大贤师只是笑,干脆取了个海碗来装茶水,顺手把已经剥好的句子递给她,“确实有事,而且是要紧事。你可知黑刀会已然取了洛阳,河南道已然半数尽在掌握之中,关内是连尚书的兵马,若我们真要起事,就只差最后一步了。”
闻人俟有消息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连往嘴里塞的橘子都忘了吃,“连尚书竟然还没拿下长安吗?”
大贤师摇了摇头,“包围长安容易,要打入长安却很难,圣女此行以桃木诛杀冥虚子,觉得这桃枝威力如何呢?”
闻人懂了,她还是有些不解,“那桃枝若是敌人的话,确实十分可怖,我听闻哥舒将军曾以桃花为阵屠戮千军,长安为烨灵帝禁脔,恐怕比那赤梁战场上的分支要更加厉害。不过连尚书都奈何不了这个,难道大贤师觉得我可以吗?我不明白。”
“我自然不是让你去打长安。”大贤师将身边一封信递给闻人俟,“武斗不成,自当智取。如今我等已经打出了清君侧旗号,若是连长安也进不去,岂不是平白叫人笑话?何况太玄子视我等为仇寇,我们才需防范长安的桃花,但若是太玄子视吾等为友呢?”
闻人俟愣住,这话说的当然没错,但是太玄子难道真的会答应吗?他有子嗣有兄弟,哪里有必要与起义军商量皇位的。不过大贤师既然这样说,总不能是特意把她从赤梁叫回来耍的,所以她姑且半信半疑地打开信封。这是林以重写来的信——林以重虽说明面上只是书院院长,但是赤仙会中许多事务都是他在处理,闻人曾经腹诽,大贤师聚民为兵说不得也是他的主意。
信上说了细说了这几月来他的布置和手段。赤仙会和黑刀会合流本就是林以重大力促成的,早在黑刀会起事之前,赤仙会便将信众渗透淮南道,如今想要合流,竟然并未遇到多大的阻力。他又转道长安,原本只为劝服应渡,却有了意外之喜——连衡包围了长安城,这让他抓到了可乘之机。林以重不愧是多年的官场老油条,竟然说服连衡与两会合盟,原本只算是匪兵的赤仙会与黑刀会,现在倒是官匪勾结了,倘若连衡愿意,兵部尚书诏安一下匪兵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最为重要的是,其中提到了一个新的朝廷——
或许那并不是新的,毕竟这朝中仍尊太玄子为皇帝,庶务百官自处,具体细则由诸位丞相统领,大决议便当以一腔热血为祭,听取太玄子天音决议。这与如今的朝廷并无什么区别,但是——太玄子会是永远的皇帝,一道能让人信任的天音,一位不存在的神。太玄子今朝过后或许升仙,也或许自此消弭,但百姓如何知晓此事呢?他当然可以做永远的皇帝,就像那在庙宇中接受跪拜的神像,不言不语,却寄托着千万人期望。太玄子今岁过后就不会再有言语了,但是那有如何呢?本来百姓就不能得见天子,只要收拢权势,将天音的解释权垄断在几位大臣手里,那和如今自是不会有什么区别的。
而林以重拉拢连衡和赵百成的,便是这可垄断天音解释权的宰相之位,只要太玄新朝的构思能成立,那么大烨本就十分富余的宰相之位,再多几个又有何妨呢?遇事难断,那便投票决议就是了,烨灵帝此前荒废朝政的时候,几位宰相们不也是如此过来的吗?这样的新朝对皇室以外的人,实在没有什么坏处,毕竟除了这皇子龙孙,也没有想过要登基的事情。但若是有机会成了宰相,头上还没有皇帝压着,哪个官员不愿意呢?或许世家会舍不下这个从龙之功,那便是这起义军“清君侧”要做的事情了。闻人已经彻底明了了,她要做的就是说服皇帝,只要长安桃树不反对,那么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
长安依旧在太玄子掌控之中,所以闻人入城之事第一时间就被他察觉了。不过闻人并不担心这件事,这位荒唐的皇帝,在成为仙人之后仿佛真有了仙人的心肠,看在她曾经浇灌那么多桃树的份上,不真的在长安作乱,便不必惶恐会为桃花斩杀。她徒步到了那桃花树下,这棵桃树被照顾得很好,比之当初闻人俟离开长安之时要更为粗壮了,宫苑的废墟已经彻底被吞没,有些干脆嵌进了树身之中,盛开的桃花将半个长安城笼罩于树影之下,凛冽的寒风被桃花一绕,似乎也变得温柔起来。
闻人伏跪在地,利刃撕扯开腕上的皮肉,让殷红的血水顺着指尖滴落在地上,她能听见桃树根茎凑近带来的窸窸窣窣,最后一根细枝甚至是珍惜得吞掉伤口渗出的最后一点血色才缓缓褪去。太玄子确实克制极了,她想起曾经自己在桃源斩断的那节手臂,妖桃不吸进最后一滴血是不会罢休的,但是……他们不一样。闻人俟空茫的眼中倒映着繁盛的桃花,声音沙哑却掷地有声,“某有一事启奏陛下。”
“今观朝堂之弊,莫甚于壅塞;天下之苦,莫深于不平。大烨之危,非在边患,而在萧墙之内;非因天灾,实为人祸所致!”
“观彼朱门贵胄,身居华堂,心同朽木。父子相继,把持清要之职;姻党勾连,垄断进取之途。或倚祖宗余荫,平步青云;或仗金银开路,窃居高位。问其农桑,不知五谷;询其兵事,未识六韬。终日唯知宴饮酬唱,竞相奢靡;彼此包庇徇私,共结网罗。”
“致使寒门才子空怀济世之志,终老林泉;布衣英杰纵有安邦之策,难叩天阙。如今大烨民生沸腾,众生犹如鼎中焚蚁,岂不痛哉!”
“尤令人发指者,帝归长安,天音尚存,彼辈竟生裂土分疆之念,暗怀觊觎大宝之心。武安所持御诏真伪未明,二皇子身负弑父疑云,豫王虽居摄政之位,实为傀儡之身。满朝公卿,竟无一人为天下计!”
“我乃山野布衣,于世家眼中不过草芥,本欲独善其身,偏逢乱世难全。幸得天下义士相扶,方能存续至今。然见陛下以万金之躯,宁损己身而不伤百姓;以天子之尊,甘受污名而护佑黎民。古语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如此明君,怎不令天下豪杰倾心相随?”
“今感于陛下浩荡天威,遂奉天举义,非为犯上,实为:清君侧之奸佞、开寒门之通途、解百姓之倒悬、扶社稷之将倾。愿天下有识之士,共鉴此心,同举义旗,再造清明!”
闻人俟并不清楚太玄子究竟会不会同意他们的想法,将太玄作为国号,永生永世供奉太玄子为皇帝,这件事对他来说会有吸引力吗?但是她清楚,太玄子在乎国运,在乎民心,若是起义军掀起战火,那他在与冥虚子的争夺中就会少一分胜算,但若是起义军皈依新朝呢?若是起义军以太玄为号,千千万万百姓尊太玄子为永世的帝王,天下归心,自是于国运有益。
“这是在威胁朕吗?”陌生又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太玄子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但是语气却很冷淡,她无法分辨其中的情绪,只是强自镇定,“非也,是为助力陛下登仙。”
太玄子嗤笑一声,他自幼长在皇室,林以重也曾教过他,他怎么会不懂这折檄文里写的到底是什么?但——苍生危如累卵,民生有倒悬之急,这话没有说错。哪怕他知道这就是他们的计谋——把天下苍生和大烨皇室放在天平上要他做抉择,无非是要看他是太玄子还是晁玄曦,但太玄子已经被困长安,既然无法走出去解决这群逆贼,那收下这份糖衣炮弹也无不可。毕竟不论飞升或是自此身死道消,子嗣后裔的意义便是为身后供奉,为了“先帝”的祭祀香火,但若这些都有了呢?若是太玄一朝真千万年尊太玄子为皇,那晁氏血脉能否得帝皇之位,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允。”桃花簌簌,太玄子轻叹,“不可伤我晁氏儿女性命。”
闻人俟再三叩拜后告退,当夜,连衡军入长安。
【银奢靡】
【持卡人:柯郁乔】
【折卡人:柯郁乔】
处于极端低电量状态写得很糟糕当个大纲看吧(闭眼)
——————————————————————————————————————————
1
“臣顿首再拜......”
我拢了拢身上的裘袄,放下笔又拾起火钩翻了翻炭火。也许是桃花开遍京城的缘故,今年的冬天说的上暖和,就连雪都是穿过花树的间隙,飘忽着落在地上,出京城十几里都见不到往年的白毛风。
一旁煎药小锅里咕咕地冒着热气,如今丫头还在外面奔波,这些琐碎小事也只能我自己来做。小子跟着去准备前往蓬莱的“热气球”了——据说这东西是西域边远之地传过来的,能从空中飞行千里之遥,算是解决了如何登岛的难题。
我提起小锅,倒出二煎的药,和一煎的药汁混在一起。热气蒸腾的碗放在一旁,我合上墨迹干透的请命奏折,坐在胡椅上长舒一口气。
此一去不知命数如何,无论如何要做万全的准备。
前几日托房尧联系了他远在关外的女儿青旋,花了重金从霜原部落那里买了一支千年野山参及数支百年野山参,不久家乡那边也送来了几支百年灵芝。
总该见一见太玄子。
自呈上请命奏折,豫王也未多说什么,只是寻常的些安抚话语,允了我自蓬莱返回后致仕。
一日,我捧着那一盒天材地宝,踏入了桃树栖身的大殿。
大殿里空无一人,只有那一株粗壮的桃树。但我能听到那棵庞大的树里流淌着的声音,模糊,遥远。我恭恭敬敬地奉上那一支千年野山参和几支百年灵芝。桃树的枝丫摇晃了几下,将它们卷入枝干,这些天材地宝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正愣神的时候,无数云雾凭空而起,而有人正坐在那雾的源头——正是太玄子。
“东西不错。”祂似乎很满意地回味着那些天材地宝带来的灵气,“如此,柯爱卿有何事?”
“臣请陛下登仙。”我拱手后跪伏在地。
“朕本来就要登仙。”
“如今,陛下修成正果一事已是天下皆知,大烨之正统必然是民心所向。”我顿了顿,“臣请陛下登仙后,不再过问人间之事。”
太玄子没有说话,我只得继续说下去
“若陛下登仙后频繁降下神力,必然招致后继者的依赖,此后便是懒政怠政,频繁祭祀......后果不堪设想。”
我听见祂唤我平身,我瞥见一抹遥远漠然的神情,“你是那姜姓的后人,这次出山入世,也是为了那冥虚子?”
祂抬手打断了我的回话,又挥了挥手,渐浓的雾气环绕,将我推出梦境,祂说——
“先把那第八十一张牌呈上来吧。”
待我回过神,人间仅过了一刻时,最后一张银质的奢靡灵牌应声而断。
2
数日后,我坐守在蓬莱岛边缘。
几日前还能在那竹编的载具上跟梅瑛插科打诨,下了框子一个个面色凝重地要结冰。
我呼了口气,指挥家仆带着咒钉和雷法清心铃,沿着岛上的灵脉关隘布阵。三枚主钉,一支交给了房尧,一支让小子钉在了汇入灵脉的分支,而我带着传信的乌鸦,等候在主脉的咽喉之处。
冥虚子不笨,那桃树的根系枝条几次试图袭击,却我手执帝钟掐诀喝退。不过这些只是权宜之计,若不是房尧在岛中央拖着冥虚子,我怕不是早就成了树肥。
赤梁的王子就在不远处起阵。我向来不喜中原以外的教宗和道法,动不动就要以人为祭,就算不死也要去半条命。我紧了紧衣袍,两壶落地前煎好的参汤就藏在裘袄里保温。
有一个算一个,回去之前都别想死了。
玄鸟鸣起,赤梁的圣火淬进了兵刃,而我举起铁锤,将第二枚主钉死死钉进了主脉。
玄鸟再鸣。
3
咒钉所成的大阵成功抑制了冥虚子的灵力,同样,祂未曾注意蓬莱岛的上空,不寻常的黑云正在凝聚。数九寒冬的时节,云间却翻滚着雷鸣。
直到一阵眩晕袭来,我用最后的力气抬起手,乌鸦振翅而飞,发出第三声鸣叫。紧接着,数道炽热的白光落下来,直直击中蓬莱岛中央的那棵庞大的桃树。
阵已成。
我平静地躺在地上,方才已经把装着参汤的皮囊交给了成功返回的小子,希望他能按着那几个深入险地的家伙吊住命。
感觉就在这里一起被烧成灰也不错?
我这样想着,极亮的雷光几乎落到我的眼前——
而后是一团阴影挡住了那炫目的白光。
“房尧?”
失去意识前,我只闻到血的味道,还有轻微烧焦的烟气。
4
再醒来时已经在返程的热气球上,据小子和梅瑛说,上了筐子不久房尧就昏了过去,而我却醒了过来。
我手搭上那惨兮兮的让的手腕,脉象与灵力皆有些虚弱,但并没有紊乱和衰败的迹象。从小子手里接过皮囊,我含了一口参汤,撬开这个昏迷乌鸦的嘴喂过去。
远处的雷云还在不停歇地闪着雷光,远飞了百十里地都能听到那轰鸣声。我长松了一口气,再度昏过去之前只看到小子手忙脚乱地抄起皮囊,掐开我的下颌开始填鸭式的往里灌。
总算是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