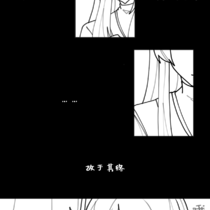






我燃尽了,结尾不写了总之。折卡了!钱花完了!符咒也撕了!大师也见过了!
闻人俟脑子里还沉浸在刚刚会上的数据里,烨灵帝又为了挥兵赤梁而征收赋税,其中盐铁为甚,可教中的兄弟们,出力最多的就是盐工和矿工。她有心想做些什么,却觉得十分无力。
她看着大贤师在对面桌案坐下,听着他身上环佩相撞发出的清脆声响,哽在喉中那句“不如我们就反了吧”又被吞入腹中。太玄子如今什么威慑,身在长安的她不是最清楚吗?那千顷桃花一夕长成,多少屋瓦百姓被其损毁,而那桃花可吸食人的血肉长成,若是开打,那会中的兄弟姊妹,不也只是成了太玄子口中食饵罢了……沉甸甸的现实压在她心中,以至于叫她几乎不知要如何开口。
“不必担心。”大贤师一向似乎有洞察人心的能力,就连她藏在心中的惶恐也能知晓。“如今时机不太合适,但亦有圣女才能做的事情,你可愿去波罗国一趟?”闻人俟有些困惑,“波罗国?”
“是啊,波罗国曾说过会举办一个佛法大会,召集各地高僧,若是想除去那蓬莱妖人……或是太玄子,都是一个机会。”
闻人眉头一蹙,显然不太乐意,这样的不乐意并非是她不愿意为此奔波,而是不愿意去求助所谓的佛法高僧。“那些劳什子高僧有什么用处?难道大贤师你真的信他们有这个能力吗?我们这些年见过了多少僧道,其中多半都是欺世盗名的废物罢了。”
“为什么不信呢,”大贤师轻笑,“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那些僧人虽然大多是个半瓶水,但是去走上一趟也并不费什么事情。何况我想叫你去,还有另一件事——蓬莱在大烨构下了四方大阵,北方的自有那些朝廷命官发挥一点他们的功用,而南方山岭众多,想要寻得其踪未免太难。”
“我从江南道那边得了消息,说是南方的那枚符咒应是在岭南地带,你此去波罗,便在岭南多留几日吧。”
闻人俟点头领命,她要带的行李不多,虽然南方道路难走,但是教里还是出得起几个信众陪她一起的,何况她的耳朵也不是什么摆设,说不得比普通人还要「耳聪目明」一些哩。
只是闻人俟没有想到,损兵折将来的这样快,她虽说出生在南方,但是到底未曾来过岭南,这般狂野的风也不是两湖地带会有的。台风呼啸而过时带来的声音,几乎遮住了其他的所有声响,闻人俟用力扒在一棵树上,虽然雨天在树上是个十分愚蠢的行径,但是她如今与信众失散了,目盲在此刻成了最要命的缺陷。无法感知到附近还有什么安全的地方,远处奔腾的水声越来越大,几乎如她幼年窥见长江河泛时一般令人惊恐万分,身下的树自然也成了唯一的庇护所。
“怎么有人在这里!”她动了动耳朵,被风雨吹得麻木发僵的脑子缓慢运转,才恍惚地意识到是有人在附近,嘶哑的喉咙艰难地发出声响,她不确定自己的声音能否被捕捉到,但是如果不找到一个合适的庇护所,即使没有被水流冲走或者葬身雷霆之下,也会因为失温而死去的。
好在她的呼救确实起了作用。等闻人俟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她已经置身于一个干燥温暖的环境,她能注意到身上湿漉漉的衣服被换成了温暖舒适的布料,在惊慌之前发现里衣似乎还在身上。这样的消息给了她一些安全感,闻人慢腾腾地从稻草铺就的床上爬起来,一只手握秸梗,打算看看这个东西能不能当做临时的拐杖。
“你已经醒了?”声音似乎是一个年轻的男人,或许二十岁左右。“我在附近山上发现的你,怎么有人在台风过境的时候进山,如果我没发现你的话,可能就危险了。”
闻人把脸转向那边,然后礼貌地道谢,“多谢恩人,我现在感觉好多了,我是和伙伴们一起要到波罗去的,地图说往这边走要快一些……不知恩人可否告知,现在我们在哪里?”
“恩人谈不上,我只是恰好路过罢了。”男人摇了摇头,然后自我介绍道,“我是冯有德,算一个云游道士吧,这是青云观,是附近一个废弃的道观,已经没人住了,我也是暂住在这里。”
“你刚刚提到波罗,你也是要去那个佛法会的吗?只是……”冯有德声音不太确定,“我看你并不像佛门弟子。”
“我是闻人俟,”闻人从善如流地改了称呼,“冯道长叫我闻人便好,我们确实是想去那个佛法会的,听说那里都是些高僧,我们从长安来……不知道长可曾听过妖桃作乱的事情?我们便是因此才想前往波罗,或许能问到一些除妖的法子。”
冯有德有些诧异了,“竟然这样巧?我也是要往波罗去的。”
闻人猜测对方或许是因为巧合的缘故起了疑虑,如若她不是被救的那个,或许也会有一样的想法,于是开口说道,“竟然是这样吗?不过我看地图这里便是去波罗国最快的路了,也因此才想横穿山岭,未曾想遇见了风灾,这风灾竟然这般恐怖,我此前竟然从未听闻。”
冯有德恍然大悟般点了点头,然后才笑倒,“这样的风灾算是小的了,我小时候都在南方居住,有几次遇见的风灾能把房子都掀了去,要是那样的大风,恐怕我们如今是寄身之处也无了,这风只要躲避两日也就不足为惧了,只是你的朋友,失散过后恐怕是有点难找了……我之后要继续前行,或许这些食粮就留给闻人姑娘吧,你在这里等人也比较安全。”
闻人此行就是为了佛法会去的,她的性命与之相比实在是无关紧要。所以她耳疾手快地抓住了冯有德袖摆,“恩公若是不嫌弃,便带着我一起上路吧,我虽目盲,但耳朵好用,必定不会给恩公带来麻烦的……倒是这山寺虽可遮风避雨,若是有野兽前来,我一个盲女又能如何应对呢?”
冯有德不由得迟疑起来,闻人俟再接再厉,“我可以在这观里留下文书,好让找来的伙伴不必寻我,只是恳请恩公莫要将我一人留于此地,毕竟这风灾我等从未遇见过,若是有什么不测,其他人寻不到这里来,我孤身一人在这里,岂不是只有任人鱼肉的道理?”
冯有德彻底被说服了,毕竟将一个弱女子留在山里,确实是挺危险的,大不了自己带着人先走出这岭南大山,寻到城镇再将人托给官府吧。
“等等……”风雨已停,二人计划按照之前的道路翻过这座山,先去最近的县城休整一番。冯有德正在前头开路,闻人忽然抓住了他的袖子。
冯有德有些困惑,虽然闻人看起来很难照顾,但是其实一直都没有麻烦到旁人,所以他侧头询问“这是怎么了?”
“我闻到了桃花的味道。”闻人用手指向山头的位置,冯有德先是觉得不可能,随即很快想到,有什么不可能的?长安不就有棵常开不败的桃花吗?二人对视一眼(虽然闻人看不见),决定转换方向往山上去。
果然在山上有棵桃花树,什么桃花能在秋天开呢?哪怕是在气候温暖湿润的岭南地区也不可能,何况冯有德一眼看见了那树木之上的一纸黄符。他想起长安城曾有传言说蓬莱仙人曾在四方布阵以吞噬万民,恐怕这就是其中之一了。
只是,这阵法要怎么破比较好呢?桃树与符咒相生相依,恐怕寻常法子无法毁去。若是点火,先不说这可是山林之中,光这几天的台风雨就不存在一个点燃的可能性。闻人说道,“我曾经听闻阳间的桃木克制这蓬莱桃树,不如我们试验一番如何?”
冯有德当然是有带桃木剑的,他觉得此举未尝不可,于是对着桃木拦腰挥剑,就见桃木若羽化一般化作碎光散去,只留下一张黄符落下。闻人耳疾手快抓住那张符咒,把它随手一折塞进口袋里,“这个符咒带去法会,说不定还能问问那边的大和尚如何处理。”
冯有德默认了她的处理方式,经此一役,原本打算找到城镇便把人留下的他也觉得,或许带一个目盲却十分敏锐的姑娘没什么不好的,不过当他们停留在城镇休整的时候,闻人俟还是修书两封,一封寄给大贤师,一封寄留在客栈,避免可能找来的信众们找不到人。
作为累赘的那一个,闻人索性承包了二人的出行费用,虽然一开始冯有德还有异议,但是在闻人掏出那张奢靡卡之后就不再计较这个了,毕竟不让人花钱可是会死的,这种坏人不能做。
二人一路艰辛,终于到了波罗,事实上就和闻人此前所想的差不多,这里也并不都是货真价实的高僧,但是也没有完全令人失望。一位已经即将坐化的老和尚认出了那张符咒,给了他们一些建议。妖人会用符,那难道凡人便不会吗?阳间桃木对那蓬莱木有克制之用,却对蓬莱上仙无用,这只是因为十年树木难抵千年树妖的功力,若是使用符咒或是阵法来加成,或许会有一战之力。


过了中秋,仍带着夏日余韵的热风中已经染上了几分凉意。枯黄的树叶随着秋风卷下,在石板地上摩擦出轻微的唰唰声。一片小叶顺着半敞的窗户轻轻溜进室内,落在案几上。杜玦指间夹着一根算筹,无意识地敲击着案几。母亲的最后通牒言犹在耳——“不成家,便安心回来,司天台不是你该待一辈子的地方。你的年纪也不小了,官做到三品还不够吗?也该为杜家传宗接代。”阻碍她观测星宇、推演规律?这比陛下天马行空的难题和玄铭灵牌都更让她难以忍受。思及此,她有一个计划,一个能一劳永逸堵住母亲的嘴,且绝不干扰她自身研究的绝妙计划。
时值季度交接,玄铭灵牌造成的一系列事件导致官吏大量流失,杜玦趁机向太玄子讨要了司天台可自行寻找人才的特权。一时间民间凡是在算学观星二事上有天资之人通通被吸纳进了司天台。契机出现在一次枯燥的公务交接中。这次来汇报近日观测结果的是新来的司丞,杜玦记得这个与自己志趣相仿甚至自带了观星仪器入职的女子,楚方圆。她着一身半旧青衫,洗得略有些发白,却浆洗得十分整洁。未能被发绳束住的碎发散落在眼前,透过间隙看得出此人眉眼清润,不知为何姿态却像是正在压抑着什么。
总不能是要一刀捅死我这狗官。杜玦自嘲地想了想,将桌面上的星图略推开些,示意对方上前。公事公办地交代完,杜玦本以为对方会如常人般寒暄或告退,却见楚方圆捧着发放回去的卷宗,目光已被其中一幅失传的《璇玑图》拓印牢牢吸住,指尖不自觉地临摹着其上繁复的星轨,口中喃喃:“此图标注的赤道偏移,与现行算法竟有三分之差,是因岁差未计,还是观测基点不同……”
那一刻,杜玦脑中灵光一闪,她开口打断了楚方圆的沉浸:“楚司丞。”
楚方圆蓦地回神,眼神里还带着一丝未褪尽的思索迷惘,下意识地应道:“大人有何吩咐?可是此卷归类有误?”杜玦站起身,走到她面前,以一种志在必得的认真表情问道:“我急需一位名义上的婚姻伴侣来应对家母,以继续我在司天台的观测与研究。我知道楚司丞志在星宇,应是同道中人。我,杜玦,司天台监正,可为你提供查阅禁库秘藏、使用观测仪器的便利。若是仍觉不够,我姑且可以称得上是陛下的宠臣,略有自信可以举大烨之力搜寻你想要的典籍。你我合作,各取所需,如何?”
这番突然其来的提议,让空气瞬间凝滞。
楚方圆明显怔住了,瞳孔微缩,这完全超出了她熟悉的任何情境范畴。但下一刻,她那习惯于处理未知信息的头脑已开始下意识运转:利弊、可行性、潜在代价……她的目光扫过杜玦案几上堆积如山的星图与算筹,那里有她梦寐以求却无缘得见的前人笔记。在当朝,平民出身意味着她不依靠权贵便几乎没有上升的可能,甚至当前的一官半职也可被轻易夺走。若能借此直接便捷地接触到那些典籍便再好不过,更何况这位杜大人还位列点卯之册……
楚方圆没有像杜玦想象中那样表现出羞赧或愤怒,反而认真地像是在解一道难题。她谨慎确认道:“杜大人之意是仅表面婚姻,人后仍然是同僚?秘库典籍,皆可借阅?若是我说……想借杜大人玄铭灵牌一观呢……?”
“自然。”杜玦怔了一下,点头,“玄铭灵牌也可给你研究。”这句话成了压翻天平的最后一颗砝码。对知识的渴求和玄铭灵牌的好奇瞬间压倒了一切世俗考量。楚方圆深吸一口气,眼神恢复了清明与坚定:“既如此……楚方圆愿与大人合作。只是细节需约定清楚,以免日后纷扰。”顺利达成合作,两人立即在官署存放卷宗的偏厅内迅速敲定了这桩婚姻的所有条款。居住分区,财务独立,人前表演的尺度把握以及楚方圆所能调阅资料的范围。甚至于出乎杜玦预料的,楚方圆同意她利用自己折卡。
于是,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婚姻震惊了京城。权倾朝野的司天台监正杜玦,竟与一名不见经传的平民小吏缔结百年之好。一时众人对这二人的地下办公室恋情议论纷纷,话本子一连出了数刊对二人恋情的大胆推测。
婚礼定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吉日。杜府张灯结彩,红绸一路从门口铺到楚方圆的临时居所。宾客盈门,仍在京城的文武百官多来道贺,好奇、探究、祝福的目光交织在这场堪称离奇的联姻上。杜母虽不甚满意楚方圆的出身,但好在杜玦终于成家,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她看着不远处正在行却扇礼的二人,与杜父相视一笑。
楚方圆身着繁复的花钗礼衣,黄金宝石打造的沉重头饰让她有些不适地微微动了动脖颈。她平日疏于打扮,此刻薄施粉黛,在跳动的烛光下,显出一种不同于往常的清丽。杜玦则是一身大红翟衣,金线绣着的翟鸟纹衬得她平日里熬夜以至于总是疏离而冷淡的面容也多了几分人间烟火的暖意。她难得地没有在思考星象,而是按照礼仪官的指引,完成着一项项繁琐的仪式。
“饮合卺酒。”喜娘端着托盘,笑容满面。
两人各执一半葫芦制成的酒杯,注视着对方一同饮尽。杜玦的动作流畅而标准,楚方圆则稍显生涩,但她学得极快,目光低垂,配合得天衣无缝。酒液微辣,带着一丝甘甜,滑入喉中。
“结发礼。”又一声唱和。
喜娘小心地剪下两人一缕发丝,用红线缠绕,装入锦囊。杜玦看着那缕属于自己的青丝与楚方圆的缠绕在一起,目光微动,这种与某人就此绑定的感觉此时并不讨厌,反而让她的心里慢慢漾起一丝暖意。楚方圆则看着那锦囊,下意识地思考起在特定时日举行这种结发仪式是否对应某种特殊的契约星象。
待所有的礼仪终于完成,闲杂人等退去,新房内只剩下她们二人。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酒香和烛火的气息,一时寂静无声。喧嚣过后,这刻意营造的温馨氛围反而凸显出一种微妙的尴尬。毕竟除了官务上的往来以外,她们对该如何独处实在缺乏经验。
最终还是杜玦先打破了沉默。她抬手替楚方圆摘去义髻,再挨个除去那些沉甸甸的首饰。“辛苦了。”她说道,语气是她惯常的平静,"虽然现在说这个有些冒昧,但是能否趁着洞房花烛夜一并将纵欲卡折断?”头上轻松不少,楚方圆也跟着松了口气,但听到杜玦的这番话,她还是愣了一下。如此的开门见山……
"当然,现在还不急。但纵欲卡还是尽早折去为妙。或许我们可以借房中术验证‘法于阴阳,合于术数’之说与星象的联系……”杜玦将茶杯推向对面,为二人各斟了一杯清茶。两人对坐饮茶,窗外依稀还能听到前院隐约的喧闹,更衬得室内一片宁静。红烛噼啪作响,光影在两人身上摇曳。也罢,正好可以趁机研究玄铭灵牌。日后再说更是徒增尴尬。楚方圆暗中为自己开解一番,闭一闭眼,道:"那就全凭大人差遣了。”杜玦失笑,看着她这副严阵以待的认真模样,先前因为仪式而起的一点微妙情感也随之淡去。有这样一位聪慧、清醒且志趣相投的合作者,比应付一个期望她成为贤妻良母的古旧伴侣要省心多了。
杜玦唤侍女们将数张毛绒绒的毯子铺在那格没有糊窗的窗子下面,又搬来矮几和笔墨纸砚,紧接着屏退了所有人命她们一概不许进入后院。
"这扇窗是专门留作屋内随心观测星象之用,不料今日倒用于此处了。”杜玦挽着楚方圆的手坐入毛毯中,一手摸出玄铭灵牌,一手便开始脱去衣物,"我对房事只有一些理论知识,要是感觉不舒服就告诉我。”矮几上,笔墨纸砚与那张岩石纵欲卡并排而放,旁边甚至还摊开了一卷标注着经络穴位的星图。清冷的月光混着烛光洒在铺着厚毯的地面上,也洒在杜玦逐渐裸露的肌肤上,泛着象牙般细腻的光泽。
楚方圆看着杜玦动作利落地褪去外袍、中衣,直至只剩一件素色里衣,不由得微微屏息。她努力维持着研究者的心态,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追随那流畅的肩线、隐约可见的锁骨,感觉自己的心跳比平时快了几分。她深吸一口气,也依样开始解自己的衣带,手指却有些不听使唤的微颤。“先从……观测气息与星位对应开始?”杜玦的声音依旧平稳,但她靠近时,楚方圆能感受到她身上传来的、不同于寻常的温热。杜玦的手指按上楚方圆的腕间,似在探查脉搏,指尖微凉,却让楚方圆皮肤激起一阵细小的战栗。“嗯。”楚方圆低应一声,试图将注意力集中在杜玦所指的星图方位,以及体内理论上该随之流转的气机。然而,当杜玦的指尖顺着她的手臂内侧经络缓缓上行,带着一种探索未知领域般的专注时,那清晰的触感却扰乱了她所有的推算。
杜玦回忆着典籍中的记载,手指顺着被里衣半掩的肩头一路滑到肚脐。她观察着楚方圆的反应,如同观察星象变化,记录着她呼吸的逐渐急促,肌肤温度的升高,以及眼底那层理智逐渐被水光淹没的过程。“此处……对应天枢位,气感是否……”杜玦的话问了一半,便停住了。因为她发现楚方圆并没有在对应星位,而是仰着头,眼眸半阖,纤长的脖颈拉出一条优美的弧线,唇间溢出一声极轻的、与她平日清冷形象截然不同的呜咽。这声音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杜玦心中漾开一圈陌生的涟漪。她一直以为情欲不过是需要观测和理解的生理现象,但此刻,楚方圆真实的、不受控制的反馈,却带着一种奇异的冲击力,穿透了她理性的壁垒。
楚方圆感觉自己像一艘迷失在星海中的小舟,从身体深处涌起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拍来,简直要将她溺亡。杜玦的手指不再仅仅是记录数据的工具,它们带着某种魔力,点燃了一簇簇细小的火焰,让她不由自主地想要靠近,想要更多。她原本抵在杜玦肩头的手,不知何时已悄然环上了对方的脖颈,指尖陷入那柔软的衣料中。“大…人……”她无意识地唤出声,声音带着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依赖与渴求。这一声呼唤,彻底击碎了杜玦最后的研究者心态。她看着身下之人染上绯红的面颊,迷离的眼神,以及那微微张开的、泛着水光的唇,一种强烈的、原始的冲动取代了冷静的分析。她俯下身,不再是出于实验目的,而是遵循着本能,吻住了那两片柔软。含糊间,杜玦轻轻附在方圆耳边:"别叫大人了。明琼,这是我的字……”算筹、星图、观测记录此刻都被抛诸脑后。笔墨被无意间碰倒,在毯子上洇开一小片墨迹,如同她们此刻紊乱的心绪。矮几微微晃动,那张纵欲卡滑落在地,无人顾及。
*此处有一些十八岁以上限定的文字
月光静静地流淌,笼罩着毯子上交叠的身影。喘息声取代了低语,探索变成了占有与给予的本能共舞。楚方圆没法再思考星象和黄帝内经有什么联系了,她只是紧紧抓着杜明琼,在陌生的情潮中浮沉,感受着对方同样不再平稳的心跳和逐渐失控的力度。杜玦发现理论终究是苍白的。这种肌肤相亲的炽热,这种灵魂仿佛都在颤栗的共鸣,远比任何冷冰冰的数据更令人着迷。她沉溺其中,早已忘记了最初想要研究的理论,只凭借着直觉和涌动的欲望,带领着彼此奔赴那未知而令人心眩神迷的彼岸。
窗外秋风依旧,室内却是一片春意盎然。那扇观测星空的窗,今夜映照的,是两颗在人间情欲中暂时迷失,却又无比贴近的星辰。
咔的一声脆响,两人交握着的手下压着的纵欲卡已应声折断。但这细小的声音被淹没在二人带着暖意的共鸣中,需得到明日才能被发现了。
持卡人:王焕荼。
省流版:折卡是用的太玄子的赏赐,用法是路费和给狱卒的贿赂。
烨灵帝化身太玄子重登皇位,是谁也不曾想过的事情。闻人俟在那日混乱中因为耳朵过于灵敏,被有心避人的烨灵帝放了个假,等她听说了这件事的时候,所剩的只有一片残垣断壁和开得极繁极艳的桃花了。
太玄子化身的桃花并不比冥虚子所化更有安全感,但好在,作为造反势力的赤仙会一向小心,有几处暗哨潜伏在多个路口关隘,时刻等待着接应的命令。而她这样的“异人”,对于已经超凡入圣的太玄子来说再没有什么用处了,太玄子轻而易举地同意了她请辞的说法,甚至以诸多金银珠宝相赠,看起来实在是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他甚至记得关心女孩一个人携重宝出京会被贼人盯上,叫来如今繁忙的王都尉作陪。
闻人俟不敢假定太玄子心存善意这样的天方夜谭,只能想是否自己身上有什么可疑之处,然而实在找不到答案。这件事一直到她与王焕荼见面才得到了解答,王都尉是一个很健谈的人,同时对于长相漂亮的人都多有几分爱护之意,很是细心地为她解说了一番。原来是有一位同为花鸟使纯秋进献的侍女银杏刺杀了皇帝,虽然闻人俟没有什么嫌疑,但是显然坐在皇帝这种位置多年的人必然不可能没有疑心病,所以她也在猜忌当中。王焕荼将她送到了场外寄住的农人家中,这家的农人正是赤仙会的信徒,王焕荼将手中的玄铭灵牌塞给闻人,笑到,“这灵牌虽然有万般不好,但唯独用来威慑是为妙机,你如今身负重金,恐怕还是要早日脱手为好,免得被贼人盯上,落得人财两空。”
闻人谢过对方后走进屋里,手上细细摸索,才发现这竟是一张「铜奢靡」,自己此次得到的赏赐倒是差不多能折断……那么太玄子叫王都尉来为自己送行的做法看非常可疑了,他是期待自己的臣子监守自盗吗,还是希望自己能顺理成章地难逃一死呢?
闻人并没有过多思虑,而是叫众人商议南渡的事情,不论是将情报带回荆州,还是去撕那符咒或是除妖法会来灭杀两位伪神,都不是在长安可以做到的事情。
而恰有一位信徒在会上提到,往南的关隘见到了那与刺客银杏极为相像的侠客,闻人心中一动。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位侠客刺杀皇帝,那自然也是赤仙会的朋友了,何况二人一起坑了那位倒霉的花鸟使,也算是有一段渊源了,何不干脆请那位侠士共谋大业呢?
赤仙会毕竟经营多年,为了此次圣女的安危更是小心谨慎早做准备。于是虽然闻人出发得更晚,却还是在银杏渡江之前赶上了对方。
皇帝发布的通缉令还没到达,但是这样锋芒在背的感觉不做他想,银杏不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会有任何代价,只是觉得长安那边的反应实在太快,不符合她对大烨腐败的认知,而司徒京也太过没用了,竟没能多拖上几日……还是说,他也是追缉的一环呢?毕竟那「护送」的侍卫大概已经回去通风报信了,恐怕司徒公公也很是不满吧?
银杏注意到马蹄声音越发急了,遂转身藏入道路一旁的竹林当中,身形如燕一般踏竹而上,正打算伺机而动。未曾想追在身后的追兵也跟着停下脚步,银杏有些不屑,所以说这些官兵都是一样的路数,还是怕死。不过这样也好,人在林中比骑马赶路更轻快,她一样可以摆脱追兵。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一道声音准确报出了她的名讳与方位,“银杏,林中左侧的第十三棵竹子上面的便是你吧?”
“不必惊慌,我并非任何人派来的追兵,而是来祝你脱困的人。”一个身着白衣身披红帛的女子孤身进入林中,她眼睛闭着,但走起路来却毫无迟疑,在靠近银杏之时停了下来,给二人进退留足了空间。“我是闻人俟,我在纯秋大人那里听说过你的名字,或许你也曾听过我的?”
确实,闻人俟这个名字银杏并不陌生,毕竟这位目盲的女子曾经也是烨灵帝眼前的红人,虽然这样的红人不过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但是不妨碍她知晓这个人的存在。只是,烨灵帝或者纯秋,都不是她所在乎的人,何况他们也不可能叫这样一个小姑娘来带领追兵吧?虽然她的耳朵看起来很好用,但是银杏毫不怀疑,自己只要一招就能轻松杀死她。
“你的刺杀很成功,烨灵帝已经死了……但是有妖桃从其身中复生,如今自称太玄子,他记得烨灵帝的所有事情,也包括刺杀的情况,如今长安上下已是被通缉令贴满,想来他是不会放过这次刺杀的参与者的。”闻人俟见她没有动作,料想银杏或许并不介意多听她说一些话,于是继续说道,“如今通缉令一散开,多个驿道关口恐怕都要紧张起来,哪怕银杏侠士想要走水路,情况也是不容乐观,但是我赤仙会已在此耕耘多年,在漕帮势力里亦是说得上话的,不知我可否邀请侠士,一同乘船南下?”
银杏才知道情况如此严峻,难怪朝廷的反应如此迅速,原来那狗皇帝竟然没死!她脸色阴沉了一瞬,从树上一跃而下,靠近闻人,压低声音质询,“看来我还应该感谢你们雪中送炭了,但是帮我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我怎知你不会转手把我卖给那狗皇帝。”
闻人笑道,“我知晓你心有疑虑,但这难道还需要什么理由吗?自古便有荆轲刺秦的美谈,虽然我贫弱不比侠士,却也愿助这般有胆魄的侠士一臂之力。何况我家乡多是因为朝廷暴敛暴征而无家可归的贫苦百姓,大家拜入赤仙会便是结为兄弟姊妹,自当互帮互助。阁下杀了那狗皇帝,也算是为我们出了一口恶气,纵然萍水相逢,也是异父异母的亲姊妹了。我等自然是没有坏心思的,只看银杏侠士是否愿随我等入荆州,以期来日共讨这非君非人之辈?”
银杏并没有完全相信她说的话,毕竟如果有人刚刚被做棋子利用,恐怕也很难马上相信其他人。但是借赤仙会的势力摆脱追查,对他来说确实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所以她审慎地答应了借道的事,却并不肯承诺会为做赤仙会做什么事情。
闻人并不在意这件事,毕竟大家有共同的敌人在此,难道赤仙会真打上长安了,银杏会不想再取太玄子性命吗?只是在临上船之时,银杏并没有踏上那只用芦草掩盖的小舟,而是语气莫名地询问,“你知道,汝阳公主如何了吗?”
闻人沉默不语,汝阳公主当日便以身故,这是长安如今人人皆知的事情了,只是她的死法众说纷纭,无人能下一个定论,不过银杏走得早,恐怕还不知道这件事。于是她摇了摇头,空茫的眼睛看向远处,“我于宫中没有什么势力,因此也不得听闻。”
“你的人不一起走吗?”银杏又问。一起乘船的只有闻人和几位摇桨的船工,当时追击的熟面孔,如今都还在岸上呢。闻人摇了摇头,“长安的情报需要有人去整理……何况还他们还有旁的事情要做。”
看着小舟顺着夜色飘荡远去,岸上一骑才出声发问,“我们真的要帮那个劳什子花鸟使越狱么?要打通狱卒可是要花不少钱的。”
零头的信众横了他一眼,“圣女大人已经留下了用来打通狱卒的钱,又不是从你兜里掏银子,你有什么意见?”
那人讪笑道,“这事不是叫大哥你也头疼好久吗……这钱若是花在我们兄弟姊妹身上不好吗,那个什么花鸟使,虽然确实是个倒霉鬼吧,但那不是他自己倒霉嘛。”
几人不着边际地闲话几句,又策马返回长安。此刻的长安城一片混乱,因着桃花暴动的缘故,满城百姓都是灰头土脸的,有些贼人便趁乱作祟。赤仙会的几人趁机挤入城中,头人厌恶地将一个企图趁机猥亵妇女的地痞流氓摔在地上,“就他了,这种人也是死不足惜,先把他舌头扒了,省得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几人通力合作,这个恶人生生痛昏了过去,在几日后他们终于花重金收买了狱卒,假借当初纯秋硬是带走了他们妹子进献皇帝的说法,叫人放他们进去多多「照顾」那位花鸟使,实际上暗中狸猫换太子,将人偷渡了出来。
而纯秋本人一直到登船才搞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然而这艘船已经行舟过江心,唯见碧云落江涛与两侧深红映浅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