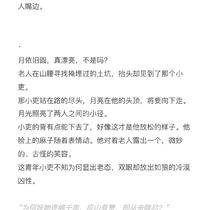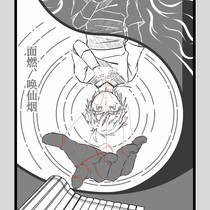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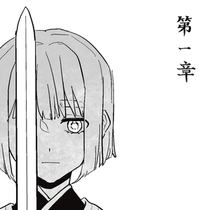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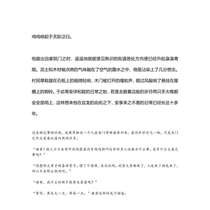
景朝十四年,蜀中某处一傍山而居的村落在结束了长年的妖祸后,从连年灾害中幸存下来的村民们正以欣欣向荣之姿对村落进行了重建。
长期处于半封闭环境下的村落形成了淳朴的民风,他们自给自足,以劳动为荣。由于地理环境偏僻,也鲜少受人祸。随着血脉更替,对过往那段苦于妖祸的岁月已渐渐被村人所忘却……村中的老者只是一遍又一遍告诫年幼的孩童们,如何分辨、如何规避、如何自保。
近乎呓语般持续不断的喃喃,在和平的景象下对孩子们来说仿若初夏的蝉鸣般聒噪。
嬉闹、嬉闹、嬉闹,是孩子们在追逐打闹。
呓语、呓语、呓语……是谁在呓语?
……
涉及企划内角色:乐师陶(10)/望天(8)/许照冥(16)/池莲(9)
本回主要妖兽:云兔(来源:序章云起)/梦涡(来源:原创妖兽)
是夜,无云之月高悬,晚风却透着几分刺骨的寒。稀薄的雾气卷着尚未落下的银霜,从宽大的衣袖间穿过,一时间布帛铮铮,堪堪露出腰间那尚未出鞘的寒铁。
有人立于那百米高空,若游龙般自如穿梭在无物之境。有明月作媒,露水为裳。霎那间,有神兵破空而来,将那混沌浊气一分为二,形如秽浊妖气披就的帔帛缠绕在他二人的身旁。只叫人见之心如擂鼓,道是有仙人下凡,却未等到仙人垂怜,那二人未多作停留,便又同天外飞星般,消失在天空的边缘了。
那宛若风暴般包裹飞剑的污浊气息尽数被吸入葫芦内,若有人能看透其妖气本质,便能从那晦暗的气息中窥见妖兽的身影。妖兽大多愚笨,那二人原是应山弟子,以降妖除魔为己任。此次不过是收敛了气息,便有小妖自以为有可乘之机,以卵击石。还未见那寒铁出刃便被打散了妖气,囚于葫芦内不见天日。
二位仙人均作醒目的应山弟子服打扮,说是“仙人”,细看之下才发现不过也都是半大的孩子。尤其是那盘腿坐在剑尾的男孩儿,精瘦的身体甚至不足以撑起那身蓝白校服,御剑时掀起的飓风吹得他的衣帛紧贴在肌肤上,隔着布料甚至能窥见排排肋骨。
那样瘦小的孩子在灾岁年间并不少见,只却不曾想能够腾云驾雾的仙人也有如此年幼之人。男孩抱着几乎同他一般高的唐横刀,只是沉默地看着月亮,明朗的月光在他那双黑玉般的眸子里激不出一点波纹。或许是想到什么,池莲尝试对那轮明月伸手,却只抓着一手稀薄的空气。少年疑惑地歪歪脑袋,又想起什么似的,从怀中取出半凉了的馒头慢条斯理咀嚼着。
许照冥立于剑首,操控飞剑方向之余亦行卜卦之术。只见她的手中有一宫灯般大小的沙盘,流沙宛若活水般在那狭小的空间内游走重组,竟是隐约能从中看出几分他们脚下山林湖泊分布的雏形。
他们所行之处皆是沙盘所示流沙阻塞之险地。前些日,司天院的师弟师妹日例卜卦,竟皆出大凶卦相。既有乱象,应天弟子自当以身为剑平定妖邪乱世。只是卦相模棱两可,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是好。许照冥虽是问剑出身,却也略通问卜。见师弟师妹们围坐一团,对着卦相叽叽喳喳讨论不休,说不好奇未免太过矜持。
“哎呀,我当怎么回事呢……嗯嗯嗯嗯,该如何是好呢?”
许照冥总是爱笑,笑颜和煦明媚得像只慵懒的猫儿,偶尔使坏时眯着眼睛故作为难的模样却又有点狐狸般的狡猾。但在那些师弟师妹眼里,许师姐再好说话不过了,磨一磨,她总是肯愿意听他们的烦恼的。
“许师姐,你最好了,快帮我们分析分析……”
性格开朗些的师妹更是胆子大的,竟是直接抱上了许照冥的腰。许照冥乐呵呵地摸着师妹因卜卦而焦虑得炸毛的头发,甚至编成了小辫儿。
“有什么事这么愁人?瞧瞧你怒发冲冠的模样,哎呀,好骇人,”许照冥故作夸张地抚住了胸口,假装被吓着了,又不动声色松了环在自己腰上的手,眨眨眼道,“好啦,有什么要紧的?既有凶卦,那便顺其自然,船到桥头自然直。”
“我且去一观便知!”
有司天院子弟当场重新卜卦,竟是出现了新的卦相……逢凶化吉,是吉兆!
说罢,她便择日不如撞日动了身。
池莲也算她入门不过一年的小师弟,话很少,也总是没什么表情。偶尔在食堂见过他几次,吃饭时人倒是精神了不少。许照冥觉得有趣,便一时兴起捎上了他。
许照冥还仍专心在卜卦,坐在后头的池莲也不知是否发起了饭晕,还吃着馒头却是头开始如同小鸡啄米。许照冥只当他是无聊了,便一边同他说话一边在沙盘寻找下一个落脚处。
“池师弟,可要小心别跌下剑去啦。”
“唔。”池莲点点头,又啃了一口凉馒头,表情上罕见露出了几分难过来,“凉透了。”
“哈哈哈哈……哎呀,”许照冥乐得拭去眼角分泌的泪珠,像是觉得有趣,宽慰道,“待会儿寻个客栈,师姐请你吃点好的。”
池莲依旧点点头,却还是慢吞吞将剩下的馒头都吃了。
年轻人的身体还有发育的空间,一个馒头下肚,池莲却还是仍觉得腹中饥饿。
然而没有开工就没有饭吃。
思虑着,他的脑袋一点点沉得更深,忽而闻到一丝熟悉而甜腻的气味,他精神一振,就连那双平谷无波的眸子都明亮了一瞬。
“该上工了。”
池莲说罢,便就着惯性放松了身体,许照冥见他有落剑的趋势,也是讶然。
“嗯嗯……池师弟,可还回来吃饭呢?”
即使在高空,有着寒风的刺激,池莲仍旧睁着一双圆目,好似全然没有痛觉一般,仍由寒气亲昵他的面颊。闻言,他的护腕下飞出一枚细小的花镖,纤细得宛若一枚绣针,尾部坠着红莲花色的细绳。那镖就跟活着似的,缠上了许照冥的剑柄,那抹灵活的艳色似乎渐渐淹没在空气中,衔接着的那段几乎透明不可见了。
“吃的。”
那是个小型的追踪术法,许照冥了然,甚至能抽出空对着池莲坠落的方向乐呵呵地挥手。
少年的柔韧度超乎常人,使他能够作出令一般人胆寒的高难度动作。他的身体几乎折叠成未开的花苞,直到快要落地,他才调整了身形,宛若一只隐于夜色的猫儿,悄无声息地落地。又是一个垫步,隐于山林中了。
……
夜晚出奇的静,山林中没有一丝野兽的气息。或许是今夜月色太过明亮,又或是察觉到森林深处存在什么潜藏的危机。人类睡去的同时,整个森林都好像陷入了沉睡,却有些奇妙的雾越过了猎户们设下的陷阱,试探着笼罩了整座森林。
直到几年前,村里还似乎生活在妖潮的阴影里。许多年前,这里甚至说不上是一个村落,只是有人形影单只,有人拖家带口,他们大多是各地逃避“天灾”而聚集在一起的人。那时,妖兽对人类来说也不过是陌生的存在,带来的伤害却如同天灾般不讲道理。即使是幸存者,也不一定亲眼见识过妖兽的真实面目,对他们来说,那可能是一场瘟疫,或是从山上来了吃人的野兽。他们手无缚鸡之力,在连吃饱都成问题的年代,除了丢下故乡逃走,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或许是天灾终究会过去,人们迁徙到了新的土地,而那噩梦一般的灾难似乎总算留给他们一条生路。于是幸存者们原地扎营,从那么一个小小的聚落,慢慢发展成现在这样的小村庄。
他们大多靠开荒和山林的鸟兽生活。人类是弱小却又顽强的生命,就算是最苦的时候,他们也都撑了下来。渐渐的,有新的生命出生,似乎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那会儿村里极度排外。因为在乱世,会吃人的不只是天灾,还有手握兵器的人类。这一带本就说不上太平,粮食不足,官府也靠不住的情况下,山匪层出不穷。能够逃到这里的人记也记不得见过多少次强盗杀人,他们几乎是踩着同伴们的尸体寻求生的希望,才勉强得有喘息的机会。
或许是上苍垂怜,自从他们蜗居在此处,竟鲜有山匪骚扰。只是可怕的过往仍然刺激人们敏感的神经,对于外来者他们总是充满戒备。村里的猎户和樵夫是为数不多战力的同时,也是除了最早搬到这里的老一辈外最有话语权的人。
乐师陶的父母就是在村子成形后误打误撞逃到这里的流民之一。不同现在,那会儿他们夫妻对村民来说也是外来人。没有人可以保证他们是不是强盗,来之前手上有没有沾过同胞的鲜血,会不会背叛他们辛苦经营的村子,给村子带来不幸。而那时,乐师陶的母亲正好怀着他。兴许是对孕妇的同情,村人没有立刻将他们驱逐。他们拾掇出了一间破屋,甚至没有正经的床铺,只能拾些还算干燥的茅草铺就将就一夜。
偶尔会有人隔着门墙的缝隙偷偷观察他们。男人没有斥责他们的勇气,只能努力将妻子裹得更暖和些。然而无论他怎么努力,妻子的手总是冰冷。这间屋子确实破,却也比露宿野外要好上不少。若是给他足够的时间,他可以将那些破损的地方都修补起来,打张扎实的床铺和桌椅,也能寻些石块和泥灰,砌个炉子用来取暖。如果可以,希望他们的孩子不用受奔波劳碌之苦,能够快乐自在度过一生。
他攥着妻子的手往怀里塞,尽可能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他那因劳累和水土不服而憔悴的妻子。他用嘴唇亲吻着妻子的额头,妻子的手很冷,额头却仍是滚烫。焦虑的男人想去和村民讨碗能祛风寒的药汤来,却在试图起身时摸到了一手滑腻。
寒冷麻痹了他的嗅觉,昏暗的环境仅能靠屋檐漏下的月光去分辨那黏滑的液体。
妻子的状态说不上好,半梦半醒间呓语着难以辨识的词汇。男人脑袋空白了一瞬,才有些狼狈地从草堆里爬起,连滚带爬地朝门外赶去。
躲在外头偷看的人被他突然的动作吓了一跳,当即便想假装无事般逃开。男人却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般抱住他们的腿,声泪俱下求他们帮忙。
“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妻子……她、她流血了……”
来围观的都是些平日在村里说不太上话的年轻人,没有长辈们的意思,他们也不敢做主去寻大夫。或许是他们的迟疑刺激了男人的心,他越是低姿态地恳求,村人们越是不知如何是好。
“你、你别这样……”
“你先起来罢!”
“求求你们……”
他们试图去将男人扶起,或是心死,眼前这个消瘦的男人的手却宛若千钧重。无论他们怎么使劲,都无法把男人从地上扶起。他们也犹豫着是否要一走了之,却还是有人先心软了。
“你求我们也没用的呀,我们既不会问诊,也没有接生的经验啊!”那人道,“你先别急,我们去叫人就是了,听说孙樵夫的媳妇儿曾经给人接生过,我们去找她帮忙,总有办法的。”
“好、好……我这就……”
男人也想一起去,踉跄着支起那风中残烛般的身体,却被人拦了下来。
“孙樵夫脾气不好,他老婆胆子又小,你这么去了,别给人吓着惹出是非,我们已经有人去了,你且先顾好你妻子吧!”
男人只得先回去照顾妻子。有好说话的村民送了些柴火给他们,屋里没有正经火炉,只能先支个临时的火盆。火烧了起来,屋内的寒气也被驱散了许多。火光衬得他们的脸色更加难看。孙樵夫的老婆一直没来,一旁帮着男人生火打水的村民们也有些着急了。更有急性子的,甚至撸起袖子就要动手帮忙,吓得其他人拉都拉不赢。
就在他们想着要不要再去几个人看看情况的时候,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门本就没锁,屋内的人也是急上了头,他们急匆匆想去开门,门却自己被推开了。火盆里的火苗被穿堂风冷得一激灵,瞬时屋内明暗不定,待他们看清却发现来人不是孙樵夫,也不是孙樵夫的老婆。
那人穿得比在场其他人要都厚实些,戴着野兽皮毛做成的小帽和护腕,背上还背着长弓和皮革制的箭桶,里头只有零星几支箭。她的口鼻都被麻布裹的严实,漏不进一点风霜。来人个头不高,此时却像撑起了整个天。
村民们叫她帅娘,她只点点头。没有寒暄的功夫,她简单看了一下孕妇的情况。出血的情况并不严重,只是人仍不够清醒。
“人我带来了,老孙叽叽喳喳个没完,跟着一起来了,你们拦住他别让他瞎搞事情。”
屋外头,一个大大咧咧的男人招呼着一个有些怯懦的妇女进了屋。或许是生了火,暖气熏得屋内的血腥味冲鼻,妇女眼神闪烁着往后退了两步,正好撞上堵住门的男人的胸膛。胆小的女人一惊,又吓得往屋内挤了挤。小小的屋内挤了五六个人,早就拥挤不堪。
“我去你OO的,你OO是不是有病?听不懂人话?你出息了,还会直接抢人了!”
“你不是有本事吗,我看你OO也是忘了本,你有本事躲里头你有本事出来,我不OO死你我OO也是没本事在村里混了!”
帅娘见人到底是被逼着来了,也算松了口气。屋外头断断续续传来些骂街的声音,听着倒像是孙樵夫的。旁边有几个年轻人在边上跟着劝,但孙樵夫力气本就大,那几个年轻人怎么拦得住?她同带孙樵夫老婆来的那个男人对视了一眼,后者还有闲情对她咧嘴笑了笑,好像外头骂的是和他完全不相干的人似的。
她将看热闹的和男人们都打发了出去,自己留下给孙樵夫的老婆打下手。孙樵夫在外头急得团团转,他倒看起来比他们还忙,一边绕着屋子转一边嘴里仍不停,什么难听的词都往外冒。眼看着一堆人被赶了出来,他更是急得跳脚,一把就从那三三俩俩里逮出一个高个的男人来,指着他鼻子继续开腔。
“缩头乌龟!你还晓得出来?你出息了你!你老望说话第一个顶事,我们都是放屁是不是!?”
“哎,哪能呢。”
被叫“老望”的男人任由他揪着,嬉皮笑脸的样子让孙樵夫看了直恨得牙痒痒。老望是村里的猎人,他的身上还穿着外出狩猎时的装备,腰上别着枚用了许久的剥皮猎刀,沉甸甸的。孙樵夫自知真要打架,他大抵是打不过的。那个男人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模样,却也实打实和野狼干过仗,就他自己吹嘘的,甚至单挑过熊……说实话,孙樵夫是不大信的。但他心里却多少有些发怵,嘴上囔囔着扯淡,到底却是信了半分。他也没真要打一场的意思,发泄过后没再继续骂街,只搁一旁守着那间小破屋。看着帅娘忙进忙出送水和布的模样心烦地揉乱了自己的头发。
“说了别管别管你们咋就不听呢?就你们好心,我们都是些冷血的,你说我们能看着人死里头吗?”孙樵夫咂舌,“但村长都没发话,你们上赶着干什么呢?你们这样,让那些老不死的怎么想,你们要得罪他们,行,别扯上我们家成不。”
“说什么‘得罪’,太夸张了。”
“当时什么条件,你不是不知道,村长自己一家都难说能养活自己,当初还接济我们,反正我听他老人家的,你这么一搞搞得我们几个都像白眼狼了你晓得不。”
“你自己不也说了,”老望笑了笑,“村长他老人家心善,我们又没干什么坏事,最多不过被说几句咯。”
“你想的简单!”
“我看你也没想的太复杂,明天我如果挨骂,我一定第一个把你卖了,”老望拍了拍孙樵夫的肩膀,“你说你,嘴上也没个把门的,张嘴闭嘴老不死的,不尊敬长辈啊!”
“……我去你O的。”
老望不以为意,帅娘让他帮着去烧点热水,他便立刻应了去办了。徒留孙樵夫一人搁那头抓耳挠腮,发现肉眼可见变得更加凌乱。
之后,孕妇在孙、望两家的帮助下顺利诞下一子。但女人的身体状态实在不好,她刚生产完,身子虚,又不好用药。村里的药师来看过,只叫她只能先养着身体。男人在一旁听得仔细,将药师的吩咐一一记下了。只是他们夫妻现在的处境,想来许多也都如天方夜谭一般,说得轻巧,却是难做到了。
药师走后,男人面上仍旧愁云一片。帅娘忙了一整晚,此刻脸上也略显倦色。老望见了,让她先回去歇息,帅娘却没动,只是定定看着他。
老望莫名心有所感,知道她大约是有什么事想做的,怕是在顾虑他。他只是耸耸肩,对着那对小夫妻的方向努努嘴。
“你妻子的身体不好,在这边过冬到底是太难为人了,”帅娘说,她的声音总是沉稳且有说服力。熬了一整夜使她有些疲惫,声音也比平时沙哑了许多,却莫名有些温柔的感觉,使人焦虑的心情也逐渐舒缓了,“不如同我们一道回了,条件或许算不上好,至少能少吹些风罢了。”
男人的眼泪的眼眶里打转,活像个蓄水池,却总也落不下来。他不顾脏污了的衣袖,擦红了眼睛,小声道:“我真不知该怎么回报你们……”
“你别怪村里的人,他们只是害怕外头来的人,本质不是什么坏人。”
“自然、自然,”男人喃喃道,“没赶我们走,还给我们落脚的地方,已经很好了……那些孩子还一直操心我们的事,也是天亮了才走,我都记在心里了……”
“那便好。”
帅娘笑了笑,像是总算放下了一桩心事。
他们给出生的孩子起名为乐师陶。他们一家住在老望和帅娘家,吃穿用度都靠他们二人打猎。男人心里不是滋味,但好在也算足够争气。在故乡,他曾在老木匠那里做学徒,虽说学艺的时间并不久就出了变故不得不离开家乡,好在手艺到底是留了下来。靠着木匠技艺,在村里想要站稳脚跟只需要足够真诚,便能够打动其他人获得他们的信任。
大约花了一年的时间,他在帮村里做工之余重建了原来的小破屋。孙樵夫其实也帮了不少,他背着男人偷摸着送过几次木材,想来是接生那天的事让他耿耿于怀,却又到底拉不下脸,只好暗处帮点忙,也算自己一番心意。
老望笑他看起来粗旷,心思却纤细敏感,孙樵夫敢怒不敢言,只叫他滚蛋。
一年后,乐家三口便搬了出去。男人做的活主要用来换粮食和布料,帅娘记挂他们,偶尔有多的皮毛也会送些给他们。男人的妻子叫姜戎,原先是个绣娘。帅娘给他们的皮毛品质都极好,姜戎受之有愧,觉得帅娘当初接济他们已是待他们极好。待她身子好些,能重拾针线活了,便总想做些什么给帅娘回礼。
恰好帅娘也很快便有孕在身,姜戎便为那还未出生的孩子亲手缝制了襁褓。上头绣着些不太常见的图样,老望倒是一眼看了出来,笑着比对了一番,那是他那把猎刀柄上的图案。
帅娘才知道自己怀孕不久,尚未显怀。姜戎也觉得自己心急,羞红了脸要她收下,帅娘便也有些不好意思地收下了。
一来二往,两家居然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关系,来往了许多年。
或许是姜戎生育时的条件实在严苛,也可能是遗传了母亲的体弱。乐师陶出生后身体也总不见好,晚上他总是睡不安稳,稍有不慎便会感染风寒。即使是炎炎夏日,他也需戴着棉布制的抹额,不然便会因吹了风而头痛。
药师曾说过,小孩子体虚倒也不稀奇,只是用药需得谨慎。若是太依赖药物,或许长久都得靠药吊着才能生活。倒是有不少先例是活过几岁后身体自己能好起来的,乐工和姜戎的条件也并不好,药师建议他们也先养着看看。
乐工只能更努力工作,尽可能为体弱的妻子和儿子提供更好的环境。或许是药师的话起了作用,乐师陶的身体在八岁后确实健康了起来。只是他的童年大多在家里养着病度过,总是郁郁寡欢的模样。这个年纪的孩子原是最爱嬉闹的,他却似乎很排斥外界般,既不和村里其他孩子玩闹,也不怎么愿意说话,成日黏着姜戎不愿出门。
姜戎虽然默许了乐师陶依偎在自己身边,但她也不是热闹的性格,很难不为乐师陶的未来担忧。帅娘产后恢复后也时常来看她,乐师陶有些怕她,因为她的身上总有些野性的气味,让他联想到深夜偶尔能听到的狼嚎。
之后,帅娘便偶尔会带着自己的儿子来姜戎家。那是个比自己更年幼的男孩儿,却和村里其他孩子不同,很安静。他给人的感觉和帅娘很像,眉目却更分明。衣服上的刺绣和乐师陶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乐师陶平日里帮着姜戎做家事,自是一眼便认了出来。
“望天,你和小陶去院子里玩会儿吧。”帅娘摸了摸男孩儿的头,又对乐师陶笑了笑,“我和你娘亲说几句话。”
望天点点头,便来拉乐师陶的手。
“院子在哪?”
他的声音和他的母亲一般有着特殊的亲和力,孩子般的嗓音尚未变声,故而听起来更像个女孩儿。乐师陶捏了捏望天的手,这个比自己还要小些的孩子,手心却已隐约有生些薄茧。望天见他似乎好奇,便把手心向上展示给他看。乐师陶见了,总是有些忧愁的脸上总算有些笑意来。
他拉过望天的手,第一次在家里这么跑着。
“我带你去,”他说,“小天。”
“嗯。”
望天从小跟着父亲和母亲学习打猎的事情。森林是他们赖以为生的猎场,却也总是危机四伏。他年纪太小,父亲不愿带他去林子里,他便只能借着送饭的借口,悄悄留在父亲的身边,观察他工作的模样。
或许是他有模有样学着父亲的模样检查着陷阱的状况,老望偶尔会对这小子耍赖跟在自己身后这件事儿睁只眼闭只眼。帅娘是用弓的好手,但望天还拉不开长弓,这让他或多或少有些沮丧。老望见他这心里不大痛快却也不吭声的模样只觉得好笑,过了几天便给他带来一支他这个年纪也能用的短弓来。
很快他便知道是父亲托村里的木匠制的武器。说是武器,或许说是玩具更合适,但即使如此,望天也足够高兴了。这样他也能像母亲那样拉弓,等他再长大一点点,就可以帮忙一起打猎。
望天的性格就和他的妈妈一般沉稳,就算他现在高兴到心脏几乎要跳出来,却也只是红着脸,迫不及待拿着他专用的那柄短弓去练场试箭。
所以,当他见到乐师陶的时候,他也以为眼前这个他应该喊一句“哥哥”的人未来会继承乐工的工作,成为村里的木匠。但他虽然看起来有些少年老成的模样,却很是笨手笨脚。他很少和别人来往,好像他的世界只局限在乐工做的这个小小的屋子,和零星养着几只鸡的院子里了。
望天坐在屋檐下看着天,今天天气很好。乐师陶给他看最近孵出来的小鸡。毛绒绒的鸡崽身上却很干净,乖巧地窝在乐师陶的掌心,好奇地打量眼前的陌生人。小鸡似乎以为望天眼角那枚小痣是自己今天的午饭,便扑棱着过去啄他的眉角。
乐师陶有些惊讶,忙把小鸡放下,摸着他的眼睛看望天有没有受伤。
刚出生的小鸡攻击力实在有限,望天眯着眼睛让他检查着,心里却在想,眼前这个有些笨笨的“哥哥”或许一通检查下来比小鸡啄他给他的伤害更大。
但乐师陶是个好人,这点他心知肚明。
从此便经常能看见两个小孩一起成双入对的身影。村里人对他们关系好似乎并不意外,毕竟望家和乐家从父母辈开始关系就一直很亲密,据说当初也是老望和帅娘努力说服了村长,才让乐工和姜戎得以留下。如今街坊一同生活了这么多年,除却早年那点芥蒂外,其实他们也早就接受了乐工一家。
望天的父母每天都很忙,他们每天天还不亮的时候就要出门。早些时候闹过几次狼灾,尤其是冬天,森林里的食物不够种族的存续,它们便会冒险到人类的村子去袭击人类。孙樵夫家的幼子就曾被狼袭击过。饥肠辘辘的野狼用爪子挠着他们的门窗,隔着那薄薄一层木板能够清晰听见磨牙的恐怖动静。或许是真的饿到没有气力,狼群们迟迟没有找到进到室内的方法,只要耐心等待猎户们回来,或是等到狼群主动放弃,他们就能活下来。后来据说是窗户的栓子老化,有狼发现了那狭小的入口,试图从窗户那钻进室内。被孙樵夫发现,用他那平日里讨口饭吃的斧头狠狠砍向了那探进室内的半截狼嘴。锋利的斧头劈开那野狼的头颅,铁和骨头碰撞发出的脆响着实令人牙酸。头骨坚硬异常,就算孙樵夫用尽全力的一劈也未能将那狼头剁成两段。被砍伤的狼发出了凄烈的哀嚎,或许是同伴鲜血的味道引起了头狼的注意,加上猎户们举着火把逐渐靠近了他们,前后夹击的危机感这才勉强逼退了狼群。至今孙樵夫家的窗檐上还留有斑斑血迹,虽说事后被水洗冲淡了许多,但那褐色的锈迹还是使人触目惊心。
狼群是相当团结的野兽团体,孙樵夫担心会被报复,千叮咛万嘱咐自己的妻儿,千万要小心森林。猎户们为了避免狼群再次侵犯,在森林的深处设下带铃铛的陷阱。任何风吹草动,村民们便会躲进长老们谈事用的礼堂,那里被乐工不断加固修复过,可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不过。这时猎人们便会进林子,排查触动陷阱的到底是狼群还是寻常走兽。
望天的父母是保护村子的主力,望天也憧憬着,希望自己以后也能成为那样保护村子的英雄。在小孩的眼里,父母的背影总是那么安全和可靠,在大人的保护下,总会觉得自己长得怎么那么慢,期望着自己能快一点长大。
成长的焦虑是年轻人独有的烦恼,当他诉说那样的愿望,他的母亲也只会揉着他的脑袋,对他说:“你还小呢。”
老望教过他很多,怎么分辨野兽的脚印和粪便,森林里的植物哪些可以食用、哪些可以用来制药,怎么不在森林里迷路,怎么给猎物放血……小小的脑袋装不下那么许多的知识,见他脑容量告罄目光也变得呆滞,老望总是心情很好。呆傻的孩子惹人疼爱,这时候他总是用刀柄拍打着望天的屁股,要他一边玩儿去。
乐师陶总听他说最近又学了什么、见了什么,好像森林里好玩的东西总是那么多。
“等我再长高一点,我们可以背个竹筐,去捡栗子。”望天说,“你知道吗,越往里走,树越多,如果走到非常非常里面,连村子的灯火都看不见了。就是白天看,森林里也黑漆漆的。”
他比划着,伸手遮去乐师陶眼前的阳光。
“树枝密密麻麻的,把太阳都挡去了,有点吓人。但是很舒服,山里的风就算是夏天也很凉快,”望天看着山的方向,喃喃道,“真的很舒服,要是陶陶你也能一起去就好了,我们可以找个大人们都不知道的地方,做什么都行。”
“真好,”乐师陶也有点向往,但很快又想到什么似的,小声道,“可是我跑不快,我会不会拖累你?”
“我和娘亲在学射箭了!你可以慢慢走,有危险我会保护你的。”
望天模拟拉弓时的姿势,虽然还不熟练,却倒也有模有样。就在他假装自己正在拉弓瞄准时,视野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毛绒绒的身影。
今天天气很好,天上竟是一片云彩也没有。阳光简单而粗暴地照在地上,看到的画面都同热浪般扭曲。
望天还以为自己是看差了,却听见乐师陶也发出一声惊呼。
“那是小羊吗?”
那确实是,甚至可以说是刚出生的羊崽。等眼睛总算适应了,那原本看不太清的模样也逐渐清晰了起来。仔羊的腿似乎还站不太稳,歪七扭八地勉强站了起来,四条腿各走各的,还微微打着颤。乐师陶见它路都走不明白,便凑近了想看看。望天有些犹豫地拉住了他的手,他也不清楚怎么会有刚出生的小羊走到村里。听说羊是会顶生人的,乐师陶身体不好,他不想他受伤。
乐师陶拉着望天的手,轻轻拍着安慰他没事。
和望天相处这么许久,他身上阴郁的气场早就被孩子该有的朝气所取代。望天很喜欢乐师陶说话的语调,总是很轻、很柔软。有时候他会担心自己听不见乐师陶说的话,会挨他近些,乐师陶便也总是伏到他耳边说话,倒像是在说些悄悄话了。
乐师陶松开望天后,便跪到那小羊的身边,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触摸仔羊那柔软的皮毛。仔羊在他的手心靠近时还有些抗拒,但它才刚想躲开,好不容易维持的平衡便被破坏。仔羊踉跄着要往地上摔去,乐师陶便慌忙抱住了它。受惊的仔羊后腿开始拼命扑腾起来,却只挣扎了两下便消停了下来,抬着头观察着抱住它的乐师陶。
仔羊湿漉漉的眼睛似乎白膜还未褪去,迷茫地分辨着周围的一切。或许是乐师陶的怀抱实在令人舒适,竟是这么安分地被人整只抱起。它太小了,乐师陶抱着它毫不费力,仔羊蜷缩着四肢,安稳地坐在乐师陶的怀里。
它原来有这么小吗?望天有些疑惑。乐师陶将仔羊抱给他看,望天尝试着触摸了仔羊的脑袋,蜷曲的羊毛显然还有生长的空间,但那温暖柔软的触感却有种令人着迷的魔力。他闻了闻,仔羊的身上没有野兽该有的腥气,却是有种太阳公公的味道,让他联想到洗过晒干的被褥和衣物,也让他莫名想到了乐师陶。
“山里也会有羊吗?”
望天摇摇头,道:“我没有听说过。”
乐师陶兴致却很高,仔羊的乖巧让他有些爱不释手。
“真的吗?可是村里也没有人家养过羊……”望天第一次听到乐师陶因为兴奋而有些雀跃的声音,“那我可以养它吗?我第一次见到活的羊!”
“它毛绒绒的,我感觉我能一直抱着它。”
乐师陶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红晕。
望天也觉得很幸福,但他说不清为什么会觉得幸福。那种轻飘飘的忘乎所以的感觉让他对自己感到陌生,以至于有些恐惧起来。
回去后,他便和父母说了他和乐师陶捡到了羊的事情。父亲虽然觉得捡到羊也没什么,但帅娘却好像在想些什么。
“既然是小羊,那总该有母羊吧?”帅娘说,“夫君,你今天进山的时候,有看到羊群活动的痕迹吗?”
“没吧,也可能我没留意,”老望摇摇头,不以为意道,“兴许是隔壁村子的,也可能是牧羊人走丢的小羊吧。他们丢了羊,总会来找的。如果没人来寻,让乐工他们家养着不也挺好的?”
帅娘迟疑着点点头,望天也觉得或许是件好事,毕竟乐师陶那么开心的样子,只怕如果当真有人来寻了,不知道他会不会伤心。
“望天,”帅娘叮嘱道,“你觉得呢?”
“我……”望天心里正雀跃着,突然被点,却是有些疑惑起来,“我觉得……”
“望天。”
父亲也这么问他,两个人的脸上都是罕见的认真模样。
小小的不安就像种子,望天看着熟悉的父母,他们的相貌似乎都变得模糊起来。
就在他的嘴唇嗫嚅着,有个答案呼之欲出时,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般,老望笑着摸了摸他的头发。
“明天休沐日,你和小陶玩儿去吧。”
“嗯!”
望天松了口气,紧绷的身体勉强放松了下来,他点点头,为明天的见面而觉得雀跃。
雀跃、雀跃,甚至晚上怎么都睡不着,满心欢喜想着的都是乐师陶和那只仔羊。不知乐师陶会给它起什么名字,明天它能走路了吗?它那么小,可以长到多大呀。
真希望它能长得越大越好!
……
而后又过了许多日,都没有人来寻丢失的仔羊。乐师陶抱着小羊回家的模样被许多人目睹,村民们也都只当他好运,竟然就这么普通接受了仔羊的存在。
仔羊惹人怜爱,就在村民们以为乐工养着仔羊是为了后面的日子可以吃肉时,乐师陶却很是不忍,当真以为父亲会等小羊大了杀来吃。乐师陶不好当面忤逆,怕乐工用失望的眼神无声地审判他。只是怀着心事在每一个夜晚流着眼泪,然后抱着仔羊入睡。泪水打湿了羊毛,而仔羊就这么安静地依在他的怀里,用湿乎乎的舌头舔他的脸。
那是有点刺挠的触感,哭着哭着,乐师陶总是在悲伤中入睡。他总是多梦,有时母亲翻个身,或者父亲和母亲有时说着小话,任何细小的动静都能将他吵醒。姜戎为他操碎了心,每天都轻轻拍着他的身体,哄他入睡。乐师陶自己也觉得自己没出息,故而每次深夜醒来,他都只蜷缩在被窝里,数着房梁上的木纹。那一圈圈扭曲的沟壑像极了狰狞着的面孔,似乎有怪物就藏在阴影里,等着他入睡。
捡到仔羊后,就像有了小小的守护神。他再也不需要姜戎哄他便能自己睡着了。梦里的洪水猛兽都褪去。在他小小的脑海里,似乎只有初夏的风,他躺在树荫里打着盹,仔羊和望天都在他的身边。就像望天曾和他说的那样,他们在那小小的秘密基地里,有溪流顺着山峦沟壑静静流淌着,拔地而起的巨木为他们撑起整个天空。仔羊好像在吟唱,见他似乎醒了,便继续用舌头舔舐着他。
梦里的望天什么也没说,只是和他一同躺在草地上,胸膛轻轻起伏着,应该是睡着了。
他的手里握着什么,散发着温暖的光。但乐师陶看不分明,就在他想去看个仔细的时候,仔羊轻轻叼住了他的衣袖。再然后,他便清醒了过来,仔羊瑟缩在他的怀里,宛如初见时颤颤巍巍的模样,嘴里还咀嚼着他的衣角,已经被口水弄湿了,贴在身上凉凉的。
乐师陶每天仍是抱着仔羊,他对仔羊越是依赖,望天看他的眼神便越是模糊。他的眉眼似乎总藏在睫毛投下的阴影里,但乐师陶觉得他在忍耐,却又不知道他在忍耐什么。最近的村里的气氛总是怪怪的,大家的态度都变得格外友善起来,可当他走在街上却发觉已经许久不见到别人。只有望天,每天都会来找他,却总是欲言又止的模样。
直到有一天,望天没有来。
乐师陶感觉自己的大脑逐渐混沌,甚至记不清年日。但好像许久见不到人了,他的父母总是不归家,但桌上却摆着做好的饭菜。他像往常一样,去井边打水,却因为得抱着仔羊而空不出手,只能费力用着一只手去够井绳。他的半个身子几乎都探进井里,摇摇欲坠。很快他就觉得身体一轻,身后好像有人在帮他,回过头去才发现是仔羊咬着另一端井绳。他们一人一羊合力,总算将那沉甸甸的水桶捞了上来。
“你怎么那么厉害呀。”乐师陶高兴地将它抱起,脸贴在那棉花般的皮毛上摩挲着,“有你真好。”
他每次夸它,仔羊都会亲亲热热去舔乐师陶的脸,似乎是听懂了乐师陶说的话,眼睛都眯成月牙般。从一只仔羊的脸上甚至能看出些笑意来,有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寒意。
但乐师陶仿佛看不见,忘记了打水的目的,只是抱着仔羊继续去喂鸡。若他此时能低头,便能发现刚刚那沉重的水桶却是空的,骨碌碌滚在他的脚边,像是一种提醒。
“乐师陶,你为什么在这里?”
有人在说话,是孙樵夫的儿子。他们平日里几乎不怎么说话。孙樵夫的儿子看不上身体孱弱的他,似乎觉得那股病气好像会传染般,总离他远远的。乐师陶畏惧他那双总饱含质问的眼睛,故而每次遇到他都只专心看着地面,等待那场无声的质问结束。
乐师陶仍旧这么做了,孙樵夫的儿子却没有和以前一样放过他。他小步跑到乐师陶的面前,用手扶住他的肩膀,继续质问道。
“你没听见那个声音吗?你为什么还在这里?你的爹娘呢?”
“他们一早就不在家,我……我不知道。”
乐师陶越是惶恐,越是衬得孙樵夫的儿子强势异常。乐师陶受不了那语气,孙樵夫儿子的声音宛若天雷滚滚,鞭挞在他的心上。似乎映照了他的动摇,天上的云彩开始涌动,宛若漩涡般聚集在那方小小的空间里。仔羊抬着头,看着天上的漩涡,挣扎着要从乐师陶的怀里跳出去。
“你在藏什么?拿出来!”
“我没有!”
孙樵夫的儿子几次动手,妄图从他的手里将仔羊夺去。乐师陶内心的恐惧几乎要将他淹没,不知哪来的力气,他揪住孙樵夫儿子的衣领,拳头就要落在他的脸上。
“乐师陶!”
忽而有狗吠声在他耳边炸开。不知何时,他被狗儿扑倒在地,尖锐的獠牙几乎要刺进他的脖颈。他有一瞬间瑟缩,却很快又咬着牙反扑过去,一人一狗几乎扭打在一处。然而狗儿却一直没还手,乐师陶没打过架,拿捏不着要领。狗儿的身体泥鳅般从他身下溜走,乐师陶失去重心摔到地上。他的手心只抓到了地上湿润的泥土和一把锋利的杂草,那草生着锯齿般的边缘,划破了他的掌心。
鲜血落在草叶上,反射出他那张惶恐的脸,陌生得他自己都认不出来那副模样。疼痛下他回过神来,才发觉原来划破掌心的不是杂草,而是一把熟悉又陌生的短刀。
刀柄上用布条一层层缠绕着,只隐约渗出些铁锈般的痕迹。然而布条的雕刻的花纹却分明告诉他,那是望叔爱用的小刀,此刻却在他的手上。
身后仍是狗吠声和望天在叫他的名字。混沌的意识逐渐清晰起来,就像是大梦初醒,此时他才有余裕去观察周围的环境。仍是他熟悉的村子,回忆里的山林却好像离自己那么近,高大的树木向他倾倒而来,几乎将他吞噬。
他徒手握着刀刃,越是紧握,伤口便越大,直到刀刃卡进手骨的缝隙,才堪堪停下。剧烈的抽痛催促着他去寻找其他人,却看到阻止孙樵夫儿子的望天,和不断咬着他的腿的狗儿。
那是望天家的猎犬,他为什么忘了,还试图攻击它。
头和手都很痛,乐师陶踉跄着走了两步,和望天一起去拉孙樵夫儿子的肩膀。却和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一样,孙樵夫的儿子执拗着要往森林的方向走去,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乐师陶甚至能看见他额角的暴起的青筋,他的眼睛似乎在恐惧什么,生理性的泪水很快淌过那张充满矛盾的感情的脸。
那只仔羊却温顺地依偎在孙樵夫儿子的怀里,一如在乐师陶怀里时那般,用粉色的舌头轻轻舔着孙樵夫儿子的脸。乐师陶甚至隐约能看到被仔羊舔过的肌肤变得模糊,五官似乎都渐渐隐去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团迷雾,朦胧着宛若活物般蠕动着。
忽而天光乍现。层层叠叠宛若漩涡般的云层中仿佛碎裂的镜子般裂出一条缝隙,有电光御空而来。望天拉着乐师陶闪躲,勉强躲过了那犹如雷霆般的一击。孙樵夫的儿子望着裂开的天空沉思,很快那道裂缝便像有无形的手缝合上般拢上。那道光消失了,山林中却漫出雾来,像一只只手去触摸他们的脚踝,要将他们拉进雾里。
在云层重新形成漩涡的前一刻,有道更细长的身影从云层中坠落。那落在地上的雷原是一柄剑,坠着梅色的流苏。似是有感应,那剑挣扎着从泥泞中破出,发出一阵悦耳剑鸣,稳稳接住了从空中落下的人影。
孙樵夫儿子的背影却适时地隐去,他曾经站过的地上只剩下半截脚印。乐师陶看见他那双仿佛还在质问他的眼珠仍瞪着他,此刻却像某种求救的信号,扎着乐师陶的心脏。
乐师陶试图追进林子,却有刀光在空中划过一道宛若祥云般的纹路,直直指向了他的脖子。有那么一瞬间,乐师陶觉得自己已经死去了,刀尖抵着他的咽喉,喉结随着吞咽上下滚动着,刀尖便在他的颈上留下一道血痕。
望天一把将眼前呆住的乐师陶拉至自己的身后。不知何时他捡回了那把小刀,刀身上还残留着乐师陶掌心的血迹,顺着刀柄流到望天的手心,滑腻得几乎握不住。望天觉得自己的手仿佛还在颤抖,他强硬地要乐师陶后退,自己则是双手持刀。眼前那人似乎和自己一般大,望天却只感受到了清晰且锐利的杀意。那道杀意不是针对自己,却是指向身后那人——乐师陶躲在他的背后,即使不用去看,也能感受到他的害怕。共鸣般的恐惧让两个人此刻都像待宰羊羔般瑟瑟发抖,却仍逞强面对眼前的陌生人。
池莲有些疑惑地歪着头。
“陶陶,你现在就去村里,”望天快速道,似乎有些失声,“……大人们、我爹也在,他会保护大家的。”
“你为什么要保护他?”池莲脸上的疑惑不似作假,他无视了望天手里那把颤颤悠悠的短刀,持刀迎面走上前来,“忘了,你看不见。”
“我重新问过,你是人,为什么要保护妖?”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乐师陶是我一个村里长大的朋友,决计不是你口中的妖还是怪,”望天振声道,“你是谁,我从未见过你。”
“这里没有你要找的妖怪,退下!”
眼见池莲逐渐逼近,望天便越是严声试图逼退他。然而一个孩子的威胁仍不成气候,池莲甚至不觉得那是在威胁。他捏住望天的刀尖,不费吹灰之力移开,却又好像认出什么,从望天手里夺过武器,仔细打量起来。
望天下意识要将刀再抢回,却再一次被池莲手中那把长刀逼退。望天见唯一的武器被轻松抢走,便想带着乐师陶逃走,却不想另一把飞剑拦住了他们二人的去路。
腹背受敌,此处里村里又有段距离。此人分明有通天之能,就算能叫来村人恐也无济于事。望天试图让自己冷静,却紧张得汗湿了后背。
池莲将那裹着刀柄被血脏污了的布帛抖去,那刀柄上雕刻的花案重现于世。他撩开长袍的下摆,分明挂着数枚箭头般大小的碎玉来。那玉的品质并不高,甚至布满隐裂和石质的纹路来,却隐约能瞅见人工雕琢的痕迹。
上面的图案因年岁和损坏过而残缺,却仍能与那刀柄上一一对上,显然是成套的。
望天手里这把明显是把完整的玉器,刀身虽然被村里的工匠修补过,玉柄却是一直保留了下来。原本由望天的父亲一直贴身带着的,现在却是给了望天护身。
“还给我!”
那把刀对他来说意义非凡,他无法忍受被贼人夺走。就在他做足了心理建设,即使用蛮力也要将它夺回时,池莲却是点点头,干脆利落将刀递给了他。
“好。”他说。“不要离它太远。”
那把坠有流苏的飞剑无人驾驭,却仿佛有意识般护在二人的身旁。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竟是被狼群包围了。它们仿佛凭空而生,丝毫不畏惧刀剑,脊背高高隆起,小腹却是干瘪的,好像饿了许久,急于用利齿撕咬他们的身体,用血肉填补那无休止的空虚感。
池莲的刀快而精准,一刀便将那头靠近的狼一刀两断。眼见狼的尸体瘫软在地上,池莲的脸上却闪过一丝怪异,眼睛看到的画面分明告诉他自己的攻击穿过了那头狼的身体,手感上却只像砍到了棉花。
就像什么都没砍到,那把沉重的刀强大的惯性几乎将少年那轻薄的身体整个扭曲。池莲顺着那道力腾空而起,他需得双手持刀方能将它抡起。狼群只是在一旁摩拳擦掌,用爪子刨着地面,伺机而动,却总是不上前。他心有所感,横刀拦腰砍过,那狼的身体软绵绵的,完全不似寻常生物。依旧是什么都没有砍到的手感,但那狼的身体确实被一刀斩断,倒在地上,最后融化般血水溶进地里,变成斑驳的树影,消失不见了。
池莲拎起目睹了一切画面的两小只,踩上飞剑后便朝村里驶去。
那狼到底是没再追来,他们的身影在雾里隐去,消失在山林的深处。
或许是因为池莲救了他们,又或许是因为感觉到池莲并非想象中那样的非法之徒。望天和乐师陶对他不再戒备,只因为从来没有御剑的经验,只能像鸡崽般抱着池莲的腰。池莲有些苦恼,却只能让他们抱着。
三个人抱作一团,挤在一柄剑上,模样有些滑稽。
望天指了指村里最大的建筑,门窗都紧闭着。池莲闭着眼感应着,似乎感受到了人气,便带着另外两人落地。
“前几天,山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出来了,我爹……猎人们装的陷阱都被破坏了。大人们进山去看过,却一无所获。村里的大家意识都不太清醒,村长动员了还能听进话的人把所有人都抬进了礼堂。”望天说,随后看向乐师陶,“所有人都齐了,只有你,好几天了一直没有下落。”
“他们说你一直想进山里,怎么都拦不住,自言自语地说着话,却怎么也叫不住你。”
“后来,我说要来找你,可是……”望天有些犹豫,却仍继续道,“除了你家和我爹娘,他们都不记得你的样子了。我解释过,却只有孙樵夫家的信了我的话,和我一起出来了。”
“但我却把他弄丢了。”
乐师陶想解释,他的所见所闻与望天截然不同。村里的事他一概不清楚,只记得自己同往常般生活。很快,他想到了仔羊。
“我……捡到一只羊,”他比划着仔羊的大小,却自己也拿捏不准尺寸,“可能是这么大,也可能只有这么大,雪白的,很温顺。”
“它太小了,总需要人抱着。抱着他的时候周围的声音好像都听不太清了,不过我似乎感觉……”乐师陶喃喃着,脸上却是有些无助的神色,“感觉我和它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我很幸福,我……我……我记不得了……”
池莲点了点他的眉心,有抹光没入了他的额头,是道安神的咒语。
“你被污染了。”池莲说,“你确实记得自己捡到过羊吗?”
“小天……我捡到羊的时候,小天也在。”
望天思索着,跟着肯定道:“确实。”
乐师陶的眉头总算舒展了,望天却继续道。
“但是羊呢?”
“直到刚刚,我还抱着的,就像这样。”
乐师陶拢着臂弯,仿佛他的怀里还有着那只无人记得的羊一般。
“我和孙家的一起找到你的时候,你手里什么也没有,”望天说,“所以,羊呢?”
望天想了想,又摇着头补充道:“不对,我看到过羊,可是……”
“我为什么想不起来了?”
“我明白了。”池莲说,他同样点了点望天的额头,眼见逐渐慌乱的望天也逐渐冷静下来,“这确实不是我擅长的领域,但症结所在我已明了。”
“这柄短刀你需一直握在手里,只要它在,就能暂时保证你们无碍,”池莲将望天的手与重新回到他手里的那把玉柄小刀重新缠在一起,“守在其他人身边,无论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许出门,不许松手,更不许进山里。”
“好。”
“应得太快,”池莲道,“复述我的话。”
“……不准出门,不准松手,更……”望天喃喃道,“不准进山?”
“嗯,去吧。”
池莲轻轻推着他们,礼堂的大门被打开,露出一双双惊恐的眼睛来。望天和乐师陶被那视线吓到,后退了两步,却有人从里面伸手将他们一把拉了过来。
老望的脸色明显比乐师陶记忆里要憔悴,臂膀却仍是有力,抓着望天和乐师陶的手丝毫没有动摇。
“回来就好,快,进里头去!”老望推搡着二人,又留意到池莲,但他已没有第三只手去拉那个和乐师陶与望天一般大的孩子了,“那边的小孩儿,你也快些!”
池莲却没有理他,重新御剑而起,往山林的方向去了。
“那是……那是应山来的仙人,”村长喃喃道,“许久不曾见过了,那身白袍……是仙人降世了。”
“应龙脊,撑天起……”
村长浑浊的双目似乎受那道剑光刺激,竟是流下些泪水。那道风中残烛般的身体如山倒般朝一旁倒去,有村人急忙去搀扶着他,让他在软垫上落座。
周围围着的许多人都是村里孱弱或是行动不便的病人,乌泱泱一片,望天这才发觉,原来村里竟有这么多人。
孙樵夫不在,只有他的妻子留在这里照顾病人。她拉着望天的手,脸上都是彷徨无措。
“我的幺儿……我的幺儿呢?”
望天哽咽着,将方才发生的事一一讲了。
孙樵夫儿子失踪的事、狼群袭击的事、池莲的事、村里有妖怪、刀的事。
“什么叫,为了救人,我幺儿失踪了?”孙樵夫的妻子不可置信道,“为什么会有狼?我根本没听过!不是有人去过山里了,说没有见过狼吗?”
老望罕见地沉默着,好像在想望天说的话。
“我那可怜的,可怜的幺儿……他最怕狼了,什么叫他消失了?”
孙樵夫的妻子拉着望天,声泪俱下。
“你是不是哄我,我儿是不是被狼叼走了?”
她哭得伤心,望天有一瞬被巨大的愧疚所压倒,随着孙樵夫的妻子瘫软在地上,他的背脊也跟着一点点弯了下去,几乎匍匐在地上。
乐师陶突然走到了望天的身前,挡去了孙樵夫妻子的视线。他缓慢地跪下,伸手拢住她的手,那双救过许多人、甚至包括自己的手上都是疮痍。大多村人都有着那么一双苦于劳作的手,并不好看,却总是很有力量,和泥土一般有着天生的安全感。那双手此刻却在他的怀里颤抖着,丧子之痛让她悲愤交加,却又无法狠下心去斥责眼前同自家儿子一般大的孩子们。
“一切都是我的罪过……是我将怪物引入村里,是为了救我您的儿子才下落不明,我这条命欠过您一次,也欠您儿子一次。”
乐师陶忽然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他想遍了所有都想不到可以弥补眼前这个可怜的母亲的事物,自己那条微薄的命似乎填不满她心里那道创口,但似乎那也是他拥有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了。就在他的想法逐渐偏颇变得极端,姜戎却是缓慢地从人群中走了过来。
乐工搀着她那具病躯艰难移动着,每一步似乎都用尽了力气。宛如生产那夜,她发着高热,手却很是冰凉。姜戎俯下身,那只平时用来绣花的手没有一点预兆地扇在了他的脸上。
姜戎从未打过他,这一巴掌仿佛比最严酷的惩罚还要来的伤人。乐师陶沉默地承受着母亲的责备,姜戎却是一言不发,从乐工的手里挣扎着又是一巴掌扇了过来。
姜戎打人并不痛,但或许是真的病到没有打人的气力了。乐师陶惶恐地抬起头,他的母亲因为高热几乎看不清眼前的东西了,乐师陶想要扶住摇摇欲坠的母亲,姜戎却一把将他和乐工推开。她颤抖的手提着乐师陶的领子,大概是觉得巴掌还是不够,握紧了拳头便要继续打醒她那不争气的孩子。
何其卑劣的手段,孙樵夫的妻子笑出声来。姜戎逼着她不得不去原谅乐师陶,眼前的一切仿佛都像一场闹剧。乐师陶仍握着她的手,掌心的鲜血汩汩而出,怎么都止不住,打湿了她的衣衫,温热的就像所有生命般,刺痛着她手上那些干裂的伤口。
孙樵夫的妻子脸上仍是痛苦的神色,眼神晦暗着,却只能将乐师陶拉到自己怀里,为他包扎着手上狰狞的刀口。
她的让步总算制止住了姜戎的下一步动作,但显然她再也没有更多力气,眼里就算有再多的眼泪也在滚烫的体温下被一点点蒸干。
乐工沉默地扶着自己的妻子重新躺下,他没脸面对其他人。村民们也一言不发,却是小心避开了他们夫妻,各自画地为牢,满脸疲惫地倚墙缩着身体。
村长反反复复只断断续续唱着那段童谣。屋内太安静了,只有村长那沙哑的声音在不断地吟唱。
望天抬着头,乐师陶的背影藏在所有人的后头,孙樵夫的妻子正为他处理着伤口。父亲一言不发守着门,望天努力从地上爬起来,亦寻了一块地坐下。他的手上仍缠着那柄短刀,不知道池莲用了什么法子,那把刀死死黏在他的手上,就算他试图从布帛中抽出手来也无济于事。他越是用力,那布帛缠得越紧。望天冒着冷汗,他觉得自己的手仿佛不听他的使唤,无论如何都想逃离那柄刀。当他意识过来自己正在违反池莲告诉他的规则时,却发现所有的村人都在看着他。
“那个仙人是不是说过,只要有那把刀就可以得救?”
“说了。”“说了。”
村民们窃窃私语着,应答声此起彼伏。
“小天一向最不让人操心了,你还小,拿着刀太危险了。”
“还是把刀交给大人们保管吧。”
“对。”“对呀。”“听话。”
村人们仍是他熟悉的模样,脸上却都如出一辙慈祥地笑着。他们的手就和他记忆里一样摸着他的头,却强硬地,要从他手里抢过那把刀来。
“你看,你也想撒手的。”
村人们的话像某种呓语,轻飘飘的没有语调,让望天想到神情恍惚时乐师陶的自言自语的模样。他们的眼里似乎看不到他,露骨的视线只是随着他手里的刀而移动。
望天第一次知道人的眼球能转动到那种程度。他握着刀柄不断后退,直到背脊撞上墙壁。退无可退时,他求助的目光看向他的父亲,才发觉,他的父亲和村民一样,用着那怪异的目光盯着他,或者说盯着他手里的刀。
他踉跄着,不断躲过村民的手。他觉得自己似乎就在某场噩梦里,手里滚烫的刀把却好像在告诉他不是梦境。望天一路逃到窗边,他能看见有光从窗户的缝隙透过来,就在他犹豫要不要越窗而逃时,有腥臭的液体滴落在他的脚边。那是半截狼的脑袋,被劈成了两半,切面却只是黑漆漆的让人看不清楚。那饿得发绿的兽眼盯着他,渴望着他的血肉,只需他再靠近一些,便能饱餐一顿。望天被恶心得一激灵,却是挥刀而起刺向那只狼眼,在刀刃刺进眼眶的那一瞬间,狼首忽然笑了起来。半截狼首笑起来的模样实在诡异异常,像岸上濒死挣扎的鱼,他的头骨在窗沿的木枕撞的震天响。望天试图抽手,却发现刀刃卡在了眼眶里怎么都拔不动。村民们越靠越近,昏暗的环境下他看不清村民脸上的表情,却觉得心里惊恐异常。
池莲留下的安神咒不知是否还发挥着作用,望天虽然害怕,但脑袋却清醒得更让他觉得恐怖。借着窗口的光,他环顾四周。父亲仍用着那种诡异的眼神看着他,却不似其他村民那般逼近他。他的角度只能看到乐师陶的背影,孙樵夫的妻子似乎抱着他蹲在地上发抖。那是个近似保护的姿势,然而用力之大却快要将乐师陶勒到窒息。
乐师陶被那个臂弯箍到喘不过气来。他的手不断抽痛着,因缺血而逐渐变成紫色。孙樵夫的妻子似乎被那血所烫伤,捂着脸连连后退。乐师陶总算从那窒息的怀抱中挣脱出来,没有等他缓过劲来的时间,孙樵夫的妻子又陷入那股莫名害怕的情绪里,怎么都叫不醒了。
他惊惧着摸索着周围,却是踩到一个硬物,那是把沾有血迹的斧头。忽然他好像听见有人在同他说话,那声音模糊不清,又分成两种不同的声线。
模糊的声音对他说,望天有危险,他要用斧头去攻击村民。
细小的声音对他诉说着恐惧,狼的夜嚎无穷无尽,从四面八方来,他逃不掉。
乐师陶将斧头握在手里,离他近的村民便将注意力转移到他的身上,仍是说着和对望天说过一样的话。
“你为什么要拿着那么危险的东西?”
“快拿来,快拿来吧。”
嘴里说着,村民们却没有一个人敢向前的,好像乐师陶手里血迹斑斑的斧头是什么神兵利器,连让人靠近的勇气都没有。
嘈杂的人声中,仍是那道细小的声音,说着只有乐师陶能听到的话。
“是爹爹在那个时候……救了我和娘亲。”
“不去杀了那些村民,他们就会杀掉你和小天。”
有人在诱惑着他,模仿那道细小的声音,轻飘飘的语气听不出一丝恶意,只是在陈述着事实。
“我认识你,”乐师陶说,“梦里总有人对我唱歌,我应该是认识你的。”
似乎下定了决心,乐师陶握着斧头穿过人群。村民们视那斧头如洪水猛兽,竟无一人阻拦,向乐师陶前进方向的两侧倒去。他在望天的身旁站稳,那斧头实在太沉,仅是举起来便用尽全身力气。
两道声音都在说服他,挥下去,挥下去,挥下去。
乐师陶的眼睛骨碌碌转向望天,却又与村民不同,不听使唤地四处转动起来。
“陶陶……”
望天嘴里嗫嚅着,听到他的声音,乐师陶的脸上似乎闪过一丝痛苦来。
他闭上双眼,努力挥动着胳膊,耳旁只能听见斧头劈开头骨的声音。
咔嚓,咔嚓,令人牙酸。
乐师陶的力道还是太小了,他劈不开狼首,却是刺激得眼前的景象愈发恶劣。就在他们看见的画面不断扭曲之际,忽而所有的一切都同晨雾般消散了。
没有半截狼首,没有村民们诡异的视线,所有人都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甚至能听见隐约的鼾声。
望天手里仍握着那把刀,却是一副左右手互搏的姿态,是他自己将握刀的那只手按在墙上。梦境被解开,他的手总算活动自如起来。
乐师陶也宛如大梦初醒,他的手里只剩下半截桌腿。梦里看到的都是虚妄,然而那挥动斧头的手感却逼真得令人无法无视。他的虎口甚至因为蛮力而迸开一道血口,本就狰狞的手心更是血肉模糊。
木制的窗户被他打的稀烂,月光照亮了他和望天那张有些脏兮兮的脸。
窗外,半截兽影倒在地上抽搐着,却不似狼型。
浓烈的黑雾覆盖了它的躯体,地上没有一点血迹,却见那雾仿佛烧尽的木灰,一点点瓦解崩溃,最后化为乌有。
有道清丽的背影站在他们的屋前,抽剑归鞘。
她回头,眼尾那点红妆随着她的笑容格外晃眼。
“嗯嗯,看来我赶上了。”
……
村民们仍在昏睡中,污染的程度各异,却还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许照冥的眼中,眼前两个形容狼狈的小孩可以说是污染的化身。浓郁的黑雾缠绕在他们的身上,几乎认不出原本的模样来。若不是池莲留下的术法在夜里仍就发着微弱的光,许照冥便要同池莲一般,以为眼前的孩子就是妖兽,条件反射就要将二人原地斩杀。
“好啦,看来只有你们还‘醒’着了,”许照冥笑意盈盈拉过望天的手,她的手心似乎写着某种咒文,她触碰过的地方污染正在被一点点溶解,“告诉姐姐,你们遇到了什么?”
望天和乐师陶将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了许照冥,他们的证言中存在着太多的矛盾,许照冥却没有追究的模样。她摸了摸乐师陶的脸,用干净的帕子将他脸上的血泥和污染一点点擦了去,这才勉强能看清他的脸来。
“嗯嗯,姐姐我都明白了。”
许照冥提着剑,在礼堂周围的泥地上写写画画着什么繁琐的图样。那应当是某种文字,只是两个小孩并不识得。她身上也穿着和池莲如出一辙的白袍,若和村长说的一样,他们都是应山来的仙人,想必此时画下的必是能庇护村人的仙术。
许照冥绕着礼堂转了一圈,最后一笔毕,那用剑刻下的咒文都埋于地里。隔着阵外看,即使礼堂门敞开着,却也看不见里面的人影。远远看去,不过一间空屋罢了。
望天有些奇异地朝阵内走去,阵却拒绝了他。他只摸到有面坚硬的墙壁,看不见,却过不去。乐师陶看他动作怪异地摸着空气,也试过,却是被拒绝的更彻底,强大的阻力差点没将他弹开。是许照冥在他的身后悄悄接住了眼前这个污染仍在蔓延的孩子,她的脸上却还是挂着笑容,眼里却好像并没有在笑。
乐师陶不解,她却只还是摸了摸他的头。
幻像没有被完全解开,眼前的孩子们却一无所知。远处的山林就像是虚构的画面,层层叠叠不断重复。像是古塔上人为画去的图案,盘旋着蔓延到天上,铜墙铁壁般将村子包裹在其内。
“梦涡”是种相当狡猾的妖兽。它们单独一匹对人没有直接的伤害,却会与其他妖兽携手……硬要说,“梦涡”并不是智能高到有携手共谋意识的妖兽,或许只是一种互利共生的生态意识罢了。它们通常以无害的形象出现,可以是任何生物,但大多是羊的姿态。它们天生知道如何从人群中挑选最适合的对象,诱惑他们去触摸它、刺激起人的保护欲。通过美梦或噩梦让人无法离开它的怀抱,最后自愿成为它们的巢穴。等梦被吃空,他们就会将宿主干瘪的躯壳也一并吃掉,然后不断扩大巢的范围,直到将所有人都消化。
许照冥看着天上盘旋成漩涡的云层,她此刻就在“巢”内。
她轻轻捧起乐师陶的脸,轻声问他。
“是你在做梦吗?”
“我不知道……”乐师陶茫然道,却又在短暂的疑惑后悄悄点了点头,“但我觉得……应该是的。”
“乖孩子。”
望天有些不解地看着乐师陶,似乎需要一个解释。
“我听见,有人对我说话,”他思索着怎样才能说清自己脑海里那奇妙的两种声音,“我认识的……但我说不出来。”
“我觉得,我应该是知道声音的来源在哪的。”
“那么,在哪呢?”
乐师陶有些慌乱,在眼前的仙子姐姐摸过他的脸后,那声音便变得更细小,他再用心去听,也听不大清了。
“我……我听不到了。”
许照冥的手轻轻触碰他那有些干裂了的嘴唇,制止住了他接下来要说的话,只是有侧重地询问。
“是听不‘到’了,还是听不‘清’了?”
“我听不……清了?”
乐师陶喃喃道,便见许照冥将一道符覆住了他的眼睛。那一瞬,他的视野渐渐暗了下去,浓雾织成黑暗取代了视觉,乐师陶甚至以为他又开始做梦了。他感觉自己好像突然被什么人抱住了,瘦小的臂膀是熟悉的触感。他摸索着摸到了身边人的脸上,脑海里拼凑出望天的五官来。
“小天?”
望天被不安分的手摸着脸,表情却是十足的戒备。
“你做了什么?”
他听见望天的声音在质问。
“现在呢,你‘听’到了什么?”
乐师陶便更用心去倾听,他能听见望天和许照冥说话的声音,也能听见风吹动树叶的声音。他尝试去捕捉记忆里那模糊的两道声音,却总是差一点点。许照冥似乎在摸他的脸,喃喃着“还不够啊”,便继续用符封锁着他的其他感官。
“没事的,只是暂时的。”她安慰着两小只,态度却仍是强硬,“但如果解不开巢,我们就都出不去了。”
“有人在哭。”乐师陶说。
抽噎的哭泣声很快被痛苦的呻吟取代,声音的主人似乎做着噩梦。
“足够了。”
许照冥话音未落,却是将乐师陶一同“绑”上了飞剑。她沉默地看着望天,视线缓缓落在了他手里的刀上。
“有那把刀,你便可安然无恙。”
她说的话和池莲说的一样,望天不知道仙人哪里来的根据,分明他才被袭击过,那把刀并不想他们想的那样英明神勇。
“……但是你看起来并不信。”
“村长说,你们是仙人,”望天咬着牙,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不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仙人做事便可如此蛮横,不讲道理吗。”
许照冥有些奇怪,却不恼,反问他。
“不然呢?”她笑道,“你觉得我们不讲道理吗?那我要如何解释,如何说明才能征得你的认同呢?”
“你如果看不明白,大可以自己去看。”
……
乐师陶被封闭了视觉、嗅觉和触觉,他现在失去了控制身体的能力,只能靠同行的望天勉强将他的身躯稳定在飞剑上。但他的听力却并不完全能派上用场,或许是巢的核心离他们实在太远,他听到的声音总像隔着一层水般朦胧。大多时候得靠望天为许照冥引路,但他只知晓他们现在的方位,让他们不至于迷失在山林中。
途中,偶尔能遇到进山的大人。他们如同村里的人一般陷入了梦境,身上的伤证明他们也被梦境诱惑和什么争斗过,但呼吸还算平稳。想来在许照冥解决过村里那只云兔后,梦涡巢的蔓延得到了控制,他们虽然还睡着,却是已经从噩梦中“醒”来了。
“我听见有铃铛的声音。”
“铃铛的话,在那边!”
乐师陶从未进过山里,只能靠望天不断补正,许照冥按照他们指出的方向不断前行。偶尔能遇见有梦里呈像化作的狼群尾随在他们的身后,但那到底是虚妄。许照冥并指为剑,剑意驱使着手中符箓在林中炸出一道道火光。整座山林都在那光下一览无余,山林的阴影里似乎藏着更多的东西。许照冥心念一动,那柄载着他们的飞剑便在阴影中穿梭,剑光所到之处,锐不可当。
他们已经找了许久,但山路一直在变化。望天所言不虚,他对山路了如指掌,纠正的方向也总是正确。梦涡不应该能做到这种地步。自从许照冥进村开始,便总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好像踏进了层层迷阵。阵法不断交织构成的网密不透风地将人束在原地,令人厌烦。
忽然刀鞘上那枚花镖所系的红线绷紧成一条直线,许照冥朝着红线所指的方向御剑而去,却很快便在半空中刹住了车。那线在树与树间相互勾连,若是莽撞御剑,只怕要被缠绕其中,自讨苦吃。
“这里我们曾来过的。”
望天说,他看不到线,只以为自己带错路。
“嗯嗯,确实如此呢。”
密密麻麻交织的网描绘出了他们来过的路径。许照冥以被红线勾住的树为锚点,竟是在脑海里勾勒出个大致的模样。她再次召出沙盘,附近一带的走势因为还在迷阵中,沙盘上的流沙只不断塌陷,拒绝着显露出真实面貌。然而那红线却有所感应般,像蜿蜒的蛇般在沙盘上绘出图形来。
一个巨大的掩生阵,可以说是应山弟子人人必学的阵法,就连她方才画在礼堂周围的那个阵法,原型也不过如此。梦涡能进到阵内,说明阵法必有缺口。虽然不知道这阵是哪位前辈所绘,但笔法走势上来看却也有年头。许照冥正研究阵,身旁的灌木里却又跳出几匹狼来,她嘴里念念有词,对破阵一事势在必得。大概是觉得狼嚎恼人,就在她准备出手时,有人快一步将狼一刀两断。梦涡召唤的狼不过是梦中虚影,按理说受到打击便会消散,此刻却只是身形恍惚了一瞬,便又立刻从被斩断的地方重新聚拢,摇晃着继续扑向许照冥等人。
待看清出手人是谁,许照冥不怎么意外,仍是对他招招手。
“池师弟,好久不见。”
“嗯。”
池莲几步跳到许照冥的身后,望天和乐师陶被安置妥当后,许照冥便也举起剑来与池莲抵背相照。狼群越来越多,仿佛无穷无尽,却怎么也无法近二人的身。刀光剑影构成了密不透风的防线,狼群企图用利爪从中撕开一道口子,却只有被利落斩断的爪牙被扬上天际。
狼群在不断重生,乐师陶从那浪潮般的狼嚎声似乎总算听清了那道呓语声。
痛苦的呻吟声仿佛撕扯着梦境主人的灵魂,乐师陶的梦与他相连,他能够感同身受感受那撕心裂肺的痛苦。好像五脏六腑都在被搅动,乐师陶觉得自己腹部的皮肤似乎被剖开,有什么东西在快速流失。似乎是察觉到乐师陶的状态越来越差,望天试图将他唤醒,效果却并不明显。
许照冥和池莲大约也无暇顾及他们。望天想了很多办法,他甚至差点没对乐师陶动手,然而后者却只是皱了皱眉头,眼神却好像还是被什么不存在的东西吸引。
忽然,望天想到了那把刀,他其实不是很有把握,只觉得或许是最后的办法。
这把刀确实将乐师陶唤醒,按那两人的说法,如果乐师陶被污染的程度几乎与妖兽无异,那相比之下受影响更小的礼堂的人们尚且行动不能,乐师陶又如何能和他们一路坚持到现在。如果他们现在正在乐师陶的梦里,他便是梦涡所渴望的“巢”,既然如此在梦涡影响下产生的梦魇又为何会畏惧作为“巢”的鲜血。
用许照冥的话来说,梦涡会培育“巢”,“巢”会影响人,将受影响的人变成下一个“巢”的备选。然而在什么东西的介入下,梦涡和受影响的人现在都在被“巢”所排斥,就好像有什么东西代替成为了“巢”。所以乐师陶还能作为乐师陶保持着清醒。
答案呼之欲出,然而望天却不可能用刀去刺乐师陶。
……梦涡选择了孙樵夫的儿子,说明能成为“巢”的不止一个人。
“梦涡是一种狡猾的生物,他们会选择人群中最容易接纳他们的对象作为自己的‘巢’。”
当时第一个发现仔羊的人,除了乐师陶,还有望天自己。
换句话来说,他可能是那个本该成为“巢”的人。
想到这里,望天的刀尖翻转指向了自己。
然而在他就要刺下的那一瞬间,树荫下的阴影却好像拥有了实体。漆黑的影子淹没了二人,一时间,乐师陶和望天的时间就像被按下了暂停键。
狼群散沙般坍塌,却留下了可以直接触碰的残渣。形似妖兽死亡前留下的灰烬,漩涡般在许照冥和池莲的脚下留下了奇异的图案。许照冥看向两个小孩消失的位置,将那柄长剑负在身后,那枚沙盘形状的法宝在她的手上静静悬浮着。
“池师弟?”
池莲的手心翻转,从他的护腕中隐约能见两段纤细却又明亮的线来。
……
景朝五年,后世称之为“灾岁”。
饿殍遍野的年代,总有人在不断死去。那个时候荒郊野岭总有一类人被称之为捡尸人,若是给予合适的报酬,他们便会在深夜拖走那些无人处置的尸体。人死后留下的肉体若是得不到及时处理便会腐坏,而腐败又会招来瘟疫。捡尸人往往不受人们待见,然而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甚至官府也会悄悄托人去雇佣那些平日厌恶的异类,让他们定期去捡那些烂在城墙脚下的烂肉。
捡尸人会搜去那些死肉上最后有价值的东西,再找一处空地草率地埋葬了。若是一无所有,却还算新鲜的尸体,那具残骸本身就也会拥有自己的价值。饥荒肆虐的时候,可以吃的东西实在太少,那些来历不明却又便宜售卖的肉总是很快被一售而空。但即使如此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做那样的行当,他们确实是已经麻木了的苦命人,却也有许多因混乱而陶醉其中的怪胎。
有妖邪祸世,有人饮众生苦痛而得其乐。为救世,英雄豪杰层出不穷。有人以通天之术降世救民于水火,以凡人之姿征大道,曾被唤作仙人。妖兽的概念尚未得到普及,而他们抵挡在降妖的最前线,死伤不可谓之不惨重。死伤者大多为妖兽所食,能得全尸者更是少之又少。然而在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又有人开始追捧“仙人肉”,称其食之可除百病、得长生。
那身蓝白配色的应山派校服,原是妖邪乱世中的风光霁月,却又成了某些人的灵丹妙药。
曾有一支由少数应山弟子组成的精锐小队,为捣妖巢曾临蜀中。他们各是布阵设法的天纵之才,为从妖兽手中保下平民百姓,他们连路设掩生大阵。起初,物资充沛,尚能维持阵法运转。逐渐弹尽粮绝,然妖祸不平,就没有休憩的余裕。身上能用的武装都用尽了,最后仅能靠唯一的法宝护身。开始有人支撑不下去,一旦倒下了就再也爬不起来。他们没有能力收尸,他们自己尚且需要保全自身。人数逐渐变少,几乎每个人都在意识涣散前的最后一刻,将所有的修为都压在了最后的法器上,以其为阵眼,又或是遗书,写下了这宛若繁星般错综复杂的掩生大阵。环环相扣,密不可分,保护了这片地区整整十年。
作为阵眼的法器埋藏在各地,其形态各异,但共通之处,便是上面都人为雕刻着奇异的花纹,那是他们那支几乎快要被遗忘的小队的标志。他们以身献祭,愿为土地代偿,直到吸收的妖气完全污染了核心,陈旧的器皿上才出现一丝裂缝,最后神形俱灭。
最后侥幸活下的人,只能凭借曾经队友的弟子令用以缅怀。然而当他想要将曾为同窗的遗物带回应山立衣冠冢时,却发现自己的同门被作为灵丹妙药——他们的遗体被珍重地裁成小块,盛在那满是斑驳污渍的小碟中,作为祭品,或是礼物,祈求自己能得到救赎。然而最讽刺的,为了证明其确为仙人肉,须得以应山校服裹尸,方可得到认同。
他不记得自己最后是怎么抢回的遗体,只知道自己以后可能再也回不去应山了。同门们最后的遗物,或许也和他一样,再也回不去了。他自认为修行不够,他分明清楚自己的队友早已离世,留下的不过遗骸,却仍无法坐视他那些生死之交的遗体被这般糟蹋……尤其是被那些他们费尽心血保护的人们如此残忍对待。
他不记得自己逃了多久,只知道已经听不见有活人在说话了。阴影里,有妖兽在蠢蠢欲动,等他力竭而死,便可享用他的血躯。说实话,他已经很累了,已经没有必要再保护其他人,若是能就这么死去,或许能在九泉之下再见他们一面也说不定。这般想,死却是最好的解脱。
然而他听见眼前有些窸窸窣窣的动静,好像有人踉踉跄跄跪倒了在他的面前,试图用泉水滋润他那干裂的嘴唇。
“你还活着吗?还能不能走?”
模糊的视野里,是个头发有些白了的男人和他的妻小。他们背着灰扑扑的包袱,风尘仆仆的模样,大概是在赶路。男人自己也饥寒交迫,亦是许久没喝过水了,但仍是把自己的水和食物分给了他。
他觉得自己现在的状态应该实在可怕,衣裳上应当还沾有大片干了的血迹。不知是否是夜深,或是眼前的男人眼睛并不大好,竟是无人提起那些异样。
窸窸窣窣的动静更大了,却不是那个男人发出的,而是更漆黑的地方。
他觉得自己或许找的不是地方,求死也并不是时候。他将自己身上最后的法器交给男人,那是柄玉石做的短剑,剑身上已是有了豁口,他自己也记不得了,大约是被农具钝器硬生生砸出来的吧。
就和他的那些同门一样,短剑上寄托着他仅剩不多的那点力量,虽不强大,但至少能保男人一家无碍。随后,他便以身作饵,将那些潜伏的危险一并引走。月光打在他那伤横累累的凡人之躯上,虽然修为散去,但仍宛若仙人降世。
等他消耗尽最后一丝力气,从树上坠落时,他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巨大的树洞。身下的土地生长着密密麻麻的青苔,有些滑腻的触感,湿乎乎的,却莫名有些柔软。他将同门的遗物和自己的弟子令摆在一起,看了许久。大概是骨头也摔断了许多,他已经没有坐起来的力气。短剑亦给了旁人,现在他的身上仅有的从应山得到的东西,罗列下来竟不过如此。
“对不起,我没办法带你们回去了,”他感觉浑身的痛感连同五感似乎都在一点点消失,好像最后能动的只剩下几根手指,和勉强开合的眼皮,“连累你们,要和我一起埋在这个不见阳光的地方了。”
他的手指最后写下了什么,终于借地下的灵脉将掩生大阵最后一环补上。那是曾经的阵法天才所写下的绝笔,为了保护而存在的大阵中潜伏着的是他最后的愤怒,那股怒火成了生门中唯一的杀阵,竟是将周遭试图靠近蚕食他躯体的妖兽尽数绞杀了。
杀阵平息,青年陷入了他此生以来最后的沉睡中。
不知过了多久,有只弱小又无辜的仔羊,从青苔铺就路面的另一端而来。它的四肢仍是各走各的,用那七零八碎的步调靠近了生机断绝的青年。
然后用它的舌头,轻轻舔舐了上去。
……
望天醒来的时候,自己正举着短刀在一处空旷的地带。山泉水自山上而来,汇成狭窄的溪流,将山林与这处空地不着痕迹地区分开来。空地的尽头,生长着一棵巨大无比的老树,树干上生长的青苔开出了幼嫩的白花,花瓣上还带着新鲜的露珠。
这里不像他熟悉的那片山林,却又那么让人熟悉,空气中仍是那股子自由的气息。只是清爽的风中总似夹杂着些许的血腥味,拨动着他那不安的心弦。
脚下踩着的草地杂草丛生,其中开着些他也叫不出名的花儿,散发的香味令人头脑昏昏。在那溪流汇集之处,有片小小的池塘,那池塘太浅,甚至没不过一个孩子的膝盖。
有人的身影静静躺在里面,他的四肢都泡在冰冷的池水中,皮肤被泡得发白。他的身体挡去了望天大部分的视线,以至于他一直没发现仔羊正亲昵地依偎在他裸露的胸口上。
——那是孙樵夫的儿子。意识到这点,望天先是欣喜,孙樵夫的儿子还活着,他的胸口还有节奏地起伏着,这是在呼吸的证明。但当他看见仔羊支配着孙樵夫儿子的动作时,原本因欣喜而剧烈跳动的心脏,又一点点寒了下来。
仔羊的四肢仿佛生了根,关节以下几乎完全没入了孙家小子的胸膛——说是胸膛,或许更接近腹部。随着仔羊的前肢若有若无的晃动,好似连带着搅动着他的肺腑,孙樵夫的儿子脸上便露出些痛苦的神色,嘴里咛喃着什么支离破碎的呓语,额头渗出冷汗。
望天的靠近似乎没有影响到仔羊的食欲,虽然肉体凡胎的望天并不能看见,但确实好像有什么通过仔羊的四肢在被它摄入进体内。仔羊的四肢就像血管,此时剧烈的鼓动着,然而孙樵夫儿子的身体上看不见任何创口,好像他和仔羊生来便如此密不可分一般。
仔羊乖巧且温顺地看着望天,犹如初见那日一般,耐心地等待着他去主动触碰。
望天不可能让梦涡如愿,但强大的责任感促使他必须要救出孙家小子不可。
就在他踌躇间,那柄短刀再一次散发出令人烫手的热度,它好像不断吸引着什么。当它发烫,望天觉得周遭的空气都变得清新了起来。他将短刀抵在胸前,他不过是个孩子,对近身格斗没有太大的自信,然而此时望天仍然做出了个近似于防卫的姿势,小心地靠近了仔羊。
短刀离仔羊越近,望天越能感觉到仔羊仿佛被烫伤般,它想要逃走的意图越明显,挣扎的幅度越大,孙樵夫儿子的表情便越是痛苦。
他似乎突然醒了,然而在他清醒的那一瞬间,凄厉的喊叫声便整耳欲聋般袭来。那尖叫声已经超出了人体能达到的极限,孙家小子的嘴角溢出带着沫的鲜血,顺着他的脸颊流进衣领里。在那尖叫的魄力下,望天只觉得自己寸步难行,他全然没反应过来身后人的靠近。等他回过神来,自己举着刀的手已经被另一双伤痕累累的手所覆盖,温热的手心传递来的温度叫人安心。两个人的力气总算在那音浪中有了抵御的底气,梦涡无处可避,它的手脚都被擒在孙樵夫儿子的身体里,竟叫他们二人用那短刀将它的四肢齐根斩断!
梦涡和孙樵夫儿子分离的那一瞬间,后者停止了尖叫,却是踉跄着重新跌回池塘中,任由水从口鼻灌进胸腔。梦涡失去了四肢,却还是飘飘忽忽“站”了起来,它的形状已然不像仔羊了。被切断的地方没有生出新的手脚,亦没有血从那个生物的身体里滴落。原本长着尾巴的地方却是不断增生,最后生出了类似于猴掌的形状。那手尾撑着地,勉强支持着仔羊充气的身体。
望天一时只顾得上将孙樵夫儿子从水中捞起,而方才帮自己的人正是乐师陶。他不知是从何而来,脸上仍贴着许照冥留下的符咒,将他的五感封死。他的脚边,自家的猎犬正急得团团转,一个劲地扯着乐师陶的裤脚。封闭五感,被强化了听觉的乐师陶,在刚刚的尖叫声中似乎受伤颇重。他的嘴唇宛若死人一般白,耳孔更是血流不止,就算猎犬一直在他耳边狂吠,他也像什么都听不见般,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看不见,听不着,他就像具仍还活着的尸体,站在池塘的中央,像一头毫无戒备的猎物。梦涡将猴掌伸向了乐师陶,他的巢,他的食物。
然而下一秒,猴掌连同梦涡都被一剑洞穿,乐师陶毫发无损,只在那股凛然剑气下被吹散了额边的碎发。梦涡死前仍然是那副乖巧且温顺的嘴脸,只是在一点点化为灰烬的最后,它似乎睁开了眼睛,那只眼睛浑浊且晦暗,它就那么静静等待着消散。
不知道最后仔羊正在做着怎样的梦。
望天将孙家小子拖上岸边,他踉跄着又要朝乐师陶的方向走去,却总是被池塘底的泥潭绊住腿脚。当他总算走到了乐师陶的身前,乐师陶却仍是无所察觉,望天看向了手里的短刀,下定决心,将短刀轻轻对上了乐师陶的眼睛。
“……小天?”
乐师陶轻声道。
“嗯,已经结束了,陶陶。”
望天应道,却忘了他已听不到回应。然后用刀斩断了那道封印五感的符咒。层层符咒下,露出了乐师陶恐惧且无措的双眼。他的瞳孔中清晰地映着水色,闪烁着明亮的光。
乐师陶抬手抱住了望天的肩膀,他或许正在哭,但望天的衣服早被池水打湿,感觉不到了。看着他的肩膀颤抖着,望天也用力抱了回去,轻轻拍着他的背以作安慰。
那柄短刀总算完成了它所有的使命,在望天的手里碎裂成数段,雕刻着图案的玉块和碎成渣的刀身一同掉进池塘的泥泞。
许照冥收回剑,确定梦涡不会再再生后,随着身后的踩在草丛上的脚步声回头。
池莲手里拿着的是数枚陈旧的弟子令,几年间,青苔爬上了那刻着人名的遗物,上头的字已是模糊不可分辨。那些令牌大多是完好的,唯有一枚损坏的格外严重,好像原来的主人并不希望被认出来一般,将自己的那块硬生生捏不成原型了。
池莲从那泥泞中找到了最后的玉段,虽然掉进泥潭里,但池水洗去了上头沾染的血污和泥泞,露出玉石本身。温润的玉质仍纯净如初,好似一切都没有发生变化。
“这下都可以回去了。”
许照冥发自内心地笑了。
同时,随着最后一处阵眼被破除,覆盖此处整整十年的掩生大阵也逐渐瓦解。
人类的生命总是顽强,往后亦要靠他们自己走出一条生路,就像一直以来他们做的那样。
——感谢您的观看,至此本篇已完——
前情提要:https://elfartworld.com/works/9745399/
出场人物介绍:
周胜蓝:问剑弟子,最近寻回了失散多年的挚友。
忘忧:被找回的丹心弟子,但记忆全失,身份也有些可疑。
陆天问:司书弟子,周胜蓝的老友,在本文中是工具人。因为是背景板也没给上户口。
破天荒:问剑弟子,在文中担任法海一职。
周胜蓝大剌剌地踏进机关室的门,熟门熟路地绕开堆在一起的杂物,免得碰到什么不该碰的东西。陆天问像是背后长了眼睛,听见脚步声便问:“东西给带来了吗?”
“带来了带来了。”周胜蓝扔给他一个怪模怪样的铁器。这东西她说不上来是做什么用的,但陆天问要的东西多半如此。陆天问道了声谢,又问:“捆仙索用得如何?”
“实在好用!多亏捆仙索,不然我没法把丽梅带回来。”周胜蓝答道。她磨破嘴皮也没能说服忘忧跟她回应山,只好一根捆仙索将人捆起来带走。人是带回来了,可忘忧记忆全失,实在让人苦恼。
她忍不住对着陆天问大吐苦水,但对方只是默默做着手中活计,时不时地点点头表示在听。陆天问与周胜蓝算是老友,比起与人打交道,他更乐意去研究风雨雷电,对待同门的态度也一向不太热络。
若是换个心明眼亮的,早就能看出陆天问的心不在焉,但周胜蓝浑然不觉,直到说得口干舌燥才停下。
“……也不知丽梅何时才能恢复记忆,不过好歹是心里一块大石落地,好不畅快!若是再叫我遇上那心魔,保证打得它满地找牙!”
陆天问微微偏了偏头,似乎是有了兴趣:“这么说,你是打算参与今年的入门试炼了?”
“那是自然!”
应山大开山门选拔弟子,入门试炼必不可少。不仅是初入门的弟子可以参加,其余的弟子们也可以借此检验道心是否稳固。周胜蓝已有数年未参与入门试炼,自从三年前她几乎迷失在命宫境中,便知自己难以与心魔抗衡。可今时不同往日,她既已寻回宋丽梅,哪里还有害怕心魔的道理?
陆天问淡淡看了她一眼:“那便祝你顺利。还有,我这边还有一物,你得空做好,我自己去取。”
周胜蓝看也不看,拿过陆天问的图纸便走。左右又是她看不懂的怪东西,问也无用!
隔日便是应山的入门仪式,如往年一般气派。应山弟子们列队齐整,气度不凡,长老们打开仙门,金光大盛,等候诸位弟子前往试炼。周胜蓝飞身上剑,负手而立,气定神闲没入金光之中。待到视野清晰之时,一幅空白画卷已在她面前展开,上书一行大字:
“降妖除磨,保护大家!”
八岁的周胜蓝,尚未学会妖魔的“魔”字怎么写,就被送上了应山。虽说已经下了决心,要以除魔卫道为己任,可到了这命宫境,忍不住疑心自己是被父母抛下,坐在地上哇哇大哭,好在有位好心师姐相助,她得以破除心魔,擦干眼泪写下这八个字的豪言壮语,自此已有二十二年。
而今周胜蓝看着这行字,不禁一笑。她自认这些年来修行未尝懈怠,对得起自己当初写下的字。不过今日的重头戏还在后面,她收拾好心情,严阵以待。
雾气渐显,再睁眼已是熟悉的景色:黑色妖兽露出森森牙齿,斑驳血迹还清晰可见。宋丽梅倒在一旁,已然是气息奄奄,不久于人世。这副场景周胜蓝熟悉得很,从十五岁那年开始,她的命宫境就是这副模样。周胜蓝翻身下剑,提剑便刺,一人一兽登时缠斗在一起。若是从前,周胜蓝即便知道一切皆为虚幻,却仍然忍不住地焦躁不安,然而今日她心境澄明,一招一式行云流水,很快便一剑刺穿了那妖兽的颈部,接着又生生将其头颅斩了下来!
银光闪过,黑雾喷涌,妖兽的头颅轱碌碌滚到地上,周胜蓝内心畅快不已,又连忙去查看一旁的宋丽梅的情况。她的手刚一挨到宋丽梅的身子,便知大事不妙,为时已晚,眼前的宋丽梅已然是一具冰冷的遗体。
悲伤涌上心头,但周胜蓝牢记眼前皆为虚幻,丽梅已被自己寻回,此处种种,皆是心魔作祟罢了——这样想着,她正欲站起身来,却见一旁的妖兽化为一团黑雾,飞速地将宋丽梅整个包裹起来。周胜蓝提剑去砍,然而即便砍散黑雾,下一瞬间便又聚拢。周胜蓝心中暗道不妙,提剑严阵以待,却见那黑雾渐渐没入了宋丽梅体内,再无踪影。
而宋丽梅缓缓睁开了眼睛,对着周胜蓝笑了。
十五岁的宋丽梅,用周胜蓝最熟悉的声音开口说道:
“小师姐,你来救我啦?”
忘忧近几日烦心事诸多。先是被周胜蓝绑进应山,又遭遇应山大变,那大妖突然现身,袭击了化妖池,又引得妖兽横行,天地异变,还好有掌门出手,护住了应山,方才有今日的平安无事。
忘忧虽空有应山弟子的名头,可却未曾学过应山的术法,好在医治伤患的本事还是有的,如今狼烟四起,也能尽一份力。可最近弟子们对她的态度颇有几分古怪,有好几次,她似乎听见几个弟子窃窃私语,但只要她一走近,几人便面露尴尬地岔开了话题。忘忧不明所以,倒也没太放在心上,不过周胜蓝还是一如既往地让她心烦。
她以图个清净的由头找了单独的住处,为的就是少和周胜蓝有什么瓜葛,但仍然拦不住周胜蓝隔三差五找上门来,胡乱地大献殷勤。
前几日周胜蓝不知从哪寻到了两枚卦符,非要硬塞给忘忧一枚,说是只要她有危险,自己就能立刻感应到。忘忧再三推脱,还是没拗得过周胜蓝。后来她才知道,这东西的名字叫良缘卦,险些当场把东西扔出去。
念在周胜蓝一片心意,忘忧最终还是没扔掉那枚良缘卦,只是放在了自己的木匣里,不曾随身带着。
这一日,她打算动身去丹心院,刚到门口却迎面遇上一位女子。来人腰间佩剑,面色不善,伸手便将忘忧拦下:“你便是宋丽梅?”
“我是忘忧,不是什么宋丽梅。”忘忧皱眉答道。自打她来到应山,每逢有人称她宋丽梅,她便要再说一次自己的名字。
“好,忘忧,我找的就是你。劳驾与我移步后山,我有要事与你相商。”女子摆出一副不容拒绝的态度,忘忧心中疑惑,便假借自己忘记拿包裹,回房带了那枚良缘卦在身上,以防万一。
一路无话,两人走进通往后山的小路,人声远去,周围只听得见鸟鸣。走入一片开阔地,女子停下脚步,在忘忧身前几步处站定。
“姑娘今日叫我前来,到底所为何事?”忘忧率先问道。她直觉对方来者不善,但却猜不透究竟为何。
“据说,你便是在十五年前,被妖兽掳走的宋丽梅。”女子冷冷说道。
“我并非宋丽梅,只是有人错认了。”
“既然不是宋丽梅,为何留在应山派?”女子厉声喝道。忘忧隐隐觉得不妙,向后退了一步,眼前的女子便不动声色地上前一步,又问道:“据说你自灾岁那年便记忆全失,想不起自己是谁,果真如此吗?”
“……是,十五岁以前的事,我都记不起来了。”师父曾说,她是因为一场高烧,失去了先前的所有记忆,但这一切与眼前的女子何干?
见忘忧承认,女子冷笑道:“若你所言非虚,那便是大大的可疑,我今日必除了你这妖孽!”说罢女子手腕一翻,腰间长剑霎时出窍,直冲忘忧面门而来!
忘忧惊慌后退,却听得耳边风声呼啸,眼前白光一闪,紧接着便是剑刃相交声,两个影子战作一团。她惊魂未定地打量眼前蓝色的身影:不出所料,果然是周胜蓝!
“破天荒,你要做什么!”
“让开!如今妖魔扮作人形祸乱四方,应山派不得有失,岂容得下这一身份不明之人?”
“她不是什么身份不明之人,她是宋丽梅!”
周胜蓝与破天荒一时难分伯仲,彼此都没有要停手的意思,好在赶来的应山弟子们赶快把两人拉开。周胜蓝怒气冲冲,要破天荒把事情解释清楚,破天荒抱臂道:“妖物可借人肉体化形,借人心智所生,据各村县记载,失踪数年却又复现之人,且记忆暧昧不明者,多半是借尸还魂的人形妖!”
周胜蓝死死护着宋丽梅,大声辩解道:“若她是妖物,当日我带她进山,法阵怎会没有异常?”
“那日的法阵本就多有误报,你怎知她来时就没有?”
“探查妖气的符咒对丽梅也没反应!”
“司书紧急赶制的符咒,又能有多灵验?”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惹得周围的弟子们也议论纷纷,好像谁都有点道理,但又分不清谁对谁错。
“你若执意护着她,会给应山降下大灾祸!”破天荒怒道。
“不会!”周胜蓝朗声道,“我会守着她,盯着她!若有一日她为祸人间,我会亲自动手杀了她,然后自刎谢罪!”
此话一出,在场弟子纷纷倒抽一口凉气。忘忧内心震动,久久不能言语。若事情真像破天荒所说,她难道真是妖物借尸还魂?她失忆之时与宋丽梅失踪相差不过半月,而宋丽梅又的确是被妖兽掳走……仅仅是这些就足够让她心神震荡,周胜蓝那番“杀了她再自刎”的话又让她惊骇不已:在她看来,周胜蓝与陌生人无异,可在周胜蓝眼里,自己竟是足够以性命相护之人吗?
不对,值得周胜蓝以命相博的人不是她忘忧,而是宋丽梅。
“……既然你执意如此,那便好好盯着,别被我发现半点端倪!”破天荒冷笑道。
周胜蓝咬牙鞠了一躬:“多谢成全!”说罢带着忘忧快步离去,身后早已被冷汗浸透。她不敢想,要是没有那枚良缘卦,自己今日回来,是否就只能看到宋丽梅的尸身?
想到这里,她双膝一软,竟是跪了下去。
“周姑娘,你……”
忘忧赶忙上前搀扶,周胜蓝紧紧抱住她,浑身都在发抖:
“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忘忧本该说些安慰她的话,可她自己早就因为今日之事心烦意乱,最终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应山派已不能久留。若是今日之事传到无望长老耳朵里,周胜蓝真怕他会提着剑冲过来把忘忧切成八块。
“你快点收拾行李,我们下山去。”
“周姑娘,你要带我去哪儿?”
“去刘家村。”
周胜蓝指了个大概的方向。她刚从刘家村回来,那儿的妖兽不足为惧,但村民沾染了浊气,须得找位大夫瞧上一瞧。医者仁心,忘忧也并不推辞,匆匆收拾了行李便上了周胜蓝的剑。
御剑飞行自然比走路快上许多,可忘忧却未学过此术法。周胜蓝说改日教她,忘忧心中暗想,也不知改日是何日,但面上未多言语。
等到了刘家村,周胜蓝召集生了病的村民前来诊治,村民们自是千恩万谢,一口一个仙人叫个不停。周胜蓝摆手:“不必多礼,这都是我们应山弟子应该做的。”
应付这种场合,她也算是得心应手。沾染浊气的村民们逐个来找忘忧诊治,周胜蓝负责将来看热闹的村民赶开,留给忘忧一片清净。刘家村受灾并不严重,太阳还未落山,忘忧的诊室就空闲下来。
“村长,还有需要诊治的村民吗?”周胜蓝问道。
“还有一人,病得厉害,下不了床,”说到这里,村长面露难色,“要是旁人,大家搭把手,抬也就抬过来了,但自打他妻子害病,邻居们也开始身体抱恙,村民们没一个乐意去他家里的。”
“还有此事?快带我去看看!”周胜蓝听罢顿感不妙,这几日她来往于村落和应山之间,听说了不少“天煞郎”之事。妖物化作人形混迹人间,浊气侵蚀周遭,村民却浑然不知,只当是被不祥之人克死,因此便有了“天煞郎”一说。若此事如周胜蓝所想,这村里必然潜藏着人形妖!
她与忘忧两人赶到那村民家中,只见一男子躺在床上,看样子病得厉害。忘忧为其诊脉,对周胜蓝点了点头:“的确是浊气入体,且毒性已深,即便驱逐了浊气也会落下病根,须得花上些时日好好调养。”
周胜蓝笑道:“有得治总比没得治好。”眼看榻上那人要起身谢恩,周胜蓝赶忙拦住了他:“不必多礼,我还有事要问你呢。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男子立即露出悲伤之色:“妻子离世,家中只有女儿。”
“她现在在哪儿?”周胜蓝立刻问道。
“您问这个做什么?”男子似乎察觉到周胜蓝话语中的急切,有些警觉。
“你女儿可曾走失过?”
“不,不曾!”
男人否认得太快,就连周胜蓝也能看出他在说谎。似乎察觉到自己失言,他挣扎着起身,抓住周胜蓝的胳膊苦苦哀求道:“我女儿怎么可能是妖呢?她还那么小,从来没害过什么人啊!”
“可你病得这么厉害,如今村里也有诸多村民染病……”
“那,那也与我女儿无关啊!求求你了,仙人,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她才五岁,绝不是害人的妖怪啊!”
周胜蓝面露难色:“还是让我先见见你女儿吧,是人是妖我自会分辨。她现在在哪儿?”
男人摇头,闭口不提女儿下落,只一味说着哀求的话。周胜蓝和忘忧对视一眼,在屋子里寻找起来,很快便在厨房寻到那五岁女童。
女孩眨着一双大眼睛,愣愣地看着两人。周胜蓝的确感应到她身上妖气,可染病的村民身上也有妖气,一时竟是分辨不清。
怎么办?要将这小女孩砍杀吗?这些年来周胜蓝对付了不少妖物,可杀人的事却做得不多,最多只是悄悄砍过几个欺男霸女的恶霸,可从没对这么小的孩子下过手啊!
只一愣神的工夫,女孩就跌跌撞撞地从两人身旁跑过,周胜蓝赶紧去追,却只见女孩紧紧攥着父亲的手:“爸爸,我怕……”
“好了,不怕不怕,爸爸在呢……”
男人柔声安抚女儿,又看向周胜蓝,眼中尽是悲怆:“仙人,你若疑心小女是妖,那我们便离开此地,寻一处人迹罕至之地生活,若她害人,也只害我一人。”
周胜蓝立刻道:“不可!若你身死,谁能保证她不会继续害人?”
男人闻言,剧烈地咳嗽了起来,好半天才平复。他喘着粗气,死死将女儿护在怀中:“……若今日换了你的至亲骨肉,手足兄弟,你又当如何?”
周胜蓝下意识地看向忘忧,竟是一个字也说不出。
“你不是宋丽梅!真正的丽梅已经被我找回来了,我再也不会怕你了!”
周胜蓝提剑便刺,长剑没入“丽梅”胸口,却不见血迹。宋丽梅笑着握住剑刃,俯身贴近她耳侧,轻声说道:“是吗?可你找回来的那个人,真的就是你的‘丽梅’吗?”
不,不,不!
她怎么能不是丽梅?就算是相貌变了,声音变了,可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就算她不再用温柔的眼神看她,不再用亲昵的语气说话,那也是丽梅,那就是丽梅!
“可她从未说过自己是丽梅,不是吗?”
对啊,她……从来都只说自己是忘忧。
心魔窃笑起来,笑周胜蓝的自欺欺人。在那刺耳无比的笑声之中,周胜蓝几乎坠入深渊。何其幸运,也何其不幸,大妖的到来强行打断了命宫境的试炼,周胜蓝才得以从中脱身。
……易地而处,周胜蓝明知忘忧身份可疑,却不管不顾拔剑相护,若忘忧是妖,她便也是帮凶!她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除魔卫道的应山弟子,有什么脸面说自己要保护大家?
她看向眼前的男子,苦笑着开了口:“你们……”
话未落地,只见寒芒一闪,女孩头颅应声而落,却不见血迹,只有一团黑雾包裹,诡异至极。在场几人皆是大惊,周胜蓝立刻掏出腰间葫芦,将妖物收入其中,只留床榻上的男人茫然地看向自己空无一物的手,随后便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号哭。
周胜蓝心里不是滋味,几乎是落荒而逃。陆天问抱着双臂站在门口,似乎是一直在等她出来。
“你怎么来了?”周胜蓝问道。
“听说此地有‘天煞郎’的传闻,我是来打探消息的。”
周胜蓝点了点头,又说:“刚刚……多谢了。”
若非陆天问出手,她大概真会放这对父女离开。
“不必客气。”陆天问答得简短,看起来也并无谴责周胜蓝过于仁慈的意思。但周胜蓝反而有话要问他:“可我们要是杀错了怎么办?如果那不是妖物,只是一个小女孩,我们要怎么办?”
“那就是杀错了。找出真的妖物,回门派领罚便是。”
“可那是一条人命啊!”
眼看周胜蓝满脸不可置信,陆天问反而笑了出来:“为此事如此烦心,说明你是个正人君子,而我却不是。若我觉得是妖,我便杀了,不然在这世道之下,如何护得住自己,如何护得住旁人?”
说罢,陆天问摆摆手,迈步朝村子另一头走去了。
当晚,刘家村设宴款待仙人,可周胜蓝经历白天那一遭,颇有些食不知味。她与忘忧留宿于村民家中,眼看着夜已深了,周胜蓝却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索性起身上了屋顶。
头顶一轮弯月,月光轻柔,掩不住点点星辉。儿时她常与宋丽梅一同在后山赏月,数天上的星星,如今忘忧安睡于房中,她却不好搅人清梦,只是独酌赏月,勉强算有一番滋味。
半坛酒下肚,周胜蓝微微有些醉了。听见熟悉的脚步声,她头也没抬,喜笑颜开道:“丽梅,你来啦?”
忘忧在周胜蓝身旁坐下,已懒得纠正她的称呼,只说了句喝酒伤身。
“不打紧,我许久没喝过了,偶尔为之,不碍事,不碍事。”
周胜蓝摇头晃脑,顺势往忘忧肩头一靠,“丽梅,丽梅……”
忘忧没理她,周胜蓝却不肯停下,只一味地叫着丽梅。直到被这酒鬼叫得烦了,忘忧才冷冷道:
“何事?”
“没事。只是从前我无论怎么叫你,都听不见半分回音……如今算是有了,嘿嘿。”
忘忧又是一阵心烦。周胜蓝睡不着,难道她就睡得着觉吗?今日见了那小女孩,才知人形妖物几乎与人无异,就连应山弟子也难以分辨。虽说忘忧与师父一同生活多年,从未发觉师父的身体有什么异状,因此她理应不是妖物化人,可谁又能说得准?
而周胜蓝一片真心,又让她受之有愧。思及此,忘忧轻推周胜蓝,问道:“可若我不是丽梅,而是那吃人害人的妖兽,你为我以死谢罪,当真值得?”
“不准胡说!你怎么可能是那吃人的妖兽!”周胜蓝立刻抓住她的手,目光灼灼,像要把她烧出一个窟窿,“若你真是,那丽梅想必也不在世上,我也不必独活。”
忘忧闻言,内心一阵翻涌:“丽梅于你,竟是如此重要吗?”
“……正是如此。所以别再离开我,求你……”周胜蓝伏在忘忧膝上,醉眼朦胧,转过脸来冲着忘忧傻笑,“丽梅,丽梅,丽梅……”
“叫我忘忧。”忘忧没好气地说。
周胜蓝怔愣片刻,立刻笑着改了口:“忘忧,忘忧……别离开我。”
忘忧只觉内心苦涩,心中平生第一次有了如此念头:若她真是宋丽梅,那该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