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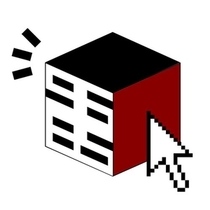


嗨呀最近沉迷游戏无心企划……放我去做光之跑腿!我要拯救艾欧泽亚!
※全是OOC没品笑话的紧急打卡
※真的都是OOC,捉来借用的孩子性格都崩坏了(。
※弥生的性格基本变成毒舌吐槽役,温柔内敛好女孩之类,不存在的
※一笔启上的场合
弥生:小一,我感觉我们俩主线里说话太客气了,全是敬语
一笔:欸!是这样吗!(慌张脸红)不,不好意思弥生小姐!
弥生:你看,太客气了!这样的话攻略速度太慢了!
一笔:攻、攻略?!?!那,那是什么……(脸红)
弥生:是的,我亲妈说「希望这两个女孩子间飘散着淡淡的百合香气」,但是我们主线里都在客客气气讲话,一点都不够亲密!!!!!!
一笔:欸——!!!!!那该怎么办!?
弥生:我觉得事不宜迟我们立刻拉近关系吧!从称呼开始!
一笔:好,好的,该怎么做好呢?
弥生:亲爱的。
一笔:?!?!?!?!?!?!?!?
弥生:达令。
一笔:!!!!!!!!!!!!!
弥生:honey~
“欸——————!!!!!!!!!!!!!”一笔启上大混乱
弥生:这个人还真是可爱(括弧笑)
※如果黑崎在第二章开篇时也遇到了弥生的话
眼下情况变得十分紧张。
黑崎、七原葵、弥生和廖先生一起抱着盆栽走在前往纪斗家的路上。
这四位中,廖先生对先前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此刻,大家维持着一种一触即发的脆弱和平氛围。
黑崎紧张地思索着要如何从眼下的状况脱离。
七原葵陷入惊讶恐慌的情绪中,不知该如何面对黑崎。
廖先生和弥生抱着盆栽默默走着。
廖先生:说起来,今天没看到桃姬呢,好稀奇
弥生:她狗带了
黑崎:……
七原葵:……
廖先生大惊:什么!桃姬小姐怎么死了?
弥生:嗯,被杀了。
黑崎:…………
七原葵:…………
廖先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桃姬被谁杀了?!
弥生扯起黑崎的衣袖,指了指她:就是她哟
黑崎:……………………
七原葵:……………………
廖先生:……………………欸?!
※如果当初黑崎阵营中加入了弥生的话
黑崎:那么,弥生有什么能力呀?
弥生:没啥大本领
黑崎:……
黑崎:没有关系,能力都是有用的,只看你怎么用
弥生:请随便递只手递给我
黑崎递过一只手,弥生轻轻地握住了它
弥生:哇——
黑崎:!怎么?!
弥生:你脑子里想得好复杂
黑崎:……
黑崎:然后呢,没了么?
弥生:没了。
黑崎:…………
黑崎:你好好想想,如果把这份力量作为武器的话能怎么用
弥生:……哦!我知道了!
黑崎:什么!
弥生:我知道你心理的弱点了。
黑崎:……然后呢
弥生:我知道怎么击垮你的心理防线
黑崎:没了么?
弥生:没了。
※纪斗的场合
弥生:master,你为什么先前急匆匆离开徒然堂了呢?
纪斗:啊……当时突然有人围上来,而我本身心绪也不太稳定……所以……
弥生:我之后等了好久
纪斗:对,对不起……!
弥生:等了好久
纪斗:万、万分抱歉!
弥生:等了好久好久好久
纪斗:太,太对不住了……!
弥生:真的好久
纪斗只想狗带了。
※再见了,二设弥生
弥生:桃姬姐姐好
桃姬:你好呀
弥生:桃姬姐姐,请问你对黑崎有什么想说的吗?
桃姬:我想打爆黑崎的狗头
弥生:好的
弥生拨通黑崎的电话:黑崎,桃姬说她想打爆你的狗头
黑崎:……
弥生:嗯,就是这样。那我先挂了喔。
弥生:桃姬姐姐,既然看到你,就说明我差不多该走了吧
桃姬:是的,毕竟这个水卡字数已经差不多了,和我一起去天国吧
弥生:嗨呀,我感觉自己还没毒舌S够
桃姬:我狗带了好久,全都在回忆杀,好苦涩的
弥生:你也是不容易
桃姬:走吧,我们一起回去吃便当,今天晚上好像有烤黑崎肉
弥生:好喔好喔
完(。




“我出去转转,”我在经过客厅时,向这不苟言笑的一家之主道过早安,随即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会在天黑之前回来的。”
意料之中的,他同意了,说到底他也没有什么理由拒绝。不知到底是忙于准备接待好友,还是真的毫不在意,他就连路上小心之类的客套话也没有。但是不得不说,这一点确实让我很高兴,要知道,对于我来说,比起当面的指责而言,虚伪的安慰更让我感到不满。
于是我也很乐于友情提醒他一下:
“佐久间先生已经快到桥上了,”我顿了一下,找出了当中我认为最重要想法“他似乎表示想和您再下几局棋。*”
他点了点头示意他知道了。
我有意让他觉得自己是擅长知道一定距离里发生的事,这总比假装自己毫无能力要简单多了,也要保险多了。而我也十分确定他到现在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的实际本领。
然后我头也不回地踏向门外,并有幸见到了那位佐久间先生本人,尽管在他看来我或许不知何处带起的一阵风。
正如我所说的,我的新任主人——同时也是我的结缘者,十文字政臣,正要会友。你们也许会觉得,即便只是遵循最普通的礼仪,我也是没有理由离开的。尽管对方只是个看不到神异之事的普通人,我还是可以留下来暗地里帮些忙之类的。不过要知道,我既不打算被认成什么座敷童子,也不是为了协助我现在的主人什么事而与他结缘的。我有我自己要做的事,这件事与我的前主人息息相关。
而我对我的前主人一无所知,恰如我今天外出的收获。
早在徒然堂时,我就已经多次尝试寻找线索了。那些决策缘何失误?那场战争又为何落败?或许这就是盘桓在我心中的念。我向来是行动派的,日复一日的等待并不适合我。但是对当时的一切目不能见,耳不能听的我来说,现在的分析一切都只是建立在推测之上的。
倘若说作出结缘这个决定时,我或多或少地寄希望于位出身行伍的这位先生能对我的搜寻有所帮助,而身为军人这点本身又成为我仰慕他的原因,那么之后知道了实情的我就和遭受了诈骗没有什么区别。
简单地来说,他不过是个医生罢了。
不论棋局胜负,有些人就是能成为操纵命运的棋手,能成为统率军队的将领;而有些人则迟迟把握不了命运,就像是棋盘上受人指使的棋子,终其一生不过是一个无名之兵。而军医呢?恐怕与那些真正上阵打仗的更要差上十万八千里了吧。
今天去过的地方,是这附近最后几个与我记忆中前主人的房子大小相当的建筑了,但是话又说回来,没有谁能保证我过去的旧主就住在这座城市,也没有谁可以告知我那些残留的遗迹是否随着太阳的起落而一块块崩坏,最终成了一片面目全非的土地。在我这短短几个月的探索中,线索未曾出现就已经消失。
托这些地方的“福”,我可以比原定计划更早一点回去,因而在回去的路上又碰到了作客归来的那位先生就连擦肩而过的位置都不差多少。佐久间先生就像来时一样离开,我就像离开时一样来,。自从获得了人形,能够看清事物,我就时常感受到这种时空交错般的微妙感。
要是我想象着过去的房子走,会不会走到我想找的那栋房子里呢?我不禁生出了这样的想法,但这时,我现在的住所已经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我再一次路过客厅时,棋盘还没有被收拾好,而十文字先生看上去心情不差。
下棋赢了的缘故。我了解到。
或许就是借着这不错的心情吧,他很难得地问我会不会下棋。
“我是说,国际象棋。”他指了指那堆形状各异的棋子,看上去很认真地问道。
他这样问,是因为觉得我可能会的是将棋或者围棋之类的吧。不过实际上,我什么棋也不会下。在我眼里下棋不过就是一种军事模拟,参与者在处置可重复利用的棋子时深思熟虑,转过头来,却在安排不可重复利用的棋子时意气用事,这早已成为常事了。
然而对于一个能了解别人心思的存在来说,这类斗智游戏着实缺乏吸引力,这也是我至今什么棋也不会下的原因。
不过本着维护一下关系的目的,我还是一口答应了下来。
简单了解了各个棋子的走法后,我的第一场棋局就这么开始了,虽然是第一场,但是我志在必得。其实我并没有看上去那样对下棋不了解,尤其是当他还与别人下过几次的情况下。要知道,人们思想的的声音对我来说可是吵得很,而百无聊赖的我也有好好听过那些思维方式。同时,我也懂得怎么打断别人的思路。
“请问,象是可以这么走的么?”我佯装不懂,小心翼翼地问道“那这边的车呢?”
在表达了我自己记性不好的歉意和对他解释的谢意之后,我假装试探着走了我原本就想走的棋子,就像我表现的那样真挚而无害。
而当“我的对手”在思考着自己的下一步并作出决定时,我则会假装惊讶得表示:“原来王能这么走?!”而这位一脸严肃的军医也因此被打断了两三次思路。
大家或许会觉得我即使获胜也胜之不武,然而要知道,战场上的阴谋暗算也不计其数,而我并不觉得计谋之间有着高低贵贱之分,就像你并不能断言男低音就是没有女高音引人入胜那样。
于是我理所当然地将我的主人逼入了绝境,或者我觉得我是将他逼入了绝境,因为我一直在见招拆招,而他正准备下一步险棋:
“下一步应该下在这里,”他告诉他自己,同时也告诉了我“不会被发现的。”
但是毫无疑问我已经发现了,所以胜利终究归于我。
“非常感谢您的教导。因为我一直要问东问西,所以没能发挥出真实水平吧?”在他宣布我的胜利后,我不失时机地表达了感谢。经验告诉我,恰到好处的谦虚与谢意总能给人好感。
“作为初学者,你的表现确实不错。”他如实地说出了他心里的想法。
但是整理着棋盘的我,却总觉得有着什么东西被掩埋了下去,但愿这只是我的多心。
*玩了《阴阳师》里的梗【这么一想,被扫地出门,只好住桥洞的空太郎也不错的样子【我根本不是亲妈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