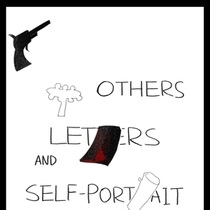
※我有一个 美丽的愿望 就是长大以后三更(
然,然后做不到…!!!本想一口气写完三篇一起发上来!是我想太多!不该相信自己的手速!先贴一篇保命打卡了!(跑
※ 擅自捉了些角色过来,若有性格拿捏不到位或是时间线bug都以亲妈的安排为准!
对大部分徒然堂的九十九来说,每日接触得最多的人类是芜木虚方小姐。她总是挂着温柔的笑脸在一楼的咖啡屋工作。闭店后有空闲的话,会来和我们聊天。大家的往事,只要肯说出口的,无论开心、热烈或是遗憾、感伤,她皆以同样庄重、诚恳的姿态来倾听,是十分亲切、美丽的人。化形后我对人类最早接触的印象也源自她。
清净屋是除开虚方小姐外大家相对熟悉的一群人类。每逢有清净屋来店里交接工作,我都喜欢和小一凑过去瞧瞧热闹,大家也很欢迎清净屋们的到来。毕竟平日里外人都看不见我们,能和见得着自己的人类说说话总是有趣的。清净屋们的性格也各有不同,我非常喜欢去看看他们。
浅原一真先生是位僧人。他的话很少,不过待人很温和,我们有什么疑问他都会尽可能回答。店长小姐提醒我们不要对浅原先生做失礼的事。在日本,人人对僧侣都怀着敬重之心,况且一心向佛、专注修行是很辛苦的精神锻炼,大家也就尽可能不去扰他清净。我很喜欢在浅原先生来店里的时候,远远地找个地方望着他——浅原先生宁静的面相、波澜不惊的神态所透露出的气质我很喜欢。总觉得看着这个人浮躁的情绪就能平息下来,这是否就是所谓的出家人参禅所得的气度呢?
相较之下,京桥先生算是和我们熟络多了,大家都喜欢亲切地唤他作阿式。阿式没什么架子,还喜欢说些俏皮话逗大家开心,三两下就跟我们打成一片。阿式是初来东京的大阪人,听说他刚到车站就失了钱包,机缘下来徒然堂做清净屋。我们都笑话阿式冒失,他也就顺着哈哈笑着承认,是个非常豁达、经得起玩笑话的好人。听阿式说,他本是一位刀匠,然而眼下废刀令已出,原本立志要投身锻冶工艺的他失了方向,才决定来东京寻找答案。我很喜欢听阿式用开玩笑的语气讲自己讨生活的不易、赚钱好难、填饱肚子是大事之类的事情,听年轻的人类说说自己的烦恼和打算非常有趣。有时想起阿式先生,我会好奇为什么这个人如此开朗呢?明明奔波生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真如他所表现出的那样豁达吗?在离开徒然堂后,偶尔我会挂记起他,不知总是笑着的阿式能不能得偿所愿求得安身立命的方法呢?
在被小一发觉我喜爱去看清净屋们后,她曾经暖暖地笑着评价道:“弥生小姐真的很喜欢人类呢。”起初我很惊讶收到如此评价。因为凭心而论,我对人并没有特意想去交好的心意,也不会因为与人类交谈而多一分快乐,只是很喜欢观察他们的举动——如此也可被归纳为喜欢人类吗?或许感兴趣也是“喜欢”的一种吧。
因为本体是日记本的缘故,七原葵小姐是众多清净屋中和我关系最亲密的一位。葵小姐是位热情、开朗的女学生。今年春分造化日后,习惯写日记的她听闻今次有日记本的付丧神化形,特意找到我打招呼,我俩言投意和,她也愿意对我说说体己话。
“和弥生讲话,常常给我一种在和自己的日记聊天的错觉呢。”
“是吗?”
“可能是因为弥生总给我一种‘什么都可以包容、什么都能原谅’的气场吧……想起自己在日记里倒苦水做自我检讨的时候,我那本一定也像你这样听着我发牢骚。”
七原小姐身上那股热烈、新鲜的生命活力我非常喜欢,虽然她尚还青涩,但青春的健康感和向上的劲头非常迷人。我的原主人在少女时期也如她这般散发着生命之美,看着葵小姐总有种昨日重现之感。
清净屋与普通客人不同之处在于,清净屋强大的灵力可以令他们拥有多个付丧神。桃姬和黑崎二位九十九就同与葵小姐结缘,由于葵常常来徒然堂做客,大家也都与二位付丧神熟起来。
听葵小姐说,自幼时起桃姬小姐便伴随她长大,多年来的朝夕陪伴,两人的感情十分深厚,我也很欣赏桃姬姐姐淡然自若的处世态度。在我的印象里,桃姬小姐的话不多,总是用含着充满慈爱的温柔眼神注视着葵和我们。每次葵小姐和我分享上学的趣事、自己平日闹的糊涂一类琐事时,我都注意到桃姬小姐总会捻袖轻笑——就像父母在听孩子讲笑话那样。作为一把存在了许多年、远洋而来的桃木梳,桃姬小姐见识过许多事物,只要有空,她都愿意为我们娓娓道来那些新奇神秘的故事。
与桃姬不太一样,黑崎小姐是个冷峻、干练的付丧神,是眼下和葵一起并肩战斗完成清净屋工作的强大九十九。大家对外面的世界,尤其是清净屋、狂百器一类的话题非常热衷,每次像黑崎小姐这样直面狂百器战斗的付丧神都会被我们围着东问西问。黑崎小姐也总是亲切地向大家回答关于狂百器的话题。
每次葵小姐她们来徒然堂这里打招呼时,我总会感觉黑崎小姐有种说不出的分心游离、忙碌不堪的感觉。听葵说,自从和黑崎搭档后,工作完成的效率大大提升,黑崎小姐总能在制定应对狂百器的对策上提出绝妙的见解,是令葵小姐非常钦佩并放心的好拍档。看来优秀的工作成绩也都源自于黑崎小姐时时刻刻的劳心吧。
想到黑崎小姐,我在脑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是葵第一次带着桃姬和黑崎来徒然堂的那个下午,大家都热络地说着话,我偶然注意到身着华丽洋服的黑崎小姐独自站在窗边,远远地向外面看去的模样。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棂进来,在黑崎小姐的脸上留下分明的阴影。她抱着胳膊往外面看去,目光远远的——我下意识地也跟着看过去,只看见白云青天。那时候的黑崎小姐就如现在这样,思考,思考,不断地思考着,明明四周如此热闹,她却像是脱离开来、置身于外般不受周围影响,专注地思考着。专注投身思考的黑崎小姐十分迷人,那时我就这样被吸引住,直直的注视着她。
黑崎小姐在思考些什么呢?下一次应对狂百器的计划吗?还是说正在为葵小姐谋划人生?又或者是更遥远、更虚的事物?不断思考的前方有着什么东西,黑崎小姐用这人形之躯探究到了怎样的答案?她就像是思绪的水滴汇成的大海,我真想知道这片海洋深处的声音。不知道今后会不会有机会与她促膝长谈呢?
除开虚方小姐和清净屋们,若是不出门的话,大概就剩下一楼咖啡馆的客人们我们见得比较多了。话虽如此,比起前面,客人对我们而言其实交互之感实在是太低了。除开体质特殊、灵力强大的人外,大部分寻常人类不在特殊的日子是见不到付丧神的。我们能看见、听到人类在做什么,他们却看不见、摸不着我们,可以说是不对等的关系吧。我想,在徒然堂静候的九十九恐怕都曾经同我一样注视过客人们——他们的喜怒哀乐、一举一动都预示出无数可能——人是很有趣的,可惜于我们而言,人类不过是施加不了影响、交流不到信息的局外人。在徒然堂,结缘这个话题是人人避不开、逃不掉的。听朋友们畅想、许愿自己的有缘人会是什么样非常有趣,美丽的女子、强大的武士、珍惜器物的少女、老奶奶、刀匠……大家各式各样的猜想我都爱听听,但注视人类的时间越久,心里越是感到困惑:对我而言化形有什么意义吗?
在徒然堂醒来的大家,或是留有缱绻的念想,或是怀着未竟之事苏醒,大家基本上都有想去做的事,而我却毫无想做什么的欲望。刚从混沌中获得意识时,萦绕在我心间的是前主人在日记里留下的思念之情。我的主人与恋人无奈分离后,时常在日记中抒发思念、企盼重逢的心意。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她等候了一生也没能守到意中人归来。小一曾经问过我,如果能得到结缘的机会,我会不会去寻当初原主一直在等的人的音讯。可是,在我看来,主人虽生前留下遗憾,她的一生也依然是很好的一生了。除却对挚爱的思念,她时常在日记写下今后的打算,遇到了如何的困境,而后又是如何从绝境里走出来,每日的进步、生活的哲思、家人过世的伤感、担起家业的勇气、敦促和激励自己的话语……这已经是足够好的一生了。我已经陪伴主人好好地走完她的一生,多余的事情已经没有必要了。既然如此,这难得的人形之躯赐予我真的好吗?
在我不断思考自己有没有必要醒来的过程中,发生在虚方小姐身上的一件小事给了一些启发。
由于在春造化日彻夜忙碌,而后的几天又为新化形的九十九劳累,虚方小姐不慎患上感冒。虽然不是太严重的病,但确实影响到状态,闭店后店长便直接让虚方小姐回房躺着休息。虚方小姐平日待我们很好,大家都很担心她的身体,虽然她告诉我们只需要吃点药睡一晚就好,我们还是拗着她答应了放我们进屋守候的请求。担心都挤在虚方姐姐的房间会影响到休息,大家决定每隔一阵子换着进屋坐守。
人类真是脆弱呀,一场小病也能打垮一个人,变得虚弱无力、无计可施。我们付丧神只要原形不灭,就不会有其他困扰。我静静坐在虚方小姐床边的座椅上思考,人类还真是柔弱啊。
大约凌晨3点左右,虚方小姐突然醒过来。那时我才换班进来坐了没一会儿。我去桌上取来掺好温水的水杯递给她,看着虚方一点点喝下,然后缩回被窝。
“晚上好,弥生。”
“晚上好,虚方小姐。你感觉好些了吗?”
“嗯,应该已经退烧了。我有些睡不着。”
“太好了。”
我有些不知该怎么办,自己并不是很会讲话逗乐,不像阿式或者歌丸那样能调节气氛,只能同尚无睡意的虚方姐姐讲一些不太有趣寒暄,这样很无聊吧?
“要是小一在就好了,”她温柔地抬头看向我,“小一能和虚方姐说好多有趣的事,我就只能问一问身体情况,不太有趣呢。”我无奈地笑了笑,不好意思起来。
“没关系啊,”她认真地看着我,“最重要的是这份心意。弥生愿意陪在我旁边,这就足够了。擅不擅长调节气氛、说话又不有趣,这些都不重要啊,弥生愿意为我着想的心意已经是最最重要的了。”
虚方小姐的话点醒了我。不只是在这件事上,它还使我想到了自己有幸获得人形之躯的意义。
在过去,作为一本日记,我陪伴了主人经历她人生的风风雨雨许多年,这段旅程回想起来令人开心。虽然无法为日记之外的她切实地做些什么,但我能感觉到因为有我的存在,每一笔字迹、每一次对自己的祈愿和激励,这些东西一定都真实的对她产生过影响。如今的我没有想去做的事情,但要是还能像过去那样抚慰、激励、陪伴着什么人的话真是不错呀。
要是还有什么人需要我的陪伴就好了,即使我能够做到的事情真的不多。这一次能幸运地从混沌中醒来,是不是命运的指引呢?
我努力地去回想第一次见到纪斗先生的情景。
那只是个和平日没什么区别的下午,我随意地坐在徒然堂通向二楼的楼梯上打望着一楼的客人们——这是我和小一没什么安排时喜欢做的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只是看见一个模样落魄的身影向自己这边慢慢走来。虚方小姐注意到,亲切地询问客人有没有兴趣看看二楼。印象中,纪斗先生还被虚方姐热情的招徕吓了一跳。暮气沉沉的客人看起来仿佛失了魂儿,茫然地在店里走着,我想他或许是刚失意于工作的人吧。
突然间,我注意到一件事,这位垂头丧气、神色蔼蔼的客人正瞪大了眼睛,直勾勾地朝着我看过来——我以为自己身后放着什么,回头看去一无所得,再回头,他依然一言不发注视着坐在楼梯上的我。
“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您看得见吧,这位九十九。请不用害怕,这是一种缘分。”店长小姐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
虚弱黯淡的他在我眼前愣住。
“要来二楼看一看吗,上面有很多非常棒的商品哦?”虚方小姐温柔地笑着。
我看见他慌张地低下脸,不自觉地双手握紧,用需要竖耳凝神才能听到的音量小声说道:“不用了,不用了。”
然后转身逃也似的离开了徒然堂。
End



原本小满的卡,终于打上了【暴风哭泣
名字是随便起的X】
我想好自己到底要提出什么要求了,空太郎这么告诉自己。此刻恰是沉静的夏夜,将窸窣虫鸣也一饮而尽的夏夜。
彼时空太郎正呆在那间刚刚才属于他没几天的房间,躺在他还没认熟的床上假寐。身为意识体的九十九既不需要睡眠,也不需要房间,他所需要的不过是整理自己思绪的时间,就像人类记录着的日记。但那个满脸严肃的家伙就这么不容辩驳地告诉他:
“这是你的房间,有什么事可以过来找我,我的房间已经和你说过了。”
简短而高效,一如军队里所追求的那样。尽管空太郎没有使用能力,而十文字政臣也没有明说,但这个事实在空太郎眼里就是这么显而易见,仿佛他脸上写着大大的“军人”两个字一般。
也许对于空太郎来说,这两个字是真的写着的,早至在看到这张脸之前。
那是空太郎“日记”的第一页,那天的空太郎不再拥只有思绪这一个感官。比视觉更早到来的是声音,毫无规律的敲击声砸在地面,屋顶和其他很多很多地方;毫无规律的声音之外,是另一种规则的声音,不时加重,又不时放缓,总是与思维的变化相吻合;最后这些声音和思绪终于团成了一团,组成了如今空太郎所知的“人”的形状,于是他也得以依葫芦画瓢地把自己捏造成类似的东西。当时的自己到底做得怎么样呢?空太郎也曾这么想过,但这终究是些不可考的事情了。直到现在还清楚得记着的只有房间里满坐着的人,挂着和自己的结缘者相似但又不相同的表情。那里的气氛更为凝重,思维也更为单一,仿佛将同一份想法复制黏贴一样。
这就是自己第一次化形时的情景了,没有原因,不明时间。在那段长长的岁月里,只有那一次,自己睁开了“眼睛”。
青年模样的九十九摇了摇头,翻身坐起来的同时,将自己从思维的泥潭里拔了出来。虽是夏季的傍晚,此刻屋子里终究还是很暗了,唯剩下一层微微地蓝紫色,将窗户的轮廓勾勒了出来,放在寻常人身上的话,恐怕现在早已点起蜡烛,拉亮电灯了吧。 而前者在如今早已不多见了。
现在的人们或许需要一个杯子重的灯泡,一块杯子重的煤炭,又或者是杯子本身,但一个杯子重的烛台绝不再是必需品了。破门而入的科学带来了很多东西,也卷走了很多东西,空太郎并不打算将自己排除此列。然而他又远非一个单纯的烛台,他绝不仅仅是一个烛台。
其他几个房间里的光在地面上投射出了方方正正的图案,脚步声在走廊回荡开。
在那个地方么?
这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转了一圈,又沉到了最底部。比起声音,意识的所在才是更为便捷的定位方式,只要你能够使用他。空太郎直到如今还可以靠着这种本事数清一整个屋子的人,要知道他当时就是靠这种方法了解旧主人家里的房屋构造和人员数量的,尽管如今支撑这些记忆的事物和人员都早已不复存在了。
随后传来的就是拉开椅子的声音,这位出身行伍的人又开始了日复一日的伏案工作。
“我没有路,所以不需要眼睛;当我能够看见的时候,我也会失足颠仆,我们往往因为有所自恃而失之于大意,反不如缺陷却能对我们有益。*”句子和思绪一同流出,此外还掺杂着许多产自东洋的九十九不能理解的语言,奇怪的一点却是,明明不能理解语言本身,它承载的意思却没有因此蒙上丝毫阴影,就像思想并不依凭语言而存在那样。
这或许就是自己唯一与众不同点,空太郎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他人听闻声音,便讲出回答;看到事物,便描绘外形。而他自己历览思绪……
空太郎的“日记”之所以被他称为日记,是因为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自己才能翻阅,恰似人们的日记那样。他并非不曾用这罕见的感官发出消息,但结果自然是石沉大海,或许是他人根本接收不到这些信息,又或者是因为他们无法给出回应,但无论如何,空太郎打算试一下。
就像他在脑海里记述“日记”一样,他抽出了自己所知的最纷繁复杂的思绪,然后尽他所能,像抛洒渔网一样——
可是思想的渔网并没有能够成功撒下。话在嘴边,嘴却被捂上;图在眼前,笔却被抽走就是这种让人不爽的情况了。
尽管结缘时,因为时间仓促并没有想出要求,但空太郎还是保留了自己提出一项要求的权利。归根打底还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并不会结缘,不过既然现在困扰已经初现雏形,及时遏止还是很有必要的。
“可以的话,”空太郎听到自己这么说着“我希望点燃和熄灭蜡烛时都得到我的同意。”
*《李尔王》,十文字政臣在翻译的那本。
迷迷糊糊写的……完全不知自己在写什么,而且还憋了很久
大概就是空太郎有新能力了吧?



改完版
修正了一些小bug
添加了伏笔
引用的作品不符合时代背景请见谅
空太郎从咖啡馆走回了二楼,夹在指尖的是一盒没开过封的火柴——“徒然堂咖啡馆”,底下还印着些地址联系方式之类的小字——每天只点一根的话,这盒火柴大概能用上好一阵。
烛台上的半截蜡烛静静地立着,与昨天熄灭时别无二致,不过以它的长度来说,撑不过今晚了。
这是空太郎再次醒来的第三晚,也是自己点燃蜡烛的第三晚。
醒来或许是个不恰当的措辞,他只是处于什么也看不见因此不得不假寐度日的状态罢了。只要燃起烛火,即便没有人形,他也能“看”到别人的想法。并不是听到别人脑海里响起的自言自语,也没有什么嘴唇的开合、声带的震动,仅是一种以他能理解的方式将别人的思绪呈现在他眼前的,和嗅觉听觉别无二致的感官方式,他习惯将其视为阴影。
的确就像日光下得人影那样清楚分明。
如果天上的太阳也的确穿透人心,那就无怪乎一代代人类将其奉为神明了,他这么想到,没有什么他穿透不到的地方。
刚得到人形的他将这归功于点燃的烛光,然而那个能够点燃油灯的“少年”则否定了这一想法。
“你看不到么?”几年前的今天,自己也是这么端详着自己的本体,询问那个与自己本体相似的付丧神。外貌平凡的烛台除去抓握的部分外,铜制的主体已不再光亮,底座花纹的缝隙里泛着些绿色,述说着它所经历的的不短不长的历史,烛台上蜡烛的顶端仿佛富士山的山口,被熔融的蜡液迫不及待地溢出那个不大的凹陷,又在冷空气的阻拦下不情不愿地停下脚步。
不远处,貌似少年的付丧神愣了下,四下望了望并无他人,才意识到是在和自己说话,下意识地张了张嘴,似乎有什么答案呼之欲出,然而它终究没有出来,少年又将它咽了回去。
最后还是空太郎不耐烦地把本体放回桌上:明明简单的否定就好,冒出来的却全都是毫无头绪的话语,既混乱又无聊。即便不用能力,也能读出对方满脸的疑惑。
然而就是这个畏畏缩缩,满肚子混乱想法的家伙,却莫名其妙挺过好几个造化之日,该说是傻人有傻福么?不过自己也没有维持人形的必要也就是了,所谓的有缘之人并不能解决自己的困惑哪怕一分一毫。
空太郎并不是喜欢自讨没趣的家伙,这也不是他第一次交流失败。回想起去年……
微寒的春风吹进来,并没有听到习以为常的风铃声。尽管是旧式的陶土风铃,甚至没有一层釉,而底下坠系着的纸片上用好看的花体字——那是什么字体?意大利还是其他什么国家的?——叙说着一句话“I had the keys but no instructions*”。
不过这句话的含义并不是由本人告知空太郎的,说本人或许有些不太恰当?总而言之,是他自己知道了这件事,而疑惑的源头并未开口说过一句话,尽管她的思绪曾使他感到好奇,甚至可以算得上有一丝着迷。
犹记得当时,新装的路灯并不比天上的繁星逊色多少,深紫色的最后一丝晚霞也即将匆匆谢幕。时至今日他也说不出,风铃声和那沉沉地思绪,究竟哪一个是晚风先送来的。
他走向窗边,旧日那个风铃不知去向,取而代之的是不知何时站在窗边少女,那并不是他所熟知的少女。
印象中出游的日子就是这天晚上,同时也就是俗人眼中所谓的百鬼夜行,然而随着现如今上至数学、物理,下至电灯、水瓶一股脑的传入,这种说法越来越被视为无稽之谈,警觉如夜巡的的士兵,也没有发现分毫的异常。
当年旧主手下操练的士兵,是绝不会如此懈怠的。空太郎并没有亲眼见证过作战时的种种,但他对此坚信不疑,要是他是能够带上战场的武器就好了。
尽管不满于那些夜巡兵的粗心大意,他还是套上了一身类似的军装,毕竟这也是离他心目中的军人最接近的概念了。
在他还没有化形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不能分清说出来与没说出来的话语。没有谁是可以真的不假思索说出什么的,而他看来,说话不过是将一句话重复几遍,和那些在脑子里一遍遍打转的念头毫无区别。直到他所悉知的第一位主人的孙子的孙子都能用与他父亲如出一辙的话语教训自己的孩子,他才第一次睁开了双眼,意识到了浓重的训斥来自于谁,浅浅的不满又来自于谁——稚嫩的思想给予他的刺激并没那么强烈,就像声响有大有小,影子有深有浅一样。
这一点对于付丧神来说也不例外。
付丧神之间的经历大相径庭,思想也因此千差万别,不论是样貌年轻却背负着重重阴影,还是像他身边这位着巫女装的少女,身量已足,想法却与孩童无异的,都不足为奇。
“我是你的话,现在已经在准备晚上出门了”军绿衣装的付丧神适时打断了那些毫无营养的怀想,“一朵云根本就不值得看那么久……”
原本柔和的思绪瞬间像碰到火星的爆竹那样炸了开来,爆发出怒火几乎可以灼伤自己,不单是言语上被冒犯到的不满,也包含有被人捅破秘密时的气恼。考虑到空太郎的能力,怒火并不仅仅是一个比喻。不过挑起事端的一方并没有直面这阵怒火的打算。
“行吧行吧,你好自为之。”触了霉头的空太郎摆了摆手,向楼梯走去,难得好心却被当成驴肝肺,果然自己应该少管闲事。
年轻人往往是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痛的,这句话似乎也同样适合用在青年模样的空太郎身上,尽管他的年纪早已不是一个青年了。
“之前那个风铃,怎么了?”
浊化了。浮现在他脑海里的只有这短短的三个字,诚然,词语即沉默的一部分,是可以被说出来的一部分*。但没有声息的三个字此刻比白纸黑字的判决书更加鲜明,此外就是无法辨识杂乱声音,仿若收音机里的白噪音。
“……然后呢?”
消灭了。
怎么会呢?
空太郎几乎要喊了出来。
当时明明没有感受到混乱的情绪,即便是一丝一毫不满也没有。难道是因为哪一晚忘记点上蜡烛了?
仍旧处于错愕之中的付丧神魂不守舍地走下楼梯,对不慎在楼梯撞上的男子也不过是略略点头致歉,甚至没有注意到他们交汇过一瞬间的视线,没有发现这远不能算上是常事。
你看到的不过是些在日光之下,阴影之上的东西而已。
阅读思绪的付丧神猛然收住踏出的半只脚,扶在楼梯上,忍不住回望向沙发上那个小小的人偶。徒然堂的店长端坐着,空白的思绪如同收不到信号的收音机,而方才不慎蹭到的男青年,已经拐过弯,去到空太郎出来的房间了。
*珍妮特·温特森《守望灯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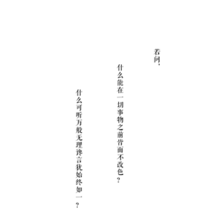
我并不在意事物的形体,我眼中的他们不过是物体所反射的光。
我走进一楼的咖啡店时,摆在大厅里的西洋大钟刚敲响第四下。晚春的阳光仍旧是迟到早退,懒散的光辉将空气中的微尘,着洋服的年轻女性,以及她手中花纹繁复的骨瓷杯都勾勒的一清二楚。明明是毫不相同的场景,我眼前的光景却和墙上挂着的那幅油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照见光的地方明亮,照不见光的地方黑暗,这全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此刻是下午茶的时间,人头攒动的咖啡馆里,只有我的脚下没有影子,光线穿透我的身体,一如我看穿别人的心。而我也得以旁若无人地离开了咖啡馆,或者说是咖啡馆若无其事地吐出了我,这并没有区别。
好在我并不为此困扰,声音与图像本是迟来的嘉宾,观察他人的表情和倾听别人的话语一样多余。我既不靠别人的宣讲了解世界,也不靠人们的行为认识他们,尽管他们想做的不过是在别人心中留下一个他们想要的倒影,而上述两种方法是他们仅有的手段。但实际上,这在我心目中称得上是滑稽可笑的。
然而可惜的是,我并不知道如何向你们分享这份笑料,它并不比了解洋人们的笑点更容易。因为要知道,我是可以知晓别人的想法的,这是我与生俱来的能力,就像听觉,视觉,嗅觉等等很多感官那样,它也是我的感官之一。看到人们耍出这些小小的花招,就像看到蚂蚁无法不爬过圆圈的边缘就离开画在地上的圆圈,就像人们无法不打破鸡蛋就取出蛋黄一样,当然,我并不是说我就可以不打破鸡蛋就取出蛋黄,但是我可以不撬开人们的嘴就取出他们的思想。
在我还只是桌上的一个小小的烛台时,我的某一位思绪复杂些的主人——请容我这么叙述,因为那会我并没有化形,没有办法为每一片飘忽的思绪对应上一个实实在在身体——那位主人决心要逗一逗思绪简单的另一位,恐怕是他年幼的儿子吧,便在他儿子恶作剧时假装并不为所动,现在想来,恐怕还会摆出一副严肃的神情吧?不过他当时恐怕并没有笑,因为在感受到他想要放声大笑的同时,年幼的小主人的失落之情却像暴风雨前的乌云一样肉眼可见,可见当时他父亲忍住了将要绽开笑容。
虽然这段经过是如今我推想出来的,确切性并不可考,但是我从那时便意识到了有很多事往往并非是它表现的那样的,就像一个人不笑并不意味着他不开心。而我之所以觉得它们有趣,不过是因为我与你们的的视角不同罢了。
这份能力仅是单向的,窃密者不会让失主知晓自己的存在。否则像我这样闲逛在街上时,恐怕有无数人乃至于非人之物想要冲上来杀我灭口。而我觉得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
不知在你们想来,我的能力究竟是听到人们在脑海里自言自语的默念,还是让他们想到的东西浮现在我的眼前呢?这大概也是旁人想象的极限了,这就像让聋子鉴赏婉转的女高音,用黑白照片向人们描述色彩一样不靠谱。
或许照片还是个可取的想法?毕竟图像有着明暗度之分,而情感也有平静和强烈之分。就拿街角那个小吃店来说吧,那个奋力吆喝的店员声音是洪亮的,行动是富有朝气的,然而在我的黑白照片上,他却算得上是明度最低的,就连他自己也早已厌烦这份工作,换行大概是他的唯一选择;相比之下,另一边的店员看上去笨手笨脚,连收拾餐具都要担心他是否会摔碎了碗碟,但他确实是一心一意想要学些手艺,恰如照片上亮度分明的人脸。
然而更多人只是趋于暧昧不明的灰色:
买菜回家的主妇行色匆匆:“今天做什么菜色比较好呢?能让家里人都爱吃。”仿佛他们的全部人生都维系在这一件事上。
回家路上的女学生们叽叽喳喳得聊着小说——“我很喜欢这句话‘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但爱就在里面。那意思是说,爱在外面寻找破门而入的机会。*’听起来很浪漫。”
抛出一个东西的优点是对朋友推荐东西的惯用伎俩,小女生的常见行为,我对这种毫无营养的话题早已深恶痛绝。
“这话要是放在三年前我会很喜欢,但是现在看来,不过是一堆空话。”
后者的回答也是我司空见惯的,她讨厌说可以。她是那种人,觉得“可以”是对罪恶和失败的许可,“不可以”才是权力。*
看吧,即便是相同的亮度,也有如此多纷繁不同的想法,要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有时就是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这就是为什么黑白照片并不能完完全全地类比我的观感,同样的亮度下也有不同的色彩,不是么?
但即便是同在黑白的底片上,也有着曝光过度的部分,他们或许常常默不作声,但他们的思绪确实熠熠生光。
就如迎面走来的那一位。
靛蓝色的眼眸和高挺的鼻梁都昭示着她出身异国;即便是对西洋所知无多的我也能从她打扮中感受到一丝所谓“贵族的气息”,如果不是由于付丧神的特性,她一定能吸引一整条街的目光。长款的风衣后摆跟不上她追随自由的速度,微微地飘了起来,露出了里侧抽象的星光,那是和自由与存在一样模糊的东西。
“我就在这里。”
这是就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骄傲甚至有些自负。尽管在别人眼中她只是匆匆走向她的下一个目的地,毕竟她的结缘之人是个承担责任的清净屋,但或许她自己都不知道她的道路通往何处。
她是燃烧的星星,追寻着不知是否存在的原因。
然而星星终究是要燃烧殆尽的,在这一点上,它们和立在烛台上的蜡烛没有区别,我也曾想知晓自己存在的原因,不过如今,比起追寻自己缘何而被点亮,我更在意我想要照亮谁。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的名字叫黑崎。
尽管我不在意别人的音容样貌,那并不意味着我宽心到挑战世俗的礼仪,春分以来打这段时间我终于习惯了在见到别人时问好,在说话时直视对方(或者是他们脑后的墙)。因此我还是在走近时对她打了打招呼,她似乎那时才发现我,突然被人撞见的惊讶之后,她还是向我点头示意。
我回到咖啡馆时五点的钟声刚刚敲响第一下,呆在一楼的九十九示意店长在找我。
“你或许完美错过了你的有缘人,”小小的人偶依旧毫无表情,她是极少数习惯我单方面对话而不觉得有何不妥的存在之一,但她这次却一反常态的开了口“刚才有位先生想要买下你的本体。”
的确是一件重要的事,结缘对九十九来说和人类的婚丧嫁娶一样重要,而我也不打算当一个任人宰割的“弱女子”。
“是什么样的人?”
“你离开时在楼梯上撞到的。”
是么?我当时撞到人了?我仔细想了想在发现先前的不对劲:普通人是不会看见我的,更不会朝我道歉。或许我该改一改对外界毫不在意的态度了。
“我和他约好明天这会再过来,不介意的话留下和他谈谈吧。”
“……好的,有劳费心了。”
或许见到了的时候,我会知晓我所想要的事物了。
*珍妮特•温特森《守望灯塔》(没错老是这本书,谁叫我最近刚读完它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这个大家估计都知道
------------------------------------------
上一篇:http://elfartworld.com/works/137113/
一个结缘前春分后的故事,原本想接在上一篇后,结果发现有些怪怪的,大家就勉强无视这个bug吧
尝试了第一人称
希望大家看的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