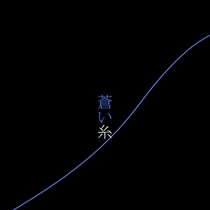午後,大大的落地玻璃窗開敞著,任由微風將外頭濃郁的薔薇芬芳吹送至屋內,也吹得那象徵著高雅純潔的白色手工製古典蕾絲窗簾隨之輕揚,微微起伏的白色波瀾令觀者平添了絲涼意。
室內,一名相貌纖細俊美的青年優雅閒適地坐在沙發上頭,赤裸的掌不同於平常總是穿戴著潔白得近乎刻意區隔出他人與自身距離的裝飾手套,而是一下復一下,輕柔緩慢地拍撫著枕臥於膝上,嬌小可愛如陶瓷娃娃般精緻的女孩後背,嘴角噙著淡雅溫柔的笑容,顯得身周氣場無比柔和,整體如畫似的安寧美好。
「嗚……不……」突然間,女孩小小的身子開始打起顫,下意識朝著能讓自己安心的地方靠去,瑟縮成團皺眉囈語著,蓬鬆的裙襬隨著姿勢變化而改變,猶如含苞花蕾一般半綻在沙發上頭。
早在女孩情況不對時就有所察覺的青年也不管手中翻閱至一半的書籍,就這麼隨手棄於一旁後將女孩抱擁入懷,輕撫喃語:
「喬麗,我可憐的小公主,又作那個噩夢了嗎?」
那個過往所造成的夢魘。
※
晚間,墨色深濃的黑夜降臨大地。
除卻天幕星光滿佈閃爍外,唯獨地面一幢被修剪適宜的庭園林木圍繞,佔地遼闊的鄉間別墅此時仍是燈火通明如白晝,雕工精細嵌有金屬飾物的厚重大門此時正敞開著迎接賓客。
對於貴族們而言,出席各個社交場合本身就是他們展示身份彰揚家族的職責,是不容錯失任何結識攀比的機會,也因此身著各色華麗禮服,手持燙金請帖的貴族們陸續依約出席,只為了不錯過今晚的盛會。
相較於屋外偶有紛擾的寧靜,屋內則是衣香鬢影觥籌交錯的夜宴場景,悠揚的樂曲奏響著,舞池中旋轉翻飛的各色裙襬交互錯開,盛放;舞池外是三兩成群交談言笑的人們,手裡持著盛滿酒液細細雕琢的精緻玻璃杯,或高談闊論或低低吃笑,伴隨著芳醇酒香未曾停歇。
水晶吊燈與燭光相輝映著,在華麗無比的宴會廳內投射一片暈黃光輝,明亮的曖昧顯得一派奢靡,高貴、優雅,而無聊至極的人們。
做為宴會主人,安斯艾爾有義務要和這群徒具其表,僅只有名頭好聽的人們打交道,臉上掛著交際應酬用的微笑,客氣有禮不過份熱絡,如同他自身。
為了能持續在這個圈子保有家族的名聲,為了掌握並利用事業經營所需的人脈,身為當家他必須時常參與甚至舉辦這類費時耗力且花銷頗鉅的社交活動,今晚便是這慣例的其一。
他很清楚,為了家族即使再怎麼厭惡反感也得保持著紳士風度,優雅得體地微笑應對一切,因為他代表的就是整個伯特蘭家。
一開始接近他想利用他,或是懷抱惡意等著看伯特蘭家沒落的人不少,對此他是習以為常,潛伏著逐步將其擊潰後吞併;不過從這一年開始,接近他的人逐漸看向的不再只有家族,而是連他本人也一併列入打量範圍內。
聯姻的事他不是沒考慮過,最快也最具效力的聯合兩個勢力的方法,只是他還不急也不願使用這手段,為了喬麗,也為了自己。
他並非那無能之輩,必須靠著女人衣裙才能撐起這個家,何況為了家族他已經將喬麗排在家族的後一位,他對這僅存的唯一親人虧欠太多,那些犧牲是無法用金錢彌補回來的,他想過在不久的將來他珍愛的珍寶出嫁時,他會親手送出一整座城堡的嫁妝給予他的小公主做陪襯,如果有哪個不要命的渾球敢來向他提親的話。
安斯艾爾一邊從容應對著往來賓客,一邊假想著真的出現未來妹夫這可恨的敵人時他該如何對付,孰不知他的這份顧慮在此刻的他處已經以另一種方式永遠地結束了--
「不……不要!」女童嬌軟清脆的嗓無助呼救著,蓬鬆裙襬下的纖細雙腿退了幾步後轉身就想跑,卻被立即抓住了那細瘦嬌小的肩膀拉回原處。
向來被兄長寶貝呵護得緊的女孩第一次遭遇到來自生人的無禮對待,被高大陌生又滿懷惡意的神秘男子襲擊的恐懼使稚齡孩童無法動彈,只能睜大湛藍色的雙眸,無聲呐喊。
『救我……哥哥!』
等女孩被找尋過來的僕役們發現時,女孩昏厥在地小臉蒼白無血色,唯獨脖頸與臉頰處沾染上點點紅跡,得知消息的安斯艾爾強忍著焦慮強裝無事地送走賓客後,迅速趕往女孩身旁守候和派人查明當晚情況。
然而女孩的情況時好時壞,重金聘請的名醫能者皆是給了他情況不明無法可解的答覆,以至於安斯艾爾這段時間幾乎是一有空閒便寸步不離瑪喬麗身旁,照料著過了好幾日仍是昏睡多於清醒,不能照曬日陽且容易感到異常饑餓的瑪喬麗。
可即使給予再多的吃食湯品,卻也只是入口即吐,完全無法正常進食吞嚥。
「神啊,請垂憐祢的子民,請庇佑可憐的瑪喬麗……」青年兩手輕輕交握住女孩過份纖瘦的手,多日未能好好進食使瑪喬麗憔悴許多,連帶的讓就近看護的安斯艾爾也跟著消瘦不少。
即使如此,比起外在變化,內心的煎熬痛楚才是使得年輕當家迅速萎靡的主因之一,他是如此害怕,害怕稍一用力便會折損其脆弱,害怕稍一移開目光便會永遠錯失女孩,他日復一日地向上天虔誠祈求著,祈求這唯一的存在能夠安然渡過此次危機。
看著躺在床上蒼白無血色的女孩,他一臉哀痛的皺起眉來,將額輕輕觸抵在掌中女孩虛握的小小拳頭上,青年難得的脆弱更顯得這份無聲傷悲深沉。
悲傷與不安籠罩在整個伯特蘭家,人心浮動惶惶,直到這日為止。
突如其來的襲擊使他錯愣在原處,頸項傳來的劇烈刺痛卻又再再提醒著自己,現在攻擊並肆意啜飲著自身血液的人,是他珍惜疼愛的妹妹。
反抗?不,他只是靜靜地任由女孩飲用著自己的生命,而後伸手擁抱著瑪喬麗,輕柔拍撫著女孩的背,就和往常哄女孩入睡時一樣溫柔。
「對不起……讓妳一個人這麼害怕,我的小公主……小珍珠……」
是他的錯,他不該放下女孩一個人,即使是為了家族--為了這狗屁家族,他犧牲了他唯一的家人!
家族該做的是守護著他的族人,她那時該有多麼害怕恐懼?他捧在手裡細心呵護的珍寶,美麗的、可愛的,他的小珍珠,他竟然放任著她一人去面對!
「沒事的--不管妳到了哪個世界去……哥哥也會想辦法去找妳……」
持續地大量失血使得安斯艾爾開始感到昏眩,手的拍撫動作開始逐漸轉緩,最後只是擁抱著女孩。
不論何時,她始終都會是他的妹妹,他的小公主,他摯愛的珍寶,如今他已無法繼續陪伴著她下去,那麼他便許諾下他的來生。
曾經是虔誠教徒的他放棄信仰,放棄天堂救贖,只為了選擇回到女孩身旁。
「--所以,別害怕。」
露出了只在女孩面前展露的溫柔淺笑,虛弱地喘著息,最後,他終究是闔上了那雙和女孩同樣湛藍的眼眸。
※
「我的小珍珠,妳忘了嗎?哥哥是不會離開妳身邊的。」
他完成他的承諾,回到女孩身邊,只為了他的信仰。
一再背棄他的神不信也罷,現在他所信仰的,是他一直委屈著的女孩。
早在那晚過後他就不必再繼續承擔著當家身份,如今他只願守護著女孩,為女孩而存在。
「哥哥是只屬於喬麗的。」

176 cm,實際年齡約莫300來歲,有著E CUP傲人上圍的純血族女性
性格大致算是溫和包容(對女性),對兩性的態度有落差
情感表達直接,喜歡肢體接觸感受人的體溫,特別喜歡親近女孩子
也許是外貌因素,意外給人一種較年長的感覺
拋棄血族身份追隨戀人(人類)至人類社會中隱匿生存,直至戀人逝去後多年仍未離開人類世界,只是轉輾於各地流浪旅行,代替戀人看看這世界
曾經張揚過,但與戀人相處的年歲使她變得溫和低調
會來就學純粹只是出於好奇以及對戀人的承諾,並不打算久待
※ 外貌 ※
外表大約27歲上下,有著成熟女性的風情魅力,卻不落於俗艷
光澤溫潤的珍珠白色及腰長捲髮側綁成民俗風編髮,平時美麗的矢車菊藍雙眼,唯獨吸血進食時會因為興奮而轉為嫣紅眸色,右眼眼角有顆淚痣
※ 能力 ※
凍結液體使其固化
※ 使魔 ※
姬瑪 ( Gemma )
貓型使魔,形象近似土耳其安哥拉貓,純白優雅,兩眼則為漂亮的淡水藍色杏仁狀,體毛有著如絹般光澤與觸感,唯獨尾巴蓬鬆柔軟得誘人抓取
獨立、不愛搭理人,對其主珮兒菈也是抱持同樣態度,經常擅自外出遊走,即便如此仍是個相當護主的使魔
受珮兒菈影響對女性的接觸比較能包容

「哎呀?」打開員工休息室的門,準備脫下制服圍裙就回去休息的珮兒菈,此時被裡頭那個早就下班應該已經回去,現在卻坐著椅子上對著包包上的綿羊布偶說話,像在等人似的女孩給引起了注意。
「小加,怎麼還沒回去呢?」視線輕輕掃過女孩的布偶,低聲溫柔地詢問。
帶了點腔調,珮兒菈那慵懶嫵媚且富磁性的女中音使人聽起來極為順耳放鬆,溫柔而溫暖地緩人心緒。
「珮兒菈姐,妳真的不打算在這邊繼續做了嗎?」女孩微㿜起嘴,有些悶悶不樂。
雖然只有短短一個禮拜,但她是真的很喜歡很喜歡這個成熟可靠又溫柔的大姐姐,想到對方只做到今天就覺得可惜難過。
「小加妳這可愛的孩子!」將解下的制服圍裙放在一旁桌上,直接從後方摟過坐著的女孩上身,以臉頰摩挲那頭柔軟的短髮同女孩笑鬧,好一會兒後才停下玩鬧,保持著這姿勢和女孩說起話來。
「先前就說好只是來賺旅費,不會一直留在這的。」她答應過人不會停下自己的腳步,即使她知道,『那個人』所期望的並非這個意思。
「不能再多待幾天嗎?」身為獨生女的女孩一直嚮往有個姐姐,總是故作堅強的她好不容易遇到了個能夠讓她放鬆撒嬌的對象,縱然不捨但她不希望造成對方困擾,只是她也想替對方做點什麼充作餞別禮,好好替女子送行,於是她開口挽留。
「沒辦法呢,我也差不多該為下一個旅行目的地做準備了。」因為姿勢關係女孩看不見珮兒菈臉上那溫柔又帶點無奈的微笑,女孩這麼親近她她是很高興,不過以女孩的身份來說,這可不是個好現象。
「我可以問問是哪裡嗎?可以去找妳嗎?」女孩有些緊張躊躇地問著,生怕會就此和女子斷了聯繫。
「不確定吶,畢竟我是要回去……唸書,那裡是不開放外人進出的。」說到關鍵處時珮兒菈壓低聲音含糊帶了過去。
血族以外的人進入是很危險的,特別是這樣一個年輕青春的小少女,真來探望只怕就像誤入狼群中的綿羊一樣,想到這,珮兒菈的視線再次落在一旁的綿羊娃娃上,不意外地和娃娃對上了視線,淺淺一笑。
「那、那我能不能給妳寫寫信呢?」不知為何女孩感到異常地心慌,慌到想抓住些什麼,想得到個肯定的答覆,急切的模樣和平時大不相同。
「--如果是現在的小加的話,不可以。」鬆手,動作輕巧地將女孩拉離懷中,轉動對方的椅子朝後退了半步彎下身,使兩人面對面後淺淺微笑,她說。
她知道女孩喜歡親近她,她也很喜歡這個可愛的小妹妹,可她也知道,女孩現在只是因為逞強太久而產生了依賴。
為了自立而獨自一個小女生離鄉背井來到完全陌生的異國,為了生存不斷說謊欺瞞著關心自己的人們,為了堅持自己的希望不斷強迫自己努力下去,認真的可愛的,寂寞的孩子。
血族的生命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不過轉輾旅行於世界各地的兩百年時光也足夠她去知道許多未曾記載於世界檯面的事。
她曉得女孩是為了證實自己才選擇這條路,笨拙卻努力不懈的見習魔女,所以她更不能讓自己的存在擔擱了女孩的夢想。
她能讓女孩撒嬌讓女孩依靠,但這不會是永遠,女孩終究還是得靠著自己成長才能獨當一面,於是她拒絕了女孩。
「現在的……我?」女孩困惑地重複著前段對話的話語,隨後唇瓣便被珮兒菈微涼的指尖輕輕觸抵著,打止了探問。
「噓~接下來的得妳自己去思考了,再說下去可不行呦。」嫣然一笑,眼眉動作間盡是一種獨屬於珮兒菈所有的魅惑風情,使人望而心跳不已。
「但是等小加想明白了話,我想綿羊先生會很樂意替妳送信給我的,我很期待那一天吶。」話畢,纖長美麗的指緩緩下滑,改捧住女孩的臉,而後湊近女孩耳畔悄聲低語道:「下次要在外面和魔寵說話時,記得靠近一點,看起來像抱著娃娃總比看起來像在和娃娃自說自話的好,小小魔女。」
「……珮兒菈姐妳究竟是……?」女孩瞪大了雙眼直盯著眼前人看,那過份驚詫的模樣令珮兒菈禁不住發笑出聲,低低的很是悅耳,牽引著人心。
好不容易笑夠了,這才肯回應女孩的問題,以著極其動人的笑容輕吐兩個字。「秘密。」
*
【以後不要太輕易相信他人】,這是她那天對女孩說的最後一番話。
她之所以會挑選那間餐廳做短期打工地點的原因,主要她對那裡很感興趣。
除了店家本身營業情況有些特別外,出入那裡的人們身份也相當特殊,純粹的人類、魔女見習生、惡魔以及其他非人,彼此間雖有隱瞞但能夠和平共處相安無事這點實在勾起她的好奇心,因此她進去成為了其一。
那間店的人都不錯,對女孩而言也的確是個很好的實習場所,只不過女孩實在太過單純了,稍稍一些言語設套就傻傻的要將自個兒全盤托出,令她忍不住開口提點了下。
總歸來講很有趣,有趣到要不是她承諾過要替人多看看這世界,也承諾要重新修復和家族的關係,她想她會在那間餐廳多待一陣子做觀察。
「學校……嗎?」她對家族沒太大留念,不過對於血族她倒是不排斥去多認識其他種族的人。
如同人類依膚色去分種族,血族也有各自不同的種族,她想藉這機會去瞭解看看。
「明天……吶~」尾音微微上揚,帶著笑意她低語呢喃,輕飄飄地有些不真實,最後溶於空氣中再也尋不著,一如她的存在。
【答--答--】
被細微而規律的聲響喚回意識後,入眼所見的是一片深濃的黑,什麼也看不見。
她猶疑片刻後想伸手往前探看,但不知為何身上卻隱隱有種被捆縛住的約束感和灼熱感,緊得令人渾身發疼,燙得肌膚像是快要燒起來了一樣,幾乎喘不過氣。
『怎麼……了?』她睜大了那雙平時總是受人讚賞,乾淨美麗的祖母綠眼眸,卻怎樣也看不清那片黑暗,獨自一人面對未知情況的不安迅速地侵襲著女孩,徬徨焦慮,內心感到極度的不安定。
她記得在失去意識前,她還在和又一次失約的哥哥鬥嘴嘔氣,像平常那樣發脾氣鬧性子朝大上自己許多的哥哥宣洩著不滿的情緒。
可是,現在又是什麼情況?哥哥呢?這裡好黑好暗,她的身體好熱好痛……爸爸、媽媽,你們在哪裡?哥……
『哥、哥哥--』語帶哽噎地泣喊著,她好害怕……好害怕好害怕,大家都不見了,大家都去哪裡了?為什麼丟下她一個?是不是不要她了?這裡好黑好可怕,有沒有人在……
【答--】
『……?』什麼聲音?
【答--】
啊,是剛才喚醒她的聲音。被緩而慢的滴水聲拉回了注意力,女孩停下哭泣,縱然焦急慌恐,可她還是努力地想找出聲音來源,好讓自己能從這份情緒中脫逃開來。
也不知是巧合還是錯覺,她總覺得眼前的黑暗從她被水聲引走注意力後開始逐漸淡化散去,漸漸地週遭的景象依稀可以看見,而她也察覺到鼻間縈繞著的是熟悉的人的味道,直到此時女孩才明白身上的痛楚是來自於兄長的擁抱,緊緊擁著像在害怕失去她,彷彿一鬆手她就會消失不見似的,異常地脆弱。
『哥哥,怎麼了……嗎?』女孩小小軟軟的手貼在兄長身上輕推,兄長的異常讓她遲疑,片刻後決定仰首張望四周去察看情況。『發生什麼事了嗎?』
『噓……絮白乖,別看。』溫暖的大掌在女孩剛有動作時便輕輕覆上了女孩的眼,掩去了某些不希望她知曉的事實,青年微微鬆開另一手,虛摟著女孩的同時也將自個兒的額頭靠抵在女孩額前,細說輕語。
雖然還是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不過兄長陪在身邊的事使她總算安心了下來,她的世界只剩下青年虛弱卻溫柔的低喃聲,如同往常一般,每每吵架過後,哥哥總會在最後來哄哄她。
『別怕,有哥哥在,哥哥會保護小絮白的……』
哥哥是個相當溫柔的人,這點不論對誰都是如此,她從未看過哥哥生氣過,最多只有那帶點困擾的笑容而已。
或許是他們年齡相差有段歲數的關係,哥哥對她一直是百般疼愛萬般包容,即使她在哥哥身上留下了無法抹滅的傷害也一樣。
「!?」睜眼,她迅速坐起身來,警戒地打量起四周。
寂靜,寢室內除了空調運作的機械低鳴以及自己不住的喘息聲外,再無他人在,胸前隨著喘息而起伏劇烈,薄薄一身睡衣被冷汗給打濕,直貼在身上,只是此刻的絮白卻無暇顧及難不難受的問題。
『滋--』細小的物體燒灼聲驚醒了她,發覺身周隱隱飄散著熟悉的黑霧後,她隨手揮之打散去,可隨即又聚攏了起來。
用一副難以形容是悲傷還是厭惡的神情看著黑霧,她深吸了口氣坐在床上抱緊雙膝,將自身縮得小小的,嘴裡喃喃說著安撫己身躁動情緒的話語。
「噓--不要想不要想不要想不要想,不可以想……沒事的,我不要緊的,沒事的,沒事的。」
「我可以的,沒事的……不能想,不能要,不可以,不可以,沒事的、沒事的--」
一再一再重複著相似的話,從那天開始,她便是這樣一個人撐過來的,即使只是個自欺欺人的作法,卻是她唯一能保護自己的方法。
『妳必須控制妳的情緒。』向來沉默的父親總是皺眉看著她,深深嘆口氣後對她這麼說,而母親--
『聽話,不要亂發脾氣,不能哭,不能鬧,乖一點學著長大點,好嗎?』
『妳什麼時候才能懂事點成熟點?』
『我沒辦法對那孩子笑!沒辦法當作什麼都沒發生一樣接納她!』
「!?」掩著耳,低語的速度比剛才更加急促,不停地說服著自己安撫心緒。
「沒事的,我可以的,一個人也沒關係的,這裡沒有別人,不要想不要想不要想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過了好一陣子,細碎的喃語才逐漸轉緩,平復下來的絮白鬆開掩住雙耳的手,任其自然垂落於身側,濃墨似的烏黑長髮深酒紅色的髮尾末梢襯得那身肌膚異樣蒼白,顯得嬌小的她格外地柔弱。
頰枕靠於膝頭上靜默不語,就著窗外照射進來的微光,視線隨意打量著這還有些陌生的寢室。
她知道她這樣只是在逃避,但她在逃避什麼連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她害怕,所以她避開了家人,避開了人群,一個人劃開了共存的距離拒絕了他人;然而卻又貪婪地想和他人有所接觸,想和他人有所關連性,不願亦不甘獨自一人終老,也因此才會在在知道有這所學園後選擇說要來就讀,她從抑鬱的家中逃到了不知道她的這兒,而母親不想看到她這點成了她最有力的說辭。
很卑鄙,她知道。
但她想學會控制自身的能力,想改變自己的狀況,她不想自己又再次失控傷人,她想再次牽上那斷掉的羈絆,她想……
「哥哥……」對不起--
闔眼握拳,在心中默禱著那藏掖許久的期望。
總有一天,她會帶著笑容回去的--回去她的家。
在一夜無眠中,她又一次期許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