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神是真正的神,而我的愿望成真,那么如今你一定会在哪里活着。只是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所以无法给信封写上收信人的地址。
过去我认为自己无力,脆弱,甚至没有办法保护自己。但是在那样的厄境中,我们相遇,留下了回忆。不是猎人且并不健壮的我,依靠你教授给我的护身的方法,还有一些幸运,活到了现在。
是的,我活了下来,怀着一颗没有泯灭的心。过去在很多个瞬间,我都对这样的世界和无能为力的自己感到绝望,只觉得一切席卷而来,无情地带走了我珍视的人与物。但是,每当发现你还在为了保护谁而挺身而出时,我便意识到还不能放弃,倘若还活着,就应该努力到最后一刻。
我好像一直站在天平的中央。一边我想着我需要做点什么改变这个世界,哪怕是付出生命,我也要把我仅有的一切全盘付出,像飞蛾扇动翅膀投身到烈火中去,壮烈地燃烧自我;另一边我想着也许我只是该活下去,孱弱的能我活到现在已经非常不易,受过那么多的关照与帮助,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生命,受伤也好,残疾也好,变成血族也好,变成怪物也好,只有活下去这件事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终于,直到现在,我能写信,能讲出这一切时,才意识到活着本身已经是一种巨大的意义。如果没有人活下来,谁会记得那些已经牺牲的人们呢?在见证者的目光下,与逆境对抗的战士们被定格在最为勇武的瞬间,变成永恒。而作为见证者活下来,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那一日的情景依旧会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我时常分不清哪些是真实的,而哪些是我的臆想。我意识到那也许就是我们的诀别,但我仍然许下了那样的愿望。活着终究是不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对于你来说如何,我至今没有答案。但就当作我自私,一时冲动,就算违背了你的意愿,也请原谅我。我希望你依旧活在某个地方,哪怕再也不会见面,我记忆中的你只停留到那一瞬间为止也没有关系。
我们的人生本来就像是两条短暂相交的线,但在我心中,好像只有交错之后的人生才有了色彩与意义。在那之前,我的人生游移不定,始终得不到心理上的满足。遇见你之后,我在你身上感受到了强大与平静,见证了你对真相锲而不舍的追逐(尽管真相让人如此沮丧),不曾放弃战斗的坚定意志。在我将要被真相带来的恐惧压垮时,又是你将我从深渊中拯救出来,让我踏出泥潭,迈向前方。我想我该活下去,是因为你对我如此期望。
圣女制度如今看来变成了一件荒唐之事,而圣女的血也不再有过去那样的功效,失去了意义。但是那是人们曾经试图抵抗过的证明,她们代表了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人类极端疯狂的举措。褪去宗教的外衣,她们是当今人类的先驱。而随着一切的结束,剩下的圣女们也活了下来,也算是一件幸事。
在如今的时代,和平成为了常态,需要武力的地方更少了,大家正在试图建立新的秩序。但是过去的灾厄时代还未远去,还有一些人活在阴影里,但是一切正在变好。现在我找到了我的使命——那并不算是新的,但那是一种延续。大教堂虽然没有神父,也不举行宗教仪式了,但孤儿院和学校还是保留了下来,我在那里给一些孩子们教书。并且我还在书写,写一些过去其他的事情,也写一些给孩子们看的书。很多孩子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没有见识过那些灾难,我希望他们多多少少知道一些,记得一些。希望他们看到有增生的大人不要觉得他们丑陋,遇到害怕吸血鬼的人不要觉得他们古板,知道教会曾经做过的实验不要觉得他们愚蠢。人性是十分复杂的,扭曲的环境会催生扭曲的人性,但那仍然是属于人的部分,不应该被全盘否定。我想让他们知道,无论时代或出身,其实大多数人都十分类似。
爱尔莉丝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花花草草,涂涂画画。虽然年纪还很小,但是已经可以认一些字,自己读一些东西,就不像以前那样爱缠着我讲故事了。每当我又被噩梦困住,感到不安与动摇时,牵起她的手,就会重回平静。过去带给我们经验或阴霾,未来带给我们恐惧或希望。行走在这样的世界上,拥有珍视之物,才能拥有对抗一切的勇气。
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也许是在某些地图上没有名字的地方,又或者在更加遥远的其他岛屿或大陆呢?希望你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健康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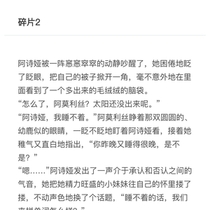



「你的愿望是什么?」
突如其来的声音仿佛某种低语诅咒,尤尔娅·马尔蒂眨眨眼,确认自己并非沉浸梦中。她已经从尤裡卡的城堡离开,正在独行的路上,星夜之下的呓语仿佛某种诅咒,又像是一些诱惑。
她沉默下来,如果要说愿望,谁又没有愿望呢?许多愿望充盈心中,复活米娜、世界和平、大家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是最后她只是摇了摇头。混乱之中,她只愿意忏悔,而不想依靠祈求。
“愿望需要付出代价,我的女儿。”利冬曾经教导过她,现实的男人难得没有笑意,声音残酷冷静。
所以她拒绝了。
这并非强制迫使的许愿,是否开口都只是自身的选择。尤尔娅·马尔蒂不去期盼,却向着教会的方向跑去,在所有人惊慌逃离的时候,她向着混乱的中心冲去。现在的战况相当混乱,以她的能力,以她“人”的本身,自然不能改变战局,更没办法做任何事,苍白的混乱的血色的一片中,只有女人的头纱狂舞,她瞪大眼,金色中倒映着血与黑色的影子,破败的一切中,什么都没有。
她看到了神。
短暂的沉默中,她转过身,继续向着目的地跑去。以单纯的人力出发是件漫长的事情,她还要在中途干涉一些混乱,所以到的时候,也已经是差不多结束的时候。高跟鞋踏过曾经跳舞的广场,百合花已经烧成了灰烬,镰刀的锋芒被显露无疑,可是尤尔娅·马尔蒂什么也没有攻击,停留在教堂门口时一滴眼泪都没有掉。
这是她生长的地方,即使是一无所知的人,也知道教会谋划了什么,召唤了神与诅咒。她的身体已经开始变异,在路上尤尔娅听说了许多人开始产生同样的排斥,也许很快她也会长出肢体变为怪物,可是那又如何呢?身形就算变化,灵魂也依旧如常。
她不会为任何人辩解,也没那个资格去做任何一方的战士,她来得太晚了,在神消失之后才到访此地,赠送给阿尔文·伊诺克的花种培养的花朵早就消失殆尽,她的眼里倒映着曾经亲爱的长辈、疯狂的许愿者的雕像,教会中的资料告知了许多残酷的内幕。米娜死于一场实验,还有很多很多圣女死去……这一切都源于她最亲爱的两个人。
出乎意料的,这次她并不觉得多么崩溃,甚至不去憎恨或者诅咒。她立了一会,又眨眨眼,最后在把几个受伤的修女神父送出去之后,在阿尔文的“雕像”前伫立,她从口袋拿出一个丝绸小包的花种,放在了他的脚下。
踮起脚,她拥抱对方的身体,而后闭上了眼。
她没资格替任何人原谅,包括她自己。所以……她决定伪善,将一切苦痛都诉诸以爱。
不知道是不是该说意料之中,利冬幸存下来,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打算去死,所以很轻易在教堂找到了自己的女儿。形容狼狈的男人一眼就看到了白发的女人,她脱掉了那身修女服饰,只穿着一身裤装,正在教堂附近的区域帮忙援建。
尤尔娅·马尔蒂捐赠出了大部分的存款,她本就攒了不少,又从尤裡卡那里弄来许多,虽然依旧是杯水车薪,但尤尔娅并不在乎,只是把东西分发出去。而后她卖掉了自己的枪与镰刀,为许多人弄来粥水,安慰痛苦的孩子们,已经出现异形的身体依旧温柔地拍抚那些孩子们的肩膀,然后唱起了玛歌修女曾经唱给她听的歌谣。
“你没必要这样。”利冬对她说。
“我知道自己什么也做不到,父亲,”她对自己的父亲说,“可我想做点什么。”
因为她不再信仰神,所以褪下了衣装,可是她依旧信仰着善,甘愿做一个伪善者。
……玛歌修女失踪的几个月后,她突然背起行囊。
“我想去找找她。”尤尔娅这样对尤裡卡说。
对方对于她的行为觉得匪夷所思,只是问:“那我怎么办?我可是付了你钱的。”
“您可以跟我一起走,我们去旅行。或者……”尤尔娅笑了,“您等我几年?我会回来的。我只是想找找故人……米路、玛歌修女、珍珠……我去看看。”
“你找那个女人干什么?”
“看看她,带她回来。我有了自己的房子,虽然不大,但是我想让她住进来。还有米路和珍珠……”
尤尔娅说:“找不到也没关系。这只是我自己图个心安而已,你不用太在意。或许她已经死了。”
“你说得对,那如果她死了你该怎么办?”
“不怎么办。找不到我就回来,不过……”
“尤裡卡先生,等我死了,”尤尔娅·马尔蒂说,“能请你把我研磨成骨灰,撒在随便哪儿吗?谢谢你。”

露西娅到教堂后,生活就好像重新掉了个个儿,又像野马停足走进牧场,骤然发现黑夜重新成了黑夜,白天再一次充当白天。该这样说:从前的生活总是颠倒过来的,吸血鬼猎人追着他们昼伏夜出的猎物跑,到了日上三竿才想起倒头就睡。好猎人总在夜里精神矍铄,眼睛明亮,天晚渐冷时,工会里头不让点篝火,从齐马蒂来的好猎手们就上外边去,烧热了酒,大笑大叫,到后半夜,有人对视几眼,提枪而走,这一场才偃旗息鼓。
第三礼拜堂的一个尖顶立在整个圣伯拉大教堂的最东边,贴着亮闪闪的瓦片。到了冬天,太阳刚刚好升到那尖顶上,就是钟表转到第八轮的时候。天一亮,石头棱柱边缘最先开始发光:露西娅就在这时候醒来。她是圣伯拉大教堂里最早睁开眼睛的几个人之一。早些年,吸血鬼们喝下西比迪亚的血,走进教堂里,还老在夜间走来走去,近年来也学人类追着太阳作息,圣伯拉的夜晚又静下去,只剩下些莽撞的脚步声与病房里痛苦的呜咽。露西娅有时候会醒得很早,早到天还没亮,能听见血流在腹中空响。她就安静地躺在床上,等待那顽固的炎症消退,再慢腾腾地起身,穿过长廊和中庭,把食堂的炉子烧得通红亮堂。——圣伯拉不缺孩子的身影,年纪还小的见习修士,病房里的孩子,年轻而还未禁食的圣女,孩子们早上最不顶饿,于是她握缰绳的、盐和血渍过的手也习惯和进灰面粉和水中。加入黄油,加入奶,还要放进鸡蛋、更多的糖,秋季,树叶远离叶脉的边上开始打卷,供应给百合花广场的烘烤饼干从一早开始准备。
一个影子。一个漆黑的、佝偻的影子出现在厨房门口。巡夜人的脊柱永远往下垂着,像被提灯压弯了的枝梢。赫里伯特·罗根在圣伯拉巡夜的第十个年头,有一只钟在他的脑子里滴滴答答地走,一遇见光亮就响,把他赶回十尺见方的蝙蝠洞里。他是在圣母像和大书库间逡巡的沉默石像,阴影里的守密者,只在晨昏线中露出一点影子。罗根神父在这座教堂中负责巡夜这件事显得十分奇怪:大教堂不需要巡夜人,毋论教会猎人中分明有更好的人选。他大约每半年会遭遇一起夜间亡故,罗根神父便临时替那个可怜灵魂祷告,一星期里又有一两次,将太阳落山后还赖在礼拜堂和书库中的孩子们遣送回他们该在的地方。仅此而已。这是一份简单到乏味的多余工作,没有别的用处,好像只是把他从太阳底下扫进夜里。
这时天快亮了,露西娅正在厨房里灵活地忙碌,她可以同时看着窑炉下的火苗、煎锅里正在焦化的白糖与发酵面团,自然还能留意罗根神父到场。于是露西娅和善地问候:“你今天来早啦。”
那团黑色的影子动了一下。一只提灯的手从袍子里伸出来,把近乎烧尽的马灯放到一旁,里面只剩微弱的火。罗根神父说:“我带来了羊奶。”
他袍子下的另一只手提着一只铁桶,落到案台上,沉闷地“咕咚”一声。露西娅探头看了看,紧接着回答:“请等一下。”
她提走那桶羊奶,归置到厨房另一头去,而罗根神父点点头,走到角落里,在那儿安静地待着。不过几分钟,露西娅打开窑炉,这里面顿时充盈了一股蓬松的热气,像被阳光炙烤过。她往罗根神父怀里塞进去一块热气腾腾的面包和半个烘烤过的土豆,并拍拍他的胳膊。罗根还是垂着头。他们年纪相仿,男人脸上的皮肤因年龄增长而皱巴巴地垮到了嘴角,露西娅就比他更容光焕发,脂肪在安逸的生活里取代了紧实的胳膊,就像糖取代盐,使她看上去愈发丰腴和和蔼。过了好久,罗根用着沙沙作响的嗓子,对露西娅说:“今天会有太阳,是个晒豆子的好日子。”
“噢。”露西娅愉快地说,“谢谢,罗根神父,我正要问。”
罗根提着他生锈的灯走了。太阳已经越过第三礼拜堂的尖顶,将它慷慨的光亮倾斜到圣伯拉的中庭。他小心避开一切阳光照射的地方,沿着墙根的阴影前行。先是鸟儿在叫,然后是水声与人声,这座大教堂正在阳光下醒过来,显出它活泛的那一面。
罗根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了门,拉上窗帘,在黑暗中吃掉还冒着气儿的面包和土豆,就了点水。他呆呆地在桌前又静坐一会儿,才咯吱、咯吱地艰难起身,摸到床沿,背对着门和窗和衣躺下,在太阳高悬之前,沉沉睡去了。
赫里伯特正往灯中添油。他的手哆嗦着,油泼洒到灯的外侧,又顺着玻璃弧面淌下去,在桌面上滴成一小滩。门在这时候响了,“笃、笃”两声,赫里伯特慌忙放下手里的东西,为门外的人开门。敲门的是修女玛歌,她手中握着一盏蜡烛,深黄色的烛光照出她紧抿着的嘴唇和深凹的眼窝。赫里伯特急促呼吸了几次,紧紧攥住门把,右手指尖探了几次,摸索到提灯手柄,沙哑地说:“玛歌修女,我正要出门。”
“把灯放下吧,罗根神父。”
门外的修女说。她的视线顺着赫里伯特肩膀和胳膊落到马灯旁的那一小滩油上,停了一会儿,才开口道,“今晚不用再巡夜了。安纳托会代您的班。请跟我来。”
……他们一前一后走到长廊上。玛歌握着蜡烛,一团温吞的光,只照亮些空气,聊胜于无。但是她走得很快,就像这条路早已经熟稔于心,赫里伯特缀在背后,没带上那盏最后也没能添上油的提灯,佝偻着,他很高,却整个被拖进黑暗里。他的喉咙抽动着,滚了好几次,没能蹦出一星半点的词句来,只是一些粗重的呼吸,在黑夜里一起一伏。倒是玛歌在行走到第二礼拜堂时静静开口了,她露在外面那只金色眼睛在烛光中快要化成黏稠的琥珀色,直直盯着前方,那里是一团漆黑的夜晚。
“您应当知道,”她说,“艾莉夏·罗根没有提出别的愿望,在神圣成年前最后一个夜晚,她希望待在父亲身边。”
“……感谢您,玛歌修女。”赫里伯特脚步虚浮,梦游般地跟在背后,滞了很久才如此开场,声音小而远,他像是遗忘了语言和文字,正一个从梦里把它们找回来,于是说得很慢,语法也有些颠三倒四,声音又压得很低,像是自言自语,
“您也许不知道……我和阿莉……从南方的村落里来。她没有见过她的,母亲。我那时候是个……是个记信员,到秋天,也在,田里替别人做算数。阿莉跟着我,坐着骡子拉的车,赶一场接一场的丰收。”
“我知道这些事。”玛歌沉静的声音在前方响起,“我进入教会前曾在乡下生活,往山里赶蜜蜂。阿莉说你们也跟着蜂农追过花期,还说您会用草叶编织动物。”
“是吗……是这样。我以前会,她喜欢您。”赫里伯特的声音快起来,仍然细小如蚊呐,“我还会看一些天气,一些天气,靠云的形状和风的方向。不是每次都准。阿莉喜欢这些,但是她总看不准。于是我们打赌,她什么时候猜中了天气,而我又走了眼,我就去集市上为她买一件礼物。”
“您是个好父亲。”
“不,不。我总是说话不算话。直到阿莉十一岁的时候,我攒了些钱,赶集时买了一双新鞋给她。她穿着那双鞋,从集市上一直走到家里,到家时,我才发现鞋跟磨破了她的脚。她难受的时候从来不愿意向我喊疼,也不向我说我没有见到的时候,她在教堂里做什么。”赫里伯特的声音放得更低,双手在袍子下交叉握紧,他哀求似的问,“但是我在她的手臂上发现了那些痕迹,玛歌修女,您告诉我,你们对她用过什么?那些东西……会疼吗?”
修女骤然停下脚步。赫里伯特一并停下,他们一前一后凝固在走廊中。时间静静地从他们身边流过。
好一会儿,才有人有了动作。玛歌目不旁视,将手里的蜡烛抬高一些,艾莉夏·罗根那小小的名字镌刻在烛光下流动着金色的线,她冷冷道:“到了。”
他们推开门,这响动才被屋内的圣女留意,里面发出小小的一声惊叫。“爸爸!”女孩儿从房间里扑出来,赫里伯特连忙从玛歌身后向前了几步,从黑暗里接住她。屋里有灯。阿莉和他的面孔被火光照亮了一半,他的后背留在黑暗中,修女静静站在那里,和她的烛火一起。赫里伯特就着火光仔仔细细看着女儿的脸,阿莉的面孔像他自己——像他,而不是早早就去世的母亲,她的眼角下垂,颌骨上本应该有个圆弧的轮廓,却因为久未进食长出不合理的棱角。她的声音和脸上都没有喜悦,下嘴唇很薄,咬得发白。阿莉紧紧抓住她的父亲,握住教士袍的下摆揪成一团,紧接着,从他肩上往后看,怯懦地说:
“晚上好,玛歌。”
“晚上好,阿莉。”
玛歌仍秉着烛光,眼中阴晴不定。她确认过那女孩儿已经看见自己的问候,转过身去,带着她的烛火安静地退进夜色中,很快便远去,再看不见了。阿莉在父亲怀中,突然爆发出一声响亮的啜泣。
她大哭起来,像一场来得又急又快的雨。雨水打穿顶棚、打落树叶,把微弱的火苗打成一阵烟。赫里伯特慢慢跪下来,让她的脸颊靠着自己的,手掌放在瘦削的背上,一下、一下地拍。
雨下了半夜,过午夜后渐渐小了。赫里伯特替她擦干净脸,掖紧被角,艾莉夏侧躺在床边,细小的胸膛随着抽噎颤抖。她的父亲坐在一旁。
“爸爸,”女孩张着眼睛,看着火,眼泪流进枕中,眼睛里倒映着父亲,“我好害怕,我好害怕,爸爸。”
赫里伯特握着她的手,在潮湿的手掌中写道,
“睡吧,阿莉。睡吧。明天会是个好天气。”
赫里伯特·罗根带着他的女儿刚到圣伯拉大教堂时,城下町只有如今规模的一半大小。百合花广场还没有种满百合花,尖耳朵们走在城里还被人戒备。第二年天气转凉,圣伯拉忽然开始筹备舞会,几位修女和神父彼此问候,找不到提案者,就去问阿尔文·伊诺克,阿尔文只说不是他的主意,又朝他们眨眨眼睛,说,这样有何不可?阿莉那时候还听得见,她既不会跳交际舞,也不会唱歌,好在那时候圣女不在舞会前献歌,人也少,她只管拉着父亲跳进池子里,跳他们会在田野里跳的踢踏舞。一开始只有城下町的居民会来,后来他们种上铃兰湖的种子,百合花广场就成了百合花广场,教会猎人的身影也出现在舞池中,渐渐从北方来的尖耳朵客人也悄然造访。玛歌为圣女们挑了一支圣歌,只是阿莉几近失聪,不再有机会学了。
罗根神父已经十年没有走进人群中去。醒来时,天色从窗帘下遗落了一小截。罗根迟缓地眨着眼睛,嗓子干得发疼,投影在桌面上巴掌大的橙黄色光晕告诉他又逃过一个白天。巡夜人醒来后第一件事是给生锈的提灯添油,只有那灯亮着,他才看得见路。教士袍的袖子被挽到手肘,同一件事做了十年,他稳稳当当地让油流进灯芯里去,窗外,夕阳也正流进山坳里。
罗根推开门。
从七点开始,十一点、两点各添一次油,礼拜堂、病房、书库、马厩,最后是墓地,巡夜人沿固定的路线在大教堂建筑群里逡巡,十年如一日。这天圣伯拉大教堂也睡得较平常更晚,不断有陌生客人造访西比迪亚的会客厅,礼拜堂的圣母像注视着他们经过,低垂眼睛,只差流下眼泪。厨房里的甜香福音随着修女和神父们走动而四处撒播,人多起来,就显得巡夜人不再像夜里游荡的幽灵,只是人群里最孤僻的那一个,他匆匆地从他们身边经过,袍子漆黑得像浓夜染色,里头跳着一小撮火光。
添完第一轮灯油,教堂里的人就少了。
巡夜人登上礼拜堂东侧的一座钟楼。这座钟楼比阿尔文·伊诺克发表演说的那一个矮一些,登楼门前长了很深的杂草,鲜有人来。好几年里,巡夜人在这儿只遇见过波赫约拉,今夜见到了第二个。年轻人从钟塔上往下俯视,单片镜的链条垂到肩上,他所面朝的方向能看见百合花广场的一角。罗根登上石阶的响动惊扰对方,年轻人收回目光,他们彼此对视,巡夜人举起灯,端详他片刻,问道:“阿洛伊斯?”
被他叫做阿洛伊斯的少年人怔了一会儿,“您还记得我?”他这样说,又想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而巡夜人已经把灯放下了,好像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后来去病房里看过你的名字。夜晚里发生的事情不多,过去多少年也一样。”
“我如今叫恩斯特。”年轻人老老实实地说。他穿着教士服,圣徽垂在胸前,不再是住在病房里的孩子,而是行走在圣伯拉教堂里的一位年轻神父。巡夜人又登上几阶,站在他身边,即使佝偻着脊背,也比他高出一大截来。他是不是看得更远?恩斯特想道。
他们静静地站在那里,度过了夜晚中的一小部分。那百合花广场一角的光景连番变化,跳舞的人不断转来又轮走,像月光下一些交错的弧线。他们都戴着面具,即使正在跳舞,彼此也看不见面容。恩斯特只是远远看着。
巡夜人离开前问他:“你会加入他们吗?”
恩斯特犹豫片刻:“或许会吧。”
“那很好。”罗根说,“那很好。”
他垂下双手,转身走了,黑色的背影很快溶解在钟楼下的黑暗中。
第二次添完灯油,罗根遇见修女玛歌送圣女们回房间去。他隔着一条长廊看见那条明亮的队列,玛歌领在排头,也见到他,略微致意后错身而过。她这时候像守着羊群的狗。在十数位圣女中,罗根只刻意留意了缀在最后的一个。圣女艾薇已经十七岁,比其他同伴高出一截,她在今天将头发放下了,换了新的发饰、新的裙子,正在那队列的最末左顾右盼。巡夜人第一次见到——或者说抓到——这女孩是在马厩中。这倒是个不寻常事件。就像他与阿洛伊斯——如今叫恩斯特的神父提及,夜里发生的事情很少,少到巡夜人记得里面的每一桩和每一件。让孩子们回到他们该回的地方去也是夜间工作的一部分。他常在大书库和礼拜堂里抓到忘记日头落山的孩子,空病房也有一次,马厩倒还是头一遭。那女孩是切利人,嗓门很亮,用浓厚的口音向他解释她从房间里溜出来是为了生病的马匹,上一个照顾马儿的修女前些日子因故离开了,她知道如何不被马踢。她一口气连珠炮似的讲完,才讷讷地摸自己的鼻子,问:“你是不是没有听懂?”
“我农忙时也跑过切利,能听懂。”巡夜人说,“我过去有一个女儿,她和你一样喜欢动物。”
罗根目送着圣女的队列消失在黑暗中。等到他查看过马厩和第三礼拜堂外的花园里蓬勃生长的大蒜,绕回中庭时,里面响起了断断续续的圣歌。巡夜人在墙根处停住脚步,静静地聆听,那支圣歌已经接近尾声,末梢的一个音符消散后,一阵短暂的寂静充盈了中庭。
歌声再响起时,声音的主人唱起了一支切利小调。
罗根提起灯走过去。那个切利女孩放下了头发,着新的发饰、新的裙子、脚上的鞋也是新的,她在唱着田野和湖泊的切利小调中转着圈,跳一支不成样的舞。巡夜人打断这一切,艾薇小幅度地一抽气,显得前所未有地慌张。罗根弯下腰,握住她的一只手。
“我不告诉玛歌修女。”他在那只因为紧张而显得潮湿的手掌中写道,“那双鞋会磨脚吗?”
“不会。”艾薇很快又很小声地回答。
“不会吗?”
“有一点,”那女孩说,“可是我还想跳舞。”
那时月亮正升到半空。
巡夜人握着女孩的手,让她踩到自己的脚背上,而他踩着那支切利小调的节点。如果你在过去听过切利人唱歌,就会发现他们的歌声和腔调一样是饱满的圆弧,像稻穗垂在田埂上或是丰收节时月亮在井中的倒影。因此,他们的舞蹈也是一些圆弧,一、二、三、转一个圈。那时月亮正升到半空,中庭里一片敞亮,地面就像浸了水,巡夜人放在墙边的灯火也摇摇晃晃,显得微弱,又好似也在跳舞。
等罗根再次提起灯,月亮已经沉到塔楼后面,中庭又涌上一片轻柔的黑暗。艾薇重新踩进她的新鞋子里,脚跟只磨得有点红,没有破皮和流血。她亦步亦趋地跟在巡夜人身后,沿他和玛歌修女曾一前一后走过的路回到自己的房间。巡夜人在这条路的终点又成了一棵佝偻着的沉默寡言的枯树,枝条上挂一盏灯。
艾薇抬头望着他,眼中火光闪动:“晚安,罗根神父。”
“晚安,艾薇。”巡夜人也低声说道,“我想明天会是一个好天气。”


一个中秋节突发paro段子也要拿上来嘚瑟一下,是的,是我。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有分栏啊——想要paro分栏——)
=========
雷涅把头枕在向导的大腿上。
他一开始是有些犹豫的,他刚从四天没有合眼的战场上下来,向看起来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的神父摇了摇头。“有点脏。”他低声说,或许指的不仅仅是物理意义。
年轻的神父朝他微笑。“没关系的。”恩斯特说,拉过洁白的外袍在自己腿上铺平,甚至还邀请似地拍了拍,“这样您更舒服一些,不是吗?”
神父仰望着他,柔软的浅色眼睛里带着他所熟悉的、诚挚的恳求,就像是他才是那个请求帮忙梳理乱糟糟的精神世界的人。
雷涅无法对神父说“不”。于是他顺从地躺下来,打开自己,让神父开始他的工作。
*********
恩斯特行走在墓园里。
这不是他第一次走进雷涅的精神世界,也不是他看到的最糟糕的样子。情况不是很好,但也远谈不上糟,他知道这个哨兵足够坚韧,可以承受更多。但他不应该默默忍受这些,只要自己在场。
向导像个魔术师一样擦亮阴沉的天空,摆放明媚的、下午三点钟的柔和暖阳,撒下几缕点缀晴空的丝绵般的云朵。他抹去墓碑旁边横斜蔓生的杂草,唤醒新生的、带着露水的嫩草覆盖荒芜的地面。恩斯特一块块擦净那些静默矗立着的石碑,直到它们像打磨过的表面泛着柔和的光。然后他俯身,挨个在墓前放下一支洁白的百合花。放到正中间那块大理石的墓碑面前他犹豫了一下,换成一支鲜红的、开得正是最美时候的玫瑰,想了想,又配上一支娇嫩的、半开的粉色花苞,用缎带仔细地系好,轻轻地、端正地摆放在那里。
他无声地从雷涅的墓园里退出来,哨兵似乎已经睡着了,搁在他腿上的脑袋发出轻柔而均匀的呼吸。向导屏着呼吸——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以一种缓慢的、绝不会惊动哨兵防御机制的速度调节着他的感官,把听觉与触觉的阈值滑块往下拨动,低到尽可能的底线,低到周围的风声、簌簌的叶子震动的声音、偶尔响起的鸟鸣和远方沉闷的枪声都无法打扰他的安眠。低到哨兵无法觉察落到沉睡中的自己头发上的手指。恩斯特梳理着他的头发,就像刚才为他梳理精神世界里冗余的杂物,温柔地打开被血和灰尘纠缠的发结,捻去硝烟留在上面的痕迹。哨兵的头发和他给人的那种粗粝和严肃的感觉完全不同,它们细软而服帖地擦过他的手指,像山羊肚子底下柔顺卷曲的内层绒毛。
睡吧,哨兵。恩斯特把低语着的精神波长从指间轻柔地散发出去。你还可以再多睡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