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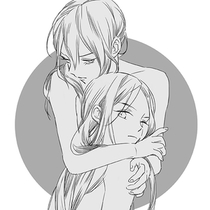
長谷部+宗三,嫌惡組,no腐向,腐向評論也NG,謝謝合作。
attention!雖然連ヘイト創作的へ字都算不上(當社比)但是會出現刀劍之間認真地互黑,何でも許せる方向け
==========================================================
进入视野的第一样东西,是僧衣的下摆。
他在朦胧之中觉得有些奇怪。谁会把僧衣垫在刀架下面?难道是他被放在僧衣之上了吗?但如果是那样的话,视野中僧衣与自己的距离又有些微妙地遥远。
如果能靠近些看看那袭僧衣就好了。
这么想着,视野中的僧衣就真的急速接近了自己。
“……?”
最先感受到的,是某种难以言喻的沉重感。然后是离自己很近的地方发出了一声钝响,某种从未经历过的不快感觉从视野上方缓缓扩散开来。僧衣的格子纹填满了整个视野,他花了好一阵子才明白过来,似乎不是僧衣接近自己,而是自己掉了下去。他静静地留在那里,等着听到声音的某个下人来把自己放回去,但就在这样等待的时间里,让人烦躁的不快感也一直在主张自己的存在。
不知等了多久,不远的地方传来纸拉门被拉开的声音。有人大惊小怪地叫着他的名字,是一个高亢得有些奇怪的声音。大概是哪里的小姓吧,他忍耐着完全陌生的不快感,静静盯着格子纹的一点这样想道。
“我还想说为什么过了这么久都不见新刀出来……宗三左文字你这是做什么呀!你不会是被衣襬绊倒了吧!?”
开门进来的小姓咋咋呼呼地说着一些意义不明的话,却就是不把自己捡起来。宗三左文字恨恨地抬起头,看到的却根本不是什么小姓,而是一只长相愚蠢的狐狸。
——……抬起……头?
稍微开放了一些的视野边缘可以看到无力地投在地板上的白皙手腕,他想凑近一些看看清楚,那手腕却朝他的方向自己弯曲了过来。
他眨了两三次眼睛,试着让那条手臂朝右边移动,手臂就真的有些笨拙地朝右倒在了地上。
“啊——……我知道了,刀剑男士里偶尔也会有像你这样的呢,刚得到现世的身体结果不知道怎么用……你等一下,我去叫近侍过来好了!还有你一直这样趴在地上脖子不痛吗?”
痛?
虽然不太明白,不过宗三左文字也模模糊糊地察觉到那应该就是指正在折磨自己的陌生不快感。他笨拙地用两条手臂撑在地上勉强立起上半身,一个动作停了好几次才做完。
……近侍?
终于从名为疼痛的不快感中解脱之后,他才有空暇思考这个熟悉的单词。
这样啊,是要叫人来把我再放回刀架上啊。
虽然狐狸的话里还出现了好几个没听过的词语,不过那对宗三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笼中的鸟儿……就算对牢笼之外的东西发生了兴趣,又能怎么样呢。
狐狸像是完全没注意到宗三的负面思考,还在兴高采烈地啰嗦。
“对对,说到这个本丸的近侍是宗三你也认识的人呢,本丸里有认识的刀剑男士在你也会过得比较舒服吧!”
狐狸说了一个名字,是宗三完全没有印象的名字。谁让他历代的主人都喜欢搜集名刀呢,宗三左文字怎么可能记得住那些十把百把地排列在一起的刀的名字。
狐狸走后,宗三一个人在略显狭窄的和室里等待了一会儿,能够自由活动新得到的手足毕竟还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以至于和室的门再次被拉开的时候,他不禁感到有些不快。
“审神者有事不在,所以由我谨奉主命前来迎接。身体感觉怎么样了?”
与纸门之外的阳光一同洒下的是一个温和有礼的青年声音,听起来似乎是有那么一点耳熟,但果然还是记不起来。宗三懒洋洋地将视线投向声音的主人,依次进入视野的是金红两色的刀拵,西蛮教士风的服装,端正的脸庞和温和的笑容,……紫色的双眼。
“……啊,呀,是你啊……”
宗三抬起衣袖掩口而笑,而后第一次听到了自己发出的声音。
“下贱的无铭刀。”
宗三左文字是真的对压切长谷部这个名字毫无印象,不过不是因为不记得,而是因为不知道。在桶狭间的战场上第一次遇到那把刀的时候,他还没有名字。无论是开战的号角吹响的时候,还是义元的头颅滚落在尘土之中的时候,宗三左文字都没有被拔出来过一次。如果是新的主人……他怀着这样淡淡的期待被从义元的尸身上拔下来,还未习惯那个年轻人手掌的温度就被扔给了一旁的小姓。
“磨短。茎表里刻上……「织田尾张守信长」和「永禄三年五月十九日义元讨捕刻彼所持刀」,就这样吧。”
之后他几易其主,一再被刻上新的印记,然而只有最开始的那个年轻人漠不关心的声音,深深烙在他的记忆之中。
小姓恭敬地双手接过他的时候,他第一次感觉到了那道视线。
从那时起就被信长佩在身上,不知沐浴了多少鲜血的无铭刀,依然保持着温和的笑容,看着他的眼神却还是跟那时一模一样,充满了嘲讽与轻蔑。
“有力气说话的话,就表示已经可以自由活动身体了吧。站起来,无用的装饰品。”
说起来,无铭刀的名字的前半部分宗三好像还是有点印象的,毕竟他得到名字的时候,宗三和他姑且还是侍奉着同一个主人。他已经忘记了那天的天气是晴是雨,抑或那个茶屋主人到底犯了什么过错,依稀记得的只有信长静静起身时传到自己身上的震动,无铭刀出鞘的时候也没有声音,雪光般煌煌生辉的刀身朝下挥去的画面不知为何看起来缓慢异常,像是一个毫无真实感的白昼梦。
一瞬之后,刀身上溅满了鲜烈的红色。
如果宗三在那时就有人子的身体,他一定也是会蹙眉抬袖覆住口鼻的。信长空挥了一下无铭刀,甩去不断滴落的血珠,没有名字的付丧神面无表情地站在一边,满身淋漓的鲜血似乎没对他造成任何影响。比起无关紧要的茶屋主人,信长似乎对爱刀的锋利更为关心,当天之内无铭刀就被赋予了名字,短短的四文字,既无雅趣也看不出一点文才,这样的名字还不如干脆就一直无名算了,你不这么觉得吗?——宗三那天难得主动跟无铭刀说话,也许是他刚好心情不错,也许是他很久没有近距离看过那么大量的血了。无名的付丧神……现在应该叫压切了,压切的表情微尘未动,只是轻轻抬起眉毛做出了一个勉强可以算是困扰的表情。
“无论名字如何,身为刃物只要能斩……敌人就够了吧?”
宗三到现在也不知他那句话究竟是有心还是无意。
听说给了无铭刀后半部分名字的,是他的第二任主人。远征归来的宗三走到审神者的房间前,听见无铭刀对审神者抱怨信长将他赏赐给连直臣都不是的家伙,擅自抱怨完一通之后话锋一转又请求审神者称他“长谷部”而非“压切”,连三岁小儿都看得出的本心。宗三站在纸门之外一动不动地听着他们的对话,指尖感受不到一点温度,想必脸上的表情亦然。
当初是谁说的,有认识的刀在就会过得比较舒服?
互为钢身铁骨的时候尚且无法理解彼此,何况如今这副连自己都不甚理解的人类姿态。
莫名其妙的不快感从身体深处沸沸而起,宗三伫立在廊下的阴影中许久,终究还是没能拉开那扇薄薄的纸门。
转身离开的时候,似乎又感觉到了那道令人厌恶的视线,他猛然停下脚步,门里传出的依旧是无铭刀与审神者疏松平常的会话。
数日之后,他与无铭刀同队出征,途中却遭到了名为检非违使的乱入部队奇袭。混乱的战场之中,碰巧身处同一个地方的两人自然不得不并肩作战。数不清是第几个敌人倒伏在地上的时候宗三抽回刀身的动作慢了一瞬,视野的角落似乎有什么以惊人的速度朝着两人中间直冲过来。
传入耳中的是衣袂割裂的声音,映入眼中的是长谷部脸上的新鲜伤痕。
“……哈哈!”
长谷部发出的声音,比起笑声反倒更像是渗满狂气的战吼。敌方打刀胸前的伤口喷出大量鲜烈的红色,全身溅满血液的青年顺着抽刀的势头已经回身冲向新的敌人,与此同时的宗三左文字则是抬起衣袖掩住口鼻后退一步避开了飞溅的血沫,两人的动作流畅得没有分毫冗余,仿佛他们从四百多年前开始就一直重复了无数遍这样的动作。
前进的一步与后退的一步,两人之间一瞬空开的距离,一如那个狭小的茶屋中鞘內的他与那道雪光的距离,遥远得近乎绝望。
只是如今,异族的野兽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发出厌恶的咆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