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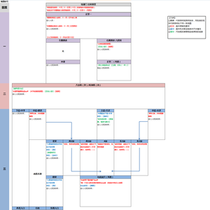



人家已经二章了我还停留在第一章……而且这次仍然还没有谈上恋爱……!(摔 我这么努力工作能涨工资吗东家……!
标题其实没什么含义,就是说中秋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 写得仓促,如有BUG或OOC请用力敲打我!
强行把中秋前和中秋后要交待的事都塞在了一起。
一般人称其为……过渡段(
前接:http://elfartworld.com/works/76077/
关联:http://elfartworld.com/works/81837/
流水账,只求交待一下必须交待的情节,还有情报传递什么的OTL
———————————————————————————————————
柳云岸一身风尘策马回到镖局,已是太湖之行三日之后,再过几日便是中秋。今年的三伏天刚过不久,天气仍然酷热难当。可这看起来温文尔雅的文士仍然穿戴得整整齐齐,斗笠摘下,竟是一滴汗也看不到。他前门刚下马,二虎已经笑嘻嘻地迎了出来。
“柳先生您回来啦。”
二虎接过马缰,又有点好奇地偷偷打量着这个上元镖局里最难捉摸的人,“柳先生,东家和总镖头让您调查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柳云岸一副“这事也是你能问的?”的眼神瞟了二虎一眼,看得他脖子一缩。但他嘴角带笑,也没多生气,“正要和他们说。那两位现在在哪?”
“应该是在里屋吧。您也知道,东家大病初愈,总镖头又是个爱操心的,总怕他累着伤又复发,没事总爱关在里屋不出来……”
“先生您回来啦!我想吃糖糕!”
“先生我想要纸鹞!燕子那样的!”
一阵脆嫩的稚声突地穿过院门,打断了两人对话,一个约摸七八岁的孩童窜过来,紧紧抓着柳云岸衣摆不放。紧接着一个接着一个,全都粘了过来。柳云岸出门并不多,多数时候都窝在自己房里不知捉摸些什么。可每每出门总会带回些糖葫芦,糕点,纸鹞,木刀木枪之类的分给镖局里的孩子们。久而久之孩子们也都知道这个会说故事的先生出门回来会有好东西吃,有好东西玩,都纷纷粘着不放。柳云岸也不恼,变戏法似的,笑着从马鞍口袋里掏出一个又一个小玩意儿。孩子群里时不时爆发出一阵欢呼。
“丹梅。”
廊下不远处一直看着这里的女孩偏偏头,似乎不确定院门口的那人在叫自己。直到对方朝自己招手,她才缓缓过去。
柳云岸从袖口里摸出一对银簪,道声失礼便侧身插入她两侧的发髻团子。那银簪不大,只比少女手指长点,十分纤细。前头用银丝与细黄水晶珠子串成一簇簇小黄花模样,被银叶子隐隐约约地挡着,活生生一对银敲珠串的细小桂枝绕在发髻上。他又退了一步,似是观望了一阵才点头温言笑道,“我看着这对簪子就觉得十分适合丹梅,又十分适合这个时节。果然是没买错。你且看看喜不喜欢?”
少女面露惊喜之色,摸着头顶发簪便奔去内屋找镜子。柳云岸一身礼物都分发完了,这才整整衣衫,进了内院。
屋内确实只有裘鹤假扮的李铭与刑远二人。为了尽量不出岔子,只要在镖局内这一身装扮裘鹤从不卸下,行事作风也与真李铭毫无差别。柳云岸也按当年的称呼,唤他东家。只是刑远小心谨慎,平日里无事并不愿意让裘鹤随意外出。这可憋坏了恣意逍遥的唐家小少爷,柳云岸敲门进屋时还什么动静都没有,待两人见到是也知道李铭真实身份的柳先生,裘鹤又恢复了那股百无聊赖快要打滚的模样。
“你就让我出去嘛。就一天!我都快被憋死了……”
另一个木头人冷冷的看了他一眼,并不说话。
柳云岸一看便知刚才又在争论什么……或是说,单方面争论什么。他也禁不住弯起嘴角,露出人畜无害的笑容,“关了这么多天,确实该出去散下心。不过装成李铭出去还是有点风险。不如就委屈小少爷,扮成女装吧?”
“女装……”李铭外表的裘鹤竟然没有反对,似是仔细思考了起来。柳云岸趁热打铁,笑得有如春风拂面,“就说是总镖头的远房表妹,这几日来临安游玩,便住在镖局里的。”
这一次木头人冰冷的视线落在了他的身上,“镇远镖局的事怎么样了?”
说起正事柳云岸收了笑容,撩起衣摆坐定,趁着端茶的功夫定下心神暗地里运起心法。他本就功底深厚耳聪目明。这时下里顿时灵台澄亮,屋里屋外有多少活物分别是些什么,处于什么方位都听得一清二楚。待确定没人偷听了,这才点头道,“我先从我做的结论开始说起吧。镇远镖局的失镖案子,应与我们无关。”
李铭正敲着核桃,听他这么一说被勾起了兴趣,好奇地探出身子,“这怎么说?”
“镖局保镖,一般有三知,这是既定的行规。三知,知镖,知托镖人,知收镖人。少了这其中一样,镖银和护镖风险都必然成倍增加。这是镖局行当的默认规则。而有两样不知的,多半是生死镖,也就是十有八九会出事的镖。”
“你是说……”李铭的眼睛闪亮亮的,“镇远镖局这趟镖,是生死镖?”
“嗯。”柳云岸端茶又喝了几口。在外奔波了几天,又是顶着午后烈日回镖局,他是真有点渴了,“我打听过了,镇远镖局这镖只知道是要送往清河郡王府的,押送的是一个雕花木盒子。四寸见宽,约八寸长,盒内有什么全然不清楚。拖镖人不肯告知身份,只说事成有一千五百两白银。”
“一千五百两……”刑远那一向没什么表情的脸上也出现了一丝波动,“这一个雕花木匣子,竟值得三万两白银?!”
“而且还不知道盒子里到底是什么物事,也不知托镖人身份。”柳云岸放下茶盏,端正脸上浮出一丝冷笑,“两不知的三万两生死镖。这不出事反倒要算是稀奇事了。”
他顿了顿想起什么道,“我在路上也遇到了银鱼卫。官场又向来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时只怕皇城司也在关注此事了。”
刑远沉默着,似乎在想什么。李铭偏着头,仍有疑问,“这也不能说明和咱们失镖的那事无关?”
“嗯,确实如此。”柳云岸此时笑得颇轻松自在,“但也没法证明有关。这就是关键。”
“我倒是能猜出先生几分意思,”刑远低声道,“两次失镖,托镖人,镖内物事,收镖人均不相同,更莫说受镖镖局不同,劫镖人也不一定相同。这要说有关,凭现在的信息也太少了些。”
李铭点点头,砸碎一个核桃,“那这桩事就算是解决咯。暂且放到一边。”他说着把碎壳连带果仁都推到一边,又拿过一个新的核桃。三人又据最近临安动态交换了一些情报,这才各自告辞歇息不提。
过了中秋,原本大家都盼着能休整个几天。这时原本各处也都在忙着家宴团员,本就没什么生意上门。镖局里更是各个都悠闲自在,懒洋洋的。谁知没几天便来了位带着小孩的男子投贴拜门。当家的带着总镖头与柳云岸迎了客人,又聊了好些时候这才送走客人。只是那个孩子却留下了。
送走那拜贴的刘平,柳云岸冷眼看着那孩子跟着打杂仆役走远,这才拦住李铭与刑远二人,低声道,“东家,总镖头,务必屋内一叙。”
李铭与刑远对视一眼。这先生平日里温文尔雅,少有如此严肃之时。顿时二人也紧起十二分神色,三人径自进了李铭日常起居的后院主屋。这里一面墙外是刑远的住处,另一面墙外则已贴着空无一人的西厢房,少有人来。
“我便开门见山了。”柳云岸确认四下里无人靠近,这才视线落在已落坐的两人身上,“二位对先前这事,如何看待?”
刑远首先沉吟道,“我看过那字条,确是李铭当年笔迹。”
柳云岸微微一笑,这笑得几乎可以称得上微微一哂了,“只要稍许掌握些诀窍字条便可以作假。莫说他人,便是柳某自己有心仿字也能仿个七八分。”
李铭在椅子上盘着腿。私下里他不用那么绷着,多少也就自在了些。这动作多少给他增添了点孩子气,“先生觉得那刘平有假?”
“不好说……”柳云岸下意识地打开折扇又闭上,这多是他思虑时的动作,“我刚拿言语刺他,那反应倒是……若真是傲气,反倒简单。只不过又不像是能做捕头的性格。若是装的……那倒要更仔细着他。”他停顿了一下,又微微摇头,“现下丢的镖、东家的‘事’、还全都云里雾里的一团,本就怕横生枝节的当口,人员变动最是忌讳。更不用说是这样证明不了路子的来人。我之前并不想收这个孩子,便是此意。”
“他毕竟只是孩子。若是字条是真的,怎能让李铭背了诚信。”
邢远仍是面色冰冷,惜言如金。此时若外人见了,只怕都以为他对柳云岸拒绝孩子这件事多少心怀怨恨。但镖局里熟识的人都知,他一向如此面冷心热,言语间只是叙述,并无不满。
柳云岸笑了一声,眼角却不带丝毫温度。这模样无端给他平添三分寒意。“我知晓总镖头的意思。一个孩子能做的毕竟有限,翻不出多大浪花。可孩子能做的事情,也不比实际上少多少。”
他折了折了手中扇,又道,“那孩子拿着李铭的手书,若是真的,保不准他手上还有什么能让东家露馅的东西。若是假的,那他的来历目的于我们而言更是两眼一抹黑。届时若他有些什么动作,我们再想补救可就晚了。”
“先生意思,是还要把这孩子送出去?”
“那也不用。”他舒了口气,那点寒芒便转瞬即逝,复又平和。“我现下里仔细想想,柳某在厅上虽是试探,但其实也是冒失了。总镖头的善心之举,反而弥补了我的过失……这以退为进,说不准倒是好事。”
李铭……裘鹤与邢远相视一眼,都猜不出面前这人到底在沉吟些什么。但柳云岸只是打开折扇复又合上,似乎没有解释的打算。
“为什么?”裘鹤终于耐不住好奇问道,他虽然少经磨练,心思单纯,可人却聪明。话一出口他也便意识到问题所在。若手书是真的,镖局力拒孩子于门外,与往日李铭作风并不相符,更说不通。若手书是假的,李铭又怎能分辨不出?若有心者顺着这条“不正常”的线索继续追查,只怕多少会意识到镖局有什么变故。柳云岸见他自己已经明了,朝他笑笑,便转了话头。
“事到如今,如果这两人没有什么计谋当然是最好不过。但如果在谋筹什么,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总镖头答应把孩子接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想好了。东家——”柳云岸转头朝李铭模样的裘鹤道,“你须尽量避开和那孩子同处一室的机会——尤其是要避开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他盯着主位上的小少爷,眼里一点精光闪现,全然不似平日里春风拂面,“小孩子倒不怕他对东家有什么身体上的不利,但是最得防着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揭穿你。这于镖局,于现在的东家,都是最大不利。”
“这我有分寸,不消你们嘱咐。”李铭笑嘻嘻地靠回椅子,手里还剥着个核桃扔给柳云岸,全然没有个东家样子。可当年李铭本人也便是这般十分没架子的模样,谁也没说不好。
邢远也道,“那孩子的房间我已经派人安排好了,远离前厅和主屋。李铭平日里和我在一起,不会有多少接触的机会。你用不着担心。”
“嗯……”柳云岸仍有思虑,“至于孩子本人,让大人监视反而不妥。好在镖局里收留的孩童甚多,也不打眼,我会让五儿他们留神,这倒不是最打紧的。”说罢他又转向另一边的邢远,速度之快使宽大白衣旋出一个圈儿,“总镖头,人我们虽已经接下,但来路我们还是一定要搞清楚。那刘平的家底,来路,和那孩子关系如何,都得查个水落石出。这且不说,那孩子的来历,其父母和东家当年是否有过交情,最好也得弄得清楚明白。其实这个才是最主要的,知晓了这个主动权就在我们手里。”
“刘平和孩子的底细我已经派人去查了,不日应该就有回报。”邢远靠着椅子,永远是那副雷打不动的冷面阎王模样,“但那孩子父母和李铭的交情,只怕难。”
“柳某清楚。”柳云岸点头道,“若查到了,这当然是最有益的。可这只怕也是最难查证,也最不宜去查证。”他冷冷地加强了‘最不宜’的语气,言语间似乎又在盘算什么,“所以我们只能放到最后,实在要查,也只能暗地里旁敲侧击,决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為了騙催稿的人相信無形催稿最為致命從而逃避催稿所以我不得不在約好的時間里更新了……但從結果看來我還是被催稿了啊!?這不對吧!?這麼勤勉怎麼可能是我,下一篇我一定要拖,姓嚴的有種就把我臉朝下按在鍵盤上%^U%&FIGH^*&$CV%RI^T&*$VRBT*&I&F%VT*^(I^G&
前情提要:http://elfartworld.com/works/75772/
上元鏢局:http://elfartworld.com/works/72112/
老闆:http://elfartworld.com/works/73271/
=======================================================
“你好了没啊?我先回去啦。”
他好像听到小伍的声音。对面的草丛窸窸窣窣地响了一阵,小伍拿手巾擦着嘴站起来,一脸的苦闷。
“嘴里恶心得紧,我先回去讨杯茶水漱漱口。你也快点啊,不然要挨徐哥骂的。”
等等,不要回去。等一下。
他张开嘴想叫住越走越远的小伍,可胃里又是一阵翻江倒海,逼得他再次蹲下呕吐了起来。
他好像跑在城外的土路上。说是路,其实只不过是行人和车马在荒草地里反复碾踏出来的痕迹而已。从来没有人整修过的小道被踩得尘土飞扬,不一会儿就弄脏了新浆好的官靴。他已经在这条路上跑了不知多久了,眼前金星乱撞,嘴里也难受得很,但现在还不能停下。要再跑快一点才行,要赶快回去才行。
虽然他已经忘了自己要回去哪里。
他好像站在那个客栈的后院门前。他看见徐捕头和小伍他们就在院里,但他始终不敢进去。要是这次又吐出来了,可就要丢脸丢大了。他使劲握了握刀柄给自己打气,这才壮着胆子朝院里喊道:“头儿,我回来啦!”
徐捕头只是背对着他摆摆手道:“回来做什么,你就别进来了。”
听徐捕头的口气,倒像是看不起他刚才跑出去呕吐的样子。他心中有气,也忘了害怕,大踏步就朝院里走去,却总也走不近那扇咫尺之遥的院门。他焦急地叫着“为什么呀?头儿!”一边拼命想往院子里走,徐捕头慢慢转过身来,官帽下的脸像隔着雾气一样模模糊糊,怎么也看不清楚。
“因为我们就要被雷劈死了啊。”
他也不知道惊醒自己的是雷声还是自己的狂叫声,可能两者皆有。
客房的门虚掩着,昏黄的油灯在地上投下一长一短两个影子。有孩子的声音从门缝里断断续续地传来,不知是在跟谁说话。
“是,对不起,给叔叔添麻烦了……我家哥哥只是做噩梦了而已……是,不碍事的,谢谢……”
说话的孩子又赔了好几次罪,长些的影子才慢慢走开了去。孩子退回房间关上门,飞奔到他面前摸着他的额头轻声叫道:“平哥,不怕,已经不打雷啦。”他觉得有点尴尬,干笑两声起了身,孩子马上给他递上一杯热水,大概是他睡着的时候出去新倒的。这下刘平真的只有苦笑了。
“元宝儿乖。哎,真丢脸,都不知是谁在照顾谁了……”
距离益州城外的灭门惨案,已经过了两年。王家客栈十二口人,一夜之间全被乱刀砍杀,去查案的捕快们也不幸被天雷劈死,刘平是当时的捕快里唯一一个活了下来的。这案子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流言交飞,端的是满城风雨。
——只是没有人愿意真的去查。
刘平还记得自己走在益州城的街上,路旁的闲人围在悬赏榜前窃窃私语。“听说整整起出了二十一具焦尸呢,十二个被砍死的,八个捕快和一个去认尸的,烧得都分不出哪儿是梁木哪儿是人骨了,天可怜见哦……”“但说是天雷引火呢,也不知是哪个作了什么孽,……”
闲人说到这里就像卖关子一样低下了声音,刘平也没兴趣再听下去。实际起出的尸骸是二十具,因为八个捕快的其中一个就走在他们身后。刘平却只是懒得纠正那人。
死者长已矣,被留下的人还是要活下去。刘平去找了那个一夜一日之间就失去了双亲的孩子,袁家不算大富大贵,倒也家境殷实,不知从哪赶来的许多亲朋好友挤满了小小的灵堂,有些哀哀哭泣,有些已经开始争吵谁来领养小天保,穿着丧服的天保只是面无表情地站在墙角,却没有一个人理会。刘平站在灵堂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混合着线香和金箔臭味的污浊空气之中,他注意到只有一个男人把孩子抱进怀里,牢牢捂住了孩子的耳朵。
啊啊,最后会是他来收养孩子吧。刘平记得自己当时漠然地这样想道。他猜得也的确没错。男人是袁辉的表弟,早年跟袁辉一起做过些生意,算起来也不是什么近亲,收养孩子的时候似乎颇费了一番周折。一开始互相推托的亲戚们一听说有人站出来了,又换了一副脸色,有的说不放心一个没家没室的大男人养孩子,有的说这人无事献殷勤,怕是对孩子有什么坏心。听说最后是孩子死死抓着表叔的衣襬不肯放手,那男人也说除了袁氏夫妇的遗物,袁家的家业他一分不要,这事才算完。
之后刘平常常去探望小天保,可能是想确认那男人是不是真的有信守诺言,也可能只是想求个心安。两年的时间不长不短,大概也就刚好足够他跟孩子混熟,所以接到那男人的死讯的时候刘平几乎是连跑带跌地冲进了那男人家里,像两年前一样身穿丧服的孩子一声不吭地紧紧抱着一个小小的锦盒,直到看见刘平才终于小心翼翼地递了出来。
“表叔说,有事就去找这个人。”
稚嫩的声音里听不出鼻音,刘平愣了一下,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说什么,只好笨手笨脚地把天保搂进怀里,牢牢捂住了他的耳朵。
隔了一瞬,温热的小小身体才终于轻轻颤抖起来。
锦盒里只有一张已经发黄的纸条,上面写着“他日袁辉袁兄有事之际,李某定当倾力相助”,落款是上元镖局的李铭。听说上元镖局是临安府的老牌镖行,李铭可能是里面的镖师,虽说也是个危险活计,但要是能把孩子寄养在镖局,倒也不失为一个好去处。至于刘平自己,在益州也没什么亲人,决定带孩子去找李铭之后自然也就辞了捕快的工作。两人一路车马颠簸,到得临安来,已经是八月十七。找到上元镖局倒是没费多少力气,投了帖之后过不多时就被引到了内堂,看来这李铭在镖行内地位还不低。等了一盏茶的工夫,三个男人走了进来,中间那个一脸胡渣的朝他打个揖道:“客人久等了,在下便是上元镖行主人李铭。”
主……主……主人啊,难怪接帖的小厮和引路的仆役都一脸郑重。
刘平还愣着,天保已经走到李铭面前双手递上了那张字条刘平还愣着,天保已经走到李铭面前双手递上了那张字条,李铭长相豪快,说话也是一般的豪爽,看了字条略一沉吟就问起了袁辉的近况,刘平这才慌忙解释前因后果。好容易说完了,三人却都陷入了沉思,像是各有各的难事,又隔了一会儿,左首的白衣男人首先发话:“恕在下无礼,敢问我等如何得知刚才这些话是真是假?就算是真的,足下又如何证明这孩子就是袁先生的公子?”刘平早在路上就已经预想到李铭可能会生疑,只是没想到对方会如此直白,也不知是不是自己哪里礼数不周惹怒了这位先生,只好硬着头皮道:“在下所言之事全是有案可查,若是先生不信,大可去查个仔细;至于这孩子,李先生应该也是见过的……”话未说完,天保扯了扯他衣袖,小声道:“李先生没见过我。平哥,他们不信,我们走罢。”
这几句话声音不大,却不带一点感情,怎么听也不像是由一个十岁小儿说出来的。三人听了这话都有些面色不佳,李铭更是一会儿瞄瞄左边,一会儿瞄瞄右边,好几次想说什么又吞了回去。刘平当捕快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各路镖师没少见,在部下面前这么畏畏缩缩的镖行主人却也是新鲜,他性子本又直爽,心里想什么,脸上登时就现了出来,当下撇了李铭一眼,牵了天保朗声道:“元宝儿说得对,上元镖局是名门大家,原不是我们平头小民能高攀得了的。他们不要这个信字,我们走便是了,无谓白白受人冷眼!”一则他年轻体壮,毕竟又在衙门当过差,二来上元这几人的态度也着实让人不忿,这几句话说得中气十足,连门外的僮仆都忍不住探头探脑地偷看。刘平自出了这口恶气,也不管对面三人脸色了,拉着天保抬脚想走,一直在李铭身后沉默不语的冷面男子却不知何时已经挡在了自己的去路上。
“……慢。无论过去有没有约定,孩子送到门前了,难道要把人扔出去不成。”
后面那一句像是对李铭说的,声音比天保更冷淡几分,却丝毫不惹人生厌。这下可大出刘平意料,转头看时那人神色仍是木然,一双眼睛却是看着低头不语的天保。
这个人有很好的眼睛。
那边李铭沉思片刻,终于像是下了决心一样开口道:“说得不错。刘兄,适才是我们失礼了,如若刘兄还不嫌弃,孩子就寄放在我们家罢,只是不知刘兄意下如何?”
“啊……这……我才是,虽然刚才说了那些气话,但要是李先生肯收留天保自然是再好不过……”
情势转变得太突然,刘平边吞吞吐吐地回答边偷眼打量那个白衣男子,只见他两眼微闭打开了折扇轻轻摇着,看来是既然主人发话了自己也不打算再追究的意思。虽然刚才他是真心带着天保要走,但一个大男人带着孩子连落脚处也不大好找,老实说,孩子能留在镖局真是放下了他心头一块大石。刘平思及此处,不禁朝李铭和那冷面男子连声道谢,免不得又和李铭相互推辞一阵,完了抬头一看,天保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院子里。上元镖局的院子和别家院子无甚差别,只是多了一大群鸽子,鸽群中一个杏黄衣衫的少女正忙着给水喂食,少女看见天保来到院子里也丝毫不停手上动作,只是笑着招呼一声,几只胆大些的鸽子便扑簌簌地飞近了天保,端的是憨态可掬,就连天保也难得小声笑了起来。刘平小心翼翼地出到院里,却还是惊飞了几只鸽子,不免有些难为情,只好搔搔鼻头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跟天保说了结论,天保只是点点头,倒是那喂完了鸽子的少女听见他说的话欢叫了起来。
“你以后要住在这里吗?你福气了,这里可是很好的!我叫丹梅,你叫什么?啊,这些鸽子都是我养的,你以后可以随便找它们玩!你几岁了呀?要叫我姐姐吧?哎呀,你住在哪间房?”
少女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刘平和李铭在一旁看着也只有苦笑的份。天保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朝她鞠了一躬。
“那……元宝儿,平哥走啦,等平哥找到活干再来看你……呜哇!?”
“平哥不一起留下来吗!?”
话没说完就被天保一把扯住衣角差点跌倒,但天保自己似乎比刘平更震惊。大人们愣了一愣,冷面男人——李铭刚刚介绍说他叫邢远——便蹲了下来,轻声问道:“怎么了?”
他大概是想伸手摸摸天保的头,只是天保极自然地往旁边闪了一闪,小手却还紧紧攥着刘平的衣角。
“啊……我……当然不能一起留下来啊?没事的,元宝儿不用怕嘛,这儿大家都是好人,又有鸽子,平哥隔段时间也会来看你,你看……”
“……死的……”
“啊?”
因为没听清楚天保说的话,所以刘平自然而然地也蹲下来,这才发现孩子的嘴唇抖得厉害。
“……因为我是丧门星,所以平哥走了,会死的……!”
不光嘴唇,声音更是抖得厉害。说出来的话也支离破碎,除了刘平以外,大概没人听得懂他在说什么吧。
表叔出门收账,再也没回来,母亲出门迎接父亲,回来的却只有两人的死讯。而父亲——,刘平想起那妇人哭倒在地的样子,面容和声音都已模糊,只有那句话还活生生扎在他心上。
出门做生意的父亲,只不过是不想打扰他们母子安眠。
——都不知道是谁在照顾谁了。
可他毕竟只是十岁的孩子。连邻里街坊那些风言风语的意思都还不能完全明白,只知道因为自己是“丧门星”,所以离开自己的亲人全部都会死。
刘平有些僵硬地抓住天保的肩膀,喉咙里像刀刮一样猎猎生疼,他的声音大概比天保抖得还厉害,但想说的话毕竟是磕磕绊绊地说出来了。
“元宝儿,你听着,平哥不死。平哥找了工作,就在镖局旁边租个房,元宝儿每天来看平哥,不来的话平哥就去看你。平哥……平哥不死。”
最后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又重复了一遍三岁小孩都不会信的空洞承诺。天保定定看着他,眨了两三次眼睛,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平哥不会死。
……当然也不能饿死。
刘平离了镖局,在街上转了半天,偌大个临安城居然就是没有一处招人。他又不熟地理,不知不觉间走到了没什么人气的小巷里,慌忙想要出去,三转两转反而迷得更深。转眼白日西沉他才找到一家开着门的店铺,日落后这些小巷更显错综复杂,还兼不知从哪吹来的阵阵阴风,饶是他胆子再大,看清眼前店铺的招牌也不禁吓了一跳。
“哇,怎么是个棺材铺子!……等等,招工……”
店门前贴的招工告示似乎已经受了多年风吹雨打,几乎连字迹都快要看不清晰。他以前是公差,对这类俗称的晦气行当倒是没甚避忌,只是不知人家现在还招不招工,不过管他呢,试过不行再算。刘平主意定了,抬脚就往店里走,可巧店主正一副闲得无聊的样子坐在店面纳凉,一听他来应聘连挑也不挑,三下五去二写了契约画了押,这才上下打量起他来。
“哎呀,真是难得有人来这种店见工,年轻人骨架不错啊。”
虽然说法有点奇怪,但毕竟是在夸自己,刘平也不多推辞,挠着头笑了起来。
“我也就这副身板比较结实了,您有什么粗重活尽管吩咐,关老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