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女因强制回忆而崩溃昏倒在地,这让安德烈略有不满。他咂嘴道:“什么嘛……这样就不行了吗?”
但是也正因如此,这段过于悲惨的记忆使得魔法瓶中的液体更加明亮,血红的光芒从瓶盖的缝隙处泄漏出来,将黑暗的房间映得通红,宛若盛夏火烧云一般,美丽却恐怖。
安德烈拿过魔法瓶仔细端详,表情中有一种说不清的满足感:“不愧是史上最强的魔法少女,魔女与人类孕育的奇迹,愿望有多强烈,怨恨也就有多强烈。如果使用了这样的精华液作为魔法的催化剂,恐怕会发生不得了的结果吧,黑白颠倒,阴阳逆转,想想似乎有点可怕呢。”
不过,恶作剧似乎做得有些过头了。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是混沌魔女,只要维护好平衡就可以了,但天平两头究竟是什么,不是他所在意的,而姐姐也不会因此生他的气吧。
想到姐姐,安德烈抬头望了望墙上的挂钟,已经七点了,是时候回家了,姐姐一定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在等着他。于是他摸出自己的钥匙,将其插入虚空之中。
然而他还未有下一步的动作,他的身后响起了一个男人惊恐的声音。
“你是谁?!”
安德烈并不惊慌,平静地转过身去,那位魔女猎人就站在那里。安德烈像是早已料到一般无奈地笑了起来,懒洋洋地叹息:“啊啊,真是不走运啊。”
猎人看见对方的面容在阴影中浮现,不仅倒抽冷气:“安德烈大人……”
“那么我该怎么称呼你?费什先生?不过那也是你欺骗我姐姐编造的假名吧。那么……主人?”安德烈突然爆发出谜一般的大笑,让猎人完全摸不着头脑。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猎人说着蹲身扶起少女,此刻少女浑身冰凉,只有微弱的呼吸才能证实她生命的迹象。
“只不过用了唤醒记忆的咒语而已,没想到她就承受不住了。但也正因如此,我才能确定魔法少女的愿望原来还能这样反向利用。”
安德烈优哉游哉地将魔法瓶放入衣袋里,正打算离开时,却听到了扣动扳机的声音。他不禁笑了起来,像是陪孩子玩耍似地漫不经心地举起双手:“喂喂……你胆子还真够大的啊,竟然敢对混沌魔女开枪。”
“如果敢伤害她的话,就算是混沌魔女我也会下手的。”猎人严肃地道。
安德烈见对方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便也收起笑容,露出了不耐烦的表情:“哈?稍微和你玩了会过家家,你就已经开始忘乎所以了吗?”
猎人不语,只是举枪瞄准安德烈。枪口死死追随着对方的一举一动,附魔猎枪的枪身散发出淡淡的金色,印刻着的铭文也随之亮了起来。
“我说了,我是认真的。如果你不用魔法治愈她精神的创伤,那么我就会开枪。”
“治愈?那是我姐姐干的事。”
“所以这就想跑吗?”
话音落下,扳机扣动,子弹出膛。
“真是不像话。”安德烈低哼,朝飞来的子弹抬起右手,轻轻念动咒语,子弹瞬间调转方向,朝猎人头颅极速旋转飞去。
猎人轰然倒地,墙上时钟秒针也只走过了一秒。
安德烈望着流到脚边的鲜血,又看了看昏倒在猎人尸体边的少女,连连叹气:“哎,你这个做奶奶的,没有教育过孙子要尊敬长辈吗?真是太失望了。”
算了,还是回家吧。安德烈打了个哈欠,转身走入虚空的大门之中。没有什么比姐姐做的晚餐更能吸引人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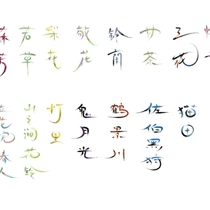

あおい坐在微微发凉的石阶上,双手托腮,静静目送日光的逝去。
此时暮色已降。深蓝,绛紫,橙红,就这样深深浅浅一层层地将天空晕染过去,最终在远方黛色山脉背后悄无声息地隐了踪迹。群鸟归林,灯烛亮起,又是一个夜晚的来临。梅月时,寒冬仍未舍得收走衣袂,春意薄寒,更何况是黄昏,但这对于本就生活在冰冷海中的あおい来说算不了什么。
她并没有要回去的意思,只是依旧默然坐着。
那天医生问她,是不是很喜欢蓝色,她自然而然地笑着点头答应,医生也只是淡然地回了一句:“这样啊。” 但就是这一瞬,あおい意识到,她的回答带着一份天然的残酷。医生无法视物,自己之于蓝色的热爱也许或多或少对他造成了伤害。她张了张嘴,想对他说对不起,但却犹豫着最终什么都没能说出口。
如果能让医生看到自己心爱的蓝色就好了啊,最好不仅仅是蓝色,世界上所有的颜色都想给他看。あおい是这样想的。
她记得有一位姓白金的画师,能够画出让目盲者感受到的光绘。今日从医生家里结束工作后,她便特意兴致冲冲地绕了远路去找他。然而白金先生告诉她,这种光绘不仅无法绘制出蓝色,而且对全盲的人毫无作用,这让她心里一下子落了空,失落地一句话也说不出。
“对不起啊,没法帮到你的忙。”白金先生惋惜地说。
“啊……嗯……”あおい勉强挤出了笑容,连连摆手道:“哈哈,没事啦,白金先生不用道歉……是我自己想得太简单了。让盲人视物什么的……哪有那么容易嘛。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好了。”
紧接着,像是要转换心情似的,あおい轻轻叹了口气。她环视白金的画室,不由地感叹道:“白金先生好厉害啊,不仅会画画还能用画帮助到眼盲的人。像我就不行啦,除了会放电好像就没什么别的本事了呢。”
“但是你不是同时在小森花屋和黛医生那里打工吗?你一下子帮到了两个人,不也很厉害嘛。”白金安慰道。
“说是这样说啦,但我果然还是想要有强大的能力啊,比如像别的夜明神一样‘啪’地一声发射出火球来呢。”
白金被少女夸张的手势逗得笑了起来,而あおい也冲破了方才略显忧郁的心情,回报以灿烂的笑容。
笑声过后,白金略显深沉地道:“我们……还真是有些相像呢。”
あおい眨了眨如海水湛蓝的眼眸:“诶是吗?大概因为我们都是萤者吧。”
显然あおい没有理解白金话语的含义,亦或者她并未意识到自己潜藏的那一份心情。白金也没有去深究,只是用温柔的微笑一笔带过:“啊,也许是吧。”
有些事情,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但是很快地,从白金那里出来后,之前的失落又重新回到了あおい的心里。她一步步往回走着,大概因为是有些累了,步伐要比平日要慢得许多。
她看见路边石阶,便随意坐下休息,托着脑袋呆呆地坐着,毫无目的地望着远处的山脉,从夕照直到月出。
看来白金先生这里是没有路子了,治愈眼盲这种事那位流星的夜明神也恐怕无法做到,否则这世间早就没有盲人了。为什么会如此执着于让医生看到东西,あおい恐怕自己也说不上来。她只是觉得医生那过于平静的面容,反而会让她想为他去做些什么。但是她又害怕医生会觉得她自作主张,多此一举。
“啊……那要怎么办才好呢。” あおい微微嘟起嘴,烦恼地叹了口气。
然而,似是回应一般,空中不知从何处传来细碎轻盈的铃声,簌簌坠落在她的耳边。あおい下意识地回头向上望去,只见石阶尽头站着一个十岁模样的小女孩,黑发红衣,像是来自他世。那个女孩用独眼朝あおい投来她从未见过的神色,没有孩童特有的稚气,只是那样平和地凝视,让她莫名产生了一丝敬畏感。
“回去吧,萤者,真正的夜晚就要到了。”女童这样说道。
“你是……”
话音未完,狂风骤起,吹得あおい睁不开眼。但也只是短短一瞬,风止住了,女童也消失不见,只剩下石阶两旁的竹林依旧摇曳着,沙沙作响。一切恍若幻觉。
半晌,あおい这才回过神来。她抬头一看,发现此刻自己正站在朱红色的鸟居之下,而鸟居额束上正明晰地写着永暗神社的字样。鸟居如蓦然出现的鬼魅一般,这抹红色在浓的化不开的山中显得异常突兀。自己究竟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她丝毫记不得了。但这也让她顿时清醒了过来,时间已经很晚了。
あおい整了整被风吹乱的头发与衣服,借着自身散发的柔和光芒走下石阶。是时候回家了,希子还在等着她。
天空中的暖色已尽然融化在夜中,只有西边天尽处还倔强地留下一道残红,似是光明与黑暗撕斗中白昼落下的不甘的血迹。
繁星起,弦月升;影祸终至,长夜将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