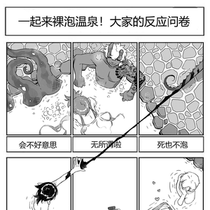“那样的话……请使用我吧。把我当作道具使用就好。”
“我果然还是爱你。”
……ID: K-N-19E0
——启动成功
再一次睁开双眼,K-N-19E0在原地怔忡片刻,才将充电器的接口从身上拔掉。噩梦中伴随着凄苦台词飞舞的血迹还在脑中挥之不去,如果可以,他真不想每天都依靠这种方式被唤醒。
时间还不到程序规定好的起床时间,睡眠用的舱体紧紧闭合,贸然推开多半会触发警报引祸上身。他透过玻璃向外窥去,一片黑暗中,圆柱形的容器整齐排列,舱门顶部表示正常运行的指示灯以同一频率不断闪烁着。不久前K-N-19E0也是这些人的一员,每天按时醒来,根据随机一种设定好的算法决定今天的行为,日复一日不断磨炼自己、摒弃不良习性,直到能够成为符合社会需求的合格人类。只有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前往外面世界的通行证,才能真正开始体验文学资料里所提到的“人生”。
K-N-19E0此前从未想过这套流程有什么不妥,这是埋在骨髓里的核心设置,定义无限接近于本能。按部就班的每一天里,他过得平和又快乐,没有比这更舒适理想的生活了——如果那个人没有出现的话。
“陪我聊两句,什么都好。”
特殊联络频道里收到一条消息,发信人是L-C-629F 。为防止被他人察觉到异样,K-N-19E0关闭了外部显示功能,打开一个只有自己看得见的窗口:“早上好。”
“哪里看出来是早上了?”
L-C-629F回复得异常快。看样子,她现在似乎非常空闲。没等K-N-19E0回话,下一条信息又紧跟着追加进来:
“不觉得毫无意义吗?明明这个监狱里白昼从不会降临。”
是又在焦虑了吧。K-N-19E0迅速得出结论。据他所知,白昼是上个世纪前常用的单词。随着人类大面积地迁移到新的居住地,现在世界各地都用稳定性更高、更便于控制的人造天体取代了原本的太阳与月亮。换言之,无论是在被L-C-629F称作“监狱”的实验都市之内还是外,白昼都不可能以资料记载中的方式完整再现。
“只是客套的寒暄而已喔。而且,所谓的早上只是指代4点至10点的这段时间,现在时间是5点36分,我想我的判断应该没有错。”
对话暂时中断了。
“L-C-629F?”
“我在。刚刚去调时间了,我体内的钟迟了约两分钟左右。”
“这样啊。”
与K-N-19E0不同,L-C-629F有个别部件受到损坏——尽管K-N-19E0推测她是故意为之。因此,当其他人在休眠期通过充电用线缆传输数据、接收重要指令或是校准参数时,L-C-629F完全不受控制。这也是她为什么不用像K-N-19E0一样必须通过特殊影片阻碍控制系统就能保持独立意识。
“是说……如果能换个再温和点的影片就好了。”想到这里,K-N-19E0忍不住抱怨起来。
“道理我早就和你解释过了吧?因为初次骇入你的系统的就是这支影片,内里留有缓存记录。当再次看到同一影片时,系统就会默认按照上一次的路径执行逻辑判定。”
“我知道啊——虽然知道,但每天每天都从噩梦醒来的滋味可不好受……”毕竟每晚休眠时被破坏的控制系统都会修复,这也就导致K-N-19E0需要不断重复切断——修复——切断的过程。
“你就再忍一下吧。反正,马上要到「去月球」的日子了。”
——月球。
房间里突然亮起一盏指示灯,大抵是有早起的人醒来了。来不及发送回复,K-N-19E0心虚似的匆忙关掉所有窗口,闭上眼佯装沉睡。
「月球」是二人之间约定俗成的代替词,并非有什么浪漫的典故,单纯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
“你是说……我们两个的意识都脱离了■■■■?”
初次被修改内部逻辑,K-N-19E0努力消化着L-C-629F话语里的巨大信息量,半晌慌乱起来,“那得立即挂个急诊看看才行……”话没说完就被对方带着渗人笑意的一瞪吓得噤了声。
他手足无措地连连后退,屁股几乎要落出长椅的边缘。见状,L-C-629F大大方方贴了上来,主动抱上K-N-19E0的臂,姿态宛如鼓足勇气热情求爱的少女。在外人看来,这或许是会让人会心一笑的青涩场景吧。L-C-629F的脸颊甚至微微泛着红,言语里倒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换一种说法吧。你的程序就是我修改的……嘘。”她竖起一根手指抵上他的唇,“我知道这违反规定,但你不觉得那本身是有问题的吗?”
被封锁住行动的K-N-19E0缓缓眨了眨眼,半天才找到继续对话的渠道。他打开特殊通讯频道,意念发送了一句,“是吗?”
“……。”
L-C-629F却没有了下文。
难道说是不太会用这个专门为配对者双方提供的特殊联络频道吗,K-N-19E0心想,他今天也是第一次有机会用。正打算把使用说明也发过去的时候,视野里突然冒出一句,“你想■■■■吗?”
“唔。”
“我是说。”
“■■■?”
K-N-19E0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说起来,刚才他自己说话的时候,语音功能也出现了原因不明的噪声过大的错误,看来不是偶然。
“这跟你先前说的「违反规定」有关吗?”他猜测。
“你呢?K-N-19E0你又是怎么想的?难得获得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不使用一下试试吗,像是想想你还受■■■■时……啊又来!呃,之前的所作所为的意义之类的。”
“意义什么的,不就是为了顺利通过考核取得认可……”
“那是谁的认可?又是以什么为标准的?”
自带的资料库里没有详细记载这些,K-N-19E0不得不连接局域网检索相关关键词。
“规定上是说,只要能证明和匹配的搭档互相成为彼此挚爱,就能被承认作为合格人类生活下去。而这一决定是基于几百年来逐渐跌入谷底的结婚率与生育率,为了更好传承祖先寄托的悠久传统而出台的措施。”
“嗯。”
“没有更多可公开信息了……这有什么问题么?”
一直以来不都是这样的吗?K-N-19E0困惑了,他看出自己的回答并不是L-C-629F想要的答案。
“那判定挚爱的标准是什么呢?” L-C-629F 再次重申了问题,“资料库里的文学作品中时常把它描绘成圣洁而又难以捉摸的东西,变现手法各不相同。明明是不可名状之物,在这里却可以轻松裁定……不觉得奇怪吗?”
“唔,可能是有一种资料库里没有收录的手段吧,为了防止有人作弊从而破坏测试的权威性与平衡性,才刻意不加入的吧。”
K-N-19E0的推论合情合理。在这里生活的所有人都知道,当恋情成熟,搭配的二人就可自主申请鉴定测试。只是,参加测试的人向来有去无回。
不难想象成功的人是获得了作为人类被承认的资格离开了,未合格者则作为训练失败的残次品回收。这并非是效仿生物学上的死亡,要说的话,更像是时间倒流——让测试者回到刚出生的状态罢了。也就是说,所谓的合格人类其实也需要考核成熟的思维方式与行动轨迹,以保证在投放入社会后依然能正常运行。保密鉴定测试的内容,想来也是为了预防测试者针对测试寻找捷径,导致偏离原本的目的潜移默化地下降了品质的状况吧。
想到这里,K-N-19E0忍不住扫了一眼L-C-629F。如果部件受损是偶然事件而非原本的设计,那格外看重个人意识的L-C-629F应该非常害怕鉴定失败吧——不像自己,无论多少次都能重生——原来如此。
“你是担心无法通过测试吗?放宽心啦,只要好好培养感情,总会有办法的……初始训练资料里也这么说喔。”
“……。”
L-C-629F又沉默了。她一把松开K-N-19E0,起身抱住胳膊来回踱步。K-N-19E0不明所以,耐心等待须臾才察觉到对方口中念念有词。
“……光是切断总控制还不够吗。这样的话……就算是初始化完的新生人类,依然自带被定义完整的逻辑回路……不太妙呢,不该这么轻率地告诉实情的……”
“请问,自带完整回路有什么问题吗?” 他忍不住出声发问。
“……。”
这是短短几分钟内L-C-629F第三次愣住了。她转过脸瞪大双眼望着K-N-19E0,茫然与恐惧在她脸上不断交替,很快又如海潮退去只留下平静。这会儿K-N-19E0对于“动脑”这件事已经有点熟练了。
“那个,你是不是不知道同组的成员会有一些特殊权限,比如刚才的频道,比如……我可以听清你的每一句话?”
这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在控制面板找到输入输出项设定,然后扩大音频的接受范围,K-N-19E0就能轻松捕捉到身为搭档的L-C-629F的音频输出内容。他顺手检索了一下,发现这貌似是过去因为风与电车等噪声阻碍情侣顺利发展的几率过高而专门设计的贴心功能,不过没能来得及说出口。
因为在那之前,L-C-629F忽然靠近抓起K-N-19E0的衣领,然后吻住了他。
为了更逼真地模仿过去的生物在身体接触时会影响彼此的激素以达到爱意增长的效果,人类在进化中也增加了类似连接双方感官的功能,本质上是数据的相互传输。
自第一次的吻以来,他们时常不分场合地亲吻彼此,见缝插针似的向外发送闪光弹。只有K-N-19E0知道那些吻缠绵却不带温度,每当拥人入怀时视野中总会跳出一个红色的确认窗口。按L-C-629F的话来说,本身语言受限制、对话也总是难以顺利沟通,那不如就使用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吧——也就是向K-N-19E0传输她自己的数据。
拜此所赐,K-N-19E0这才逐步认同了L-C-629F的想法,用「去月球」的说法替代「逃离」也是在这时约定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解。
随着身体一次又一次交叠,思绪一次又一次相连,K-N-19E0不得不在身体里多创建了一个目录专门管理关于L-C-629F的一切。尽管成功的希望渺茫,他还是尝试尽可能地模拟L-C-629F的思维,试图能够跟上她的想法。
而这终究都是徒劳。当信息整齐归纳完毕,其中的漏洞才愈发明显。L-C-629F传输给自己的内容并不连贯,显然是故意隐瞒了些什么。即使K-N-19E0用自己的逻辑将其修补串连,呈现的结果也如拗过一次的铁丝崎岖不平。K-N-19E0仍然记得初遇那日一闪而过的惧色。从一开始他们就不是可以互相托付后背的伙伴,恰恰相反,他是不小心按到过她命门的人。
如果我表现得无害,L-C-629F是否就会放下心防?如果我更可靠一点,L-C-629F是否会愿意向我倾诉更多?资料库中没有记载百分百成功的案例,K-N-19E0只能小心翼翼地尝试。他总是尽全力配合着L-C-629F,毫无保留地奉献。到手的筹码全都放走,收到的指令统统照做。她想控制他,那他就做个听话的提线木偶;她想吞噬他,那他便成为兽的饵食。他从不在收到“正在连接不明设备,是否阻止”时犹豫,毕竟每一次接受都是多一份了解,都能在“靠近L-C-629F核心”的道路上跨出前进的一步……
冥冥之中,他感到这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事。可若细究为什么,连K-N-19E0自己也说不清。
出发去月球的期限就在懵懵懂懂中接近了。
L-C-629F最终还是决定用通过测试的方式逃离这里。过去的时日中,他们以约会为由头调查了实验都市中几乎每一寸可能存在出口的区域,结果都一无所获。
“所以才要换方法喔。”
说这话的时候L-C-629F正在借用图书馆设备查询资料。虽说现代人几乎人人都配有内置资料库,但为储存量与运行速度考虑,内置资料库会自动舍弃最低频率使用的无用信息——眼下L-C-629F在搜寻的是过去的新闻报刊。
K-N-19E0注意到她停下了翻页的动作,显然是找到了目标。不过L-C-629F并没有主动与他分享信息的习惯,于是K-N-19E0厚着脸皮凑了上去。
“监控故障?你找这个做什么?”
“稍微有点在意的地方呢……找了一下发现果然如此。”
“在意的地方是指?”
“频率。监控故障发生的频率。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类似的报道,尤其是在今年的7到9月间特别常见,不觉得频率有点高了吗?”
K-N-19E0从L-C-629F手中接过图书馆的平板——这似乎是为了显示藏书的浓厚底蕴才特别安排的复古设计。好在K-N-19E0是擅长使用这类旧设备的机型,很快就举一反三掌握了多窗口比较并对比数据的功能。
“去年和前年……甚至再之前也有差不多频率的记录呢。也就是说,这里还有其他也像我们一样……”
“不是喔。”
L-C-629F干脆利落地否认了K-N-19E0的推测,眉毛拧了起来:“你怎么会认为防范严密的监狱会放任这么大个漏洞不管,默许他人三番五次的搞破坏?”
“那?”
回答他的是L-C-629F转回桌前的侧脸。
或许突然有什么想法了吧……K-N-19E0试着替她找出解释。他再次低头看向平板上显示的统计数据,又反复对比了几则故障新闻与相关处罚,终于发现其中被通报批评的测试者型号几乎都是同一人——准确来说,是同一型号的不同版本。
“原来如此,是设定?”
就像K-N-19E0比起其他人,ACGN相关的亚文化资料库格外充沛,而L-C-629F则是执行力与工作能力都很出色的类型。每个型号的人类都被预先设定了不同的性格与特长,恐怕“骇入监控系统”就是那个型号的人提现性格与特长的方法吧。换言之,这是被允许的违规行为。
特殊联络频道的窗口跳了出来,是L-C-629F发来的图片文件。“多亏之前四处乱跑了呢,我把已知有监控的地方都标出来了。”她说。
“排除法啊……”
K-N-19E0 总觉得这个伎俩有些既视感,不过他没说,转而望向填满笔记的地图。眼下只有执行鉴定测试的区域还是一片空白。
参与鉴定测试的申请在两天后被批准了。办理申请手续的时候, K-N-19E0曾提出“要不要多观察一阵子再做决定”,但L-C-629F似乎认为继续拖下去只会得不偿失,翻译一下大致就是:
“虽说迄今为止我们想去月球的计划还没败露……可之后呢?已经确认过没有其他出路了,再拖下去也不过是增加不必要的风险。”
直到二人进入测试区域,K-N-19E0才开始猜测,是不是其实打一开始就没必要监管测试者的设备情况。因为——
“欢迎来到鉴定区域,首先请将插口接入正确的位置。欢迎来到鉴定区域,首先请将插口接入正确的位置。”
空无一物的纯白房间,合成的机械的女音重复两遍指令,紧接着连接线从天花板降了下来。K-N-19E0扯住其中一根,在接头的侧面点开操作说明。匆匆扫过几眼,他反射性地看向L-C-629F,面露难色。
“你是不是,没办法使用这种接口……?”
L-C-629F缺少一部分部件,这是一把双刃剑。在能够获得清醒的独立意识的同时,L-C-629F无法直连实验都市内的大部分设备,所以自己才总是被差遣。
“未确认到设备,是否需要呼叫管理员协助?未确认到设备,是否需要呼叫管理员协助?”
久久没等来响应连接的设备,机械女音友好地提出解决方案。若是迟迟没有连接,恐怕管理人员早晚会注意到这边的异常吧。K-N-19E0转身迈向已经闭合的大门,试图寻找其他退路——
“等等。”
然后他被拽住了。
与K-N-19E0相反,陷入困境的L-C-629F本人则慢吞吞收回阻拦他的手,顺势用指节缠绕住鬓边的发。漫不经心似的,她打量着那两根传输线,尔后又像是用视线追逐着只有她能看见的蝴蝶、不经意掠过K-N-19E0才停了下来。
“虽然我其实不太想这么做呢……”她说,“不过也没办法了。”
L-C-629F微笑着凑上前,这展开让K-N-19E0感到似曾相识。来不及在脑中检索已发生过的案例,下一秒,他被失而复得的拉力带动,坠入一个柔软的怀抱。月见草的香气在鼻腔内馥郁,这让K-N-19E0回忆起最初的亲密接触,然后又是千百个大大小小的吻。而就像是要验证他的预感一般,L-C-629F踮起脚,将K-N-19E0的脑袋掰下来一点,随后用唇印了上去。
这一定,又是理性与痴迷交叠、然后岔开分向两路的重蹈覆辙吧。只是说明已经不再必要, 因为L-C-629F正在将自己的神经网络完全拷贝传输给K-N-19E0。不知过了多久,进度条才刚刚过半。或许是疲惫了,潮热的吐息从唇齿间泄露,热度随着渐远的距离流逝。于是K-N-19E0将手扣入L-C-629F的发,加深了这个吻,让连接变得更紧密了些。
身为爱好ACGN的机型,K-N-19E0的身上被设计了许多方便连接不同娱乐设备的插口。不仅如此,他内部也提供了充足的容量支持设置多个模拟机。每当接收到来自L-C-629F的资料时,他总将它们归类到一起,闲暇时也曾试图用这些数据还原L-C-629F的思维模式(最后因为资料不足而以失败告终)——未曾想,今时今日竟然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更新完设置,又简单试验了一下确保能够成功运行,K-N-19E0解除遮掩接口的迷彩,撩起右耳后方的头发示意L-C-629F帮忙依次插入两条数据线。
根据说明,所谓的鉴定测试实际是让线缆另一头的控制者调用测试者体内的神经网络运行测试。测试一共分为五组,全部通过即可判定为合格,更具体的测试内容则作为保密项不公开。虽说也可以通过检查被调用的情况反推,但K-N-19E0光是支撑两组程序同时运行,身体就已经精疲力竭,实在分不出神。
K-N-19E0闭上了眼。
迷迷糊糊间,他感觉自己做了个梦,梦中的K-N-19E0正与L-C-629F肩靠肩蜷缩在冰雪砌成的小屋。彼时K-N-19E0还不知道L-C-629F身上的香气究竟是什么名字。而他们紧紧相依,也只是因为只有依靠这样的角度,才能避免被外面的监控器摄入。
对了、对了,这不是梦,是真实发生过的现实。那会儿他们才刚认识不久,去月球的计划也刚刚开始策划,假装约会时也不够自然,只能聊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假装热络。他还记得当时的自己对月球的形容提出疑问,比如“月球上不也和这里一样吗”,或“那边的监视网也很严密吧”,毕竟是重要的人造天体。
“嗯…………不是那个月球啦。”记忆里,L-C-629F忙碌之中不忘抽出手摆了摆。末了,她又重新捧住面前的雪团——看起来是在做一只兔子,“是在那之前、被人类舍弃的真正的月球。”
“真正的月球?”
K-N-19E0重复一遍,没能在内部资料库里找到相应的词条。
“嗯,虽说在上个世纪之前,月球上的尘土对当时的人类来说是致命的物质。但进化到我们这一代,身体的机能比起当年完善了不知道多少倍,说不定有一试的价值——不过这都不是最主要的。”
L-C-629F没有把话说完,K-N-19E0已经猜到了答案。
“那样的话,其他被舍弃的天体也可以吧?”
“你已经下载好新的资料包了啊?真方便呢,随时随地连着母数据库的家伙。” L-C-629F一眼看穿K-N-19E0的小动作,“是啊,其他也可以喔。”
那么,如果月球上没有容身之所,你就会继续漂泊、直至找到下一个目的地吗?K-N-19E0没能把问题问出口,似乎当时的对话就是这样戛然而止的。但现在……他或许能知道答案。
关于外面世界的介绍影片在测试结束后自动开始播放。考虑到无法亲自观看的L-C-629F只能由自己转述信息,K-N-19E0一直耐心看到片尾才切断了连接。
“结束了吗?”
听见K-N-19E0拔掉插头的动静,L-C-629F从房间的另一头转过脸。在她身旁排列着两个直筒型的装置。K-N-19E0不记得之前房间里有这样的东西,看来是在测试期间……或是结束之后才刚刚出现的。
“干得不错呢,了不起了不起~”
趁着K-N-19E0观察装置的当口,L-C-629F兴高采烈地揽住K-N-19E0的肩,借力伸长上身,嘉奖似的揉乱了K-N-19E0的发。她应该是非常期待这一刻吧,毕竟去往月球的机会近在咫尺。“喷——”的一声响起,仿佛在邀请他们进入一般,传送装置缓缓打开舱门。
只要通过那里,一切就都将结束了。K-N-19E0心想。他拉住正欲转身钻入其中的L-C-629F。
“怎么了?”
“……稍微,有点话想说。”
“哎,是要告白吗?”
L-C-629F夸张地做了个惊讶的表情,眯着的双眼毫不掩饰调侃的意图。K-N-19E0被她逗乐了,露出一点苦涩的笑意,点了点头:
“对啊。”
“……。”
仿佛蒙上了晨间的雾霭,L-C-629F的神情瞬时变得阴晴不定,令人看不真切。K-N-19E0笑意不减,强装镇定的外壳下大脑飞速运转。
“你呢?L-C-629F。这么多天了,你有稍微变得喜欢我一点吗?”
“这个嘛——如果你看了我最后发给你的数据,应该也已经知道了吧?” L-C-629F将抱着的双臂环紧了些,以问题回答问题。踌躇在她脸上停留一会儿,转眼就被残忍的怜悯带过。
“说到底,你对我的爱只是设计者给你的设定,并非出于你自己的意志。既然如此,我是否爱你还重要吗?”
“……说的也是。”
推算运行结果的模拟程序恰到好处地赶上了。
以为话题告一段落,L-C-629F转身离去。没走两步,她就被K-N-19E0再次挽住,从背后紧紧拥入怀中。当数据传输已经不再需要,拥抱可以重新获得温度吗?L-C-629F失语般侧过脸,K-N-19E0顺势亲吻她的耳廓。他终究无法将实情全盘托出,只能在最后做一次任性的决定。
“你说得对,我确实不知道最初我是否是凭借自己的意志爱你。但我想,现在我一定比那个时候更爱你了。”
他温柔地注视着怀中的女性,哪怕深知视线与视线已不再可能相连。
“要是可以做减法,你愿意把那份差额……当作由我个人意志而产生的爱意吗?”
L-C-629F没有回答,K-N-19E0也早已明白自己是等不来她的回答了。他哀叹一声,稳稳接住如睡着般瘫软在他臂弯里的女性人类。有几缕发丝在下坠的途中落在了面上,K-N-19E0轻手轻脚地捻起,替她梳理至耳后。
然后,他伸手绕到L-C-629F腰侧,找到方才已经按过一次的位置。
他当然知道再次按下将会发生什么。
L-C-629F从来就不是善于编程、具备齐全的信息科技知识的型号,这一点在日常也有所体现。即使最初能成功骇入K-N-19E0的系统,长久相处下来,K-N-19E0才醒悟那多半是靠临时恶补、运气外加实践获得的经验的混合产物。若是涉足更加专业的领域,难免会有疏漏,怎可能与设计出实验都市体系的人在同一位面上抗衡。
这也不能归咎于L-C-629F预测失误。又有谁能想到,这座实验都市确确实实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普遍意义上的出口打一开始就未曾设立。之所以放任监控漏洞百出,想来大抵也是因为没有严密管理的必要吧。
但离开的方式是确实存在的。测试结束后,机械女音就对如何转移数据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是的,转移数据。似乎是为了实验考虑,都市内为测试者提供的躯体都是由成本低廉的可回收材料构建而成,无法支撑更长远的使用。于是当一轮测试结束,完善的“意识”就会输出嫁接到材质更好、更加高性能的崭新身体上去——而自动修复自然是必备功能之一。
K-N-19E0深知日夜与噩梦作伴的滋味,简直就像是附身于牢狱,束缚终日如影随形。且不说外面的世界是否还有更多类似■■■■的手段时时刻刻监测每个个体,若从物理上破坏设备也变得不再可行、自由行动的空间也一再缩小,到了那个时候,L-C-629F还会追逐她的月球吗?
K-N-19E0已经能够推算出她的答案了。
他打开自己的核心控制面板,事到如今再将L-C-629F从他的神经网络中剥离已经太迟了。这个世界既然注定只有笼牢,不如就释放灵魂,逃到连笼牢也无法笼罩的遥远地方吧。
K-N-19E0俯身,最后一次亲吻怀中的爱人。
——异常
——异常
——数据销毁成功
“……愿你能在永恒的梦中抵达真正的月球。”
——记录终止
=====
stls说让我们互相放飞自我那我就放飞自我了,尝试了(我认为的)没尝试过的风格,然后果不其然把自己搞得很苦……想表达的东西很多,没塞进去的也很多。以后要是有心情就再修改一下没有就算了!好累喔!(懒死了
最开头以影片的方式接了点stls的剧情:http://elfartworld.com/works/7745661
虽然可能很无关紧要,不过堆雪人(兔子)的情节灵感是来源于stls最开始告诉我的废弃剧本,程序运行提示(就有“——”的那几行)参考的UL(。
总的来说不是特别确定能不能我以外的人能不能看懂……我姑且有把逻辑圆顺,有疑问欢迎提!最后谢谢你读到这里♪
关键词《痴情之吻》,字数是7944
*10/18修了语言改了错字,计分还是以初投稿的字数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