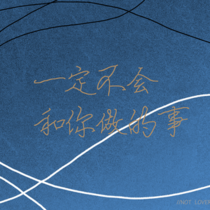草写得好烂看过算过吧!!是苏醒part,舞台还在写(怎么还没写完)
字数2401
---
林蕊想大喊出声。
……也就是想想,她没那胆子。
这一秒,她的嘴巴——或者说下半张脸,被一只带着薄茧的手捂得严严实实,额头感触着冰凉的墙,陌生的体温贴着她的后背。
心跳的律动隔着衣物传了过来,一下又一下,规律而平稳。
……
该、该不会这人做惯了劫持别人的事儿吧?
想到这里,林蕊慌得心脏都快飞出来了。它在胸口咚咚咚咚咚咚地往喉咙口躁动着,等那只堵着出口的手一松就随时要嗖一声弹射起步离开身体似的。
……小姑娘哪见过这场面啊!
平日里出个门,不认识的人就算是离她近点儿,保镖都恨不得要按着那人脑袋请他滚蛋了。让陌生人贴身?不存在的。
可、可她现在怎么就被人捏着脸呢?!
“老实点,不许出声!”
低沉的声音伴着气息警告似的刮蹭在林蕊耳边。
与此同时那只手像要往下挪似的动了动,说不定马上就要掐住她的脖子——啊啊啊!
下一刻,果不其然。
“——!!!!”
它挪了!
林蕊吓出了一身冷汗,完了这是不是要交代在这儿了?这人手上该不会还拿着什么武器吧?枪?匕首?电视里不法分子都这样的……
可这人的目的是什么?随便抓个人杀了?绑架谋财?希望是后者呜哇哇哇……
眼泪不受控地啪塔啪塔往下掉,可那只手的动作却在这时停顿。
咚咚咚咚咚,身后那人的心跳突然乱了。
“……女……女的?!”
暂且不管这人为什么会不知道自己是个女的,林蕊立马反应过来,机会来了!趁着对方愣神的空档抓着那只手狠狠咬下,她在一声痛哼中重获自由。
她立马逃开,手忙脚乱贴着墙一通乱摸试图找个能防身的东西,可这破房间干净得和毛坯房似的,最后只在自己醒过来的床上摸到个枕头。
哇……凑、凑合用吧!总比什么都没有强,万一他要打人至少可以护下脑袋……
林蕊一把抓起布料有些粗糙的枕头,用它蹭了蹭眼角冒出来的泪花,努力瞪视那个掀了帘子走过来的男人。
她这才看清男人的长相:面上一道长疤自左脸剌到右脸,眉骨上还打了钉……虽然五官硬朗,长得很是好看,但这差点把“我是坏人”四个大字印在脸上的眼神也太吓人了点吧。
她吞了口口水。
她刚刚有看到门,可是这男人挡住去门口的路,逃不掉了……
“你、你开价吧!钱……可以给你,不要伤害我!”
呜哇……希望钱对他好使……不然可怎么办?
刚才她醒过来的时候,就只是摸了把帘子,他就捂着她的嘴把她按到墙上去了。
现在她咬了他一大口,会、会被怎样啊……?林蕊越想越慌,一睁眼看到陌生的天花板都足够离谱,怎么还碰上这样的事……保镖呢,她的保镖呢?人呢!平时一个两个管闲事管得可宽,现在真遇到事就都不见了!
男人的声音却远远传来,他似乎没再靠近,语气也柔和了不少。
“……我会不伤害你,那个。”
“……”
哪个?
林蕊悄悄把遮在面前的枕头拿下来一点,露出一双眼睛。
像是不知道要看哪儿似的,男人眼神飘了飘,神态中不知为何带了些紧张。
“你是不是也……不基道这里系什么地方?”
他努力地说着普通话,却还是压不住口音……听着像是广东那边的?
林蕊喜欢看TVB,还挺熟悉粤语的腔调,放平时她可能会觉得广普好可爱好好笑,可现在实在没那心思。
大概是刚刚那一下被吓蒙圈了,脑袋和舌头都打着结,开口声音还是颤的,语调“呼~”地往破音边缘飘去。
“我我我我不~知~……”
“嘘!!如果系绑架,会有人看着我们,你小声点。”
眼看着音量也往上飙去,男人立刻打断林蕊,皱着眉头紧张地在唇前竖起手指。
啊……?什么意思?
这句话让林蕊消化了好一会儿。
她眨巴眨巴眼,男人也眨巴眨巴眼。
稍顷,林蕊总算反应了过来,小心翼翼地,用气声问道。
“意思是说,你不是绑架犯……?”
“不是啊。刚才是误会,咳,对唔住。”
男人松了口气,举起空空的双手证明自己没有藏凶器,像是有些抱歉似的垂下眼帘。
“有可能你是被我牵扯进来的,我会负责,带你逃出去。”
“牵、牵扯?呃……”
啊,也就是说,绑架犯要绑的其实是这个人,而她很可能只是因为刚好路过目击就被一起抓过来了?那她真的是好倒霉……可她为什么不记得有这一段?
林蕊搓着脑袋仔细检索脑内的记忆,她最后能想起来的是自己开车上了高速……然后……
然后怎么了来着?她怎么到这里来的?
而趁她苦苦思索的空档,男人已经将他的“负责”付诸行动。
他轻手轻脚地在屋里翻翻找找了一阵,林蕊思考无果回过神来时,刚好看到他躲在窗边看外面的情况。
“有……有有有有人吗外面?”
“能看到的没有。”
“还有看不到的……!?”
“说不定。”
说不定算怎么回事?林蕊哆嗦了一下。
可是万一真的没人呢?也有可能绑架犯以为他们俩还要躺很久,出去干什么事情了,再万一那家伙比较粗心,忘记锁门……
那现在就是唯一一个可以逃的机会了!
说着是有点离谱,但凡事都有个万一嘛,人生在世,乐观很重要。
她这么想着,把自己挪到门口,伸手摸了一下门把。
……
草。
好像。
还真开了!!!!!!!
“你快过来!”
林蕊立马跑过去扯男人的袖子,满脸严肃认真观察着窗外的男人被又突然拔高的声线吓了一跳。
“小声——”
“门开了!”
“…………啊?”
林蕊没拉动男人,他好沉,于是指着门口强调了一遍。
“门没锁,被我打开了!快跑!”
“怎么可能……”
显然是没考虑过门没锁的可能性,男人一愣,但他还是立刻把身子贴到门口,转动门把。
“……”
居然真的开了!!
他憋了半天没说出话。
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整理完了情绪,他恢复了冷静,将门推开一条缝,一边从缝隙里盯着外边的情况一边小声嘱咐林蕊。
“外面也说不定会有危险,你躲在我后面出去。如果我叫你跑,你不要回头。”
“啊……?那、那你呢?”
“……”
他没有回答林蕊的问题,只是回头看了她一眼,深吸一口气。
“你管你小心。”
这句电影英雄似的台词让面前这个人的身影镀了一层令人动容的史诗光辉,林蕊突然一阵感动。
“我可以记住你的名字吗?”
她扯住了男人后背的衣服,不知为什么,对方的身体僵了一下,愣了两秒才给出回复。
“……周灭。”
“周灭,我记住了。我叫林蕊……回头一起逃出去,我们就是过命的交情了。”
把话说得万分笃定,半点没考虑会遇到什么问题似的,可发颤的手指出卖了她心里的慌张。
她在给自己鼓劲。
周灭大概是看出来了,眼神一凛。
“走。”
“嗯。”
两人做了十足的决心,似乎在那一秒达成了什么感天动地的情谊,可当他们离开房间,一脚踏进柔软的雪地里。
外面却没有什么危险。
只有数十个与他们一样一脸蒙圈的人,同时从各自的木屋里缓缓走出。
[01]
“你觉得,天堂会是什么样的?”
长桌的一端,克莱尔漫不经心地摇晃着酒杯。在她的对面,诺亚正沉迷用刀叉分解铺满奶油的松饼。他们是偶然在餐厅门口遇见的,搭话的时候被带位的女仆误以为是同伴,于是顺势邀约、坐在了相近的位置。
稍迟片刻,诺亚抬起头,正对上克莱尔探寻的眼。
“天堂吗?我想……应该是有很多有翅膀的美少年美少女的地方吧?我不是教徒哎……不太清楚呢。”
“那么,现在我们也确实看见了有翅膀的人,诺亚你觉得这里就是天堂吗?”
“……?”
长及颧骨的刘海下,诺亚缓缓眨了眨眼。
[02]
诺亚的莫名并非毫无缘由。相较于他人,他缺少了两段重要的记忆。第一段是初次醒来时被聚集在一起的人们为没头绪的状况小声议论的部分——那天他醒得特别晚,几乎是在探索时间的最后才找到了大部队汇合。
而这也间接导致了另一端记忆迟迟无法被想起,直到几天后经笠纱季的好心点醒,诺亚才明白过来:
“也就是说……我现在是死了吗?”
“我想是的。你……完全不记得来到伊甸前发生了什么吗?”
诺亚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我只记得AYUNA酱在直播的最后唱了一支走调的歌。”
“……谁?”
“是我喜欢的Vtuber喔!设定上有双重人格的样子,明明有时候唱歌堪比天籁,有时候却跑调跑得听不出来原本是什么歌,很可爱吧?只可惜直播时间很飘忽呢,我经常会不得不在上班期间偷偷地听。”
纱季推推眼镜,显然不打算继续下去这个话题。她翻阅几页手中的剧本,迅速提笔涂涂改改,口中则接上了先前的话题。
“总之……我记得自己最后被车撞到,醒来又见到天使,会这样想……也很合理吧?先前听到过……其他人询问‘自己是不是死了’,比如那个黑肤色举止很像动物的孩子……既然推测的结论相同,我想起因……应该也不会差太多。”
诺亚点点头,口吻像是在评论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这样啊。那有点遗憾哎。”
“……你突然听到自己的死讯,人倒是很平静呢。”
“毕竟,也没办法嘛!”
[03]
一直以来,诺亚都是个非常乐观的家伙。这并非天性使然,而是“比起怨恨悲伤引发的滚雪球,尽快调整好状态才更有益于继续迎接人生的新Event”。初中的休学事件亦是如此。
他打一开始就没太把同学给自己使的绊子当回事——学校里到底都是受淳朴民风影响长大的孩子,没事找事的手段对诺亚来说也不痛不痒。虽说白白增添了麻烦,诺亚已经尽力把经济损失压缩到了最小。更何况,学校对种族歧视与校园暴力的问题较为关注,只要不被逮到空,那些讨人厌的家伙没那么容易下手……这些想法,即使在诺亚摔下楼梯被送入医院依然不曾改变。
他比谁都清楚自己的受伤是纯粹的意外,非要怪罪的话就是时运不济,心中并无怨恨。就结果而言,意外反而成就了永绝后患的契机,并附赠一个中二病看了根本把持不住的酷炫徽章,怎么想都不亏。信息消化过快已经到了缺根筋的地步了。
所以,在得知自己的死讯后,诺亚内心的感言从“突然穿越异世界好厉害!”转为 “人类都会死但我死了竟然能穿越异世界,赚到!”, 倒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04]
但若说诺亚从来不会感到困扰,似乎也不完全是这样。
自到达伊甸园以来,诺亚就过上了现代人最无法忍受的日子——没有Wi-Fi。即使用魔法插座充上了电,手机的左上角也一直显示圈外无服务,白白浪费了这个月的流量包。转生小说怎么没提过这点,诺亚趴在桌上,不死心地刷着无网络连接的YouTube。倘若日后还能有机会联系作者的话,一定要好好抱怨一下。
异世界穿越的新鲜劲过去,起初光怪陆离的非日常也趋向于平稳。一下子被剥夺生活乐趣的诺亚犹如失去燃油的发动机,无论做什么都只能吐出无助的黑烟、提不起劲。按理来说接下来的桥段不该是天降异族美少女吗?可眼下自己熟络的除了厚着脸皮拜托改稿的纱季老师、磕磕绊绊尝试相处的室友,就只有长着一张明显不是教科书上的女主角脸还喜欢说让人听不懂的话的克莱尔。
“当我们演出‘单元剧’时,在舞台的灯光下,虚构的人物便脱离我们自身诞生了,但是在舞台落幕后却又不复存在。这种昙花一现的虚构,在诺亚看起来又是一种怎样存在?
“假设一个人爱上了一个虚构的角色,他所爱上的绝不是扮演角色的演员。可是那角色又是真实存在的吗?还是只是幻象呢?”
那日在餐桌上,克莱尔从容不迫地接连对诺亚抛出疑问。思考从未触及这种层面、也无法理解问题从何而来,诺亚硬着头皮对付了几句就被吓得落荒而逃。原本想着“或许之后看到这个人都该绕道走了”,付出行动时却意外在背后窥见克莱尔不断盯着没有网络的SNS发送信息,亲切感顿时将畏惧一扫而空。
剧本大致完工的那日,克莱尔再次找上了门。彼时诺亚正在研究从商店里买回来的3D拼图,试图打发时间。
“你这是……?”
一眼看见诺亚正在把屋顶竖着往落地窗上对接,饶是能言善辩如克莱尔一时语塞。注意到克莱尔投来的视线,诺亚把拼图翻了个面:
“啊,装错了。”
看来3D的弊端是视野会有盲区。诺亚不好意思地笑笑,一抬头则被克莱尔枯槁的左臂吓了一跳。克莱尔看出他的反应,淡淡解释:
“和伊甸人打闹被施了魔法。”
“欸欸?!不、不要紧吗……能复原吗?会痛吗?”
“我问过女仆小姐,说是可以自然康复……还好吧,虽然要难看一阵了。”
明明用着轻松的口吻,诺亚却看见凄哀从克莱尔的神色里一闪而过。灌满Galgame攻略的脑子当然知道这时最应该做些什么,遗憾的是三次元无法无视物理规则。他窘迫地扒拉出一件皱皱巴巴的衬衫:
“那个……如果不嫌弃的话,请先用这个遮一遮吧。”
“谢谢你。”
克莱尔灿然一笑,接过就立即穿上了身。发皱的衬衫与华美礼裙格格不入,虽说克莱尔本人不太在意的样子,诺亚反而愧疚起来。
“那、那你本来是有什么事?”
为了驱散这份不自在,他想起最初的起因。克莱尔笑意不减:
“你对恶魔怎么想?”
“那当然是——真的假的好酷啊!!”
要不然怎么说这人缺神经呢,一句话就被轻松带跑。不知是否早有预料,克莱尔神神秘秘地从手包抽出一张对折的纸。
“那么,就麻烦你转交给那位白色的恶魔先生了。”
[05]
诺亚在四处转了几圈,最后在森林的入口找见了符合特征的白恶魔。他高声招呼了几句,被唤作诺法加的男人没有否认,只在双手抱胸等着诺亚靠近。看来是没有认错,诺亚快步上前,恭恭敬敬地用双手递交折好的信纸:
“是克莱尔托我交给你的。虽然没有信封!不过请放心,我没有看过里面的内容。”
“辛苦黑黑古牧先生咯。”
白色的恶魔接过信件,展开后仅仅扫过一行便合上信纸揉捏成团。魔法在他的掌心汇聚成火焰,转眼就将纸张化为灰烬。这让还在纠结“黑黑古牧”是不是指自己的诺亚瞪大了双眼。
“黑黑古牧先生还有别的想问我的事情吗?”
诺亚踌躇片刻,想了想,姑且还是履行一下接了委托的职责:
“嗯……你在生气吗?”
“欸,为什么会这样问?”
“因为烧了信……话说好厉害喔!是真的有火耶!”
“只是没有兴趣继续往下读罢了。”诺法加耸耸肩,看样子不愿多提。他感知到诺亚放光的双眼,脸上又恢复深深笑意,“还想再看一次吗?”
“可以吗?!”
话音未落,明黄色的、悦动着的火焰再一次从恶魔的掌心出现,火舌沿着纤细手指蹿腾而上,尔后消失不见。诺法加翻掌收起,重新掩紧了羊毛披肩。
“表演结束了,再看就要收费了喔。”
啪叽啪叽啪叽啪叽,诺亚小幅度地快速鼓掌,后者则犹如谢幕的魔术师点头致意。掌声一停,诺亚又再次恢复成之前欲言又止的状态。半晌,他像是得出了答案。
“所以……克莱尔的手臂也是和刚才差不多的法术造成的吗?”
「伊甸人」、「打闹」、「魔法」、「转交的信件」、「没有兴趣」……这些关键词拼在一起,不难想到这个答案。诺亚有点怀念RPG中任务列表的核对表,太过依赖提示的恶果就是拖长了反射弧。
“是哦。”始作俑者大方承认,脸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意兴阑珊。他用指尖戳着披肩下摆的穗子, “她的手臂过一段时间自然恢复了,影响到表演可不好。”
“真体贴呢!虽然稍微有点坏心眼。”
诺亚诚实地表达感想。诺法加故作委屈:
“欸~我倒是觉得她挺满意的呢?如果她不喜欢的话,那一开始就不会做出那种事情喔,我不过是满足了她的愿望而已。”
“恶魔会免费满足别人的愿望吗?”
“所有愿望都是交易,交易需要付出代价。”
“那恶魔也会有愿望吗?”
“……。”
没有立即听到回答,诺亚缓缓眨了眨眼。
“你默认把自己放在卖方的位置呢,偶尔不考虑转换立场试试吗?而且感觉你好像什么都做得到,我非常好奇你会不会也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呢……?”
诺法加轻笑一声,点点下巴:
“哎呀,这样说来……我确实有想要的东西呢。不过是什么东西就暂时保密吧。”
原来如此,是好感不够。
“如果黑黑古牧有想要实现的事情,可以来找我做交易哦?” 那厢,诺法加又恢复了蛊惑人心的恶魔本色,“什~~么愿望都可以,甚至说想做大总统之类的也没问题。虽然代价很高,但是也不是不能做到。”
话说回来,诺亚还真有非常非常迫切想要实现的愿望。他匆匆从口袋里翻出手机,满怀期待地脱口而出:
“你能帮我连上Wi-Fi不?”
“可能需要你五根手指做报酬吧。上十分钟的网。” 白恶魔双手环胸思考了一瞬,慢条斯理地开出天价网费。
果然还是好感度的问题。诺亚心想。
[06]
“不是噢?这才不是交易。而且那家伙的逻辑根本就是不讲道理。”
简单复完命,诺亚悄悄向打听克莱尔「打闹」的缘由。简而言之,手臂的状况并非克莱尔的愿望,而是一次实验的结果。那边克莱尔还在阐述事情的经过,诺亚却被克莱尔的发言惹得忍俊不禁。
“怎么了?”
她停下来询问他。诺亚当然不会把“你居然想跟恶魔讲道理”这种话说出口,只好忍耐想要摸摸克莱尔脑袋的冲动,摇着头说“没什么”。
“……。”
克莱尔没有继续追究,转而从一旁的纸袋取出一套崭新的衣物。
“这个给你。”
“欸、欸……我收下不太合适吧。”
“有什么关系。要记得穿喔?”
“嗯……”
或许是因为准备剧目的关系,诺亚这两天没少看恋爱题材的作品,脑回路受酸甜展开侵蚀。他小心翼翼地试探一句:“唔、如果是我会错意的话那不好意思……不过,你是不是……?”
“……”
克莱尔眼里闪烁一瞬,目光直直地定在诺亚脸上:“就是送个礼物,我觉得很适合你,别想太多?这样还有得换洗。”
“啊………抱歉!!!!我想也是呢……!” 果然是想太多。“但我收下真的好吗?”
“有什么好不好的?我想看你穿的样子。”
“可是可是,如果克莱尔有更在意的人、或者其他在意克莱尔你的人……会误会的吧?这样不要紧吗?”诺亚越说越小声。看来侵蚀程度还挺严重。
克莱尔闪电般地挑了挑眉毛,语气里有几分不容拒绝:
“在这里我没有比诺亚更亲近的人了。假如还有其他在意我的人,连争夺的勇气都没有肯定也会被我拒绝的。你再不肯收我可要生气了。”
“………………我知道了。”
“你好像不太开心?”
似乎误把无措理解成不情愿,克莱尔偏头凑近,试图从下方偷看诺亚刘海下面的表情,诺亚反射性地避开了。
“不会!……我现实里,很久没收过礼物了……所以不太清楚应该用什么态度应对。”
他珍惜地将收到的礼物抱在胸口,塑料袋簌簌作响。
“克莱尔你希望我收下的话,那我就收下了。”
[07]
人在被告知“不要多想”的时候,言下之意的“给我多想”与“不准多想”概率几乎对半开。诺亚确实没有再多揣测克莱尔的举动,只当是强势惯了的人不习惯更加友善的表达方式。同时,他也有了其他猜测。
于是隔日一早,再次被克莱尔差遣送信的诺亚在白恶魔又一次施展完燃烧魔法后,决定先斩后奏:
“失礼了。”
他撩起袖子凑上前,双手则按住诺法加的肩防止挣脱,一连用力吸好几口气后,才抽身退回。未料,恶魔却在这时抬手截住了他的去路。
仿佛是学着诺亚的样子,诺法加贴近诺亚的颈边浅浅一嗅。恶魔身上的草木清香再次充盈鼻腔,诺亚整个人都紧张起来:
“怎么样??有怪味吗??”
诺法加没有回答,似笑非笑地回望着诺亚。片刻之后他像是厌倦了,慢吞吞伸个懒腰,“黑黑古牧的味道让我有点饿了呢。”
“欸?!果然很糟糕吗?!”
“怎么会呢。是很好吃的味道喔?”
稍迟两拍,诺亚才想起今天的早餐是现点的香煎培根,恐怕是在那时沾上的气味吧。也就是说,自己身上并无异味?但恶魔的审美和人类一致吗?他无法确定。又或者,
“难道说……光是每天洗澡还不够,应该像诺法加先生一样,有帅哥的味道比较好?”
这么一想,克莱尔三番五次的给诺法加写信难道另有隐情?诺亚由始至终都很守规矩地没有偷看过信件,自然也无法得知切实内容。不过,在第二次送信之前,自己事先提醒克莱尔“对方或许还会烧掉信件哦”,克莱尔却执意让他去送。
诺法加微微一哂,堂而皇之地丢下一个直钩:“如果为了这样的事情烦恼,我有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喔。你想要帅哥的味道的话,我可以给你。”
“要怎么做?”
“哼哼,因为今天心情还不错,所以这样的小事可以直接决定喔。”
恶魔凭空抽出一张A4纸,瞬间金光窜动,未知的文字自上到下显现出来。他指着最末端的两道横线,“在这里签个名就可以永远有你所说的帅哥气味了,不管发生了什么身上永远都会是香香的呢~”
“噢噢噢噢出现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恶魔契约!!!!!……可是可是,太大材小用了吧!!!明明是恶魔契约……!!!”
“什么愿望都可以实现的。这点小事肯定没问题的嘛。”
“那确实。”
“对吧对吧~心动不如行动——趁我还想给你优惠价的时候。”诺法加这会儿活像个带货主播。
[08]
“所以?你就签了?”
森林附近的空地,不少人在这里制作舞台演出用的道具。电锯与捶打的声音此起彼伏,诺亚则在卡梅莉亚的协助下得以与约里克共用同一套工具。
“嗯……!毕竟是恶魔契约啊!异世界穿越不签恶魔契约算什么异世界穿越,大家都会想签的吧?”
“……要不是看在这两天一起干活觉得你还算器用的份上,我这会儿就该劝你离我妹妹远点了。帮我换个螺丝刀。”
“别这么说啊~”
诺亚笑着把指定的工具递了过去,顺便蹲下帮忙固定住木板。
“你别看我这样,多少还是有在考虑的!就算现在一时半会儿用不到恶魔的力量,谁知道日后会不会需要。现在实践一下也没有坏处嘛。”
“这倒也是。”约里克被说服了,“具体是什么内容?”
“说是随便给哪个人类当一天狗就能在身上飘七天帅哥的香味。”
按着的木板停止了颤动,诺亚抬起头。另一边的约里克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前言撤回。果然你还是离我妹妹远点。”
那演出的时候我可就困扰了!!诺亚心说。他试图打消疑虑:“放心吧,我没有打算拜托卡梅莉亚帮我喔。”
“那就好。”
“那么麻烦你了。”
“等等。”
刚刚拿起的工具又一次被丢下了。约里克神色复杂,各种表情在他脸上一晃而过,最后他无奈地举起双手做投降状:
“抱歉,我对男人不行,放过我吧。”
“……也未必要做到那一步?普通地当成过家家一样的程度?”
“你适可而止一点,哪有人把特殊play弱化成过家家的,分级都不一样了。” 迅速领会到和脑结构不一样的家伙继续辩驳也没有意义,约里克痛苦地按住眉头,自行思考对策,“不过我想就算我不奉陪你也会找其他人的吧?这样好了,我们两个换一天房。”
“咦?”
“我只是担心莉亚身心健康的安危。还是说你打算在大庭广众之下玩那种play?”
“……说得也对。”
有了前车之鉴,再次寻求信赖对象协助时诺亚多留了心眼。他故意忽略了他人无需了解的契约报酬,只告知需要获得协助的支付条件,又将内容描述得委婉了些,才勉勉强强让克莱尔点头同意。
事实证明约里克的担心果然不是多余。第二天一早,克莱尔就将被魔法催眠的诺亚绑在了椅子上外出待了一天,直到夜间才回房休息。幸而二人是临时室友,倒也不用多费口舌向他人解释这种诡异情形。
但不知是不是错觉,诺亚总觉得克莱尔的情绪不太对劲。
[09]
接踵而来的忙碌日常没留给诺亚太多追问的机会。并非刻意,意识到的时候诺亚已经有一段时日没见到克莱尔了。
比如第一天是因为排练。自早上搬运完演出道具,排练的日程就撑满了整个下午与夜晚。真正站在台上之后难免还是会因为紧张而忘词,诺亚不得不抽出更多时间巩固记忆并与演对手戏的卡梅莉亚磨合,于是第二天也在繁忙中过去了。再后一日,诺亚跑去借了漫画作为演技参考,道具、着装也有调整的必要。即使有魔法相助,经验上的短板却是无论如何都需要下功夫弥补的。
再次敲开克莱尔的房门,诺亚甚至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怀念感——虽说他其实是来领之前换房时落下的虎鲸玩偶的。
“……你最近用了什么熏香吗?”
与热情打招呼的诺亚不同,克莱尔脸上并无喜色。她皱起眉头,眼神里带有几分审视。诺亚被她盯得不太自在:
“嗯、嗯……不好闻吗?”
“与其说好不好闻,这个味道让我想起一个人。”
“呃。”诺亚当然知道她说的是谁。“所以克莱尔不喜欢?”
这不是个好问题。克莱尔顿了顿,少见地眯起眼:“是不是呢,诺亚怎么猜?说喜欢你会比较开心吗?”
“说真话我会比较开心……大概吧。”他不确定。
心不在焉的神色忽然从女性的脸上消失了。克莱尔面无表情,凉意沿着冻结的皮肤一寸一寸散布。
“那我就直白一点。认识的两个人身上突然出现同样的味道,对于不知道原因的人来说,会很自然地猜想那两个人是不是上过床、事后还一起洗澡用了同款沐浴露。嗯,对我而言还是蛮刺激的够有冲击性。”
“……原来还有这种说法!” 被诘问的对象暂时没能回过味,自顾自地用右手握拳轻轻敲击掌心。这反应似乎激怒了克莱尔,她大步上前,直接伸手拽住了诺亚的领口。诺亚不敢挣脱,只得在惨叫中被拖着趔趄了几步,后知后觉领悟到大难临头。
“所以呢?诺亚愿意好心告诉我真相吗?是睡过了,还是没睡过?”
明明手上实施的行径粗暴无比,声线却轻柔得堪比天使耳语。诺亚慌忙用这辈子最坚决的语气迅速招供:
“没有啦放心吧我对那张脸冲不起来不可能睡的!!!”
“是吗?”
可惜克莱尔不为所动。她更加放柔声音,身体暧昧地前倾。不得不称赞克莱尔在做这种技巧时娴熟又煽情,温度拿捏得正好。诺亚的心神被突如其来的拥抱勾去几秒,尔后才蓦然察觉到有只手不知何时已伸向他的后腰。
“但是啊~对方若是想从诺亚的这里进入的话,诺亚的想法和反应就不太重要了吧?反正,也用不到前面。”
“唔、唔唔……”
诺亚支吾起来,并非因为被猜中正解。皮肤隔着衣物被克莱尔暧昧地触碰,在感到衬衫将要被那只不安分的手从后面掀起之际,诺亚仓惶逃脱。
“可可可这种事讲究你情我愿的不是吗!我、我多少还是有点力气的,让我做不想做的事可没那么容易屈服喔!”他是真的被吓到了。为了验证辩词的说服力,诺亚甚至一俯身将克莱尔拦腰抱起,又在手上掂了几下,才把她放下——放在了安全距离之外。
“但是他有魔法呀?'你情我愿'…诺亚有过经验吗?”
“诶、这个…这个………多少…还是会…有的!”
不过是在游戏里就是了。如果被知道自己明明一无所知还装作讲得很有道理的样子……会被讨厌的吧。诺亚的心脏紧张地狂跳起来。
“那诺亚究竟是为什么,染上诺法加先生的味道……”
“好啦不要用这么奇怪的说法!!是契约啦契约啦,就是之前拜托你的那个!”
事到如今诺亚终于想起当初自己省略了说明。
找到症结之后就好办了,诺亚松了口气。事实证明他还是太天真,现实可不像游戏一样只给固定的选择支,矛盾与和解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固定套路。
“……既然要找恶魔做交易,为什么不换些更有用的?” 克莱尔双手抱臂,颇有几分不依不饶的架势。
“有用的?比如?”
“比如让自己长成自己喜欢的脸,这样就没必要留长刘海了?”
“唔……我对自己的脸没有什么不满喔。”
“那为什么不肯露出来让大家看到的?”
这有点像是闹脾气了。先前第一回合的争吵就让从没遇过类似事态的诺亚精疲力竭,偏偏克莱尔此刻又挑了最敏感的问题紧紧逼问。诺亚不知道秘密的重量对于克莱尔来说是否合适,无论是太轻还是太重都会让桥梁大幅度倾斜直至分崩离析。而他还没有做好面临这一刻的准备。
“嗯……为什么要露出来让大家看到?”
斟酌再三,诺亚选择明知故问。参考之前时常对不上电波的对话,克莱尔多半会阐述自己的理解吧,之后只要附和几句再带过就好。
他的算盘很快落了空。被反问的克莱尔张了张嘴,最后只憋出一句,“算了,做什么都是你的自由。”就转身作势要走。诺亚刚想挽留,她忽地又停住,踱回到诺亚跟前:“衣服不喜欢可以还给我,我自己穿。”
“……。”
“……。”
“是我语气不好。” 诺亚服软了,“刚才也是,突然把你举起来了,对不起。”
“没有。我只是想拿回衣服?这样你可以穿你自己喜欢的。”
像是想要表达“才没有生气喔没有喔”,克莱尔温和而又诡异地微笑起来,手指不由分说攥紧了诺亚的领口并飞快解开纽扣。锁骨与半片胸脯猝不及防地暴露在视野中,诺亚慌忙抓住克莱尔阻止她继续。
“干什么?”
克莱尔抬眼蹬他。诺亚不知所措,哑然别开脸不敢对视,须臾后又犹犹豫豫地挪回肢体交叠的地方,然后用手将掌中的手包裹得更紧了些。
沉默在空气中蔓延。诺亚不确认克莱尔是否能读懂自己含蓄的哀求,只好努力将自己的温度传给紧握着的那对发凉的手。没有任何攻略告诉他现在应该怎么做,他希望克莱尔教会他,如果她也愿意的话。
“呜……”
克莱尔的回应是钻心的痛楚。她踮起脚,发梢不听话地滑进敞开的衣领,在诺亚感受到瘙痒之前,疼痛将那触感覆盖了。克莱尔死死咬着诺亚的脖颈,这让诺亚几乎想要呻吟出声。但诺亚明白自己没有逃跑的选项,谄媚似的用手臂揽住克莱尔方便她借力,任她在这个故意伤人心的坏家伙身上尽情泄恨,直到她满意为止。
不知过了多久,连痛感都麻木了,克莱尔终于松开了他。漫长的噬咬中二人姿势换了几番,此时克莱尔整个人的重心都压在了诺亚身上。她伸长上臂勾住对方,又轻轻扭动身子。纤细的腰有意无意地摩擦着,在诺亚的腹上留下几个发烫的落点,于是躯体便贴合得更紧了些。
“诺亚。”
耳廓被呼吸灼烧着,被唤到名字的人僵硬地转脸望去。感知到了诺亚的注视,克莱尔愈发放慢速度舔舐自己的手指,露骨地暗示,“想不想,尝试会变得轻松和快乐的魔法?”
“……。”
没有人能抵抗这种诱惑的。诺亚心想。是什么从面部剥落,又是什么浮上了赤裸的表面?诺亚看不见自己的脸,也无法从克莱尔幽暗如海底的双眼里窥见更多。“这次是什么?吸血鬼的契约吗。”他牵过克莱尔的小臂,脸颊蹭到了流淌至指根的唾液。而他继续下移,一直顺着找到布满青色血管的腕。
侧头咬上的同时,诺亚听见自己含糊地应了声:“好啊。”
——就让我奉陪到底吧。
[10]
时间回到被约里克拖去换房的那天。
意识到自家妹妹的室友“不太正常”,青年如临大敌,当即丢下工具就想带着诺亚回去收拾行李。诺亚起先被他拖着走了几步,然后像是突然想起什么,反手拽停了对方。
“稍等一下,我顺便借个凿子回去。”
倒不是什么大问题。约里克松开手,“你要那个做什么?”
“啊……我最近在拼拼图,”
“拼图?”
“嗯,是立体的那种……本来想送给诺法加先生的,后来觉得已经拆封了再送也不太好,干脆就想先拼完吧。但我一开始不小心拼错部件,之后越错越多,就导致整体都不太契合。现在不得不修改拼接位置,多开几个槽出来了。”
“……。”
约里克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哽了半天,才勉强吐出一句有气无力的,“你直接把拼错的部分拆了重装不行吗。”
闻言,诺亚面露难色:
“不行喔。已经,完全卡住……拆不开了。”
=====
我果然还是不擅长写长文……到后面耐心渐渐消失,实在改不动了大家凑合着看.jpg(什么人啊
克莱尔与诺法加的部分都是rp改编【划重点】,因为还是想尽量圆个故事出来所以改动了一部分,和原记录有那么点出入。纱季老师和约里克是被我强行抓来配合讲相声的,谢谢两位中人借我角色!!!希望没有太ooc。随后诺哥真的辛苦了(………)越写越觉得这篇应该叫《诺哥在背后付出了太多》,感恩……
怎样都好的信息,文中提到演技参考的漫画是问何洛借的《好想告诉你》的一二卷。实在是插不进就……有缘再说吧!!!或许之后会用到。拼图的离谱程度大概是原图纸是一栋洋房,但是被诺亚拼成了样子有点怪的挖掘机这种,脑补一下特摄片玩具或许能理解(太失礼了对不起特摄厨!!!)。那么最后感谢阅读♪
字数是9053
01
藤野宙站在伊甸园的一棵树下,沈如夏正在他身边一圈一圈地转,嘴里正快速念叨着某些藤野无法听明白的口令,临了变换了两个手势,随着一声喊叫一小捧糯米猝不及防就洒在藤野宙身上,始作俑者却仿佛松了口气一般的拍拍手。
“没问题了,早知道我就带着五雷令出门了!”沈如夏掐着下巴,片刻又快速展示了几个手势“昨天游艺室真是吓了我一跳,要不要我教给你九字真言呀?”
“嗯…好学吗?”藤野宙抖了抖衣服,把顺着领口飞进来的糯米里抖出去,转身跟上了沈如夏。
“这个最简单了,”沈如夏竖起大拇指,也不顾在网络上千千万的教学视频直接开口“不过要交学费的。”
02
“嗯……看过剧本之后其实我还在想要不要叫飛遊帮忙客串一下的…”
“诶,为什么没有呢?”
“总觉得我们三个站在一起不像是校园剧,更像是《非正〇会谈》吧。”
“?”
03
“吹凉的关东煮……不会很好吃吧,万一你再吃坏了。”藤野 货真价实的日本人 宙对着沈如夏提出的提议如是说,他看了看那杯挂满水珠的半凉关东煮皱了皱眉,总觉得哪里不对。
“没关系的,这有什么,我们演就是要力求真实的!”沈 凭空幻想只靠经验不听劝 如夏拍拍胸脯做出保证,在咬下第一口萝卜之后露出了无比扭曲的表情。
“对不起,我知错了,我们的排练再延迟两小时吧!”藤野宙看着龟缩在床的沈如夏叹了口气。
04
“长台词吗?我觉得有些地方随行发挥就能有很好的效果。”
“长台词说起来很帅的啊,配合一个连贯的长镜头下来很有感觉,无论是MV还是影视剧,一气呵成下来的一个片段都很有力量的。”
“唔…确实,不过长台词到时候是不是很容易忘词,万一到时候记不住的话。”
“诶,没关系的,经纪人小技巧,到时候台下准备提词器,或者准备好稿件就可以了,有时候我也会抄在手背上喔。”
“?不…可是这里根本没有提词器一说吧,这是什么娱乐圈内幕吗。”
05
正式演出前藤野宙还是委婉地提出了关于沈如夏眼睛的问题,询问到时候他需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准备,沈如夏停顿了一下,十分坦然地摆摆手。
“经纪人虽然不负责台前工作,不过有时候还是要出场讲一些通稿,这个样子肯定不行啦,我有特别的办法,到时候我会用化妆品盖住让它看起来不那么吓人的。”
藤野宙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视线还是落在了那张画着不明符号的黄色符纸上,狰狞的咒文和沈如夏看起来并不契合。注意到这道目光,沈如夏突然凑了上去,阴恻恻地开口:
“在中国,对于算命的人来说,有些东西即便算到了也是不可以说的。它也一样,天机不可泄露,”沈如夏手指点在那张符纸上,十分认真地说,随后她突然笑了一下,转身离开了房间“不过可以加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