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队长……队长!”
卡纳在一声又一声的呼唤中睁开了眼,罗斯克雪原上的寒风总是冷得刺痛骨髓,阳光自遥远的天穹上洒下,却未能带来一丝暖意,只是耀眼到让人想要流泪。
他站在关口,他的队员们拥抱他,为他欢呼。他们说,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他们说,战争结束了。他依然记得他们的面容,与他们胸前晶石上镌刻的名字与编号。他们是魔法师,也是捍卫银顶城的士兵。他们与来时的模样相差无几,只是咆哮的北风令所有人的面容都染上了一丝沧桑。
罗斯克雪原的日出震撼依旧,只是这里的积雪不再是圣洁的白。凝固的血融化了凛冬,被泪水稀释后冻结成了玫瑰的红。他们站在这绯色的花海中歌颂他的仁爱,可只有卡纳看到,在朝阳之下,他们的影子蠕动着,嗤笑着,用凄厉的声音质问他:
“你为了保护你的小队,却对我们见死不救,这就是你所谓的正义吗?”
他无法回答他们。
“你们用魔法垄断话语权,阻绝了普通人追求真理的道路,这就是你所谓的无私吗?”
失去头颅的维罗妮卡掐住他的脖子,用讥讽的声音指责他的伪善。
他无法回答她。
被套上项圈与脚镣的龙化病患者们自阴暗的缝隙中走过,他们远远仰视着高高在上的他,用因干渴而沙哑的嗓音向他问候:
“你给了我们虚假自由,却从来不肯正视我们身上的苦难,这就是你所谓的仁爱吗?”
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最终,他的世界被黑暗所吞噬。又一抹纯白的影子向他走进,他的语气绝望,却有一种疯狂的平静。他抬起头,像是同他求教那样问他:
“三代人的债,却要由百十年后无辜者的鲜血来还,这就是你,这就是银顶城所谓的秩序吗?”
他依稀记得当年他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但他没有来得及开口,清晨的阳光便唤醒了他沉睡的意识。他支起身,鸟儿送来了庆典的喧嚣,而他只是木讷地例行晨祷、洗漱、更衣,而后来到位于塔顶的观赛台。
这不是第一年四强角逐,却堪称是第一届称得上是公平竞争的角逐。年轻的火花们放下立场与成见,自由地为了自身的荣誉和胜利迸发,反倒是看台之上,宣布要初次合作的四方领导人却远远做不到像他们发言时所说得那样和平。
“您的脸色很差。”塔尔文的声音因那坚固的头盔而显得沉闷,早在庆典之前,他就勒令参赛的骑士们加练,只是胜利的结果在贤者的健康面前显得如此无关紧要,他的视线始终落在贤者的身上,语气充满了担忧和急切,“您该好好休息。”
诚然,最近令卡纳操心的事确实有些多。魔物讨伐队的重伤、疯长的藤蔓、还有有关雪山的只言片语,风声的矛头对准了钟塔,甚至有些话语已经变相传入他的耳中:
“钟塔是否气数已尽?”
在魔物变得凶暴,不,也许早在炼金术出现的那天起,社会构架的动荡就是必然出现的。而卡纳一直在做的,也许只是让这一天来得慢一些,再慢一些。
“您已经做得够多了。”塔尔文时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十分关心卡纳,甚至有一丝矫枉过正。没有人比高洁的银顶城之枪更加忠诚,更加尽责,以至于偶尔在不经意间,卡纳也曾想过逗逗他,问他:
“你效忠于我,还是银顶城?”
但这个问题毫无意义。
伟大的贤者即是银顶城,魔法的至高点即是银顶城的意志。
卡纳听得见人们的欢呼,听得见在那欢呼背后汹涌的潮声。他记得那位激起浪花的年轻人,一如他记得每一块晶石的颜色与质地。瞬间炼成的武器哪怕大多只能想弹药一般发挥一次性的效用,这依然会让一些人联想到传说中的龙血。被钟塔放逐的孩子毫不避讳地在赛场上展示自己的手段,而这无疑又将引发一场臆断的风潮。
“今天的赛事还真热闹啊。”银舌雀时机恰好地同他没话找话,而他的思绪却飘到了三年前的雨夜。他记得那个叫维德的孩子,他记得他当时的表情,还有他质问他的话:
“三代人的债,却要由百十年后无辜者的鲜血来还,这就是你,这就是银顶城所谓的秩序吗?”
秩序。
是啊,这样的秩序已经维持了太久太久,经由背负贤者之名的他们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他们循规蹈矩,却也不断变革,在不断螺旋上升的岁月之中,毫无疑问,魔法即是银顶城的秩序。
但他却说:
“由他们开创一个新时代,倒也不坏。”
他端坐在那里,透过赛场,透过晶石,透过他的双眼,他看到旷野之上,自雪原归来的年轻人对世人宣称:“教授我魔法的老师,是一头龙。”
他看到眼中满是恨意和绝望的龙化病人用血液将蓝铃花染红,他们坠入地心,却也拉开了一个时代的序幕。
他看到因工期延误而失去家人的铁匠擦干眼泪,将手中的书稿散播给所有追寻学识与真理的人,至此黄金色的灯火逐渐燎原,永不熄灭。
他看到玫瑰色的雪原上尸骸遍野,死于战乱的亡灵无法归乡,只得徘徊于风雪和永恒的孤独之中。
他看到巨龙盘旋于钟塔之上,透过晶石向继承祂们学识的人类宣布:
“魔法起源于吾……逝于……魔法……逝于……”
他看到数十把兵器如同羽翼在维德身后张开,他看到一抹红光自那封印魔法的伤痕处一闪而过,他看到西敏在瞬息之间用电光偏转了那些剑锋所指的方向,而后那位平民出身的骑士在市民的欢呼声中拿下了这一场的胜利。
他知道那个孩子看到了什么,他知道那个孩子想破坏什么又想建立什么,他知道这一切源于什么,又要终结于什么。
但正如三年前他回问维德那样:
什么是秩序。
贫民窟出身的魔纹骑士。
四处流浪四处征战的龙化佣兵。
以及扎根于黄金之家、自毁前程的原魔法师。
出身立场各不相同的年轻人此时聚在一起,一同接受着人们的致意。卡纳缓缓地闭上眼睛,从过去到现在,从繁荣到动荡,从战争到和平,在这漫长的更迭中,透过一代又一代人书写的历史,他已见证了太多教训。
所以他抬了抬手,温言制止了一旁压抑着愤怒的塔尔文。人们常说,这一代贤者软弱又温吞,也许事实确实如此。
“罢了,塔尔文。”他说,“今天我们什么都没看到。”
——枫华庆典篇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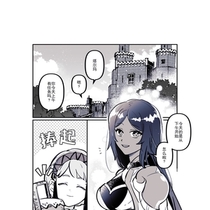






(一)
「我想。温德米尔你,应该还记得认识兔子先生。」
默利晃了晃手里的粉色兔子玩偶。
「......」
「兔子先生说,今天有奶酪哦!只要你睁开眼睛。」
「......」
「行了温德米尔,快起来,睡这么久,脑袋瘪掉了。」
「......」
嗯,好像醒不过来了。
那么,兔子先生,在这里陪着他吧。
默利走在街上时,天已经黑了。
「如果我变得很胖很胖,兔子先生还会喜欢我吗」
「兔子先生说,他喜欢肉乎乎的感觉。所以,多吃点吧」
「那如果很久很久之后,我忘记兔子先生了呢?」
「…….请不要忘记,兔子先生,想活下去」
想到了一些很久之前的事情。
会忘记吗……
(二)
风与月是两个遥远的精灵。
一个奔跑在地面,一个受禁于宇宙。
风是安抚稻草,摧毁房屋的存在。
而月只是月,挂在穹顶的公主。
山峦之外是山峦,云层之上是云层。
风一遍遍地仰望天空,脚步却丝毫不停。
追求着什么,又等待着什么。
风无从知晓。
他掀起一层层海浪,掀翻一座座塔楼。
(三)
默利来到了约里德的废弃宅邸。
残破的大门上挂着一面旗帜。
那是约里德家族的徽标,只不过被一个巨大的红叉压在身下。
或许是因为工程量巨大,或许是因为那些可怕的往事。
这间宅邸荒废数年却始终未被拆除。
如今这也只是一间大房子,一位落魄贵族的躯壳。
似乎仍有些声音在这里回响…..
「哥哥的房间就在你的左边」
「当然,温德米尔也可以搬过来和我一起睡」
默利抱起小温德米尔,轻轻丢在床上。
「谁是最重要的人?」
「哥哥!」
「要听谁的话?」
「哥哥!」
「在哥哥和爸爸妈妈姐姐里选一个呢?」
「哥哥!」
温德米尔对答如流,像个上了发条的机器。
默利十分满意地揉了揉小家伙的头发,替他盖好了被子。
就像每一个甜美童话的结尾。
默利轻轻吻在温德米尔的额头,被窝里一大一小两只手紧紧相扣,似乎可以阻挡风暴,阻挡洪水。
咔擦…….
默利推了推宅邸的墙。
像被白蚁啃坏的树干,墙壁直直倒了下去。
说起来,自己认识温德米尔多久了?
再过两个月就是第九年了。
时间过的真慢啊。
默利在宅邸漫步许久,知道月亮高悬,才动身离开。
很大,即便只剩下残骸,宅邸依旧占据了很多土地。
家族并未给自己留下什么。
哦,有两具尸体,挂在旗杆上六七个月。
那是出牢笼的日子,再次见到父母时,他们早已无法说话,支配魔法也不行。
毕竟被挂在风口里数个月,温德米尔根本认不出来。
(四)
风来到一座火山。
愤怒的神明一遍又一遍的惩戒着大地。
「我在拯救他们。」
神明头也不抬地说道。
「这是我的爱!这是我的爱…..」
「您怎么哭了。神明大人」
「那是热烈的结晶。」
熔岩被洒向高空,冷却成坚硬的岩石。
熔岩被灌入大地,沸腾成炽热的血水。
「您的信徒们都变成岩石了。」
「那是他们对我至死不渝的守护。」
「这真的是爱吗,神明大人,我看到的只有苦痛。」
火山停止了喷发。
整片大陆都安静下来。
她看了看脚下的世界,黑色的河流与灰烬森林,大地的脉流早已被熔岩斩断,凝固的人怀抱着寒冷的心。
「爱是改变,同化,爱是……」
火山嘶吼着,伸出浆红的触手,妄想抓住这个质疑她的精灵。
(五)
「默利。」
希德尔抱着一沓手稿走出书库,迎面撞上想要进去的默利。
「啊,希德尔,日安」
「……日安」
熟悉的面孔,却不熟悉的表情。
默利沉着脸,侧身进入书库。
还没走吗?
希德尔看了看窗外,欢笑声不绝于耳,又是一年枫华庆典,热闹的节日。
时间与记忆是死对头,禁魔仪式还是前天,现在就已经忘记这件事了吗。
明明是那样不明所以的愤怒。
麻木的人们。
「叩叩叩」
默利来到无尽书库的中央,敲响那个隐秘的门扉。
棕红的门在默利眼前出现。
轻扭把手,贤者的门便被推开。
「默利。」
「贤者大人。」
默利站在门口,脖子上缠着绷带,无神的双眼直视着屋子里的卡纳。
「进来吧。」
「…….」
卡纳站在书架前,拨弄着手里的西洋镜。
咔咔咔咔……
西洋镜转动的声音很像钟塔运行。
「要问点什么?」
卡纳头也不抬地说道。
「我现在……依然可以使用魔法……为什么。」
「你觉得西洋镜是怎么转动的?」
「…….发条轴轮?」
「那这样呢?」
卡纳转动手指,一根细长的轮轴从西洋镜里飞出,这是齿轮机械的心脏,温德米尔曾对这些小玩意儿很感兴趣。
西洋镜依然转动着,只不过少了齿轮咬合的声音。
「……」
「魔法师拥有操纵这些的力量,即便你不相信龙,他的力量也依然赐福予你。」
「为什么没有把我禁魔。我杀了莉莉娅!蛋糕刀划开了她的脖子!」
「………」
卡纳并未回答默利的疑问,继续摆弄着手里的小玩意儿。
「卡纳大人。」
「重要吗?默利。」
「……..」
「不信仰龙与钟塔的你,我所做的处置便毫无意义」
「我想获得一个答案。您毁掉了我的家,绞死了我的父母,拯救了我和温德米尔,给予我还算正常的生活,如今……」
「你和他很像。」
卡纳打断默利。
「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默利,我只是规则处理,你姐姐莉莉娅的死…..」
「…….」
「这个送给你。去吧,去找你认为可以获得答案的人。」
默利接住那个桃红色的西洋镜。
没有轴心依然可以旋转。
没有信仰依然可以吟唱。
(六)
风的旅途没有终点。
这是风在见到珍珠时的自我介绍。
「留在这里吧,欣赏我美丽的光。」
珍珠从蚌壳中跃下,伸出一双纤细洁白的手,轻捧住风的脸颊。
「那些人,都是你的客人吗?」
风指了指蚌壳后,一小座堆起来的白骨。
「他们呀!都是我的追随者!」
珍珠穿着洁白的裙子,在风面前轻轻转着圈。
「这是,凝聚成钻石的爱呀!」
风牵起珍珠的手,感受着那其中的温度。
冰冷、僵硬和机械。
「可是却他们都死去了,人类无法在海底生存,他们的身体早就被鱼吃光了。」
「可是爱不会!」
珍珠的眼中积满泪水。
「凝聚、守护与洞察!这是爱的真谛!」
珍珠声嘶力竭。
风松开少女的手,转身去向更遥远的地方。
(七)
「特里维亚老师,好久不见。」
「…..默利。刚从卡纳那里出来吗?」
特里维亚放下手里的小刀,抬头看了看这个挡住自己光的人。
「您在……分尸小松鼠吗?」
特里维亚握着一把银色小刀,桌子上躺着一只棕色皮毛的松鼠,松鼠的四肢被细麻绳固定牢靠。
「看看它们的……内部构造。」
松鼠的腹腔被划开,粉嫩的皮下组织与筋膜暴露在外。
「有什么事情吗?」
阳光被结结实实挡住,特里维亚所幸将刀与松鼠搁在一旁。
「它…..不痛吗?」
「用了幻睡魔法,不痛,再过一会儿他就会在睡梦中死去。」
「…….老师,死亡的时候会感觉到疼痛吗?」
「嗯?」
似乎是个很有趣的问题,特里维亚的嘴角勾起,隐没在黑暗里的眼中涌现出少许的光。
「如果是死亡的瞬间,会;但如果是死亡之后,收获的只有疲倦。」
莉莉娅…..一定很痛吧。
「谈谈吧,工具是什么。」
「一把蛋糕刀。」
「捅穿心脏?」
「划破了脖子。」
特里维亚拾起刀,将刀柄压在松鼠的颈脖上,不出一会儿,心脏便停止搏动。
「大脑一片空白,意识恢复时已经没了气息,惊恐慌乱,然后镇定下来……我说的没错吧。」
「…….」
默利轻轻点了点头。
「我想带走重伤的弟弟,她,发了疯,拿刀威胁我放手…….我不能让弟弟再流一滴血…….她朝我扑过来,我夺过刀……」
「哼哼。」
「我没有办法……就算我受伤也没事,但是温德米尔。」
特里维亚推开椅子来到默利面前,俯视着这个混乱的少年。
房间仿佛一个破洞的瓶子,任凭乌黑的海水涌入,直到沉底。
片刻后,黑暗占领了这里。
特里维亚捧着一柄白色的蜡烛,将它递给默利。
「还记得姐姐长什么样吗?」
「和我一样的黄色眼睛,棕褐色长发……」
「血泊里的姐姐也是那样吗?」
默利抬起头。
蜡烛微弱的光照在特里维亚的脸上,缠着绷带的脸颊与枯瘦的皮肤,白色的眼球嵌在没有一丝肌肉的眼眶里。
「记住她的样子。」
「……..」
「这是你所能做的,为数不多的补偿与救赎。」
「即使你的目的是拯救他人,即使你可以顶着正义女神的胸章。」
(八)
风重新回到了自己诞生的村庄。
印象里,故乡的夏季总有一场流星雨。
记忆开始的地方藏着水晶。
风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但村庄已然被海水淹没,大片的房屋只剩下几个露出海面的屋顶。
「你好,归乡的旅客。」
「是你淹没了我的故乡吗?」
「是我,我叫塞壬。」
「可以把村庄还给我吗?」
「可以。」
塞壬弹奏竖琴,美妙的歌喉伴着音乐。
海水在她的指挥下向日出的方向退去。
「那么,你要这些断壁残垣有什么用呢。在我到来的时候,你选择了离去,他们没了你的守护,都失去了生命。」
「我想看流星雨。我想坐在那个屋顶上。」
风指了指远处。
「流星雨早已消失。」
「你离去的太久了,群星被打乱重新拼凑,如今这里只剩下永悬的月亮。」
风顺着塞壬的目光抬头望去。
那是个金色长发的少女,精致的笑容犹如一颗皓石。
「带着这些重新上路吧。」
塞壬将三个瓶子塞进风的手中。
分别是,思念、陪伴与守望。
(九)
默利从钟塔走出,卡纳与特里维亚的话久久驻足在脑子里。
头好沉。
现在该去哪。
默利望向一个熟悉的方向,但自己手中没有万花筒。
「默利。」
是阿尔伯特。
「阿尔伯特,你好。」
默利将手背在身后使劲拧了拧,朝阿尔伯特挤出一个微笑。
「有什么事情吗?」
「这个,还给你。」
阿尔伯特递过来一个盒子。
「这是?」
默利揭开盖子。
「………」
粉色的雨衣,被叠理整齐,印有温德米尔涂鸦的那一面正巧于最上方。
「希德尔很感谢您的雨衣,虽然他并没有用到。」
「……..」
「祝您好运。」
默利抓着阿尔伯特的盒子,手背青筋凸起,盒子被捏得变形碎烂。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颤动。
心跳声盖过了所有声响,心脏每一次搏动都牵动着全身上下每一块肌肉。
默利靠在一旁的树上。
窒息感,阵痛感,分配给每一个器官。
从未有过的感觉…….
种子要发芽了吗……
冬季精灵。
「温德米尔是我的底线。我会保护好他。」
「只能听我的话,这样温德米尔才不会受伤。」
「在家里要照顾好姐姐哦!姐姐生病了。」
「回家时,先拥抱。」
根茎撕破种皮,贪婪吸收着周围的养料。
像倒刺一样,在默利的心脏上扎根。
抽起的茎叶抵着心房的顶,似乎要将这里撑破。
默利从未遇想过种子发芽的情景。
就像孩子们把头放进被窝,夜晚的怪物便会离开一样。
靠着这个方法,默利躲避了一直以来的所有。
(十)
风终于找到了旅途的终点。
要到顶上去,去找月亮。
这是他对收藏家说的话。
「如果您下定决心,这趟旅途便不在话下。」
收藏家仔细擦拭着每一个展柜。
「这些,都是你的收藏品吗?」
「他们是我的爱人。」
风贴着透明展柜朝里看去,犹如小人国一般的景象。
「他们从出生就在里面了吗?」
「不,是我邀请他们进去的。」
收藏家晃了晃手里的笼子。
「可是,他们不会愿意的,他们没有自由。」
「自由?可笑,奢侈,愚昧。」
「........」
「只要我对藏品足够专注,他们对我足够畏惧,这就是至死不渝的爱。」
风在收藏家的目光下退向角落,轻轻搬下那里的拉杆。
「你!住手!」
收藏家拿去铁笼与镣铐,向风冲来。
但风只是风,收藏家撞在墙壁上,昏了过去。
「走吧!你们自由了。」
风对着那些小人欢呼道。
「别让他再抓住你们了!」
「嗯?你们怎么不逃跑.....」
「你们.......」
小人国的居民们看着这个庞然大物,短暂的震惊后重新投入自己的生活。
(十一)
温德米尔全身上下缠满绷带,好像神话故事里的木乃伊。
默利瘫在床脚,手里举着名为「兔子先生」的玩偶。
温德米尔什么时候可以醒来?
默利捏了捏兔子先生。
兔子脑袋软趴趴地倾倒在一旁。
兔子先生也不知道。
真没用啊,明明是温德米尔除我之外唯一的伙伴了。
「还记得风精灵的故事吗?」
默利从床脚的缝隙里掏出一本童话。
「他从收藏家的城堡逃出来后.....」
「好吧,这个故事我也不太喜欢。」
默利将童话丢进垃圾桶。
「第二十七天了,温德米尔依然在沉睡之中。」
「这时,王子已经来到她的身边。」
「传说,真爱之吻可以唤醒被睡眠纺锤刺伤的公主。」
「那么......」
默利轻轻闭上眼睛,俯下身去。
迎接双唇的确是一层有一层冰冷的绷带。
公主没有苏醒。
(十二)
风精灵死在沙漠中。
一片可以将所有事物转化为沙砾的地方。
火山、珍珠、塞壬与收藏家成就了风所有的回忆。
月亮在哪里呢?
风在濒死之际仰望夜空。
「你好啊,风。」
「月。」
少女身上满是锁链与镣铐,行走时铃铃作响,像一只玻璃风铃。
「你终于找到我了,王子。」
月把风的脑袋轻轻放在自己的双腿上。「终于记起来了吗?」
「嗯.......」
「这里就是我们相遇的地方啊。」
大片的星辰跟随着月离去,犹如新娘和她的裙摆。
风再也不用仰望天空,再也不用麻木的旅行。
所有赋予给月的,都是他所谓的爱。
风精灵最渴望、最畏惧的东西。
----------默利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