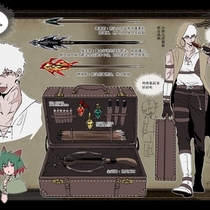当海浪再次撞上这艘小帆船时,希波利斯第六次吐了出来,把胃里最后一丁点蘑菇粥放归大海。逸闻学者瘫靠在船舷,用毯子和斗篷把自己严严实实裹好,只露出一双颤抖的手,将糟糕的旅途写进书卷。
“大概还有多远。”希波利斯脸色惨白如新雪,气若游丝地问道。那位执着帆脚索的灰白色巨塔没有立刻回答他。索利多金币般的双眸凝视着前方,右手收放自如,控制着帆船的速度与航向,让这简陋的小船行驶在惊涛骇浪。
“快了。”巨塔的回答简洁而迅速,其惜字如金让希波利斯联想到那位红袍的审判长。换成是以往,希波利斯便会追问起他是如何在学会对抗冰海,追踪猎物,判断航向。但现在,逸闻学者的体力只够他问出关键的问题了。
“老猎人——或是拉尔夫先生。我好奇你作为怪物猎手的传说,但我更好奇,”一阵小小的颠簸让希波利斯停顿了一小会儿,“是怎样的变故让一位传奇隐退在渔村之中?”
老猎人没有回头看他,金色的眼睛穿透波涛与浓雾,搜寻着目标。
“我没有隐退。”他的声音低沉且沧桑,宛如一张陈旧的琴,“只是将探寻谜团选作新的方向。”
“呃,我觉得像你这样狩猎大师,一定知道古怪的漩涡是卡律布狄斯所为,何必还跑一趟。”希波利斯诚实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回答他的却只有狂风呼啸。
“经验主义只会留下遗憾。”良久,老猎人才给出自己的回应。“但如果真的海怪卡律布狄斯捣鬼,你不是在重操旧.......呕!”
帆船不闪不避,迎面撞上一堵浪潮。冰冷的海水把希波利斯浇了个透,学者两只手扒拉在船舷,第七次吐了出来。
“所以说,呕。是什么让您选择了新的道途呢。”他怀抱着那本被裹在防水鹿皮袋里的硬壳书,牙齿打颤地问道。
“无知与谜团才是真正的恶兽。”老猎人缓缓开了口,“就像你无论枭去多少只海德拉的假头它都能存活,唯有发现真正的脑袋才能将其一击毙命。”
“所以你仍是猎人,只不过狩猎的对象换做了真相与疑云。”希波利斯打着哆嗦,飞速写下他的话语,“但这是一条更艰难的路。你面临的对手无血无肉,遁于虚无的迷障。”
“藏匿得再好的野兽也会留下行踪,隐瞒得再深的真相也会埋下痕迹。”老猎人的声音低沉而笃定,“我也有疑惑需要问你,诗人。”
“逸闻学者,或者简称学者。”希波利纠正道。
“我曾读过你的故事,戏剧与小说。你擅长撰写不着边际的史诗,离奇夸张的情节,动人煽情的悲歌。”
希波利斯试图争辩,但一波新的浪涌让他收了声。
“你为何选择了新的道途,将编篡真实确凿的书册当作新的目标?”
风浪渐渐缓和。罗西亚的希波利斯攥紧了那本《科利恩万物全书》,没入长久的沉默。
老猎人没有追问。他收起帆,将船锚扔入水中,又挽起袖子,摘下手套放进腰侧的小包。
“天要放晴了?”希波利斯勉强打破尴尬。
拉尔夫并未立刻回答他,只是将握起那柄最沉的铁矛,把之用另一卷麻绳牢牢捆上,掂了掂手。
希波利斯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平静的海面上,一个漩涡正在汇聚。涡流之间,两对发光的眼睛透过海面,散出幽光。
“别掉进水里。”老猎人沉声说道,猛地将投矛朝那阴冷的眼眸掷去。
漩涡激荡了海流,铁矛刺穿了寒风,海面为卡律布狄斯的鲜血染红。异怪发出愤怒的长啸,裹携着洋流,试图将船只吞没。老猎人的左手握紧了麻绳,将之作为驯兽的缰,右手则掷出第二支矛。
海兽发出愤怒的咆哮,激流汹涌地搅动船只,将其拽向波涛的中央。拉尔夫的双手一寸寸地拽扯着麻绳逼近猩红的漩涡之眼。卡律布狄斯的背鳍与长尾已然清晰可见,其掀起的湍流几乎要挣断束缚,扯碎帆船。
在船只崩毁或海兽力竭之前,老猎人松开了手。从压制中挣脱的卡律布狄斯飞速沉入水中,麻绳飞速地窜入海面。但就在其几乎要随之消失的前一会儿,拉尔夫的右脚猛地踩上绳尾,再一次拽住对方。
愤怒被挑衅点燃,仇恨在酝酿,两对发光的眼眸幽幽地出现在前方。背鳍扯开平静的海面,修长巨硕的身躯猛然从水中跃起,带蹼的前爪挥舞着,纺锤型的头颅裂成三瓣,以层叠的尖牙袭向船首持握着狼首巨锤的白狼。
在被口齿吞没前,他的双臂骤然化作巨狼的利爪。狼首巨锤化作卷册中记载的流星,凿上刺入海兽侧颅的铁矛。
骨骼碎裂的声音宛如丧钟,铁矛钉进怪物的大脑。沉重的一击将其猛地掀到一侧,砸起水花与海浪。海兽的尸体沉下去了数秒,接着缓缓浮起,涌出的血弥开一大片猩红。平稳的风浪中,老猎人重新戴上手套,弯下腰拾起那串麻绳,系于船尾,又将船锚从水中拽起放好。
“返程了。”他升起风帆,平静地对我说道。
小屋外,热烈的篝火同舞蹈与歌唱交织在一起,驱走黑暗。小屋内,希波利斯坐在火堆旁,裹着毯子,将《科利恩万物全书》摊开在桌上。
“咚咚!”门被重重锤了两下,在逸闻学者喊出“请进”前,来者便推开了门扉。老猎人站在屋外,将一串腌鱼精准地抛进希波利斯怀里。
“渔民的感谢。”拉尔夫说道,指了指自己行囊上挂着的一长溜腌鱼。
“这么快要启程了?”希波利斯痛苦地将腌鱼们推到一旁,捧着书用力扇了扇味道。
对方沉默地颔首。
“祝你好运,拉尔夫先生。”希波利斯在毯子里朝他挥挥手以作告别。
“愿你写书的旅途一路坦荡,学者。”
老猎人掩上屋门,脚步声渐渐融进夜色里。希波利斯拿出羽毛笔,蘸了蘸墨水,将今天的见闻抄于书上。
他的故事已然谢幕。他的道途开启了新章。
经过商议,临时组成的队伍选择探索市集——出发前她们设想,这种人员汇聚的地方或许能听见或者刻意打听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她们一起走进安宁祥和的午后集市,路过木偶戏剧场,商定分开探索后在此汇合。
瑟拉芬娜注意到许多小孩环绕在糖果铺周围,想着童言无忌,或许孩子们的交谈中会透出什么特别的消息,便向那个方向走去。
但环视聚集的孩童时,一种怪异感先于一切理性判断短暂攫住了她的心神。再细细看去,这里孩童微笑的模样及其相似:明明呈现在一张张不同的小脸上,却比一群绘画学习者对着同一个模特画出的速写还要雷同。
这个场面潜藏着难以言说的怪异,这里的孩子应该出了问题。瑟拉芬娜相信自己的观察力和直觉,不过比起单纯地观察推断,她更喜欢发散思维做出一些小小的尝试——以甩开内心滋长的不安并支撑自己的结论。
于是她捡起一块圆润的小石子包上糖纸,递给其中一个小孩。
“谢谢您!”孩子礼貌地道谢,像完全没看见她之前的操作一样撕开包装将石子含在嘴里,向她点头致意。那张小脸上仍然挂着纹丝不动、越看越显僵硬的微笑。
石子似乎在他的嘴里被来回吮吸,碰上牙齿发出轻微响声。但在瑟拉芬娜观察的一段时间里,孩子并没有用牙齿咬那块“糖”。
如果他咬了,会有牙齿崩裂的场面吗?会打破他诡异的笑容吗?问题的答案暂时不得而知了。
有点可惜,但也还好——至少目前她的举动没有让什么潜藏的危险浮出水面。
而那个孩子没把石子吐出来也足以佐证,先前的怪异感绝非她脱离人类生活太久产生的错觉。
她本想再问一些与剧院相关的问题试探他们,但突然觉得没有必要了——无论是稍纵即逝的一丝危险预感,还是理论上这些孩子对剧院的事知情的低可能性,都让她认为不必多此一举。
于是她转身离开糖果店。
市集中的人们依然乱中有序地生活着,例如右侧前方一个摊主正热情叫卖:“这位先生,给您身边的女伴买一枝花吧!”
花?瑟拉芬娜下意识抬手摸摸耳钉,向声音的来源看去。
那是一个用布料假花装饰的小摊,摆着插在瓶中的花和精致包装的花束。
但这些花的状态似乎不佳,瑟拉芬娜走近,重重地皱起眉——无精打采地垂头,花瓣皱缩、颜色变深,一派残损凋零的景象。
对曾经打理花园和处理房间插花的她而言,这简直难以容忍。
但花摊的顾客似乎浑然不觉,被推销的男士经过一番挑选买下垂头玫瑰,女伴又欣喜地从他手中接过,小心翼翼地别在耳边。
或许整个集市的人都有问题。
瑟拉芬娜被不知从何而来的一阵不悦感包围,她干脆使用血魔法做了一点伪装,使其中一朵花看上去重焕生机。而挑选花朵的顾客对此视若无睹,无人选中那朵看上去娇艳盛放的鲜花。
一群行尸走肉。
烦躁的情绪在心里滋长,她并不喜欢应对这种山雨欲来的压抑,甚至宁愿爆发点什么冲突,但又忌惮未知且顾及之后的任务,不得不忍。
带着这样的心绪,她无心再逛集市,走回木偶戏的摊前打算与队友汇合。
在此驻留的片刻,她又注意到木偶戏观众的欢呼声过于整齐划一,比她做人类时家中老旧摆钟的节奏还要精确。
“好!”十几轮整齐划一的喝彩过后,她终于忍不住做点什么破坏他们的节奏,例如比众人慢半拍地结束喝彩。
依旧无人受到她的干扰,观众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像玻璃罩中上好发条自顾自旋转的八音盒,不受外界影响地运转着。
市集除了这种诡异感觉和随之而来的各种碎片化猜想之外收集不到更多信息,等队员齐了,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