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间百器,皆具魂灵。
灵则缘起,来莫可抑。
悲乐喜怒,爱怨别离。
万相诸法,梦幻泡影。
==============================
渴望,思念,孤独,怨恨……这绝不是人类仅有的感情
抱有欲念被主人抛弃的器物,在春秋时分,化为付丧神。
而暗怀心愿的人类,也在寻求着某种际遇与改变。
人与器物的命运与缘分,无论善恶,在踏入这扇门时开始。
欢迎来到徒然堂,
今天的你,也在期待着什么?
企划完结
填坑小组:http://elfartworld.com/groups/1381/?p=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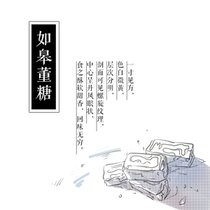



开心的投喂了逐魂猫头鹰。并且借豆花人头一用!(????
也不是很懂为什么写食物写了一晚上,失智。
进度越发慢了,两个企划都是坑仿佛要将我撕裂.jpg
________________
姑苏城隍庙街巷口栽了棵酸枣树。
说它是酸枣,那滋味自然是算不得美妙的,路过鸟雀且不惜得啄食,倒叫果子生得肉饱皮嫩,得着个好品相。只味儿实是酸涩,除街上的郎中捧得个竹扁筐,拿个长竹竿子敲下一筐来,说是晒磨了添一味药,旁的人再不爱沾这个。
要说左右巷子的住客,那一个总角垂髫时,没馋过这街口的酸枣,便是父母长辈们特特与说了要酸倒牙,可不亲尝一回,那里就能甘心,待一回尝了真个酸得倒牙,便安歇几日,再过几日瞧着那红彤彤的枣儿,竟又馋起来,连着过得两三回,那股子新鲜劲过去,便再不打这枣儿的主意了。
连那害了喜的妇人都不喜爱,嫌这枣儿酸是酸,却涩口,不若去寻街上叫卖的鲜酸枣,小片荷花叶子包了,系鲜亮红绳,讲究些的人家,还往叶片里头加一指头香,这样的枣儿,十文钱能得一包,秋分日前,那灵枣牙枣青州枣,一街净是卖枣儿的,那一家卖的枣儿不是又大又香甜,俱是好滋味。
偶有路人不明个中缘由,见这树生得好,果儿也鲜亮,眼瞧着,喉咙管子先动一动,咽了一管子唾沫,到了时节,也不需竹竿儿来敲,无人打吃的枣儿就落在地上,满地皆红。路人就在树下拾一两颗又圆又红的枣儿,朝褂子上一抹,忙不急往口里头塞,甫一入口,脸已叫酸得皱起来,一口过后再不敢吃了,那红彤彤的果子还扔还在地上。
在这酸枣树下,不知何时起摆起了一家吃食铺子,店主人是个机敏利落的性子,账算得极快,招呼谁都能透着一股子亲切来。他浑家生得一双小眼睛,穿一身粗布衣裙,谈不上美貌,只皮子白,拾缀得干净,便叫人看得顺眼了。
这二人无子无女,倒也看得很开,总说子女皆是缘分,菩萨跟前头的缘分不到,那里又能强求,便一心做这门小生意,也不拘一种来卖,春日里便卖寒食的乳酪乳饼,片了鲜捞上来的大鱼,卖熬煮浓稠的鱼片羹,初夏时分鲜樱桃上撒了碎冰再撒酪,再热些便做冰雪凉水,备上好些不同味儿的,路过的那一个都乐意摸几个大钱出来,就这么站着吃过一碗才走。
待时节一过,冰雪凉水便也不卖了,倒还有人专程问过一嘴,咂么咂么,还有些可惜。这摊儿就置在酸枣树下,扎个小亭,置几张桌椅,谁人都可以坐下歇上一歇。夫妇俩总做最合时宜的生意,酸枣树上的果子本无人要的,这年倒被动上了脑筋,这几日枝头上还飞来一只夜猫子,棕灰的毛色,明黄厉目,人都说不吉,道那是夜里喊魂的逐魂鸟,那摊主人却浑不在意,拿杆子敲枣儿,却不赶鸟,只随它站在枝头拢着翅膀歪脑袋瞧着。“它能瞧得懂哩。”店主人与他浑家玩笑。
树上敲下枣儿来拿酒浸了,给食客们一人端上一小碗,权当做个添头,不知拿什么方子制的,这酸枣竟真叫他去了涩,又酸又甜还带着酒劲儿,招了不少食客喜欢。
可要说这枣儿,且还称不上是秋日里的主角,便在这嚼吃一只酸枣的功夫,最大的角儿掀了头帘上桌了。不是旁个,正是宋人爱的那味蟹生,取自家河湖里头捞得的小蟹,斩了螯脚,去了泥沙秽物剁成小块,佐以盐、醋、葱、姜、并胡椒、花椒粉、茴香、草果等数十味料,事先熬了香麻油,将鲜香的料儿朝蟹上一浇,便能上桌。
因整治这蟹生用时极短,前后不过给客人留了个洗手的功夫,便也作洗手蟹,市井中人再没有不爱的。
赵衔这日也在摊前坐了,自然也点了这道洗手蟹。他点了蟹,自个儿却不吃,边上还坐了个白衣裳墨色裙摆的姑娘,清凌凌面上一双水润桃花眼,抬眼瞧人便是一片波光,这姑娘拿了箸挑碗碟里的蟹螯,满面的好奇,搁下箸用手拈起来,放进菱口里细细地吮。
她吮一口汁儿,还要抬眼瞧一回赵衔,眼里透着依赖,半点不遮掩。赵衔却不看她,他在这里等人,掀了袍角在凳上坐了,说是等人,却看似随性写意得很,半点不着急。那树上的夜猫子咕咕叫两声,把脑袋横过来瞧他,喙子上下一碰,竟从枝头飞落下来,在一片惊呼中神气地落在赵衔跟头前,一双利爪掐进木桌里。
这夜猫子落在桌上,踱着步子昂首挺胸只不怕生,还探头去瞧面前两只碗碟,叼了个枣儿一囫囵吞了,又去看那洗手蟹,赵衔也不惧它,倒像是个老熟识,挑了个蟹身与它吃。
这湖河里头的小蟹,寻常贵人家是再不吃的。因嫌肉少壳多,远不比大蟹肥美。贵人们吃蟹,将蟹腿独挑了下锅子,又剥了蟹壳,取蟹黄蟹膏来制酱,蟹肉自有下人们细细挑了,千般做法,连吃三日再没有重样,这街头小蟹且入不得眼。
可秋分日前,再是肥美的大蟹也还未长成那肥美的模样,便只有这小蟹,就着佐料,连壳带肉一并放进嘴里,还很可以嚼吃一番。这鸟儿毫不客气地吞了,哗啦啦拍拍翅膀,做出个满意的模样来。
有这样美味,这夫妇摊子的生意自然就极好。往来食客许多,还有三两闲汉甩出些整钱,叫个楞头楞脑的小子去酒楼打得二两酒,并请了个茶博士,拿那酸枣与蟹下酒,砸了钱的人就极得意,朝周围一众食客咧着嘴怪模怪样的作揖,道是请乡亲们一并听个热闹,再一扭头,命那茶博士速速讲来。
这茶博士不看茶,倒与人斟酒,口里说些南北轶事趣闻,说得有模有样,一会子说京里侯伯公一掷千金搏美人一笑,一会子又道江洋大盗横出世,烧杀抢掠真奸邪,还笑了一回那山野匪首浅滩身死,一窝贼子无首,道大快人心,便是今年虎丘山曲会,说不得都比往年安稳热闹些。
那夜猫子原还在碗里叼蟹吃,听得这席话,抬起脑袋来,嘴里咔咔响动一番,也无人知它说了个甚,赵衔身边的姑娘极好奇的瞧它,伸手要去抓,叫这鸟儿避过了,似是不喜她的样子,倒是朝赵衔除蹦了两步,翅膀一扇,索性立在他肩上。
要扣着人的肩,也不管一双铁钩似的爪抓花了那身锦袍。便是这样,赵衔也只不生气,还露着笑,真像是个温吞的好脾气了。那姑娘鼓起脸来,她周身氤氲淡淡水汽,柔荑摸过木桌,留下一道水痕,那茶博士正讲到兴头上,倒是无人注意她这些许异样。
人群正中,叫从茶楼请了来的茶博士一双嘴皮子耍得天花乱坠,不时便有人叫一声好,掷下一两个赏钱,得了钱,越发笑容可掬起来,很愿意卖力再讲一些。茶博士一双钩子眼早早盯准了这摊上坐着的公子与那貌美的姑娘,知道这些富家子弟出手自来没个把门,没得小斯丫鬟打理,千金万银也能撒出去,可不是这行当最喜见着的客主,哄得一两个,半月都能有酒有肉。
存着这心思,将嘴咂过一回,便又道:“却还有一桩古怪事,单小人在此碎嘴鼓噪一回,列位听过便罢了,可做不得准。”
晓得这样说,才更叫人在意,做了个犹豫模样,待听客催一两回,便肯讲了,“列位也知,那匪首白窦华,叫从自己窝里赶了去,落下山崖粉身碎骨。我们官爷带了十来人去寻尸首,愣是没得着,那样高的山崖,人亲眼瞧着那恶人摔下去,怕是砸得糜烂,尸骨不存了。正应了那个理儿,所谓天理昭昭报应不爽,合该他遭此一劫。”
此话一出,便有听客在人群中起哄,拿话头嘘他,道:“这些个事情,谁人不晓得,早传遍了的,三岁小儿也说得一两嘴,我今再添几个钱,可要你把知道的都倒出来!”说着,真个掏出几个钱来,在手里头摇得叮当作响。
那茶博士神秘地笑,嘴上把着火候顿一顿,才又接着道,“原也是这样说,可小人得着一条信儿,倒觉出些不对味儿来……”
他压低了嗓子,拖着音吊众人的胃口,竟真个听起来阴恻恻,叫不少人搓起膀子来:
“说有那么一富户张家,夜半起了一丝红光,有那胆子大的邻家捅了窗户纸偷拿眼去看,嚯,你们猜怎么,道是那红光正是个人影儿,满头满脸的血,凶神恶煞,怕不是那白窦华凶煞气儿不去,托成厉鬼,专挑有仇怨之人来锁魂来了!好一恶霸,想是不平了这口怨气,再超脱不得呢——”
他话音未落,却听一人嗤笑一声,朗声驳他道:
“这话好没道理,恁他一个山贼,本就该遭千刀万剐的腌臜东西,便是再做百年善事,也未必超脱得,说这白窦华心口有怨气,怎地也不问问,那自他手里糟了祸的善男信女,可也要吐一吐自个儿那口怨气呢?”
只见一中等身量,着细布衫,扎四方巾,眉目端正的男子越众而出,驳了那茶博士一席话,人却只淡淡扫他一眼,便不再多看,自顾自转向坐在一边的赵衔,端正的面上露出个带些儒生气的笑容来,拱手与他见礼。
“洞庭一游后两年未见,真个是巧,竟在此处碰着了。”一开口,那儒生似的笑中的儒气减了些,又透出一股子商人的精明来,只听他道,“市井闲话不听也罢,叔明兄别来无恙,今日可还有事,若得空,不若过府一叙,你我久不见,也好仔细说道说道……你看如何呀。”
赵衔笑而不语,他站起身子,先是自兜里摸出半吊钱,添在那茶博士盆子里头,这才掸掸袍角,朝那扎方巾的男子见了一礼,道:
“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他身后,那棕灰的夜猫子定睛瞧着两人,从喉咙眼里发出一声低鸣,而本在赵衔身侧的美貌女子,却不知何时隐了踪迹。
那鸟儿拿脚爪踩了踩女子位子上浅浅一滩水渍,旋而耸起身上细细的绒羽,极厌恶似的甩动脚爪,扇动翅膀腾空飞起,在这蟹摊子上方盘旋一圈,又鸣一声,终于调头飞远去了。
